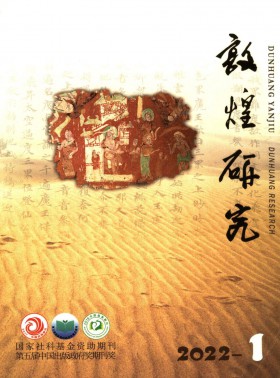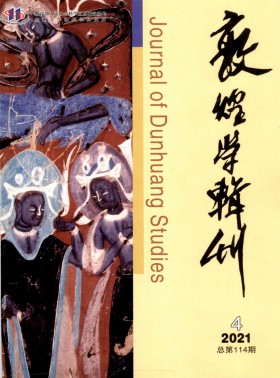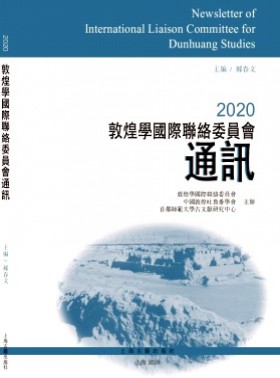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敦煌丧葬仪式和丧俗文的关系研究,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敦煌丧俗文及其应用状况考述
周绍良先生最早将敦煌文学分为三十类,并首次列出“祭文”一类。之后谭蝉雪先生对敦煌祭文的“来源”、“用途”、“名称”、“祭祀地点”、“祭祀对象”、“宗教性质”、“体裁”等各方面情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考察,认为敦煌祭文当包括亡文、忌日文、亡斋追福文、临圹文、行香文、祭畜文、祭鬼神、山川文等。黄征、吴伟在其所编的《敦煌愿文集》中,则将亡文、临圹文等全部纳入“愿文”的范围之中;郝春文先生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祭文应当独立为一类,亡文、临圹文、亡斋文、行香文等属于斋文,而不应该包括在“愿文”范围之内。本文所指的“丧俗文”则相对宽泛一些,包括祭文、亡文、临圹文、亡斋文、行香文等与祭祀礼仪相关的文献。从数量上看,敦煌丧俗文总数在150卷左右,其中祭文的比重较大,其次还有大量的亡文、临圹文、行香文、追念文等。下面分类说明并讨论其与各类丧葬仪式的关系,特别是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
(一)一般祭文
在敦煌遗书中有不少祭文,其范围相对比较宽泛。除了一般的祭亡文之外,还有祭祀社稷神、风伯、雨师等自然神之文,以及祭祀马、牛、犬、驴等生产和生活中重要动物的祭畜文等。敦煌祭文在继承前代和中原地区祭文的基础上,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形成了一套基本的写作模式,如敦煌写卷S.381《十一娘祭婆婆文》:惟岁次丁亥五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孙女十二娘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婆婆之灵,伏惟灵天然德厚,自性矜怜,每蒙训育,与子无异。久染时疾,医药不诠(痊)。和祸来迍,我兮无依,肝肠分裂,戾(泪)也涓涓,愿灵不昧,请就歆隆,伏惟尚飨![10]P222-223观其内容,上引祭文显然是一篇祭祖母文。祖母新逝,孙女儿万分伤感:“我兮无依,肝肠分裂”,用朴实的语言写出了晚辈的悲伤与孤立之感,很有代表性。上引祭文虽然比较简短,但形式尚称完整,从中可见敦煌祭文的基本模式:即开头点明祭祀的时间、祭祀者和逝者的关系以及祭祀所用的物品等,文末则常常以“伏惟尚飨”的祈求语结尾,其现场感和实用性特征非常明显。除此以外,敦煌写本祭文中也有少数篇幅较长,辞藻较为华丽,内容较为丰富的作品,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敦煌地区祭文写作的不同面貌,P.3214《祭寺主文》堪为其例:维岁次己巳八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当寺徒众法藏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安寺主阇梨之灵。惟灵天生慈善,轨范立身,温柔有德,泛爱仁人。投真舍俗,禁护六门。在寺无分毫之阙,茸理实越人伦。为僧清格,并无氛氲,释中硕德,众内超群,营私建塔,触(处)事匀均。将谓永沾不替,同佛教而(如)长春。何兮妖祸降坠善界,愿亲思之闷绝,合寺咸喷。今生一弃,弥勒会因。路边司箪,请来饮真。伏惟尚飨!从内容上看,这是一篇僧人祭奠寺院长老的祭文,与上举祭文相比,增加了部分赞述逝者功德的内容,且遣词造句更为典雅一些。虽然是寺院的祭文,但仍然采用了世俗祭文的格式,说明儒家文化影响很深。此外,如S.5744署名“徐彦伯”的《祭文》,也是一篇文笔典雅,辞采华美的祭文。总体上看,多数敦煌写卷中的祭文都注重实用性,体现了民间文学朴素、真挚的特征,只有少数出自文人笔下的作品才带有华美倾向,并在文中使用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和佛教典故。那么,上述祭文主要是在丧葬活动中的何种仪式上使用的呢?对此我们可以从其内容和感情倾向上予以考察:1.从内容上看,祭文和下文的临圹文、亡斋文、脱服文的区别在于,祭文主要是表达生者对逝者的哀悼、对生者事迹的追述等,而后面几种则还包括了为亡人追福、为生者祈福等相关部分;2.从感情倾向上讲,祭文抒发的感情往往比临圹文、亡斋文、脱服文等更为悲痛,哀伤,所以它应该是在亲人去世不久的丧葬活动中所使用。因此,祭文应该是逝者亲属在入殓之后的祭奠仪式上所使用的哀悼文。
(二)临圹文
敦煌写卷P.2622号写本书仪记载:“柩车到墓,亦设墓屋,铺毡席上,安柩北首。孝子居柩东北首而哭,临扩设祭。”可见,敦煌“临圹文”是在灵柩运到墓地以后,在“下葬”仪式上所使用的。由于儒家和佛教丧葬仪式的不同及其相互影响,所以敦煌地区的下葬仪式也往往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临圹设祭,祭奠并宣读祭文;后半段则为佛教仪式,延请僧人念诵佛事斋文。因此临圹文也分成普通临圹祭文和僧人所用临圹文。前者往往篇幅比较短小,内容比较简单,如敦煌写卷P.2622、P.3886《临圹祭文》就有具有代表性:“不能自没,奄及临圹,幽明道殊,慈颜日远,以今日吉辰,迁仪宅兆,欲就去官,不胜号绝!”可见其内容主要表达孝子对逝者的告别,以及孝子的悲痛哀悼之情。作为佛事斋文的临圹文则迥然有别,因为是僧人所用,所以文中便不免带有宗教色彩,这对临圹文的结构与内容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S.6417《临扩文》云:无余涅槃,金棺永寂;有为生死,火宅恒然。但世界无常,历二时而运转;光阴迁易,驰四相以奔流。电光飞而暂耀,等风烛以俄消。然今亡灵寿尽今生,形随物化;舍兹白日,奄就黄泉;体逐时迁,魂随幽壤……破无明之固,卷生死之昏云;入智慧门,向菩提[路]。又将功德,次用庄严持炉至孝、内外姻亲等:惟愿三宝重护,众善资持;灾障不侵,功得圆满。摩何般若,利乐无边;大众皮诚,一切普诵。这类临圹文跟敦煌其他斋文结构有相似之处。敦煌临圹文的结构“可分五个部分:号头、明斋、叹德、斋意、庄严。敦煌祭悼文中有十数篇临圹文,这些临圹文在内容、结构上大体一致”。在内容方面,文中在表达对死者的哀悼之同时,也包含了不少的佛教佛理和用语。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儒释结合的祭文形式,富有宗教色彩。这类祭文与斋文的结合,正是敦煌祭亡文的特点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敦煌临圹文不但受到了儒佛文化的共同影响,而且也与临圹设祭的仪式有关。
(三)亡斋文
亡斋文,也称“追福文”或“延福文”。根据前文对于敦煌丧葬仪式的考述,死者家属在埋葬活动完毕后,要把亡灵请回宅中,设置“真堂”并在不同时间进行祭奠,“亡斋文”就是逝者家属在不同祭祀周期祭奠亡灵的仪式上所诵读之文。这些祭祀仪式活动包括七七祭、百日祭、小祥祭、大祥祭等,所以敦煌遗书中留下的这类亡斋文为数不少,是敦煌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祭祀的周期不同,以及祭祀仪式和抄写习惯等原因,敦煌遗书中的亡斋文在格式上存在着一定差别。有的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如写卷S.343《亡兄弟文》内容完整,由“号头”、“明斋”、“叹德”、“斋意”、“道场”、“庄严”等六个部分组成。此文明言“故于此晨(辰),设斋追福”,在表达对亡人的悼念的同时,也表达了为其祈福之意。S.6417《亡考文》云:演庆昌源,延晖秀岳;风标邃远,器宇清高。奉公输战胜之能,不失田单之操。处众多德,学及西河。于家□(竭)孝弟(悌)之名,寔有感笋之业。将谓久留仁(人)世,永覆宗枝;何图云云。但以业风动性,水有逝流;影电驱驰,于临某七云云。珍羞霞错,罗百味而参差;玉馔星繁,旬(间)此珍而新春。还疑香积之国,犹如欢喜之园云云[8]。文中的“云云“二字,表示有所省略。保留的部分主要表达了对逝者的赞颂,对斋祭用意之说明等内容。由于斋祭活动常常请僧人或道士主持,所以所用些斋文体现了部分佛教或道教的思想,犹如上述临圹文一样,敦煌亡斋文也是祭文与斋文的结合体,体现了祭祀仪式对丧俗文结构与内容等方面的影响。
(四)脱服文
对于“脱服”的本义,武汉强曾概括指出:“脱服,义同脱孝、脱素,指服丧期满,脱去孝服。”按照儒家的礼制,孝子在服丧期间要穿孝服,期满以后则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脱去孝服并恢复正常的生活,脱服文即是在这类仪式上所使用的应用文。敦煌写卷中保存了一定数量的的脱服文,比较典型的文本有S.343《愿文范本等》:斯乃生恩至重,掬(鞠)育情深,尽礼苫卢,屈身草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泣血终身,莫能报得。慈颜一去,再睹无期,堂宇寂寮,昊天罔极。但以礼章有[限],俗典难违,服制有终,除凶就吉。然今丝(缌)麻有异,生死道殊,灵凡既除,设斋追福[8]。
由上述引文可知,《脱服文》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逝者再次表示哀悼;同时又从礼制、感情等几个方面,劝勉服丧者摆脱悲痛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敦煌写卷S.2832《脱服文》内容与之类似。“脱服”的主要用意在于“营斋建福”、“辞凶受吉”,因此《脱服文》文本往往呈现一种对比的结构、劝勉的语调和相对乐观的气氛,从此对逝者的哀悼悲痛即将成为过去,逝者的亲属毕竟还要面对现实的生活。这类《脱服文》主要是在敦煌丧葬活动的哪种仪式上使用呢?上引写卷S.2832《脱服文》开头几句已经点明:“三年受服,服尽于今朝;累岁严灵,灵终于即夕”;另外写卷P.2237《脱服文》之首亦云:“夫目月亦流,奄经三载。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说明《脱服文》是在三年之丧期满时所使用的,根据上文对敦煌丧葬仪式的考述观之,很可能是在三年斋祭的“大祥斋”的仪式活动上所使用的。从敦煌文献看,丧俗文还有很多,如奠不治身亡的《亡文》,盖棺告别的《盖闻无余涅槃金棺永寂文》,祭周年的《忌文》,小祥、中祥、大祥时用的《追福文》等[14]。此外,敦煌所见祭奠亡者的还有“行香文”、“释奠文”等。但“行香文”主要是在忌日祭奠皇帝或皇后所用,释奠文主要是祭奠孔子等先师的应用文,虽然也与祭祀活动和祭祀仪式有关,但与本节所讨论的“丧葬”活动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赘。
敦煌丧俗文与丧葬仪式之关系
前文在考察敦煌丧葬仪式与丧俗文的使用状况时,曾对二者相互关系有所涉及,现在此基础上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祭文、斋文韵诵活动是丧葬仪式的核心。前文曾指出,祭祀活动的本质是出于人对于天道、自然的敬畏心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神交流沟通的需要,这也决定了仪式本身具有叙述功能。丧葬仪式中的一切行为、工具、装饰等无不是为了达成人神交流等文化心理的需要,僧道之人凭借其特殊身份协助完成这一交流活动。但在全部仪式活动过程中,作为交流中介的语言表达,即祭文韵诵活动是祭祀仪式的核心,助祭者代表祭祀主体陈述对逝者的哀悼、祈福等诸多诉愿,因此可以说祭文、亡斋文等丧俗文的本质就是祭祀仪式诵辞。在祭祀文化发展的早期,巫祝的助祭活动只是一种口头语言行为,随着文字的发明和语言的发展才逐渐出现书面文本。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文字被巫祝等少数贵族所掌握,根据早期的符号和甲骨文等看,文字沟通人神的功能远大于实用功能,巫祝的“告”、“号”则是向神灵传递人类诉求的主要方式。敦煌遗书中的丧俗文写卷,保留了丧葬仪式的详细环节,是口头文学与书面相结合的形态。从这些方面观察,我们可以说敦煌丧俗文源出于丧葬仪式,是丧葬仪式进一步深化、抽象化、文明化的结果。
(二)丧葬仪式决定各类丧俗文的结构模式。纵观上文所述的各种丧葬仪式,无论是逝者刚去世时的“入殓”、“出殡”等仪式,还是去世后的各类斋祭仪式,不难发现时间序列是其中隐含的一条重要线索。在这个隐而不见的时间序列中,死者与生者的距离越来越远,生者从最初的悲痛之中逐渐摆脱出来,在以各种祭祀仪式表达哀悼之情与祈福心愿的同时,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生活。在列次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丧俗文,无论是普通祭文在其开始时对祭祀时间与祭祀者和逝者关系的交代,还是亡斋文中的“号头”、“明斋”、“叹德”、“斋意”、“道场”、“庄严”等结构设计,都体现了祭祀仪式中的时间序列和人物之间各种关系的变化,由此可见祭祀仪式对丧俗文结构与内容的深刻影响。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敦煌丧俗文是真正的仪式和实用性的,它不同于出自文人笔下的单纯抒发感情的祭文作品,其内容完全依据各类丧葬仪式的需要而设计和写作,我们甚至可以从一篇丧俗文的基本内容及其篇幅的长短、辞采的华素等方面推测当日丧葬仪式的基本情形,这也是敦煌丧俗文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民俗价值的根本原因。
(三)丧葬仪式对丧俗文的文体风格有重要影响。综观各类敦煌丧俗文,可以发现多数作品具有韵诵特征,用骈体形式。这种形式除了与仪式的节奏气氛相配合外,更由于音乐的介入,而形成了一种庄严、肃穆甚至悲伤的氛围,造成更为神秘的沟通人神的效果。
本文作者:陈烁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