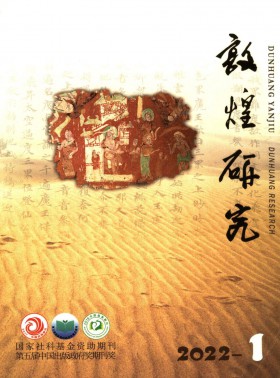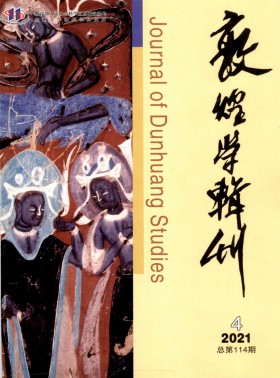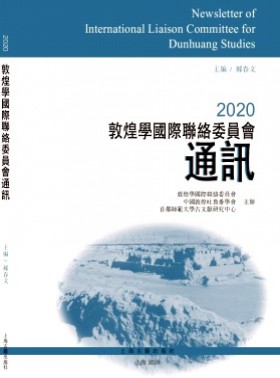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敦煌艺术理论探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1.法国的丹纳、中国的马奇、美国的奥尔德里奇等艺术批评家或美学家,都曾以“艺术哲学”为名写过很好的书;一些艺术批评家如司空图、道济、刘勰、朗格、科林伍德等也写过很好的书,这些书虽未贯以哲学的名字,但确是艺术哲学的上称之作。①他们都以自己对艺术的独特见解,构造了各自庞大的艺术哲学体系。什么是艺术哲学?这往往取决于艺术家各自对什么是艺术的体认。 艺术是人表达自己的存在的特殊方式。人通过艺术对时空进行自由地切割,从而构造一个同人的现实存在相对应、但又同人的现实存在性质不同的虚拟的世界;人需要这个世界,因为人不满足、甚至厌恶自己的现实存在,人在自己创造的这个虚拟世界里为自己的精神、理想寻找寄托和解放。人不可能只待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除非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人需要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存满足,需要处理实实在在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各种现实关系,需要对既定的各种精神规范负责;但是,一当人创造了自己的虚拟的世界,人的一切现实的经验都会经受一种极为复杂的、超验的洗礼,现存世界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关系,即会放出新的光彩。人所特有的这种来往于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用现实世界的经验和教训构筑虚拟世界、用虚拟世界的光彩映照现实的能力和活动,并非为个别艺术家所独有,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这种能力和活动,只不过有强和弱、自觉和不自觉、执着和不经意之分罢了。有没有无此能力和活动的人?有没有只死心塌地生活在功利的现实世界的人?可能有,如果有,这种人当是很出类拔萃的,亦是很令人畏忄瞿的。 2.艺术哲学同通常的艺术理论不同。它不把如下问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如各类艺术形式的形成历史和社会条件;艺术形式本身的结构、规律、特点;艺术形式的制作者禀赋的风格、技法;形式之间的横向关系、纵向承传等。艺术哲学是艺术的形而上学;艺术哲学不排斥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而是把上述问题所揭示的关系当成既定的资料,通过对它们的分析,了解艺术形式是如何表达人的存在状况的。 一般艺术哲学(这里暂不专讲宗教艺术哲学)所要探讨的人的存在状况有三个层次:艺术是怎样表达人对现实世界的反抗意绪的;艺术是怎样表达人对现实世界转化意绪的;艺术是怎样表达人对现实世界的空灵意绪的。这实际上是人的三种审美境界。 以《窦娥冤》为例,先说说第一种境界。窦娥蒙冤,将在恶势力的屠刀下丧生,她立誓:若自己无罪,行刑后,血溅旌旗,六月飞雪。这本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她真的被冤枉了。但当她被砍头后,她的誓言果然实现了。她(当然首先是艺术家关汉卿)用殷血、白雪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激烈的反抗和控诉。个体的肉体毁灭了,但它的精神高扬了。这是一种艺术的审美境界,它内涵着善同恶的永不妥协的对立,标示着个体肉体存在的脆弱性同个体精神存在的坚忍性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这种境界的主调是不和谐,而这里,不和谐正是一种美:漫天大雪,一片银白,但它却掩不住从冤尸潺潺流出的殷血。第二种境界,我用历史上有名的“蓝狱”中一个被杀的人的一首诗来说明。 明时,太祖诛戮功臣,曾在洪武时被封为大将军的蓝玉以谋反罪就刑,为扫除党羽,受牵连的一万五千人先后被推向刑场。其中有个叫朱寿的,当开斩的鼓声已响,刽子手手中映着落日余霞的屠刀就要举起时,他竟占诗一首:“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已斜。黄泉无故人,今夜宿谁家?”现实如此残酷,受牵连无端被砍头是这等不公平,心中没有一点愤恚、一点怨恨、一点不平?从诗看,确无。现世界没有是非,他也就不分辨是非了,现世界没有公正,他也就不计较公正了,现世界无处伸冤,他也就不考虑伸冤的事了,现世界已不容他再活下去,他也就不再留恋尘世那些斩不断的情缘了。他这会儿只想着黄泉道上如何赶路的事了。这黄泉没有阴风惨惨,没有厉鬼挡道,而仿佛是一条供他旅游的路径,虽然有些陌生,但却饶有兴味。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走累了在哪家店铺歇脚啊?这是一种把可怕的死转化为平淡的回家的境界,一种把生存的无奈境况转化成可供陶醉的状况的境界。夕阳、鼍鼓、屠刀、含冤难诉、身首异处——这些令人心肝具裂的景象,被一句“今夜宿谁家”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立即转而对受刑人面临生存极端处境,却能以平常心淡然处之的心态,表示由衷的赞佩。第三种境界,就是庄子在几千年前描绘的,后来又融进儒、释的思想,在中国人的生存中和中国人的艺术观念中绵延不绝的禅的空灵的境界,一种引导人进入齐生死、等高下、游无穷、无忧、无碍、无待、无己的境界。面临生存的极端状况,改变心态,视死如归虽不易,但若要在整个活着的时候超越生存的一切感性和理性的判定,将是非、曲直、善恶、贵贱、否泰、喜怒、哀乐、生死、有无等等,一样对待,就是更难的事了。这是一种需要终生修炼,同一切感性体验始终背道而驰方能达到的境界。这里我举丹霞子淳禅师(1064~1117)的一首《无题》诗为例:“长江澄澈即蟾华,满目清光未是家。借问渔舟何处去?夜深依旧宿芦花。”②也是一首写归宿的诗。浩瀚的长江水面上映射着月亮的光华,微波涟涟,银光万点,静极,广极,美极,这景象映入人的眼睑,有一种入归的感觉吗?还没有,因为这时现象和感觉还是两分的;只有驾着小舟,轻轻划过江面,没入银色的月光、银色的水光和银色的芦花融为一体,一切都分不出彼此的苇丛中去,才算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在这种境界中,没有生的欢乐,亦无死的恐惧。在这种境界中,无须将生存的无奈转化为生存的陶醉。在这种境界中,有生命的(如人、如芦花),和无生命的(如月、如水、如船)是和谐为一体的。在这种境界中,人与万事万物,自我与流动的现象,都在宇宙的永恒的静谧和神秘中融解了:宇审就是自我,自我就是宇宙,生存的永恒的真谛就在于此。 3.如果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表现,那么,艺术哲学就是探究形式中融化着的“意味”的。这是借用别人的概念的一种说法。“有意味的形式”是英国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的用语。他把意味解释为同现象事物不同的东西,解释为“终极的实在”,说:“当我们把任何一件物品本身看做它的目的的时刻,正是我们开始认识到从这个物品中可以获得比把它看作一件与人类利害相关的物品更多的审美性质的时候。……我现在谈的是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并赋予不同事物不同意味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终极实在本身。”③这个“终极实在”亦被他称作“一切物品中的主宰”、“特殊中的一般”、“充斥于一切事物中的节奏”。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不太集中谈“意味”。而是谈“气韵”(如画论),气韵似乎更动荡些;谈“神韵”(如诗论),神韵似乎更生动些;谈“太极”、“道”、“天地之心”(如文论),这些似乎更朴素,更自然些。这里的自然同贝尔说的“终极实在”有共通处(都指人心之外的一种存在),但不同处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艺术家对人之外的绝对独立的存在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总喜欢通过艺术在这样的存在与心灵之间架起桥梁,表现人的精神同自然的精神的共鸣、谐振。在中国艺术家那里,自然,是被人的精神“软化”了的自然,而精神,又是被自然的气韵充盈着的精神。因此,在中国艺术家的多数作品中,人同自然是很谐和的。#p#分页标题#e# 4.在这里,艺术与宗教有了相通的性质。宗教同艺术一样,也是人为自己构造的虚幻的世界,宗教亦用这个虚幻的世界表达人在现实世界实现不了的理想和意愿,亦借助虚幻的形式或关系,将人在现实世界充满冲突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关系予以重构,使它变得和谐。天国里的物质供应总是很丰富的,天国里的人和人(神与神)的关系也是非常和谐的,固然这关系极为等级森严。 5.但是,宗教毕竟是宗教,艺术同它有着本质的区别。艺术的时空观同宗教的时空观是根本对立的。其一,艺术并不宣称自己构造的虚幻世界是一种客体的、乃至占据实在空间的世界。构造艺术虚幻世界的材料是占据一定空间的,但这个空间并不是艺术向人的精神展示的那个虚幻的空间。艺术构造的虚幻世界是主体性的、精神性的、不占据物理空间的,在人看到的地方不占,也不告诉人它存在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而宗教则宣扬自己构造的虚幻世界是一种客体的、同现实世界一样占据着广大乃至无垠空间的世界,一种现在触摸不到、但今后可生活于其间的彼岸世界;其二,艺术构造的虚幻世界,相对构造者和欣赏者,在时间上以瞬间方式存在。它既不存在于人的现实存在之前,也不存在于人的现实存在之后,既不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前因,也不是人的现实存在的结果。它是间于人的现实存在之中的一个个、一次次美丽的闪光。宗教构造的实际上是虚幻的世界却宣称,相对它的构造者和膜拜者,它在时间上以永恒的方式存在。它既存在于个体人的现实存在之前,也存在于个体人的现实存在毁灭之后,既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前缘,也是人的现实存在的归宿。它宣称:相对人的短暂的现实生活,人的宗教的、与神同在的生活是永恒的;其三,宗教的虚幻世界,除过是人的一种精神需要外,还带有一种由外部力量(如宗教宣传、政治权力)强加于人的性质,所以,对于膜拜者,宗教是自由的,也是不自由的。宗教宣称的秩序多是凝固的,对规定这种秩序的教义的稍许变动,往往要经过艰难的斗争甚至血腥的博斗。艺术构造的虚幻世界一般说来,对人没有强迫性,你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也可以不进入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后,你可以自由地、不须要以任何教条作准则,来对这个世界作新的自由创造,因此,就艺术世界对不同个体的宽容态度而言(或反过来,就任何个体都可以对艺术世界进行随心所欲地创造而言),它是超时空的存在,是无规范、无边无垠的存在,多样性的存在。其四,宗教构造的虚幻世界作用于人的“思惟空洞”:人作为个体,依恋自己的生命,因而对它最终将无可挽回地走向寂灭难以理解,难以作出令个人乐于接受的理性的解释,思惟在这个对个体来说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处于空白、空虚、空洞状态。宗教用信仰来填补这个空白。它给个体描述感性生命走在尽头时的境界。艺术对虚幻世界的构造,是个体自主选择的一种“精神自由”。它不回答个体热爱生命、但又无法改变它最终归于寂灭这个背谬的问题。它是个体在存在历程的无数个瞬间,将生命从现实生活中升腾起来的自由活动。 6.宗教艺术把宗教的虚幻世界和艺术的虚幻世界结合起来,构成一种奇特的虚幻世界。艺术世界不论它多么虚幻,人总会觉得它是人的世界,是人参与其中的世界,即便其中没有勾出人的形象,人也不会觉得它是异己的,人同它有一种亲和感。宗教世界则不然,它愈是虚幻,则人愈觉得它遥远。它是神的世界,人的异己的世界,人对它有一种敬畏感、恐惧感。宗教,比如佛教,最早是不允许人把佛陀绘成具象的形象的,教徒为了崇拜佛,便面对一个被塑成柱子形状的东西诵经礼拜。这时候,那根抽象的柱子主要只是一个崇拜的对象(当然,由于崇敬,那柱子在教徒的心中肯定会引起某种审美的感觉)。后来,人不满意于自己对着一根抽象的柱子的膜拜了,于是便叛离教规,为佛塑出了具体的人的形象。这时,佛的超时空的、神秘莫测的、难以亲近的性质在人的心里不自觉地发生了变化:佛同我们毕竟还是有共通的地方啊。随后,佛啊,菩萨啊等等便被塑得越来越美,人有多美,他们就有多美,甚至比人还美。就这样,一个崇拜的对象,同时成了审美的对象。可以说,宗教,一旦同艺术结缘,它的神性便被人性的光晕所衍射。人面对宗教艺术,是面对神,还是面对人?是崇拜神的威力,还是欣赏人的美丽?是向一种同自己截然不同的力量曲膝膜拜,还是同一个有力量有智慧有善心、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同类进行对话?这些,在此时都显得界线不太分明了。宗教艺术是宗教向人堕落(亦可以说是向人提升)的一种感性表达。 7.在这方面,敦煌艺术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我们经常把敦煌艺术的这种活动称作敦煌艺术的世俗化。对敦煌艺术的世俗化解释,是对敦煌艺术作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当然,与世俗化倾向相对应的,敦煌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变化与特点,它同一般世俗艺术的联系与区别等等,也就成为对敦煌艺术作哲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了。 8.敦煌莫高窟的众多雕塑和壁画中,有数不尽的表达禅境的作品。禅是中国人融会儒、道、释的精义而创造的体验生存意义的宗教的、艺术的境界。儒学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学说,给中国人展示的境界太冷峻。人被网在森严的伦理等级秩序中,被要求主要考虑怎么对别人、对社会负责任。但个人存在的许多事,如饥寒温饱、孤苦无援、生老病死、等等,儒学一般是不予解答的。即使是对这些问题有所触及,也是用冷漠的口吻给予训导。比如,要作在生年过半时达到“不惑”(大概也包括对生死问题不惑),生年将尽时要你“从心所欲不逾矩”等等,都是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而如何做到?就不知道了,你自己去考虑吧。殊知,处在迷惑中的人要不惑,须有人指引迷津才成,被生存重负压得气也难喘的人要从心所欲,谈何容易?道学藐视儒家,讨厌那张网人的网,所以,它教人弃仁绝义,弃学从愚,无己,无待,无碍,融于自然,游弋无穷,以此求得精神的解放。但是道学过于玄虚,对于习惯由外部可感力量来支配自己生活的多数中国人,这种实现自由的方式不易被接受。中国的士大夫以及搞学问、作诗、绘画的人,在自己的艺术想象中,多少掌握了这种方式,为自己在现实生活的罗网之外造出一个新的宇宙——一个“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恽南田《题洁庵图》语)的宇宙,一个“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方士庶《天慵庵随笔》语)的宇宙。但是,为生存疲于奔命的多数中国人很难做这种精神功夫。他们最容易接受的还是那个外于自己的佛。这个佛不象儒那样漠视他们生活中的琐事,那样对他们的终极思虑置而不论。也不象道那样要他们在自己心中构造自由世界。这个佛赐给他们一个在他们之外“早已”存在的神的世界,而这些神(尤其是在神与人之间互传信息的观世音菩萨)既关心他们的来世,也不责备他们对现世(如儿女情长、追名逐利、种谷收麦、升官发财)的眷恋,确立了一个在憧憬来世与善待今生之间实现平衡的原则。中国人是乐于接受佛的。同时,他们也不排斥儒的教导和道的境界。固然,作禅的功夫的多是中国的士大夫和古代知识分子;但是,信佛的中国老百姓也改造佛,创造融会儒与道的佛的完美形象。研究敦煌艺术,可以理会中国的禅在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百姓那里的联系与区别。#p#分页标题#e# 9.儒、释、道都拿出了一套用来教导人如何剪裁生活的准则。都在告诫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你应该喜欢的,什么是你应该厌恶的。比如,儒要人积极用世,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则把追名逐利的世人看成同大鹏不可比拟的,只能是在蓬草间、屋檐下低飞的麻雀;释教人善待今生,而主要还是教人修行来世。这三种对待生存的准则,在中国人的眼中,都有它们存在的必要,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都有它们实践的影子。而在中国人的心里,他们在这三者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艰难的选择,因此,生存对中国人来说,是既丰富又贫乏的(不知实践那个信条时就感到无比空虚),亦是既辉煌又暗淡的(徘徊往往使他们感到颓丧)。敦煌艺术以特有的历史性的画卷,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人上述的生存徘徊状况。 10.敦煌莫高窟处在一片广袤的沙漠和戈壁的包围之中。这是一种有寓意的现象。中国人在无垠的焦渴的包围中找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乐土,在那里建造了一个类似“总非人间所有”的奇境、一个让生命得到憩息的“家园”。那是佛的世界,也是人从焦渴的生存走向绿荫遮崖、清泉润石的仙境的所在。它在地理上同外界是隔绝的,但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它同外界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的雕塑、壁画,那样地扬溢着飞动的旋律,那样地充满着同佛的冷静的冥想形成巨大张力的感性热力,那样地表现着人对于同这个存在家园相对应的现实世界的批判和肯定,怨恨和眷恋,想割舍又急切地要投入其怀抱的矛盾心理。它实际是中国人依恋世俗、改造世俗、从而使自己能够亲近世俗的热情创造。她历经沧桑仍然活生生地活动在我们面前,是她千年来不断同她的创造者、膜拜者与欣赏者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和有关生命真谛的对话的结果。 11.在敦煌艺术中有许多可以理出系统的世俗存在的符号(包括儒和道的概念、范畴)、艺术的符号以及佛的符号。这些符号是如何在敦煌艺术这个统一的系统中相互对立、相互转换、又相互融和的?这是对敦煌艺术进行哲学研究的非常复杂和细致的工程。 12.可以把敦煌艺术宝库看成中国人创造的希望人从中体验生存形而上意义的“学校”。上述几个符号系统转换的奥秘,正是这个学校要教导“学生”从事破译的主要课题。有多少去敦煌朝觐的人(无论是朝觐神,还是朝觐艺术),就有多少破译这个奥秘的方法和答案,在这方面,艺术家,教徒,旅游者,都是平等的。用哲学的观点看,敦煌艺术永远是一种开放的艺术。有人用语言同她对话,有人写出文章同她对话,有人不说也不写,只是把对她的印象和理解轻轻地、深深地藏入心底,用心同她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