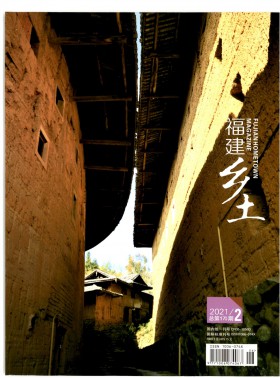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特征,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1](P.3)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基于思想及文本的思考与论争。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1917~1949年)乡土文学理论既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乡土社会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与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立场也处于变化之中,又使之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 本文试图探讨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态特点,并历时性地追踪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以期在整合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找寻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历史启示。 一现代乡土文学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乃至命名方式都受到国外乡土文学及乡土研究的启发。尽管作家们在接受国外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时,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和倾向,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乡土文学描写的都是偏远的乡村、小镇的故事,文本中的背景往往与现代都市有意无意地构成一种对比关系,突出或强化地方色彩,在对乡村、小镇的自然景物、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流露出对乡土世界及乡土民众的同情,隐现着对于现代都市的复杂心态,这些基本特点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艺术理念上,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直接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零星地散见于单篇论文、书信、序跋、创作谈、译后介绍之中,往往三言两语,点到即止,缺乏西方文学理论的严密的体系性。但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又绝非穿着白话外衣的古老灵魂的死灰复燃,其精神是现代的,其价值取向也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庞杂的理论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家的思考与批评。废名援引波特莱尔的话说:“所有伟大诗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的,要成为批评家。”[2](P.57)现代乡土文学作者也是如此,无论是夫子自道,还是相互辩难,其言论既为阐释以往的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又预示着一种新的创作动向,因而,在这些看似散乱、庞杂的理论资源中蕴藏着关于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的全部。 显然,这些理论形态并不是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是常态,因为“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系统”[3](P.46),它更多地与政治立场、政治激情、集团利益乃至私人恩怨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恰恰是这活生生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现代乡土文学的窗户。 二现代乡土文学理论虽然不是以体系性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的,但是透过表面零散、杂乱的理论话语还是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自身的统一性、逻辑自洽性及其历史流变。 在功能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轫期,期间确立了最基本的乡土文学理论,即鲁迅的“乡土启蒙论”。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4](P.439) 这是鲁迅对《呐喊》的文学功能的概括,也是其启蒙文学的理论宣言。鲁迅要改变的主要是乡土层民众的精神。鲁迅强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P.526) 简而言之,鲁迅的“乡土启蒙论”是以“为人生”、“改良人生”为目的的,而鲁迅等人之所以要改变当时的人生,乃是源于对现代性的追求。 现代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迫切的使命,“乡土启蒙论”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即思想文化入手,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正如林毓生所言,鲁迅等“五四”先驱“要求通过建立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所必需的新的思想文化基础,来全面解决当代的问题”[6](P.63)。受鲁迅的影响,青年作家许钦文、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胡也频、许杰、赛先艾、黎锦明、王任叔等以犀利的批判锋芒穿透种种乡风民俗、乡间悲喜剧,直指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虽然作品的故事情节、风格特征各异,但是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的理念为价值尺度。 “乡土启蒙论”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特有的理论。“乡土启蒙论”赋予乡土文学以明确的启蒙意图和功利色彩,即鞭策落后、抨击专制,以达到改良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而形成其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的独特品格。 同情农民是世界范围内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主流倾向。乡土文学的兴起大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致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日益萧条;另一方面与城市工作相比较,农耕劳作更加艰辛,加之农民生活较为贫穷,从而使作家对农民充满同情。因此,同情农民、为农民呼喊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普遍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城市生活也有其不如人意之处。 “乡土启蒙论”与世界乡土文学普遍同情农民的思想倾向相一致。但是,鲁迅超越了同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农民,指向了乡土社会的思想、文化、习俗及其孕育的农民思想,这在世界乡土文学中是极少见的。以赫姆林•加兰为代表的美国乡土小说就没有启蒙诉求。困扰美国农民的不是精神枷锁,而是城市化和西进运动造成的萧条、沉闷与单调(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同,但大同小异),与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没有启蒙的必要。但是,“乡土启蒙论”却致力于把乡土层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的解放,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对乡土层民众的精神毒害,为之争取做“人”的权利。因此,乡土批判是对农民的更深沉、更急切的同情,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严厉的批判,其独特品格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决定的。#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作家涉足乡土文学略晚于鲁迅,也大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启发,但是,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意图中的启蒙诉求相对减弱,而对地方色彩的追求却有所增强。因而,其乡土文学理论是功利论与纯艺术论的折中。在同情农民、关注乡土社会在动乱时世中经受的压力等方面,自由主义作家与鲁迅派作家并无分歧,但为什么启蒙诉求会减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溯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自由主义作家或者是“五四”的先驱,或者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都赞同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发民智,即主张启蒙。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7](P.271)启蒙的目的就是教会被启蒙者使用自己的“知性”,而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一旦学会使用“知性”,其结果必然是引发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作斗争,这是对既有秩序的全盘颠覆。但对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斗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换言之,启蒙的逻辑结果就是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这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势必导致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减弱,而地方色彩有所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地方色彩是偏远的乡村在与现代都市的对照中赖以确认自我价值,从而获得身份认同的根本,地方色彩缓和了启蒙叙事过于沉重和压抑的气氛,因而,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整体风格显得较为轻松、明快。值得强调的是,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守着这种相对淡然的启蒙立场。 鲁迅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追溯到对于启蒙的态度和认识上,但是,两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启蒙诉求的缓急程度不同而已。 三自由主义作家所害怕的启蒙的后果正是创造社、太阳社后期等左翼作家、批评家所需要的结果,他们要求作家描绘的是启蒙后的农民,因而,合乎逻辑地否定了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另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话语,其核心观念是“文学是宣传”。虽然这是创造社后期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学的功能,并非专门针对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的功能不仅从属于这一总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对乡土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宣传论”肇始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对于乡土文学理论而言,“革命文学论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左翼文坛彻底放弃了“乡土启蒙论”,转而提倡“宣传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8]钱杏?在肯定文艺宣传的正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宣传文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煽动,要起煽动的作用”[9](P.170)。“宣传论”随之成为左翼作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瞿秋白在批驳苏汶时说:“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10] “文学是宣传”是左翼文学的基本理论,左翼乡土文学的功能也自然是宣传,同时,这一理论出炉的历史语境显示了它对于乡土文学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左翼话语中的“群众”、“大众”主要指农民,不仅因为农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更因为农民在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中被看成是最值得联合、发动和依靠的对象。 当时,左翼作家极力否定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就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因为宣传是为了发动农民,而作为发动对象的农民应该具有相应的素质,不能像阿Q那样思想觉悟低、体格孱弱,于是,钱杏?指责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11],宣称“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11]。“宣传论”塑造的是不仅有斗争思想而且有斗争能力的农民形象。任白戈主张,“将目前正在历史底任务之下喘息着的农民底现实的生活或英勇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要宣传他们“花一般的理想,火一般的感情,铁一般的意志”[12]。显然,20世纪30年代左翼批评家强调乡土文学宣传功能的真实含义是正面宣传,鲁迅的“乡土启蒙”思想被彻底否定了。因而,不论左翼文坛如何调整与鲁迅的关系,都仅仅是一种姿态。 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是宣传”的基础上,40年代的左翼文坛进一步将乡土文学的功用定位于工具。当然,工具论的说法并非源于40年代,30年代左翼批评家就有取消文学独立性、以政治价值来衡量艺术价值的说法,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13](P.103),但这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连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周扬对此也有所保留。周扬指出:“忽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把方法问题完全还原为单纯的世界观的问题,这错误是早已正当地受到了批判。”[14]然而,运动确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5](P.848)。由于运动的严肃性,使一部分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至1942年后文学工具论便达到极点”[16]。 例如周扬,虽然此时也谈到文艺的特殊性,但已经把“文艺服从于政治”作为绝对原则了。周扬指出:“文艺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文艺可以离开政治任务,艺术家可以和政治乃至政治家疏远的一种遁词。”[17](P.389)也就是说,艺术家就是革命工作者,艺术就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也最先表现出来。 #p#分页标题#e# 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对作家的艺术构思及文本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贯彻、宣传政策,作家只能根据政策设置情节、划分人物身份,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认真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对于作品人物顾涌的思想、性格、行为的塑造紧紧与他是中农还是富农的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既然艺术是工具,就要起到正面的效果,于是作家们都心照不宣地宣传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至于消极影响则完全回避了。周立波知道,“北满的,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他认为“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18](P.287)。在周立波看来,写不写消极影响是涉及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在本质上,工具论仍是一种“宣传论”,无非是把宣传的范围、内容、目的进一步具体化。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强调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塑造与农民政治身份相符的文学形象,是一种对外宣传。既要求继续对外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又倡导对内宣传,主要是对农民宣传新的农村政策,要求文学作品与政策、法规保持高度的一致,宣传最终成为乡土文学的核心功能,左翼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并使之得以实现和巩固。 应该说,“乡土启蒙论”和“宣传论”都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所独有的文学现象,“乡土启蒙论”倡导乡土批判,“宣传论”推崇美化农民,两者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从中不难看出经典乡土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变异,其中既有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观和思维水平问题,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要与政治需要,而这两种因素的重点在于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用的关系。“乡土启蒙论”基本上是作家、批评家对于乡土文学的阐释行为,是鲁迅等人面对愚昧落后的乡土世界的真诚的艺术思考,作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而左翼批评家则以主动向政治靠拢的姿态介入乡土文学批评,并日益表现出为文学“立法”的倾向与冲动,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文学批评与政权的合作变得更为密切,文学理论的“立法”性质更为明显,乡土文学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 四启蒙既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功能,也是它的目的,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政治立场分歧的加剧,作家群体的政治化色彩越发浓厚,文学日益成为作家表达政治理念的载体。因而,面对贫穷、饥饿、动荡、兵连祸结的乡土世界,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目的日益殊异,左翼作家力证革命的合理性,而自由主义作家则意在警示政府,简言之,就是颠覆与警示的分流与对峙。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根据政治革命的需要,确立乡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鼓励农民起来革命,以颠覆旧政权,李初梨将革命文学的形式归纳为“讽刺”、“暴露”、“鼓动”和“教导”[8],即讽刺、暴露敌人,鼓动和教导农民投身斗争,而斗争的对象就是国民党政府。钱杏?指责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政治思想!有的不过是残败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军阀,官僚的片断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的。”[19](P.362)对于1928年的左翼作家而言,反政府的迫切性要远远大于反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用意,自由主义者看得很清楚。苏雪林指出,新写实主义(即左翼乡土小说)鼓吹“复兴中国,非推翻现行政制,改用某种主义不可”,认为这是“野心家的别有怀抱,是非常可怕的”[20](P.265)。 叶公超相对委婉地指出:“小说根本就没有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21]“改造社会”依然是针对左翼文学企图颠覆政府的写作意向而言的。 颠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革命,而革命却是一个可以公开使用的概念,因为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事业、理论和追求,只不过双方对革命的解释各不相同罢了。左翼作家主张乡土小说的革命叙事凸显的是农民与地主的二元对立,而地主阶级最终依靠的是政府,因此,革命的矛头实际上对准政府,这种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乡土文学的主流则已经转向在旧政权被颠覆之后,如何发动群众斗争地方豪强、建设新的村级权力机构了,而且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颠覆了旧时代的准则和规范,因此,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建设为主、颠覆为辅,颠覆是为具体的建设服务的,这就是“赵树理方向”的基本内涵,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起建设与颠覆的作用———才是核心所在,“老百姓喜欢看”是为了能够最大范围、最有效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赵树理的艺术观念顺应了左翼文坛的需要。在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如何颠覆旧的遗留,特别是那些深入人心的旧的观念和习俗,应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题材中常见的移风易俗的叙事依然是沿着“赵树理方向”前进的。 颠覆的目的决定了在创作方法上摒弃写实主义,转而提倡新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其意图是要求作家既要面对现实,又要避免启蒙立场———回避农民蒙昧的精神和乡村落后的文化。直白地说,就是要求作家对乡土现实进行选择的描写。“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22],“要摆脱‘旧写实主义’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旧意识而获得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3]。无论是舍弃琐事,还是获得新的宇宙观、人生观,其实都要求作家放弃写实主义直书善恶的较真精神,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取舍之间的奥妙就在于是否有利于为革命(或曰颠覆)提供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论证。#p#分页标题#e# 自由主义者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乡村苦难,同样充满了忧虑和同情,苏雪林、沈从文、李健吾等人可谓忧心如焚。苏雪林对当时的乡村现实相当了解。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时,苏雪林说:“肚皮饿着时,以及虐待受到无可再受时,驯良的会变成杀人放火的罪犯,恋田园的会举家逃亡,顽固的也会赞成革命理论。” [20](P.263)苏雪林不仅关注着农村的灾难,而且体察到了农民革命的现实原因及其复杂心理。沈从文算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的乡土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的身份和姿态写作,对于战争背景下行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经济上、心理上的压迫与伤害,可谓义愤填膺,即使在创作像《边城》这样较为温暖、浪漫的小说时,沈从文对于乡村现实的黑暗依然耿耿于怀,表示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描绘农民“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24](P.72)。后来,沈从文又写出了与《边城》极具对照意味的《长河》。虽然沈从文有意减少对现实残酷性的写实,而作成“乡村幽默”,但是,其湘西小说中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湘西现实的忧虑。李健吾极为同情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乡土层民众,在评介芦焚的《里门拾记》时,感慨普通百姓的血泪人生,在论及叶紫时,也无限同情“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25](P.125)。农民、苦难成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对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萧条真正负责的应该是政府,因此,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政府多有批评,如沈从文公开表达了对“地方特权者”的不满,指责“地方政治不良”[26](P.333)。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创作目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恰恰相反,意在帮助政府,给政府提供警示,自觉承担了“诤友”的角色,因而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写意。沈从文承认其湘西小说回避了更为严酷的现实,并在《水云》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当时在左翼作家中盛行的现实主义,但是,沈从文许多含蓄的表白其实都指向现实主义。苏雪林则说得很直接,她以“喧阗叫嚣”形容之,指责其“被歪曲被利用”[20](P.265)。李健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25](P.156)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现实主义,而主张有距离地写意,偏爱温情、平和的乡土书写。梁实秋虽然口头上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主张其中“不必含有人道主义的色彩”[27](P.258),主张写普遍的人性,用意仍然是回避黑暗的乡土现实,因为黑暗就是革命的理由。 如果说苏雪林亲近政府的心情与姿态较为平和,那么沈从文则要急切得多。沈从文一直关注乡土层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为乡土世界陷入道德退步、生活艰难的困境而忧心忡忡,但他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他批评政治,嘲讽新生活运动,心情激愤,其实是替政府担忧,但是,政府不仅不领情,反而横加指责,乃至迫害,致使当时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据国外学者易劳逸统计,仅1929~1936年间,就有“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28](P.38)。 自由主义者最终陷入两边不讨好的窘境,因此,在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文字中,沈从文一再以孤独的边缘人的语调申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痛苦,鲁迅说他“忠而获咎”[29](P.45),确实是洞悉了自由主义者的困境。 总之,自由主义者面对当时乡土社会的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胡适温和改良的思想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其乡土叙事意在警示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用苏雪林的话说,就是“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20](P.265)。 五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共同起点是“乡土启蒙论”,对致力于现代性追求的乡土中国而言,“乡土启蒙论”无疑是治救旧文化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集团化和政治化,乡土文学理论出现了分流,自由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依照各自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发展、流变。 从周作人到沈从文,自由主义者没有放弃启蒙立场,启蒙的理念与政治改良结合在一起,警示就成为其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了。左翼乡土文学理论出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否定了“乡土启蒙论”,进而推出“宣传论”,其创作目的日益集中于颠覆。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 值得深思的是,左翼理论以鲁迅为旗帜,却彻底否定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并由此导致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土文学领域的虚假叙事,艺术价值丧失殆尽,无法发挥其政治作用,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当下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