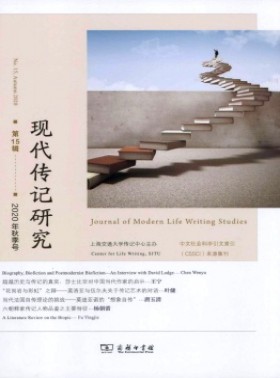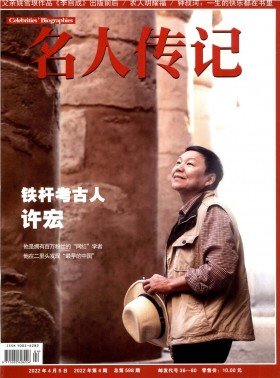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传记文学史理论思考,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出版是中国传记文学界的盛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壮举。令人赞叹并敬佩的是:这部皇皇四十余万言巨著的写作,不是组织的“写作班子”,而是全靠的“个人书写”——作者是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郭久麟教授。正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著名出版家王维玲在《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序言中指出的:郭久麟这部专著从事的“是传记文学史上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郭教授的大著不是一般的“填补空白”——所谓的拾遗补缺,而是高质量地填补了中国传记文学界和中国出版界有关成果的缺失。《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是有目共睹的硕果,郭久麟付出了艰辛的创造性的劳动,他的贡献应该得到高度的评价。 说郭久麟付出了艰辛,笔者是目睹者之一,为了《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这个“大工程”的写作,他舍弃了一切的娱乐活动,付出了授课之余的全部时间与精力。2006年暑假,当其他教师纷纷外出避暑之际,他却顶着山城39—41摄氏度的高温,足不出户,日复一日,熬更守夜地写作。 说《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是“创造性的劳动”,是强调郭久麟没有人云亦云,步人后尘。他见解独立,论从史出,而不是唯上媚权。郭久麟在充分肯定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成就之后,也敢于揭露传记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足见其史家之风骨。郭久麟指出:在创作倾向上,中国传记文学作品明显偏重于英雄而忽略平民百姓;在人物评价上,他批评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教条,还严重地束缚着传记作者的头脑,使他们总是把政治领袖、杰出人物写得完美无缺。”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传记文学作品,特别是企业家和明星的传记开始出现商业化与庸俗化倾向。” 在郭久麟这部传记文学史著中,不乏掘佚钩沉之篇章。例如,在第六章“五四以后他传文学创作”这一章中,对张默生传记文学创作的述评,就使一个传记文学大家跃然纸上。 将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写进《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笔者非常赞成,也非常佩服。王实味之死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剖片,但却折射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某种命运。正如郭久麟的评价:“通过王实味个人的历史悲剧,揭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一条线索,其意义是很大的。”对当代传记文学作品及其作者,郭久麟的评论始终坚持直言不讳。例如他评论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在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别具一格、别开新面、新颖独特的传记”之后,也严肃指出“这部传记在总体上的缺点:对鲁迅的描述和评论的片面性”。 再如,评论《李敖快意恩仇录》时,指出李敖“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如在批判国民党时,连孙中山先生也一起批判了”。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语言文字非常到位,从不用“穿靴戴帽式”或者“断然绝然式”的语调和口吻。作者富有才华而不卖弄,具有真知灼见而不以权威自居。例如,第三章中评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先是指出“《多余的话》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瞿秋白的思想、文艺和人生,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然后篇末总结说:“《多余的话》在感情上的真诚朴实,博大深邃;在写法上的自由挥洒,无拘无束;在语言上的精纯凝重,含蓄深沉,都是无与伦比,难以企及的。古人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篇临终遗言表达的耿介拔俗之思,潇洒出尘之怀,实在是令人深思,远不是当代人可以完全洞悉或随便评说的。”这段文字非常精彩。从近年俄国解密的前苏联有关中国革命秘密档案得知,在1920—1931年期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几乎每三天一个指示,每五天一个会议,每七天一个决议,事无巨细都要按他们说的办。显然,瞿秋白等,都不过是他们“支部”的办事员而已,既然如此,当年中国革命的曲折,瞿秋白等何罪之有?《多余的话》最后一句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瞿秋白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传记文学是对传主的历史或者片段史的研究、记叙与描写。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编年史,一个世纪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一些名人和非名人的活动史。可以说每一部真正的传记文学都是历史的一个小小剖面或者剖片,而为研究历史、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史料。因此,传记文学一方面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的积淀与扬弃。由此观之,一个世纪的传记文学史是多么的重要了。显然,仅仅靠文学才华和写作灵感是不行的,靠一点断代史知识加传记文学作品的分类也是不行的。从事百年传记文学史的写作,必须具备传记文学理论家的深厚素养,必须具备传记文学史家的眼光与胆识,必须具备传记文学作家的才华与经验。无“巧”不成“书”,郭久麟正是这样一位集传记文学理论家、传记文学作家和传记文学史家于一身的集大成者。笔者还要“锦上添花”,指出郭久麟同时是一位传记文学教育家。早在2005年,郭久麟教授就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在重庆西南大学育才学院创办了“传记文学研究中心”,开设了“传记文学研究”选修课。所以,成功绝非偶然,成功属于为“大工程”做好各种准备的郭久麟。 毫无疑问,《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出版,奠定了郭久麟在中国传记文学界的重要地位。 当然,《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也存在微瑕。 在此,笔者特提出几点意见与郭久麟教授商榷。 其一,《把一切献给党》的传主是吴运铎,作者却不是吴运铎,而是何家栋。这部传记文学作品的创意、采访与写作,都是何家栋独立完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何家栋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这类传记文学作品不同于后来的“口述实录”,其著作权应该属于作者而非传主。《我的一家》和《战斗的一生》的真正作者也是何家栋。何家栋还是《刘志丹》的编著者之一。毫无疑问,应该将何家栋先生加入20世纪优秀传记文学作家之列。#p#分页标题#e# 其二,《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也存在某些“遗珠之憾”,如没有入选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还有石楠的《张玉良传》、梅志的《胡风传》、韩石山的《徐志摩传》等也被忽略了,当然,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其三,《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最后一篇入选作品是连方?的《半世纪的相逢——两岸和平之旅》,而这篇作品按说是不能称为传记文学的,因为没有传记文学的属性。其实是一篇游记,或者可称为旅游通讯作品。即或看重其政治意义与现实价值,顶多将其列入《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附录部分即可。 最后,笔者想借此机会提出一个问题,向中国传记文学界的朋友们请教:应该如何看待外国作家撰写的中国人物的传记?例如,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撰写的《伟大的道路——的生平和时代》(又译《传》)。笔者认为:这部传记的品质、价值及意义,都绝不亚于甚至还高于中国作家的同类作品。希望能引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