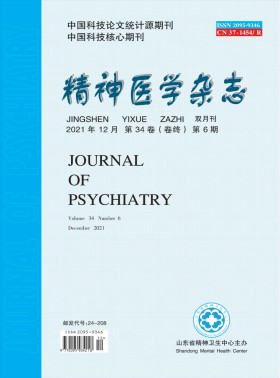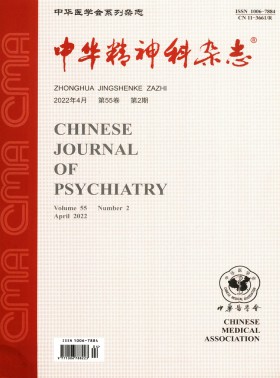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精神生态视角下的菊花,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菊花》是美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斯坦贝克的一篇短篇小说,自发表以来就受到批评家的好评,被誉为“斯坦贝克在艺术上最成功的小说”[1]、“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2]等。其情节并不复杂,讲述的是加利福尼亚萨利纳斯山谷一个农场里一对夫妇在特定的一天的生活,以及发生在女主人公伊莉莎与一位流浪补锅匠之间的故事。伊莉莎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三十五岁,热爱并擅长种菊花,和丈夫亨利一起过着平淡的日子。在平淡的生活中伊莉莎的内心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补锅匠的来访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也在她原本就不平静的内心世界激起了波澜。她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位理解并欣赏自己的人了。于是,她把她所珍爱的并寄托了她渴望和梦想的菊花交给了补锅匠,此后,她的内心世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和强大。后来当她和亨利驾车去萨利纳斯的路途中,她发现菊花被补锅匠抛弃在路上,花盆却被拿走了,伊莉莎失望至极,但是却躲着亨利像个老妇人似的哭了起来。 故事的情节虽然简单但里面刻画的人物却是丰富而又深刻的。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内涵时,斯坦贝克在给乔治•阿尔比(GeorgeAlbee)的信中提到“他(读者)不经意地读完故事后会体会到某种很深刻的东西,但却说不出是什么东西,怎样深刻。”[3]本文以斯坦贝克《菊花》这部短篇小说作为文本,从精神生态角度对其中的人物进行分析,关注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生态状况,分析其精神生态错位的表现,并探寻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以期通过挖掘其内在的“深刻的东西”对读者有所启发。 1自我迷失与人性扭曲:探析错位的精神生态 著名学者鲁枢元教授在其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中把生态学大致划分为三个方面:以相对对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生态学”,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态学”,以及以人的内在情感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精神生态学”[4]。“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5]精神生态学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正遭受着与自然生态相似的危机。斯坦贝克在《菊花》中通过对伊莉莎这一悲剧人物的刻画,帮助读者洞察到了人们错位的精神生态。 1.1女性身份的界定:甚感压抑 在《菊花》[6]这部小说里,斯坦贝克通过伊莉莎这个悲剧命运人物的塑造,把一个生活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男权社会里的女人的情感世界和心理历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那个特定的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男性世界的排斥和男权势力的压制使女性身心倍受压抑和束缚。 伊莉莎被囚禁在社会对男女角色的既定中。在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她们不得不安于“家庭中的天使”一般的角色。当时的社会认为真正的女性应该是“虔诚的,纯洁的,顺从的,持家有术和深居简出的。”[7]故事中的伊莉莎就是按照这种界定的标准生活的。首先,她是一位称职的家庭主妇。房舍被打扫得“整洁、明亮”。生活也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冬草储备了起来”,“精致的白色的农舍”四周环绕着紫色的天竺葵,她还在“房前台阶上放着一块供擦泥的垫子”,在“房子后面堆着易拉罐”;在亨利洗澡时“她把他要穿的黑色西装放在床上,把衬衫、袜子和领带放在旁边。上过油的皮鞋放在床边的地板上”。其次,她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当亨利在她面前炫耀刚刚做成的一笔菜牛的生意时,她说“你真行”去鼓励自己的丈夫,去满足自己丈夫的心理需求。当亨利把详细的去城里庆祝的安排计划告诉她时,她没有任何异议,只是回应“好,当然好啦!”来顺从自己丈夫的安排。再次,她是一位恪守妇道的女性。她把菊园周围架设“围栏”,然而“围栏”挡住的不仅是“牛、狗和鸡不进入菊园”同时也成为她主动压抑自己“本我”需求的道德界限,当补锅匠“向围栏靠近了点”时,“伊莉莎的眼睛变得警觉”起来。尽管后来经过和补锅匠短暂的交流之后,她许久以来被压制的对性的渴望被补锅匠这位陌生男子重新唤醒,情不自禁地“手向他的裤管伸去”,但她最终还是“面带愧色”地站了起来。在这里,斯坦贝克冷静客观地描写了伊莉莎性骚动继而性压抑的过程,读者不难感受到在男权社会如此强大的社会文化传统面前,面对这种身份被界定的现实,以伊莉莎为代表的女性所承受的这种压抑人性的精神磨难。 1.2男性身份的模仿:遭遇尴尬 对于伊莉莎来说,虽然她没有走围栏,而且遵守了妇女行为的基本守则,但是透过围栏的空隙,她的向往、理想和追求已经传达到公共空间。 伊莉莎向往男性世界的权利。她用男性化的穿着来刻意掩饰女性柔弱的外表,“园艺服遮住了她的体形”,把“一顶男人的黑色帽子拉得很低,挡住了视线”,穿的“鞋子又笨又大”。尽管被排斥在由“亨利和两个商人装束的男人”组成的男性世界之外却“不时地回头望望身边的男人”,并急切想参与男性世界的决策,于是在亨利回来之后便问“亨利,和你谈话的人是谁?”补锅匠的突然造访激发起伊莉莎内心世界对男性世界自由的渴望。伊莉莎被补锅匠对自己流浪生活的描述所吸引,“那一定很有意思,非常有趣,但愿女人也能有这种生活”。伊莉莎还诉求和男性共享的平等,她想通过在亨利面前极尽为妇为妻之道,同时倾心培育菊花“使黄菊花花瓣大到十英寸”,来证明“我具有这方面的天才”,而得到亨利的认可,同时在补锅匠面前也毫不示弱,“说不定你会碰上对手的,我也能磨剪刀,也能把小锅的凹痕敲开,或许我能给一个女人能做些什么。”为了实现自我,伊莉莎做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在男性世界的认可和接纳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追寻。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太阳。伊莉莎的追求和理想都在亨利的“我希望你能在苹果园里也培育出那样大的苹果”的漠视和贬抑以及补锅匠的“这种生活对女人不合适”的排斥中遭遇尴尬。#p#分页标题#e# 1.3迷失自我的回归:倍感失落 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拒绝只扮演她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不健全的;但是不承认她的性别也同样是一种不健全。男人是有性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征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否认她的女性气质就等于在否认她的人性。”[7]伊莉莎也想成为一个健全的自我,在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同时,还能保持自己的女性特质。 补锅匠的突然造访,激发了伊莉莎被压抑的女性特质,在补锅匠面前“脱下帽子,把乌黑漂亮的秀发披散在肩上”,“胸脯由于激动上下起伏着”,希望自己的柔美能在这个她认为能欣赏和认可自己菊花的男人面前同样得到欣赏,然而补锅匠仅仅是“把视线集中了一下,然后下意识地把目光移开”。尽管有些许的失落,伊莉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还带着一些期盼。她认为或许是因为自己长时间的压抑自我,是那种男性化的装扮掩盖了自己的女性身份,才没有被补锅匠所欣赏。于是,“她把沾土的衣服脱下来,扔到一个角落”,然后洗浴,用力搓洗自己身上的污垢,“用一块浮石在身上搓:小腿、大腿、腰、胸部、胳膊,直到皮肤被搓得通红,”然后“她换上最新的内衣、最好的长袜和最能衬托她的美的外衣。她细心地收拾着头发,描了眉,涂上口红”。在伊莉莎看来,此处的洗浴具有宗教意义,就像基督教洗礼一样,经过这种神圣的仪式之后,一个全新的自我就会展现在别人面前。于是她“端庄地坐下来”,在那里憧憬和期待着“那一抹阳光飘带”早日灿烂自己压抑的生活。这看似美好的一切,亨利却不知所措,只会唐突地用“精神”和“强壮”来赞美自己盛装的妻子。但是,毕竟此时的伊莉莎已经不是以前的伊莉莎了,她的自我意识已经苏醒,内心比原来强大了很多,现在她已经意识到“我很强壮。我以前怎么没意识到”。在她看来,尽管丈夫不能理解和欣赏自己,但这依然不能阻止自己内心的向往,“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帽子戴好,她要确信帽绳和帽檐都摆在最好的位置”,期盼着和一个能欣赏和理解自己的人相遇。对伊莉莎而言,菊花承载着她的梦想,寄托着她的希望,菊花被补锅匠带走了,也意味着自己的梦想开始实现了。当她看到“路上有一个黑点”时,尽管“她知道那是什么”,内心很痛苦,很茫然,也很失落,但是她却束手无策。 《菊花》的写作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当时的女权运动方兴未艾,妇女为了取得与男性平等的的权力和地位以及自我价值而抗争,但却屡遭失败,妇女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女性的价值始终得不到男性的认可。在当时社会背景下,面对那种无助、无依与无奈的现实,伊莉莎尽管受到男性世界公然的蔑视和贬抑,但是她能做的只是“强抑着自己不去看它”,“全身扑到丈夫的怀里,不想看到车子和牲畜”,在那里“像一位老妇人一样”地“啜泣”。斯坦贝克在《菊花》中通过对伊莉莎男性特征与女性特质的频繁转变进行了细腻的描写,刻画出她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从压抑、躁动到醒悟、绝望再到无力地屈服,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妇女无奈的现实。 2价值观偏狭和情感疏离:洞察深层次原因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不景气,1933年,美国大萧条最为严重时,有1500万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占当时全美国劳动力的1/4。在以农业为主要经济基础的加利福尼亚州,农场破产,无数农业工人失业。让当地社会和经济局势更加恶劣的是,成千上万来自俄克拉荷马和阿肯色州的无家可归的农民移民至此。以往的“美国梦”普遍幻灭,人们普遍忙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而对内心的、感情的生活麻木,心灵世界朝着务实功利、简单直接的方向发展。同时,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和信任,人们之间的情感被疏离在各自的追求中。 在生活中,亨利扮演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支配型的男性角色。自然和女性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可以利用和开发的资源而已。他对土地掠夺式的开垦,以至于“肥沃的土壤在排犁深翻过后放着光泽”,急切地“卖了三十条有三个年头的菜牛”以获得经济利益,对机器的着迷和尊崇,以及对女性角色的既定和约束,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亨利而言,女性就像自然一样是可以被控制和被征服的。他已经习惯了伊莉莎的顺从和附属,在他看来,伊莉莎和他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必须要服务他,取悦他的。种菊花远没有种苹果获得的经济利益大,因此她要求伊莉莎“我希望你也能在果园里培育出那样大的苹果”。日常生活的平庸化使亨利和伊莉莎之间缺乏心灵沟通和交流,和妻子的关系生疏和冷淡。他需要的仅仅是一个生活上的伙伴而不是精神上的伴侣,他功利性的婚姻关系就是在残酷的现实下的一种价值观偏狭的选择。 补锅匠的出现似乎给伊莉莎的生活带来转机。伊莉莎本来以为补锅匠能知道自己的需要而且理解自己的思想,她梦想着补锅匠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然而,由于现实生活压力太大,补锅匠无暇顾及自己以及伊莉莎的内心感受和精神追求。对他而言,居无定所,三餐不定时,解决温饱是第一要务。他利用了自己的花招骗取了伊莉莎的同情、欣赏和金钱。当他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他就再也不在乎伊莉莎的感受也不想费心和她交流了。当伊莉莎问他为什么说他的那种生活对女人不合适时,铜匠说“我不知道,夫人,我当然不清楚”。这时,他已经失去了对伊莉莎的耐心,同时也关闭了和伊莉莎情感沟通的心灵之门。当他把菊花公然抛弃在路上而不是路边时,他疏离了伊莉莎的情感,亵渎了伊莉莎的信任,撕裂了伊莉莎的梦想,也践踏了伊莉莎的自尊。 3结语 在《菊花》这部短篇小说中,伊莉莎渴望、追求、寻找着默契、欣赏和信任,但最终却在这个功利实用主义至上的世界里遭到漠视、否定和背叛,“哀莫大于心死”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反映了人类精神层面的深层困境和危机。正如鲁枢元所说的那样“科学越来越发达,而人却越来越无力;技术越来越先进,空间却越来越狭窄;商品越来越丰富,生活却越来越单调;世界越来越喧嚣,心灵却越来越孤寂。”#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