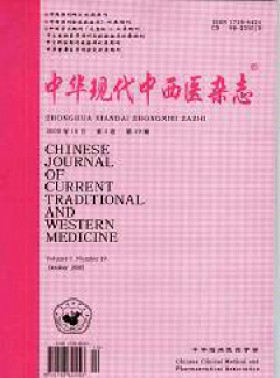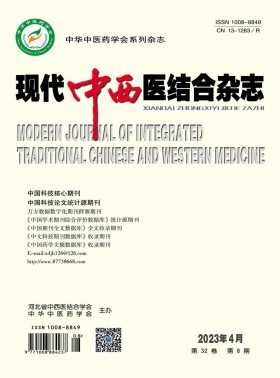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中西审美意象对话的趋势,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审美意象理论起源于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建构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西方文论中同样十分重视审美意象理论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中西审美意象理论的比较具有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中西文学批评家从各自的传统出发,对审美意象理论进行阐释,这样的阐释标示着中西艺术美学的巨大差异。 中西审美意象有着各自所关注的核心,中国审美意象的核心在写意,偏重抒发作者的主观情志;西方审美意象的核心在摹象,侧重于描绘事物(事理)的客观形态。中国文论中意象的概念首见于《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不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里的言、象、意虽然并非针对纯文本而言,但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文本构成的要素,“言、象、意”为一个由表及里的审美层次结构,可以理解为文学言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意蕴层面。在文学作品中,人们首先接触的是“言”,通过“言”可以看见由“言”所构成的“象”,最后才能得见“象”所表示的“意”。“立象以尽意”,圣人创造“象”来表达他们的“意”,立象是尽意的前提,尽意是立象的目的。意象即为表意之象,象的存在是为了引导人们进入意的层面。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首次论述了“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是以陶钧文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在这里刘勰认为意象是“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的结果,即作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感悟和思考而发生的一种艺术想象的产物。它既是外物感召的结果,又绝非外物本身,而是作者本身的主观情感与艺术想象在符号层面的审美构成,是主观和客观一体的产物。刘勰又对意象的创作规律进行总结,他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这样的规律偏重于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意志,把对外物的感觉放在第一位。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审美意象即为“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在某些理性观念和抽象思维的制导下创造的具有求解性和多义性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1]这样的界定建立在中国传统审美意象理论基础之上,认为本质上来讲,意象即为“表意之象”,是理性思维和抽象观念主导下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艺术反映,是作者以象征手法创造的艺术形象。同时,他把意象分为一般的“观念意象”和“审美意象”两种范式,“审美意象”是“观念意象”的高级形态,而论述审美意象的特点正是从观念意象开始的。图腾、习俗等属于一般观念意象的范畴,都属于“象”,在中国文化中,这些“象”的列举是用来反映“意”的,如英雄胸前佩戴的大红花象征了荣耀,小孩脖子上挂的金锁象征了长寿,而脱离这些象征意义,红花、金锁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同样,在高层次的“审美意象”中,“象”即“至事”,“意”即“至理”,意象即为以“不可言之事”述“不可言之理”。换言之,至事是为至理服务的,形象实际上已经变成某种意义的载体,“意”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审美意象理论中重写意的审美核心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诗学观念,认为诗主要表现诗人的情志,即写诗人之意。而西方的审美意象理论则继承了“模仿说”的理论传统,认为“模仿自然”是文学创造的最高法则。康德指出:“对于艺术家所提出的最高要求就是:他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2]所以西方的审美意象理论更侧重于对于“象”的描摹。康德在其著作《判断力批判》中对意象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在这种形象的显现里面,可以使人想起许多思想,然而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和概念,与之完全相适应。因此,语言永远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它,使之变得完全明白易懂。”[3]他指出没有恰当的语言来表达意象。康德阐述语言和意象的关系,用中国传统批评话语可以概括为“言不尽象”,而在《周易》中我们发现与此结构类似的观点“言不尽意”,这也体现了中西审美核心的根本差异:“尽意”、“尽象”。朱光潜先生总结康德的意象概念为“一种理性观念的最完满的感性形象显现”,审美意象是对这一感性形象的再现和临摹。瑞恰慈在《文学批评原理》中指出:“人们总是过分重视意象的感觉性。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为一个意象的生动性,而是它作为一个心理事件与感觉奇特结合的特征。”[4]这边指出审美意象的功用在于感觉的“重现”,即是对感觉的描摹。而庞德则吸收了中国古典审美意象理论的部分因素,并揉合法国象征主义诗学观,创造出了意象派诗论,他认为诗歌应该描绘“意象”,即“一种在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性的集合体。”这种“意象”是以间接的手法处理“事物”(不管这个“事物”是主观的思想还是客观的事物)的结果。“意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一个思想,它是一团、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具有活力。”此外,还强调“准确的意象”能使情绪找到它的“对等物”。[5]根据庞德的理解,意象作为现代诗歌的基本艺术符号,它指涉的是“诗人的感情、智性和客观物体在瞬间的融合,它暗示诗人内心的图景,它锋利而具体有着坚固的质量。”[6]不管是康德的“感性形象”,还是瑞恰慈心理与感觉结合的特征,抑或是庞德提出的“理性和感性”集合的“对等物”,虽然对于审美意象所描摹的物质的具体认识不同,但他们的审美意象理论概括言之即为摹某种之象,再现某种情感、体验。 审美核心的不同必然导致审美追求和审美表现上的差异。西方的审美意象理论偏重于“摹象”,侧重对“象”的刻画,认为意象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艺术化认知的结果,是客观在主观情感中艺术的残留。西方艺术强调形象,而对这种形象的欣赏却需要阿波罗式的静穆关照。在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在奥林匹斯山上俯视世相,人世间一切事物只有经过他的光辉照耀才能得到形象。他对人间美丑悲欢一律关照,而又保持冷静客观。这大概是西方人追求客观事实、客观真理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待外部世界的根本态度。他们这种观察世界的态度和方式,反映到对意象的关照欣赏中不只是要求感官的愉悦,而是同时获得知识和真理,即获得对其本质的认知。无论是创造还是接受都渗透着这种客观的精神和关照的方式。可以说,强调审美关照,强调在审美关照中获得内在世界的真实,这是西方艺术的根本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审美意象再现的真实,反映的准确清晰,所以西方文论更多地强调如画性。艾略特在评价但丁时称赞他的诗“是一种视觉的想象”,但丁是一位寓言家,而“对一位有能力的诗人来说,寓言就意味着清晰的视觉意象”。庞德认为,“我们相信诗歌应该准确地再现各别的事物,而不是表现模糊的一般,不论它是多么……具有吸引力”。[7]中国艺术则侧重于内省式的体味和领悟,因此审美意象的追求不在对“象”、“形”的外部情状的真实描摹,而是着力于对“意”的追求。通过“象”,作者希望读者能够领悟到的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又特别强调“委曲”、“含蓄”,强调“言有尽而意无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希望文章能够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所以作者往往在保留意象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模糊性的处理,从而扩大艺术的表达和想象空间,增强艺术的感染力。《诗经•蒹葭》中,“伊人”意象时而在对面,时而在身边,时而在水中央,真是如同在幻景中,在梦境里,但这丝毫不能阻挡主人公的爱慕和热情,不顾“道阻”,“溯洄”而从。正是这样一种模糊朦胧似真非真的意象深刻地刻画出了一个痴情者的心理情态,体现了他对所爱者的强烈感情。这种意象的模糊,使全诗具有一种朦胧的美感,生发出韵味无穷的艺术感染力。谢榛说:“凡作诗不宜逼真,如朝行远望,青山佳色,隐然可爱,其烟霞变幻,难于名状;及登临非复奇观,惟片石数树而已。远近所见不同,妙在含糊,方见作手。”跟西方审美意象强调如画性相对,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是模糊的。它通过形象呈现出内心的人生体验,并通过这种呈现暗示言外的不尽之意,而西方审美意象的创造要求遵循客观逻辑,通过形象显示出本质的真实。后者求实,而前者恰恰“化实为虚”,以象外之象,言不尽之意。#p#分页标题#e# 各自的渊源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中西方审美意象理论更多地呈现出对立的局面,主要体现在写意与摹象的审美核心差异、务虚和求实的审美追求差异以及模糊与清晰的审美表现差异。然而两种意象理论的发展并非平行前进,而是在发展中呈现出某种相互影响、甚至是趋同的态势。到了20世纪,随着中国美学的西方化进程以及西方对中国传统美学的关注,这种态势显得更为突出。如在论述审美意象本质特征的时候,童庆炳先生引入西方现代派先驱卡夫卡的观点:“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8]而在对审美意象进行分类的时候,童先生引入了西方符号主义的相关理论。这样的西方概念的引入并非机械地对中国传统审美理论的添加,实际上是童庆炳先生在中西审美理论对比审视的基础上,对西方审美意象理论的接受和认可。中国传统美学是强调“写意”的美学,卡夫卡的理论强调对思维中所呈现的“难以解释”的象的描摹,于是这样的借鉴和引用体现了童先生对“象”的兼顾,对“写实”的认可,虽然这样的“象”和“写实”早已脱离了“再现说”的窠臼,而带有主观的认知性和情感性。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批判艾略特审美意象的观点,指出其过分地强调“如画性”的教条,他认为审美意象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描述性诗歌中,仅仅靠再现或者描摹外部世界的图像去创造意象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意象的创造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经验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创造性认知。相对于中西审美意象理论的对立,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二者的趋同。不管中国美学家在理论诠释中对西方再现理论的接受,还是西方批评者在对“意象”的重新界定中对于中国古典审美意象理论的借鉴,都体现出一种对话精神。相对于在对立的层面建构各自审美文化的传统体系,这样的对话无疑更加具有时代意义。在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当下,跨文化接触日趋频繁,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日益紧迫。这就需要研究者以一种全球眼光和人类视野去关注审美问题,而不是单纯地站在民族或者地域的立场守护传统、固步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