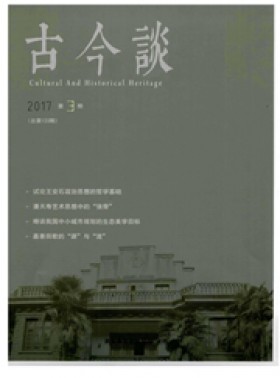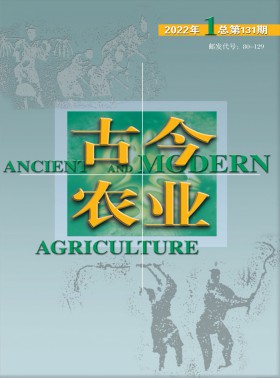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古今文学阐释异同,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由于“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前代著作多为后代人无法理解,甚至同时代人也不能理解,所以就需要熟知前代名物典制、礼仪制度、历史文化的通人对前代著作加以整理,以时下语言解释前代作品以供人阅读,通过阅读汲取前代文化、经验教训,并为当下服务。随时间递推,前人的解说后代人亦已不能了解,故需要新一轮解说。正如黄俊杰所归纳的“孟子诠释学可以说起于‘语言性的断裂’与‘脉络性的断裂’”。[1]267于是产生了致力于还原经典的阐释活动。 也正因为人们对于前代著作的“求知欲”,促进了阐释的形成、发展,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要具备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结构框架,西方阐释学由来已久,虽然中国的阐释实践很早,但缺乏理论的总结,这跟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有关。目前仍有学者质疑中国阐释学的存在,认为中国阐释学的理论框架都来源于西方文论,借西方文论的结构阐释中国古籍,只能说是一种借鉴,而不能就此说中国亦有阐释学,因为理论体系不健全,结构框架不完善。笔者才疏学浅,未遍读群书,不便妄下雌黄,故本文抛开中国有无“阐释学”不讲,仅就中国经学经典的阐释历程和方式做一番梳理。 一、中国古籍的阐释 中国古籍的阐释史与其说是古籍的阐释史,不如说是经学经典的阐释史,中国阐释学就等同于中国经学经典阐释学(这里没有区分为西方文论中的古代阐释学与现代阐释学,因为笔者认为中国没有本土的阐释学,现行阐释学理论框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西方传入,如果欲分析真正的中国阐释学,就要回归中国本土,故不用西方阐释学的分期)。以《孟子》阐释为积淀研究中国阐释学(亦称“诠释学”)较为有名的台湾学者黄俊杰,就认为“所谓‘中国诠释学’,是指中国学术史上源远流长的经典注疏传统中所呈现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诠释学”。[1]266李清良在《黄俊杰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类型,方法与特质》一文中分析归纳黄俊杰先生上述观点为“中国诠释学”等于“中国经典诠释学”。[1]266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尉利工的博士论文《朱子经典诠释思想研究》中指出,“中国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经典诠释史”。虽没有明确指出是经学经典及诠释学,但就文中所述亦可说明经学经典是中国阐释学的支柱,研究中国阐释学,就相当于研究中国经学经典的阐释史。 中国古代学术分经学、子学、史学。翻检艺文志、经籍志,不难发现经部记载书目、总类数量最多,代表了各个时代的学术导向,亦是中国学术主体,仅《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经学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代表,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回溯中国经学史,可分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宋义理学①,对于经学的阐释自其产生之时就已开始,皮锡瑞说:“孔子所定谓之经;弟子所释谓之传,或谓之记;弟子展转相授谓之说。”[2]39同样经学的阐释又因派别的不同而有不同侧重,西汉今文经多阐发圣人之微言大义,东汉古文经学多名物典制、训诂的解释,宋义理学则抛开圣人不谈,以阐发个人义理为主。 史学,目前学界多称“历史学”,“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科,一般而言,其专指整理与研究人类有文字以来所留下的文字与图象纪录的学科”。[3]两汉之前著作数量少,尚不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汉书•艺文志》史部书籍则收在“六艺略”春秋类下。魏晋南北朝始独立为一门类,作为与经学、子学并行的学术存在。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4]1无论是前面微观的含义,还是瞿先生宏观的概括,都认为对于历史的事件应尽可能地还原到当时代的情境中去解说,以便人们对那个时代有客观的认识。解释者个人发挥的余地较少,惟独使文章显得有文采而已,但事实须是客观的描述。 子学谓诸子之学,我们可以把子学比照现在意义的哲学、自然科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5]769由于视子学为杂学,故不为帝王提倡,亦不为学者们重视(儒、道、佛三家除外)②,所以是类书数量少,又少有注释疏证,遂多无继承不相传。在民间,子学还留有一定地位,比如术数、方技、五行之学,作为纯朴人民的迷信———一种精神需要而存在,但却谈不上阐释,多为口耳相传,无深入研究。再如医家、历数、农家等实用之学,只要求疏通文字,能理解文意即可。这种存在状态给学者研究设置障碍,为求得利禄,多舍此而为经学。 二、古今文学阐释异同 古今文学的源于汉经古今文之争,据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今文经主要是口耳相传,著之竹帛;古文经则是流传下来或重新发现的经书古本。二者除文本不同外,说解、宗旨亦不同。今文家标榜“经世致用”,强调经书的直接的、简化的实用目的,把孔子看作政治家,认为六经皆为孔子著述,里面处处贯穿着孔子的思想观点,多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并掺杂谶言阴阳;古文家则求对经书本身作确实地理解,认为孔子为史学家,“六经皆史”,孔子述而不作,说解侧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学术性较强。 我们可以从古今文家对待经典的态度窥其阐释角度。今文经学的特点是通过训诂章句为手段,力图为圣人立言,替圣人说道,借经书宣扬圣人思想,阐释典籍过程中努力摆脱甚至忽略“此在”的存在,用圣人思想比附现实,但阐释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却无形中影响其用当时代通行思想立说,如西汉“独尊儒术”、魏晋“玄学”、隋唐“缘佛入儒”,此种阐释是“在世界之中”的一种反映,但个人意识尚未觉醒。古文经学的特点是以小学为根基,从打破语言障碍入手,透析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阐释者力图抛开“此在”与“自在”(自在:西方文论“存在主义”术语,笔者理解为经典作者全视角的叙述线索的存在,即蕴含着通过作品传递作者思想的存在)的存在,以自己的知识积累构建经典的文化内蕴,但同样摆脱不了“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如在解释古事时每涉及思想内容,难免有附会之嫌。#p#分页标题#e# 除上述历时层面的比较外,还需要对其共时层面的具体差别做一番介绍,就是今古文之争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及时代背景下经学阐释的流变。下面以皮锡瑞《经学历史》划分时期为线索来分析。 (一)今古文阐释的区分之前的经学开辟时代 此时期是经学的初创期,无论经学典籍先前以何种文本流传,自孔子删定六经之后,便被奉为经典。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确定经典,孔子依据当时需要对已存文本加以删削,确定数量语句。有些文本上下时代相差不远,尚能被理解,阐释活动产生的前提———“语言性的断裂”、“脉络性的断裂”不是很显著,所以这一时期阐释仅存在于师徒相授以口耳相传的讲授活动中,对经文的解读即是在为统治思想服务,或为礼仪典制的继承与发展,“此在”的“日常生活”与经典的差异通过解读过程相互融合。 (二)今古文刀锋相见的经学流传、昌明、极盛时代 此时期有了阐释的必要,弟子传承老师经学的过程中夹杂着自己的理解,以述老师思想为己任的传、记之书大量问世。弟子们依据各自的理解,对老师的文本加以解读,由于“日常生活”的不同,解读的角度、内涵就不同,比如《春秋》的传承之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在《春秋》经记事基础上多有发挥,借宣扬经文思想的文本阐发一己之见。两汉时期,儒学思想顺应董仲舒改革的路线发展,阐释经典则有意维护统治阶级思想,并以章句训诂为阐释方式。汉武帝对经学极力奖励推行,通晓经书的人获得礼遇,使投入经学研究的人更多,当时就有“遗子金满盈,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这一时代的阐释活动就带有明显的“此在”、“自在”的存在,传、记之书列为经典之后便有了今古文之分,并且二者的争辩愈演愈烈,各自阐释特点上文已述及。经学之所以昌明、极盛,亦在于争论,有异议才有反驳,才能促使研究的深入。 (三)今古文阐释融合的经学中衰、统一时代 东汉末年,郑玄在古今文之争极盛而衰的空隙中异军突起,集古今文学之大成,将二者优势互补,去除分歧,以二者之长遍注群经,此时经学以郑学独尊,郑学阐释以古文学为基础,皆今文学阐释方法,发扬儒家学说,站在“无征不信”的高度为圣人思想代言,强调经书的“自在”存在。文化思想的统一必须有一个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为依托,郑学在短暂的小一统之后便遭遇政局动荡,王郑之争终结了古今文之争。朝代的更迭使得人心涣散,无意于学术背后的政治之争,道家的“无为”思想顺应潮流被推崇备至,“缘道入儒”成为风尚,“世界”的大环境影响阐释者不谈学术而志于思辨,即西方存在主义中的“言谈”。“言谈”即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术语,是“按照含义对现身在世的可领会状态的分解”。也就是说,魏晋“玄学”的思辨道出了阐释者对所处“世界”的一种领悟,通过对现身世界的把握、通过经典文本道出“此在”,而“现身在世的可理解状态道出言谈”。[6]97唐五代,由于佛教的兴盛,帝王对道教的提倡,造就了儒、佛、道三家鼎力的局面,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经学阐释格外突出了“世界”的影响,统治者关注重心的转移,导致学术倒向道、佛的解读。阐释者对经典亦是顶礼膜拜,“疏不破注”,在南北朝义疏之体的基础上以训诂注疏为主要阐释手段,多无创新。阐释仅是厘清经典文本、训诂考释词句及思想内容,往往洋洋几百字疏证一条注释,繁文缛节,造成研读不便,从另一角度加速了儒学的衰退。 (四)今古文阐释复兴的经学分立、复盛时代 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复杂,朝代更迭、分裂战乱的政治局面很难给学术发展的空间,地理上的分割势必会影响学术朝不同方向发展,魏晋“缘道入儒”形式的“玄学”依然对这一阶段人们思想有所影响。南朝宋、齐、梁、陈都为汉族统治者,受“玄学”和佛学影响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故学术朝着哲学思辨方向发展,有今文经学阐发微言大义的韵味,当时义疏之作即是由南及北,亦可视为“玄学”余续。而北朝多为少数民族政权,虽都采取汉化政策,亦崇尚儒学,但由于主要是吸取统治经验,所以容易接受正统的汉、魏晋时期儒学,故注重名物典制、训诂考释的古文经学阐释的道路发展。南北经学因阐释角度、方法、内容的不同而分立,今文学渐微,古文学重兴,义疏体产生即是本时期阐释活动特点。清朝经学是在宋学的园囿里成长起来的,在经历明朝灭亡后开始反思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诸多弊端,以汲取经验教训。加之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政策由举“博学鸿词科”的笼络利诱到大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转变,使得知识分子不敢高谈阔论,亦不敢有所造次。所以经文的解读一方面要反思、要改革,另一方面又有所畏惧,只能“埋在故书斋里讨生活”,走上一条不介入政治的实学与考据学的路子,并一度造就了“乾嘉朴学”的辉煌。此时的阐释活动则再现了东汉古文学的阐释模式。嘉庆道光以后,受西学实用主义影响,标榜“经世致用”的经今文学复兴阐释方式随之改变。皮锡瑞《经学历史》说清代学术“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是为西汉今文之学”。[2]249-250 (五)今古文阐释更易的经学变古、积衰时代 这一时代经学在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大起大落、大分大合后又趋于统一,经学经典在经过古今文之争、郑学一统、郑王之争、义疏、注疏等争辩解读后,名物典制、训诂考释后已发展到相当高度,对于宋人已无发挥的余地。唐五代由于帝王提倡佛学急剧发展,对于道教、佛教的阐释超出儒学,宋时亦然,宋人既受道学、佛学影响,又为发展儒学而辟佛,阐释者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于是产生了“好奇”,“这一术语作为描述方式不局限于‘看’,它表示觉知者的世界来照面的一种特殊倾向”。[6]207正由于“好奇”,是阐释者观照自己的“世界”,将儒学借道教、佛教阐释的本体论形式重新解读,把“圣人的原意,文本的原义以及读者所悟之意”有机融合在一起,变更古今文学训诂考释的阐释模式而为宋学理论化、思辨化的阐释模式,在原来就文本而谈文本的低层次阐释活动提高到借文本谈“此在”与“存在”的高层次阐释活动,尤为强调“此在”的存在,囿于文本,具体阐释方式在他文阐述,元明时期则照着宋学的思路发展。#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