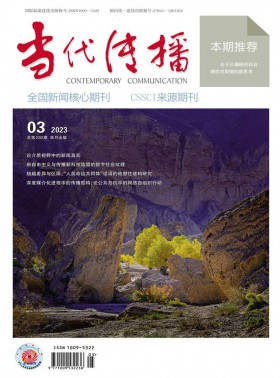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传播视域下的底层形象,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成为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的文学现象,由于他关注现实,与当下生活的紧密联系,受到作家、读者乃至评论家的欢迎。特别是2004年以来,随着曹征路的《那儿》、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的面世,关于底层的创作与研讨更是让“底层文学”的概念大放光芒。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家竞相涌现,有罗伟章、陈应松、尤凤伟、刘庆邦、王祥夫等,甚至一些早已成名的作家贾平凹、迟子建等也将笔触伸向底层。由于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1](P47)所以他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被他者言说。因此在作家的代言、媒体的宣扬与底层读者期待视野中出现了不同的底层形象。 一、底层文学中的“底层”人物叙事 底层文学中的底层人物大都处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作家似乎带有“苦难焦虑症式”的心态认为凡是底层就必然生活贫困、缺少欢乐、还经常遭遇难以预料的不幸。在作品中运用大量的篇幅来刻意书写底层人物的悲惨命运。为了让命运坎坷多舛的人物最终走上毁灭道路,不惜采用叠加式的方法叙述苦难,将种种意想不到的不幸与灾难降临到作品主人公身上,甚至采用极端化的充满血腥味的场面来渲染苦难的强度。[2](P28)荆永鸣的《北京的候鸟》中,到北京谋生的“来泰”,充满希望的以为在首都很快就能过上好日子,可是他拉三轮车却被保安无辜殴打。《我们的路》中春妹的被骗、贺兵的死、工钱被扣、工人为了工钱向老板下跪。曹征路的《霓虹》中倪红梅身上的各种极端不幸却令人深思。父亲为了在火灾中抢救工厂的财产而被烧伤致死,婆婆又瘫痪在床,自己成了下岗工人,为了生计好不容易爱上的那个人又偏偏是个无赖……所有倒霉的事都轮到了她,所有这些好像都是为了将她逼到绝境,使她在无奈之中只能去做皮肉生意。 《那儿》中的杜月梅也是由于丈夫早早的死掉、自己下岗后也卖过早餐试图自食其力,可由于女儿患病住院需要大量的钱才走上了暗娼的道路。可以说作者总是唯恐底层人物苦难不足,将大量的不幸予以堆积来凸显人物的悲惨命运。在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中为了加强苦难的震撼力,作家采用夸张而又荒诞的手法来描写一些充满血腥恐怖气息的场面。《马嘶岭血案》一位穷困的农民和“我”仅仅为了二十元钱杀掉了勘察队所有的人,最后杀红眼的九财叔连我也不放过。其中九财叔连杀七人的场面,作者运用大量的篇幅将其叙述的惊心动魄、鲜血四溅,充满暴力色彩。九财叔与勘察队之间的矛盾是被夸大了的城乡冲突的体现,是人与人之间因隔阂而不能沟通的结果。《太平狗》中程大种与他的太平狗来到城市时,狗被驱逐、人被排斥。他为了证明狗没有狂犬病,将自己的手指伸进狗嘴里,紧挤狗的牙齿让它咬破自己的手。当狗嘴里流出人血时,他高兴的告诉周围人狗时健康的,没有狂犬病。他以自我的折磨换的别人对他和狗的暂时宽容。城乡处于二元对立之中,农民在面对城市时自我内心总有一种自卑感,他们为了生存、有时甚至不惜采用自我折磨的方式来换得城里人认可。 底层人物一直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城市是他们想象中的乐土。他们千方百计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寻找命运转变的奇迹。尽管他们都曾经努力过,可作品中的他们总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在苦难中一步步走向了堕落。作者在描写底层女性时将她们首先放在一个很贫困的环境中,而且为了生活、或是为了自己的某位患病亲人在极度需要钱的情况下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这种堕落成为她们没有办法的选择,以此来换得人们(读者)对这种行为的同情与理解。邵丽的《明慧的圣诞》中明惠看到从城里回来的桃子赚了钱受到村民的羡慕,来到城市便直奔洗浴中心做了最能赚钱的按摩女。王手《乡下姑娘李美凤》中的李美凤身体被老板占用的过程中心理没有任何的不愿和悔恨,她似乎因能找到这样的“靠山”、能拿身体赚钱而感到欣慰。《家园何处》中何香停进城后先是在张继的引诱下失身,接着又被转给别人玩弄,最后她也自觉地走上了卖身的路。杜秀兰刚刚做了家庭保姆照顾一位瘫痪在床的老太太时感到工作不错,很快却成了宝良、贝良兄弟的情妇,继而被介绍给他们的朋友去做(《女佣》)。还有像尤风伟《泥鳅》中的陶凤、寇兰,这些如花的生命都走上歧途。“当代小说似乎离开了三陪女就不能揭示底层的艰难与困境”,“这些作品不像是一枚揭示底层艰难的苦果,倒像是一颗让人难以咂摸的怪味豆”。[3](P35)作品中的底层女子在穷困与无奈中只有堕落到靠出卖肉体来谋生,这成为她们唯一的出路。她们大都是柔弱善良的,在生活重压下被迫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她们的转变过程应该充满矛盾与冲突,可作品没有写出她们的内心煎熬,没有心理的不安与自责。似乎金钱的获得就可弥补她们的损失,钱成为她们放弃人格和尊严的理由。作品中过多的性话语与性描写的存在使底层文学在如何正确地塑造女性形象成为一个亟需重新审视的问题。 底层叙事中的女性农民工进城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沦为按摩女、二奶的现象在底层文学中屡见不鲜。而男性农民工堕落的抒写则大多由穷苦走向愤怒,因愤怒而导致一种失去理性的报复。尤风伟的《泥鳅》中,蔡毅江本是一个来城市在一家搬运公司打工的善良本分的农民,在一次为别人搬家的过程中在卡车上出了意外,伤了他的命根子,老板跑了,没人对这次事故负责,他去看病却受到医生的侮辱。身体受伤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得不到补偿,身体功能的失衡也使他的性格扭曲逐渐发展为心理变态。由虐待妻子到对社会的以暴抗恶,最后成为当地黑势力团伙的头目为别人充当“保护伞”而走上了不归路。王祥夫的《一丝不挂》中的“阿拉伯兄弟”在被老板欺骗后愤怒之中抢劫了老板,并剥光了他身上的衣服才让他回家去。在底层文学作品中作者为处于苦难中的底层没有安排合理的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着力刻画了这些弱势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和谐行为。将底层置于绝对的二元对立处境中使他们的抗争走向极端,最后滑向堕落的深渊而自我毁灭。底层生活中不可否认总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可这一幕幕苦难使他们的生活永远处于绝境,没有希望。作家这种追求快意的放纵式苦难书写,将苦难的细节夸大,必然是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扭曲。面对作品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底层究竟是怎样的?甚至我们会怀疑作家这种迷恋苦难的背后有无其他原因。#p#分页标题#e# 二、主流媒体传播中的“底层”形象 被认为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底层毫无疑问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不协调、分配不公等原因造成的。2002年3月,朱?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从而使得“弱势群体”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我国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弱势群体,国家非常重视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工作。早在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志所作的报告中多次强调了与保护弱势群体有关的内容,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人共享发展成果”;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并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中央还出台了许多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文件,自2004以来中央每年下发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这些表明国家非常重视弱势群体,而且要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国家也意识到保障他们的权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关系到改革的深化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尊重弱势群体主体地位也是和谐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底层叙事。在官方底层叙事中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底层叙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们经常看到官员亲民的形象,他们给底层人物送温暖的事迹屡屡报道。特别在春节临近的时期,新闻中有关农民工与生活困难户的报道就增多。各级领导们给生活困难户送去慰问品时,农民工满面笑容的在摄像机前数钱。这表明底层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在国家和政府的关怀下底层人民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底层现在的处境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而且国家也在努力改变底层的生活状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官方底层叙事中的底层人物大都处在欢乐之中的,他们也是享受改革成果的一分子,并逐渐融入当下的社会主流。“底层”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要利用这一时机,通过自身能力的提升是有可能摆脱底层的圈子。在我们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中,底层文学苦难书写中那一群衣衫褴褛、生存的基本条件不能保障的底层多少显得有些不和谐。作品中对苦难过分的渲染使底层文学中的底层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中的底层形象发生了偏差,这种对社会转型中优秀面缺少反映的书写使底层文学在传播中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三、底层读者期待视野中的“底层”形象 在文学活动中,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只有经过传播与接受活动,才能成为现实的作品,文学作品的价值才能得到显现,文学的活动才能完成。这一过程是经过读者的阅读活动来完成的。根据“接受美学”的见解,一部作品完成之后、在读者接受之前,便已隐含着读者。所谓“隐含读者”,是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的,是指本文自身设定的能够把本文提供的可能性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也就是说,是作者预想出来的他的作品问世之后,可能出现的或者应该出现的读者,这种预想有时是自觉,有时可能是不自觉的。[4](P294)底层文学作家在创作时也会有“隐含读者”的存在,这就是他们写出的作品会被什么样的读者阅读。 首先作家的创作动机会影响隐含的读者的存在,当下一部分底层文学作家的创作就是为了评奖,这样的动机就决定了他们的创作隐含读者就是某些评奖委员们或者知名度较高的专业评论家。选择底层题材也是为了追求时尚,是一种争夺题材资源的结果这样的作品就难免不会出现扭曲底层形象的状况。同时作家赋予本文的思想内涵和作品的选材也会决定隐含的读者的存在。底层文学作品就是描写底层的人和事,这决定了无论作家有无明确的意识,在他作品的隐含读者中都会包含真正来自底层的读者。这就表明底层有可能成为底层文学作品的读者,他们可以通过阅读最终要转变成现实的读者来接受作品,当底层面对描写自己群体的作品时他们会做出怎样的评价呢?读者在进行文学阅读之前,头脑里并非完全空白,而是有一系列由各种经验、趣味、素养和理想等综合而成的结构图式或心理图式,这就是姚斯所说的期待视野。底层读者在阅读描写自身状况的底层文学时也会有一个期待视野,这会影响他们在具体的阅读中对作品作出的评价。读者阅读经验的期待视野形成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文学艺术修养以及特定的生理机制等具有一定的联系。底层读者阅读期待中的人物应是他们从自身的现实处境出发所希望看到的一种。底层的阅读期待视野会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底层有“富”的想象。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作为弱势群体的底层在物质方面处于极端的贫困状态,他们本能的有着摆脱贫困状况的愿望。刘旭在《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中提出“彩票是底层致富幻想的一种”[5](P52)。 现代社会人们的暴富心理极度膨胀,处于贫困中的底层更是想一夜暴富脱离“底层”,彩票就成为他们想象中的理想捷径。他们幻想一旦中彩后的种种美妙生活,这就是彩民的精神,也是对底层想象暴富心理的真实写照。其次,底层渴望成功。底层对富不仅仅停留在幻想的层面,他们也希望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一个个进城的农民工都希望在城里找到生存的门路,希望自己能够衣锦还乡。他们也希望看到自己周围的人获得成功,因为在别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这种心理使他们期待视野中希望出现的是通过拼搏,历经磨难而最终获得成功的人物。在当下一些打工者的作品中较多的反映了打工者的成功梦想及其对于成功的渴望。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是无法忍受的,而是对生活充满信心,抱着乐观的态度,并坚信自己的努力会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即使处于贫困之中的底层人物也有欢乐与喜悦,物质财富的多少不是决定人们幸福的唯一标准,底层生活虽然清贫可有他们的乐趣。 在底层读者的期待视野中他们希望的是底层人物通过自身的努力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希望过上到富裕幸福的生活。底层文学作品中很少写到底层人物的这种愿望能够实现,他们美好的愿望总是一次次的落空,离开贫瘠的土地在城市中依然找不到安身之地,生活所迫往往成了以身试法的杀人者或是堕落成出卖肉体者。底层读者本来处于贫困中他们对于自身的前途堪为担忧,可作品为他们呈现的情景更为惨淡,这种作品怎能引起底层的共鸣呢?#p#分页标题#e# 在底层文学的书写中作家不应高高在上以底层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不要把底层预先放到重重苦难之中然后再试图解救他们,更多的应做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与底层站在一起以平等的视角来看待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底层人物的生活也有奋斗的过程、成功的喜悦以及迷茫与困惑,而不单是处于苦难中。即使处于贫困与不幸中的底层人物也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不应将他们性格简单化甚至公式化、概念化。社会在发展,底层人物的生活也在变,他们是处于动态中的而绝非一成不变,作家更应看到底层的变化与希望,跟他们一起体会生活得酸甜苦辣,而不能用自己理念来代替他们的生活。文学纵然是一种虚构,然而这种虚构有它的现实意义。文学用虚构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生活期待视野中所不存在的新的视野,读者在期待视野与生活实践视野的交融中拓展生活期待视野,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来努力改变现实的生活。而生活现实的改变又一次为文本的改变创造条件。这样在生活期待视野与文学期待视野的交替影响中,为文学与现实、美学与历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接通文学与现实,这也就增强了文学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底层文学要表现底层的人与事就不能不顾及底层读者,它应该让底层看到希望。描写底层的日常生活与普通喜乐,写出他们的真情实感,而不应流于符号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