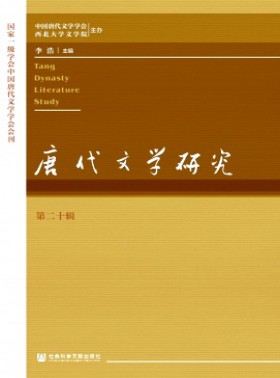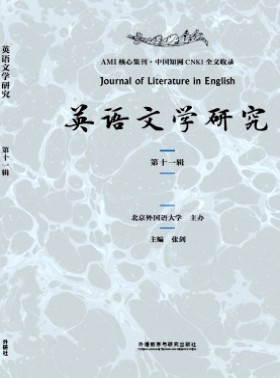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