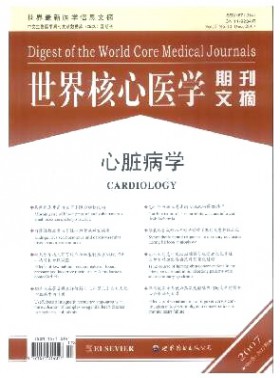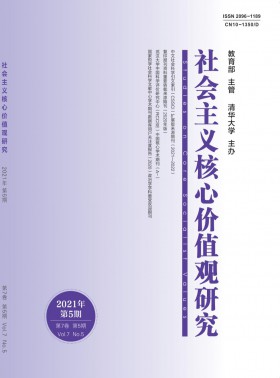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基础。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常正能量,宣传得也很广,小学生都会背诵。但如何做到像报告所要求的那样,“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1]42,则不是一项简单的、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核心价值观在践行层面遇到的问题,既需要在实践上对其教化涵养的方式方法进行科学设计调适,更需要在理论上对其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思考反省。
一
报告讲的“融入”和“转化”问题,也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问题。再好的价值观念,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践行,就无法发挥扬善去恶、移风易俗的精神教化作用。前段时间崔永元曝光的影视娱乐界的一些黑幕,在网络媒体热炒,网民的关注度非常高。某些影视明星扭曲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做派,对社会风气产生很坏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建设,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核心价值观在践行层面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价值观的认知问题。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字面意思通俗易懂,但我们对其内涵的认知是否达到了像字面上那样清楚明白的地步,就不好说了。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很多东西,是古今中西多种复杂的观念杂糅在一起的,包括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综合了各方面优秀的或者说先进的价值观念,按照我们的需要或者理解组合成的一个观念系统。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整体)不等于要素(部分)的简单相加。所以,这些观念加在一起是不是构成了一个逻辑自洽、功能完善的系统,或者说,系统内的各个观念之间是不是达到了很融洽的地步,就需要进一步思考了。比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组价值观,讲的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念。“富强”按照西方人的理解,是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讲究弱肉强食,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讲究“霸道”;“和谐”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就是要讲究“王道”,但在西方人看来,恐怕只有以大治小的和谐,或者以小事大的“和谐”,难有强弱平等、互利共赢的“和谐”。最近大家都很关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我们把美国在中美贸易上那些霸道的做法拿来对照检视一番,就可以发现,特朗普这次把西方国家所谓“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理念的自私性、狭隘性、虚伪性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主要由中国倡导的一些国际准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在国际关系中很难落实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再比如,讲到社会层面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对于某些影视明星来说,他们的做派反映出他们所理解的“自由”,恐怕是不受约束、为所欲为的自由,并不是在法治、平等、公正等责任之下的自由。古人云:知而不行,是为不知。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倡导富强、和谐、自由、法治等价值观不对,只要是人类文明中的优秀的或者说先进的价值观念,都是我们应该倡导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些价值观念的“转化”和“融入”或践行问题的复杂性。这些价值观念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念背后的文化传统乃至哲学基础不同,把这些观念放在一起,它们的践行问题,就成为一个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针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郑永年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络版上,题目叫做《中国人为什么讲不好“中国故事”》。他说关于中美贸易战,虽然是美国发起的,但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对中国那么大的反应,某种程度上跟我们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方式有关,我们讲着讲着把人家讲害怕了,而不是说讲着讲着让人家更亲近你了。西方媒体为什么强大?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思想体系,有个知识体系。中国人为什么讲不好中国故事?这里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但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没有一个自己的知识体系[2]。我觉得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在践行中遇到的问题,与此有些类似。因为今天我们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大部分要么是古人的,要么是外来的,真正属于自己的、能够称得上原创的比较少。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上很缺少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有力支撑,尤其是缺少既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又能面对今天的现实,而能解决我们时代问题的原创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支撑。
二
具体怎么“转化”,怎么“融入”或者怎么“践行”,是伦理学家们和教育学家们需要研究的问题。这里我仅只结合价值观念的哲学根基,来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问题做一点反思。因为价值观和哲学观密切关联,我们在价值观建设中碰到的许多问题,往往根源于我们的哲学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体系在某些方面,有时候不完全能够自洽,甚至我们社会生活中盛行的某些价值观念,往往存在着混乱,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我们哲学观念的不自洽,或者说源于我们在哲学观问题上的困难和纠结。那么,今天中国人的哲学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观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汉语中“哲学”这个词是怎样产生的。在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中,文学、史学、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分类名目早已成了学人乃至受过基础教育的普通人的常识性知识概念。但如果从知识史和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做一番追究,可以发现这些名目和概念其实大多并非中国人的固有观念,而是或直接来自西方,或是受西方知识分类的影响而后形成的。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和学问中,本来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史、哲等学科的分别。与注重“专门之学”的西方学术相比,中国传统学术更强调“博通”,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与人事相关的典籍、制度等,而不像西方那样直接以自然和社会为对象;其分类标准也主要按事物与人的关联及对人的功用来区分,而不像西方那样主要以研究对象为标准①。如《大学》中就有一段关于中国古人的知识观念的著名表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段话对于心、身、家、国、天下的关系的论述,即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人在宇宙人身的“类别”与“层级”问题上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念。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等今日所谓的人文学科中,学术分类也只有所谓经学、子学、史学等名目。直到晚清和五四前后,即清末民初三十年间,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体系才最终确立起来。就哲学这门学科来说,中国虽然有源远流长的哲学传统,但“哲学”这个词在中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引进概念。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哲”这个词,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哲”在古代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人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近似于西方所谓的“哲学家”、“思想家”。1874年日本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将希腊文philosophia(爱智慧)译成中文“哲学”。晚清大学者和思想家黄遵宪又将“哲学”一词转介到中国。经过王国维、严复、章太炎、康有为等人的使用,“哲学”一词在中国落下脚来。但这个时期的所谓“哲学”,还基本上与传统“宋学”或“国学”无异。冯友兰先生1915年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学习,他曾追忆当时的情况说:“中国哲学门有许多教授,这些学者有的是古文学派,有的是今文学派,有的信程朱,有的信陆王。其中有一位,信奉陆王,教我们的中国哲学史,是两年的课程,每周四小时。他从尧舜讲起,讲到第一学期末,还只讲到周公,就是说,离孔子还有五百年[3]292。冯友兰先生讲的这位教授,就是陈汉章先生。陈汉章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门讲的“哲学”,其实就是传统陆王之学。真正的现代学科制度意义上的“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则是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哲学”东来以及在中国传统思想研究和经学研究中引入西式“哲学”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和学科体制以后的事情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和冯友兰把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等,参照西方“哲学”的标准予以改造,也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寻找出那些与西方“哲学”的内容大致相当或相似的思想素材,为“中国哲学”划定范围,并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和思维逻辑加以重新组织和表述,为“中国哲学”确定形式,建立了中国哲学的学科典范。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和摹本来诠释和建构中国哲学,自然难免会带来“削足适履”的危险。“哲学”与“中国”的相互脱节和隔离,导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一些鲜活的、具体的内容被凝固化和简单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对于中国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和民族文化的推陈出新都造成了一定的制约。正因如此,中国现代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合理性”与“合法性”之类的质疑。十多年前,中国哲学界讨论非常热烈的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是这种质疑的一个高潮。“哲学”的西方出身及其中国建构,注定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念本质上必然就是纠结的。一方面,“哲学”自然地要求将中国的思想纳入西方的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又使得哲学必须能够呈现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和价值。中国哲学的开展就纠结在古今中西之间,在以西释中和以中释西里徘徊和延伸。建基于这样一种哲学之上的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亦中亦西的,也是不中不西的。一方面,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念对很多中国人产生了无所不在的影响,但没有完全占领中国人的心灵,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处于被放逐的地位,却并未彻底退出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这使得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如亨廷顿所说的“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4]353。哲学基础和知识体系的原创性和稳固性不足,导致我们在文化身份和价值观念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也就容易陷入迷惘或被打折扣。
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加入,使中国哲学在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创造性解释中历史性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组成的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结构,20世纪50年代以后,进一步演变成“一体两翼”的基本格局。它力图在思想融合中创造新的哲学观念,并用新的哲学观念锻造新的价值体系,成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价值根基。“一体两翼”的格局存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步又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由于教育体制、科研体制和学术评估体制等的不尽合理,使本应胸怀天下的“哲学家”变成了专业化、学院化的“哲学工作者”,使本应“改变世界”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蜕变为远离智慧、不问现实的“知识生产”活动,甚至是浅薄的概念游戏。其后果不仅使我们的哲学理论和哲学活动缺乏应有的抱负和魅力,甚至还引起人们对哲学的鄙夷、厌恶乃至唾弃。这样的哲学显然不可能真切地回应时代的问题,更难以孕育具有时代气息的核心价值观念。因此,新世纪以来,建构一种全新的哲学,以承续起中国文化渊源有自的精神慧命,表达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精神,以改变学科的尴尬状况,并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和思想提升,就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被提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这一任务显得尤其迫切。新时代的哲学,首先应该是能够直面当代现实、解决时代问题的哲学。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生的深刻变化历史罕见。但多年来,由于哲学研究的过分知识化,我们的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时代脱节,更多关心哲学史而非哲学,造成哲学研究的思想贫困。伟大的理论来自于伟大的实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富有大智慧的新哲学的产生。因此,新哲学的建构应当以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的情怀,密切关注并积极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善于把这一伟大实践上升为深刻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做出伟大的哲学创造。新哲学在各式各样的挑战面前,应当能从容不迫地应对之,并能有效地化解之。新哲学只有建立起有着强烈的穿透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创见,经受住种种挑战的考验,才能成为时代的哲学。新时代的哲学,应该是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基因的哲学。近代以来,由于哲学在学科建构上经历了西化理念和方法的洗礼,以及文化上的激烈反传统主义的盛行,使得中国哲学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迷失甚至断裂。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他反复强调,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因此,新时代的哲学,一方面要继承中国哲学的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并结合新的时代精神加以创造性发展,以接续中国哲学的“根”;另一方面,要摒弃对西方理论、方法的滥用和误用,尽力从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理解中国哲学,以再塑中国哲学的“魂”。只有找回了自己的根基和灵魂,做到与往圣先贤们的伟大心灵息息相通,并承续起中国文化源自古圣道统的精神慧命,中国哲学才能真正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主,中国哲学也才能真正激活自身的创造力,并拓展自己的生长空间。新时代的哲学,应该是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符合世界方向的哲学。在新哲学的建构中摒弃对西方哲学的盲目膜拜,找回中国哲学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文化自主,并不是说我们要简单地回到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立场,盲目地拒斥西方。在历史已经超越地域的尺度而成为一种世界的历史、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遏止的潮流这样一种条件下,试图固守传统的疆域,彻底割断与西方哲学的关联而建立一种纯粹的“中国哲学”,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与世界历史的观念相应,我们也同样需要一种世界哲学的观念。新哲学的建构应当彻底走出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二元对立的理论幽谷,在与全球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催生既与全球化方向一致又符合民族发展要求的本土哲学,只有这样的新哲学才能既深化对于人类普遍生活的终极理解,又彰显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原创智慧。新时代的哲学,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哲学。中国哲学学科在现代化发展阶段对西方哲学的模拟和仿照,一度把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表述为普遍与特殊、文法与词汇、方法与材料的关系,其后果是使“中国哲学”从普遍哲学的殿堂自我放逐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但另一方面,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对地区性知识的尊重,则容易使我们走向相对主义和对普遍性的拒绝。如果一味强调文化差异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就容易把不同的文明对立起来,从而限制我们的视野。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相对主义理解,容易滋生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并把对西方的拒绝变成对普遍性的拒绝。因此,新哲学的建构应当努力超越地域的封限,将我们民族普适性的价值理念带入到世界性的场域中去,以化解非西方思想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困限,既深入研究和分析中国人特殊的文化经验、历史意识和生命感受,又要善于从中提炼出有普遍意义的命题,达到文化的根源性与哲学的原创性的统一。惟如此,中国哲学才能为普遍哲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并在世界文明的哲学对话中占据一席之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5]171。新时代的中国哲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古今中西的智慧创造性地融为一炉,建立起集中国化、世界化、时代性、普遍性于一身的原创哲学,才能“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23,并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自己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支撑。只有建基于这种新哲学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才能逻辑自洽、功能融洽,并在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得到自觉、有效的践行,从而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5]162。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郑永年.中国人为什么讲不好“中国故事”[EB/OL].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三松堂全集:第6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5].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作者:魏长宝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