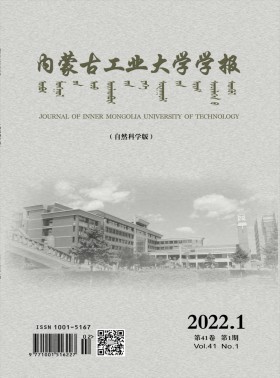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 三圣 礼 儒家
一、元圣――礼的启创之路
关于“礼”的起源,众说纷纭,以多元起源观为主。“礼”是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礼”的集大成者――周公“礼”源于其,应为大众所接受。周公制礼作乐,“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的宗法制特征十分明显,一个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另一个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周公把宗法制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服务于奴隶制的上层建筑。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
周公建立、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期,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周公言论见于《尚书》诸篇,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史上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是以其终生辅国安邦的圣人。
周公因其儒家奠基人的地位,被汉儒称为“元圣”。周公“摄行政当国”、平定“三监”叛乱,对国事进行改革,是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
周公第一次提出德的概念,统治者替天行道的观念开始转到敬德保民的观念上,从《牧誓》“恭行天之罚”可以看出对敌人多讲天命的周公,对“天”的观念已经有所发展。“天命”是否转移,怎样才能保住“天命”,取决于有没有“德”,桀纣失掉天命是因为失“德”,周人要保住“天命”则必须有“德”,因此周公在教导周人时多讲“明德”。“天命”就变成可以保持和争取的了。人不再盲目地服从“天命”,而有了主观努力的可能,这是积极的进步。
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为圣人。周公思想对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汉代儒家将周公、孔子并称。
二、至圣――礼的扬弃之路
孔子一生所追求的正是周公的事业[2]。“文武周公”是孔子最为推崇的人物,周公为周朝制定了礼乐等级典章制度,使得儒家学派奉周公、孔子为宗,唐开元时期,改以孔子为主。自东汉以来,人们常以“周孔”并称。
在教育上有“周孔之教”的概念。总之,言孔子必及周公,这是古代尊崇周公的表现。这种尊崇除了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之外,主要还反映了古人对西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珍视,以及对周公这位伟人的真诚敬仰。这在历史上曾为弘扬、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教育起过积极作用。
孔子和周公在教育思想上存在渊源关系,在教育实践上也存在继承关系。周公生活于三千多年前,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奠基人的话,那么周公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开创者。
孔子一直宣称其思想源自对周礼的继承,“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奔走列国,克己复礼,就是为了光大周礼。但同时孔子用“仁”对“礼”进行进一步的阐释,仁为礼之体,礼为仁之用。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分割,这是对周礼的扬弃,孔子所展望正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见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三、亚圣――礼的发展之路
孟子是一位精通礼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辨礼义,为僵化的等级性礼学注入新的内容。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又加入自己对儒学的理解,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全面而巨大,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天命、德治思想,并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在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仁义”,不过是“礼”的别名,仁、义、智、礼、乐这五者均可集合在传统意义的“礼”下。仁义的宣扬不过是孟子内心对“礼”忠实外化的结果。
孟子对孔子十分推崇,曾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并尊孔子为“圣之时者”。孟子一生以维护和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唐宋之后儒学迎合了儒学对佛道挑战的需要,孟子的地位愈益提升,《孟子》由子书升格为“经”,孟子也被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孔孟”成为儒家道统的核心。此后数百年,“孔孟”成为儒家的正统,得到顶礼膜拜。
当然,孔孟之间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突出表现为二者性格气质的巨大反差。孔子博大,孟子精深;孔子温和,孟子激扬;孔子中庸,孟子偏激。正如二程所言:“仲尼,无所不包……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然而已。仲尼,天地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孟子还进一步将“礼”内化为一种心理感受,进而升华为一种道德的自觉意识。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高于动物的地方在于礼乐道德规范背后的心理差别[3]。
尽管孟子与孔子在性格、气质乃至思想上都存在一些差异,但这种差别并非是本质的,并不妨碍二人在思想上的密切关联。以历史眼光看,就对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言,孔孟当推为魁首。后世孔孟合称,以“孔孟之道”指称儒学,并不是完全无视二者的区别。朱熹曾直言:“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孔子则就切实做功夫处教人。”可见朱子也正视二者理论风格之不同。况且,思想家的价值正在于其独创性。如果孟子完全同于孔子,那么孟子存在的价值就会失去,后世便不会有“孔孟之道”的说法。
“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就无法建立和维持。
参考文献:
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西方汉学;《孟子》;民主与人权;文化性;生物性;德性伦理;角色伦理
中图分类号:B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067?06
从16世纪末西方耶稣会士(Jesuits)登陆中国,发展出真理与谬见杂糅的传教士汉学,到19、20世纪之交西方专业汉学的正式形成,直到今天专业汉学的多维展开,西方汉学已经走过了四百多年的漫长历程。《孟子》的西译和研究伴随了这整个过程。1990年以来,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汉学家们带着各自的问题视角,又一次探入《孟子》文本,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现代诠释,并且形成了几次较有影响的争论。惟如此,《孟子》就成为西方各种思潮、倾向相互碰撞和激荡的“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激活了《孟子》,使它有可能成为西方自身思想建构的构成性力量。
本文择取西方汉学界关于“孟子与现代民主、人权”“孟子人性论的文化性与生物性”“孟子与德性伦理、角色伦理”的三次争论,分别梳理其历史脉络,揭示其现实关切,并尝试做出理论评判与回应。了解这些争论的来龙去脉,其实也是一项“揽镜自照”的工作,借此可以引起我们更多的理论反思与方法自觉。无疑,这项工作对于在当前全球化的学术语境中,中国思想如何面对东西方文化冲突、因应全球化与本土化挑战时,放言于心声,中的于现状,在世界格局中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伦理原则、思想根基,更好地参与跨文化对话,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关于孟子思想与现代民主、人权兼容性的争论
1990年之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但美、苏两大集团“冷战”时代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间的意识形态领域。而其焦点便集中于所谓“文明的冲突”以及民主、人权等话题上。同时,在西方经济增长变缓后,亚洲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亚洲部分地区的民主实践也成为东西方文化和政治经济比较与对话的大背景。民主和人权是普遍性的还是特殊性的?包括孟子思想在内的传统儒学资源与现代自由民主、人权之间可否兼容?这些都成为国内政治学界和海外汉学界持续关注的问题。其间与《孟子》关联较密且较重要的著作包括: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与杜维明主编的《儒学与人权》(1998)、郝大维(David L. Hall,1937-2001)与安乐哲(Roger T. Ames)的《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1998)、贝淡宁(Daniel A. Bell)的《超越自由民主:东亚语境中的政治思考》(2006)、欧阳博(Wolfgang Ommerborn)、Gregor Paul和罗哲海(Heiner Roetz)编著的《人权论域中的〈孟子〉:中国、日本和西方接受〈孟子〉的里程碑事件》(2011)。以下我们依次来探视一下这些著作各自的理论建构与思想倾向。
狄百瑞和杜维明主编的论文集《儒学与人权》[1]集中讨论儒学资源与现代人权观念的关系,其中专论孟子的是汉学家华霭仁(Irene Bloom,1939―2010)的论文《基本直觉和共识:孟子思想与人权》[1](94?116)。此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说明孟子思想与现代人权观念的相关性:其一,孟子关于普遍道德潜能(“性善”)的观点相关于现代的平等观念;其二,孟子的“天爵”观相关于“人之尊严”的现代观念。作者指出,之所以聚焦于这两个方面,是因为它们同是孟子思想和当代人权思想的核心要素。而且,“关于人权的那些共识性看法在我们今日变动的现代文明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而(孟子思想的)基本直觉――对人之平等性、责任、关联性和尊严的肯定――不仅跟这些共识一致,也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拥护、支持着它们。”①[1](111)中国的人权建设可以从《孟子》等古典著作中获得理论支撑,这是华霭仁一贯的看法。
郝大维与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2]一书以实用主义(pragmatism)为中介,尝试为中国乃至美国寻找切合自身语境的民主模式。作者认为,“中国从来都是、而且将继续是一个社群社会(communitarian society)”,“实现中国人民的正当欲望需要提倡一种社群社会的民主形式,而这种社群社会的民主形式与当前支配西方各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是有抵触的”,[2](9)“这种社群社会的民主形式”就是儒家式的民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儒学”视为中国古典思想资源的“总名”,又以孔子作为儒学的总代言人,不过孟子的学说也常见引用。他们认为儒家式的先贤民主体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迥异于西方以个体权利为基础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而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实用主义思想是土生土长于、也适宜于美国本土的哲学传统。孔子与杜威一中一西,可以“再睹钟情”(love at second sight),并且联起手来,为自身正当性积极呐喊。在他们看来,“儒家式的民主”的比较优势并非仅仅体现于亚洲:
发展一种儒家式的民主典范不仅会有益于亚洲的民主化倡导者,而且还会有益于西方社群主义民主的倡导者。正是这种彼此受益的可能性,提升着中国的民主的希望,使之从一种可能性变成一种有理由的 预期。[3]
就其思想实质而言,贝淡宁《超越自由民主:东亚语境中的政治思考》[4]一书只是对郝大维、安乐哲之理论的丰富。郝、安二人重视从哲学切入点的差异处谈儒家民主与西方自由民主之别,贝淡宁其书则从当代中国及东亚的政治现实和日常生活入手来论证东亚传统价值的正当性。例如在人权问题上,作者尝试以孟子的思想为基础构建某种儒家的理论,认为“在孟子关于战争的思想与当代使用人权这一概念的正义战争理论之间有着一些相似之处”[4](10)。作者自陈其主要观点:
我认为在东亚地区有着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同的、可以在道德上进行证明的不同理论,对东亚而言,正确的选择并不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简单地实行西方式的政治模式,而是至少从东亚的政治现实与文化传统中吸取那些可以为东亚所接受的成分,它们同样可能为当代西方自由民主主义者所接受,而且后者还可以从中获益。[4](8?9)
笔者以为,这种壮人心志的观点在理论上当然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从另一角度看,郝、安、贝诸人的观点实际却助长了某种中国或东亚“特殊论”立场,在描述性地提示中西差异并试图从哲学传统或现实习俗做出某种解释之后,并没有提出一套明晰可靠的替代自由民主的可行方案。他们的学说具有浓厚的语境决定论和文化保守主义色彩,难免文化相对主义和“学术偷懒”之讥[5]。
由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罗哲海、欧阳博(Wolfgang Ommerborn)和卡尔斯鲁厄大学Gregor Paul三位教授共同编著的《人权论域中的〈孟子〉:中国、日本和西方接受〈孟子〉的里程碑事件》[6]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这项研究成果是在德国蒂森基金会(Thyssen- Stiftung)和德国“惠光”日本文化中心资助下进行的。尽管冠以“人权论域”之名,但此书基本可视为一部《孟子》在中国、日本和欧美的接受史,只不过其视角专注于政治学领域而已。作者强调,《孟子》一书中有很多与当下人权讨论具备相关性的质素,例如“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第17章)的个体价值观、对人的生命的高度看重、关于自我和道德自律的前设概念、仁政理念、对反抗暴政和弑暴君正当性的论证、国家以民为本的主张,等等。此书延续了罗哲海在《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7]等论著中的一贯思想,在历史观念上强调某种“重建的‘调适诠释学’”(reconstructive‘hermeneutics of accommodation’)②[8],即在当下语境中通过理论重建,揭示《孟子》中已然包含的相关于现代人权论述的理论观点,说明《孟子》这一轴心时期文献在现代语境中的资源性价值。
罗哲海等人在很多理论点上跟安乐哲代表的实用主义路向针锋相对。安乐哲为了论证儒家式社群民主,曾经借助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的视角,否认古代儒家传统中具有西方本质主义意义上的个体自我观念,认为儒家只拥有“关系自我”的观念(参考本文第二、三部分的论述)。罗哲海等人在根本上不同意这一主张,他们转而以狄百瑞提出的“社会个体”(social individualism)概念来指称儒家式的自我观念。他们也反对安乐哲、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等人的文化(相对)主义、实用主义进路,转而倡导历史性地理解儒家尤其是孟子的伦理观,同时张扬一种人权话语的普遍主义视角。他们也引前文提到的华霭仁为同调。
自由民主和人权话题往往关涉到思想史研究中的普遍主义与相对/特殊主义问题。普遍主义者倾向于“运用那些超越文化和语言差异的概念,透过所有表面的不同,去发现中国思想中对普遍问题的探索”,而相对主义者则倾向于“透过所有的相同点,去揭示那些与受文化制约的概念系统相关的,以及与汉语和印欧语言结构差异相关的关键词汇的差别”③[9]。尽管存在着简单化的风险,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将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罗哲海、华霭仁列为普遍主义立场的代表,而葛瑞汉(Angus C. Graham,1919― 1991)、安乐哲、于连(Fran?ois Jullien)则可视为相对主义视角的代表。对西方汉学世界中普遍主义/相对主义问题的关切散见于本文各处,这里笔者不拟将其单独拈出进行讨论。
二、关于孟子人性论之文化性与
生物性的争论
1967年汉学家葛瑞汉的长文《孟子人性理论的背景》[10]发表,受其启发,1991年安乐哲发表了论文《孟子的“人性”概念指的是“人的本质”吗?》[11]。安乐哲认为,英文nature一词所包含的本质主义倾向并不适合表达汉语“性”字的“过程”含义[12](72?90)[13](305?331);如果将“人性”译为human nature,那么就将跟中国思想格格不入的意涵强行纳入到中国思想中,从根本上说是疏离(而非接近)了中国思想。同时,安乐哲指出“性”主要是一种成就性的概念:
“性”最重要的是修养和成长的结果。……对孟子来说,就任何重要的意义上而言,不曾发展的人(即缺乏教养的人)还不是“人”。“性”是参与文化社会并做出贡献的成员的标志。没有文化修养,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因为像动物那样行为的“人”,确确实实就是禽兽。社会中的人,从质的角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别,即从非人的“人”,到用模范行为界定和提升人性本身的圣人。“性”这一概念表示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人”化。[11](163-164)
安乐哲以上看法有文本支撑,可成一家之说;不过,过于敏感于“性”字与nature的中西方语境差别,乃至把这种差别绝对化,却又忽视了“性”有与nature相通的一面。安乐哲将孟子的人性概念置于一种过程或“事件”(event)本体论范围内进行讨论,借助杜威的词汇来解释孟子思想,虽然他宣称“这既不是使孟子成为杜威,也不是对孟子提供一种‘杜威式的’解读,而宁可是试图用杜威的词汇去激发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思考孟子”[13](321),但其排他性立场也使其盲视了孟子思想中的其他重要方面。而且,强调“性”之文化成就的一面,势必导向对精英主义乃至人之差等的肯定。事实上,安乐哲确实是一位对古典儒家思想和政制传统过度溢美的汉学家。受激于安乐哲在人性、人权等问题上的相对主义立场,华霭仁在《孟子的人性论》[14]《〈孟子〉中的人性与生物性》[15]《孟子人性学说中的生物性与文化性》[12](91?102)等文中倡论《孟子》中的“共同人性(common humanity)”思想,并援引西方社会生物学理论④[16],有针对性地强调《孟子》所谓“性”是社会生物学意义上的普遍人性。华霭仁认为,孟子的人性观念是“孟子在一系列‘被迫’参与的争论中孕育出来的”,而华霭仁本人站出来跟安乐哲进行商榷和论争,约略也有这种味道。
华霭仁之所以会不同意安乐哲,当然跟二人在学术旨趣上的差异和对立{普遍主义立场、社会生物学倾向vs.文化(相对)主义立场有关},然而,他们的争论并不限于哲学内部,而是高度相关于上文刚刚论述过的人权与政治议题。身处西方的安乐哲是一位不满于自由民主模式的汉学家,他认为,中国应该发展出一种依循中国自身传统的社群主义民主模式。我们知道,人性观念是人权和政治建制的一个重要基础。安乐哲认为,在人性问题上,与西方居统治地位的本质论式的、超验的本性观相比,包括孟子在内的中国古典儒家认为人性是一个发展过程,是一个个文化事件。在他看来,前者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基础,而后者则可以预示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社群主义民主模式――以此为前提,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治理模式也值得充分肯定。华霭仁与安乐哲的分歧始于1991年二人在亚洲研究年会上关于人权问题的一次对话[12](227),与安乐哲不同,华霭仁更倾向于在普遍主义前提下挖掘孟子人性思想与西方当下人权话语之间的共同之处;而社会生物学内含的普遍主义视角,在华霭仁看来正是与孟子人性思想接榫之处。
在这场论争中,站在安乐哲这边并提供进一步详细论证的是安乐哲的学生江文思(James Behuniak, Jr.),他在《孟子论成人》[17]一书中丰富并系统地延展了安乐哲的思想,其论述表现出极强的过程哲学色彩。而跟华霭仁立场相同的则有汉学家孟旦(Donald J. Munro);孟旦在《孟子与新世纪的伦理学》[12](305?315)《儒家伦理的生物学基础,或儒学何以绵延久远之原因》[18]等论文中,将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说视为新世纪不容忽视的理论,而孟子的人性学说恰恰可以从社会生物学研究中获得支持。孟子对共同人性的论证,孟子所使用的经验性论证方法,孟子伦理体系中情感的重要性,孟子对亲属情感纽带和心之评估性的强调,在孟旦看来都可以视为社会生物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只要扬弃掉孟子思想中论“天”的内容,并辅以社会生物学理论,孟子的伦理学思想就会在新世纪重新焕发光彩。
这场争论在海内外都引起了一些反响,见于汉语学界的,除了《孟子心性之学》中华裔学者刘述先、信广来的两篇论文外,另有两篇论文可以参考:杨泽波《性的困惑:以西方哲学研究儒学所遇困难的一个例证――〈孟子心性之学〉读后》[19]黄勇《评孟旦〈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20]。限于题旨,这里不做展开。
三、关于孟子伦理之为德性伦理抑或角色伦理的争论
20世纪中叶以来,作为对义务论伦理学(deontological ethics)和后果论伦理学(consequentialism)的反拨,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又译“德行伦理学”“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版图上的突出现象。受到德性伦理学启发或影响的西方汉学家,开始借鉴德性伦理学视角,重新诠释儒家伦理学说,并展开中西伦理比较研究。其中较突出者,有李亦理(Lee Yearley)的《孟子与阿奎那:美德理论与勇敢概 念》[21],还有出版于2007年的三部著作:万白安(Bryan Van Norden)的《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德性伦理与后果论》[22]、西姆(May Sim)的《重塑道德:以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为借镜》[23]、余纪元的《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24],以及艾文贺(P. J. Ivanhoe)、威尔逊(Stephen A. Wilson)乃至斯洛特(Michael Slote)等学者的一些近期论文。这些学者并不否认自己受到德性伦理学的启发,但他们同时强调,他们这样做并非旨在以西律中,或者以今律古,而是以德性伦理学为基本视域,发掘中西古典伦理学的智慧资源,在中、西、古、今之间互相投射,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它们之间会通与对话的可能性和当下伦理重建的有效路径。
万白安、西姆、余纪元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后,不出意料地引来了一些学者的理论回应,其中既有补充性的商榷意见,也有批评性的纠错探讨。就万白安的著作而言,商榷意见如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评 论[25],斯洛特认为,早期儒家(尤其是孟子)的伦理学其实更接近休谟式情感主义德性伦理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修正意见则如安靖如(Stephen C. Angle)的批评[26],安靖如认为万白安将德性伦理按之于早期儒家的的做法,观点过于独断,对话性不够,因为他并未提供关于儒家伦理之“逻辑前设”的充分说明。万白安在回应文章中为自己的论断进行了辩护[27]。而安乐哲和罗思文在《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28]一文力证儒家的自我观念是一种由角色决定的关系性自我。尽管他们也承认,“亚里士多德和儒家之间多有相似之处”[28],儒家伦理“与亚里士多德伦理之间,比它与康德或者功利主义伦理学之间,一定具有更多的相似性”⑤,但是,他们的主张却与德性伦理论者大相径庭:“我们不相信‘德性伦理学’一并其个人主义的概念基础,还有其尽可能大地对脱离我们的态度和情感的理性的依赖,是对孔子及其门徒有关养成道德感的观点的恰当描绘。”[28]与德性伦理论者相对,安乐哲、罗思文主张早期儒家伦理是一种角色伦理(role ethics),“儒家不寻求普遍,而是集中关注特殊性;他们没有看到抽象的自律个体,而是看中了处在多重互动关系中的具体的人”[28]。他们将角色伦理学喻为“奥卡姆的剃刀”(Occam’s razor),意在将德性伦理论所暗含的、然而不属于早期儒学的“第一哲学”和“个体自我”观念从早期儒学中剔除出去。
应该如何看待这场美德伦理与角色伦理的争论呢?从儒学的历史承传来看,由孔子开启、思孟学派打造,及至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儒学心性论传统,向以丰富的人性探讨、德目论列、理想人格和修养工夫讨论著称。例如,《论语》中关于孝、忠、信、仁、智、勇等德目,乃至乐、好学、主德、诸德关系、君子人格等包括德性品质与行为于一炉的论述在在皆 是[29];而从孔子到孟子,尽管思想路径有朝政治思想发展之面向,但与此同时,孟子关于“性善”“四德”的讨论显示“传统的主要德目在孟子思想中已经从德行条目渐渐发展出德性的意义”[30]。故德性伦理是早期儒家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德性伦理并非儒学全部教义,但是,如果弃置这些内容,则儒学必然面目全非。
而安乐哲、罗思文则基于去本体化、反实体论的新实用主义主张,强调儒家的关系性自我完全不同于德性伦理所内寓的个体主义观念。然而,即便是美德伦理的主将、强调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理论这两种立场之间“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31]的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本人,也主张亚里士多德有其对于个体关系性的强调,儒学之中也有其对于实质性自我的肯定,二者并非判然两截⑥。因此可以说,“角色伦理”是安乐哲、罗思文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的理论产物,或者说是“一种完全西方化的再定义(westernized reconceptualization)”⑦。另外,跟前文提示的观点一样,角色伦理也显示出安乐哲、罗思文二人的相对主义、差异化情感诉求;与角色伦理相关联的文化相对主义极度排斥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对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应有的张力视若不见。
当然,说孟子伦理学尽合于德性伦理学,恐怕也难以成立。孔孟之言“德”,往往是合德性和德行而统言之,即兼顾道德品性和道德行为;而德性伦理学却偏言品性,故德性伦理学之virtue在内涵上小于儒家之“德”。不过,考虑到德性伦理学与义务论伦理学、后果论伦理学之间相互吸取,已出现会通的倾向,可以预见的是,孟子伦理学仍将与西方德性伦理学进行细致而富有成效的比较与对话。
四、小结
中国和西方虽然地域有别,但思想并非截然二分,二者相同、相近、相通之处很多。西方之接受《孟子》并不仅仅只是西方知识学的增益和拓展,或者如赛义德所说是西方之“东方主义”投射的产物,它也是近世以降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文化交流的发展,不仅使中、西地理空间归入同一版图,而且也让中、西思想不断走向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思想各自成为对方思想文化发展的建构性力量。
学术的发展和进步迫切需要细致的对话和交流。了解《孟子》西传的文脉历程和各个阶段的问题意识,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于《孟子》、对于西学的认识,加强中国学人与国际学界交流、对话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能促进我们自身的理论反思和方法自觉,对我们自身哲学、思想和学术的建构与创新发挥镜鉴和启示 之功。
注释:
① 译文由笔者译出。除非特别说明,下文中的引文皆由笔者译出。
② 值得注意的是,罗哲海使用的“调适”(accommodation)一词,会让人联想到早期耶稣会士(Jesuit)以:“适应”为主的经典诠释策略。
③ 葛瑞汉在评论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时将后者的视角概括为普遍主义,并将自己的立场视为差异主义。
④ 此处所言“生物性”“生物学”,并非一般所谓的那种研究生物的构造、功能、发生和发展规律的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意义上的一个概念。社会生物学是“关于所有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是近五十年来西方进化生物学和现代综合进化论领域的重要进展。社会生物学诞生的标志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于1975年发表的巨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一书。威尔逊的著作对下文将要论述的华霭仁、孟旦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⑤ 无独有偶,安靖如在评论万白安《早期中国哲学中的德性伦理与后果论》一书时曾说:“本书的读者很可能也会主张,比之于义务论和后果论,德性伦理学是理解儒学的一个可靠得多的框架。”详见参考文献[26]。
⑥ 安乐哲、罗思文对亚里士多德个体观念的关系品格也有认识,然而他认为这一点无足轻重:“尽管我们是被与我们存在相互作用的他人彻底塑造的社会动物的看法,处处无例外地获得承认,但是,那并没有被视为我们人性的本质,或者,在更加抽象的层次上讲,被视为有引人注目的价值的存在。”详见参考文献[28]。
⑦ 葛瑞汉不认同安乐哲对早期儒学中“性”概念的过度诠释,认为安乐哲从“关系性”角度来解说“性“其实是”“一种完全西方化的再定义”。详见参考文献[11],第288页。
参考文献:
[1] Wm. Theodore De Bary, Weiming Du. Confucianism and Human Rights [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郝大维, 安乐哲. 先贤的民主: 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3] 安乐哲. 自我的圆成: 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535.
[4] Daniel A. Bell.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olitical Thinking for an East Asia Context [M].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吴冠军. 贝淡宁的“缩胸手术”[N].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09?12?20(B09).
[6] Wolfgang Ommerborn, Gregor Paul, Heiner Roetz. Das Buch Mengzi im Kontext der Menschenrechtsfrage. Marksteine der Rezeption des Textes in China, Japan und im Westen [M]. Berlin: LIT Verlag, 2011.
[7] 罗哲海. 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9.
[8] Karl-Heinz Pohl. Chinese Thought in a Global Context: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 [C]. Leiden: Brill, 1999: 257.
[9] 安乐哲, 郝大维. 孔子哲学思微[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序.
[10] Angus C. Graham. The Background of the Mencian Theory of Human Nature [J].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67, (6): 215?271.
[11] Henry Rosemont. Chinese Text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xts: Essays Dedicated to Angus C. Graham [C]. La Salle: Open Court, 1991.
[12] Alan Kam-Leung Chan. Mencius: Contexts and Interpretations [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13] 江文思、安乐哲. 孟子心性之学[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4] Irene Bloom. Mencian Arguments on Human Nature (jen-hsing) [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94, 44(1): 19?53.
[15] Irene Bloom. Human Nature and Biological Nature in Mencius [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97, 47(1): 21?32.
[16] 威尔逊. 社会生物学: 新的综合[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17] James Behuniak, Jr. Mencius on Becoming Human [M]. Albany: SUNY Press, 2005.
[18] Donald J. Munro. A Chinese Ethics for the New Century [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7?60.
[19] 杨泽波. 孟子性善论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78?296.
[20] 黄勇. 评孟旦《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J].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2006, (29): 313?318.
[21] Lee H. Yearley. Mencius and Aquinas: Theories of Virtue and Conceptions of Courage [M]. Albany: SUNY Press, 1990.
[22] Bryan Van Norden: 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 May Sim. Remastering Morals with Aristotle and Confuciu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 Jiyuan Yu. The Ethics of Confucius and Aristotle: Mirrors of Virtu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5] Michael Slote. Comments on Bryan Van Norden’s 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 [J].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09, (8): 289?295.
[26] Stephen C. Angle. Defining “Virtue Ethics” and Exploring Virtue in a Comparative Context [J].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09, (8): 297?304.
[27] Bryan W. Van Norden. Response to Angle and Slote [J].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09, (8): 305?309.
[28] 安乐哲, 罗思文. 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J]. 国学学刊, 2010, (1): 94?104.
[29] 陈来.《论语》的德行伦理体系[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1): 127?145.
[30] 陈来. 孟子的德性论[J]. 哲学研究, 2010, (5): 38?48.
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3
依韩非子之见,孔子死后不久,其后学就分为八派,每一派都宣称合法继承了孔子的遗产。大概每一派均与孔子的某一位或某几位弟子有关,或者受到了他们的启发。虽然对孔子思想互相冲突的诠释在于“道”的分裂,但看起来却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动态。在公元前5世纪,儒家并不居于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但是,对于为思想话语设定议程,儒家似乎发展了最为丰富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事实上,孔子的亲密弟子,象神秘的颜回、忠信的曾子、颖悟的子贡、博学的子夏,以及其它门人等等,已经在孔子的第二代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即便儒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何时最终成为最有力量的学说这一点并不清楚,她确实稳稳当当地成为思想界一种杰出的声音。不过,是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才使得儒家学说得以流行。
孟子(公元前390-305)抱怨战国初期(公元前403-221)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是墨家的“兼爱”和杨朱(公元前440-360?)的“为我”。从孔子死后一个世纪的历史境况来判断,周代封建礼制的崩坏和强力霸权诸侯国的兴起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孔子将政治道德化的企图遇到了嘲讽,被认为是迂阔不实的,而财富和权力的主张则喧嚣至上。当时,受到更多关注的是那些隐士(早期道家)和现实主义者(原始法家)。前者逃离尘世,在大自然中创造精神的殿堂并过着宁静的生活,后者则试图通过辅佐雄心勃勃的君主获取财富和权力,来影响政治的进程。儒家拒绝离开政治舞台在山林中修养自己内在的宁静,因为他们无法承受舍弃人类社会的想法。他们也无法使自己认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因为他们的社会良心驱使他们去负起承担人民良知的责任。他们处在两难的境地。他们希望积极参与政治,但他们不能接受以现状作为权威发挥作用的合法场所。他们厌恶权力政治,但他们又无法使自己脱离国家事务。简言之,儒家是在于而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既不能遗世而独立,也无法有效地改变他们所处的世界。
孟子: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
孟子以凭借自我风格的方式传播儒家之道而著称。孟子最初受教于他的母亲(这进一步加强了作为教育者的母亲在儒家传统中的重要性),然后,据说成为孔子之孙的学生。作为一位社会批判家、一位道德哲学家、以及一位政治活动家,孟子杰出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他投身于教育一个士大夫阶层的任务。这些士大夫们不直接参于农业、工业和商业,但对于国家的正常运作、尤其是人民的幸福,这些士大夫们却至关重要。在反对重农论者的缜密论证中,孟子机智地运用“劳动分工”的理念为“劳心者”进行辩护,并看到了“服务公益”和“生产力”同样重要。[1]对孟子来说,儒家可以作为学者服务于国家的重大利益—不是成为官僚行政人员,而是承担着教导少数统治者行“仁政”和“王道”的责任。在同封建君主打交道的过程中,孟子不但使自己表现为政治顾问,而且是王者之师。他使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一个真正的君子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2]
于是,孟子所倡导的是一种“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作用和功能,“有机知识分子”投身于儒家之道的保存与扩展(“有机知识分子”在组织结构上与社会相连,但在思想上服膺于根本的道德重建)。致力于弘扬儒家“人能弘道”的信念,孟子为“有机知识分子”创造了文化空间和政治场所。根据卫道骑士而非从属执行官的角度,孟子重新诠释了儒家“大人”的理念。对于那些通过政治操纵来行使强力的人,孟子表示蔑视。对于他们不能实践真正的天命的感召,孟子表示谴责,因为最终分析起来,他们不过就象臣服的妾妇那样仰承君主的野心。与之相对,真正的大人依天道而“居仁由义”。[3]这样,孟子就重新将儒家学者界定为卫道的骑士。忠实于儒家的精神,孟子认为道的承载者就是“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作为道德典范而逐渐直接参与政治,他们履行着维护社会结构意义的神圣使命。
为了说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其所处时代具体社会和政治现实的关系,孟子批评墨家全体主义和杨朱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墨家倡导“兼爱”,但孟子却坚决主张,墨家待陌生人如同自己父亲的告诫,将导致待自己的父亲如同陌生人。而另一方面,杨朱提倡“为我”,孟子则坚决主张,过度关注个人利益将导致政治的失序。委实,在墨家的集体主义中,“父亲身份”无法确立;在杨朱的个人主义中,“亲属关系”无法确立。[4] 既然家庭的调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国家的治理是天下太平的基础,为了给人民带来真正的福利,无论墨家的集体主义还是杨朱的个人主义,在政治上就都不是切实可行的。
对于社会改革,孟子的策略是通过强调正义、公益精神、福利和模范性的当局,从而将利益、私利、财富和权力的语言转变成道德的话语。孟子并不反对言“利”,毋宁说,他是恳求诸侯国的君主们去选择大利,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将会确保他们的利益、私利、财富和权力。孟子敦促君主们放眼于他们的宫殿之外,与其臣子属下以及看似不相关的大众培养一种共同的纽带。孟子坚决认为,只有如此,君主们才能维持其统治甚至保持其将来的生活状况。他鼓励君主们推行他们的仁爱,因为这甚至对保护他们自己的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孟子对于以民之所同然作为政府管理机制的诉求,是建立在他这样一种强烈的“民本”感之上的,那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不能以王道而行的君主是不宜为君主的。在对儒家正名原则的生动有力的运用中,孟子得出结论:失道的君主应当受到批评、匡正,或者废黜—作为最终诉诸的手段。[6]既然天意人民的幸福应当得到保障,且统治者有责任承担这一义务,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革命”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众愿所归的。
孟子政治的民本概念基于他的哲学观点: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趋于完善,而人性本善。虽然孟子承认生物性与环境因素在塑造人类状况中的作用,但他却坚持:只要意愿如此,则我们就能够成为有德之人。依孟子之见,意愿需要转化性的道德行为,因为无论何时只要我们决定将本然的善性化为自觉的意向,我们本然的善性便会自然流露发用。作为一种阐明,孟子将其仁政的思想建立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论断之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7]
孟子还观察到:人皆有天赋的四种情感: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就象“火之始燃”或“泉之始达”那样,四种情感构成培养仁、义、礼、智这四种根本德性的基础。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成为有德之人,并不是因为我们被告之必须为善,而是因为我们的本性,即人性的深层向度,自然地流露为善。
孟子认为,我们都具有内在的精神资源,以深化我们的自我意识,拓展我们公共实践的网络。尽管会有生物和环境性的限制,我们却始终有自由和能力去纯化和扩展我们天赋的高贵(我们的“大体”)。虽然孟子在现实的层面上接受人有“食”、“色”的本能倾向,人之异于禽兽者仅在几希之间,但他却坚决主张:我们能够扩充那几希的差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通过集中于“四端”,将自己转化为本真人性的真正典范。[8]
孟子有关在人格塑造中完美的等级的观念,生动地阐明了这种自我的连续纯化和拓展:
可欲之谓善,
有诸己之谓信,
充实之谓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大而化之之谓圣,
圣而不可知之谓神。[9]
而且,孟子断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0]通过发掘内在的精神资源,在人性的潜能中获得自我的觉解,这种深刻的信念使得孟子给儒家事业增加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向度。从孟子的这种视角来看,学习成为“大人”,需要培养人将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生活经验来加以体现的那种感受性: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11]
正如孟子所设想的,儒家学者是模范导师、政治领袖、创造意义的思想家和有机知识分子。
荀子:儒家学术的传播者
如果说孟子带来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成果,荀子(约公元前298-338)则真诚地将儒家事业转化为一种现实和系统的探究,这种探究在于人类状况,尤其在于礼制和权威。公元前30世纪中期,在富足而强大的齐国都城稷下,聚集着一批活跃的学者,以其渊博、思想的精微、逻辑、经验主义、头脑实际和善于论证,荀子普遍被确认为其中最杰出者。荀子的所谓“非十二子”,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思想界的概貌。他对同时代几乎所有主要思想潮流之缺失的深刻洞见,有助于建立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和社会劝导的儒家学派。
结合同时代人的各种睿见,以阐述一种关于自我和社会的综合性的观点,荀子的这种能力显著地开阔了儒家的话语。不过,荀子的主要论敌却是孟子,他坚决攻击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是一种天真的道德乐观主义。
荀子忠实于孔子的精神(孟子亦然),也强调修身的中心地位。他将儒家教育的过程—从学习成为君子到仿效圣人,从习诗到践礼—概括为一种积累知识、技能、睿识和智能的不断努力。荀子认为,除非进行有效的社会约束,人类易于滋生过度的需求以满足其感性欲望,那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这一人类繁荣昌盛的先决条件。对荀子而言,孟子一派性善论信守最严重的缺失在于:它排除了礼制和权威,而礼制和权威对于保持有机社会的安定团结颇为需要。通过强调人性本恶,荀子简别出人心(人的理性)的认知功能作为道德的基础。经由自觉地控制我们的欲望与感性,以符合社会规范,我们就会成为有道德的人。
和孟子一样,荀子相信所有人通过修身能够达到完美的可能性,相信人性和作为基本德性的正义感,相信作为王道的仁政,相信社会和谐以及教育。但是,关于所有这些如何得以实现的观点,荀子和孟子却有着显著的不同!由荀子所塑造的儒家事业,将学习视为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对于转化人性,诸如古代圣贤、经典传统、习俗规范、师长、政府规章制度以及政府官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资源。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一个人类社群的充分社会化的参与者,他或她成功地升华了自己的本能要求,去促进社会的公益。
在法令、秩序、权威和礼制方面,荀子讲究现实的立场似乎有接近法家关于社会一致政策的危险,后者是专为统治者的利益而设计的。荀子关于行为客观标准的坚决主张,或许会为权威主义的兴起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而权威主义则导致了秦朝(公元钱221-206)的专制。事实上,韩国的理论家韩非(约公元钱233)和秦国的丞相李斯(约公元前208)这两位最有影响的法家人物,便都是荀子的学生。不过,在儒学作为一项学术事业而继续的过程中,荀子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荀子不同意法家的策略:以社会文化多样性为代价来强化国家权力。他对“天”的自然主义的诠释,对文化细致入微的理解,对“心”在认识论方面和语言在社会功能方面的富有洞见的观察,对道德推理和论证艺术的强调,对发展演化的信念,以及对政治制度的兴趣等等,都显著地丰富了儒学遗产,以至于他被尊为儒家的典范式学者超过三个世纪。
孟子和荀子将儒学深化并拓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在孔子亲炙弟子那里所罕闻的关于人性与天道的看法,被充分地阐释为一种一贯的“天人合一的”观点。根据孟子和荀子的诠释,学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包容了将我们的生物性实在转化为自我审美表达的整个过程。修身的丰富语汇—举止的合礼,心智的滋养,灵魂的净化,以及精神的升华——与同样细致入微的“经世”艺术的语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儒学提供了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内圣外王”。
政治的儒家化
为时不长的秦王朝的专制统治,标志着法家的短暂胜利,但在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8年)初年,君主绝对专权、周边所属王国完全服从中央政府、思想的大一统以及无情地强化法令,这些法家的实践被道家的休养生息和无为而治所取代。历史上,这种实践通常被认为是黄老之术—被归于黄帝和道家神秘创始人老子的统治术。象陆贾、贾谊等几位儒学思想家,在政策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甚至在董仲舒(约公元前179-104年)之前,在汉家朝堂之上已经可以听到儒家的劝导,并且,刚刚出现的将帝国建立在儒家原则之上的趋势益发明显。实际上,汉代政治逐渐的儒家化,在王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恢复封建制,还是于朝堂之上实行煞费苦心的廷礼,都使得汉儒们在塑造政府的基本结构方面贡献良多。通过广泛搜寻和口头转述而重获佚失的经典,汉王朝决定补偿秦代焚书所造成的文化破坏,这显示了将儒家传统作为形成中政治意识形态有机组成部分的自觉努力。
在武帝(公元前140-87年)这位具有法家专制君主气质的统治时代,儒家劝导已经在中央官僚体制中树立了牢固的地位。在皇权和政府明确的分离中,在通过举荐和征选双重机制的官员选拔中,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中,在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中,以及在教育系统中,儒家的影响显而易见。随着礼制在政府行为、社会关系的界定以及民事纠纷的调节方面变得日益重要,儒家的理念也在法律体系中获得了牢固的建立。然而,直到丞相公孙弘说服武帝正式宣布只有儒家学派方可得到国家的支持,儒家才成为官方认可的帝国意识形态和国家崇拜。
结果,儒家经典成为各个教育层次的核心科目。公元前136年,武帝于朝廷设立五经博士,并于公元前124年分配五十名官派学生跟随他们学习。这实际上创建了一所帝国大学。到公元前8年,登记注册的学生达三千人,并且,至公元1年,每年有一百人通过国家主办的考试进入到政府之中。简言之,那些受过儒家教育的人开始为官僚体系配备人员。公元58年,所有国家举办的学校要求祭祀孔子,而在公元175年,政府化了几十年组织专家学者经过会议所许可选定的经典版本,被颁刻在了巨大的石碑之上。这些石碑树立在都城,直到今天,他们仍然完好地保存在西安的国家博物馆中。试图永久保存和昭示神圣经典确定内容的行为,象征着经典儒家传统的形成。
儒学作为汉朝官方意识形态的建立,常常被欢呼为孔、孟、荀之教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胜利。从儒家精神性的视角来看,这种胜利至多是一桩混合各种成分的幸事。汉代之前,儒家传统中从未有“上帝之事归上帝,恺撒之事归恺撒”的类似说法,但是,真正的儒家从来都对现实持一种批判的立场。象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中国的宗教》,将儒家的生活取向描绘为“对世界的适应”,[12]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儒家从内部转化世界的信守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儒家接受国家事物的可完善性以及尊重现状并以之作为出发点,但如果现存的权力关系不能够再保障人民的幸福,儒家常常又毫不妥协地要求既存的权力关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
不过,作为反映统治阶层少数人利益的官方意识形态,汉代的儒学本身基本上表现为一种利禄之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的仁义之道被完全拋诸脑后。事实上,在汉代的政治文化中,有关儒家之道的争论者们专注于两条相互冲突的道路上:为了修身与社会责任的本真的儒家追求,以及以修身为代价的社会进步的政治化的儒家目标。诚然,一旦那些作为调味剂添加到儒学传统之中的人们也成为政治上的显赫,政治操纵和道德匡正之间可能性的范围就会变得非常广泛。在各种形式的变项中,混合它们的摸棱两可之处便会成为一种生活的现实。
董仲舒:天人交感
象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一样,董仲舒非常重视儒家的经典《春秋》。但是,董仲舒自己的著作《春秋繁露》,却远非一部具有历史判断的著作。那是一部在《易经》精神笼罩之下的书。作为一位异常献身学术(据说他因潜心学问而“三年不窥园”)和坚决服膺道德理想主义(他常为人所引用的一句话是:“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13])之人,董仲舒在将儒学发展为具有汉代诠释特征的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武帝宣布“独尊儒术”,道家、阴阳家、墨家、法家、巫师、医师、方士、堪舆家以及其它三教九流,都对汉代精英的宇宙论思维有所贡献。董仲舒本人就是这种思想综合的一位受益者,因为在阐释自己的世界观时,他自由地涉猎了当时的各种精神资源。他提出了天人交感的理论,在一年的四季、12个月和366天以及人体的四肢、12关节和366块骨骼之间进行竭力比附。天人交感理论基于一种有机观,其中,存在的所有形式都是在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彼此相互关联的。从这种亲源关系形上学(metaphysics of consanguinity)中所引出的道德是:人的行为具有宇宙性的后果。
对于“五行”(金、木、水、或、火、土)的意义、人与天数的相关性、以及同类事物的感化作用,董仲舒进行了探求。就象他对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根本价值所进行的研究一样,这些探求使得董仲舒能够将儒家伦理与自然主义宇宙论有机结合,从而发展出一套精致的世界观。董仲舒所完成的不仅仅是对作为“天子”的君主进行“神学的”合理化论证 ,毋宁说,他的天人交感理论为儒家学者提供了判断统治者品行的更高法则。事实上,他有关“灾异”的修辞,即断言洪水、干旱、地震、彗星、日食、甚至象“妇人长须”这样的自然现象都是警告统治者不良行为的天象。后来这种灾异说扮演了一种对于专制君主荒淫无度的有效威慑。董仲舒给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具有深远政治涵义的诠释力量。
董仲舒的思想模式反映了预言、卜测和象数思辩的学术倾向,这在当时颇为流行。作为“今文”学派的拥护者,这些学者们将他们的论证建立在汉代“新经”的基础之上,并致力于探求经典的“微言大义”,以作为影响政治的一种工具。王莽(公元9-23年)篡位的发生,部分原因就在于当时流行的儒家知识分子认为天命的改变不可避免这样一种要求。
虽然董仲舒的思想颇为流行,但他的世界观却并不为汉代的儒家学者所普遍接受。以“古文”学派著称的那种更具理性和道德性的诠释儒家经典的进路,在西汉崩溃之前已经颇具吸引力。一种可供选择之物是杨雄(约公元前53-公元18年)在《法言》和《太玄》中提出的世界观。《法言》是一部以《论语》体裁写成的道德格言集,《太玄》则以《易经》的风格表达了一种宇宙论的思辩。古文学派宣称他们对在汉现的以“古文”写于秦统一之前的真正经典进行了重新修订。而古文学派在东汉(公元25-220)则广泛地为人所接受。随着博士机构和帝国大学在东汉的扩充,经典的研习变得益发精细。就象犹太法典和圣经的研习一样,儒家学术变得高度专业化,甚至到了作为一种道德话语而生命力枯萎的地步。
然而,对于政府、学校、以及社会,儒家伦理仍然在较大范围内发挥着强大的影响。直到汉代结素,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受到了儒家经典的熏陶。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得以牢固确立,并且,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学校都举行常规的的祭孔仪式。孔庙遍及全国。朝廷继续年复一年的表彰孔子。儒家圣祠最终矗立在全国两千个郡县的每一处所在。结果,与“天”、“地”、“君”、“亲”一道,“师”成为传统中国最受尊敬的权威之一。
尽管被奉若神明,但是,通过不断学习的个人范例,孔子的师表风范使他自己成为普天之下最高贵的人。孔子这位常人和神化式人物,在中国社会发挥着巨大的象征力量,同时,他又不失其作为人的属性。即使是对孔子的神化,之所以灵验,其原因也是道德转化而非别有所在。
佛道时代的儒家伦理
东汉末年,统治者的无能、官僚系统的派系斗争、管理不当的赋税体制以及宦官专权,促成了大规模的太学生抗议。朝廷于公元169年囚禁并处死了数千太学生和同情太学生的官员。这种高压政策使得思想上的反抗得以暂时终止,但是,随着衰退经济日见下滑所导致的民不聊生,一场大范围的农民起义随之而来。由儒家学者和道家宗教领袖领导的农民起义,会同公然的武装暴动,推翻了汉王朝并结束了第一个中华帝国。随着汉朝的瓦解(与罗马帝国的崩溃不同),“蛮族”由北方侵入。北方中国平原地区有几个敌对的部族控制,战乱频仍,劫掠不断,南方中国则接连建立了几个短暂的王朝。从公元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这段分崩离析的时代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儒学的衰落、新道家的高涨以及佛教的传播。
然而,佛道两家思想在精英中的杰出以及在大众中的流行,并不意味着与儒家传统的消长。事实上,儒家伦理与中国社会的道德组织结构难以分离,孔子继续被普遍地赞誉为圣人的典范。杰出的道家思想家王弼(公元226-249)坚称:孔子虽未“言道”,却比老子更能“体道”。儒家经典仍旧是所有知识文化的基础,并且,贯穿整个时代,各种有关儒家经典的繁复注释也不断产生。在中央官僚系统、官员选拔和地方行政那样一种政治建制中,儒家价值从未停止过占据主导地位。生活的政治形式也明显是儒学化的。当象北魏(公元386-535)那样的蛮族国家采取汉化政策时,大体上也是儒家特色。在南方,通过建立基于儒家伦理之上的家族统治、家族世系以及祖先礼制,也在进行着试图强化家族的系统化尝试。虽然儒学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她却为世家大族的行为准则、地方精英所容纳,间或也被蛮族征服王朝所吸收。隋代(公元581-618年)中国的重新统一,以及唐朝(公元618-907年)持久和平与繁荣的恢复,给了儒学的复兴以强有力的促动。带有详细“传”和“疏”的官方版本的《五经正义》的出版,以及儒家礼制在政府实践(包括著名的大唐法典的编纂)各个层面的实行,是儒学实践的两个突出例证。基于文字能力的一种考试制度得以建立。这使得掌握儒家经典成为政治上成功的先决条件。并且由此,在以儒家术语界定精英文化中,考试制度的建立或许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制度性革新。
不过,唐代的思想和精神气质却是由佛教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道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唐朝在哲学上的原创性主要是由诸如吉藏(公元549-623年)、玄奘(公元596-664年)和智顗(公元538-597年)这样的僧人学者所代表的。在这一历史脉络中,儒家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非预期后果,那就是象《中庸》、《易传》这些最具形上学意义的儒家经典,在某些僧人和道士那里得到了格外的突显。唐代李翱(公元772-846年)的《复性书》,标志着一种可能的儒家思想的转折,也预示着宋代(公元960-1279)儒家思想的某些显著特征。不过,儒学复兴最有影响的先驱是伟大的文学家韩愈(公元768-824年),他从社会伦理和文化认同的角度进行了有力的攻击。他探讨并引发了人们对究竟什么构成儒家之道这一问题的兴趣。自从11世纪以来,道统问题在儒家传统中激发了相当多的讨论。
在政治领域,由唐太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明智、心胸开阔的大政治家所代表的政府风格,显然具有儒家的特征。《贞观政要》这部应当是唐太宗统治的可靠记录,迄今仍然是常为人们所引用的代表卓越领导艺术的文献。但是,必须注意,正是在这个时代,专制的机制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之中,以至于作为政府唯一合法形式的皇权被视为理所当然。结果,那些经过竞争性科考并被配备到官僚系统当中的士大夫们,就成为儒家之道的事实上的承载者,这与孟子那种作为卫道骑士的有机知识分子的理念相去甚远。不过,唐朝几位辅宰相在君主面前仍然显示了如此令人敬畏的形象,以至于他们继续唤起了有关个人尊严和政治责任的孟子精神。对他们而言,“从道不从君”的儒家理念,是一种实践的德性,而不仅仅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
孔子和孟子、荀子这两位后学,开启了儒家人文主义的第一期发展。到公元前一世纪前汉的高峰期,儒家传统在中国的道德教育、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伦理方面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力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儒学是规定文化精英生活取向的正统,在中国哲学和宗教的景观中,她同时又是和许多其它的思想潮流—道家、法家、阴阳宇宙论、五行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相并存的。诚然,就象董仲舒“天人合一的”综合主义一样,儒家人文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其包容性。这种包容性象征着一种深思熟虑的努力,努力将看似不兼容的一些观念系统安置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观之内。当然,尽管儒家的影响在政府建制、社会组织以及文化生产方面仍然存留,到公元一世纪,儒家人文主义的第一期开展却是逐渐减弱的。虽然儒家人文主义在佛教和道教的时代仍有进一步的发展,她真正给人印象深刻的复兴却是在11世纪。英文中经常提到的Neo-Confucianism的出现,标志着儒家人文主义的第二期开展。
注释:
--------------------------------------------------------------------------------
[1] 《孟子》第3章上:第4节。
[2] 《孟子》第3章下:第4节。
[3] 同注15。
[4]《孟子》第3章下:第9节。
[5] 《孟子》第7章下:第14节。
[6] 《孟子》第1章下:第8节。
[7] 《孟子》第2章上:第6节。
[8] 《孟子》第4章下:第19节。
[9] 《孟子》第7章下:第25节。
[10] 《孟子》第7章上:第1节。
[11] 《孟子》第7章上:第4节。
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4
一、儒家人格修养学说中的尚武精神
尚武精神在本质上表现为勇武刚健的阳刚精神,这正是儒家人格修养所要求的。
《礼记·儒行》有云:“儒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其刚毅有如此者。”这体现了强烈的春秋“武士道”精神。儒家原典,尤其是《诗经》中,令人振奋的刚健精神俯拾皆是,比如“有力如虎,执辔如组”、“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等。《诗经·郑风·大叔于田》还描写了一位勇敢善射、与老虎赤手相搏的青年猎人形象。《易传·乾卦》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自强刚健精神的最佳诠释。《尚书·皋陶谟》记载了“九德”,其中“栗”、“立”、“乱”、“毅”均有“坚、刚”之意,而“简”、“刚”、“强”三种品格更为勇者所必具。钱穆先生说:“据《论语》与《周易》,儒家论人事皆尚刚,不尚柔。”
孔子关于人格修养还有著名的“智仁勇”“三达德”之说。“勇”其实是孔子仁学体系的重要内容。由这种刚毅精神而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种精神力量发展到极致,便有了“杀身成仁”的大节大勇和令人心潮澎湃的“武士精神”。这种精神的宣誓一直回荡在华夏两千年的历史长廊中。《论语·泰伯》:“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不可夺也。”《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此实堪称前无古人之大气魄,胡适将孔子所言的君子称为“见危致命的武士道君子”。孔子的这种“杀身成仁”精神后来为孟子继承,并提出了异曲同工的“舍生取义”说。
孟子在人格修养方面还提出了独特的“养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同志后来将孟子的“浩然之气”和“大丈夫”人格称之为“豪杰精神”,并深深推崇。至孟子时,尚武精神作为儒家人格修养精神的重要内容,被发挥到了极致。
二、儒家思想中的军事尚武精神
军事尚武思想在儒家思想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尚武精神在《尚书》中被推崇备至。《尚书》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尚书·甘誓》有关于战士们不畏强敌、勇往直前的描述。《尚书·牧誓》中还有周武王勉励军士的记载,号召士兵们以勇猛威武的军容和果敢坚毅的精神,勇往前进,成就自己君王的功业。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对军事和武备很重视。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射”和“御”都是当时社会中最重要的军事技能。孔子也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弟子冉有为季康子帅军与齐国作战,大获全胜。季氏问冉有深谙军事的原因,冉有回答说是“学之于孔子”。另外,《论语·颜渊》和《论语·子路》两章都讲的是练兵习武的重要性。所以,孔子并非像后世的腐儒一样,是只讲修身、文化之类的书呆子。孔子认为,只要武力用于为民取福,就值得提倡和赞扬,所以他才对管仲的武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另外,儒家仁学体系从一开始就接纳和包含了暴力。孔子提倡保卫国家等正义之战,所谓“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另外,《左传·定公十年》与《史记·孔子世家》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鲁定公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与夹谷,孔子负责会盟事宜,他主张外交等文事应以武力作为后盾。后来在会盟中,齐国企图劫持鲁定公,而孔子一人退齐师,以致齐景公“惧而动,归而大恐”。所以,梁启超在《中国之武士道》中赞曰:“非大勇熟能与于斯?……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至矣!”
孟子与孔子一样,反对不义之战和纯粹以功利为目标的战争,但他绝不是一个“非战主义者”或“非暴力主义者”。
孟子主张为施行仁政而采用战争工具,他把这种正义的军队称为“仁义之师”或“仁者之师”。他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儒家军事尚武思想的命题,如“仁者无敌”,“以至仁伐至不仁”,“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等等。
孟子主张“诛其君而吊其民”,“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并提出了具有一定民主意识的“君主易位”思想。由此,又直接生成了儒家思想中的暴力革命思想。
儒家暴力革命论来源于《尚书》中的“伐无道”思想。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诛一夫”观点。这种对无道之君可以暴力诛之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起义和革命。“诛乱除暴”、“解民倒悬”在古代战争史上具有神奇般的号召力,直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孟子的主张属于王道,而荀子则兼尚霸道。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思想较之于孔孟具有更强的“刚性”。
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5
无论人们抱怎样的态度,当代新儒家作为中国现当代的一个思想文化派别或思潮的存在乃是一不可掩盖的事实,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之加以定位,例如从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中定位,从中国现当代思潮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从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定位,从纯学理的(哲学的或宗教的)层面定位,从学术史的层面定位,乃至从人类文化的现展及其前景方面定位,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对新儒家还必须从儒家思想自身的传衍发展的角度为之定位,这关涉到对儒家和儒家传统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如何认识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与核心内容?当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新儒家对儒家思想的诠释和发挥能够代表儒家思想之现展所应有的方向吗?亦或表现出某种实质性的误导与不相应?这一类问题的讨论和诘难已经与来自自由主义方面的批评有实质性的差异,因为在后者的批评中通常已经预设了新儒家思想与儒家传统之间的一致性。
在来自传统营垒的诸种批评中,又以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对当代新儒家思想的检讨较具影响力和代表性。[1]本文的思考与拜读余先生的文章有关,但本文的立意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呼应或回应余先生文章中的问题,[2] 而是立足于客观地分析新儒家道统论的形成及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儒家与新儒家的道统论(特别是儒家自身的发展中所谓道统与学统之关系)的一点认识。
一、 梁、熊、冯的有关思想
余先生在文章中论及三种道统观:一是为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由韩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学加以发挥倡导的“主观的”、“一线单传的”道统观,它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二是钱先生本人所主张的谓“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3]而余先生所论新儒家的道统观乃是特指“哲学家的道统观”而言,此所谓新儒家又是特指由熊十力的师门传承所形成的哲学流派,更确切地说主要是指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师徒而言。[4]
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5]到韩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传道系统,[6]再到朱子《中庸章句序》明确提出“道统”一词,传统儒家的道统观确是与具体的传道谱系关联在一起。至于余先生所说“思想史家的道统观”自然已与宋明儒所谓“道统”的本义相去甚远,此在钱穆先生的著作中,本来就属退一步的说法或云姑且言之之意,因为钱先生本来就对理学家所谓道统持批评的态度。
至于“哲学家的道统观”,依余先生所论:“自熊十力起,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但是他们重建道统的方式则已与宋明以来的一般取径有所不同。他们不重传道世系,也不讲‘传心’,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在这一点上,他们确与陆、王的风格比较接近。由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诸人对于‘心’、‘性’、‘道体’的确切涵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他们的道统谱系因此也有或严或宽的不同。但无论严宽,大致都认定孟子以后,道统中断,至北宋始有人重拾坠绪;明未以来,道统又中断了三百年,至新儒家出而再度确立。”[7]
说熊先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反驳。[8]至于余先生一方面说熊十力等新儒家“不重传道世系”,另一方面又说他们有自己“或宽或严”的“道统谱系”,我们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区别?大致说来当代新儒家的所谓道统谱系至少不似韩愈、宋儒那样明确而直接,而往往是隐含在他们有关儒家思想之发展、演化的论述中。且就熊十力先生的思想而言,即便是此类松散的道统谱系也并不完整或者说尚未形成。因为就当代新儒家而言,所谓道统谱系之形成的重要一环是必须对宋明儒家的思想脉络进行系统的疏理和分判,此项工作是五十年代后由牟宗三先生完成的。
传道谱系的提出是与判教关联在一起的。熊先生的判教更多的是在大乘佛学空、有二宗与儒家思想之间进行,这是种广义的判教。就儒家思想自身的传衍发展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说熊先生的思想更近于陆王(例如他说“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9]但他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后儒如何传道,而是儒家精神义理本身的问题。且与牟宗三等人不同,熊先生并不一般地认为由先秦到宋明标示着儒家思想一个新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虽然同样以心性之学为儒家思想的血脉,但熊先生对于心性的理解实与唐、牟等人有很大的不同。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曾论及熊、牟心性理论的差异,指出:“就总体而言,牟宗三似乎更注重本心、性体即内在即超越的方面,因而也就更注重‘性体’的超越义;熊则更强调其‘即存有即活动’的方面,因而凸显了‘心体’的创生义。此所谓‘创生’又并非是限于道德领域而言,而是一种承自于先秦儒家的广大悉备、生机盎然、活泼泼的生命气象。熊常使用‘宇宙的大生命’一语,盖与此有关。他说:‘宋明诸大师,于义理方面,虽有创获,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却孔子广大与活泼的意思’。”[10]
若从经学方面讲问题则更复杂些。熊先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囿于传统经学的框架,试图把儒学诠释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因而强调“孔子不反知,极注重科学。”[11]“程朱说理在物,故不能不向外寻理。由其道,将有产生科学方法之可能,”[12]孔子外王学的真义乃在于“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特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13]且认为“孟、荀识短,犹不敢承受也。七十子后学之同乎孟、荀者当不少”。[14]所以在其晚年所著《原儒》中,熊先生可以说是独尊于孔子。说“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也可以是宽泛地讲,指他们在文化上有一种强烈的续统和担当的意识。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余先生对“新儒家”所作的狭义的限定,那么所谓“道统意识”就只能是宽泛地讲。
梁漱溟先生作为“五四”以后新儒家思潮之开山者的地位已很少受到质疑。我们自然也可以笼统地说梁先生在倡导“新孔学”方面亦表现出了强烈的续统意识,但实际上在梁先生的思想中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道统”观念,他也几乎没有论及道统问题。梁是一位实践家,是一位实践意义上的儒家。此所谓“实践”不仅是指个人的身心修养,而且是指由“内圣”而“外王”,把自己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影响社会人文的实际行动。可以说梁先生的兴趣所在并不在于把儒家思想诠释为某种义理系统或疏理出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乃至确定某种传道谱系,孜孜于建构某种哲学体系更是他所着力反对的;[15]梁先生所看重的只是对儒家思想的某种解悟, 他要依据此种解悟整合自己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并基于此种认识决定自己的实践原则和努力方向。
在有关心性的认识方面,梁先生又与熊十力先生等有很大不同。梁固然讲“良知”,讲“理性”,但他所谓良知、理性主要的是从现实的层面(而非超越的层面)讲,亦可以说他所谓良知、理性只是道德实体而非宇宙实体。[16]梁先生基本上是从人生态度、人伦化关系、伦理教化的层面理解和阐发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精神义理,他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伦理有宗教之用”,“礼乐有宗教之用”等等,主要是着眼于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此与牟宗三先生等从心体性体“即内在即超越”的特性来说明和证成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应当说有实质性的差异。
冯友兰先生是“先论旧学,后标新统”,但其所谓“新统”之“统”实非儒家“道统”之“统”。他说:“新理学又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所以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的‘指’。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废话’,有似道家,玄学以及禅宗。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17]可见他所谓“接着讲”,亦可以(或者说亦只能)在十分宽泛的意义上理解。
实际上,就与传统的关系而言,冯先生的思想理论中有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是在形上学方面,他申明自己是接着公孙龙、程伊川和朱晦庵哲学中有关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讨论讲的;[18]二是在人生境界方面,他实际上更倾向于孟子、《中庸》、庄禅、程明道、王阳明等,这从《新原人》“天地”章的论述和引证中不难看出。就人生境界而言,程朱、陆王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由于冯先生把朱子的“理”形式化、逻辑化、抽象化了(此方面他也不同于名家,后者是扣紧名实关系立论,冯则是着眼于逻辑分析),所以其思想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并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但无论如何,两方面都与儒家的“道统”没有直接的关联。事实上他在三十年作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引述《宋史·道学传》和朱子《中庸章名·序》的观点,言朱熹被视为“道之正统”的传人且以此自居,[19]但冯先生没有对此作任何的讨论和评论。
表现为某种文化承当的续统意识并不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道统谱系”来讲,有强烈的道统意识者(如熊十力)亦未必就有自己系统的道统论。新儒家道统论的系统阐发者是牟宗三先生。
二、牟宗三先生重建道统的三个环节
如果说韩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道谱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对佛都的外在仿效,那么到了朱熹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实际上已不能与韩愈同日而语,应当说它标志着宋明理学发展的成熟与深入,至于宋儒的道统观在后世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则是另外一回事。同样,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也是新儒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牟宗三先生理论中的“道统”观念,可以区分为广、狭两种不同的涵义。从广义方面说,其所谓道统观念乃是泛指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或称之为内圣成德之教。牟先生指出:“中国本有之学的意义以及基本精神则限于‘道’一面,亦即‘德性之学’。如在科学一面说学统,则在‘德性之学’一面自可说道统。”“中国‘德性之学’之传统即名曰“道统”。[20]牟宗三先生五十年代所论与“学统”、“政统”相对而言“道统”基本上是在此种涵义上说;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诸先生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言及“道统”也基本上是在此种涵义上说。这是扣紧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特质与重心说道统,是从中国历史文化一体相联、一脉相承的统绪(《宣言》称之为“一本性”)上说道统,尽管人们对此历史文化传统的具体认识会表现出各种差异性,但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或者进一步说从“德性之学”(内圣成德之教)的意义上肯定有一道统的存在,应当不会有太大的分歧。实际上,熊十力先生对道统观念的认识也止于此,他说:“盖一国之学术思想,虽极复杂,而不可无一中心。道统不过表示一中心思想而已。”[21]
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牟先生思想中狭义的道统观念,此所谓道统或许更接近于宋儒的本义,它要落实到“道”的具体传承上说,落实到传道谱系上说,其中特别关涉到如何认识评价和确定宋明儒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疏理、诠释和确定宋明儒自身的义理系统、发展脉络和传道谱系。当代新儒家既然是接着宋明儒讲,则此项工作必然为一不可跨越的环节。
具体地说,牟先生重建儒家道统的努力主要包含以下三个理论环节:
1、重新肯定孔子的“教主”地位。孔子所创立的“仁教”乃是儒家“道之本统”,故道统当自孔子讲,而不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此一认识实与宋儒不同。
近代以来,围绕对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上之地位的重新认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与分歧。在传统营垒内部,至少有两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要而言之,其分歧集中表现在: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传承来看,孔子究竟是“述”者还是“作”者?前一种观点可以举钱穆先生为代表,后一种观点则以熊十力、牟宗三师徒为代表。
钱穆先生强调孔子思想与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孔子是“述而不作”,他只是发扬光大了三代文化,而不能说是别开一个方向或开创一个世纪。以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仁学为例,钱先生指出:“孔子实能深得周公制礼作乐之用心者,故于‘吾从周’,‘吾其为东周乎’之全部理想中而特为画龙点睛增出一仁字。”[22]“仁”字虽为孔子所“增出”,包含了孔子的创意,但它又毕意只是在总结周文化基础上的“画龙点睛”,此从根本处说仍然只是“述”而不是“作”,“故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始产生孔子,不能谓由有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造也。”[23]
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可以说与钱先生适成对照。他肯定宋明儒学之为“新儒学”的两点贡献:一是“对先秦之庞杂集团、齐头并进,并无一确定之传法统系,而确定出一个统系,藉以决定儒家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具体地说是确定了“以曾子、子思、孟子及《中庸》、《易传》与《大学》为足以代表儒家传承之正宗”。[24]二是改变了汉人“以传经为儒”的观念,“直接以孔子为标准,直就是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而言成德之教以为儒学。”故宋以前是“周孔”并称,宋以后是“孔孟”并称,“周孔并称,孔子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骥尾,对后来言,只是传经之媒介”,“孔孟”并称,则是以孔子为教主,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始正式被认识。”[25]
强调孔子的“教主”地位,即在于指出孔子思想的意义不在于“述”,而在于“作”;不在于传承,而在于创造;不只是构成文化发展的“媒介”,而是开辟了独特的生命方向,开辟了“价值之源”。与钱穆先生不同,牟先生不是要把孔子融入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历史脉络之中,而是要使孔子从历史的视野中凸显出来,所以他十分强调孔子的生命形态与生命方向之独待性:
“孔子既习六艺,亦传经。然六艺孔子以前之经典(《春秋》稍不同),传经以教是一事,孔子之独特生命又是一事。只习六艺不必真能了解孔子之独特生命也。以习六艺传经为儒,是从孔子绕出去,以古经典为标准,不以孔子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为标准,孔子亦只是一媒介人物而已。”[26]
牟先生的思想亦与其师熊十力先生有所不同。熊先生亦强调孔子是“作”者,是教主,但他基本上没有摆脱近代今文经学的影响,是从“孔子作六经”的角度来确定孔子的地位,[27]牟先生则认为此点并不重要。他说:
“对于诗书礼乐春秋,无论是删、定、作或只是搜补,有述无作,皆不关重要。要者是在仁。仁是其真生命之所在,亦是其生命之大宗。不在其搜补文献也。有了仁,则其所述而不作者一起皆活,一切皆有意义,皆是真实生命之所流注。然则唐虞三代之制度之道与政规之道惟赖孔子之仁教,始能成为活法,而亦惟赖孔子之仁教,始能见其可以下传以及其下传之意义。自其可以下传言,是孔子之所以承继唐虞三代之道德总规与政规者;自其下传之有意义言,乃见其必有一开合以期新的综合构造之再现,所谓重开文运与史运者。是则仁教者乃对于道之本统之重建以开创造之源者也。诗书礼乐春秋可以述而不作,而仁教则断然是其创造生命之所在,此不可通常著书立说之创造视之也。”[28]
仁教乃孔子所创立。仁教即内圣成德之教,即儒家“道之本统”。由此说来,儒家道统当是自孔子讲,而不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从此种意义上说,牟先生所谓孔子确乎是一“截断众流”的孔子。
牟先生有时亦自尧舜禹三代说道统,但其时所谓道统之涵义已与宋儒不同。他说:
“然自尧舜三代以至孔子乃至孔子后之孟子,此一系相承之道统,就道之自觉之内容言,至孔子实起一创辟之突进,此即其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是。……此一创辟之突进,与尧舜三代之政规业绩合而观之,则此相承之道即后来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语出《庄子·天下篇》)。此‘内圣外王之道’之成立即是孔子对于尧舜三代王者相承‘道之本统’之再建立。内圣一面之彰显自孔子立仁教始。曾子、子思、孟子、《中庸》、《易传》之传承即是本孔子仁教而开展者。……自孔子立仁教后,此一系之发展是其最顺适而又最本质之发展,亦是其最有成而亦最有永久价值之发展,此可曰孔子之传统。”[29]
尧舜禹三代所传之道乃是“政规业绩”之道,是文制之道。此是“王道”之道,而非内圣之道。内圣之道自孔子始。此一认识实与宋儒有实质性的差异。我们可以注意到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道之本统与孔子对于本统之再建”一章,开篇即追述道统说之源流,并没有提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十六字心传。我们不难推知,牟先生实际上也不能够接受朱子《中庸章名序》所谓尧授“允执其中”于舜,舜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于禹、汤、文、武、周公相承至孔子的说法。因为按照牟的观点,儒家作为传心之法的“道之本统”乃是自孔子始,而非自尧、舜、禹三代始。从此种意义上可以说,孔子的思想又不只是截断众流,而且是劈空建立。
牟先生的有关思想,在新儒家阵营中亦属特殊。熊十力先生虽以“六经”属孔子,但仍然十分强调孔子与先圣之间的继承关系。他指出:
“孔子之所承藉者极其宏博,其所开创者极其广远(广者广大,远者深远),巍然儒家宗师。自春秋战国,久为华夏学术思想界之正统。”[30]
“《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尧舜以来之大成。此皆实录。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已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孔子自言‘好古敏学’,又曰‘述而不作’,曰‘温故知新’,盖其所以承接者既远且大,其所吸收者既厚且深。故其所定六经,悉因旧藉,而寓以一已之新意,名述而实创。”[31]
此是说孔子是以述为作。而在牟先生看来,孔子思想中的“述”与“作”两方面必须加以明确区分:“述”是表现在文制方面,“孔子立教的文制根据就是周文,而周文的核心则在亲亲之杀,尊尊之等。……孔子继承(述而不作)这一套,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其中心观念,就是凭依亲亲尊尊文制。”[32]孔子之“作”则是表现在仁教方面。此方面孔子是四无依傍,开宗立派,奠定两千年多年内圣之学之宏规。“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33]故孔子作为圣者的地位只能够从仁教方面讲。
牟先生的有关思想与梁漱溟先生更有实质性的差异。梁先生可以说恰恰不是以“孔孟”并称,而以“周孔并称”。这是因为他讲儒家精神及其对历史上中国社会人生的影响,基本上是落到礼乐层面来讲,而非落到心性的层面来讲。落到礼乐的层面来讲,则必然强调孔子对周文化的继承方面。梁先生说:
“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34]
“孔子自己所说‘述而不作’,……恰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古宗教之蜕化为礼乐,古宗法之蜕化为伦理,显然都经过一道手来的。礼乐之制作,犹或许以前人之贡献为多;至于伦理名分,则多出于孔子之教。孔子在这方面所作功夫,即《论语》上所谓‘正名’。其教盖著于《春秋》,‘春秋以道名分’(见庄子《天下篇》)正谓此。”[35]
显然,此所谓孔子“寓作于述”“以述为作”与牟宗三先生所言孔子创立仁教之义,相去甚远。它所指的是确定伦理名分,此在很大程度上仍可归属于文制方面。此方面之“作”不可能是劈空建立,而仍需由传统“蜕化”而来。至于说孔子“其教盖著于《春秋》”,则更是牟宗三先生等所不能接受的。
2、宋明儒如何是以“孔孟并称”?牟对“四书”有一判释,以《论》、《孟》、《中庸》、《易传》为儒家道统所系,《大学》则为“开端别起”,并由此分判出宋明儒之“大宗”与“旁枝”。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确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的地位,且“四书”实已居于“五经”之上。这确实体现了儒学发展中的某种转向,此转向虽然不是自朱熹始,但朱熹于其间实作用甚大。因为所谓宋以后以孔孟并称,落实地说,只能是就“四书”而言。“四书”将孔子置于宗主的地位,并以《孟子》升经,从而以孔孟取代了传统“五经”中的周孔。自此以后,虽然宋儒的道统说仍然是自三代讲,实际上孔子于其中的地位已与此前大不相同。牟宗三先生强调此转向的重要性(其中特别关涉到对孔子地位的重新认识),却对朱熹别有一番议论。
牟先生首先对宋明的义理之学与事功之学有一判释,其中特别用很长的篇幅对永嘉党派的叶适展开批评,或者说是针对叶适对理学和孔子后学的批评进行辩正。叶适尊崇《尚书》、《周礼》,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36]这是牟宗三先生所难以接受的,因为后者强调是正是不可以把孔子所传之道与三代以下所传之道混同为一。牟先生指出:
“然自孔子对道之本统之再建言,则亦可以说一而不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王者开物成务之尽制,是原始的综合构造,是皇极之一元,而孔子对于道之本统之再建则是太极人极与皇极三者之并建,而以太极人极为本,以皇极为末:太极是天道,人极是仁教,皇极是君道。”[37]
三代以迄周公所传之道,乃是有君道而无天道与仁教,所以只能从政治的层面,从王者尽制的层面说;至于“圣”(德)的方面,则只能说是在“特殊境况”(“社会生活关系”)中有所体现,尚没有达到自觉的、普遍的层面。孔子则是三极并建。因为孔子“虽不得其位,而其德足以笼罩之”,[38]就是说外王层面的某种欠缺并不影响孔子之道的完满性,我们自然也可以(或曰也只能)这样理解孔子后学和理学家的思想。牟先生说:
“是以孔子者对道之本统之再建者。曾子、子思、孟子、《易传》乃本孔子之仁教而前进者也。故真传达孔子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易传》以及程、朱、陆、王也,决不在叶水心也。此一传统在以往虽较偏听偏重内圣一面,然此一面却是仁教之本质的一面。”[39]
牟先生复对宋明的义理之学(内圣之学)有一判释,此判释构成了他重建道统的一个关键环节。此判释是基于他对儒家经典的认识,或许我们亦可以反过来说是对宋明理学的判释影响到他对儒家经典的认识。
确切地说,对《大学》之义理归趣及其地位的论定成为牟先生重建道统的重要一环。尽管他曾认定“以曾子、子思、孟子及《中庸》、《易传》与《大学》为足以代表儒家传承之正宗”(排除了子夏、荀子),乃是宋明儒的一大贡献;但落实地说,他实际上认为把《大学》列入其中只是程颐、朱熹一系的特殊观点。[40]
牟先生的判释有一标准,此标准以他的所谓“道德的形上学”为依归。道德的形上学的核心之点无非在于:一方面就实践方面说,心必须能够通达上去,成为一超越的实体义之心;另一方面就存在方面说,理必须能够落下来,成为一即存有即活动的、心即理之理。牟认为在此前提下才能真正把宇宙存有论与人的道德实践打成一片,成就一儒家所特有的实践义的“道德的形上学”。
把心、性、天的统一、同一,即心即性即理即天(“即存在有即活动”)判定为儒家的终极立场,此一标准显然是来自陆王心学。[41]牟宗三先生不仅要据此衡定儒家思想后来发展,而且要据此衡定儒家的经典,衡定《大学》的精神义理,他指出:“尧典《康诰》言‘德’或‘峻德’皆指德行说,那时似更不能意识到本有之心性。《大学》引之,似亦并未就德行再向里推进一步说本有之心性也。须知《大学》并不是继承《论》、《孟》之生命智慧而说,而是从教育制度而说,乃是开端别起。虽为儒家教义之所涵摄,然不是孔、孟之生命智慧之继承。”[42]所谓“本有之心性”即是“心性天通一而无隔”之心性,也就是《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之心性,此心性是关涉到终极的创造性的层面来说,关涉到宇宙存有与人道德实践之最后根据来说。牟认为,《大学》中没有达到对心性的这样一种理解,其所谓“德”或“明德”只是在“德行”上说,而非“德性”上说,“‘德行’是果上之词,意即光明正大的行为。‘德性’是因上之词,意即吾人本有之光明正大的心性。”[43]亦可以说《大学》是就德行而言德行,而没有能够“就德行再向里推进一步说本有之心性”,没有能够由德行再提升一层而言道德行为之超越的根据。牟由此判定《大学》并非是由《论语》、《孟子》之精神方向发展而来,且亦不是与《论语》、《孟子》处于同一层次:
“《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不是同一系者,亦不是同一层次而可以出入互讲者。《大学》是从另一端绪来,可以视为儒家教义之初阶。由《大学》而至《论》、《孟》、《中庸》、《易传》是一种不同层次之升进,亦是由外转内之转进。”[44]
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讲出了三种《大学》:一是他本人所阐释的《大学》,且被说成系《大学》之本义。而其中的关节点即在于认定《大学》之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不能“从因地上看”,因为其所谓“明德”只是从“德行”上说,而不是从“德性”上说;是从道德行为的层次上说,而不是从本源心性的层次上说。[45]并由此将“大学”与孟子学“加以区分,判定它们是属于不同的义理系统和不同的义理层次。
二是程颐、朱熹一系的《大学》。宋明儒所论《大学》皆非本来意义的《大学》,他们对《大学》的义理有一提升,力图把之纳入《论语》、《孟子》的系统说明之;“宋儒自伊川着重《大学》之致知格物,遂想将《大学》纳于孔孟之生命智慧中而一之,因此遂将‘明德’就德行向里推进一步视作本有之心性。宋明儒于此皆无异辞也。”[46]把《大学》之所谓“明德”“推进一步”,由此说“德性”,说“本有之心性,”说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源和超越根据,此方面宋明儒“皆无异辞”。分歧产生于对此“明德”的进一步规定。依牟先生所见,朱熹以《孟子》、《大学》“出入互讲”,其结果不是把《大学》讲上去,而是把《孟子》讲下来,“朱子援引孟子以迁就《大学》,以《大学》为定本,而将孟子之本心拆为心性情三分,而心只讲认知义。”[47]心、性(理)关系被置于认知义的能所关系中来讲,这是将《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之“心性天通一而无隔”的、“立体创造”的纵贯系统,转变为以《大学》之“致知格物”为依归的平铺的、能所相对的“横摄系统”。
三是王阳阴、刘蕺山的《大学》。宋明儒中真能够把《大学》讲上去、对其义理有一提升者,是王阳阴、刘蕺山。可以说阳明亦是以《孟子》与《大学》“出入互讲”,但与朱熹不同,他不是以孟子迁就《大学》,而是以《大学》迁就孟子,无论是其对“明德”还是“致知格物”的讲法,都是以孟子为依归而远离《大学》之本义。“刘蕺山就《大学》言诚意,其背景仍是《中庸》、《易传》与孟子”,[48]亦非《大学》之本义。
在有关《大学》的三种讲法中,牟先生是主张对《大学》之本然与义理之当然加以区分,并由此形成他对于《大学》的批评。阳明、蕺山则是以义理之当然统摄《大学》之本然,此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亦不失为一种讲法,至少在牟先生的系统中可以如是说。惟伊川、朱子是“顺着”《大学》讲,遂形成儒学发展中(相对于《论语》、《孟子》、《易传》而言)的一种转向。
说程伊川、朱晦庵是“顺着”《大学》讲,这并不等于说其所讲论者尽合于《大学》的原意。从牟先生的有关论述来看,要而言之,他之不满于《大学》者无非是以下两点:一是《大学》没有达到儒家(特别是思孟、陆王一系)心性本体论的层次,没有提出一个天道性命相贯通的心性概念,甚至也没有向这个方面去讲,故无论是讲知识(“致知格物”)还是讲道德(“明德”、德行),都只是在一个现实的、平铺的、横摄的层面来讲,而没有形成由内在而超越或由超越而内在的所谓“纵贯”、“直贯”系统;二是,牟先生所最不满意者,当是《大学》经文中的下面一段:“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如果把“致知格物”与“诚意”套在因果关系中讲,并以前者为后者之因,则不免是“以知之源决定行之源”,由此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自律道德。
不过在牟先生看到,《大学》中没有论及“本有之心性”这一点是确定的,宋明儒把《大学》之“明德”提升到本源心性的层面来讲那是另一回事;而把“格物、致知、诚意”连贯起来讲及对三者涵义的解析和三者关系的认定,则可以说在《大学》中是不确定的。[49]如“诚意”传的解释,就并没有把“格物、致知、诚意”置于一个因果序列来讲,只是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且最终归结于“慎独”工夫上说,“是即打断致知与诚意之因果关系,而于诚意则单提直指,而以‘慎独’之工夫实之。”[50]这也说明经文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在程颐、朱熹这里,此一条自己被赋予某种确定的涵义,“格物、致知、诚意”被明确置于一个因果序列来讲,“格物致知”被诠释为“即物穷理”(牟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判释,言伊川、朱子一系所谓“即物穷理”乃是指“即物而穷其存在之理”,或者说是“就事事物物之存在之然而究知其超越的所以然”),因而似乎就无法逃避所谓“以知之源决定行之源”的责难。
与上面谈到的两点相联系,在《大学》中所谓“止至善”如何落实,或归于何处,可以说也是不确定的,因为《大学》之所谓“德”或“明德”并非是在终极的层面(本源心性或终极存在的层面)来讲。而在宋明儒学中则有一落实,阳明、蕺山是落在心性处讲,伊川、朱子是落在“存在之理”上讲,或者说是落在格物致知以穷“存在之理”上来讲。阳明、蕺山是以《孟子》、《中庸》说《大学》,自然非《大学》之本意;伊川、朱子所讲,亦非《大学》之本意(《大学》还只限于在“事”上说,而不是就“理”上说),但此一系统,却是“直接从《大学》上顺着讲而即可讲出者。”[51]
程颐、朱熹之所谓“从《大学》上顺着讲”,乃是使《大学》中所不确定者成为一确定者,由此遂开出一个既不同于《论语》、《孟子》、《中庸》、《易传》,亦有别于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胡五峰、刘蕺山(所谓“宋明儒之大宗”)的义理方向。[52]
牟先生把伊川、朱子一系的“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判释为“顺取之路”。“顺取之路”即是知识之路。道德不能循顺取之路而只能靠“逆觉体证”。逆觉体证也无非是本心性体的自明自了、自我呈现,此所谓“心”当然不是一形而下的“心气之心”,此所谓“性”也不能是一“只是理”、“只存有不活动”的、抽象的本体论存有。所以,在牟先生“道德的形上学”的系统中,真正的自律道德只有在“心即理”的意义上才能成立。牟先生批评《大学》的目的在于批评伊川、朱子。他要由此翻一个儒学发展史上的大案,把历来被尊为宋明儒之正统和集大成者的朱子判为“别子为宗”,把伊川、朱子一系判为“宋明儒之旁枝”。这成为他重建儒家道统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
3、衡论满清以下中国学术思想的传衍发展确定熊十力哲学的历史地位。尽管熊十力先生后来被视为新儒家学派的宗师,但在牟宗三先生的视野中,熊氏哲学的意义首先并不在于开宗立派,而在于维系儒家道统的一线之延。
牟先生在讨论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思想学术时指出,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之核心的“生命的学问”实早已断绝,“断绝于何时?曰断绝于明亡。”[53]满清三百年乃是民族文化生命的一大曲折,其中所造成的种种“歪曲的遗毒”并没有随着满清的灭亡而有所改变,生命的学问仍沉晦不显,“只有业师熊十力先生一生的学问是继承儒圣的仁教而前进的,并继承晚明诸大儒的心志而前进的。就我个人说,自抗战以来,亲炙师门,目击而道存,所感发者多矣。故自民国三十八年以来,……乃发愤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开民族生命之途径,扭转满清以来之歪曲,畅通晚明诸儒之心志,以开生命之学问。”[54]
当年牟氏初见熊十力,曾听得熊先生一声“狮子吼”:“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55]此言在熊先生处不是戏语,在牟先生处亦看得很严肃,此方面熊氏师徒表现出强烈的承当意识,认为惟有他们才能接续晚周及宋明诸儒之余绪。牟先生曾不止一次谈到熊、冯之间那个有关良知是“假定”还是“呈现”的公案,认为熊先生所言“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这霹雳一声,直是振聋发聩,把人的觉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层次”,“直复活了中国的学脉。”[56]此前自明亡,满清三百年,直至“胡适以来,一般名流学者”,“滔滔者天下皆是,人们的心思不复知有‘向上一机’”。[57]
说熊先生“复活了中国的的学派”,此所谓“复活”可以理解为“慧命相续”,牟指出:
“熊师之生命实即一有光辉之慧命。当今之世,唯彼一人能直通黄帝尧舜以来之大生命而不隔。此大生命是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之合一。他是直顶着华族文化生命之观念方向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源而抒发其义理与情感。他的学问直下是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这两者原是一下子冲破而不分。只有他那大才与生命之原始,始能如此透顶。这点倒更近乎《中庸》、《易传》的思想。”[58]
说熊的思想“更近乎《中庸》、《易传》”,这显然是强调其思想中超越的一面。牟又认为,熊先生的思想境界是“打开天窗,直透九霄”,“在这一点上,说一句亦可,说许多句亦可。在说许多句上,牵涉时下知识学问时,其所说容或有不甚妥贴处,但若不当作问题或技术上的事看,则无论如何,皆足启发。”[59]这是说对熊先生的著作,不可以单纯从“学”的方面、从知识方面看,更要从“道”的方面、从生命方面看。因为熊先生的学问,“与一般人的并不一样,不能用一般的标准来衡量他。假如从一般的专家学者的立场看,他的书中可批评的地方很多。”[60]孜孜于名言、概念,说他某句经讲的对与不对,这都是很外部的,因为熊先生思想的价值不在于此。熊先生思想的意义在于他的原始智慧和生命承当,“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这是熊先生的功劳,是熊先生开始把这传统恢复过来的。”[61]
熊先生所恢复的传统,不是知识的传统,而是“道”的传统。此传统亦无妨于说是一种“学”或“学问”,但它不是知识的学问,而是生命的学问。此所谓道的传统或生命的学问,落实地说,实际上是指儒家的超越心性论或称之为心性本体论系统。牟先生指出:
“儒家义理规模与境界俱见于《易经》与《孟子》,而熊先生即融摄孟子、陆王与《易经》而为一。以《易经》开扩孟子,揽以孟子陆王之心学收摄《易经》,直探造化之本,露无我无人之法体。”[62]
把孟子的心性论与《易》、《庸》的宇宙本体论融为一体,彻底打通天人的界限,开出一“心性天通一而无隔”的义理系统,这正是宋明儒治学的紧要处,熊先生也正是这一点接上和复活了“中国的学脉”,“故儒学之复光,中国文化生命之昭苏,至先生始真奠其基,造其模,使后来者可以接得上,继之而前进。”[63]
从道统之传承方面看,牟先生明确表示他是“独尊吾师”。他不仅激烈地抨击胡适、冯友兰等,而且也批评梁漱溟、马一浮等。关于梁先生,牟氏虽曾称赞他“生命化了孔子”,但亦谓其“锲入有余,透脱不足,”晚年则更批评他说:“梁先生这个人对中国学问知识与文化意识都是很少的”,“他和熊先生不同,熊先生讲学或许有错误,但他的民族文化意识纵贯意识很强,而梁先生在这方面很欠缺,梁先生的头脑是横剖面的,如他的‘乡村建设’之理论便是在横剖面下了解中国社会而写出来的。他并没有通过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去了解中国社会,只照眼前的风俗习惯而想办法。”[64]“梁先生对中国的学问则欣赏王学再传门下的王东崖,对‘自然洒脱’一路颇寄其向往,欲由此而了解孔子之‘仁’。其实从这一路进去也可略有所得,但毕竟不是了解儒家的正大入手处。”[65]此类批评虽不免失之于片面和尖刻,但确实部分地反映出熊门一路与梁漱溟先生在思想取向上的某种差异性。
三、从儒家的道统论到新儒家的道统论
依陈荣捷先生说,“道统”一词虽由朱熹始正式提出使用,而道统观念却由来久远:“孟子首倡传授由尧舜经成汤文王而至孔子。韩愈首倡孟子之死,不得其传。伊川首倡其兄明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朱子之时,道统之传授由尧舜而至孔孟,而中绝,而二程复兴,成为一时之定论。”[66]此外,汉董仲舒等人的有关思想,似亦可论列其中,董仲舒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67]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道统观念虽由来久远,其间却又多有变化,特别是先秦以迄汉唐的道统观与宋儒的道统观实有实质性的差异。依笔者之愚见,宋以前的道统观念的落脚点乃在于即“统”而言“道”,宋儒的道统观念则可以说是即“道”而言“统”,前者更偏重于历史,后者则侧重于哲学。换句话说,自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到韩愈排定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传道谱系,都是要通过历史的传承来确定孔子儒家的地位,孟子谓“孔子,圣之时者也”,董仲舒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韩愈著《原道》,排佛老,都有即“统”而言“道”或即“统”而立“道”之意。而宋儒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基于他们对于儒家之道的理解来排定历史上的传道谱系,这与他们以“四书”取代“五经”的权威是一致的。
牟先生的道统论是接着宋儒讲的,尽管其对于传道谱系的排列与宋儒(特别是朱子后学)有很大不同。与宋儒相比,牟先生的道统观或许更堪称得上是“哲学家的道统观”。牟氏使儒家的道统观彻底摆脱了历史传说的因素,他曾论及儒家所谓传道之“传”与佛教禅宗的“祖师之相传”的区别,指出:“师徒相承只是外部之薰习,若夫深造自得,则端赖自己。然大端方向亦必有相契,方能说传。……生命之事至为殊特,亦至为共通。若能相契,则前后相辉,创造即重复,所谓其揆一也。有引申,有发展,有偏注,有集中,然而不碍其通契。此之谓传,”[68]显然,此所谓“传”已不是指谓事实层面的前后相承或师徒相续,而是指超越的生命层面的相通相契、“前后相辉”。从此种意义上说,道统之传亦不一定从“尧之所以授舜”、“舜之所以授禹”方面来讲;[69]孔子晚年是否“独进曾子”亦不重要。[70]
儒家的道统论可以说有三个面向:一是广义的判教,此在孟子那里为辟杨、墨,在韩愈、宋儒那里则为排佛、老;二是要在现实的政治权威之外标立一超越的尺度,此是相对于“政统”(或“治统”)而言道统;三是就儒家学术思想自身而言,道统亦区别于“学派”而有其特定的涵义。
牟三宗先生言“西方道统在基督教”。[71]此所谓基督教之“道统”与儒家之道统在表现形态上自然有很大的区别,其中特别是体现在“道”与“政”的关系方面。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没有出现西方近代的政、教分离,也没有出现西方历史上教权高于皇权的情况。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教与政之间表现为更为复杂的关系。儒家的道统观念曾长期为人们所诟病,视为陈腐的象征,并与封建专制扯在一起,不惟五十年代后的大陆学术界是一片讨伐之声,即便是五十年代前的保守主义大师们似乎也讳言于此。
就现实的层面而言,宋明以后的历史上也确实出现过道统观念为当权者所扭曲和利用,使道统隶属于政统、利用道统的权威来强化自己的统治和思想专制的情况。但是,就本来意义而言,宋明儒即“道”而言其“统”的用意正是要强调和凸显儒家思想超越于现实的社会政治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儒家之道作为一种自本自根、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精神法统,它有自己的理想性、必然性、永恒性和超越性,而不能为现实的政治权势所左右,这也是儒家之批判精神和抗议精神的根据所在。朱熹言孔子:“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72]就现实的功业而言,孔子本不能与尧、舜相比,但“圣”有其独立的尺度和意义,无论此意义在现实的层面能否落实,都不影响其价值和完满性,宋明儒正是在“圣”的独立意义上言“道统”。孟子所言“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73]亦只能从此方面理解。
所以,必须把道统观念在现实中遭到的扭曲和利用与道统观念的本来意义,严格加以区分,所谓儒家道统的“封建性”乃是来自当权者对于道统的扭曲和利用,而非儒家道统本身。
道统是属于“教”的层面,因而在“教”与“政”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教”与“学”的关系问题,或称之为“道统”与“学统”的关系问题。此所谓“学统”又与牟宗三先生“三统之说”所论之“学统”涵义不同。“三统之说”中所谓“学统之开出”乃是指开出科学之统,实际上就儒家学术思想自身而言亦存在一个学统问题,即儒家思想作为某种知识系统的传衍、发展和演变问题。余英时先生说:
“新儒家正是以‘道’的继往开来者自许的。依《中庸》‘修道之谓教’之说,则新儒家所倡导的其实是‘教’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学’。从他们的观点说,‘教’是第一义的,‘学’则是第二义或第二义以下的。因为‘教’必归宿于总持一切的最高真理(道),异于‘教’的便成‘异端’;‘学’则是多元的、相对的、局部的,往往演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纷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是如此,现代的专门学科尤其是如此。”[74]
“为学”与“为道”的区分原是中国哲学本有之义,此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哲学即哲学即宗教的思想特质决定的,只要我们承认儒家思想不只是一套知识系统或架构体系,此种区分就仍然有其意义。新儒家的努力无疑是在“道”(教)的层面,他们也确实以道统的承担者自许。就熊、牟一派的观点而言,他们基本上不承认纯知识层面的探讨对于儒家传统的弘扬和重建有多大的意义,重要的在于对“道”的体悟,相应与不相应只能从此种体悟上说。
由此出发,就儒家思想自身而言,他们也不认为有独立于道统之外的纯客观的“学统”。熊十力作《原儒》,在“原内圣”、“原外王”之外另有“原学统”一章,核心是讲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为“凡经,有孔子亲作者。有孔子口说,而弟子记之者”,并指出:
“孔子上承远古群圣之道,下启晚周诸子百家之学,其为中国学术界之正统,正如一本众干,枝叶扶疏。学术所由发展也。”[75]
熊先生的经学是服务于他《新唯识论》一书所建构的心性本体论的哲学系统。牟宗三先生的思想则更为简捷,他认为儒家的道统不需要从经学讲起,孔子思想的意义在于他的“仁教”,此与孔子是否作“六经”没有直接的关系。
刘述先先生论及宋明儒家的思想特征,指出:
“如果以宋儒为标准,则内在中心的体证是最重要一件事,章句的解释其余事耳,学问的目的是在见道,其目的本不在词章记诵,更不在客观的餖飣考据的工作。对于文字的解释,一以主观的体验为基础,故此对于文义的引伸,不只当作一种错误或过失,反而被当作一种慧解的印证看待。”
“我并不是说,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不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构成一些缺点。在这样的精神主导之下,客观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道统与学统本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若纯由道统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够问,生生之仁的体证是不是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余有关考古、历史、考据的问题都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76]
这些话亦可以用来描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特征,他们同样是强调“内在中心的体证”,而卑视词章记诵和餖飣考据。熊、牟等人此方面较之宋明儒(特别是较之宋儒)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宋明儒是相对于“汉学”而彰示“理学”,当代新儒家的道统则具有针对乾嘉考据学、“五四”以后的新考据学和科学实证主义的意义。牟宗三先生言“自明朝一亡,乾嘉学问形成以后,中国学统便断绝了。”[77]此所谓“学统”不是指客观知识的学统,而是指述之于形上体验和生命承担的道统。说熊十力先生“复活了中国的学脉”,也是就重开“内在中心的体证”之门和承担道统而言。
此方面钱穆先生的观点确有区别,可以说他较为重视“学”的一面,似亦不赞同“为学”与“为道”的截然区分,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力主打破汉学与宋学之间的门户,对清代考据学亦多能够正面肯定其价值。余英时先生说:“钱先生最初从文学入手,遂治集部。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顺理成章进入清代的考据学。清代经学专尚考证,所谓从古训以明义理,以孔、孟还之孔、孟,其实即是经学的史学化。所以钱先生的最后归宿为史学。”[78]余先生并且认为“‘史学立场’为钱先生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79]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所谓“史学立场”也并没有使钱先生完全否定“学”与“道”两个层面的区分,余英时先生的文章中亦认为钱先生对儒家的看法可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历史事实的层次;第二是信仰的层次。”[80]就信仰的层次而言,儒家当然不只是“学”,而是“教”。既是“教”则不能排除超知识的体悟、体证。事实上,当钱先生说“历史就是我们生命。”“是精神的生命”,“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81]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这是由纯知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所以,尽管我们可以由钱穆先生对宋明儒道统观的批评中得出如下结论,即钱先生主张对文化传统采取一种整体(历史的)观念,而不主张采取一种超越的(哲学的)观念;[82]但我们却不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钱先生否定某种超越的、历久常新、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文化生命)的存在。而肯定此种文化精神、文化生命的存在,正是儒家道统观念最本质的内涵。
历史上儒家的道统论是落在某种传道谱系上来讲,但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文化意识,此文化意识是落在民族文化的薪火传承上来讲,就此文化意识而言,儒家的道统观念有其超越性和绝对性,而落实到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则往往是因人因时而异的,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无视于上述两个层面的区分,将某一具体的传道谱系加以绝对化,将之等同于文化传承本身,道统观念就会沦于保守、僵滞。宋儒的道统论后来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和排他性,正是与此有关。
当代新儒家也颇有宋儒“道统不传久矣”的感叹,但与后者相比,当代新儒家是更多地凸显了道统观念作为表现某种普遍的文化意识的层面,这使得他们能够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传道谱系而言道统。事实上,在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学说中,“道统”一词通常是泛指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在此种意义上,所谓“哲学家的道统观”与“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之区分亦显得并不十分重要。相对于孟子辟杨墨,韩愈、宋儒排佛老,当代新儒家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彰显的是一种更为普泛的民族文化意识。
至于落实到究竟谁最堪承担道统之传,或者谁真正把握了儒学精义,则不免见仁见智,受到立论者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视域等诸方面的限定。例如牟宗三先生的朱子学,自然称得上是朱子研究和宋明儒学研究领域的大手笔、大动作、大突破,但亦只能说是牟先生一系的特殊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对“当代新儒家”作过于偏狭的限定,那么牟先生的观念在当代新儒家阵营中亦属特殊。牟曾经激烈地批评冯友兰先生的朱子学,两人的哲学立场亦截然不同,但就一味地把朱子向客观实在方面讲这一点而言,却又不免殊途而同归。
还有一点儒要指出:与某些论者的批评恰恰相反,当代新儒家道统论的问题可以说并不在于主张超越体证,而在于知识化的趋向。程明道曰:“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传已之心也。”[83]“传已之心”一方面是“默识心通”的内在体验,另一方面则是“窗前草不除”、“吟风弄月,浩然有吾与点也之意”的“圣人气象”。而在当代新儒家这里,所谓道统之传则庶几成为纯粹学理上的判释,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为道”也即是“为学”,只不过此所谓“学”在内容特征上被认为与科学知识之学不同罢了。就“道”(教)与“学”的关系而言,在区分“为学”与“为道”的同时,儒家之道又并不一般地排斥“学”,不排斥且十分重视历史层面的知识与学养,它所强调的是必须有由艺进于道、由具体的知识达于形上的解悟的“向上一机”。叶适在批评宋儒的道统论时,曾指出儒家之道“不特以身传”,乃“存之于书”,“得之于言”,此原本不错。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典籍并不能等同于古圣贤哲人活生生的生命世界和精神境界本身,那么如何能够赋予典籍以真实的生命,即如何能够通过典籍而又超越乎其籍去理解和再现先圣先哲的精神境界呢?这就不是一个纯粹知识性的探求所能回答的问题。
与基督教相比,儒家的道统之传可以说更多地有赖于后儒的体证与诠释,所谓“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这又使得普遍的道与具体的传道谱系之间,呈现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儒家之道是要通过具体的传道谱系来体现和被人们所理解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以把某一具体的传道谱系等同于儒家之道本身,因为任何对于儒家之道的解释及此相关的对于历史上之传道谱系的判释,都不可能具有唯一性和绝对性。从此种意义上说,儒家之道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并不排斥它向现实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所展开的无限可解释性和开放性。
注释:
1 《钱穆与新儒家》一文收入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一书(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
2 由此方面系统回应余英时先生的批评者,可参见李明辉《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一文,载《鹅湖月刊》第224期(1994年2月)。
3 参见《犹记风吹水上鳞》,第56、70页。
4 参见《钱穆与新儒家》第95页。
5 《孟子·公孙丑下》
6 韩愈:《原道》
7 《犹记风吹水上鳞》,第70页。
8 参见李明辉《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
9 《十力语要》,卷三,第44页。
10 参见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新儒家评论》第一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52页。
11 《原儒》,上海龙门联合书局版,上卷,第8页。
12 《读经示要》,重庆南方印书馆1945年版,第85年。
13 《原儒》上卷,第51页。
14 同上。
15 参见《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 参见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
17 《三松堂全集》第5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18 参见《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47页。
19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5页。
20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版,第61页。
21 熊十力:《读经示要》,台北明文书局1984年版,第464页。
22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97页。
23 同上,第192页。
2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3页。
25 同上,第14页。
26 同上,第12页。
27 熊十力说:“凡经,有孔子亲作者,有孔子口说而弟子记之者。”(《原儒》上卷,第6页。)
28 《心体与性体》(一),第245页。
29 同上,第192—193页。
30 《原儒》上卷,第13页。
31 《读经示要》,第328—329页。
32 《生命的学问》,第101页。
33《礼记·乐记》
34 《梁漱溟全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104页。
35 同上,第115页。
36 叶适:《习学记言》。
37 《心体与性体》(一),第262页。
38 同上,第263页。
39 同上,第278页。
40 同上,第19页。
41 牟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判释,以三系说取代程朱、陆王之说。
42 《心体与性体》(三),台北正中书局1969版,第369页。
43 同上,第368页。
44 同上,第383页。
45参阅《心体与性体》第368页。
46 《心体与性体》(三),第369页。
47 同上,第383页。
48 《心体与性体》(一),第20页。
49 《心体与性体》(三),第403—404页。
50 同上,第403页。
51 《心体与性体》(一),第20页。
52 同上,第49页。
53 《生命的学问》,第36页。
54 同上,第38页。
55 牟宗三:《五十自述》,鹅湖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56 同上,第88页。
57 同上。
58 同上,第102页。
59 同上,第103页。
60 牟宗三:《时代与感受》,鹅湖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61 同上,第268页。
62 《生命的学问》,第115页。
63 同上书,第117页。
64 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当代新儒学论文集·总论篇》,文津出版社会1991年5月版,第6页。
65 同上书,第7页。
66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429页。
67 《贤良对策三》。
68 《心体与性体》(一),第258页。
69 朱子《中庸章句序》:“盖自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
70 参见《心体与性体》(一),第258页。
71 《生命的学问》,第61页。
72 《中庸章句序》。
73 《孟子·公孙丑上》。
74 《犹记风吹水上鳞》,第80—81页。
75 《原儒》上卷,第47页。
76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425—426页。
77 《时代与感受》,第267页。
78 《犹记风吹水上鳞》,第35页。
79 同上。
80 同上,第47页。
81 参见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5—7页。
孟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6
令人吊诡的是,文化经典热持续升温之时,恰是鲁迅作品逐渐淡出语文教材之日。鲁迅博大的思想、卓越的才华、辛辣的文笔、韧性的战斗风格,深受读者喜爱,上世纪九十年代语文教材选入鲁迅作品仍然多达30篇。然而教师们对鲁迅作品的隔膜和对鲁迅思想的错误解读,对鲁迅“民族魂”的拔高阐述,让学生“谈鲁色变”,对鲁迅作品望而生畏,编者寄希望于通过鲁迅作品的丰富内涵,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对未成年人的有效引领的梦想几近落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文化经典教学不能重蹈覆辙,文化经典教学应正本清源、返本开新、与时俱进,把握好教学原则。
一、正本清源拒儒术
有一些人喜欢把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清末的衰落耻辱史,归罪于孔子的思想,把政治的东西归罪于文化,这是错误认知,也是我们语文教师要厘清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文化经典教学,不拒儒术无以尊孔孟,不正本清源无法去伪存真,只有厘清精华与糟粕,才能真正利用儒家经典的精华,将中华文化的瑰宝发扬光大。我们要向学生们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儒学分成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内涵不一:孔孟原创儒学,体现为道德行为准则;汉唐儒学,是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宗教化过程;宋明儒学,儒学吸收佛道思想开始理论化,并形成形而上的哲学体系;现代新儒学,则把儒学与当时传入的西方思想结合起来,同时力图把儒学宗教化。如此说来,孔孟儒学与两汉儒学、程朱理学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要弘扬传承的恰是孔孟原创儒学。为了方便论述,我们暂且将两汉以后的儒学称之为伪形儒学,或儒术。尽管这种伪形儒学渊源自孔子,但显然与孔子无关,也是作为先知者的孔子不能、也不应该负责任的。
笔者以为,孔孟儒学与伪形儒学有三点不同。
其一,社会角色不同。孔孟首先是当时体制的“异见人士”,是当时执政集团的批评者,他们言论的重心都是在向执政者施加压力,时有尖锐的批评和斥责的话语。孔子从来不是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各国国君,夸奖不多,指斥不少,总是不厌其烦地劝说他们推行仁政,劝告他们爱惜民力,富民教民。其原创之道,就君臣而言,主要是针对君的,就官民而言,主要是针对官员的,“苛政猛于虎”的叹息,也主要是叹息给执政者听的,结果没有一个国君愿意接受他们,更不想实践他们的主张,孔子成为“丧家狗”,原因就在于此。与“温而厉”的孔子异曲同工,孟子更是将大丈夫人格发挥到极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那正气浩然、高度自信、傲岸清高、藐视权贵、激烈尖锐、刚直坦率的人格形象,孟子从不轻易与统治者合作,总是以“君王之师”自居,并迸出了“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民本思想。
伪形儒学则始终是历代封建体制的维护者、迎合者,他们对当政者说的话淡化了,弱化了,忌讳化了,君轻民贵的话更不敢说了,或者把孔孟说给当政者听的话扭转为针对民众去说了,如原本针对君王官员的闻过则喜,三省吾身,转而让民众去身体力行;或者把给民众说的话一步步强化,提升到重要位置,成为民众的人生之纲,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本来是指导规范君王和官员道德行为的孔孟之道,变成了指导规范老百姓道德行为的孔孟之道,变成了维护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和道德利器。这不是孔孟和孔孟之道的过错,而是孔孟的不幸。
其二,社会功能不同。孔孟学说是爱人、立人、达人的智慧之说。孔子思想究其根底,仁字唯一,仁有三义,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三是君子之仁。故孔门之学,被称为仁学。正因如此,孔子仁学才成为国人安身立命的力量源泉,才奠定起国人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处事原则和民族性格。而孟子思想最闪光、最具进步性、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他的民本思想,时至今日,这种思想仍闪耀着民主的光芒。
伪形儒学则是治人、吃人、约束人的实用之学,王霸杂用,儒法糅合,孔孟原创儒学之道统几近断绝。西汉初年董仲舒从孔子思想中找到了能够为统治者所用,有利于巩固统治的伦理精华与臣服社会的道德利器,于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而且历代皇一以贯之的运用着儒术,以统治中国社会。由此,儒术得以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政治文化当中,占据着主导性质的统治地位。应该说,儒学的流变伪形,由孟子到董仲舒,到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虽然都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时代因素,但是后世儒者不能从根本上把握孔孟学说的真精神,过分注重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过分注重自身的时代体验,则是导致流变伪形的最深刻原因。孔孟学说的最终沦落,后世学者难辞其咎!
其三,价值取向不同。孔孟思想是符合人伦、人性、人生需求的思想体系。孔子一生除了短短四年的从政经历外,大部分时间是处于贫穷、艰难和动荡不安当中的。正是始终处于颠沛流离的人生处境,孔子的思想与追求才始终是以保障和实现社会安定和谐为指归,而这种思想和追求无疑是价值向上的!更令人称奇的是,孔孟学说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种二重性立场,使得孔孟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指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未艾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桥梁。正因如此,孔孟思想才得以穿越两千多年的时光,超越阶级与时空的局限,历经岁月的洗礼,始终保有人生智慧的魅力与人性的光辉,始终保有历久弥新的生命活力。
伪形儒学则是集专制性与保守性于一体,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与追求美好生活背道而驰。为了迎合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把孔子的思想彻底颠倒;程颐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南宋朱熹则把它作为劝人守节的工具。这对于帮助统治者奴役人民,保障封建王朝的皇基永固,国祚长久,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却是以牺牲和剥夺民众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其价值无疑是向下的。儒学从此少了博爱与仁善,多了暴力与兽性;少了维新与变通,多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儒学从此成为禁锢思想、障碍前进的绊脚石,最终中国积贫积弱,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大门,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可悲之路。在影片《走向共和》中,孙中山与康有为有一段精彩对白:“四书荼毒生灵,五经钝化人心,三纲生产奴才,五常捆绑性情,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众,食不能果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爷大官,骄奢淫逸,盘剥不止,这是经济之病;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华夏四千年的专制之病。”诚如此言,那么这种专制之病就源于伪形儒学之弊!
二、返本开新拒偏狭
我们提倡进行文化经典教学要校正偏狭心态。
1.孔孟思想可以与公民教育相兼容。众所周知,教育的根基在立人,在于培育千百万“大写的人”,在于塑造具有健全人格、思想自由、独立思考、合法判断的现代公民。对于“传统文化复兴”,有人喜上眉梢,有人忧心忡忡,有人推波助澜,有人坚决抑制,对此评价的不同维度,甚至成为保守和自由的分界线。我们理解反对读经派的忧心,他们担心通过学习孔孟之道,会培养出一批批恪守本分、安于现状、甘当奴隶的顺民。其实这种担心是多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反省与涤荡了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落后、愚昧无知的糟粕部分,并且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文明之光,引进了全新的思想体系与知识技能体系,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整合,做到了先进文化体系的本土化。我们进行文化经典教学完全可以与公民教育相兼容,我们不可能因为教学经典就妨害了对公民意识的培养!我们不妨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很小的城市国家,建国短短三十几年,就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新加坡成功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兼容并蓄,既吸收西方先进科学与技术,又弘扬东方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伦理道德,尤其注重利用儒家伦理来抵制西方消极文化的影响,通过儒家学说确立学生正确做人、服务社会、忠于国家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培养出品质优良的好公民。
2.孔孟思想可以与民主科学相兼容。追求民主,是人的天性;追求科学,是社会前进的趋势。民主普及于国人,功在上世纪初的启蒙运动,前后,民主与科学的观念传入中国,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两面鲜艳的旗帜。不必讳言,当今社会,我们最大的缺憾还是民主的匮乏与科学精神的欠缺。孔孟思想有精华,也有不足,它虽然也曾闪烁过“民主”的萌芽,但缺乏“科学基因”也是不争的事实,不可能完全靠它自己的力量将中国引上科学发展的大道,发展成为像美国那样领军世界科流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在研读孔孟文化的过程中,引领学生在汲取精神营养的同时,要把握和顺应世界潮流,主动融入世界文明;告诉学生在前行的道路上决不可自设羁勒,不能自以为是;启示学生文化是公器,其价值是普世的,一个有理性的人,可以兼容并包中西文化,对不同的文化都该加以尊重,协同发扬,并且相信各种文化成就都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融会的。
三、与时俱进拒过度
“营造书香氛围,诵读经典诗文”是当今中小学提得最响、最时髦的口号之一。然而,仔细观察、分析后,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的过度成分。
1.时间过度。有学者提出读经要融入到课程当中,殊不知,学生上课时间有限,除了读语文,还要读数理化、政史地,以及费时更多的英语课程。就语文课程而言,除了文化经典,还要阅读教材选文、文言诗词、经典名著、现代时文……时间费时过度,只能让学生心生厌烦,进而抛弃文化经典。
2.做法过度。去年新学期开始之时,有正规的通讯社在网站上了一群中学生穿着特制的汉代服装集体朗诵《论语》的情形,让人觉得做法过度。解读经典,弘扬传统文化,目的不是复古,不是向明清或唐宋或周公看齐,而是为了内化吸收,转识成智,从而更好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所以读解经典,我们要从外在的形式,转为内在的积淀。我们提倡慢读重读,凝神静气,静静的阅读,把内容连续起来,前后勾连,再三品味,举一反三,总结归纳。唯有静心慢读,我们才能更好的领悟,更好的渗透到经典之中,和圣贤达到共鸣。
3.解读过度。笔者以为,解读孔孟宜执两用中,还原真相,我们不能穿凿附会,为尊者讳;我们不能把孔子贬得一无是处,讥为“丧家之犬”;我们也不能将《论语》当成“心灵鸡汤”,全盘接受,盲目向学生传授。凡此种种,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解读过度的反映!以于丹《〈论语〉心得》为例,作为一家之言,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以此来对学生启智开蒙,则完全忽略了孔孟的“批评性传统”,回避了执政者的责任义务,而一味的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责,无疑也是一种解读过度,是我们断不可取的解读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