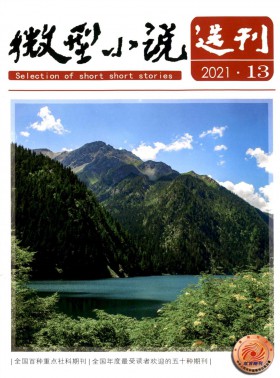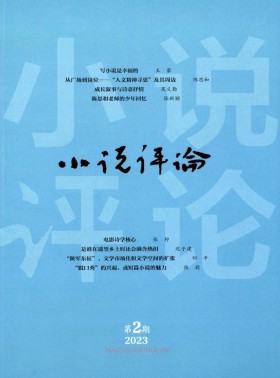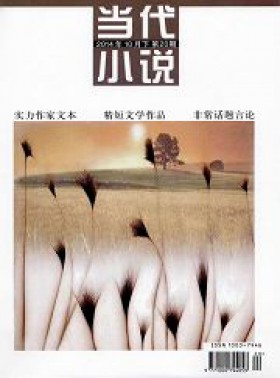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小说的生命哲学和文学史意义,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理想的小说不仅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叙述和语言上形成了成熟的风格,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美学品格,包含了丰富的文化诗学,而且,不能忽视的是,小说必然可以给人以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这是美学意义上最高的小说境界。那么,苏童作为当今文坛重要的小说家,他是如何思考这个世界,他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了怎样的哲学内涵呢?苏童是个讲故事的好手,但他的故事不以情节取胜,在他的小说中最打动人的是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对历史幽密的探寻。苏童一直是一个关注人性的作家,但他的大部分小说书写的却是与生俱来的人性缺失。在他的生命哲学中,人性的晦暗不随时间和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展示的是人性深处积淀的惰性和丑恶,并通过“人性之恶”,表达了对人性的悲观和绝望。在苏童那里,生命过程充满了种种苦难、不测、难以逃脱的悲剧宿命,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生存本身荒诞而虚无,理想和现实永远背离,青春是无法弥合的伤痛。而苦难的生命历程既无法逃离也无法救赎,唯有死亡是生命的最后归宿。 一、与生俱来的人性缺失 “性善论”和“性恶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两种主要的人性学说,然而,不管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人性都在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外在的环境影响下不断变化。尤其是在新文学以来的现代叙述中,人性的变化是启蒙现代性的重要诉求之一,五四文学的个性启蒙是期望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现代思想把人们从封建思想的牢笼里解放出来,个性解放和人性自由成为五四思潮的标示。五四时代进化论的思想也认为人是不断进步的、人性向善发展。在鲁迅的笔下,他期待如若有革命,像阿Q一样的民众是会觉醒并投入到革命中去的,而青年总是比老年进步。这样的启蒙的进化论思潮影响了五四一代的精英知识分子们。30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学则期待了人在革命中走向成熟,接收革命的洗礼并塑造坚强、刚毅的人性。当代文学中经典的红色叙事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人性在时间的流程中不断变化,趋于完善。 因此,在20世纪文学的主流叙述中,人性与成长环境、历史际遇密切相关。 但在苏童的小说中,人性却和历史进化无关,和时间变迁、空间转换无关,在少年、青年、老年的生命的自然流程中,不变的是人性的灰暗和颓废。苏童拒绝鲁迅式的启蒙期许,后期鲁迅虽然明明知道人类改良的无望,但他依然在绝望中前行,“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1]177这是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存哲学。苏童对人性也是失望的,但他既不反抗人性的沦落也不批判人性的黑暗,只是以一种超然的眼光看待他小说中的芸芸众生,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在“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城北地带》写了一群少年们的成长,他们内心的暴力和无名的欲望,他们对自我生活和对他人生活的毁灭,但他们的心灵和性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熟,“成长的未完成”也预示了人性的停滞。《刺青时代》中,幼年时代的悲惨经历和少年时代的暴力梦想摧毁了少年小拐,他成了一个古怪而阴郁的少年。在“枫杨树”系列中,“我”的祖父陈宝年、疯疯傻傻的幺叔、逃跑的陈三麦等在小说中都没有性格的变化。也就是说在苏童跨越了时间长度的叙事中,人性是基本不变的。甚至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人性也仍然是历史的轮回,单不说《妇女生活》中娴、芝、箫三代女性重复着同样的悲剧命运,虽然三个女性跨越了三个时代,但她们的人性弱点却一脉相承。《妻妾成群》中旧时代的颂莲们在陈府大院里的互相争宠和《另一种妇女生活》中新时代里顾雅仙们的明争暗斗也是殊途同归,流逝的只是时间本身,而不变的却是人性的晦暗。如果说现代性叙事强调的是历史进程中人的变化,以及宏大历史对个体生命的塑造和规约,那么,苏童的小说提供的则是人性的“不变”,人性深处那些不随时间改变的积淀和惰性。 既然在苏童那里,人性是不受历史进化影响的,人性是生来如此不会改变的,那么,苏童赋予他小说中的人物的人性内涵又是什么?说到底,苏童是个“性恶论”者,在他的小说中,人性之恶是贯穿了大部分小说的主题。但如果说人性之恶古来有之,那么面对人性的态度则有很大的不同。在批判现实主义者那里,作家面对人性之恶的现状痛心疾首,苦苦探询着改变人性的方法。 在自然主义者那里,文学的责任在于忠实地记述这种人性的现状,所谓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在存在主义者那里,面对人性的困境和悖论,作家们揭示的是生存本身的荒谬。而对苏童来说,人性之恶是生来如此的,人性的丑恶、卑贱、人心的冷酷、人与人的疏离是人性的本质性存在。在《1934年的逃亡》中,祖父陈宝年逃亡到城市过着淫荡糜烂的生活,全然不顾老家妻子儿女的死活。大伯狗崽在自己藏铜板的铁盒子丢失后,把幼小的弟弟妹妹吊起来暴打。 祖母蒋氏一生在苦难的命运中挣扎,但她同样借机打掉了环子的孩子。《妻妾成群》中,为了争宠,二太太如云不仅暗算颂莲,而且直接把三太太梅珊送上了死路。而颂莲对雁儿的惩罚也让人胆寒。《罂粟之家》中,老地主刘老侠在他弟弟弥留之际买走了他的墓地,沉草亲手杀了哥哥白痴演义,农村无产者陈茂在当上农会主席后强暴了美艳的刘素子。而苏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米》是人性之恶的一个典型文本,在《米》的人世风景中,人性的阴暗残忍、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敌对,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妹之间、情妇情夫之间的卑琐丑恶达到了极致,人与人之间相互厌恶和仇视、相互残害和憎恨让人触目惊心。苏童通过人性之恶的展示表达了对人性的怀疑,对人性的悲观和绝望。 在先锋作家中,残雪、余华、苏童都写到人性之恶,但苏童并不像残雪对人性彻底的绝望,即使人性的一点微光也受到质疑和嘲弄,也不像余华面对人性之恶的冷漠、冷静的叙述和极力渲染,使“人性之恶”在他那里成为一种的观念性的存在。不管是残雪还是余华,他们都拒绝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进行心灵探询,拒绝探寻人的善的存在的可能性。但在苏童前期小说中,虽然人性之恶是一个不变的主题,但他也写了人性的一点点温暖,像黑暗中的一点微光。即使像五龙这样的人性之“恶”的集大成者,苏童也赋予他内心的悲伤,“我对他是抱有同情的,在把他塑造成恶棍的同时,我觉得他是一个被玷污的人,是一个内心充满悲伤的恶棍。”所以,虽然在五龙的身上集中了人性恶的因素,但五龙同时也是一个被伤害的人,他从被大水淹没的枫杨树家乡逃向城市首先遭遇到码头帮人的欺凌,如果说饥俄带给五龙的是刻骨铭心的伤害,城市的淫荡对他来说是另一种压迫和欺凌。在城市里,虽然五龙最终拥有了一切,可城市给他的恐慌和恐惧却像梦魇一样永远缠绕着他,他常常在恍惚中看到被大水淹没的枫杨树家乡,到处是悲恸哀鸣之声,在城市的土地上,他常常觉得自己仍然在那列逃荒的火车上,永远都在颠簸流浪的途中。所以,在苏童的小说中,他写了人性之恶,人性的顽劣、卑微和暴虐,但他同时也写了生命的艰难和无望的挣扎。虽然人性之恶是苏童前期小说的哲学基础,但他的人性之“恶”中却仍然包含了对人本身的悲悯,如同对五龙一样的恶棍,你可以痛恨、惊诧于他的恶,但同时又对他的挣扎充满了悲悯。苏童对人性是失望的,但他同时也悲悯地注视着他小说中的人物,不诅咒、不抗议、不作价值判断。#p#分页标题#e# 因此,苏童小说中的人性哲学是超越道德判断的。 虽然,他书写了人性的丑恶、卑贱,人心的冷酷,人与人的疏离,写了“枫杨树乡下”和“香椿树街上”沉滞、压抑、冷漠的灵魂,与生俱来的人性缺失,但不是从道德的层面上予以观照,他写了人性之恶的极致,却悲悯着人性的恶和不堪。 正是因为苏童小说中细致入微的心灵书写、敏感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在观念的层面上呈示出人性的缺陷,而是从文本中自然流露出来,让你悲叹人世沧桑和命运无常。在《妻妾成群》中,颂莲受到来自大家庭的妻妾争宠的威胁,但她同时也暴虐地惩罚了丫环雁儿,可颂莲内心深处的压抑和悲伤却冲淡了这种“恶”的书写。她的落寞和伤感、无助,她对这个世界的恐慌和对死亡的迷茫,在小说中形成忧伤的抒情语调,冲淡了对人性中乖戾一面的书写。因为在陈府大院,颂莲同样是一个虚弱的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她的挣扎、她的恐慌、她内心的忧伤和绝望,使基于道德判断的价值取向失去了绝对性。“香椿树街”上生活着的无数卑微挣扎的生命,也是不能以简单的善、恶的道德标准来评判的。《城北地带》中,少年红旗怀着朦胧而狂乱的情欲强暴了少女美祺,直接造成了香椿树街上这个最美丽的少女的死亡,红旗的母亲为了挽救自己的儿子,要美祺承认自己是自愿的。 一个少年迷茫的情欲、一个母亲真实的悲伤,虽然直接导致了美的被摧残,但苏童仍然超越了道德判断的简单化倾向,他如此真实地描述了每个人内心的晦暗和真实的情感,让人性本身的粗粝坚硬地裸露。 如果说,善、恶的二元对立和对人性简单的道德判断完成的是一种明了的叙事逻辑,那么,苏童小说中人性之善、恶的哲学内涵则包含在厚重而芜杂的生活中,完成的是更为丰富的人性诗学。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说到“:如果我们想在走出这个世界的时刻不像进入它时那么傻,那就应当放弃方便的道德主义审判,并思索这些丑闻,一直思考到底,那怕它使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质疑。”[2]233苏童小说对人性的探索在这个意义上开拓了小说叙事伦理的新空间,他弃绝了对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的伦理期待,在对人性之恶的书写中同时展示了道德的相对模糊性,超越道德谱系而呈现人性的多面性和多层次,而生命和人性的多面性正是现代叙事伦理的终极关怀之一。 二、苦难的生命历程 苏童的小说不是对幸福生活的承诺,也不是对苦难生活的抗议,他温和地面对生活中所有的不幸和苦难。因为,在他的生命哲学中,生命的历程本来就是苦难的历程,命运的无常、生命的痛苦、生存的艰难是生活的本相。生命中那些重要的因素,有关生命的诞生、过程、归宿,有关生命存在的形式、个体心灵的状态,在苏童的小说中都是以悲剧和准悲剧的方式呈现。什么是生命的本相?人在尘世的一切也许注定了捉襟见肘和无法超越,而精神的飞翔的梦想寻觅到的不过是另一种颓废的生命体验。 即使是逃亡、逃逸、飞越,也无法逃离厄运和苦难。 苦难是生命唯一的真实,唯有痛苦才是生命最有质感的体验,精神的逃亡之路注定是没有归途的历险。如果说生命的诞生在苏童小说中仍然是美丽的,但从出生起生命就不得不承受痛苦和苍凉的命运。 《1934的逃亡》中,祖母蒋氏在分娩父亲时无比的美丽,“蒋氏干瘪发黑的胴体在诞生生命的前后变得丰硕美丽,像一株被日光放大的野菊花尽情燃烧。”生命的诞生是如此的美丽而庄严,但蒋氏的五个孩子最后被葬入了死人塘,最后一个孩子也被环子掠走,在城市的屋檐下沉郁而落寞地长大成人。在《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穗子生下的那些掉进河里的孩子,“都极其美丽,啼哭生却如老人一样苍凉而沉郁。”那些“苍凉而沉郁的哭声”也许预示了生命的艰辛与无边的悲怆。“在枫杨树河下游的村庄,有好些顺水而来的孩子慢慢长大,仿佛野黍拔节,灌满原始的浆汁。”野性和自然的生命蕴藏了丰沛的生命活力,但在衰败的枫杨树乡村,那些长大的孩子们也许会成为另一个幺叔、沉草、狗崽,在枫杨树乡里沉落。 苏童说“:孤独的不可摆脱和心灵的自救是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和文学大师们关注这样的事实。”[3]1“孤独”是苏童小说中一种普泛的精神状态。《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在陈府大院是孤独的,没有人理解她的忧伤和落寞。就像她十九岁的烛光晚宴,她迷恋的是那种浪漫而忧伤的情调,而陈佐千虽然欣赏她身上那种“微妙而迷人的力量”,但他作为一个男人“更迷恋的是颂莲在床上的热情和机敏。”这样的基调其实构成了《妻妾成群》基本的叙事结构,颂莲做为一个敏感、细腻的女性和陈府大院的封建男权形成了结构性的疏离,她不仅注定是孤独和落寞的,而且必将被毁灭。《罂粟之家》中,从城里读书回来的刘沉草伤感地意识到:“在枫杨树的家里你打不成网球,永远打不成。”在心灵的孤独中他唯有在罂粟花香里沉没。《米》中的五龙虽然在城市里显赫一时,成为码头帮的帮主,但他的内心仍然是孤独的,他的精神永远游离于城市之外的枫杨树乡村,漂泊了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事的五龙仍然觉得自己是在白茫茫的大水中孤独地飘荡。 在苏童的小说中,甚至是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年也生活在孤独之中。《沿铁路行走一公里》中孤独的剑,喜欢收藏那些死去的人的东西,喜欢沿着铁路孤独地行走。这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故事,他的淡淡的忧伤、他的孤独、他的渴望,都像一首忧伤的小夜曲,奏响在自我的心灵深处。苏童说“:我每写到一大群孩子,当中都会有一个孤独的孩子出现,像是一个游荡四方的幽灵,他与其他人的那种隔膜,还存在于同年龄的孩子之间,他们与整个街的生活都有隔膜,因此他们经常外出徘徊。” [4]78《海滩上的一群羊》中那个沉默的男孩子,他的世界和成人也是隔膜的。父亲带他来看海,可他感兴趣的是饥饿的海鸥、海滩上一群羊,他无法理解牧羊人的痛苦。#p#分页标题#e# 一个孩子内心的孤单和成人世界深深的隔阂,使他的心灵只向自我敞开。《樱桃》、《那种人》、《平静如水》中,不管是个体与世界的对抗还是自我内心的挣扎,都通向无法救赎的孤独的生存之痛。 人的存在不仅是孤独的,而且生存本身充满了荒诞、虚无和真实的苦难。《肉联厂的春天》和《灼热的天空》等,讲述了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现实的背离,个体生存的孤独和悖谬,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却是不能缓解的。在《肉联厂的春天》中,一心想当外交家的金桥被分到了屠宰厂工作,而终于可以正当地离开时,却在一场意外事故中死亡。命运似乎总是在和金桥开玩笑,在思想和精神领域里可以自由游走的他在现实中却捉襟见肘,纯洁的梦想和冷酷的现实永远达不成协议,金桥给了沉滞的生活明丽的阳光,可这一缕阳光却太容易被现实淹没。理想与现实、追求与宿命、过程与结果,苏童借金桥的命运表达了生活的种种悖论。在《灼热的天空》中,单纯、鲁莽、渴望在战场上拼杀的少年尹成来到沉滞的夹镇税务所,夹镇的闷热、世故、奸诈使尹成犹如笼中困兽。那个随身携带的可以在阳光下自己吹响的军号,寄托了尹成在战场上自由飞翔的梦想。在炎热的夜晚燃烧的军号其实也是尹成燃烧的心,一个人的梦想和现实背离之后所产生的巨大的破坏力量,可能会毁灭一个人,甚至酿成更大的悲剧。青春对于人来说,永远是理想无法实现的伤痛,生命是一场备受心灵和身体折磨的恶梦。而且,在苏童的小说中,人生似乎永远都是一个悖论,无论怎样的反抗都无法抗拒宿命的悲剧,生命的苦难历程就是生命的本质。在《红粉》中,秋仪从被改造的人群中逃走,可她仍然无法改变自己悲剧的命运,世事无常,不变的却是生命的苦痛和无法自救的悲凉、无法抗拒的宿命。《妇女生活》中,三代女性却重复着相同的命运,她们和男人的搏斗、对男人的期待却不断地毁灭了自己的生活,“一切都会改变的,只有人的命运不能改变”。 既然生命是苦难的历程,逃离或者寻找另外的生活就成为反抗苦难命运的可能通道。但苏童的小说没有提供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通道,逃离依然无法逃出悲剧的命运,而寻找找到的也不过是另一种颓废的生命体验。《1934年的逃亡》中“,我”本想追寻祖先的足迹,以逃离“无根”的恐慌,可最终追溯到的却是颓废衰亡的家族历史。《外乡人父子》中的冬子父子从遥远的东北回到枫杨树故乡却依然找不到家园,即使冬子后来成了枫杨树乡村最好的竹匠,可他的灵魂却只能永远在枫杨树的上空孤独地游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我”飞越那条浊黄色的河流,企图带回幺叔的灵魂,可最终发现“我”只能一次次“回首遥望远远的故乡。”《南方的堕落》中从乡下逃出来的红菱姑娘也没能逃出屈辱和死亡的命运。 在苏童的小说中,生命的悲怆和逃离的无望所见证的是用破碎和毁灭谱写的哀歌,人生的苦难和命运的无常使对悲剧生命的反抗成为更深的悲剧。 三、无法获救的人生 那么,在苏童的小说中,那些孤独的心灵、那些疲惫的灵魂、那些在苦难生活中苦苦挣扎的生命怎样完成救赎呢?救赎是可能的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理性期待通过道德秩序和意义结构的重建来解决生存的终极悖论,而尼采则希望通过生命沉醉的酒神精神超越世俗的痛苦和人生的困境。然而,人生的终极悖论是可以解决的吗?人生的罪恶和痛苦是可以得到救赎的吗?苏童的小说表达了救赎的不可能,灵魂的救赎之路最后通向的是死亡,唯有死亡以实在生命的消失来结束人世生活的痛苦经验。刘小枫曾经说过,“当人感到处身于其中的世界与自己离异时,有两条道路可能让人在肯定价值真实的前提下重新聚合分离了的世界。一条是审美之路,它将有限的生命领入一个在沉醉中歌唱的世界,仿佛有限的生存虽然悲戚,却是迷人且令人沉溺的。另一条是救赎之路,这条道路的终极是:人、世界和历史的欠然在一个超世上帝的神性怀抱中得到爱的救护。审美的方式在感性个体的形式中承负生命的欠然,救赎的方式在神性的恩典形式中领承欠然的生命。” [5]33但苏童的小说阻隔了在审美之路和救赎之路上聚合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他只是在在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想象中重构了人生的种种苦痛、悲凉和忧伤,他讲述的是无法获救的人生。既然灵魂的救赎之路最终走向的是死亡,那么苏童小说中体现出怎样的死亡哲学呢?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有独特的理解,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死生亦大焉”,认为死亡的意义在于生前的作为,是通过生前的价值来表现,所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有“杀身成仁”,孟子有“舍生取义”,所以,以儒家传统为正宗的中国文化是不太重视死亡的。庄子学派认为死亡是生命的自然属性,生与死都是宇宙的一个过程,生命如白驹过隙,而死亡则是向宇宙永恒的回归。佛家将生命寄托于来生,所以死亡不过是通往人生彼岸的一个中介。 但在苏童的小说中,“死亡”是一个经常性的事件,对“死亡”的茫然、恐惧,是苏童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且蕴涵了独特的命运观念。 在《妻妾成群》中,颂莲在目睹了梅珊被投入井中后因恐惧而发疯,她重复地说的是:我不跳,我不跳,我不跳井。 颂莲自愿嫁入陈府并在妻妾之争中用尽心机,可她终于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她最后的疯狂成为对企图改变自我命运的一种反讽。 《我的棉花,我的家园》中,书来因为恐惧死亡,逃离了玉米地里那个可能是自己叔叔的人的求救,死亡的气味使他深深地恐惧,他辗转漂泊,期待能够活下去,远离水和干旱、远离疾病和死亡、远离所有的灾难。但在他最后张开双臂像鸟一样要把火车拦下来时,却是不期然奔向了死路。《米》中不可一世、生命强悍的五龙最终明白他恐惧的只有死亡,想尽了各种方法试图治疗自己染上的脏病,对身体的焦虑和对死亡的恐惧,使强暴的五龙内心充满了虚弱和悲伤。因为中国文化中没有来世和彼岸的观念,死亡根本性的丧失无法在宗教和神学的意义上得到补救,所以死亡的降临意味着对所能感知的自身生命的丧失,对死亡的恐惧也是对生的执著和迷恋。#p#分页标题#e# 但苏童仍然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方式反抗着对死亡的世俗化理解和解释。一个民俗学家在五棵松神秘的死亡,是“仪式的完成”,民俗的仪式也是生命的仪式。 (《仪式的完成》)。祖母面含微笑地离去,不是尘世生活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关系的开启,她守候了祖父近六十年,凭着一只金锁和一把胡琴,她将进入祖父的世界。(《祖母的季节》)幺叔死后枫杨树乡村苍苍茫茫的罂粟花地绝迹、而晶莹如珍珠的大米、灿烂如金黄的麦子从此在枫杨树乡生长得浩浩荡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总之,在苏童小说中,死亡往往呈现出诗意的优雅,他以平静、优雅、静穆反抗着死亡的冰冷、恐惧和阴森。这种死亡的力量穿透了生命所有的荒芜和灾难,到达了一种模糊生与死界限的澄明。死亡是一种解脱,是从日常生活的沉沦状态中超拔出来,接近了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上的死亡哲学,就是唯有通过死亡才能获得自我的个体性和具体性,把“此在”的“此”展示出来,“向死而在”和“向死的自由”成为死亡对尘世生活的超越和向神性存在的趋近。 另外,苏童小说中的死亡也具有偶然和无意义性,死亡是一个偶然的事实,他并不能把意义赋予生命。 《肉联厂的春天》中期待辉煌生命的金桥死于意外的冷库事件,《木刻收音机》中的医生在一个闷热而孤单的午后不期然地死亡,《午后故事》中的豁子死于桥头的斗殴。《U型铁》中铁匠神秘的死亡,《灰呢鸭舌帽》中老柯宿命的因为父亲留下来的帽子而死,而《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为了一块肉被卡车意外地撞死。死亡总是不期然地降临,毫无征兆、不能预料。死亡只是这个世界无数个偶然中的一个,人处在死亡的阴影中却茫然不知。这接近了萨特的死亡哲学,他认为死亡无所谓等待,因为死亡不可预料,而且死亡不赋予任何意义,并进而指出,“死亡的本义恰恰就是:它总是能提前在这样和那样一个日子里突然出现在等待着它的人们面前。”[6]686萨特认为死亡不仅不能为“此在生存”提供意义,而是对生命全部意义的取消。在苏童的一部分小说中,死亡是因为无意义的琐事而造成的意外,或者死亡就是日常生活中不期然的偶遇,在这个意义上,苏童的死亡哲学就接近了萨特对死亡的理解。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苏童小说中的死亡哲学是对20世纪小说史中死亡美学的一种拓展。在启蒙文学中,个体生命的消亡往往隐含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抗议,死亡被赋予了社会和民族国家的意义。而苏童小说中的死亡回到了个体,回到了生存的本真状态,建构了一种个体的死亡诗学。对个体而言,死亡在神性的意义上可能是对尘世生活的超越,在世俗的意义上也可能毫无价值,只不过是一种自我生命在现世的意外和偶然中的消亡。 总之,在当代文坛上,苏童是一个对人性、生命、死亡等有独特理解和诠释的作家。他对人性残缺的展示、对孤寂的生命历程的书写、对最终通往死亡的无法救赎的人生的呈现,都可以看到苏童小说独特的叙事伦理对20世纪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他超越了简单的道德判断,放逐了启蒙叙事对人生和世界未来的期许,建构了远离宏大历史叙事的死亡诗学,开拓了新的叙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