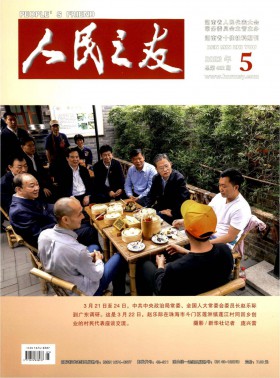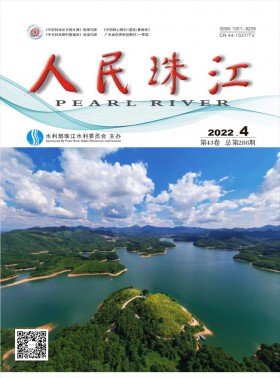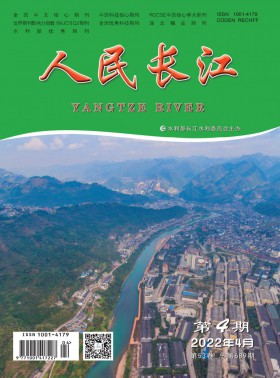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文学批评方法,生态批评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文艺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共识,但这种批评方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在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生态批评的发起人之一格洛特费尔特在她为《生态批评文摘》所写的导论《环境危机时代的文学研究》里给生态批评下了一个定义:“简明扼要地讲,生态批评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对文学研究采取了一种以大地为中心的态度。”[1]也就是说,“生态批评是对传统文学研究中以‘人’为中心的一种反拨,它强调以‘大地主义’而不是以‘人道主义’为中心”[2]。“大地主义”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形象化表述,意指人类应该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以平等和友伴的态度与自然和谐共处,而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态,为了满足自身不断膨胀的物欲,任意掠夺、破坏自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最终回归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伊甸乐园。这种批评旨在以文学的影响力加强人类生存危机意识,促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既体现了文学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密切关注和社会责任的主动担当,更体现出文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深层意蕴,其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思考的是,“大地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指向究竟是什么?其主体究竟何指?“生态中心主义”把“人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其批判的对象,而产生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是对神本主义的反叛而不是对自然的背离,人的对立面是控制人的神而非自然;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典范的伊甸园,其主宰者也并非飞禽走兽、草木花果,而是人与自然共同的造物主亚卫(耶和华),而神显然不可能成为生态批评的核心主体。所以,说到底,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是人的物质欲望恶性膨胀后,人背离了其内在自然和本真状态,失去了其自然本性而产生的连锁危机,是人的种种失衡中的一个分支。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还是要解决人自身的问题,生态中心主义的主体依然是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也应建立在对人自身体系的考察之上。生态批评的深层内涵首先应该是检视人与其内在自然之间的关系。 作为易卜生代表作之一的《人民公敌》(1882)揭示的是在对大自然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怀有私心的各色人等表现出来的种种丑陋世相,讲述的是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在捍卫人的自然本性、呼唤回归人的内在自然诸如正直、良知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和抗争。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引子,人对其自然本性的背离才是问题的实质,人心的沦丧导致了他们与社会、自然关系的扭曲,人对自然本性的回归是作者始终不易的追求。思想巨子易卜生终身努力的目标无非是对被染污的人的精神生态的维护和修复。 一、生态批评的核心问题是人必须回归其自然本性 在生态批评的讨论中,人类中心主义被当作生态危机的价值论源头而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批判一直回溯到古希腊时代,甚至追踪到创世神话中以人为世界中心的思想。这种反思是深刻而彻底的。然而,在这股批判大潮中,许多概念仍需要仔细辨析和认真厘清。 希伯来创世神话中人被放在最后一天创造出来,并让他成为万物的主宰,人作为世界中心的位置得到确立。但这种中心不是指向人的权力,而是指向他的潜质和责任。意大利哲学家皮科•德拉•米朗多拉在《论人的价值》(1489)中写到:“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最后一天创造了人,是为了让他认识这一大千世界的规律,学会热爱这一大千世界的美,赞叹它的瑰丽壮阔。造物主对亚当说:‘我不把你束缚在一个限定的地方,不强制你必须从事规定的事业,不用必然性捆住你的手脚,目的是让你根据自己的心愿去选择自己乐意的地方、事业和目标,并支配一切。其余生物都具有狭隘的天性,因此自身内部就受到我所确立的那些规律的限制,只有你一个不为任何狭隘的范围所钳制,可以在我交到你手里的那一自然界中随心所欲地立标定界。我把你创造成不是天上的生物,又不是纯粹地上的生物,不是必须死的生物,又不是不朽的生物,目的是使你超越束缚,自身成为创造者,亲手塑就自己最终的形象。你有可能沦入动物界,但也有可能仅靠你内心的意志升华为神一般的生物’。”[3]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人有高于其他生物的特性;第二,人有能力理解上帝创造万物的意图,他是这种创造的见证者和赞美者,而并非对万物予取予夺的特权者;第三,人具有二重性,神性和动物性,当人不断超越自我、更新自我时,神性的一面就会得以张扬,从而无限趋近于永恒;反之,人则会丧失作为人的特点,成为只有物质生命的速朽的生物。“人”的内涵是替天行道的使者,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把人与天、地并称为“天、地、人”三才内涵是一致的。人能否与天地同列,不是看他拥有了什么,而是看他是否具备了与天地相同的开阔胸襟、高远境界和浩然正气。 古希腊哲学中首先关注人类自我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学派,其代表人物普罗塔戈拉的名言是:“人是万物的尺度。”不仅再次肯定人作为世界中心的地位,且赋予人的一切需求以合理性。这种说法听来很令人振奋,但由于没有对人性的构成进行分析和辨别,所指含混、芜杂从而可能成为人的动物性一面泛滥横行的理论依凭。苏格拉底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命题的漏洞,鲜明地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命题,明确指出并非人的一切需求都可以成为自然的尺度,而只有道德与善的需求才值得肯定和倡导,只有利己同时利他的需求才具有合理性,德行是众善之首。有了这种限定,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又把人的本真状态定义在理性许可的范围内。 由此可知,希伯来神话和希腊哲学一开始就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意味着责任和使命而非特权。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世,尤其是文艺复兴时代,急于摆脱被经院哲学和教会长期奴役的人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发生了偏差,在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得到空前释放的同时,理性也成为人的意志不受控制、任意肆虐的借口,放大了作为大地之子的人的傲慢。尽量多的获取、占有,恣意随顺本能需求等纵欲行为被误当作解放的标志,妄自尊大、唯我独尊的思想,科学的发现、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忽略了其他生命的存在,成为今天人类欲望无限膨胀的滥觞,其负面影响随着社会进程的推进越来越清晰地彰显出来。#p#分页标题#e# 但这些并不足以成为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的依据。毕竟,人作为脊椎动物的最高级形态,有高于其他生物的智力,因而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这种兼具创造性和破坏力的理性使人的主体地位不可逆转地确立起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生态批评强调人与自然平等相待、和谐共处、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等,都是符合佛教倡导的众生无有分别高下的彻底的平等观的。在强调平等问题时,没有哪一种思想能超过佛教。但佛教所说的平等是指终极价值上的平等,在走向理想境界的过程中,佛教依然强调“人身难得”,拥有理性的人具有优于其他生命形态的特殊能力和地位。“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问题如同解决其他一切与人类相关的问题一样,必须依靠人这个主体自身。 我们更应看到,迫使人类远离自然的是背离了自然本性的人类,因而人类如果要与自然和谐共处,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回归人的自然本性,与其内在自然融为一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类走向歧路的开始,首先是对其自然本性的背离,物质主义淹没了精神追求,动物性掩盖了神性,科学的昌盛助长了人类的肆意妄为,理性的觉醒使人类陶醉在夜郎自大的征服欲中,而没有把人提升为自然秩序的代言人。人类越来越远离其自然本性和对自身的终极关怀,远离对善与美的追求,最终也导致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扭曲。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环境问题成为全球共同揪心的问题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而人类精神失衡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显露端倪了。尼采“上帝死了”的惊呼,爆出西方社会精神大厦的坍塌,其后,信仰危机、价值沦丧、孤独无助、混乱迷惘……这些情绪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人类集体迷失了自我。我们看到由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现代科学和工业化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核威胁、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物种消亡、臭氧空洞、瘟疫流行等种种令全球危机四伏的问题,殊不知,这些只是外部问题,其实,人的内部问题出现得更早、更为严重,也是所有问题的真正根源。“后现代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人们精神的失衡已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信仰的缺失、精神的空虚、行为的无能……,种种表现已令我们触目惊心。在外部生态环境毁灭人类之前,人类可能已经在精神上毁灭自己了。”[4] 回归自然,当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现代人对鸿蒙时代原始自然的表层复归,而是对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一种寻觅,是指人心从染污状态下复归于纯净,重返内心的本真状态。在希腊文中,“自然”(physis)一词,指的就是事物的“本性”或“本原”(arkhe)。“回归”就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命源头、自然本性的回溯和归依,只有人的内在自然真正得到彰显,人才可能真正成为自然中的一分子。这才应该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深层内涵。 其实,有关人的自然本性的问题,早在一百多年前,戏剧艺术大师易卜生已经在其剧作《人民公敌》中进行了透辟深入而淋漓尽致的阐述。今天重读这部作品,依然能感受到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对人心的洞察和揭示所产生的强烈的震撼力量。 二、《人民公敌》的生态伦理价值 《人民公敌》被勃兰兑斯称为是易卜生“思想最尖锐和最富有才智的作品之一”[5]。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人民公敌》是一部典型的吁请回归人纯净的内在自然,以达到建立人类社会的道德秩序、最终建立起人与自然正常关系的剧作。戏剧创作缘起于易卜生因创作《玩偶之家》、《群鬼》等剧而被诬为“人民公敌”,剧作家予以反击,因而剧中的斯多克芒医生颇有自喻成分,可以说,斯多克芒在公民大会上的演说既是易卜生对社会舆论的回击,更是他的精神独立宣言。戏剧矛盾起因于一座城市修建豪华温泉浴场,想利用自然资源为城市发展寻找契机,但浴场水源受到污染。戏剧矛盾的中心问题是整治浴场环境,坚持温泉浴场的卫生标准,为疗养病人的健康负责,还是隐瞒真相,为温泉浴场的虚假名誉、投资股东和小城人的暂时利益打算?而戏剧冲突的焦点则是独立捍卫真理的斯多克芒同各怀私心的“结实的多数派”的斗争。斯多克芒与小城里唯利是图者们斗争、坚守温泉浴场的卫生和纯净标准的行为,正是与污染了人的内在自然的贪欲以及由贪欲导致的名利、野心、投机、报复等种种恶习的斗争;他对真理的捍卫,正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捍卫。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斯多克芒乐观估计形势,试图诉求于人的自然本性,以改造重建来恢复温泉浴场水源的纯净。斯多克芒医生本是首倡建造浴场的人,对浴场发展怀有巨大的热情。但当他发现浴场水源受到污染,浴场实际上已从疗养院变成了疾病传染源时,他立刻决定把这一发现提交市长,并公诸于世,对浴场进行改造和重建。内心纯洁、正直而不谙世事的医生满心以为他的行为既是为疗养病人的健康考虑,也是为小城和浴场的信誉和长期、持续发展着想,是自己“给本乡、本地人尽了点力”,一定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奖励。身边一群支持者的热烈响应更强化了他的错觉,其实他们各怀私心,试图借此机会达到各自的目的:自称民主派的《人民先锋报》主编霍夫斯达名义上反对官僚,实质上企图在市民议会选举之时夺权;制革厂老板基尔曾被市长等人从市议会赶出来,一直怀恨在心,想借机向当权者报复;向来以稳健自诩的印刷厂老板阿斯拉克森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结实的多数派”,对浴场的大投资股东心怀嫉妒,希望让他们蒙受损失,以便相对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们的自然本性在一开始就不是以清净而是以染污的状态出现的。而不知就里的斯多克芒,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认为他们都是一群有才干、有眼光、心眼好的人,他天真地认为,这是一种“朝气蓬勃、新芽怒放的生活”[6]2 94,对自己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充满期待、喜悦甚至自我陶醉。支持斯多克芒的阵营一开始就是一个人心不齐的松散组织,只有当事人蒙在鼓里。而易卜生以调侃的笔调抒写他的单纯时,实际上是写出了人心的本真状态,写出了事情的真实过程:斯多克芒真诚朴素的做法是按常理常规本该如此的事,而在一个人心颠倒混乱的世界,反倒变得滑稽可笑。#p#分页标题#e# 戏剧冲突很快发展到第二阶段:斯多克芒与人心的各种污染源展开激烈的博弈,试图昭告世人远离被污染的浴场,更要远离被染污的精神,结果受到重重阻挠,自己反被诬为“人民公敌”。市长兼温泉浴场委员会主席彼得对斯多克芒发现的问题拒不理睬,在环境整治和利益之间、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宁愿毒害人,也不愿承担重新整治浴场的费用;宁愿牺牲浴场未来的信誉,也不愿承担决策错误的恶名;宁愿隐瞒污浊的真相,也不愿承担停业带来的损失。他先以撤销职务相威胁阻止医生消息,又以改建浴场的费用必须来源于向地方发行公债为由,诱使霍夫斯达、阿斯拉克森放弃在报上发表医生揭露浴场问题的文章;报社编辑、投机分子毕凌也因市长拉拢、有可能得到市议会秘书的职务而倒向市长一边。在利益面前,捍卫真理的联盟脆弱得不堪一击,斯多克芒终于清醒地意识到,浴场真正的毒源不在磨坊,不在制革厂的污水,而在于被名、利之欲染污的人心,是被权力意志控制的精神:“现在不单是自来水设备和下水道的问题了。整个儿社会都得清洗一下子,都得消消毒”[6]334;“咱们精神生活的根源全都中了毒,咱们整个社会机构都建立在害人的虚伪基础上。”[6]359相比之下,浴场的卫生状况已经变成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了。他终于抓到了问题的实质:一切问题首先出在人心,出在人类的精神,境由心造,是这种人心造就了这种社会,这种环境。人心的问题何在?在于为了眼前获利而不顾及长远;在于社会团体和联盟往往都是由利益构成的“结实的多数派”,而不是捍卫真理和精神自由的民主阵营;在于它只认可顶着真理的名义到处传播“道德坏血症”的陈规陋习,而不愿接受新鲜而直抵真相的真理;在于多数人宁愿做良心衰弱、在污浊的地面上爬行的畜生,而不肯做道德高尚、胸襟宽阔的人;在于利己主义发展到极致,泯灭了人对同类直至对自身健康与生命的悲悯和关怀。作者借斯多克芒之口进一步地揭示: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社会繁荣充其量是一朵散发毒气的“恶之花”,迟早会结出害人害己的恶果。斯多克芒是个医生,他是社会问题的良医,他诊断出社会的病根不在外部,而在人类精神的内部,“君有疾”,在于心,不治将使整个社会走上不归路,“照你们这样干下去,全国都会中毒,总有一天国家也会灭亡”[6]369。易卜生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揭露了了分明而入木三分,浴场的污染源仅仅是戏剧家设计的戏剧冲突的由头,环境问题也只是外部现象,是作家思想的载体,作家没有在现象上多作纠缠,而是告诉我们,被污染的浴场是果而不是因,他将矛头直指一切问题的肇端和起因,并在对治人心上狠下猛药。 经过激烈交锋的第二阶段后,以人的道德和精神划分出来的两个营垒已经判然分明,然而剧作家依然留下一些悬念给第三阶段:已经成为孤家寡人的斯多克芒坚持捍卫人的自然本性,力图还原真正洁净如初的自然。市民大会后,斯多克芒以及支持他的女儿裴特拉、好友霍斯特都被解聘,失去了工作;孩子们被通知不许去学校上学;斯多克芒太太的义父、浴场污染的主要来源———皮革厂的老板基尔也威胁着要剥夺原拟留给义女一家的遗产;更令人作呕的是机会主义分子霍夫斯达和阿斯拉克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聪明过人地认为这一切都是斯多克芒翁婿联手串演的把戏:借宣扬浴场水源污染降低浴场股票价格,再去抢购股票,以便将来洗刷净浴场名声后趁机牟利,他们不肯错过这个机会,试图来分一杯羹———这有力的一笔把蒙在丑陋人心上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剥了下来,也把斯多克芒的斗争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使第五幕成为全剧的豹尾。斯多克芒坚拒以谎言洗刷基尔制革厂名誉的要求,放弃了基尔留给妻儿的大笔遗产;他也放弃了去往新大陆的打算,要留在本地,“死守真理,以拒庸愚”[7],教育孩子们做高尚自由的人,以便将来“把国内的狼都轰出去”。斯多克芒的宣言“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6]394,道出了易卜生对人性高地孤独的坚守,剧作家最后的宣称依然是:自然的纯净必须安立在人心纯净的基础之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应筑巢于人的内在和谐之中。 《人民公敌》问世于一百多年前,然而今天读来,它依然彰显出鲜明的现实意义。1996年中国中央实验话剧院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演绎了这部戏剧;2005年由吕效平、李耿巍、田川等编剧的校园戏剧《〈人民公敌〉事件》又对该剧进行了新的诠释。他们都从剧作中读出了关注环境污染这一主题,但同时,他们更揭示出对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的执着追求才是造成整个社会物质环境、精神环境失衡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沦丧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演绎与生态伦理批评无疑是殊途同归。 三、生态批评中易卜生戏剧的意义重构 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断言:“生态文学自古有之。它的历史与文学的历史一样久远。”[8],可谓一语中的。“生态学”这一术语于1866年由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赫克尔首次提出,生态批评则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但是对人类与自然的关注,一直如浪花之于大海浮现在文学的烟波中。乍听起来,以倡导个人的精神反叛、审美的人文主义和乌托邦的伦理道德理想等著称于世的易卜生戏剧创作似乎和生态批评沾不上边,因为易卜生在其一生创作中基本没有直接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时的挪威想必还没有“环境保护”这一概念。然细想之后,其间的联系却是十分密切的。因为时至今日,人———自然———社会———自我四者已经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错杂、难分彼此的联合整体了,我们很难将其割裂开来,孤立地去谈任何一方。当我们考察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时,就不能忽略人与其他几方面的关系,尤其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更是一切问题的起源。要解决生态问题,不能只注意狭义的自然生态问题,首要的和关键的应该是人的精神生态问题。诸多生态批评家意识到,导致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人类的思想与文化对自然法则的偏离,乔纳森•莱文指出,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9]。易卜生的戏剧正是探讨如何构建健康的人类精神生态的典范之作。#p#分页标题#e# 生态学发展至今,开始有了“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之分。前者试图以高科学技术和高经济效率解决造成环境危机的伦理、社会、政治等问题,而后者则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并主张彻底改造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社会体制,建立起一种人、社会与自然相互融合的生态社会。显然,深层生态学对问题的诊断更加准确,提出的对治方法也更切合实际。因而文学上的生态批评也应与之相呼应,在更高层次上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如前文已经论述的那样,生态批评不应是文学批评与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的简单结合,也不应简单叙写现代人对原始自然的表层复归,而首先要解决人自身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生态批评中,人及人类社会依然应是研究的中心,“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至今依然是一个真命题,在我们吁请人类向自然复归的过程中,首先应该倡导的是人对其自然本性的复归。 从深层生态批评的角度重新释读易卜生戏剧,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能够衍生出更多内涵,给我们提供新的思考。贯穿在易卜生戏剧中的主题之一就是对贪婪欺诈、物质至上、虚伪卫道、道德败坏等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的批判,是对违背自然人性、违背人类健康的生活状态的批判。易卜生只承认内心真诚、思想自由、道德高尚的生活,违背这一原则,社会认可度再高,依然是缺少根基、虚幻不实、毫无价值的。他揭穿博尼克用谎言、背叛、栽赃甚至谋害骗取的盛名,而这种盛名蒙蔽着社会中的多数人,多数人就生活在人云亦云的谎言之中而不自知,甚至没有了解真相的兴趣。他剥下海尔茂温存、体贴的假面,暴露其自私、冷酷的心肠,让人们看清面具下的真面目。他嘲讽曼德牧师为了自己的声名而扼杀一个女子追寻精神自由的渴望,看到他道貌岸然的劝告下掩藏的虚伪和残忍。在《人民公敌》中,他更是把批判矛头指向了结实的多数派,指出他们只拥有强制别人意志的势力,却没有占有真理。易卜生的批判和否定是彻底的,他从不承认既有的现实,如果这现实是肮脏的;他也不认可多数,如果这多数是愚昧的。他甚至不惜将这个表面浮华的世界全部否定掉,正如斯多克芒所说的那样:“毁掉一个撒谎欺骗的城市算得了什么!把它踩成平地都没有什么可惜!”[6]368如果源头是错的,结果一定不可能正确。这个观点与生态批评强调归元、回到源头,从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关系的起点处寻找正确之路是不谋而合的。 与之相对的是,易卜生戏剧强调建立起全社会的人文精神。易卜生强调的人文精神,不是人类至上或人类中心的思想,而是指人类精神的完善,就是人的精神革命,是对现存秩序的否定,对污浊环境的精神反叛。一个人文精神匮乏的世界是缺失凝聚人心的亲和力的世界,因而没有真实意义。一个物质充斥而缺少信仰、失掉诚信、毫无公德的国家,经济繁荣、文明昌盛、科技发达等等一定是短暂、缺少根基的,因而不值得贪恋,因为一切都建立在沙滩之上。易卜生透过浮华的表象对社会本质的洞察在19世纪是具有前瞻性和预言性的,时至今日,生态批评正是在人类社会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时对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状态进行的全面反思。易卜生对倾斜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匡扶,正是人类处理好与其生活环境的一切关系的前提。他曾对勃兰兑斯谈起过人的精神革命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已经不是过去那些神圣的断头台日子里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可是政治家们不愿意理解这一点,……这些人只想搞一些专门的革命———外事的,政治的革命等等,但这一切都只是鸡毛蒜皮。需要的是人的精神的革命……。”[10]易卜生否定表面热闹、只具有轰轰烈烈的形式而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往往止于王朝的更替,而非公民社会的养成,不能从本质上促进人类的进步,他鼓吹的精神革命,是对真正意义上人的力量和自由意志的追求,也与生态批评论述的对人类本真意义的追寻异曲同工。 易卜生剧作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是探讨在充满贪婪、自私、罪恶的世界中,个体的人如何进行自我拯救,捍卫人性的独立自由,实现精神的自我回归,而不随社会整体一起沉沦。他曾在致勃兰兑斯的一封信中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11]148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对此解释说:“……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11]149这里所说的“为我主义”,也就是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但它不同于生态批评所抨击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在自然面前表现出的人类的极端利己主义),而是指个人精神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思想的对立面是损人利己、自私自利、败坏社会道德的利己主义。易卜生要求每个人都努力从总体堕落的社会中挣脱出来,批判现存的社会秩序,不断追求精神的独立和自由,净化道德,走向自我的本源,走向未受污染的、本真的自我,直到灵魂能与上帝对话。易卜生的剧作中的主人公多是这一类追求精神独立的斗士:追求“全有或全无”、为了理想不惜自我牺牲的布朗德牧师,四处寻觅、不断求索、终于回归自我的培尔•金特,对社会的法律、宗教、道德提出全面质疑的娜拉,立志革新社会的罗斯莫,为真理战斗到底的斯多克芒,都是这类个人主义者。 诚如歌德所说:“精神有一种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12]易卜生毕生都在努力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因而对每个时代致力于精神追求的人来说都能不断提供新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乎偏执地拷问人类心灵的易卜生是说不尽的。尤其对于致力于反思现代人类的自我定位、构建人与自然新的伦理关系的生态批评而言,易卜生具有先行者的价值,绿色易卜生首先是维护和修复人类精神生态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