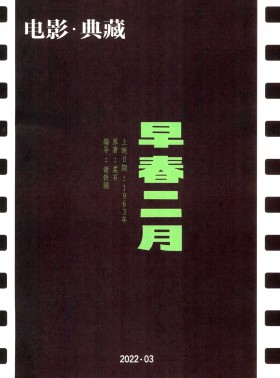福柯在1967年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另一空间》(Desespacesautres),也有翻译作“异域”或“异质空间”,福柯在文中对此有一注解,即他发明了一个与“乌托邦”(utopie)不同的新词“异托邦”(hétérotopise)。和乌托邦在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不同,“异托邦”是实际存在的,但对它的理解要借助于想象力。福柯还阐述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第一,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文化,多元文化的情形就是‘异托邦’;第二,在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中,不同时代所处的每一个相对不变的社会就是一个‘异托邦’,因为从另一个社会的眼光看,这个社会发生作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异托邦’还指这样的情形:在一个单独的真实位置或场所同时并立安排几个似乎并不相容的空间和场所;第四,‘异托邦’与时间的关系:因为时间与空间是对称而不可分的要素。‘异托邦’在隔离空间的同时也把时间隔离开来;第五,各种不同的‘异托邦’自身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系统,两个‘异托邦’之间既是隔离的又是互相渗透的;第六,‘异托邦’是空间的两极,一方面它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但另一方面,这个最虚幻的空间揭示最真实的空间。”①福柯的“异托邦”理论,给当代电影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也为我们进入贾樟柯电影空间提供了一把钥匙。 一、作为家园的小城镇 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曾经说:“电影是一种乡愁。”他用自己的摄影机拍摄了多部表达自己乡关之思的影片。在现代艺术意义上,乡愁已不仅是怀念地理位置上的家乡,更多地是指怀念某种记忆中的“精神家园”。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变动不居,使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难免产生一种漂泊无依、无家可归的怀旧情绪,这是一种现代性乡愁,也是一种文化乡愁。它反映了理想和现实的反差,它是对乡土与生俱来的一种忧患意识,它也是现代人类努力追求进步和完美社会的同时投向过去的一抹依依不舍的余光。 1993年,贾樟柯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理论专业学习。贾樟柯曾谈起大学期间一次春节回家的经历给自己的触动,“春节期间,每天都有许多我小时候的同学、朋友到我家里来串门、聊天……在谈话中间,我突然感到大家好像都生活在某种困境里。”“再到街上一走,各种感受更深了。在我老家的县城边上有一个所谓的‘开发区’,叫‘汾阳市场’,那个地方以前都是卖点衣服什么的。可是这次回来一看,全变成了歌厅!……”②显然,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哪怕是处于政治和经济末梢的小地方一如贾樟柯的故乡山西汾阳这样的小县城也不可避免地跟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实汾阳也是中国小县城的一个代表。在中国,除了北京、上海等几个大城市如贾樟柯说的是中国的“盆景”外,大部分地方都是和汾阳差不多的小县城。所以有人说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小县城,这种发现既是一种良心的发现,也是一个电影人独特的电影眼。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经历的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像汾阳这样的中国大部分小县城的空间重构正在开始,满大街旧墙上写的醒目的“拆”字是标志。物是人非、世态变幻、漂泊无据等感触引发的乡愁可以说是文化乡愁,或说是一种现代性焦虑。焦虑的根源就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 “哲学就是怀着乡愁寻找家园。”哲学意义上的家园不仅仅是生之所在,更是精神上的归属。生存的理由和生命的归属是哲学的两个永恒母题。1996年,还在电影学院学习的贾樟柯拍摄了自己第一部故事短片《小山回家》(50分钟),拍摄地点是在北京。但从片名看,“回家”一词已带有浓厚的乡愁意味,但是“回家”只能说是最初层次的乡愁。1998年贾樟柯回到老家山西汾阳,拍摄了电影《小武》(107分钟),在这里乡愁已经递进为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感。这部类自传性质的电影,有着浓厚的寻找认同意识。其实,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每个人无时不在寻求自我认同:远离家乡的游子在异乡会寻找故乡旧人,回到家乡也会寻找逝去的回忆。因为无论时空如何变幻,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记自己来时的路。影片依然延续了《小山回家》的纪实拍摄手法,将摄影机扛到了大街上,以非职业演员演绎了一个小县城的小偷“存在意义上虚无的生命流程”③。 影片《小武》的开头、站在公路边等车的小武背后的空间呈现是:“初春的田野里有一层淡淡的薄绿。远处寸草不生的山坡下是村办炼铁厂的全景,两座高大的烟囱仔冒着浓厚的烟雾。”④在这里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美好田园风光,高大的烟囱冒着的浓厚的烟雾喻示这是一个处于前现代化的混浊的城市边缘,加上画外音配的是当下娱乐明星赵本山的小品,这个边缘的乡村空间可说是一个充斥着传统、现代和通俗娱乐的混合体,也是福柯所说的多元文化交汇的“异托邦。”在这样的乡土难以寄托乡土中国的美好回忆。《任逍遥》中贾樟柯首先以影像和声音出色地构筑了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奋力赶上但又步履维艰的北方工业城市大同。在这个城市中,街道两旁广告林立,路上车水马龙,新的高速公路正在修建,商业促销活动繁荣;另一方面,纺织厂等牵动着千万职工的夕阳工业正在遭遇困难,下岗工人家中简陋的陈设与街头和舞厅的豪华形成对比。脱离学校而又没有职业的少年终日在街头游荡,冷漠地观看世态。这种反差极大的社会图景正是后现代文化表达中着力刻画的一种分裂和矛盾的当下状态。《任逍遥》里,还有多处斌斌或小济骑着摩托在城市边缘奔驰的场景,所到之处,有高大如魅影的烟囱,载重卡车行驶的公路,矿区破敝的楼房,修葺中的高速公路,一切都罩在灰蒙蒙的雾霭之中。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故乡已经成为福柯所说的“异托邦”,原来的乡土田园已经因现代性元素的侵入而面目全非。工业化的大烟囱使原来的青山变色、绿水变质,各种车辆驶过时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人们因为贫穷纷纷逃离了祖辈固守多年的家园,中国人固有的精神家园已经失落。#p#分页标题#e# 二、作为他者的都市 在山西汾阳和大同拍了“故乡三部曲”之后的贾樟柯于2004年来到北京拍摄了《世界》。或许是由于对北京这样都市生活的先验性的缺乏,《世界》这部影片将叙事的空间浓缩到了“世界公园”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性符号的空间里,讲述的仍然是那些“汾阳”人的故事。“无论是小写的他人,还是大写的他者,其实都代表一种异己的因素,一种异己的他性。”⑤《世界》中的北京就是一个他者的空间,而“世界公园”则是北京这个“他者”中的“他者”或“他者的想象”。精神分析学对此曾有一个比喻,在每一个婴儿来到世间之前,父母以及其他的人都已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说话了。于是,对于主体(婴儿)而言,除了认同这种秩序,学习说话之外,似乎别无他路。 对于片中赵小桃和成太生们来说,“世界公园”也是一个“他者”的空间或者“异域”。片头一个十分经典的镜头:近景是一个逆光的佝偻着腰的拾垃圾者背着一个大包站在镜头前面,远处是世界公园的埃菲尔铁塔和城市远景。这个镜头的寓意可以读为:世界很远,现实很近。在影片中都市的镜像很少见到,能看到的也只有城市向外的高速公路、黑夜中的布满灯光、充满寒意的街道。这也可以理解为在都市谋生的底层对都市这个陌生空间的一无所知。对于这样一个先在的空间,它是不可改变的,从外面或农村来此生活的底层人物只有不断去适应它、模仿它。于是才有了片中的“商业秘密”(二姑娘在世界公园中文早些出来打工的二小:你的月薪是多少?二小回答说:二百多。二姑娘追问说:二百多到底是多少?是二百一还是二百九?二小说:这是商业秘密。)“全球定位的摩托罗拉”(片中老牛埋怨自己女朋友小魏不接电话,同事建议老牛给自己女朋友买个全球定位的摩托罗拉手机,走哪定哪!)、护照(梁子和小桃在小饭店吃饭时拿出护照给小桃看;廖出国前拿出护照给成太生看;珠宝商引诱小桃也用为其办护照等)这些来自底层的现代性名词。尤其是护照这个符号在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仿佛有它的指称意义。护照,其实也是一种身份的认证,具有被“他者”认同的权威效力。但是,本我在寻求认同的过程中充满着痛苦的历练。在影片的一开头导演就把这些底层的伤痛毫不掩饰地呈现出来,片头字幕过后便是赵小桃在后台狭窄的过道里边走边问:“谁有创可贴?”一种逼迫感和痛苦预感油然而生。世界很大,赵小桃生活的却是角落,她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是“他者”的空间还是异质空间,赵小桃都是处于一个不能自主的空间。处于这种境地的赵小桃和成太生或许都还不能察觉自己在这样一个空间的位置,当太生得知温州女人廖要去国外找老公时,太生还自豪地邀请廖去世界公园先看看,说:“我那儿,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法国那点玩意儿都有!”而廖却笑起来说道:“可是他住的地方你没有!”。世界公园虽然很美好,但在廖的眼里却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它不属于成太生这样的人。而成太生身处这样的虚拟空间却不自知。这也正印证了贾樟柯自己所说的:“后现代的景观也无法遮掩我们尚存太多启蒙时期的问题。”⑥ 《世界》中现实的北京呈现很少,关于北京真实的镜像是在北京火车站内,小桃和成太生送梁子乘国际列车去蒙古这一小段。车站内的电梯上站满了人、鱼贯而上,后面的大电子屏幕上传来现代广告的音乐,梁子和小桃、太生匆匆话别。另一段是赵小桃在旅馆拒绝成太生要求自己用身体证明对他的爱之后坐公交车回去,公交车上的电视里放的是悉尼歌剧院、欧洲城堡、东方明珠塔、法国埃菲尔铁塔等世界著名标志建筑,光鲜而亮丽,并配有恢宏的交响乐。顺着情绪低落的赵小桃的眼光透过车窗我们看到了夜色中的天安门城楼、画像和亮着装饰灯的金水桥。另一段,小桃拿着从俄罗斯女人那里买的望远镜看城市的夜,马路上车如流水,灯火通明,字幕却显出“乌兰巴托的夜”,让人置身于一种“他乡即故乡”的恍惚之中。《世界》里人物的室外活动大部分是在城市的路上,如赵小桃坐着公交车从天安门前路过;成太生开车送梁子去火车站;成太生将三赖和二姑娘送上公交车,然后呆呆地站在路边的站牌边不知所往;成太生和赵小桃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三赖,他们在高速公路上旁若无人地寒暄,等等。《世界》里的都市镜像是通过人物心理来构建的。心理空间是人物心理所呈现的空间,也是观众观看电影时所感知的空间。片中用了几段FLASH,其中三段是这样的:一段是赵小桃接到秋平的短信说晚上接她们去城里HAPPY。赵小桃去城里的行程用FLASH动画表现的:另一段FLASH是成太生接到宋哥的短信,两人一起前去宋哥家,FLASH动画为赵小桃在城市上空飞行,越过世界公园的埃菲尔铁塔、一个布有和邓小平画像和雕塑的广场、城市建筑的上空,等等;还有一段是成太生接到廖的邀请前去约会,FLASH动画为成太生骑着马,在马上不停地呼吸,哈出的气变成了一片片纷飞的粉红色的心,飞进了马路边的黑色的烟囱里。这三段FLASH,前面两段是表现城市的镜像,后面一段则非常明白地表现了“成太生”们躁动的欲望。 三、普通的公共空间 贾樟柯电影中有大量公共场所的空间呈现,代表性的有车站、KTV包房、车厢、舞厅等,它们在电影中承担的功能和作用也并不相同,是贾樟柯对电影空间呈现的开拓,通过对这些空间的关注也表现了贾樟柯对社会深层的观察和思考。下面就车站、KTV包房和车厢三个贾樟柯电影中最为常见的公共空间加以论述。车站只与旅行有关,一般人如果不出门,不会去车站,更不会去关注车站。但车站这样的空间能承载丰富的信息,在那里适合上演人生说不尽的悲欢离合,一般为电影导演所喜爱。电影史上最早的一部著名影片之一就是卢米埃尔的《火车到站》,而现代电影《北非谍影》中飞机场的道别、《魂断蓝桥》里火车站的迎送所传达的审美意味更成为传世经典。在车站这样的空间里,人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它引起我们对过去和未来的一种想象和思考。贾樟柯尤其钟情车站这样的空间,电影中看似平常普通的车站空间呈现实际上饱含导演的对人生、命运等问题的哲理思考。对于身在其中的人来说,他们可能视而不见,然而对于旁观者尤其是贾樟柯这样的旁观者来说,却充满了迷思。#p#分页标题#e# 2001年贾樟柯用DV拍摄了31分钟的纪录片《公共场所》,这部影片没有字幕、对白和解说,成为一部单纯的影像记录,这部影片获得第13届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影片。片中所呈现的空间有大同郊外的一个小火车站、公共汽车站、公共汽车改装的一个小餐馆、候车厅、舞厅等。在贾樟柯其他的作品中也不乏车站这样与旅途相关的空间呈现,比如《小武》的片头等车的三两个行人和小武站在马路边上,《任逍遥》里矿区公路候车亭、汽车站等,电影《站台》的片名更直白,所有这些关于行人、旅途的空间在贾樟柯电影里屡见不鲜。像车站这样的公共场所,它里面包含的信息由每个进出车站的人组成,所有进出车站的人穿针引线般组成了车站这样一个信息网络空间,他们的与外界社会的交往使得他成为一个社会的人。从车站进出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车站即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也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从这里无限延伸可以到达无限的宇宙。车站这样的影像空间带给我们无限的空间想象。这种想象向外无限延伸是深刻的哲学思考,向内则是人类的终极关怀。 KTV也是一个现代性的空间,它的呈现意味着消费主义的兴起。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的“无论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用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获得超前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也迅速积累,中国传统思想“衣食足而知礼仪”出现了变异,变成了“衣食足而知享受”。由于社会思想和信仰的缺乏,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成了先富起来的人的惟一追求,KTV包房应运而生,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夜夜笙歌和盛世太平的繁华景象。贾樟柯电影里的KTV空间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首先,无论是在《小武》还是在《任逍遥》中的KTV包房,它所呈现出来的空间影像是封闭狭小而且有些破旧。里面的情绪显得压抑而私密,不会唱歌的小武到KTV是为了和胡梅梅谈情,而斌斌和女友则是选择KTV作为他们约会的地点,他们俩并排坐在沙发上看的却是动画片《大闹天宫》,与斌斌们的现实处境形成了反比。这两部电影中狭小灰暗而封闭的KTV包房成了一种压制情感和禁锢的铁笼子的象征。其次,在《世界》中的都市KTV呈现则是灯光朦胧、充满诱惑的情色场所。《世界》中有一段在KTV卫生间里赵小桃与沦为在KTV做妓女的安娜相遇继而相拥痛哭的段落,揭露了底层艰难的生活现实。同样是KTV包房,但却体现出不同的功能。一方面反映边缘小人物精神空间的被挤压,另一方面,反映的是消费主义兴起和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贾樟柯的不一样的KTV空间完全撕毁了掩盖在繁华表面的面纱,将一个现代文明异化的空间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清晰地勾勒出社会阶层分化的事实,具有真实的现实主义力量。 流动性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破旧的长途汽车,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载着面无表情、农民模样的乘客颠簸着前行,这样的巴士车厢空间也是贾樟柯电影的特色空间,也很好地体现了时代特征和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现实状态和表情。福柯曾经说殖民者到海外殖民的海船是一个漂流的“异托邦”。在电影《小武》开始就是小武上了一辆公交巴士,在拒绝买票之后,导演给观众们呈现了车厢内的空间,里面坐着一个个农民模样的乘客,表情淡漠,小武在车上作案,之后顺着小武的视线我们看到了汽车前窗挡风玻璃上挂着的像和灰蒙蒙的车窗外原野。照片随着汽车的行驶在晃动着,小武作案得手之后也呆呆地望着前方。这段一分多钟的车厢内镜头组合,信息非常丰富。尤其是前车窗上挂着的像颇有意味,它象征着历史,一段刚刚过去的历史,同时,它又提示着现在的人,历史已经发生了转折,中国社会开始转型。这个空间处理对整部影片的叙事有着高屋建瓴的作用,小武后面所经历的友情、爱情和亲情的变故与时代转型、人们价值观转变密不可分。贾樟柯电影中大量呈现的底层中国空间与主流电影光鲜的空间形成反衬,尤其是底层灰色空间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底层空间,照亮了真实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