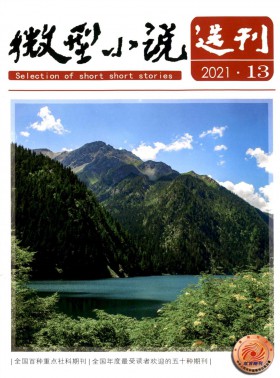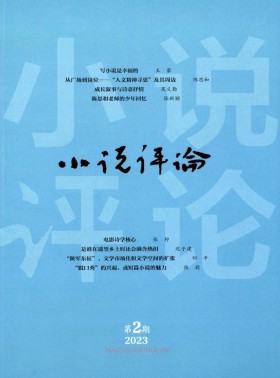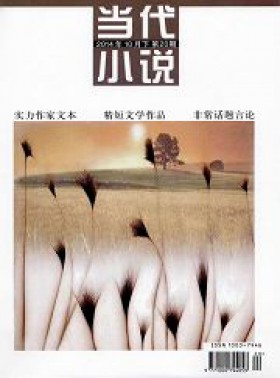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小说的民族文化精神解读,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
石舒清作为宁夏文学的“三棵树”之一,其小说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文章研究了作家早期两部小说集《开花的院子》和《苦土》,并结合石舒清所受本土和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探讨了作家小说中的民族文化精神。
关键词:
西海固;回族文化;外来文化
小说集《开花的院子》和《苦土》是石舒清的早期小说作品,也是石舒清奠定其创作风格和审美取向的重要标志。尽管石舒清的小说创作随着作家人生阅历和创作经验的丰富得以不断成熟,但其作品中的文化精神却始终受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共同影响,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领域。作为一个生长于西海固,并深切关注本土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回族作家,石舒清的小说自然体现了西海固回族的文化精神。同时,石舒清不囿于本民族的文化视野,广泛而深入地吸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形成了超越本民族的多元文化向度和独特思维。
一、浓厚的乡土意识
石舒清是西海固之子,作家的少年、青年时期都是在西海固的乡村度过的。西海固地区回族的风土人情、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成为作家表现的基本内容,也是让他成为西海固作家代表的根本原因。
(一)生存环境的乡土性
西海固地区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在石舒清笔下,生存环境总是和作品的主题相辅相成。《花开时节》中少女宰乃拜在盛夏荞麦地中如痴如醉享受暗恋滋味的情景让人感到温情脉脉,如诗如画。散文诗般的基调和养蜂人忧郁的口琴声给人制造了一种惆怅失落而圣洁的审美意境。它让人感到,发生在偏远黄土地上的爱情也可以和大都市里的爱情一样浪漫感伤,让这片土地上爱人和被爱的故事获得了平等的尊严和意义。同样,小说《开花的院子》里童年记忆中干爷爷家的花园神秘而幽深,与作家模糊的记忆一起构织了一个辽远而醉人的梦境。而在《红花绿叶》中李秀花老人入土前坟前凌厉的山风不仅衬托了送葬者们内心的纷乱复杂,也将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放置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之间。《黄土魂》中乡村小学教师刘晓燕所在的山村偏远而闭塞,简陋不堪的校园院墙上的破洞使年轻姑娘的内心更加凄清寂寥,加重了她对热闹的城市生活的向往。石舒清是一个敏感细腻的作家,他对乡村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花草草,飞禽走兽都赋予了灵魂和诗性。对大地、家乡的热爱和关注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极高的人道主义精神。
(二)人物语言和行为的乡土性
石舒清总会根据作品人物的身份为其选择最恰当的语言。由于其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是生活在西海固大地的农民,所以他们的语言不光反映了西北人粗犷和剽悍的性格,也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层次。《空宅》中二奶奶对我是那么的慈爱友善,而对与其势不两立儿媳的咒骂则体现了封建式婆婆对儿媳的恶毒和狭隘。“做母亲的生一个儿子,有三个过程,小的时候是命系儿,再大一点是淘气儿,一成家,一娶媳妇就是过寄儿”[1]是二奶奶挂在嘴边的信条。二奶奶对儿媳的敌视和对孙子的渴望正体现出了西北回族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之深。《清洁的日子》中母亲在扫屋前早早起来洗了大净还请父亲点几炷香,念一章《古兰经》上的索勒才知足而兴奋地开始扫屋。通过对母亲在极度艰难生活条件下的行为特写,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回族传统的珍视,读来让人觉得亲切感人,更让人感受到了回族身上乐观坚强的精神力量。《赶山》中几个坐在手扶拖拉机上的女人毫不讳言地讨论着收获发菜后的小小愿望,她们有的打算买一双棉皮鞋,有的打算买一个绸裹肚。对物质的简单追求,证明了西海固农村妇女的单纯和质朴。
(三)人物思想的乡土性
生存环境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长期生活在西海固这片苦土上的人们自然形成了自己对岁月和人生的感悟和认识。《民间行为》中妥小飞和花花从小定了娃娃亲,花花想,自己从两岁起就有了一个叫妥敬德的未婚夫,她很早就知道自己以后是要嫁人的,要做别人婆姨的,要给那个叫妥敬德的塌鼻梁娃娃做婆姨的,她甚至觉得自己从来就没做过女子,自己从懂事起就是个婆姨[2]。落后的农村婚嫁习俗使得花花从来没有体验过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的存在,而是早早被贴上了附属于他人的身份标签。这种落后的风俗习惯最终导致了妥小飞母亲因儿子的背信弃义被花花娘灌大粪的闹剧。《逝水》中的姨奶奶是一个苦命的老人。年轻时由于长得好看而被过路的一个汉族司令看中,而姨奶奶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免遭沦为“老蛮子”姨太太之命而连夜托人将姨奶奶嫁给了一个大她20岁的男人。就因为姨奶奶父亲的古板教条和错误决定,姨奶奶早早守寡,无儿无女,一辈子在凄苦和孤单中度过,失去了终生的幸福。姨奶奶的父亲虽然没有在作品中直接出现,但通过小舍木的听闻,姨奶奶的命运悲剧就有了深刻的文化根源。
二、沉郁的苦难意识
人类的苦难亘古就有,无处不在。石舒清的小说中也存在着强烈的苦难意识。西海固人民的苦难主要来源于生存之苦和精神之苦。仅从小说集《苦土》的名称上就可以体味到西海固大地之苦。作为苦甲天下的西海固,人们辛勤耕耘,忍辱负重,却总是广种薄收,度日如年。物质生活上的极度贫乏使人们绞尽脑汁地改善自己的境况。人们为了一些微薄的收入,可以十天半月地赶山拾发菜,可以认真研究延长扫帚使用时间的方法,可以用苦菜团子代替主食,可以用向日葵杆子充当木椽搭盖房子。人们的精神之苦往往是在物质匮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因无力与某种文化思想抗争而形成的苦闷。《黄土魂》中舍巴媳妇嫁给了一个没有性能力的丈夫,冲动之下委身于并不钟情的邹校长,于是内心承受强烈的道德谴责,而不敢轻言离婚。《空宅》中二奶奶素来和儿媳妇水火不容,难以释然的心魔成为死不瞑目的阴霾。《娘家》中的田志文夫妇因为斗气而酿成夫妻阴阳两隔的悲剧。《旱年》中的蒙面男子因为妻子的不贞残害他人性命而躲避四野……物质之苦和精神之苦叠加于西海固地区的人们身上。物质上的贫困考验了人们的生存智慧,催生了人们逆境进取的精神,但是精神之苦却比物质之苦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超越,多是由于欲望的无法满足而造成了迷茫、徘徊,甚至堕落。怎样超越苦难成为作者极力探究的问题,也是作家苦于寻找出路的所在。因而,石舒清的作品就有了一种沉郁的风格。在石舒清带有苦难意识的作品中,作家往往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审视苦难的存在,苦难存在的普遍性使得宗教对人的救赎就成为作家提供给人们化解和超越苦难的途径。
三、厚重的道德意识
道德是人的社会属性,也是文学中的重要题材。在石舒清的小说中,既有对美好人物形象的赞美,也有对道德缺失现象的批判。作家的道德意识和批判意识始终是紧密结合的。《留守》中留守农村的旦旦媳妇没有受到虎子媳妇的蛊惑放弃操守,努力坚守着传统的道德品质。她觉得自己坚持着的这种东西愈来愈显珍贵,愈来愈成为一种品质和果实。她从这种维护和坚守里品尝到了无法言说的愉悦和自得,有时竟会获得一种圣洁感。[3]而与旦旦媳妇相对,同样留守农村的虎子媳妇却忍受不了寂寞,追求及时行乐。“人一辈子有几天呢?”这是她对旦旦媳妇的劝说,也是给自己纵欲寻找的正当理由。然而,小说结尾中旦旦的返乡并没有让旦旦媳妇的坚守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支持。旦旦的变心说明了一个残酷不公的事实:在外打工的男人可以花天酒地,而作为留守家园的妇女却要承受道德的考验和身心的煎熬。长期的精神支柱瞬间倒塌,使得年轻的旦旦媳妇难以负重,内心混乱而茫然。农村中妇女的留守问题已然成为一个危及个人幸福和社会稳定的毒瘤。究竟谁之罪?是旦旦见异思迁,虎子媳妇轻浮放荡,还是旦旦媳妇保守愚钝?对于人类纯洁的品质还需不需要坚守?谁来坚守?怎样坚守?既是石舒清发出的一系列诘问,也是当下文学所要解决的现实命题。石舒清和苏联时代的道德心理派剧作家万比洛夫一样,并没有让读者冷眼旁观地对这些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让读者将其中的主人公置换成自己,深刻地思考其中的根源。对于谁之罪的问题,石舒清没有将责任完全归结到个人身上,他的道德意识是饱含对人性的尊重和思考的,在揭露人性丑恶的同时,是带有宗教式的同情、悲悯和宽容的。
四、冷静的批判意识
石舒清的小说大多是反映西海固人民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的现实主义作品。和其他西海固作家一样,石舒清用了大量笔墨状写了回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然而,出于对本族人民的热爱和救助,他的作品没有一味宣扬回族文化的先进性,而是站在客观的角度,给予冷静的思考和审视,对本族文化中的某些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民间行为》中花花娘因为女儿遭到妥小飞的悔婚而对妥母实施报复性行为———灌粪;《三爷》中三爷狐假虎威凭借“牛团长”的威名在生产队里作威作福,欺男霸女。《恩典》中大人物王厅长的闯入让原本生活自得的木匠马八斤顿时失去了内心中原有的平衡和快乐。《娘家》中田志文的女人因为受传统思想的误导,试探性地回到娘家来证实丈夫对自己的爱,而最终因为夫妻两人的执拗造成阴阳两隔的悲剧。作家对本族文化的冷静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意识应该说是受到了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深刻影响。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以降,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作家都曾一次次大胆地将俄罗斯民族的丑恶撕开了让世人去看,正是出于治病疗伤的社会责任感,俄罗斯作家们才背负了沉重的十字架,对社会生活进行积极的干预,努力为人民寻找一条摆脱和超越苦难的道路。石舒清在思考造成西海固人苦难根源的时候,除了把生存环境之苦作为物质之苦的直接原因之外,还对本民族文化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批判。作为回族群众来说,石舒清对回族深层心理文化的挖掘和剖析更具说服力,同时在帮助西海固人摆脱苦难时也更具有针对性。
五、广博的生命意识
仅从石舒清几部短篇小说集的名称就能洞察作家作品中的生命意识。获得过鲁迅文学奖的《清水里的刀子》将作家对普通人物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体现得淋漓尽致。底层意识是石舒清作为西海固作家的基本立场,他笔下的人物全部来自西海固山村的普通农民,对农民的关注既是作为农民之子的特有情结,也是作家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度体现。如果说《清水里的刀子》是从伊斯兰教视角对一个回民在世和无常后生命价值的探讨,那么《红花绿叶》则是在哲学意义上对人作为生命存在进行更为广义的思考和求索。小说中李秀花老人的突然辞世除了让自己刚刚订婚的小女儿悲痛欲绝外,其他人只是出于特殊情境的感伤。一个普通卑微的农村老人在完成了为人妻、为人母的68个春秋后被活着的人草草掩埋,只留下一个土堆大小的坟头。小说中娘家人对亡人的交代是:到今天为止,咱们两家几十年亲戚算是圆满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人一辈子没大灾大难,平平顺顺一辈子归真了,就算是享福了。[4]这种交代只能算是活人给活人寻找的借口和安慰,对于亡人一生的价值和意义,作为只在她死后才登门的娘家人是不可能替她做出公正总结的。活着的人只是为了大家的面子说一些出于礼节的话,对于亡人的人生价值无人愿意关心也无力关心。对生命意义的叩问是作家生命意识的体现,也反映了普通人对生命意义追问的淡漠和肤浅。与此同时,作家的生命意识还体现在对女性和儿童的关爱和尊重上。但凡伟大的作家都有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赶山》和《黄土魂》中的尔利媳妇和舍巴媳妇,有着同病相怜的难言之苦。虽然和有妇之夫私通,但都是出于无奈而造成的暂时性迷失和放纵。她们的丈夫都是在物质和精神上无法担当的弱男子,逆境中的女性只好代替男人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开花的院子》中大干奶奶和小干奶奶作为干爷的两个婆姨在明争暗斗中消磨着彼此的生命,谁也不能得到男人完整的爱。这是旧式的婚姻陋习,石舒清对身处其中的女人的命运流露出淡淡的惆怅和忧伤。《空宅》中的伯母由于不能生育而被二奶奶骂作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不要脸的妲己。在幼小的舍木看来,二奶奶是慈祥和亲切的,只是在对待伯母的问题上才显得尖酸刻薄。作为对立面,伯母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实质上也是极其不幸的。她和二奶奶的较量实际上既是和封建的人伦思想做斗争,也是为了捍卫个人的尊严和保护家庭的完整。石舒清作品中生命意识的体现,既是由于他始终站在底层立场来评估普通人的人生价值,又是由于他对宗教观念的内化是出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石舒清的作品很少有皆大欢喜的结尾,读者在身临其境地经历了对苦难的挣扎后,终于获得了内心的净化。
六、结语
石舒清作为一个西海固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作品中具有丰富的本土文化和精神内涵。西海固地区的客观环境和民族文化影响了作家创作的主要取向和表达诉求,即乡土意识和苦难意识。同时,作为一个已经走出西海固并走向世界文坛的作家,石舒清将在西海固的岁月和人生作为底本,通过其深刻的道德意识、批判意识和生命意识,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本土文化精神的广度和高度。
作者:吴生艳 单位:宁夏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3][4]石舒清.开花的院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357,126,200.
[2]石舒清.苦土[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