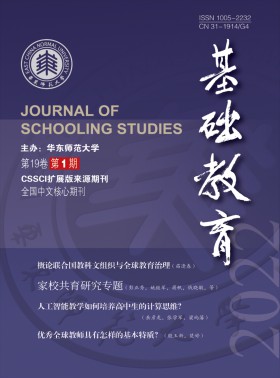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基础教育改革方案效能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世界背景中的我国基础教育“深改”
1.抓住高考改革的“牛鼻子”,对基础教育的“素质培育导向”改革形成倒逼机制。
2013年,教育部了《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框架(试行)》,确立了基于学生全面发展、持续发展与个性化发展的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2014年,教育部启动了高考改革,确立了“3+3”的高考新方案,基础教育改革的新环境指日可待。当然,国家对基础教育改革方向的干预主要是依靠多样化的评估与督导实现的,而非依赖单一的高考制度变革,用高考给学生松绑是大势所趋。应该说,多一把改革的尺子,基础教育就能多一份改革的活力,多一片自主发展、自由创作的天地。
2.依托课程改革的“轴心骨”,借此撬动基础教育改革的大船。
新世纪之初,我国学者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视为基础教育全局改革的抓手——推动国家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着力推进“三维”课程目标、三级课程体制、学生学习方式转变与教学评价改革,由此我国基础教育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新课程体制下,学校的课程权利、教师的课改创意、学生的自主空间得到了保证,僵化的旧课程体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矫治。
3.利用教师专业的“助推器”,引导改革走向实践、改出实效、落到实处。
目前,国家启动了一系列的教师标准建设,制定《教师专业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等,启动全新的教师资格认定方案,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等,实施大制度化的以“国培”领先的“三级培训”活动,试图以此把新课程理念植入教育实践的体内与教师的观念系统中去。
4.回归教育改革的“社会性”,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改革。
基础教育改革不可能被控制在学校空间内,因为每一个基础教育机构都是社会的细胞,每一次教育改革都是一次社会化行动,都会引发社会大系统的微调与重构。当前,基础教育改革引发的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优质教育资源城镇化集中问题、留守儿童教育缺失问题、家长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失语”现象、名牌大学中农村学生比例锐减问题等,都促使国家突出改革的社会性与协同性,努力把中小学校建设成为一所与社会相融合、相共生的社会机构,而非普通的知识文化传授场所。尽管如此,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较为突出,需要研究者在深入社会调研、广泛吸取异国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思考“深改”内涵,以此为国家后续基础教育改革提供参谋与建议,力促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少走弯路、直击主题、迎难而上。
美国历史上的基础教育改革大都是由教育基金会或民间教育协会组织发起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富布莱克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都曾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始作俑者。这些改革大都建立在对美国基础教育的大规模调研、分析与理论架构基础上,且都有一名关键“教育人物”的领衔与主导。基础教育改革是复杂的,如何科学评价改革的成效、成败、得失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最为棘手的莫过于评价框架蓝图的研发了。英国研究者夏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基础教育改革效能评估体系,它对我国基础教育“深改”观的确立而言颇具启示意义。夏普认为,完整的学校改革方案效能评估必须至少考虑“4板块26条指标”,这就构成了一个“8855”评价指标体系。这一体系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全面认识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框架。夏普还依据这一理论框架设定出了量化指标体系,并在全面评估美国历史上的六个学校改革方案基础上析取出了五个失败方案,即兰卡斯特方案(LancastrianPlan,1806)、年龄分段方案(Age-gradedPlan,1848)、盖里方案(GaryPlan,1906)、特朗普方案(TrumpPlan,1959)和基础学校联盟方案(即CES,1984)和一个成功学校改革方案,即学校发展方案(即SDP,1968)。从这一评价框架来看,名副其实的基础教育“深改”应该包括以下四个核心要素,即改革思想、教学改革、教师发展与学校变革。
(一)基础教育“深改”必须建立在深邃的改革思想体系之上
改革思想是完善基础教育改革的基础元素,它的形成需要改革者充分考虑四个因素,即研究支撑、基本假设、教师地位与学校态度。改革思想首先来自研究,包括对过去类似改革活动的研究与当下教育研究活动,这些研究活动及其结论能够提高改革成功的机率。所谓教育改革思想,其实就是改革者对基础教育活动的基本观念与价值体系,它们主要来自改革者对那些所谓不言自明、铁定如山式的教育假设的质疑,来自他们在美好基础教育蓝图指导下对即将要发生的教育变革的把握与预测。例如,夏普把尤金•郎(EugeneLang)的五个假设(Lang'sFiveAssumptions),即变革不可能来自学校外部,改革必须考虑父母与社区资源,必须调动学生与家庭的积极性,必定会改变学校现在的态度与权力关系,学校与非学校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等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源泉,其内在合理性不言自明。稳妥基础教育改革一定要将教师置于改革领导者的地位,聆听他们的建议,让他们担负起改革主心骨的角色,教师的支持、素质、观念是学校改革、教育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支撑点。正如萨拉索塔所言,“如果教师会跟随改革,那是因为整个改革方案的意识形态符合教育学生的利益。”在改革中,学校有可能不支持改革,极有可能敷衍改革,致使改革蓝图在实践中被架空。完善的教育改革思想必须充分考虑学校的态度,学校在改革中的实质性参与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生命线;如果学校内部的权力结构不发生根本变化,改革根本不可能发生并走向深入。所以,稳健的基础教育“深改”思想系统应该具有研究的视野、科学的理念以及教师、学校作为改革主体的参与,全面考虑这四个因素才可能提出科学、可行、完善的教育改革蓝图,为整个教育改革提供坚实的思想蓝图支持。
(二)基础教育“深改”必须强调“教与学”这个主题
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环节是教学,创建有效课堂,促使学生全体、全人、个性化发展是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始终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夏普的研究中,教师对“有效课堂”的定义剖析成为评价教育改革效能的重要指标之一。萨拉索塔指出:有效课堂基于“有效学习”,这种学习形态不仅关注“全部孩子发展”,而且还要实现学生各方面,即“认知、情感、情绪、动机与态度”的平衡发展。在美国初期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倡导教师中心式的改革,习惯了用工业主义思维去理解教育,进而把学生视为任由教育机器去模塑的“原材料”,把教学活动理解为“知识灌输”过程,而在二战后,美国教育改革方案关注商业主义思维,在教学活动中开始倡导学生中心式教学,推崇个性化学习、“做中学”与工作课程(Work),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社会底层学生的特殊关注、对学生自我实现的积极预期、家长与社区的参与等成为中小学教学活动中的全新关注点。学习是“社会——个人间的一场交易”,“知识通过‘做’来获得,没有被动的接受性”,所以,美国基础教育应质疑的是“:谁在学习什么和向谁学习,在可观察的事实背后隐藏着什么‘学习’概念?”这一质疑切中了教学活动的基础——学生学习问题,因为“改革包含的哲学理念是确保学生学有所获”。在完善的教学改革中,完整、有效、主动的学习活动才是整个教育“深改”最终生效的基石。
(三)基础教育“深改”必须关注教师的教学专业发展
教学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而教师的教学专业则是支持这一改革的“炉底石”,任何无视教师教学专业发展的教学改革必然是空洞而又虚幻的。“教学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门与观念、义务,包括个人的与人际相融合的合金艺术”,所以,“伟大的教师是伟大的艺术家,就像其他艺术家一样稀罕”。撑起教学活动大厦的正是教师的教学专业水准。因之,教师的教学专业资质不是教学活动的延伸,而是教学活动大厦的支柱与基石,我国基础教育“深改”必须从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培训与教育观念更新角度做好“深改”的大文章。教育部刘利民副部长指出,“建立教师队伍管理的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激励优秀人才长期从教、终身从教”,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基础教育改革不仅要建立教师的学术休假制度与在职专业培训,还要“与培养未来雇员的成熟教师及学校合作”开展教师培训项目,要探究“遴选出允许学生去学习、成长、成熟的优秀教师的方法”,进而双管齐下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在教育观念更新方面,改革者不仅要帮助教师建立有效教学的观念,还要引导他们“遗忘”旧教育观念,甚至要改变教师的日常工作表,促使教师的精神世界与日常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四)基础教育“深改”必须彻底变革学校系统
基础教育“深改”的基本单元是学校改革,学校既是基础教育改革的受力面,也是基础教育改革的聚力点与生力点。无疑,变革学校系统的最有力手段是国家的学校政策,变革的直接对象是学校的官僚体制。学校政策的形成主要涉及三个因素:政府介入改革的深度、政策制定者的个人态度与学校的内部结构。一般来说,有效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政府的支持力度较大,它从经济、政策、权力角度为改革保驾护航,确保有力度的改革顺利展开。就美国而言,政府支持基础教育改革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基础教育是美国参与世界竞争的工具,在冷战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变式例证;其二,基础教育承担着国民社会化、美国化的重任,因为“社会化是一个在哪里你能够变成为其他人想让你变成的人的地方。”在学校政策形成中无疑会带上制定者的烙印,会无形中发生制定者自身的“利益输送”现象,基础教育的“改革计划必须认识到教育政策制定者的威胁,并在不与改革哲学基础妥协的情况下整合他们的要求。”在改革中如何有效回避政策制定者的教育态度、教育常识对教育政策的微妙影响,是催生完善基础教育改革方案的现实要求。当然,教育政策只是变革学校系统的外因,基础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学校自身的觉醒,是学校放弃官僚结构,走向平衡的新结构。美国的基础教育发展史表明“:学校官僚机构是禁止协作、窒息学生与教师权力的工具”,因此,学校的“许多基础改革必须包括重建学校现有管理体制的内容……(在学校中)建立平衡的结构”。应该说,在当下基础教育“深改”中,我们一定要打破重视宏观改革而轻视细节改革,只顾改革前景而不顾改革后效,只管体制改革而不管学校变革等误区,努力克服重蹈覆辙的低效改革循环,努力创建持续增效的改革“增循环”。
三、基础教育“深改”的关键品质探寻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可谓轰轰烈烈,而一进入实践领域则只是“小波微澜”,甚至相当一部分中小学中“风平浪静”,改革的声音对他们而言就是“耳边风”,传统的教育、教学、管理、办学方式依然横行,旧的基础教育文化依旧在教育事业的底层中运转。在这种改革环境中,新型课堂、新型学校、新型教师几乎只是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浮油”而已,我国基础教育机体的筋骨并未被彻底撼动。甚至就连看似简单的中小学“减负”问题,我们也要把它当作“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问题来对待。作为真正有实效的基础教育改革,它一定是一场“全面、深刻、长效”的“深改”工程,一定是触动整个基础教育事业灵魂、根基的改革。我们认为,良性、深入、实效的基础教育深改应该具备以下五个关键品质:
(一)聚焦性:基础教育“深改”的实质是学校改革
有效的基础教育改革一定是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是围绕重点、以点带面、牵动全局式的改革。任何改革尽管需要面面俱到,但在具体实施中肯定只有少数几个枢纽链环,如我国当下的高考改革、美国的学校改革、英国的教学改革等。以此为支点、运用改革的“杠杆原理”来撬动基础教育改革的大局,才是实现成功改革的应有策略。改革需要聚光灯,基础教育改革的聚焦点是所有教育问题的集结点,是关联改革对象所有方面与链环的线索。在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基础教育改革是公立学校改革,学校才是改革的基本单元,学校的社会关系、教师教学、权力结构等是整个基础教育的缩影,立足于学校改进的改革才是有聚焦点的基础教育改革。这一改革思维非常值得我国学习,其合理性昭然若揭:一方面,基础教育“深改”绝非简单的国家工程,它只有落实在每一所学校中才可能真正见效,学校改革成效是基础教育改革效能的直接监测点;另一方面,立足学校的基础“深改”是一种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改革,只有这种改革才可能准确对接基础教育的现实需要。
(二)连锁性:基础教育“深改”是一次联动性实践
有效的基础教育改革一定是能波及、牵涉、关联基础教育事业全局的改革,因为每一点教育改革行动都需要社会有机体的呵护配合与连锁性反应才能完成。从某种角度来看,改革是一个正向能量的传递、传动过程,这一能量能否有效抵达社会系统的末梢环节才是批判改革深度与实效的核心指标。在这里,郎的学校改革理论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他认为,学校与社会之间是一个连续体,全面的学校改革一定是“连锁性”、“传动型”的,由此形成了一个“社会外因——学校近邻(家长与社区)——师生调动——学校结构”联动式变革。正如其所言,学校与非学校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学生能够从个人、教育、社会等方面感受到学校与非学校世界之间的非连续性。”基础教育“深改”的全程理应是:始于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化,充分考虑家长与社区资源,调动师生改革积极性,最终变革学校内部的文化与权力体系。鉴于此,在后续基础教育“深改”中,把握好改革的枢纽链环,保证改革力量的有效传递非常重要。应该说,国家、学校都只是基础教育改革力量的传递者与媒介者,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尤为重要。进一步讲,国家要做好社会要求与学校改革之间的媒人角色,其主要职能就是准确表达社会期待,并借助政策的纽带将之传达给学校;学校要做好政府、社会、社区与学生之间的媒人,其主要职能是让学生意识到学习的必要与社会的要求。基础教育改革力量传递的最终目标是要利用学校的重建、政府角色的调整来更好地服务学校、服务学生,真正发挥学校、学生作为改革终端主体的能动性。
(三)深刻性:基础教育“深改”需要深度的理念与方式变革
好的改革追求的不仅是见效,更要见“真效”、见“深效”,追求一种有深度的教育改革形态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诉求之一。当前,我国理解的基础教育“深改”主要追求的是体制机制意义上的“深效”,其标的是要解开基础教育利益链环上的“死结”,为基础教育的科学发展解套,真正实现基础教育体制、机制上的变革。而在美国,他们所理解的“深效”更多是深层的教学理念变革与学习方式变革。在约翰•夏普看来,基础教育“深改”的阻力主要来自中小学教师、政策制定者、研究者思维深处固结的一些隐性共识、正统理念与缄默意识。与之相应,深度的基础教育改革不仅需要新理念、新体制、新文化的创造与引入,更需要教师去“忘掉”旧理念,需要研究者去反省隐性改革共识,需要政策制定者去放弃心灵深处沉睡的种种顾虑与纠结。应该说,只要把这些改革意念、杂念统统革置换掉,一种全新的学校范式才能在基础教育中着陆、生根,国家才可能迎来真正有深度的基础教育改革。
(四)长效性:基础教育“深改”必须关注学校经历改革洗礼后最终沉积下来的东西
在当前,许多学者潜意识地把基础教育改革理解成为一场“风暴”,一场“龙卷风”,理解成为一种立竿见影的变革行动。其实,这恰恰是对教育改革规律的无视,是对基础教育“深改”真意的误读。有效的教育改革总是渗透性、沉淀性、慢效性的,尽管学校经历了多次改革的洗礼与冲刷,但在学校中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的都只是改革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光点。指望所有的教育改革举措都能够在基础教育机体中生长起来,那只是一种痴心妄想。夏普在反思美国历史上的五次失败学校改革,即兰卡斯特方案(LancastrianPlan,1806)、年龄分段方案(Age-gradedPlan,1848)、盖里方案(GaryPlan,1906)、特朗普方案(TrumpPlan,1959)和基础学校联盟方案(即CES,1984)与一次成功学校改革,即一学校发展方案(即SDP,1968)之后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哪怕是失败的基础教育改革,其中那些真正有效的成分也会在基础教育文化中生存下来——这就是一场基础教育改革的“终效(”即最终效果)。正如其所言,“道尔顿计划(theDaltonPlan),推行个性化教育,尽管失败了,但却被广泛吸收,兰卡斯特计划(LancastrianPlan)、特朗普计划(trumpPlan)、盖里计划(GaryPlan)成为美国教育的基础。”真正长效的学校改革一定是渐进式的,是在改革洗礼中被基础教育实践所认可、所吸纳、所存留下来的真正有效改革举措的文化积累与隐性沉淀。
(五)公平性:基础教育“深改”是一项社会平衡工程
基础教育改革的内核是学校改革,而学校改革又是社会建构工程的一部分,改革不能不关注由其引发的社会效应与其肩负的和谐社会建设使命。无论是我国还是美国,如何在教育政策中科学体现对特殊学习者群体的关注、关怀,都是学校教育政策的重要立基点。进言之,促进教育质量高位均衡,创建公平、和谐、安全的基础教育,是世界基础教育的共同追求。在美国学校改革中有三个问题始终是改革的关注点,即新移民的美国化问题、少数种族人群的社会融入问题、社会底层儿童的早期经验“赤字”问题,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决定了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主题,如兰卡斯特改革、学校发展改革(SDP)等。在我国,这一问题集中在留守儿童、少数民族儿童、家庭困难儿童的学校教育保障、名牌大学中农村学生比例降低等问题上。创建公平普惠、高位均衡的中小学教育,就“要努力推动从单纯提供机会的公平转向实际获得机会的公平”,认真解决边缘儿童在受教育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真正解决关系我国基础教育平稳发展的这一敏感问题。所以,基础教育“深改”必须具有公平普惠性的价值立场,否则,改革很可能成为生产畸形社会的工厂。
作者:龙宝新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