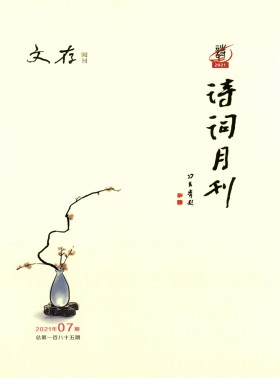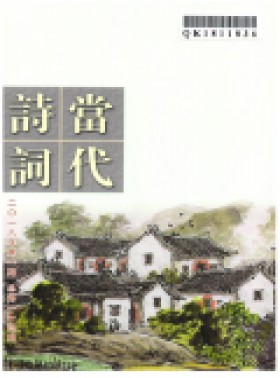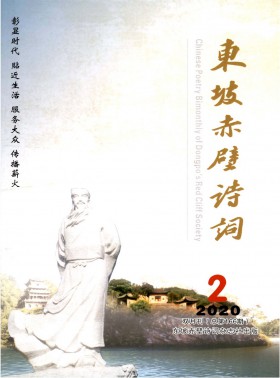诗词歌赋范文1
关键词:语文教学 诗词歌赋 丰富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有数以万计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它们犹如一颗颗闪亮的珍珠,光彩夺目。语文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熟读、背诵、鉴赏和运用教材中的诗词,还要善于运用诗词歌赋来丰富语文课堂,从广度和深度上开发诗词歌赋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那么,诗词歌赋如何同语文教学结合,又怎样发挥其作用呢?
一、渲染意境,激发兴趣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歌是艺术创作的结晶,它追求情景交融的美妙意境。讲课前,利用三五分钟指导学生抄录背诵有关的诗词,不仅利用点滴时间传授了知识,且书声琅琅,情绪昂扬,营造了课堂上应有的文学气氛,让学生领略这妙不可言的意境美,使学生从心理上把语文课同其他课区别开来,有利于集中注意力,上好语文课。同时,多次这样训练,潜移默化、熏陶感染,可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例如,语文教学中师生依靠诗情画意作画,教师的深情范读,相配的古典名画,都能让学生体会到课文中的诗情画意,激起学生对民族文化的敬仰之情。
二、拓展阅读,补充课文
课改提出的新理念,“不能教教材,而要教材教”,即要创造性地理解、使用教材,积极开展课程资源,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利用诗词歌赋同课文在内容上的联系,适时引入教学环节,作为课文的补充,以利于加深理解课文内容。
学习《南州六月荔枝丹》,将白居易的《荔枝图序》抄录给学生,引导学生深入认识比喻说明法的特点及由整体到局部的说明顺序,还可使学生了解:古人早已对荔枝不耐贮藏有真切的认识、生动的记载,体会课文引用古诗文的准确、精妙。学习《秋色赋》,把欧阳修的《秋声赋》印发给学生。通过阅读,引导学生将峻青笔下绚丽多彩的秋色同古人笔下肃杀悲凉的秋景加以对比,从而体会出课文作者写秋色的时代特征,有利于领会文章主旨。
上述两例,前者可在课文讲读后抄录补充,以印证体会;后者在讲课前印发补充,以对比认识。有些诗词歌赋,根据需要,亦可在讲课过程中补充。
三、立足诗词,培养素养
素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里有一个量的积累。在大语文观理念的指导下,语文教学应运用诗词歌赋来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文学气质、诗学素养,对语言文学的敏感力、洞察力,使学生徜徉在语文的海洋里,领悟语言文字之精妙。由于诗词歌赋短小精悍,有好些诗词在孩提时代学生就已经会背诵,教师应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积累,加以引导,激活兴趣。
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有些课文,涉及作者的思想渊源或人物的精神品德。这时,有必要借用诗词歌赋的素养追根溯源,使学生从思想本质上认识作者的人格、情操、爱憎,以更准确地领悟课文的主题,体会文章的感情。例如,学习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饮酒》,可同时学习作者的《五柳先生传》,使学生了解作者的处世态度,以尽快地把握诗的主题。
四、联系体会,借鉴练笔
不妨先来看一个颇有趣味的现象:老版高中课文第一册第一课《荷塘月色》中,引用了南朝乐府诗《西洲曲》;第二课《长江三峡》,引用了杜甫《夔州歌》《咏怀古迹》和古代歌谣;第三课《雨中登泰山》,引用了《诗经》的句子、杜甫的《望岳》、宋之问的《桂阳三日述怀》。一个单元,三篇课文,篇篇都引用诗词歌赋。是偶然现象吗?不是。打开每天的报刊杂志,你会发现不少文章是以古人诗句做题目的;看看电影电视预告栏,你也会发现有些片名与古人诗句不无关系。这说明了古代诗词歌赋的优秀篇什,是古人千锤百炼的成果,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是能使文章生色的。
诗词歌赋篇幅虽短小,但同样有起承转合,有完整的结构,有格局,有意境。在写作教学中,用它做范例,具有简洁、方便的特点。比如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之类的作文题,我们就可以拿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做例子,思考如何组织材料,如何布局谋篇。如果写《送别》之类的作文题,则可以拿李白的《赠汪伦》为例,夹叙夹议,写景抒情相结合。
五、了解民俗,积淀底蕴
古诗词歌赋距离学生遥远,有很多诗词都有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风俗民情,反映了我国民俗节日的来历及有关情景。适逢民俗节日,可向学生介绍有关的诗词,吟咏背诵,借以了解民俗节日的情况,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积淀底蕴。
诗词歌赋范文2
【关键词】 园林意境 诗词意境 园林艺术
1 在园林艺术中借鉴诗词歌赋的境界与场景表达意境
1.1 园林艺术中借鉴诗词歌赋的内容与场景
中国古典园林中,很多园林会去借鉴诗词歌赋的内容,甚至在园林中摹写诗词歌赋的场景。在这种借鉴中,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云无心以出岫…扶孤松而盘桓”、“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等,实际上就是园林的写照;可以说,陶渊明在写自己居住的环境,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种园林意境的参考与借鉴。谢灵运的《山居赋》为汉代一大赋,虽已残缺,但其对于园林的影响在中国诗文中应该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整个赋可以认为是一个山水游记,以描写田庄的山水自然景物为主,又时时表现出作者身居其中的游乐情趣。这种对景物环境描写的诗词歌赋在后世还有很多,它们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文人的园林审美观。
1.2 园林艺术中引用诗词歌赋的内容
在中国园林本身的命名上,有很多就是借鉴诗词歌赋而成。如扬州何园最初名为“寄啸山庄”,取自陶渊明诗“倚南窗以寄傲,登东皋以舒啸”;明崇祯四年,王心一得到拙政园东部园地,重新构筑,名其园为“归田园居”,取自陶渊明诗《归田园居·卷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扬州耦园的“耦”字出自《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苏州沧浪亭中的“沧浪”出自屈原“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诗句。这种运用使中国园林艺术的诗词歌赋的意境无处不在。
1.3 景点命名上使用诗词歌赋的境界
中国古典园林景点命名使用诗词境界的也很多,如苏州留园的汲古得绠处来源于韩愈的《秋怀》诗:“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又如北京北海公园的景点濠濮间,其来源是《世说新语》,其中说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间想,觉鱼鸟自来亲人”。再如寄畅园有八音涧,其“八音”二字亦有典可查:晋代左思说:“何必丝与竹,山水有轻音”;《三字经》有“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还有避暑山庄采菱渡,这个名称出自王维的诗句:“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这样的应用既是对景点的写实,又是对景点的写意。
对诗词歌赋境界的运用,实际上就是为了在园林中得到诗词歌赋的意境;这种意境在诗词歌赋的创作过程中可能都是妙手偶得。而古代园林设计者试图将思想形态变为空间艺术形态,安置于园林之中,去供园主人体悟或者抒发自己的情感。
1.4 园林意境中通感诗词歌赋的意境
由于在诗歌艺术中情、景合二为一,这就使得园林在置景时很自然地从诗词歌赋中获得启发,有的景点则是直接地把名篇佳句所描述的美景以具体的物质材料再现出来。拙政园中的听雨轩就是典型一例。听雨轩是园中一个小院,院落一角有一潭清水,水旁几丛芭蕉;如遇上雨天,人在园中,细听雨打芭蕉之声,会更加体味到环境之幽静、深远。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李义山的名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只不过是由荷叶变成芭蕉而已;同时,还使人体会到“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意境。
中国园林在结构、空间布局上也深受中国诗词的影响。如颐和园万寿山后湖有水居村、苏州长街等,沿水滨两岸有茶楼酒肆、歌船画舫以及隐约在山后的宝塔寺;每当入夜,不仅有水街之繁华、喧闹,而且有“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深幽、静谧。
2 园林景观结构近似于文章结构
2.1 园林景观与文章脉络上的近似
文学艺术在表达上忌平铺直叙;这如同园林道路形式忌直线,总是在园林其他造景要素之间迂回、曲折地设置,以这种曲折变化的道路形成渐变景观序列。
文学艺术在体例的安排上,在一个主题下有前奏、起始、主题、高潮、转折、结尾等过程;而园林也同样在主干游览路线上使景点的表达跌宕起伏、起承转合,形成一个如同文学创作般的主题脉络。
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是一个要求有严谨的章法、精炼的语言的艺术创作形式;园林艺术的创作也可以说是有意无意地符合了这一点,其在建造上力求做到增之则过、减之则少。
2.2 园林景观分区与文章内部结构上的近似
在文学艺术上,要对文章整体进行分段、分章节论述,这样的文章分割增强了文章的条理性,而没有改变文章的整体性。这就好似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分割手法;为了做到“以小见大”,中国古典园林对其园林空间进行多次分隔,分隔以后的空间通过回环的道路链接成一个整体,空间与空间之间做到隔而不断、露而不透,增强了园林赏景的趣味性。
这种园林景观与文章结构上的趋同,都是受到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相同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造就了艺术表现形式上的近似性。
3 运用题名手法对园景进行直接的点题
3.1 园林艺术中以题名表达自身境界
题名的手法大量使用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有以地名题名、以纪念性题名、以形态题名、以材料及建筑技巧题名、以个人涵养题名,等等。在中国古典文人园中,更多的是引用诗词歌赋以及古代文献来题名,以这种题名形式表现环境特点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情、标榜了自我的精神意志。
直接以景进行题名表达自己的思想境界的如苏州留园闻木樨香轩,其本义是指出轩周围种有桂花,但从内涵上讲,“闻木樨香”有悟道之意,语出宋代释普济撰的佛教禅宗史书《五灯会元》中黄庭坚悟道一段,晦堂趁木樨盛开时说“禅道如同木樨花香,虽不可见,但上下四方无不弥漫.所以无隐” 。黄氏遂悟。
从苏州拙政园雪香云蔚亭这一题名上,可以想象,在亭的周围应该是种有梅花的,园主人是以梅花的高洁脱俗来自喻。拙政园内还有一个荷风四面亭,从字面上可以发现亭的四周应该是荷花,在立意上出自济南大明湖名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在造景上隐喻了园主人的“出淤泥而不染”。
3.2 园林艺术中以题名总括景点意境
再有,中国园林中常常利用题名对整个景点进行总括,特别是在大型风景区域景点中,这种手法应用更多;此种名题通常出现在山石上,甚至直接立以碑文。如苏州观梅圣地邓尉山香雪海就是这种用法;香雪海出自清代宋荦之诗作“望去茫茫香雪海,吾家山畔好题名”,并亲题“香雪海”三字,刻于梅亭前岩上。
中国古典诗词本就讲究情景交融,景语亦情语。在园林景观中,直接以名诗佳句为景名,自然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从而真正做到景传诗情,诗情得以具象化,景观的内涵也就更加丰富了。游人至此,眼观美景,口吟佳句,也就引发出更为广泛的联想,获得更为深厚的美感享受。这种诗意化的景名使得诗与景、园与文结合起来,可谓中国园林的一大艺术特色。即使有些景点的题名不一定来自名篇佳句,但也同样有着诗意化的韵味,如西湖景点的景名“苏堤春晓”、“三潭印月”、“花港观鱼”、“柳浪闻莺”等;类似的景名在中国园林中随处可见。
4 总结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表达形式多样,但是其意境与中国的诗词歌赋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古代的造园家往往对诗词歌赋有着极深的造诣,这也使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与中国的诗词歌赋不可分割。
参考文献
[1] 盛翀编著. 江南园林意境.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2] . 翳然林水 栖心中国园林之境. 北京市: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刘天华. 画境文心: 中国古典园林之美. 北京市: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4] 谢孝思主编. 苏州园林品赏录. 上海市: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诗词歌赋范文3
关键词:隐逸情怀;文人情节;宇宙的人情化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31-02
“凡结林园,无分村郭,地偏为胜,开林择剪蓬蒿;景到随机,在涧共修兰芷。径缘三益,业拟千秋,围墙隐约于萝间,架屋蜿蜒于木末。山楼凭远,纵目皆然;竹坞寻幽,醉心既是。”
“刹宇隐环窗,彷佛片图小李;岩峦堆劈石,参差半壁大痴。”
“移竹当窗,分梨为院;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
——明·计成《园冶·园说》
我国园林,自先秦“囿、苑”始,经东晋而视野渐阔,至明清乃集于大成,终成为无数文人墨客所魂牵梦绕的一种情节。我在文首列无否先生《园冶》一书的几段截句,既是表达对这位“浮萍身世,秋水文章”①的园林大师的敬慕,也是因为这几句平实的话,道出了中国园林的美,以及在这美的背后,文人的园林情节。
《诗经·大雅》中记述了周文王的“灵囿”②,这应该是文史资料中能够找到的最早关于园林的记载。始建于秦皇而成于汉武的“上林苑”③,则成为了皇家园林的代表。北宋徽宗皇帝的“艮岳”④,更是把皇家园林的奢华发挥到了极致。从宋元到明清,从皇家到士夫,除了我们熟知的“两苑”、“畅春”、“清漪”、“圆明”等著名皇家园林之外,江南的另一种园林形式“文人园林”悄然兴起,至明清可谓灿若明珠,成为了体现园林中“虽由人做,宛自天开”⑤,哲学与美学境界的最高表现形式。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是陶渊明《饮酒》系列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幼年读之,满怀着对“悠然南山、日夕飞鸟”的无限向往,只觉清远上口。如今已趋而立,这种向往愈发强烈起来。我想,这也正是“结庐人境”,却渴望“大隐于市”的一种情节。这种隐逸的情节自古已然,从两晋到唐宋,文人将这情节寄托于山水之间,抒发在诗文之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⑥,唐宋以后,山水画的成熟,更成为了文人寄托隐逸情怀,抒发胸中丘壑的另一种形式,“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⑦至此,园林成为诗画在现实中的实现,“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彼千金万金造园亭,或游宦四方,终其身不能归享。而吾辈欲游名山大川,又一时不得即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历久弥新乎。对此画,构此境,何难敛之则退藏于密,亦复放之可弥六合也。”板桥先生《题画竹石》,说的正是这种实现,文章虽短,却道出了文人造园的真谛,而园林正是文人寄情山水、抒发隐逸情怀、描摹胸中丘壑,以及他们的哲学思想在现实中实现的方式。
江南自古以来就是天下富庶之地,尤其是从东晋到南宋的经济重心南移,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也带来了丰富的文化。这是江南文人园林的物质与精神基础。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吸取元代奢靡浮华导致统治终结的教训,“敦崇俭朴”为政之风⑧,制约了明代初期的园林建造业。到了明代中晚期,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甚至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使得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足。这种富足的生活并没有让社会进入良性的发展轨道,扭曲的封建专制制度,文字狱的思想钳制,特务横行宦官专权,政府加紧对百姓的盘剥,关外的女真民族逐渐崛起,虎视眈眈,内地的农民起义星火燎原,整个社会处在内忧外患之中。从万历到嘉靖,再到崇祯,昏聩的大明帝国舵手带领着这个庞大的帝国逐渐驶向万丈深渊,整个社会弥漫在奢华无度的享乐风气之中。江南的文人园林在这时兴起,一方面是由于文人生活的富足,生活质量的提高,有闲散的钱财支撑他们筑园造林;另一方面,则是逐渐进步的个人意识与封建专制之间的冲突,强化了文人的隐逸情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⑨,个人的进步行为无法实现,遂带着自己的哲学退于一园之内。如苏州的网师园和拙政园,“网师”即渔夫,网师园始名“渔隐园”,“拙政”即拙者之为政也。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⑩正是由于文人的狂热参与,明清园林在江南的建造愈发繁荣。江南的园林越来越体现出文人的特色,个人才华、诗情画意、哲学反思在小小一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世之兴造,专主鸠匠,独不闻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谚乎?非主人也,能主之人也。”?輥?輯?訛江南的园林,正是文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园林建造中的体现。
诗词歌赋范文4
1、门前一只狗,在啃肉骨头,又来一只狗,双双打破头。
2、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咩! 水牛下水,水淹水牛鼻,哞!
3、前不见蹄膀,后不见烤鸭,念肚子之空空,独怆然而涕下,唉!
4、不择手段------不折手断?我只轻轻地推了他们一下,怎么会不折手断呢?
5、一箫一剑走江湖,千古情愁酒一壶!两脚踏翻尘世路,以天为盖地为庐!
6、昨日作诗无一首,今天作诗泪两行,天天作诗天天瘦,提起笔来唤爹娘。
7、你依我依,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再将你我,用水调和……
8、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相思,请君仔细翻覆看,横也丝来竖也丝!
9、昨夜传诗,闯下大祸,你依我依,忒煞情多!淫词艳曲,太后生气。公主瘦瘦,王子心急!横也是死,竖也是死,不如一笑,好过咽气!
10、满腹心事从何寄?画个画儿替!小鸟儿是我,小花儿是你!小鸟儿生死徘徊时,小花儿泪洒伤心地!(经典语录 )小鸟儿有口难开时,万岁爷错爱无从拒!小鸟儿糊糊涂涂时,格格名儿已经昭大地!小鸟儿多少对不起,小花儿千万别生气!还君明珠终有日,到时候,小鸟儿负荆请罪酬知己!
11、紫薇台词:“你和她看雪,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我都没有和你看雪,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12、尔康台词:“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和她看雪,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我以后只和你看雪,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
13、小燕子雷人台词: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叫,猫不跳,鸡不飞,猪不闹……爹不疼,娘不要……
14、蒙丹与含香私奔,香父率兵追赶,在沙漠上堵住二人,众兵殴打蒙丹,同时拖走含香,含香身子拖在地上,仍奋力回头,眼含热泪大喊:”蒙丹!你是风儿我是沙!“而后口吟诗句:”风儿萧萧,沙儿飘飘;风儿吹吹,沙儿飞飞。风儿飞过天山去,沙儿追过天山去!“
诗词歌赋范文5
清代以降,唯有少数学者对“缘情绮靡”持赞赏的态度,如毛先舒《诗辩坻》曰:“古人善论文章者亦有自摅独欣,不可推放众制者,如子桓‘诗赋欲丽’,士衡‘绮靡’、‘浏亮’语是也。”[5]71表现出独到的审美眼光。大部分学者则几乎全部集中在批判上,如纪昀《云林诗抄序》曰:“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绘画横陈,不诚已甚欤?”[6]537虽拈出“缘情”二字,批评点却在“绮靡”,认为“缘情绮靡”造成了诗歌雕绘满眼,缺少诚挚的情感。朱彝尊《与高念祖论诗书》亦曰:“魏晋而下,指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之思,而无恭俭好礼、廉静疏达之意,恶在其为诗也。”[6]283将六朝浮艳文风完全归罪于“缘情绮靡”的诱导。这种批评实是明人批评“缘情绮靡”所造成六朝诗歌流弊的引申发挥。比较而言,沈德潜的批评则直入本质。其《说诗晬语》曰:“‘诗缘情而绮靡’。言志章教,惟资涂泽,先失诗人旨。”[5]532《古诗源》也重申这一观点,认为陆诗“词旨敷浅,但多涂泽”,“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7]133将陆机理论与创作联系考察,认为“缘情”本未可非,然追求“绮靡”,描摹物色雕绘,致使丧失了“空灵矫健之气”。虽未必切合陆机理论的本意以及创作的特点,但所阐释的理论却是正确的。论“缘情”,近代学者或以为与“言志”无涉。如朱自清《诗言志辨》认为,“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这个新语,是‘诗言志’以外的‘一个新目标’”[8]35。周汝昌也认为:“陆机本意之与‘言志’,与‘闲情’、‘艳情’、‘色情’并无干涉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9]58-65认为陆机所言之情,是指缘诸人之生命的喜、怒、忧、惧、爱、恶、欲之情,既与传统的“言志”之志不同,也与一般表达的诗歌不同。早期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大纲》,后来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等基本上都持这一观点。或以为“缘情”“言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裴斐《诗缘情辨》认为,言志论本身就包含着缘情的观念。言志论不仅充分认识到诗的缘情特征,并且指出了情之所生的客观依据。“缘情论既脱胎于言志论,又是对它的否定”,即继承了先秦诗论家所揭示的诗的缘情特征,否定了以志抑情的诗教观念,“于是,在缘情论里‘志’与‘情’便不存在矛盾,成了一个东西,很难以加以分别”[10]13-22。詹福瑞《“诗缘情”辨义》从内涵与外延上阐释了二者的联系与区别:“‘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汉儒说《诗》,用以补充‘诗言志’的情,主要指世情,且多群体之情;而陆机‘诗缘情’的情,主要是物感之情,多指诗人一己之情。”[11]64-65情与志互相包蕴,然而汉儒说《诗》,具有强烈的社会性,陆机言情则带有强烈的主体性。论“绮靡”,或分而言之,认为“绮靡”是同义复词,如20世纪30年代陈柱在《讲陆士衡〈文赋〉自记》中明确指出:“绮言其文采,靡言其音声。”[12]周汝昌亦有类似的论述;或合而言之,认为“绮靡”是一个词,如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曰:“绮靡,犹言侈丽、浮艳。”[13]261近年出版的几部文学批评或文学思想史著作亦有近似论述,如《中国诗论史》说:“‘缘情’为‘意’,‘绮靡’为文。”[14]202《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曰:“‘诗缘情而绮靡’一语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用‘缘情’代替了‘言志’,而在于它没有提出‘止乎礼义’,而强调了诗的美感特征。”[15]102似乎都以整体意义为着眼点的。以上论述,无论是论述“缘情”与“言志”的关系,或从诗学发展上说,或从范畴外延上说。还是论述“绮靡”,或指语言精妙,或指整体风格;或以为是一个词组,或以为是一个单词,在笔者看来,似乎都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深层本质,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二、“缘情绮靡”:诗歌发生的审美机制
研究“缘情绮靡”的理论内涵,首先,厘清“缘情”“绮靡”的语词意义及其作为诗学范畴的理论内涵;其次,必须合理阐释“情”与“志”的关系。本文基本观点是:“缘情”是从诗歌发生的角度说,是诗歌发生的审美机制;“言志”是从诗歌表现的角度说,是诗歌表现的审美状态,二者属于不同层次的诗学范畴。先说“缘情”。人们习惯于将“缘情”与“言志”对比论述,争论的焦点不外乎是内涵的界定以及二者的内在关系。这实在是一种思维视角上的误区。其实,“诗缘情”是说诗缘情而生,从诗歌发生的角度阐释诗歌的特征;“诗言志”是说诗表达情志,是从诗歌表现的角度描述诗歌的特征。二者是分属不同的逻辑层次,有着本质的差异。缘情之“缘”意即因缘。“缘情”的意义不是抒情,而是因缘于情。考其字义,则虽生于中土,却与佛教之“格义”关系密切。《说文》:“缘,衣纯也。”即衣服的边饰。引申为顺、沿着。《庄子山木篇》曰:“形莫若缘,情莫若率。”成玄英注:“缘,顺也。”汉桓宽《盐铁论刑德》所言之“缘人情”,也是指顺乎民情,与魏晋之“缘情”意义亦不同。然《汉书艺文志》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乃有因由、依缘之意,与“缘情”之缘意义相近。但是,从历史文化语境上看,陆机提出“缘情”说,正是佛教“格义”盛行之时,也是佛教开始全面向士大夫思想意识渗透之时。因此,缘情之“缘”不可能不受佛教“格义”之影响。而佛教之“缘”即是“格义”的产物,既取汉代之因由、依缘之意,又包含着特定的佛教意蕴。佛教之“缘”有二义:一是因缘之缘,指事物之间相关联的因果关系;二是缘虑之缘,是心缘外境而生识的因果关系。在佛教中,“缘”又是“缘因”之略。缘因就是二因,亦有二义:一是生因和了因。生因是能够产生果实的本源,如物种生芽,芽生果实;了因是以智慧透视事物的原理,如灯照物,了了可见。二是正因和缘因,正因是主要的因,缘因是助缘(次要)的因。若依佛教对“缘”的阐释,“诗缘情”则是说诗因缘于情——由情而生;情因缘于境——因物而感。故《文赋》曰“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思归赋》亦曰“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从诗歌发生学上看,情是因,诗是果。情亦包含智慧感悟之物理,与“道”同生;诗亦为智慧物理之载体,亦可以明“道”。故《叹逝赋》曰“乐心其如忘,哀缘情而来宅”,《文赋》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遂志赋》又曰“作诗以明道述志”。由此可见,在诗学意义上,“缘情”之情是情、志、理的三者统一。后来,萧统《同泰僧正讲诗序》曰:“大正以贞俗兼解,郁为善歌;琏师以行有余力,缘情继响。余自法席既阑,便思和寂。”说明佛教徒颂经开讲之余,缘情而作,以发抒佛理。其诗亦曰:“若人聆至寂,寄说表真冥。伊予寡空智,徒深爱怯情。”则是对缘情说的佛理阐释。次说“绮靡”。从语词上说,“绮靡”在魏晋时期并非联绵词,而是一个双音节词。由于“绮靡”同另一联绵词“猗靡”音形皆近,遂至误用,后来“绮靡”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联绵词,因此造成今人理解上的困难。“绮靡”之“绮”,《说文》:“绮,文缯也。”《六书故工事六》:“织采为文曰锦,织素为文曰绮。”亦即以素为底色,织以文彩,这似乎已成共识。问题在于“靡”究竟如何索解?周汝昌引《方言》卷二曰:“纤,缯帛之细者谓之纤,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绫,秦晋曰靡。”郭璞注:“靡,细好也。”如果依照《方言》所言,确如周汝昌所言:“‘绮靡’连文,实是同义复词,本义为细好。”然而郭璞解为“细好”——细而美,似应是形容词,而不再是缯、绫之名,其间透出了从汉至晋的语词变化信息。其实,绮、靡二字到了魏晋以后,由原来的名词转化为形容词。汉人所言之“靡”固然义项丰富,但是以“靡”形容声音之悦耳,亦为常用义。如东方朔《答客难》:“譬犹鼱鼩之袭狗,孤豚之咋虎,至则靡耳,何功之有?”“靡耳”显然是指声悦于耳。这从后来的《文心雕龙》也可得到证明:“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乐府》),“晋世群才,稍入轻绮”(《明诗》)。显然,刘勰所言之“靡”指音调的圆润连贯,“绮”指文辞的华美绮艳。可知,“绮靡”二字是并列结构,而非同义复词,更不是联绵词。这在《文赋》中也可找到内证:“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绮”喻色彩清丽;“或寄辞以瘁音,言徒靡而弗华”,“靡”指音调宛转。故陈柱曰:“绮言其文采,靡言其音声。”《文心雕龙》多次连用“绮靡”,如“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时序》),“《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辨骚》)。“绮靡”连用,其意有三:一指色彩华美,如班婕妤《捣素赋》:“曳罗裙之绮靡,振琼佩之精鸣。”二指音韵和谐,如阮瑀《筝赋》:“浮沉抑扬,升降绮靡,殊声妙巧,不识所为。”三指情感萦绕,如阮籍《咏怀诗》:“绮靡情欢爱,千岁不相忘。”从《文赋》看,既指文辞与音韵,也包含情感在内。其后谢灵运《昙隆法师诔》所说的“繁弦绮靡”,则主要从音韵与情感着眼。概括言之,“缘情绮靡”,阐释了诗歌发生与情感表达的关系,也揭示了诗歌风格的一般性审美特征。再说“缘情”与“言志”。由上所论,“缘情”与“言志”并非一个逻辑层次上的范畴,因此本文并非从诗学范畴上论述二者关系,而是从构成这一诗学范畴的主要元素上论述“情”与“志”的关系。先秦时期,情、志是同源字,二者意义并无本质区别。王运熙等说:“‘诗缘情’的说法,实际上与传统的‘诗言志’、‘吟咏性情’有着继承关系,都将诗视为作者内心世界的表现。先秦时所谓‘言志’之‘志’,本来不是不包含感情的,但当时人对于诗抒感、以情动人的特点缺少自觉。”[15]101毫无疑问,先秦所说的“志”,包含着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孔颖达《正义》曰:“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16]1454六志即六情:好恶喜怒哀乐。然而先秦的“志”比“情”内涵更为丰富。《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与“情动于中”意义基本相同,因为《诗大序》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才导致后人诸多误解。魏晋以降,情、志几乎成为同义词,二者在内涵与外延上也几乎互相叠合。以拙著《陆士衡文集校注》所收篇目统计,陆机用“情”字共出现67次,除去“”1次、“人情”1次、存疑作品《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处碑》3次之外,尚有62次;“志”共出现47次,除去“志士”6次、存疑作品《晋平西将军孝侯周处碑》3次之外,尚有38次。二词意义几乎完全叠合,如《遂志赋》序曰:“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滥。”志与情显然同义,否则就无法解释“志壮而泛滥”。情、志作为同义复词连用,在汉魏相当普遍,如蔡邕《释诲》“和液畅兮神气宁,情志泊兮心亭亭”,嵇康《琴赋》“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等,都能说明这一问题。如果纠缠于情、志内涵与外延上差别实在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情志合一的诗学观念,也使陆机诗学有强烈的儒家诗教的思想倾向。梅运生先生指出:“陆机要求包括诗赋在内的十体文章‘亦禁邪而制放’,也就是要止乎礼义,设了礼义的大防。‘诗缘情而绮靡’与‘亦禁邪而制放’是互相衔接的完整的命题,比起《毛诗序》所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命题,有了重要的丰富和发展,但无本质意义上的区别。”[14]148《文赋》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遂志赋》又曰:“作诗以明道述志。”可见,“缘情”与“明道述志”,是陆机强调的并行不悖看似二而实为一的诗学原则。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诗的发生,后者强调诗的表现。所以陆机所言之志,以道为骨,以情为气,而且情志一也。他强调“颐情志于典坟”,典坟,孔安国《尚书序》曰:“三坟,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也。”[17]4颐养高洁情志,一旦发诸诗,必然是意蕴深厚,志气充沛,情思浓郁。“理扶质以立干”正是其警策的描述。所以钱谦益《增城集序》曰:“缘情绮靡,要以言其志之所之而已。”[18]958虽然也混淆了诗歌发生与诗歌表现之差别,但论情志之关系则是正确的。上文已引,沈德潜认为,“缘情绮靡”不仅“言志”——抒情,而且“章教”——彰显儒家诗教。可见陆机诗学也是以儒家诗教为理论基石的。然而陆机所言之“理”不唯包含“道”,亦且包含四时之叹、瞻物之思、人生感悟、中区玄览等沉积于情感深处的思想理性。这种诗学思想又受荀粲“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19]320之类的玄学思维影响。简言之,“缘情”是诗歌的发生过程,“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缘情”是情、志、理的统一;“绮靡”是文辞、音韵、情感的统一。补充说明的是,陆机《羽扇赋》“夫创始者恒朴,而饰终者必妍。宪灵朴于造化,审真则而妙观”,既强调由朴至妍的文学进化观,又强调宪法自然的文学创作观。与“缘情绮靡”的理论内涵是一致的。
三、“缘情绮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从佛教语言上说,解释“缘情”之缘为因缘之缘、缘虑之缘,是否悖离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从审美风格上说,“绮靡”是西晋诗风的基本特点,与佛教有无关联?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将“缘情绮靡”放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阐释。从陆机现存的作品看,似乎很少受佛教影响。以儒为根,徘徊于儒道之间,是其诗学思想的基本特点。但是,并不能说陆机诗学与佛教没有丝毫关联。佛学发展到魏晋,逐渐为士大夫所接受。朱士行毅然出家皈依佛门,并西渡于阗取回真经;曹植熟悉梵呗经声,并应用于文学创作,即为明证。陆机早年生活在一个佛教气氛极为浓郁的东吴,维祗难、竺律炎、康僧会都是在东吴传播佛教的高僧。康僧会影响尤其深远,《高僧传》本传载:康僧会世居天竺,后随父移居交趾。出家后,受业于著名佛教翻译家支谶弟子支亮。“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汉献末乱,避地于吴。孙权闻其才艺,召见悦之,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与韦曜(昭)诸人共尽匡益。”僧会于赤乌十年(247)到达建邺,设像传道,“由是江左大法遂兴”。后来孙皓又“遣使至寺问讯道人,请会说法。会为敷析,辞甚精要。皓先有才解,欣然大悦”,并就僧会受戒,“宣示宗室,莫不必举”。康僧会特别善于援引儒学经典以阐释佛教义理,如对孙皓曰:“夫明主以孝慈训世仁德育物善既有瑞,恶亦如之。故为恶于隐,鬼得而诛之;为恶于显,人得而诛之。《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家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20]14-18这种融合儒佛的释经方式,促进了佛教在江南士大夫中的传播。陆机青壮年时期都是在这样佛教浓郁的地方中度过的。太康末,陆机入洛,洛阳也是佛教隆盛之地。译经丰富,寺庙林立。西晋译经达165部之多;《洛阳伽蓝记序》记载,“至于晋室永嘉,唯有寺四十二所”[21]4。历经战乱,尚有如此之多的寺庙,可以推想元康之前佛教的盛况。佛教信仰也开始渗透于士族之间。与陆机同时的周嵩“精于事佛”,石崇“奉佛亦至”,名僧支孝龙与阮瞻、庾敳等“并结知音之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佛教语言渗透于文学创作,并进而影响诗学思想是完全可能的。由蜀入洛的李密所作《赐饯东堂诏令赋诗》“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就是典型的佛教用语。而且由“人亦有言”句看,“有因有缘”的佛教用语已经传播相当普遍,成为习见的口语。而且钱锺书《管锥编》一三八则解陆云“文适多,体便不清”曰:“适,倘若也。”又补注曰:“晋人译佛经中常用‘适’,义与陆云同。”[22]1862也可说明佛教与文人用语的互相渗透。如前所论,“缘情”之类的意义表述虽在汉代前已经出现,但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词语,却不见载于汉前典籍,至魏晋而大行,如袁准《袁子正书》、潘岳《寡妇赋》、徐邈《答曹述初问》、徐广《答刘镇之问》等都用过“缘情”一语,可见已经成为魏晋以来的流行之语。其后法琳《对傅奕废佛僧表》、慧琳《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萧统《同泰僧正讲诗》等,直接将“缘情”一语引入佛理阐释之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缘情”与佛教有密切的联系。西晋诗风以“绮靡”为主要审美倾向。《文心雕龙明诗》曰:“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又《时序》曰:“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揺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摽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是西晋抒情诗歌词采、音韵的基本特点,从而构成了西晋诗歌“轻绮”的美学风格。钟嵘《诗品》亦称陆机诗歌“才高辞赡,举体华美”。可见,从理论上抽象出“缘情绮靡”的诗学思想,既是陆机对西晋诗风的概括,也是自己创作实践的总结。然而,追求“绮靡”的审美倾向,亦非止于西晋文士,早期佛经之翻译、传播亦有“绮靡”的倾向。天竺佛经语言藻丽,音韵流靡,早期译者颇以“失其藻蔚”为憾。鸠摩罗什《西方辞体论》曰:“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23]2405重文制、音韵,求辞藻葱蔚是天竺文体的重要特征。译梵为汉,往往只能译其大意,而文体殊隔。因此,“尚质”抑或“尚文”成为困扰着早期佛经翻译家的重要问题。然而,追求“尚文”却成为早期佛经翻译的主流倾向。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曰:“(支)越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24]270支谶授学于支亮,支亮授学于支谦(又名越),支谦授学于康僧会。支谦译经“尚文”,“颇从文丽”,道安甚至引庄子之喻,批评其译文是“斫凿之巧者也窍成而混沌终矣”[24]290。康僧会的译经风格必然受支谦影响。《高僧传康僧会传》载:“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一代模式。又注《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经,并制经序,辞趣雅便,义旨微密,并见于世。”[20]18也就是说,僧会译经妙得天竺文体,辞义允正,且又传梵呗之声,音韵“清靡哀亮”,竟成“一代模式”,可见影响之大。而其注经所作的序论,也辞趣雅洁,意旨繁富。从支谦到康僧会实际上逐渐形成了“绮靡”的译经风格。这也必然影响东吴文风,陆机浸染其中,亦必受其影响。只是史料阙如,难以确考而已。无论是梵汉文体殊隔,还是在翻译中有“尚质”“尚文”之别,但是佛经本身的特点必然对佛经翻译有潜在的规定性。早期佛教并非仅仅以只言片语开启人心,反复申说,举譬设喻,也是其特点之一。加之梵呗的清靡哀亮,也使佛经本身呈现出繁缛“绮靡”的风格。支谶所译的《道行般若经》这种特点尤为明显,如卷五《分别品》:“说诸法空,是亦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诸法空,诸法无有想,诸法无有处,诸法无有识,诸法无所从生。诸法定,诸法如梦,诸法如一,诸法如幻,诸法无有边,诸法无有是,皆等无有去异。”[25]631以无来、无去、无想、无识、无处、无生,周遍一切,无有差别,阐释“自性空”不生不灭的特点,形成了意旨繁缛的特点。而且以如梦、如一、如幻为喻,运用一系列排比、对偶的修辞句式,也形成了绮靡的语体风格。佛经中还常以绮丽铺陈的笔触描写佛国的境界,如上书卷九《萨陀波伦菩萨品》所描绘之犍陀越国:“皆以七宝作城,其城七重,其间皆有七宝琦树;城上皆有七宝,罗縠缇缦,以复城上;其间皆有七宝交露垂铃。四城门外,皆有戏庐。绕城有七重池水;水中有杂种优钵莲华、拘文罗华、不那利华、须犍提华、末愿犍提华,皆水池中生。犍陀越国诸菩萨,常共恭敬昙无竭,为国中央施高座,随次转下施座,中有黄金座、白银座、琉璃座、水精座;座皆有杂色文绣婉,座间皆散杂种香花,座上皆施杂宝交露之盖;中外周匝,皆烧名香。”写城上七宝琦树、罗縠缇缦、交露垂铃已是目不暇接;池中种种莲花也是风光满眼;佛座之华贵精美、文绣之婉流光、奇花之香艳杂陈、珠宝之交露覆盖,再加之香雾缭绕,弥漫周遭,更使人目乱心驰。铺陈描写,色彩缤纷,香罗绮泽。且多以短句为主,或连用平声,或连用仄调,极尽“绮靡”。若比较西晋酬赠应制之诗,其格局、笔法都投映着佛教的影响。西晋诗风的意旨繁缛,并非仅仅受赋体影响,也有佛教影响的元素;风格绮靡,不惟是西晋诗风的特点,也是天竺佛经的特点。许里和指出,系统地翻译佛典,“标志着一种文学活动形式的开始,而从整体上看来,这项活动必定被视为中国文化最具影响的成就之一”[26]46。一个时代的诗学是多元文化交融叠合的产物,如果仅仅从中国诗学发展史上追寻陆机诗学范畴的生成,而忽略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显然是以线性的思维替代了开放的思维,其结果必然无法揭示诗学生成的文化多元性。诚然,西晋时期,佛教思想并不像东晋那样深入文人的心底,但是佛教文化的语言、风格,却成为影响西晋文人的重要因素。这既符合对外来文化接受的一般规律,也可以从西晋诗学中寻出一些踪影。李密的诗、“缘情绮靡”诗学范畴的产生,都与佛教有丝丝缕缕的联系。
四、“缘情绮靡”的诗学史意义
诗词歌赋范文6
琴棋书画对应诗词歌赋,在古代,弹琴(多指弹奏古琴)、弈棋(大多指中国象棋和围棋)、书法、绘画是文人骚客(包括一些名门闺秀)修身所必须掌握的技能,故合称琴棋书画,即“文人四友”。今常表示个人的文化素养。
诗词歌赋是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学的概称,虽然如此,这一称谓几乎可说是业已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学的大成。其中,诗词在人们的通常思维中是有着严格格律(主要指平仄、用韵和对偶等严格要求)的两种诗歌体式(古体诗的平仄略微放宽些),是不能乱行押韵和误用平仄的;究其实,所谓的赋,其实也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对仗规则和平仄要求,只是当今一些习作者因不知而写着罢了。而这,无疑是对传统文化的严重摧残。但这诗词歌赋的创作还是有其自身的独特要求和写作技巧的,人们一旦掌握了,写好它们应该也不是什么太难之事。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