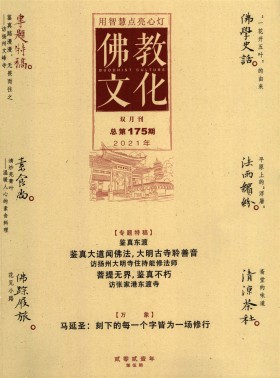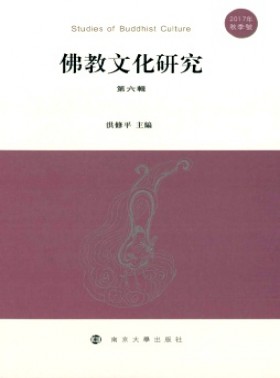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佛教对古代文学的作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自宋代以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也认为“唐人或妒询名重,遂牵合以成此传”[1],借小说以污蔑。但这种说法仅是猜测,并无实证。如果仅以欧阳询长相似猿猴这一点就遭受如此恶毒的人身攻击,似乎也显得牵强。从小说故事情节来看,“失妇—寻妻—援救—杀猿—团聚”诸情节,倒是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颇为相似。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在承袭唐传奇《白猿传》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时代特色,不仅渲染了较为鲜明的理学色彩,而且体现出“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与《白猿传》相较,可以明确看出《白猿传》对佛经“罗摩故事”的承衍痕迹,而话本则除了继唐传奇对佛经“罗摩故事”的承袭外,更多反映的是本土的文化色彩。明代瞿佑的《申阳洞记》,则完全是对“猿妖劫妇”本事的有意识的文人再创作,几乎看不到“罗摩故事”的影响了。因此笔者认为“猿妖劫妇”母题应出于中国古代猿猴好淫观念与佛经典籍中《罗摩衍那》故事的结合,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本土文化的层层浸染,佛教的色彩逐渐淡出。 一、《罗摩衍那》在汉译佛经中的痕迹 《罗摩衍那》讲述的是印度远古时代的故事,经过民间伶工艺人的口口相传,最后形成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季羡林先生认为,“《罗摩衍那》的材料至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年”[2],罗摩故事在印度广为流传,形成了庞大的罗摩故事体系,是印度文学中反复书写的题材。罗摩的形象被印度教吸纳到神谱当中,被尊为印度教的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具有很强的降魔能力,在三大神中最受欢迎。印度教诗人杜勒西达斯在《罗摩功行之湖》中极力夸大他的神性,称其全智全能,法力无边,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大神[3]。罗摩成为婆罗门教崇奉和信仰的主神,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经过了婆罗门的加工,成为纳入印度教体系的经典,《罗摩衍那》的故事弥漫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教理当中。佛教在印度兴起之后,不仅承继了婆罗门教的神谱,同时也吸纳了婆罗门教的诸多教义,因此关于罗摩的文学故事也就成了佛教的教义教理。佛教通过水、陆二途传入中国[4],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影响。到西汉时,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即当时的于阗、疏勒、龟兹、乌孙等地,这些地区与印度交往较多,受佛教影响早且深,《隋书•经籍志》记载:“其后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5]汉哀帝时贵霜帝国大月氏三遣使者向中国博士弟子口授佛经[6]。普罗巴特•穆克尔吉(ProbhatMukherji)曾说过“:海外印度文学的历史实际上是印度宗教向外传播的历史”,“纯文学似乎没有传入中国;至少,没有关于这类著作的记录,随着僧侣而到了印度国外的文学是佛教文学。”[7]从史实记载来看,佛教文学《罗摩衍那》的故事也应该随着中国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而传入中国。 初见于《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之“汉明感梦”,言梦金身神人,手持金弓,弓上两箭,张弓射向明帝。帝惊梦,夜不能寝。大臣傅毅启奏,此持弓双箭之神乃“佛”,于是汉明帝“遣使求法”[8]。这条史料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传教者在民众中活动,产生一定影响[9],当时并无书面的汉译佛经,佛经的传播方式仍是口口相传,人们对于佛的形象完全是籍口传而想象出来的。二是,对于这个金身神人的描述与印度教中罗摩一手持弓,身后背箭的形象非常一致。综合这两点,说明在汉明帝时期,《罗摩衍那》的故事已随着佛经的口头传播而在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东晋时期,佛教的讲经活动在社会上极为盛行,罗摩故事体系便随着经师的讲经而广泛传播。譬如三国时吴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第5卷第46个故事就讲的是“罗摩”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罗摩衍那》的后一半,即王与元妃被流放,邪龙劫妃至海中大洲之上,王在巨猕猴的协助下,寻到元妃,并杀死了邪龙,与元妃团聚,回国继承王位。从骨干故事的情节来看,几乎与《罗摩衍那》一样,王就是罗摩,元妃就是悉多,邪龙就是梵文的罗刹。佛教徒利用佛本身故事来宣传教义,因此称“佛告诸比丘:‘时国王者,我身是也。妃者,?夷是。舅者,调达是,天帝释者,弥勒是也。’菩萨法忍度无极行忍辱如是。”[10]第3卷,26佛本生故事在佛教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故事随同佛教流传到东西方各国,通过互相交融渗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丰富了世界各国文学”[11]。 随着佛经翻译的盛行,《罗摩衍那》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广泛。马鸣菩萨造、东晋后秦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经》卷第五说“: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又《婆罗他书》。说阵战死者,命终生天。”[10]第4卷,280-281这里《罗摩延书》即《罗摩衍那》,而《婆罗他书》就是印度古代另一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南朝梁陈时印度三藏法师真谛译的《婆薮?豆法师传》即《世亲菩萨传》说:“法师托迹为狂痴人。往?宾国。恒在大集中听法,而威仪乖失,言笑舛异。有时于集中论毗婆沙义,乃问《罗摩延传》,众人轻之。皆不齿录。”[10]第50卷,,189到了7世纪,“罗摩”故事再次随着唐玄奘翻译的佛经而广泛流传开来。唐玄奘译的《阿毗达摩大毗婆沙》卷第46说:“如《罗摩衍?书》有一万二千颂,唯明二事:一明逻伐?将私多去;二明逻摩将私多还。佛经不尔,若文若义,无量无边。”[10]第27卷,,236这里所说《罗摩衍?书》即《罗摩衍那》,逻伐?即十首罗刹王罗波那,私多即悉多,逻摩即罗摩。它记载了当时佛教徒所知道的《罗摩衍那》的篇幅,只有现行通行本2万4千颂的一半,并且所知中心内容即罗摩和悉多夫妇的离合。唐代在寺庙中的“讲经”既是宗教活动,同时也是社会娱乐活动。大批的俗众涌入寺庙听僧人以讲故事的形式宣扬佛经,又称为“俗讲”,这种大众性的传教活动使得大量佛教故事流行世间。鲁迅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12]佛经中的“罗摩故事”也就通过此途径在社会上广为流传。#p#分页标题#e# 二、《补江总白猿传》中“罗摩故事”的痕迹 中国最早记载“猿猴盗妇”见于西汉易学家焦延寿的《焦氏易林》卷1《坤》之《剥》云:“南山大?,盗我媚妾。怯不敢逐,退而独宿。”可见“猿盗妇人”的故事在西汉昭帝时就已经开始在民间流传。晋张华《博物志》卷3以及干宝《搜神记•?国》也记载了蜀中西南高山??盗取妇人并生子的传说,称“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13]但是志怪小说中“盗妇失妻”的记载,只是对一件传闻或一种现象概括性的记述,也就是说写作者将此当作真事记录,并无有意识地进行创作。所以上述记载中既没有生动的人物形象,亦不见详细的情节。直到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的问世,故事才趋于完整和精致。但从宋代以来,《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实则不然,从情节的构建来看,《补江总白猿传》应该是写作者在中国古而有之的“??盗妇”传说的基础上嫁接汉译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创作出来的,是中印文化碰撞的火花和结晶。 从下列图表来看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六度集经》中的王与元妃离合故事,以及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六度集经》与《罗摩衍那》属于印度的罗摩故事体系,是直接的传承关系,而《补江总白猿传》与两者相比,除了个别细节,骨干情节几乎相同,明显是以印度罗摩故事为底本。最大的差异在于印度的罗摩故事体系中,猴是正义的一方,协助寻妻者;而在唐传奇中则衍变成了劫人妻的邪神,这主要缘于中国自古就有猿猴“好淫”的说法,再加上传入中国的“罗摩故事”中恰又有个猴子,于是就发生了角色的错位,而援救者也就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变成了被白猿所劫的众位妇女。另外两者的结尾也不同,《六度集经》中元妃坚贞不屈,保全操守;而《白猿传》则欧阳纥妻失贞且生一猿子,也正源于此,所以才被冠以诬谤之作。但实际上,“诬蔑说”是从宋代才有的,宋学兴盛,将封建伦理道德奉为“天理”,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为大”。在这种社会思潮之下来看待这篇唐传奇,自然将欧阳纥妻的失贞视为不齿之耻辱。但在唐代社会,开放的社会风气,宽容博大的时代精神只会消弭淡化它的道德性,更多是注重其传奇性和娱乐性。这也是唐传奇在唐代兴盛的一个原因。另外欧阳纥寻妻、杀猿以及救妻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对欧阳纥的赞许和同情,并未见揶揄嘲讽之意。《补江总白猿传》结尾又写到“:后纥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出,知名于时。”[14] 完全是赞扬歆羡的口吻。因此结尾的处理应该体现出的是异质文化不同的时代精神。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有些细节也展示出不同民族的特色。从寻救线索来看,《补江总白猿传》明显借鉴了《罗摩衍那》的故事原型,脚上佩戴饰品是印度妇女的装扮,中国古代妇女并无此习俗,因此作者将寻妻的线索改为一只绣鞋。《六度集经》中描述邪龙“化为梵志,讹叉手箕坐,垂首静思,有似道士惟禅定时”。在佛典中,梵志指佛教以外的出家修道人,即婆罗门。《翻译名义集•外道》中说:“婆罗门……其人种类,自云从梵天口生,四姓中胜,独取梵名,惟五天竺有,余国即无。诸经中梵志即同此名。”[15]又据《旧唐书•西戎传•天竺》记载“: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惟梵志种姓披白叠以为异。”[16]由此可见,婆罗门教徒穿白衣是印度宗教的风俗。另外《西游记》第9回写泾河龙王化身为白衣秀士,与袁守诚打赌赛[17],显然带有印度教服饰风俗的痕迹。在《补江总白猿传》中描述白猿变化作人形,“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14],这里的“白衣”应是从佛经中的“梵志”折射而来,但“白猿”身上并未体现出佛教的色彩,更多浸染了道教意蕴。《六度集经》是借“罗摩故事”宣传佛教思想,而在《补江总白猿传》中则丝毫不见此种意图,完全是借助“罗摩故事”的骨干情节来构建和填充中国原有的“猿猴盗妇”的传说,带有鲜明的文人化的创作倾向,同时浸染了本土宗教的浓厚气息。首先“,白猿”形象的塑造带有鲜明的道教色彩。中国自古有万物有灵、物老成精的民间信仰。道教吸纳了这种观念,构建了庞杂的神仙体系。白色的毛发是老的特征,故此具有白色皮毛的动物往往容易被认为具有长寿、神奇的特质,古代志怪小说中的白泽、白虎、白狐、白鼍、白鹿、白犬等都是“物老”之神兽或精怪。东晋道士葛洪在《抱朴子•对俗》中曾说“: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18]47 “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善?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18]48“猕猴寿八百岁变为?,?寿五百岁变为?。?寿千岁。”[18]49根据道教的这种逻辑推论,修炼千年的老猿自然也应是通体白毛。《补江总白猿传》中描述白猿:“遍身白毛,长数寸。“”然其状,即??类也”。并自言透露“吾已千岁而无子”,此千岁白猿恰与道教中的神怪思想是一致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白猿传》中“天书”意象,也出于道教的观念。白猿“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天书”在古代小说中经常提及,如张荐《灵怪集•王生》写王生从二野狐手中夺得“黄纸文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19]卷453引3612。《宣室志•林景玄》写墓穴中狐翁“手执一轴书”,其书“点画甚异,有似梵书而非梵字”[19]卷449引3501。《玄怪录•狐颂通天经》写裴仲元因逐兔入大冢,“有狐凭棺读书”,“取书以归,字不可认识”[20]等等。这里的“天书”都是狐修炼法术的秘经。《白猿传》中的“白猿”具有非凡的法术,如盗妇过程神鬼不觉,“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户蔽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等。故此“天书”也应是白猿修炼法术的秘经。#p#分页标题#e# 道教为自神其教,常造作经籍而言神授,藏经之处往往被渲染在深山石室,从而夸饰经籍的神秘性,道教经典的崇拜直接构建了“天书”母题的原型。有学者曾指出:“道教经?派,尽管其散布传播的道经神授传说是为了抬高本教经典地位,以此来自神本教,却给文学中的天书母题提供了一个宗教文化中介”[21]。《补江总白猿传》中的“白猿天书”对于后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诸如冯梦龙《平妖传》中盗取如意册的白猿公,苏庵主人《归莲梦》里那本“尽是天文地理、阴阳变化、战阵用兵之术”的《石室相传秘本阴符白猿经》,钮?《觚剩》续编卷3中以3卷天书谢恩的猿仙等等叙事模式,都应滥觞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白猿的法术与《六度集经》中“邪龙”的法术相比较“,幻化人形”是两种宗教文化中不约而同的宗教思维的结果,而邪龙的“布云雷兴风雨”则是典型的印度佛教中的法术,由于以法术为主要内容的“天书”母题是本土宗教中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白猿传》的作者自然以“法术”来丰富“传奇”的内容,使得故事情节更具有神奇玄幻性。 三、《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变形和衍化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骨干故事情节明显脱胎于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但两者相比较,《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只是在故事的框架上继续承袭唐传奇,而诸多细节已难以辨析佛经“罗摩故事”体系的痕迹,经过本土化的融合与改造,“罗摩故事”已被彻底中国化,与唐传奇相比则更加世俗化。盗妇者仍然是“白猿精”,“千年成器,变化难测”且“神通广大,变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魈,管领诸山猛兽,兴妖作法,摄偷可意佳人,啸月吟风,醉饮非凡美酒,与天地齐休,日月同长。”[22]似乎与唐传奇的“白猿”同源,但却多了一个名号“齐天大圣”。话本里的“白猿”显然已经具备了“孙悟空”的雏形。历来关于孙悟空的来历就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就是沿袭《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两者相比较,故事本事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23]。另外在元末明初的神魔小说《平妖传》第一回中在描述白猿公的赞词中有一句“神通却是降龙祖,变化平欺弼马温”,返观《六度集经》,神猴哈奴曼协助罗摩降服邪龙,不正是渊源所在吗?话本中又提到“齐天大圣”住在“申阳洞”,号“白申公”。葛洪曾在《抱朴子内篇》中曰:“申日称人君者,猴也。”[18]304而元末明初的瞿佑在《剪灯新话》中有《申阳洞记》载,李生询问白衣鼠精“洞名申阳,其义安在?”曰“:猴乃申属,故假之以美名”[24]。可见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白猿”已经混杂交叠了中印两国不同的文化原型,再加上当下社会文化思想的浸染,愈发远离了印度罗摩故事体系中的原型。如果说《补江总白猿传》中的“白猿”身上还有些许“邪龙”的影子的话,在《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的“齐天大圣”则已是世俗化、圆融化、本土化的形象。宋元时代,儒释道三教经过长期的斗争,至此调和乃至三教圆融,三教均提出了教虽三分,道乃为一的思想,认为“圣人无二心,佛则云明心见性,儒则云正心诚意,道则云澄其心则神自清,语殊而心同。是三教之道,一心而已。”[25]在一派三教圆融的社会气氛下,道教与佛教不仅交际往来,而且在教义教理上也相互融通,亦佛亦道的教徒,或者是佛道俱信的民众在宋元时期极为普遍。反映在话本中,陈巡检“一心向善,常好斋供僧道”,齐天大圣是具有神通的猿妖,带有明显的道教邪神的意味,但同时又是出没于红莲寺听说禅机,讲其佛法的佛门弟子;协助陈巡检救援妻子的又是佛道联手,体现出三教的同心合德。 但在三教圆融的背后,又潜伏着佛道之争的暗流。因此话本也就显得情节曲折波澜,与唐传奇相比较显得更有故事性。佛道之争在三教圆融的大洪流之下,只能以隐蔽的形式暗涌。作为都需要依赖儒家正统官学而生存的两个并存的宗教,这种明争暗斗是不可能完全消解的,这在元明清的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同样《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中也有抑佛扬道的倾向,以渲染道教为主调。 首先,话本中增添了一位大罗仙界的紫阳真人。道教所说的三十六天当中的三清天(太清、上清、玉清),为高层修证古仙元始天尊、道德天尊及灵宝天尊所居之圣境。而于三清天之上更有大罗天,此为道教修仙的最高境界,炼就不死神仙之体,道教称为“大罗金仙”。紫阳真人法力无边,能预知如春将有千日之灾,能召神役鬼,降妖除怪。盗劫人妻的“白猿精”最终被他收伏押至酆都天牢。这个紫阳真君的原型极有可能就是金丹道南宗创始人张伯端,张伯端号紫阳,被尊为紫阳真人。《悟真篇序》中:“幼年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26]。据籍记载,张伯端任府吏数十年,一日看破红尘,纵火烧毁案牍上的文书,触犯了大宋“火焚文书律”,因此被流放岭南充病服役,“坐累谪岭南兵籍”。当时岭南属野蛮荒僻之地,张伯端此时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者,大概由于年高,服刑不长即被获释,张伯端获释后在岭南一带云游传道法。南宋社会上,宗承张伯端一系内丹学说者并无教团组织,其成员不限于职业道士。除了文人士大夫,内丹修炼也及于普通老百姓,“有市井百工之流,如缝纫为业的石泰、箍桶盘栊为业的陈楠、涤器为业的郭上灶等劳动人民,乃至乞儿、妓女、和尚,无所不有,可谓遍于社会各阶层”[27]。可见内丹影响之大。因此张伯端受到民间的崇奉敬重而留下诸多传说,人们口耳相传,说话人随机编撰为话本的素材是极有可能的事情。而且话本中写道:陈巡检在赴任之前设斋吩咐厨下“不问云游全真道人,都要斋他,不得有缺”,对全真道的强调似乎也有影射之嫌。宋元道教的重要内容是内丹,内丹的流传,已经越过纯粹的宗教界限,为社会各阶层接受,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都有感兴趣者。《春渚纪闻》载:“丹灶之事,士大夫与山林学道之人,喜于谈访者,十盖七八也。”[28]因此作为内丹南宗创始人的张伯端自然也就成了小说中的主要素材。#p#分页标题#e# 其次,话本中通过佛道的同时出场,在设计收伏“白猿精”的情节中,隐含了抑佛扬道的意趣。“白猿精”虽然修炼佛法,但佛法却不能以精妙奥义使其皈依顺服,倒是道教的法术无边,紫阳真人招徕两员勇猛的“红?兜巾天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将“白猿精”一条铁索押至眼前,并送往酆都天牢。相形之下,佛教显得苍白无力,似乎除了空谈只能束手无策。话本在凸显道教法术方面也是不遗余力。除了紫阳真人的法术之外,还增设了道教的扶乩神降的描写,“杨殿?,请仙下笔,吉凶有准,祸福无差”,这个细节作为伏笔成了杨巡检寻妻的一条主要线索。另外,话本中还具有较为浓厚的理学色彩,主要体现在张如春面对“白猿精”淫威的态度上。细述话本,对如春的忠贞的赞誉之辞散布全篇,既有如春的自表,如“:决不依随,只求快死,以表我贞洁。古云:‘烈女不更二夫。’奴今宁死而不受辱!”“我不似你这等淫贱,贪生受辱,枉为人在世,泼贱之女!”也有散文间的韵词:“宁可洞中挑水苦,不作贪淫下贱女”;“千日逢灾厄,佳人意自坚。”“悲欢离合千般苦,烈女真心万古传”;还有第三者的态度:禅寺长老言:“你孺人性贞烈,不肯依随”,长老劝“白猿精”?:“有一如春娘子,在洞三年。他是贞烈之妇”。话本中对贞洁操守的强调明显甚于唐传奇,但与《罗摩衍那》以及《六度集经》却有惊人的相似,这显然缘于佛教伦理以及宋元理学的共通性。 对比《补江总白猿传》和《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话本叙述事件的能力越来越强,除了原有的骨干故事情节之外,又增添了若干节外生枝的事件,使得篇幅比唐传奇增长扩展。增添的情节有:1.道童奉紫阳真人法旨,护送夫妇故作刁难;2.齐天大圣幻化客店诱骗夫妇;3.如春怒斥金莲,谨守贞操;4.陈巡检扶乩卜吉凶;5.陈巡检沙角镇剿匪寇;6.陈巡检投宿红莲寺求助,禅师劝说申阳公;7.紫阳真人降妖伏魔。叙事能力的增强,一是受表达形式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恐怕应该是受佛教文化以及讲经这种文艺形式的影响。这些情节的增设,使僧道成为扭转故事的关键人物,对于宗教因缘和合、因果报应的辅教弘法,惩恶扬善的社会功效等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集烟粉、神怪、因果等因素,本身也具有道教文学的特质,寓理教于娱乐,以“说话”的方式在勾栏瓦舍中浸染人心。虽然与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原型已相去甚远,但功能上的一致性(劝教)仍能折射出对此故事母题原型的摄取与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