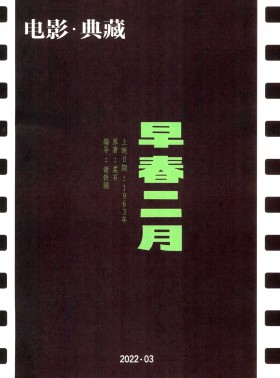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电影中体现的生命哲学,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生命哲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于德国、法国,是以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借助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来冲击理性主义美学观念的一种思潮。生命哲学提出两个口号,一是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即生命的非理性;一是生存。生命哲学思考的问题不再是人类通过怎样的逻辑方式去认识世界,而是人类在一种怎样的状态下去把握世界。它不是要对认识问题进行逻辑证明,而是力图澄清尘世经验的结构,重视人在认识世界时的主体性与自我经验。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西美尔把一种不能继续描绘的有关存在、力量和方向的感觉,即内在性称为“生命”。世界的本源是生命,生命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永恒的冲动。西美尔用两个公式表达了生命的概念———“更多的生命”(MehrLeben)和“比生命更多”(MehralsLeben)。“更多的生命”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长,即生命在一定阶段形成的表现形式。“比生命更多”指的是生命在精神阶段上所达到的高级实现。想要获得“更多的生命”的愿望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动力,这样我们也就获得了“比生命更多”的意义。生命就是意义,生命的本质是不断的自我超越。[5]死亡,从一开始就同生命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生命的必经过程,死亡是连续不断的生命过程正在培养的因素。虽然死亡一开始就寓于生命之中,但“就连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成是生命的自我超越”。[5]因此死亡也是生命的自我超越,是生的创造者。也就是说,生命一直在产生意义,而意义的产生来自于生命的本质———自我超越。
《时时刻刻》是一部意识流电影,它通过不断切换的镜头,反复出现的流水,人物不停地思考、自语和面对死亡的决绝和迷惘,把剧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状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生命哲学亦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个体生命存在”。因此,对人的内心和存在感的共同关注就是生命哲学与电影《时时刻刻》的契合点。
二、《时时刻刻》中的死亡
《时时刻刻》的故事叙述笼罩在难以言说的不安与挣扎中,给人以强烈的压迫感和窒息感,更甚的是,全篇似乎充满了死亡的气息,给人以“眷顾死神”的感觉。大多数女性题材电影总是娓娓地向观众讲述一个温馨的故事,而《时时刻刻》却以冷静得近乎残酷的方式带领观众面对绝望与死亡。故事中伍尔夫和理查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劳拉曾试图自杀;克拉莉莎则目睹了理查德的死亡。根据影片中人物对生命结束方式的理解与选择,可将其分为亲历死亡、逃避死亡和直面死亡。
亲历死亡的代表人物是伍尔夫和理查德,他们都选择了一种非正常的方式告别世界———自杀。在生命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一些行将死亡之人,死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注定的命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亡的时刻是未知的,就像“漂浮在他们生命之上的令人不快的预言,然而他们也只有在实现这一预言的瞬间才同生命有某种关系,这就好比有朝一日将会弑父的预言漂浮在俄狄浦斯生命之上一样”。[6]大多数人会平淡安稳地度过一生,但对伍尔夫和理查德来说,生命伴随着自身的发展,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使他们丧失希望,因此他们选择了自己可以主动担当的死亡。伍尔夫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这位伟大的意识流作家一生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最终忍受不了一次又一次精神崩溃的打击,在1941年溺水自尽。影片的开头和结尾为我们重现了这一场景:伍尔夫像平日散步一样走出家门,来到河边,把口袋里塞满石头,然后一脸平静地向河中心走去。在她沉入河底后,镜头给了她的手和脚一系列的特写。她似乎是很舒适地伸展开四肢,头发飘扬,任由河水带着她流动。此时死亡对于她来说,仿佛不是痛苦而是享受。与伍尔夫优雅、诗意的死亡方式相比,处于现代社会的理查德生命的结束更加决绝与直接。他在克拉莉莎接他参加晚会的下午,深情向她告白后,飞身从窗台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
西美尔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创造者。个体通过对于生命的某种适应,才能在每一瞬间保持自己。这种适应一旦失灵,就意味着死亡,正如任何一个自动的或任意的运动都可能意味着对于生命的渴望一样,这种适应也可以说是逃避死亡。劳拉·布朗是影片中逃避死亡的典型。在艰难的一天将近结束的时候,劳拉把孩子交给邻居照顾,自己驱车来到一家旅馆,准备服下安眠药结束生命,但她的内心却不停地挣扎,身为一个即将临产的母亲,她腹中的胎儿也使她难以做下最后的决定。于是猛然间,她从噩梦中惊醒,抚摸着隆起的腹部,失声痛哭。最终,她在一瞬间决定生下孩子后,离开家庭,背负抛夫弃子的骂名,继续生命。
克拉莉莎是主要角色中唯一没有产生死亡行为甚至死亡动机的人物,但她的生活被一种似乎连爱都难以弥补的绝望和不安充斥着。她特立独行,与相恋十多年的同性女友住在一起,却又照顾着多年前的异性恋人理查德。她喜欢举办晚会,喜欢大事小事都事必躬亲。她整天都忙忙碌碌的,似乎只有机械般地忙碌才能让她感到安慰与满足。生活的目的在她看来也是简单的“为彼此而活”,然而她却眼睁睁地看到了理查德死去。活着的人对于死亡的感受应该是更微妙和震撼的,直面死亡使得她也开始重新思考生活与生命。
三、死亡原因
影片中主要人物的生活与生命似乎缺乏阳光,一直是乌云笼罩。他们的命运被不知不觉地附上了无法摆脱的结局。这种无法摆脱的结局不是来自错综复杂的命运纠葛,也不是来自咄咄逼人的命运转折,而是来自于生命感觉的萎缩,即人物沉重的自我压抑和死亡倾向。影片的三个故事都发生在现代化的20世纪。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物质满足的同时,也使人们的心灵愈加干涸。现代先进的科技和丰富的物质虽然取得了一些令人惊奇的成就和进步,但人们实际上并不幸福,而是缺乏普遍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不安境地,个人的灵魂深处充满了虚无感和难以承受的悲伤。[7]所以我们看到,影片中的人物尽管都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但他们的心底依然寒冷。
1.亲历死亡:弗吉尼亚·伍尔夫———以享受的方式拥有自己。
伍尔夫是一个内心世界斑斓丰富的奇女子。她的作品细腻、动人,充满了诗情画意。作家的创作需要全身心的投入,伍尔夫对写作的投入程度更是到了夸张的地步———她不修边幅,穿着宽大的衣裙,双手插在口袋里,脑子飞快地运转,神经质般地口中念念有词。她就这样全身心地沉浸在自己构设的精神世界里,在这里,她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拘禁和约束。但同时她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烦扰。仆人抱怨她只专心写作而没有家庭管理的指示,医生告知她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即使亲密的姐姐凡妮莎也要求她按时看医生,在宁静的乡下好好疗养。凡妮莎说,伍尔夫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她有两个生活,一个是她在过的生活,一个是她的写作。可这真的是幸运吗?这样一个专注、有才情的女子,却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庸俗与无奈,她根本找不到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对接点。#p#分页标题#e#
因为有精神病史,伍尔夫一家搬到了宁静的郊区,她的一切行动都处于丈夫和女仆的监督之下:有没有吃早餐,有没有看医生,甚至连她最热爱的写作都要有丈夫的过问和许可。在和女仆耐莉讨论下午茶的对话中,伍尔夫就间接表达了她对这种被人看管的生活的不满:“我觉得没有什么比去趟伦敦更好的了。”(电影台词)后来,向往伦敦的伍尔夫乘丈夫和仆人不留意之际,悄然离家。在候车的站台上,丈夫找到了她,伍尔夫歇斯底里地爆发了:“我的生活被偷走了,住在一个我不愿意居住的小镇,过着我不愿意过的生活……我想念伦敦,我想念伦敦的生活……我正在这镇上慢慢死去,我独自生活在死亡般寂静的黑暗中……我选择不封闭在这个小镇的宁静祥和里,宁愿面对大都市的动荡。这是我的选择……可如果让我在里士满和死亡之间选择,我选择死亡。”(电影台词)这段濒临崩溃的独白,让我们得以管窥伍尔夫的内心,她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需要有一间可供自己专心写作的房间。丈夫的关怀满足不了她的精神诉求,无微不至的爱已成了囚禁,成了她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负。
西美尔说,只有那个更加完美、更加强大的生命才会选择存心死亡。“浓缩的生命达到最纯净的形式,即最高的生命,必须以死来献祭”。[8]创作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脱节,被囚禁的痛苦,再加上生活不能还她以所期望的样子,所以她失望了,灰心了。在平庸与完美之间,她选择完美。伍尔夫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与色彩,选择了离开。因为此时的生命才是强大的,闪光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伍尔夫向河中心走去的时候是如此的坦然与平静,在水中舒展的身体是那么自然、美丽。她是在放弃一切世俗与不适之后,做出生命的自我超越,以享受的方式拥有自己。
2.亲历死亡:理查德———为了成全别人的爱。
与伍尔夫优雅、诗意的死亡方式相比,理查德生命的结束更加决绝。在这个世界上,“绝望有两种,一是不愿做他自己而绝望,二是要做他自己而绝望”。[9]如果说伍尔夫属于前者,那么理查德无疑属于后者。所谓要做他自己而绝望,是指“一个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生命存在的短暂和必死,同时又意识到世界的虚无和人生无意义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天天走向死亡而又作徒然无意的挣扎时所体验到的最令人焦虑的苦闷和绝望”。[9]理查德小时候被母亲遗弃,这一特殊的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使他一生都摆脱不掉。长大后,理查德成了作家,可他的作品晦涩难懂,受众面很小。更不幸的是,理查德身患艾滋病,生命十分脆弱,随时都可能死去,但就是这不可预知的死亡使他进退两难,痛苦万分。在他看来,他获的诗歌奖更像一个讽刺,是人们因为他生病而发的一个安慰奖,“我获奖就是因为得了艾滋,发了疯还能勇敢面对!”(电影台词)其实他只想做一个笔者,记录下生活中瞬间发生的事,但命运却玩笑似的让他的生活成了一场表演,这让他感到愤懑和无可依靠。这种没有意义的生命消耗着他的体力,也消耗着他对世界的留恋。于是他每天一个人待在封闭的不见阳光的公寓里,回想以前的美好时光,遭受病痛对身体的折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慢慢抽干。
死对于理查德是或早或晚的事。也许早一步离开对他来说更是解脱,而他一直坚持着生活了十年,都是为了克拉莉莎———他曾经深爱的,如今又照顾了他十年的女人。即便有克拉莉莎十年的悉心照顾与陪伴,他依然感受不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他坚持着生活了十年是出于对克拉莉莎的报答,而不是出自内心活下去的渴望。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激动地质问克拉莉莎:“你这样做多久了?多少年了?你自己的生活呢?”(电影台词)最后,理查德坐在窗台上,独白似的向世界和克拉莉莎做最后的告别辞:“达洛威夫人,你必须放我走,也放了你自己……你对我真好,达洛威夫人,我爱你,没有人能像我们一样开心。”(电影台词)然后,他从窗台一跃而下,得到了解脱。理查德的死去并不是辜负了克拉莉莎的辛劳,相反,他对克拉莉莎充满了爱与感激,他觉得对她的回报不能只是十年的勉强活着而已,行尸走肉般地活着对他来说是污浊不堪的。他不喜欢现在的自己,也不想做现在的自己。他希望回报给克拉莉莎的是自己纯净的生命和灵魂。他要用自己的离去给予克拉莉莎更多的时间、自由与未来。他选择从窗台跳下是为了成全克拉莉莎的爱,正是他的以死去担当的爱,以整个生命的付出而给予的爱,才使爱超越了生命,超越了时间,使别人的爱得以成全,也成全了自我,获得了“比生命更多”的意义。
3.逃避死亡:
劳拉·布朗———面对真实自我。劳拉·布朗也许是最难以理解的一个角色。按照现在的观点,她有车有房,家庭和美,生活安逸,应该是最幸福的人,可她苍白的脸,随时都可能流泪的眼睛却暗示出她其实是最无助、最绝望的人。作为一名全职主妇,劳拉在其理应擅长的领域显得无所适从。在邻居基迪眼里“人人都会做蛋糕”,可在她就十分困难;丈夫对她体贴备至,她却不能和他分享内心的哀愁,只能压抑苦楚,强颜欢笑;面对乖巧可爱的儿子,劳拉更是手足无措,单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她甚至会紧张不安,不知道怎样与孩子交流。西美尔认为,一种具有极高的文化意义,同时又完全从女性的天性中自发成长起来的职业就是家务。[7]家政管理是女人的伟大文化成就,是女人理所应当娴熟的技艺。劳拉显然对这种天生的工作力不从心。她热爱读书,喜欢思考,天生是个注定与书为伴的人。现实与天性的矛盾就把她推入了这样一个两难的困境:要么放弃家庭,要么放弃自身。劳拉在两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
下定决心来到旅馆后,劳拉在房间中度过了一天中最自我、最惬意的时光。她可以不受任何打扰地读完《达洛威夫人》,恣意地思考,甚至随时结束在她看来暗淡无光的生命。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在最后的时刻逃避了死亡,选择了两者中的前者———放弃家庭,追求自身。于是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她抛弃了丈夫和孩子,逃离了家庭。逃避死亡是我们的本能。我们的享受、工作、休息以及我们所有其他的,自然观察到的行为方式,都是在本能地或自觉地逃避死亡。“我们使用为了接近死亡而消耗的生命,正是为了逃避死亡”。[6]死亡是我们必须经历的事,在死亡时刻到来之前的逃避则出自我们的本能,就好像“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这些人与航程逆方向而行,当他们往南走时,他们走着的地板却把他们带到了北方”。[6]很难评判劳拉的做法是对还是错,她出于本能地逃避,一方面为她腹中的胎儿创造了生命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寻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尽管她要为此承担世俗意义上的道德的谴责。片末,老年的劳拉再一次出现,她平静地对克拉丽莎说:“如果我说我后悔,那么我会轻松一些,好一些。但后悔有什么意义呢?当你已别无选择……没有人会原谅我,只有死亡。但我选择了生存。”(电影台词)死亡是一瞬间的事,而活着却是一辈子的事。对于劳拉来说,选择逃避死亡、背负一生的不安而活也许并不是灾难,这也是对自己生命的超越,她通过另一种途径得到了“比生命更多”。毕竟她在付出了代价后也找到了真实的自我,面对真实的自我也需要莫大的勇气。#p#分页标题#e#
4.直面死亡:克拉莉莎———走出樊笼后的坦然。
克拉莉莎是主要角色中唯一没有产生死亡动机的人物,但她眼睁睁地目睹了理查德的死,关于死亡的经验会让一时的生命达到自身纯粹的高度。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认为,爱与死有非此不可的关系。爱与死一样,是人的生命伸展到无限,是把生命攫取到伟大的循环中去,是把生命掷入永恒之流。[8]因为在内心深处还爱着○文化艺术研究理查德,克拉莉莎悉心照顾了他十年,忍受着他喜怒无常的情绪,甚至心甘情愿为理查德举办晚会。对于她的付出,理查德并不领情,他揶揄道:“达洛威夫人,你总是举办晚会来掩盖寂寞的气氛。”(电影台词)她无法接受理查德的话和看她的目光,因为这使她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如此平庸———每天都是时间安排、聚会等细节问题。她做了所有琐碎而令人厌烦的事,却觉得不幸福,不被人理解。她爱理查德,把照顾理查德当做生活,甚至生命的全部动力,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了他身上。她的回忆总是停留在十八岁和理查德初识的那个夏日的海滩,并认为那才是她此生最快乐的时光;她为了照顾理查德甚至不懂得考虑同性恋人萨莉和女儿的感受;在她的世界里,理查德永远是第一位。但理查德却出人意料地死去了。只有体味过死,才能懂得真正的爱。理查德的死惊醒了她,劳拉最后的出现点悟了她。她不知不觉中强加给自己的所谓“为彼此而活”的动力早已成了理查德和她自己想逃却逃不出的樊笼。渐渐的,她把自己困在往昔的圈子里,原地打转,承受也越来越重,无形中使生命超出了自己的所能承受,也失去了自我。
最终,理查德的母亲劳拉的出现使克拉莉莎明白了一切,也理解了理查德的选择。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克拉莉莎终于从她的樊笼里走了出来,脸上现出了难得的释然,开始变得坦然与放松。对于无法挽留的人,死亡只是一种离开的方式,这是他们的选择,我们只能面对。无论过程有多么痛苦,我们都必须接受。“我们需要坦然地接受死亡,不赞美它,也不将它混同于某个圆满的终结,而把它看作生命的对等物”。[10]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人能从逝者那里得到领悟,使自己余下的生命无所遗憾。通过理查德的死,克拉莉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也卸下了身上的重负,让自己的生命焕然一新,达到了更加纯粹的高度,获得了“比生命更多”的意义。只有这样,生命的流逝作为过程才能获得某种意义和价值。
四、结语
在影片接近尾声时,伍尔夫与丈夫莱昂那德有这样一段对话,莱昂那德问:“为什么一定有人要死?”“为了对比,”伍尔夫说,“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加懂得珍惜生活。”“那么谁会死?”莱昂那德又问。“诗人,”伍尔夫说,“充满幻想的人会死。”(电影台词)其实,伍尔夫、劳拉、克拉莉莎和理查德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人。维尔海姆·狄尔泰(WilhelmDilthey)认为,诗是解开人的生命之谜的中介,诗通过体验反思生命的意义,可以认识人类的精神世界。诗人总是紧贴生活的体验,用自己的心去捕捉生活的意义。诗人越是受到生活力量的制约,越是竭力想悟彻生活之谜,使自己在人生观的混乱中找到一个稳固的位置。具有艺术气质、诗性气质的人太热爱、太认真,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才会沉湎于自我不满中难以自拔,以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同时,他们也用生命诠释了永恒与不朽。“死亡之所以让生命沉沦,似乎是为了让生命内容的永恒性释放出来”。[6]伍尔夫、理查德、劳拉和克拉莉莎分别以死亡、逃避死亡和直面死亡这样诗意的方式退出了禁锢自己的生活,挥别了生活中的庸俗与无奈,转向了自我和天性,也成就了自己内心最纯净、最美好的诗性情结。
死亡是人一出生就注定了会伴随一生的魔咒。电影《时时刻刻》为我们展示了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位女性短短一天中的经历和内心起伏。虽然影片充满了挣扎、绝望与死亡,但这不是一部宣扬悲观情结的消极影片。在浓重的死亡阴影背后其实蕴藏着巨大的生命气息。[11]片中的人物无论是选择结束生命,还是继续生命,他们的行为都是出于自己的内心,他们或者是为了追求完美的自我,或者是为了爱,或者是为了勇敢地直面人生的种种困境与不平。他们敢于面对死亡和人生,即使是不被理解的死亡和生存。在人生的困顿之中,在对幸福与失落的反思之中,他们学会了如何生活,获得了“比生命更多”的意义,活出了生命的自我超越本色。生命的本质就是自我超越,作为结束的死亡其实也是在自我超越。生长发育并非生命本身,对个体生命存在的鉴别、扬弃、超越才是生命本身。一个人应该坦然地接受迎面而来的每时每刻,无需留恋过去,也不必担心未来,这样的生命或许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自己最真实的生命。“要直面人生,永远直面人生,了解它的真谛,永远地了解,爱它的本质,然后,放弃它。”(电影台词)———这就是生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