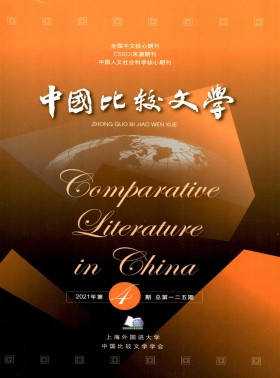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比较文学学科反思,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从克罗齐起,关于比较文学的争论似乎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争论的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围绕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展开的。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恰好是一个学科是否能够存在的关键因素。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发出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气数已尽”的谶语,并为比较文学开出了一剂药方:“从现在起我们应当将翻译研究看作是一级学科,其中含有比较文学,后者是一个有价值的但却是从属的领域。”[1](P161)2004年,作为ACLA新的学科现状和未来发展报告起草人的苏源熙,也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认为“像比较文学这样一个由例证(及例证引取理论)构成的学科,很难说有学术上的独立性”。[2](P12)同年,斯皮瓦克干脆宣布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已经死亡。2006年,在斯皮瓦克的推动下,巴斯奈特又对自己开出的药方进行了否定,直接宣称:“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3](P6)巴斯奈特等人与比较文学的“较劲”,再次激起了人们讨伐的冲动。在反对者看来,巴斯奈特等人简直是在睁眼说瞎话,君不见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多么庞大、人才培养多么富有成效、学术成果多么令人瞩目。但是,反对者似乎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巴斯奈特等人是在何种层面上认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他们并不是没有看见比较文学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反认为“过去的30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展”,[3](P6)也看到了“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确有其繁荣的一面,数十个国家设有分会,相关的杂志、学术会议、研究生项目,以及各种学术组织的繁荣景象证明,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坚实的研究领域而存在”。[3](P4)同时,他们也并没有否认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而是认为比较文学“是一个有价值的领域”。他们否认的只是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如果避开这一切入点,任何批评都是无力的。对待比较文学,应该理性地反思它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存在。首先要说明的是,比较文学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那种认为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观念,其实是对中国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误解,人们对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的合理性的追问,是假定在这种误解成立的基础上的。“一个学科能不能存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同类其他学科的特殊品格,换言之,它必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4](P56)这可以说是我们对学科理解的共识。比较文学是否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呢?一般认为,它作为学科存在的学理依据,不是“比较”而是“跨越”,即它的特定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现象。这可以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吗?在此,我们得分析一下我国的学科划分。根据1997年国务院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文学分有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而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分有“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11个二级学科。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如果我们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解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话,比较文学就是与其他学科并列的二级学科。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因素,所以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如果涉及到了跨越性的文学因素的话,其实就是僭越了学科界限,在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做的事情。但正如苏源熙的报告所说:“‘文学研究中那些指向多元文化、全球化和跨学科课程的进步倾向本质上已经是比较性的了’,那些被认定为搞比较文学的人要加入上述潮流是很方便的。”[2](P21)比如研究韩愈,怎么可能不研究他与佛教的关系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然要涉及到外来影响。研究英国文学,也不可能不涉及到与基督教的关系。如此一来,其他学科的相关人员、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等都应该归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这可能就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令人瞩目”的原因。
如果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是合法的,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归顺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之中,其研究就是不合法的。但到底是谁僭越谁呢?事实上是比较文学僭越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化时代和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的今天,研究一旦走向深入,任何学科都有可能“跨界”。比如研究中国的文体学,如果只是专注于中国文学中的文体演变与发展,而不关注它的外来因素以及它在其他国家的流传与演变,更不在世界文学的文体中观照的话,很难说这一研究是深入的。再比如研究《西游记》,如果不研究它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很难说这一研究是完整的。所以,跨越性本身就是各个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是什么独立的学科。将比较文学视为学科存在,不仅限制了其他学科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自身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旷日持久的质疑,也会因其自身的悖论而尴尬。比如,既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比较文学学科,而比较文学是研究跨越性文学因素的,为什么要与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并列呢?这种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研究与它跨越的任何一边都是并列的,这显然不符合逻辑。还有,既然比较文学是个学科,为什么不叫比较文学,而要与“世界文学”连在一起?它们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呢?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还有,为什么不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呢?假如认可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将其放在外国语言文学之下,与“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等并列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是否合理呢?这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与同样的质疑。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存在,从其研究对象看,既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因为它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内容完全可以分解在其他学科之中,由其他学科来承担。就像有论者说的:“如果这个题目非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也能写出来的话,那何必要我们读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来写呢?既然我们来写,那么,要么是这个题目明显属于比较文学范畴,要么这个题目的写法为比较文学所独有。”[5](P12)#p#分页标题#e#
问题是除了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论证的题目外,比较文学所研究的课题,又有哪个不能分解到其他学科呢?比如钱钟书,尽管其《谈艺录》、《管锥篇》、《七缀集》被公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论著,但他本人却很不认同“比较文学家”的身份,他有兴趣的是具体文艺鉴赏与批评。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足以构成学科存在的理由,是否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以构成它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呢?如果顾名思义的话,“比较”应该是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即使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像克罗齐、约翰•迪尼等人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从方法论意义而言的,也不具有特殊性,因为“对一切研究领域来说,比较方法都是普遍的”。[6](P143)更何况,这一理解一再被比较文学界所否定。因为承认这一观点,其实就等于认同了比较文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们一再辩解说,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属于本体论而不属于方法论,比较不是它的本质特征,“跨越”才是它的本质特征,它是通过对跨越性的文学现象研究达到汇通的。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比较文学独特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有人从认识论角度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分为实证与审美两种,认为前者坚持从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探讨文学间的影响和事实联系,主要是指影响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后者重视的是审美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关系的考证,主要是在指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文学确实使用这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专用的,而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更多的人将比较文学的研究类型等同于研究方法,即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是影响研究法、平行研究法、阐发研究法,以及接受研究法等。
研究方法与研究类型(或研究对象)当然有密切联系,但如王向远所说,这种混淆会“使研究方法自身的‘方法’特征不突出,‘方法论’色彩不浓,会削弱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上的指导意义”。[7](P14)在对已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的基础上,他认为比较文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比较”。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弹克罗齐的老调,而实质上,他所说的“比较”是指“跨越”。相比较而言,还是乐黛云等人所说的“文学对话意识”,[8](P78)可能更能体现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独特性,但也是建立在“跨越”基础上的。假如不是指“跨越”的话,它们就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本身就属于影响研究法。研究李白与杜甫,本身就属于平行研究法。也就是说,他们将比较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跨界视野”,也同时理解为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研究方法。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看是可以的,因为它比其他论者所总结的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更有说服力,其他研究方法只是就某一研究类型而言的,并不能“普遍适用于比较文学的一切研究对象及研究课题”。但问题是,比较文学研究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研究视野尽管是有价值与意义的,也不能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依据。从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看,学科主要是以研究对象划分的,而不是研究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上有什么特殊性呢?从这个意义上看,尽管巴斯奈特与克罗齐都认为比较文学不能作为一个学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中的“比较”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整体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并非没有道理。不可否认,国外众多大学都设有比较文学系,开设比较文学课,培养各层次的学生,但这些与学科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尽管也有将比较文学当作学科看待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理的、牢靠的,否则,就不会有争议。
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将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看待,那种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解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做法,其实是个误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原来的“世界文学”学科发展而来,而由于“世界文学”往往被人理解为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者说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所以人们将专门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文学排斥在外之后,又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外国文学”。我们先说后一种误解,作为中文学科之一的“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如吴元迈所说:“这两个概念(指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具有实质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对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所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学意识。外国文学是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而言的,而世界文学则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而言的,即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而言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如有人所声称的文化或文学的全球化。在这一意义上,把外国文学改为世界文学,表面上是名称的变化,实际上是加入了比较意识,引进了新的观念。”[9](P5)这种误解导致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用汉语介绍“外国文学”?事实上,在中文学科之下的“世界文学”学科,其宗旨除了解世界文学知识、开阔视野、进行文化交流以及审美鉴赏外,更在于总结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融化新知,突破自我,使中国文学的评价和研究及其定性和定位有世界文学的参照。所以,“世界文学”观照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民族文学,而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学;不是各民族文学量的相加,而是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
在观照的方法上,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国各民族的文学,而是“站在超越中外文学的立场”上,以世界眼光与国际视野,在互为参照中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不只是限于对文学发展基本事实的陈述与评价,而是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总结出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所以,它所把握到的不只是一些文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而是由文学与文学、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所产生的“第三者”———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以这种世界文学的总的进程及其本质作为中国文学的参照系,使中国文学在对他者的认知之中获得自我认知之道,获得自我突破。尽管“世界文学”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为基础,但它关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史”,而是世界文学共同的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这种发展规律以及文学间性并不是把握了文学史知识就能得到的,需要比较、分析、总结,所以“世界文学”是对世界各民族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一种文学研究。人们对“世界文学”的误解与这一名称本身有关,如果用“总体文学”的概念,则能更清晰地概括这一学科的性质。尽管“总体文学”是一个有争议,①缺乏明确解释与定义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从国内外学者对它的阐释看,有几点是可以明确的。一是“总体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多民族文学所共有的事实,或者说是以多民族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梵•第根就认为,“凡同时地属于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总体文学的领域之中。”[10](P178)具体研究的是“超越民族界限(至少三种以上)的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的研究”。二是它的研究方法是整体研究,当初梵•第根、韦勒克等人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的文学史”,是为了编写“一部综合的文学史,一部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学史”。他们借用“总体文学”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把世界各国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并且不考虑各民族语言上的差别,去探讨文学的发生与发展。”[11](P44-45)他们认为“总体文学”的宗旨就是编写“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他们之所以不用“国际文学史”或者“全球文学史”,就是考虑到人们对这名称的误解,而“总体文学”的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p#分页标题#e#
事实上,在欧洲一些大学,“总体文学”就是指对非国别/民族文学的整体探讨。三是它的性质是文学研究,“总体文学”不是民族文学的总和,也不是文学史的总和,而是对文学史的研究。梵•第根明确指出:“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一般’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10](P177)梵•第根将美学与心理学凸显出来,强调它的理论性,有意淡化其文学史性质。由于“总体文学”凸显理论研究,所以被人误认为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事实上,韦勒克说它“原来是指诗学或文学理论和文学原则的”,后来被梵•第根借来指“国际文学史”,而并没有说它就是诗学或文学理论。尽管二者都是从古往今来的文学现象中找出文学的本质和规律,揭示文学的不同形态与特点,但“总体文学”是以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而文学理论的重点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11](P31)“总体文学”强调比较的视野与国际眼光,强调比较视域及其汇通,强调跨越性的“文学对话”。如梵•第根所说:“站在一个相当宽广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10](P178)所以它与比较文学联系在了一起。梵•第根当初借用这一概念,就包含着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意思———“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11](P44)国外一些大学就是将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联系在一起的,如新索邦大学的课程中就有“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课程。但它又不同于比较文学,梵•第根就说:“一般文学(总体文学)是与各本国文学(国别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10](P177)这种不同并不在于他所说的两种还是两种以上的超越性关系,而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对多民族文学所共有事实进行的整体研究,而比较文学并没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但要进行“总体文学”研究,就必须要有比较的视野,或者说,通过比较文学之途走向“总体文学”。
雷马克对民族文学、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关系,曾经以围墙形象地进行过比喻,他说:“民族文学是在墙内研究文学,比较文学跨过墙去,而总体文学则高于围墙之上。”[12](P12)我国的学科设置之所以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放在一起,包含着老一辈学者们的良苦用心。它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是一个学科,而是意味着要达到“世界文学”的目的,必须要有“文学对话”意识和“跨界视野”,通过比较文学之途走向“世界文学”。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有过论述,除前面提到的吴元迈所说的之外,钱钟书还指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的基本规律,所以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惟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12](P92)杨周翰也指出:“比较文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不同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一些普遍的文学理论问题,……这是一国文学内部比较研究所无法达到的。这也就是法国人所说的用比较的结果来充实他们所谓的‘总体文学’。”[13](P3)所谓通过比较文学之途,也就是巴斯奈特所说的,将比较文学整体看作一种具有“跨界视域”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这么理解的话,那么比较文学就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具有“跨界视野”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方法的提法容易与人文科学中的其他比较方法混淆,没有体现它的“跨界视野”的话,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种视域、视角、姿态、思路、思维,或者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发展趋势。
它可以在学科层面之外的任何层面上存在,比如可以是一门课程、一个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可以通过设置系、专业的形式来实现,培养本科层次的学生),也可以是一个研究领域、一个研究主题,还可以作为各二级学科之下的研究方向(培养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可以作为研究机构而存在,不同学科的学者带着自己学科的跨界研究课题在该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对于其他学科而言,这样一种“跨界视野”不一定是必须的,要视情况而定。而对于“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学科(如果它是一个学科的话)而言,它是必须的,因为其研究本身就意味着“跨界视野”研究。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不会削弱比较文学的研究,相反会使比较文学走向更加繁荣,达到一种真正的“跨界”,也可以使其他学科的研究走向深入。比较文学遇到的外在挑战、自身的悖论,以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到底是一个学科还是两个学科,中文学科之下为什么要设置“世界文学”学科等一切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至于现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完全可以用“世界文学”学科代替,为防止人们误解,改为“总体文学”则是上上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