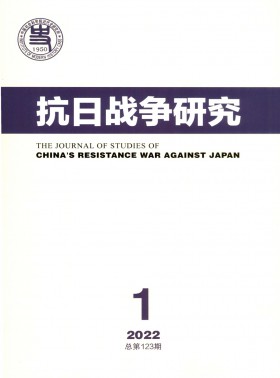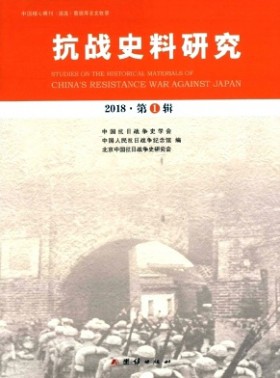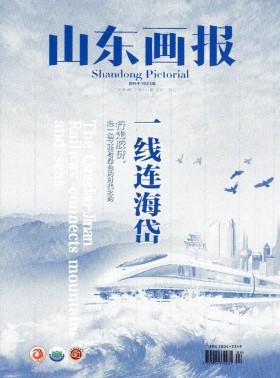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1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听着这首优美而熟悉的歌曲,你一定会想起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动人故事吧,但你知道他是哪里人吗?让我揭开这个谜吧!他原来与我是同乡。
王二小原名阎福华,河北省平山县宅北乡南滚龙沟村人,在家排行老二,村里人都叫他阎二小。1941年9月16日,二小在一个大山坡上放牛,日军300余人向南滚龙沟袭来,当日军凶狠地用刀逼着二小为他们带路抓八路时,二小非常清楚《晋察冀日报》报社的工作人员和战士就在四面的山上隐藏着。他牵着牛机智地领着鬼子在三道壕慢慢地转,从上午9点多转到了下午3点多。在二道泉山顶,他猛地抱住一个鬼子厮打,想与鬼子跳崖同归于尽,不料被另一个鬼子用刺刀从背后刺穿了胸膛。这时埋伏在轿顶山的报社武装梯队发起了攻击,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
住在两界蜂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记者方冰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并结合他平时采访的其他故事,与作曲家劫夫合作了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发表在1942年的《晋察冀日报》元旦副刊《老百姓》上。后来,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了小学课本,二小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今天,我们唱起《歌唱二小放牛郎》,重温那段历史故事,在缅怀抗日小英雄的同时,一定要不忘国耻,发奋图强,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振兴我中华,不让历史重演。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2
今天,班主任带领我们看了《小兵张嘎》这部电影。这部影片主要描写了时期,在河北省白洋淀的一个叫“鬼不灵”的村子里,有一个调皮可爱的少年—张嘎子,他和奶奶相依为命。有一次敌人来扫荡,杀了为掩护八路军的奶奶,抓走了小嘎子的朋友老钟叔。小嘎子下决心要为他们报仇,于是从一个调皮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成熟合格的小八路军战士,引发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
看了这部影片,我为小嘎子的机智勇敢坚强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嘎子勇敢地面对,机智巧妙的与敌人周旋,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游击队交给他的任务。他正是中千千万万个抗日小英雄的代表。在血雨腥风的环境下,他坚强勇敢、积极面对困难,他正是我们现代青少年学习的榜样。我们生在红旗下,在父母和老师的精心呵护下茁壮的成长,本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有些同学浪费光阴,荒废学业。湖北某市有个小学生沉迷网游,难以自拔,学习一落千丈,家长为帮其戒除网瘾,竟带着孩子徒步沿路乞讨到南京大学。这类少年与嘎子相比应该感到多么惭愧啊!有些同学遇到一点挫折就寻求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不能像嘎子那样积极的去面对。有一次,跳绳比赛上有一个同学把脚磨了一个大水泡,哭哭啼啼地给家长打电话,让家长把他背回去。这样的孩子就是温室里的花朵,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将来怎么能承担大任?
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珍惜现在的美好时光,不辜负老师,家长对我们的殷切的希望,争做新时期的好少年。
景龙池小学六年级:张维纳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3
一、根据不同年龄层次设计,丰富预习作业内容
1.预习内容多样化。
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其理解能力和思维水平都有差异,在课文预习的理解程度上应该区分任务界限。对于有一定语文功底的学生,可以在预习作业中布置动脑思考的问题。例如在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的预习任务中,“吃水不忘挖井人”本身作为一句俗语,可增加让学生课下询问或者搜查其他一些类似的、感恩助人方面的俗语和句子,这样既丰富了预习内容形式,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预习兴趣,拓展更多的语文知识,加以牢记。例如课文《永生的眼睛》的预习作业中,老师可以布置学生通读全文,然后让学生写下自己阅读后的感想,并提问学生琳达一家所表达出来的是怎样的情操及精神。
2.总结课文中心大意。
把握课文中心大意是学生阅读的基本要求,在预习课文的过程中,有效的预习要求学生必须抓住文章关键词、关键句和主要段落,老师需要根据不同的课文题材设计课文的预习备课。例如要了解的外国名著《卖火柴的小女孩》、《凡卡》、《鲁滨孙漂流记》及《汤姆索亚历险记》这些长课文,需要引导学生正确的阅读方法和技巧。如在经典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的预习中,学生需要身临其境,将自我情绪和主人公的情绪结合,以此理解故事的中心大意,老师可以布置读后感作业,让学生表达对文中小女孩悲剧酿成原因的认知,引导学生挖掘文章更深的意义。
3.提出问题,解答问题。
在学生自主预习课文的过程中,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所难免,老师在设计语文预习作业备课中应该把罗列问题也作为一项任务,要求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提出自己在预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此过程中,老师可以请其他理解这个问题的学生进行解答,因每个人在预习过程中所搜集的问题各异,在帮助别人解答问题的时候,自己也在进步,并且巩固自己的知识,最后最难的问题留给老师,加深学生的印象。例如在课文《冬阳?童年?骆驼队》的预习中,学生提出骆驼为什么要挂铃铛?“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骆驼?前一个问题则可以请平时涉猎较广的学生作答,而后一个问题涉及文章主题大意,则可以留给老师解答。例如在课文《小英雄雨来》中,老师可以引导学生提前阅读相关年代的英雄故事,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学习抗日英雄的爱国情怀。
二、抓住预习作业本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课文预习作业本来就是为课堂有序开展而服务的,在拓展预习任务、丰富预习内容的同时,一定不能脱离课文预习作业的本质,老师应该引导学生将课文教材作为预习的整体,合理、有效地研究课文内容,所以老师布置预习作业的系统性很重要。
例如在预习《金色的鱼钩》任务中,笔者设计了如下预习任务单:(1)认真阅读课文内容三遍以上,自主查字典解决生僻字、词的含义;(2)查阅资料,了解课文背景的社会现状,人民的生活方式;(3)总结每一段落的大意,结合课后练习题理解课文主旨;(4)划分课文结构,提出自己在预习中所遇到的问题;(5)摘抄课文中你喜欢或者触动你的句子、段落。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4
关键词: 课外阅读 激发兴趣 加深积淀 拓宽渠道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是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必不可少的环节。根据多年的语文教学经验,我提出以下课外阅读方法。
一、贴近童心,激发阅读欲望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正如普罗塔戈所说:“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点燃学生阅读的火把。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兴趣是影响学习活动最直接、最活跃、最现实的因素。激发兴趣,首先就要抓住童心,让学生爱上阅读。
1.巧用故事悬念,激发阅读兴趣。很多孩子都是伴着奶奶的童谣长大的。童年的梦中闪烁着数不尽的童话星星。如果我们声情并茂、娓娓动听地为学生讲述他们喜欢听的故事,很多学生就会听得如痴如醉,到学生期待故事的结尾时收住,告诉他们故事出自哪一本书,孩子们谁不想马上读这本书?如:《一千零一夜》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有一个国王,因为王后犯了错,便憎恨天下所有的女子。于是他每天娶一个妻子,第二天杀掉。很多无辜的生命消失了,更多害怕的人们逃走了。这时,却有一位大臣的女儿自愿嫁给国王,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夜讲到精彩处天刚好亮了,使国王不忍杀,允许她下一夜继续讲。她的故事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了,恢复了以往的善良,与她白头皆老。
每个人都有这么一种心理,事情做了一半,总想继续探索下去,特别是小学生,他们的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需要,希望自己是研究者和探索者。教师不妨抓住儿童的这一心理特征,吊吊学生的胃口,激起他们课外阅读的兴趣,打开文学宝库的大门。
2.畅谈读书感受,撩起阅读动机。阅读是学生的生活需要,它和吃饭睡觉一样,应该伴随学生的一生。我自己也是一个书虫,遇到一本好书,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想把它看完。有时在课堂上,谈到某本书时,我发现学生居然和我一样兴奋,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喊起来:“老师,这本书在哪里?帮我买一本。”“老师,这本书可不可以借给我看?”孩子们是很容易受感染的,一个爱看书的老师往往会带出一群爱看书的学生。于是,每节课我都有计划地向学生谈谈我的读书感受,在学生的心里“挠痒痒”,让他们产生迫切的阅读欲望,然后引导他们进行相关的课外阅读。如教学《桂林山水》后,我激动地向学生介绍我读《30天环游中国》的感受,并对书中的描写进行夸奖,学生听得如痴如醉,我趁热打铁,鼓励学生也去看看这些书,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激发阅读动机。
二、扣紧童趣,加深阅读积淀
杜甫说:“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法郎士说:“使我懂得人生的,并不是和人接触的结果,而是和书接触的结果。”书籍是学者留给人类的遗产。一本好书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在文学长河中不知保存着多少奇珍异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寥寥数笔,便勾画出黄昏旅人的落寞,简练传神。“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绝句》激起多少热血男儿的豪情壮志。在书中你可以与古人对话,感受他们的呼吸,与他们一起欢笑,一起哭泣。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巴金在谈及少年学习语文时说:“我从前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老师平时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方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摸到文章的调子……”
教师要学会挖掘每篇课文的趣味点,激发学生多看书,加深阅读积淀。如,学了《小英雄雨来》后,可以引导学生阅读《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学了《翠鸟》后,可以让学生阅读《小狮子爱尔莎》;学了《中国国际救援队,真棒!》后,可以让学生阅读《手术台就是阵地》,等等。学生会感到课外阅读是如此有趣,感到学习语文是多么有趣,并从此爱上课外阅读,逐渐加深阅读积淀。
在班级中,我们可以发挥图书角的作用,鼓励学生多看书,在班内定期举行“故事会”、“唐诗宋词朗诵会”,并评选“阅读小能手”,相信这样一定会让孩子们爱上书,爱上阅读。每天早晨,我总是让两个同学上讲台朗诵自己看到的好文章,全班同学摘记好词好句或自己喜欢的句子,日积月累,都有不少的收获。
三、珍爱童真,拓宽阅读渠道
有位现代作家曾说:“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一切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与丑陋一起呈现给你,使你驰骋古今。”是啊,“一滴墨水可以唤起千万人的思考,一本好书可以改变千万人的命运!”小学生往往还不知道该读哪些书,这就需要老师多引导学生读一些好书。
1.诗歌。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从《诗经》到《楚辞》,从“建安七子”到“初唐四杰”,从汉赋到唐诗,从宋词到元曲,它们或悲壮或豪放,或沉郁或清丽,风情万种,千古流芳。
诗歌不仅能熏陶人的气质,而且积淀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郭沫若小时候背过很多古诗:“儿时囫囵地背了许多古诗,当时并不解其意,然而入脑了。年长事更,逐渐明之,解,融于心,调度于笔。”“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定要让学生多背些唐诗宋词,可以利用黑板的一角开展“每周一诗”活动,或者课前三分钟读诗活动,还可以举行读诗朗诵会,把古诗写成书法作品,举办诗歌书法作品展览会,让诗歌走进孩子的生活中。
2.童话。孩子们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书,那就是童话。童话可以放飞孩子的心灵,他们常常想探索星空的秘密,想了解地下的情形,想听听昆虫的言语;他们想飞上天空,想潜入蚁穴……可以说,一个人在童年时代没有看过童话,那么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教师可以密切配合家长,让家长多为孩子们买书,让童话走进孩子们的童年,装扮孩子们的生活,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创造一生受益的财富。
3.名著、寓言、故事……。名著是经过时间的洗礼而保留下的珍品,它们让人百读不厌。应该多鼓励孩子去看,不同的年龄会在书中收获不同的东西。另外,还可以让学生多看些寓言、故事,充实他们的生活。
我让学生多背书,每天都要背,内容随意,可以是古诗、作文、故事、科普知识、谜语……并且每天都安排一定的时间给学生看书。我班的同学几年来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诸如少儿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大家都相当熟悉。借助大量阅读,孩子们都对课外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多同学连下课时间都舍不得玩耍,因为爱上了阅读。
乌申斯基说:“良好的习惯是人在神经系统中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会不断增值,而人在其整个一生中就享用着它的利息。”一个人读了哪些书,又是怎样读的,往往要影响他的一生,影响他的心灵空间和人文视野、价值取向和文化胸襟,影响他的精神依托和审美情趣……我们要尊重学生的生命感受,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利用课外阅读这个法宝,点亮孩子生命之灯,使课外这“冲天香阵”渗入孩子们的心田,去创造文学的辉煌。
参考文献:
[1]陆云,朱小锦.小学语文新课程校本教研问题与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