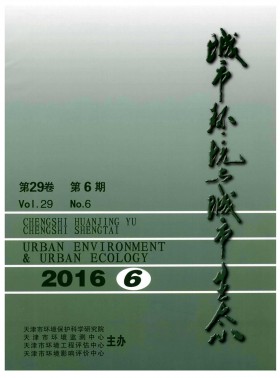诗经七月范文1
关键词:《七月》;诗歌理论;独立性追求
《七月》诗派得名是缘自于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风应该是七月诗派的一个中心人物。围绕他和《七月》形成的这样一个诗歌群体在理论和创作选择上基本走的是现实主义,主要成员有绿原、牛汉、阿垅、贺敬之等。从文学史来看,七月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是不完整的(他们没有社团和宣言)外,他们的创作也与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要求有距离,这导致了他们作品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被湮没(当然有部分人的作品除外,如贺敬之等)。现在回视七月的创作,也许可以重新定位七月的价值。纵观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对七月的研究,大都是边缘性的解读,对于七月派似乎不公平,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中,七月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也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个人创作,忽略了作为整体的七月的文学价值。许多研究者还是没有能够避开后的大的重评论述,对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得失进行系统的研究还不够。
一
七月派诗歌的发展是在现实的立足点上充分高举个性主义,以五四精神传承为己任。既有和时代接触的责任感,又具备了良好的文学美学追求,改造人生、文学审美、独立人格在七月身上都有体现。但面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和社会现实,他们无法协调这些内容,即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抓住机会,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等一系列命题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五四新文学的激进思想和功利主义,也为后来的失语埋下了隐患。
40年代中国特殊的命运使得文学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调整,为适应抗战形势,诗歌创作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都必须进行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诗派偏向文学审美缺乏社会价值和政治抒情诗偏于社会价值缺失文学审美的两种方向创作都必须加以改正,七月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承继中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进行了一次横向和纵向的综合创造。从七月诗人的理论和他们接受新文学的角度来看,在对文学的历史吸收方面七月受到多种理论影响,无论是30年代开始走上文艺中心的现实主义还是在第一个十年风光无限的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七月诗人都在学习和吸纳,五四文学精神对整个七月诗派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这其中胡风是一个重要的中介。
胡风较为深刻地学习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继承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尤其是承继发展了鲁迅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中强调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要求诗人主观精神和客观世界融合。他认为诗歌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只有情绪通过客观的形象表现才能成为诗。他的这些理论对整个七月的文学理论和历史继承都有着重要影响。
七月诗人在文坛出现是正是现实主义成为主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七月从出生就经受着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作为他们精神中心的胡风更是对现实主义有着独特的研究,这影响着他们后来的创作立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心态和中国传统文人希望建功立业的理想是很能够影响七月诗人群的,同时古典诗歌中的悲壮孤寂情怀也切合当时七月诗人的精神[1]。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进入也对七月诗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尤其是西方近代浪漫主义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叛逆精神,人性主义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精神标志,这种强烈的个性精神给予了七月诗人更多的自觉意识。民族危机中他们更多的接受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追求民主和自由,反对专制,具有强烈的社会精神,正是这种诗学意识将他们内在的传统士人的精神激醒。在此后,他们的诗在整体上显露了一种挑战者的形象,政治激情、人文精神、反叛意识;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批判力,及真、善、美的追求,都在他们的挑战者形象中得到了抒情性的融合。
诚如龙泉明先生所说“七月诗歌派是40年代启蒙和救亡的昂扬的社会激情在诗歌中的集中体现”[2],七月派是在民族解放战争高潮时出现的,作家的创作更多的也就带有一定的政治功利色彩,爱国激情、人格追求、美学选择同时还有外化的意志倾向等等都集中在了七月诗人身上。七月诗人通过关注民族现实和内心书写提升他们的人生理想,在他们心目中人是一个自觉性的统一,但他们对政治化功利色彩也带有传统“士”的理想建构,心怀天下、兼爱众生,现实中他们又更多地处于边缘,这也促成了他们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姿态。当历史的时钟停留在40年代末,“主观论”斗争的开始实际上已意味着七月开始受到社会价值的排挤,而在具有政治化色彩的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后,七月派整体上失去了最后的声音。
二
真实、独特、超前的艺术特色使得七月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与当时的文学选择有了距离,即使他们积极地从现实出发,敏锐地观察世界,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成员走到一起也是因为有共同的艺术倾向,在创作上他们继承了五四以来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自由诗的形式,更加多地走向生活,后期因为特殊的原因,七月过早地离开了文学舞台,也结束了他们富有激情的艺术生命,这似乎是一种文学顺应历史的必然,但文学的伤痕难以弥合了。
七月诗人在整体上受胡风理论影响大,强调在文学创作上主观战斗精神拥抱客观现实结合,表现了一种鲜明的战斗精神,从文学审美角度上来说,在文学艺术受到艾青的诗论影响较大。在胡风指导下,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得到了七月诗人群的继承发展,艾青的“诗的散文美”主张则在适应时代需求的同时给予了更多的现代诗歌的审美追求。绿原在《〈白色花〉序》中说道“七月诗人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3],当然这应该是从文学美学追求角度上做的一个论断。艾青对诗歌的独创性理论的发挥和真、善、美的美学理想事实上也影响了七月的整体美学追求。
艾青在《诗论》一书中明确提到‘真、善、美,是统一在人类共同意志里的三种表现,诗必须是它们之间最好的联系’[4],综观七月诗人的作品,发现他们在创作中对真实性的理解,强调诗人要注重现实生活,认为现实生活是诗歌创作的第一步,这和七月的现实主义指导从现实出发相吻合,而他们的创作更多地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入到现实生活中,诗歌感情真挚,语言简单质朴,生活感强。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描写了一个保姆的一生,用真实的笔触写就了中国的现实,诗人在作品中凝集了自己的质朴之情。在创作中他做到了诗人必须在生活实践里汲取创作的源泉,简明的理论、丰富的实践,给予了七月诗人最真实的诗歌艺术示范。除了生活性和感情的真挚,艾青在理论上还注重诗的社会功用,这一点在文学追求上似乎有些偏离,但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有着独特的一面,他十分重视诗歌的思想性,提出诗人应该是走在社会最前的旗手,影响着七月实现了小我和大我的统一。从西方浪漫派的学习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汲取,使得七月诗人的文学创作具有个性意识,经历了早期在诗艺上对艾青等人的模仿后,诗人开始结合现实找寻自己的新形式,并从西方现代派学习新的表现手法。为七月的诗美追求和新诗的艺术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七月的诗美追求主要有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真实情感、意象美、散文美和艺术风格多元[5]。无论是胡风诗的特质是对于现实关系的艺术家的主观表现、内容决定形式,还是艾青的真、善、美统一和诗歌的独立性精神以及阿垅的诗学本体论,都是对诗歌创作所阐发的文学独立性追求,尽管他们试图让诗歌创作和时代主流文学保持一致,但正是因为这些具有创见性的理论的不合时宜,为后来的七月失语埋下了导火线,直到40年后的新时期文学,才真正地被理解。
三
当中国文学从经历了那一场异常的运动后回到原来的地平线上,文学满是“伤痕”和“反思”,1978年艾青发表了《红旗》,依旧是坚持着过去的思考,《鱼化石》《盆景》更多的是他回归后对生命悲剧的人生体悟。1980年,艾青出版了《归来的歌》,归来,是诗人的一个意向,也是当时的诗歌主题。对艾青来说,写作自由、独立创作是作家的原则,然而在现代的政治格局中,他所要求的独立创作必然会和社会有着冲突,绿原在经历胡风事件后他的诗更加的冷,复出后他发表了写于特殊时期的几首诗,《又一个哥伦布》(1959)、《重读〈圣经〉》(1970),他用哥伦布的形象勾画出了悲剧后的历史,也期待着时间的判决。牛汉复出后发表的是自己写于的作品,这些诗,借助自然寄托了他的心灵,在伤痕缕缕的大自然中体验人生的创伤和痛苦,也以他的美丽死亡高声呐喊,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忧伤、对毁灭的痛恨。他们的回归不仅仅是重新写作,在创作上已经超越了40年代七月诗派对生命本体的信心,然而更多的评论把目光投向了他们的人生体验所带来的那种刚强和诗性品格的坚韧,忽视了他们在重新获得话语权后的呐喊,无论是那只被囚禁的华南虎发出的吼哮还是被雷电劈去了半边的树的屹立,他们在呐喊真实的生命和独立的人格,更是对文学独立性话语的呼唤。他们的复归在自我审视中寻找着个人与时代、理想的相通,他们复出后的作品,从人生的苦难出发寻找历史,当关注的视线更多地落在他们复归后的作品,落在那一段历史的记忆中时,忽略了他们最真切的呐喊,对独立诗歌精神的追寻。“当我真正懂得人生的严肃和诗的严肃时,却几乎无力歌唱了”[6],他们的选择正如艾青笔下的礁石:
他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他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艾青《礁石》
重新获得话语后的七月已然凋谢,但七月诗人的呐喊留下了诗的灵魂,正如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白色花》的扉页上的题辞:
要开作一支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阿垅的《无题》)
走过20世纪,重新回头来看七月的发展,重读七月诗篇,可以更多地感受他们的心灵,他们对民族、对人民的感情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很突出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也使得他们在生命意识体验中对艺术更加执著地追求。人类理想的模式化和惰性在他们如刀的文字下被撕碎了,七月用心血点燃了民族心火,却在血火中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也许可以这样概括:中国现代诗歌文学史上,七月是最积极的民族诗人,也是中国最被遗忘的歌手,他们在荆棘路上留下了血花警示后人,却在火中失去了绽放的可能。七月诗人的理想毁灭了,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会有更新的追求,但我们不能忘记在文学独立性追求上曾有的痛苦和磨难。
注释:
[1]参阅郑纳新.七月诗派与中外诗学传统,广西社会科学
1995年第3期,第87-91页
[2]龙泉明.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1期
[3]绿原.《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艾青.《诗论》,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转
引自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上海,学林
出版社2002年版,第474-475页
[5]刘扬烈.《中国新诗发展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
版,第283-289页
[6]转引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参考文献:
[1]林焕标.《中国现代新诗的流变与建构》[M].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杨四平.《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3]龙泉明、邹建军.《现代诗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4]骆寒超.《20世纪新诗综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5]江锡铨.“诗的史”与“史的诗”――“七月”诗派综论[J].
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第52-58页
诗经七月范文2
本文拟重点挖掘《诗经》中的自然科学知识,表明其对西周天命观的动摇,并为阴阳五行学说的构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人们逐步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 《诗经》 自然科学 农业 天文历法 地震 物候学 生物
《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据高亨先生考证《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约为“公元前1066-前541年”。它的内容博大丰厚,举凡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重大事件、历史传说、宗教伦理、民风俚俗、爱情婚姻、天文
地理、农业发展等等,无不囊括其中,真可谓是一部“百科全书”。对于《诗经》所蕴含的人文现象,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多有研究,本文拟重点挖掘《诗经》中所反映的自然科学知识。
自然科学知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而逐渐积累的。《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期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从《诗经》中我们看到:经过周人长期的经验积累,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具有了比较科学的农业知识。这表现在:其一是周人已经有了称之为“疆理”的治田方法,在开辟田地时,注意沟洫(田间的水道、沟渠)的建治,懂得根据地形高低、河道方向来划定田界,然后建筑堤坝,挖掘沟渠。《诗经·小雅·信南山》有:“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田匀 田匀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疆我理”,《毛传》:“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朱熹《诗集序》;“疆者,为之在界也;理者,定其沟、涂也。”是指划定疆界,验明土质;“南东其亩”,是指河水向东流的地方,亩道东西横贯,田亩在小沟的东西方向,河水向北或南流的地方,亩道则改为南北直灌,田亩则在小沟的南面。《大雅·绵》在追述古公亶父迁岐后开辟田地时亦出现“乃左乃右,乃疆乃里,乃宣乃亩”。表明古公亶父领导人们或左或右开地置邑、修理地界、治理土田、疏通沟洫、开沟筑垄。《大雅·公刘》追述公刘迁豳的事迹时曰:“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然后是“度其隰原,彻田为粮”。《毛传》训“彻”为治,彻田即是治田,开垦土地。此句也说明周人在丈量了洼地和高原之后再治理田亩播种粮食。其二,制造了较为精致的青铜农具。除了木、石制成的耒耜之类的农具外,从考古资料和《周颂·臣工》描写农官督促农夫修缮农具的“命我众人,庤乃钱鎛、奄观銍艾”的诗句可判定钱(今之锄)、鎛(锄一类工具)、銍(短镰)、艾即刈(镰刀)已用于农业生产,而钱、銍
的使用,又表明青铜已用于制做农具。其三,已经具有选种、锄草、施肥的农业常识。《大雅·大田》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以我覃耜,亻叔
载南亩。”朱熹《诗集传》解释:“种,择其种也;戒,饬其具也”,可见周人较注意选择良种。同时,许多鎛、銍的使用可判定人们也非常重视锄地。《小雅·甫田》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即锄草;耔是用土培植苗根,施以肥料,这句是讲在田间有的人在锄草,有的人在施肥,只有这样黍米和高梁才会长得茂盛茁壮。《周颂·载芟》有“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描述了众人在田里、田埂锄草的情景。《周颂·良耜》有“荼寥朽止”,表明人们已认识到杂草沤腐后用这种绿肥来肥田,庄稼就长得茂盛,就会丰收。其四,已经具有防治田间害虫的方法。《小雅·大田》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毛亨释:“食心曰螟,食叶曰螣,食根曰蟊,食节曰贼。”如何根除虫害呢? 办法就是“秉畀炎火”,把害虫投到火里全部烧死。一千多年后的唐朝宰相姚崇面对泛滥的蝗灾,就采用了这种焚烧害虫的“古之遗法”,而且“且焚且瘗”(《旧唐书·娆崇传》)使“蝗害讫息”。除此而外,从《诗经》中我们也看到其农作物诸如黍、稷、豆、麦、稻、麻等种类显著增加,畜牧业、蚕桑、园艺等也有反映。
《诗经》中表现了周人具有的天文历法知识。从诗中出现的星宿名称和在天空中的位置,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在古代天文学上占重要地位的28宿的概念。28宿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家把黄道,即太阳和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的28个星座。四方各有七宿:东方是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有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是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是井、鬼、柳、星、张、翼、轸。《唐风·绸缪》曰:“三星在天”。三星是指一夜之间,由于时间不同,三个星座顺次出现。首章的“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是指参宿三星;二章的“绸缪束刍,三星在隅”,指心宿三星;末章“绸缪束楚,三星在户”,指河鼓三星。《召南·小星》 有:“嚖彼小星,三五在东”、“嚖彼小星,维参与昴。”王引之《经传释词》认为“三五,举其数也。参,昴,著其名也。”朱熹亦认为:“参、昴,西方二宿之名。”《庸阝风·定之方中》的“定之方中”,朱熹《诗集传》释为:“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即指十月里营室星分布排列成正方形体。还有“揆之以日”,《毛诗正义》曰:“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郑风·女曰鸡鸣》表明人们已知晓“昧旦”之时,“明星有灿”(启明星放光芒)。《豳风·七月》的“七月流火”,其火,是星名,又称大火,属心宿。因为在周代各地存在着几种历法,有夏历、殷历、周历、豳历。此句寓意是:豳历五年黄昏,火星在天空的当中,六月里便向西倾斜,七月里火星向西而下,暑天即将过去。同时,在此诗中还出现了“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这表明周人在历法上的重要改革还是服务于农事活动的,正是为了发展农业。其二,对日食发生和朔日的关系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小雅·十月之交》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朔月,谓十月之朔日,即交之日也。”“按当作朔日,朔日,初一日。”“有,通又。”这就是说,在十月日月碰头的初一辛卯,日食又出现了,从此句推断,以往在朔日曾出现日食,而“据古历学家推算,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食”,“是指公元前776年9月6日的日食”。侯外庐认为:“这个记载,不仅是可以准确考定日期的最早的日食记录,也是当时对日食必须发生在朔日有了了解。”这也就是说明这一时期先民们已认识到日食都发生在农历初一。从“彼月而食,则维其常”看,人们已明白了日食和月食发生时必然是“微”(诗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即天空幽昧不明,这是“则维其常”,也就是正常的事。但这时人们对此现象不能进行科学的解释,认识不到日食的发生是由于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的中间时,太阳的光被月球挡住,不能射到地面上来的缘故,只认为“不臧”,是灾祸的预兆,所以在诗中用来表达对权贵乱政殃民带来的巨大灾异的愤慨。
地震是由于地球内部的变动引起的地壳震动,属于现代地球物理学研究的范畴。《小雅·十月之交》描写了“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地震景象,诗中人们将这种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归结为皇父擅权、褒姒恃宠,人为所致,
是由于“天命不彻”而对人们的惩罚。但这一时期毕竟产生了和当时的农业生产知识密切相关的阴阳说,认为天地间有阴、阳二气,它们的流转决定了气候的转移和农作物的生长。气原本蕴藏在地里,冬去春来的时节,气向地上蒸发,农作物出苗生长,气沉滞不能蒸发,农作物就不得繁茂。阴气其性是下降的,阳气性质是上升的。阴阳二气正常流转,气候就风调雨顺,会出现“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反之,自然界将会发生灾异。周幽王的大夫伯阳父面对《十月之交》描绘的地震现象,利用所掌握的阴阳学原理,力图来解释发生在泾、渭、洛“三川”地区的这次地震,认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丞,于是有地震”。力图从带有朴素唯物因素的阴阳说中寻求答案,动摇了将地震的发生归结于“职竞由人”的思想观念。
《诗经》还表现出当时人们所具有的物候学知识。物候学是研究生物的周期性现象,如候鸟的迁徙、某些动物的冬眠、植物的发芽、开发、结果和气候的关系的科学。虽然《诗经》产生的年代并没有系统的物候学,但是我们仅从《豳风·七月》一诗就可以判定周人已经具有了物候学常识。诗曰:“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天日子暖洋洋,黄鹏飞来飞去鸣唱)。“爱求柔桑,春日迟迟”,表明到了采摘喂蚕的嫩桑叶时,春天是昼长夜短。还有“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七月火星向西移,八月芦苇正茂畅),“七月鸣鵙,八月载绩”(七月伯劳在叫唱,八月纺麻织布),“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蘀”(四月里远志结了子,五月里来了知了叫。八月里来收谷子,十月里来树叶飘)。“五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人我床下”(五月蚱蜢弹腿跳,六月纺织娘两羽鼓动而飞,七月蟋蚌鸣野地,八月蟋蚌檐下移,九月它在房门口,十月藏匿我床底)。“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八月枣子熟了,十月里来收水稻),“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七月里来吃瓜,八月里来割葫芦,九月里来收青麻,苦菜摘来吃,臭椿砍来烧)。“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九月里修好打谷场,十月把庄稼来收藏,黍米、高粱先后熟,还有豆、麦、稻、麻)。以上向我们描述了不同季节动植物的自然变化,这些描述是非常详细的,在其他诗篇,诸如《唐风·蟋蟀》等诗中亦有反映人们具有的这些知识,对之后出现的以记载某种动植物的习性和活动的《大戴礼·夏小正》和以记述每年农历十二个月的时令、行政及相关事物为主,较《夏小正》更为丰富的《礼记·月令》等较为系统的物候学著作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诗经》中还有大量地描写草、木、虫、鱼等生物的记载,为此,三国时吴人陆玑还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书中专门解释《诗经》中草木鸟虫鱼及其古今异名,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多采此书。明代时毛晋又在吴玑所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基础上加以
注释、旁证博引,撰有二卷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资料非常丰富,所记的生物诸如蜉游、熊、罴、虺、螟、螣、蟊、贼、牛、羊、马、蝗、鱼、龟等;植物,,诸如黍、稷、豆、麦、稻、麻、桑、
蓷(益母草)、葛藟(野葡萄)、葛、李、荷华、茹芦(茜草)、荼(茅花)、蕑(兰草)、芍药、莫(莫菜)、花椒、杜(赤裳)、苓(甘草)、葑(芜菁)、蒹葭(芦苇)等等,所记动植物多达五六十种,有些生物现已绝种,其中一些植物已在后来的著作中不见了踪影。但这些记载,起码为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动植物的种类,一些动物和植物的生长习性和生长规律,从而把握周人在这方面所具有的认识水平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
综上所述,可以说,《诗经》中所表现出的自然科学知识较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可看出这些已有的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建立在较为简单的经验观察为主的基础上,带有直观性,缺乏科学的论证,还不能深刻地揭示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内在联系的过程性。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家和宗教神话没有脱离,即使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阴阳说,也出现了西周时期春初必须举行的“宜气”和“导气”的巫术仪式。但是由农业、天文、历法、地理、物候、生物、植物等方面所反映的自然科学知识标志着科学正在生长发展,它动摇了西周晚期的天命观,并为在自然科学知识发展的基础上而出现的、体现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阴阳五行学说用阴气和阳气来解释自然界的变化,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说明万物的构成奠定了基础,客观上为人们逐步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黄典诚.诗经通译新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高 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金启华.诗经全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4]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诗经七月范文3
《春秋元命苞》和《淮南子・真》开始说织女是神女。而在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和《九咏》里,牵牛和织女已成为夫妇了。曹植《洛神赋》:“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
东汉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脍炙人口:“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人从织女的角度写相思的苦衷,情味深长,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描绘得更加人间化。
南北朝梁朝宗懔在《荆楚岁时记》这样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因此,人们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农历七月初七之夜,称为“七夕”。古往今来,人们爱在这晚仰望天空,观其相会,并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天上当然没有牛郎、织女,它们只是两颗恒星。至于天河,也不过是无数恒星发出的一片芒芒白光而已。唐代诗人杜甫在诗中提出疑问:“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诗人的怀疑是对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不过是一个神话。但人们却喜欢这个神话传说,因为它表达了劳动人民热爱生活、渴望团圆、向往未来的美好之情。
历代歌咏七夕的诗很多,每每写的是天上的牛郎织女,寄托的却是人间的悲欢离合之情。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七夕》诗云:“烟霄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弦月笼烟,长空澹澹,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亘古以来,年年如此,而多少欢情离恨,都会集在这一夜之中啊。
唐朝诗人杜牧《秋夕》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夜已深了,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上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可以说,宫女的满怀心事都在这举首仰望之中了。诗中虽没有一句抒情的话,但宫女那种哀怨与期望相交织的复杂感情、那种孤独的生活和凄凉的心境见于言外。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马嵬》中有这样一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前句指的就是当时御林军进行兵谏,请求唐玄宗诛杀杨国忠、赐死杨贵妃。而后句指玄宗与杨贵妃回想起当初七夕佳节在长生殿上两人曾欢笑密约,并笑牵牛织女一年一度相见之短暂。“当时”曾“笑”他人,而今却不如牵牛织女之长久相恋,相比之下,真是令人可悯而又可笑。
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就是在七月初七的夜晚穿着新衣的少女们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称为“乞巧”。
说到乞巧,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秋日田园杂兴》却别具一格:“朱门乞巧沸欢声,田舍黄昏静掩扃。男解牵牛女能织,不须徼福渡河星。”富贵人家乞巧之声欢腾,农户人家入夜却是静悄悄的。他们本来就有耕田、织布的本领,何需再向天上的牛郎织女乞巧呢!这首新奇的小诗,热情地赞扬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宋代诗人杨朴的《七夕》也饶有趣味:“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诗句以埋怨织女的口气说,年年向你乞巧,你都把巧给予人间,难道你不知道人间的奸巧虚伪已经多得很吗?
诗经七月范文4
引发非议的关键是纪宝成校长对“七月流火”之含义的理解。毫无疑问,纪校长是用这句古语来形容天气的炎热的。批评者则指出,“七月流火”语出《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是夏历七月,天气已经开始转凉,“流火”不应该是形容天气的炎热。“火”当指星名,即古代所说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又叫大火星(西方所谓天蝎座的α星),“七月流火”的意思是说,七月大火星渐向西方,是暑退将寒的时候了。这样说来,纪宝成校长这句古语就是引用错了。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学科著称的重点大学,在那样隆重的场合,出如此明显的错误,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纪宝成校长其实并没有错。
首先,我们要明确纪宝成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使用“七月流火”这个词语的显然,他是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七月流火”的。
什么是成语?按照《辞源》的解释,成语是指两种词语:
一种是“习用的古语”。这个定义中包涵了两个要素:第一是“习用”,是指现代语言中仍在习惯使用;第二是“古语”,是指这个词语来源于古代的语言,而且一般是出自经典著作。成语的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成语的另一种则是指“表示完整意思的定型词组或短句”。
有些成语,尽管是来源于古语,但是,它的含义往往与原先那个古语已经有所区别,有的甚至大相径庭。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
1. 逃之夭夭。这个成语的古语来源是“桃之夭夭”,语出《诗经・周南・桃夭》。原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中,桃指桃花,夭夭是形容绚丽茂盛的样子。与现在说的“逃之夭夭”在词义上完全没有关系。只是以谐音的关系,以“桃”为“逃”,以“夭夭”为“遥遥”而已。
2. 落花流水。语出唐代诗人李群玉诗句:“兰浦苍苍春欲暮,落花流水思离襟”,本来是形容残春景象的。而现在“落花流水”的意思是七零八落,不成局面。
3. 每况愈下。本来是“每下愈况”,语出《庄子》:“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逾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之问于监市履也,每下愈况。’”。正,官名,指市令;,人名。监市,监市政者。,猪。履,践踏。这里的意思是说,检验猪的肥瘦,往往要踩踏猪的腿脚。猪的腿脚愈往下愈不容易发胖,所以越往下检验,(猪的肥瘦)就越看得清楚。这是作为古语的“每况愈下”的本来意思。但是后来作为成语,每况愈下的意思则是指“情况越来越坏”了。
诗经七月范文5
关键词:徐渭;《春兴诗》册;书法风格;辨伪;考证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对书家的风格确认,是书画鉴定与研究的基础,但是目前对徐渭书法风格的认识却还相当的模糊,这不能不说是徐渭书法鉴定与研究过程中的一大缺憾。如《书法丛刊》第二十六期,曾介绍一幅镇江博物馆藏“徐渭”四言联。书法水平低劣自不必说,其落款为“正德甲寅(1494年)”,此时徐渭尚未诞生,这是书画真伪鉴定中的大忌,而介绍此联的作者却用“古代书画家的这种笔误,亦不足为怪”的谬论来自圆其说,岂非笑话。如果能够对徐渭书法风格已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就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这一问题,不仅仅表现在一般书画爱好者身上,就连比较有影响的书画鉴定家们,似乎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徐渭书法的风格问题。如20世纪80年代《青天歌卷》在苏州出土以后引起的真伪之争,就是最好的例证。徐邦达先生与郑为先生的争论,最为明显的分歧首先就表现在对徐渭书法的风格认识上。要确定徐渭书法风格,势必要找出几件代表作作为判断风格的依据,因为《青天歌卷》的书法水平实在不算高明,而郑先生以为是徐渭的风格,其举例作品自然会有很多类似水平较差的作品。徐先生以为“庸俗”、“拙劣”,不是常见风格,当伪。我同意徐先生的看法,但徐先生所举之“精品”,在我看来也多是赝品(另文辨析)。在这样一种参照件不明朗的背景下的争论,当然不能形成共识。我们从后几年出版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还把《青天歌卷》作为精品之一收录来看,这次论争是没有结果的,对我们正确认识徐渭的书法风格,并没有带来多少有益的启示。并不是不允许有相左的意见的存在,但在署名徐渭的书画作品大量存世的情况下,在大家似乎都知道徐渭书法真实风格的情况下,出现这么大的分歧,就显得很不可思议了。但进次争论却给我们透露出一个信号,就是这种现象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尚待揭开谜团。
徐邦达先生是1983-1989年国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之一,与刘九庵、谢稚柳、启功、傅熹年诸位先生一同过目了很多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可以说徐邦达先生文章,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徐渭书画真伪鉴定研究的现状。刘九庵先生也是素以严谨著称的鉴定家之一,他编写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可以说又是对上述五人鉴定组过目的《中国古代书画图录》的精选与补充,他在年表的《前言》中说:“书画鉴定当以目鉴为准,辅以必要的考据。故本书所收传世书画作品,大多数作为本人目鉴为真迹者,择其有记年精要者和书画家早期及晚期罕见者栏入。”不限于《中国古代书画图录》,本书共收十五幅“徐渭”的书画作品,即便是创作时间非常接近的作品,它们的书法风格等也不尽相同。其中还有内容重复,风格各异或水平迥然有别者,根本不可能是出自一人手笔的。
徐渭书画的真伪,也有不少人研究,如杨臣彬先生研究说:“绍兴地区有专门伪造徐渭与陈洪绶字画的,但与徐渭、陈洪绶相距甚远。”徐建融先生研究说:“徐渭的名头既大……传世赝品远超过唐寅。”杨仁凯先生研究说:“张大千仿徐渭的作品也很多,有字也有画。……屡见各地有多件大千仿徐渭的《“半生落魄已成翁”七言诗》轴,……。
这些先生们所见的赝品数量很多,但被鉴定为赝品并公之于众的数量却并不很多,也可能是因为很多赝品极其恶劣,毫无研究价值所致。书画鉴定的方法很多,但我从他们的论著中,也未能得到有关徐渭书法风格的确切答案。所以,即便有很多赝品被发现,但对徐渭书法风格特点的认识,落实到具体作品时,仍然是雾里看花。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春兴诗》册存在的问题的辨析,为厘清徐渭书法的真实风格作出一些贡献,以期改变这种对徐渭书法风格特点的认识上的模糊现状。
绍兴市博物馆收藏有署名徐渭的《春兴诗》册(图1),就是刘九庵先生《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所收“有记年”“精要者”之一,它纵24.5厘米,横13.8厘米,八开册页,共16页,行草书。很多人认为,这是徐渭书法代表作之一,也有人认为是人的旧抄。其文字内容也见于《徐文长三集》卷七中,即《春兴》八首:
《春兴》紫洪S绝佳
1、好景蹉跎知几回,令春商略紫洪隈,固应带插挑深荀,兼好提尊饯落梅。
双蹇百钱苦难办,片菜孤舟荡莫催,见说山家兜子软,借穿峰顶晚霞堆。
2、乾坤瞬息雪边风,万事阴晴雨后虹,已分屠门斋后断,只难酒盏座前空。
半缗榆荚隶书客,数点梅花换米翁,小饮墙西邻竹暗,绵蛮对对语眷丛。
3、二月四日吾已降,摄提尚复指苍龙,当时小褓慈闱绣,连岁寒衣邻母缝。
一股虫尸忙万蚁,百须花粉乱千蜂,白怜伯玉知非晚,除却樽事事慵。
4、李白桃红照眼明,兰凤梨雪逼人清,一枝带蕊凭吾折,双蝶随风各自争。
粉翅扑衣犹可耐,墨钟穿帽此何黥,因思花草犹难掇,却悔从前受一经。
5、七旬过二是今年,垂老无孙守墓田,半亩稻秧空饿鹿,两株松树罢啼鹃松为盗砍。
悲来辛巳初生日,哭向清明细雨天,忽捻柳枝翻一笑,笑侬元是老婆禅。
6、昨冬不寐苦夜永。此月新弦喜昼长,柳色未黄寒食过,槐芽初绿冷淘香。
西池蝌蚌愁将动,北地秋千影不忘,描写姬姜三百句,白鱼佟饱小巾葙。
旧阅秋千,在临济赋诗数十首,几三百句。
7、胡烽信报收秦塞,夷警妖传自赣州,十万楼船指瓯越,结交邻国且琉球。
不臣赵尉终辞帝,自王田横怕拜侯,几岛弹丸觉顶物,敢惊沙上一浮鸥。
8、孟光久矣掩泉台,海口新阡此再开,色一天霞影入,寒潮万里雪山来。
迢迢支珑何方发,个个曾杨着处猜,急买松秧三百本,高阴元仗拂云材。
通过文集与墨迹内容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春兴诗》册的问题很多,具体分析如下:
1、署款时间有问题一“辛卯”年不可能书写“壬辰”年诗歌
《春兴诗》册的署款时间是“万历辛卯春(71岁)”,与诗歌中的“七旬过二是今年”相矛盾。是否为年龄推算方法有出人?徐渭自著《畸谱》所用纪年的方法,应该是徐渭自己计算年岁的方法,即出生年为一岁,过了年就是两岁,如“五十六q,……是年楸子。”“六十一q,是年樾了龋于周一甲子矣。”万历辛卯当然是七十一岁了。很多专家也都发现了这一问题,但都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此册是徐嵛解放后得于市间的,他在其著《徐文长》中说:
徐文长在旧历二月四日过七十二岁诞辰时,写《春兴》七首。
徐文长的《春兴》诗,据他手写册页共有七首。 另一首是次年之作,却在刻印时被鳊者混在一起了。
徐嵛的观点是《春兴》七首写于七十二岁诞辰时。他虽相信墨迹,但并没有解释七十二岁诞辰(壬辰年),为何书款是“辛卯”这种明显的错误。从七首诗歌的内容看,虽有描写“雷边风”等初春之景,但更多的是“李白桃红”、“兰凤梨雪”、“双蝶随风各自争”的酣春之景,其中“柳色未黄寒食过”,更明确地告诉我们是三月前后了。如果仅仅根据两次提及生日,就得出七首全是写于“诞辰时”的结论,根据是不充分的。或许不是一时所作。徐嵛还认为“胡烽”一首是“次年之作”。即七十三岁所写,也是值得商榷的。
梁一成著《徐渭的文学与艺术》附录,徐渭《年谱》把(春兴诗》册排在壬辰年:“二月四日七十二岁诞辰,作春兴诗七律”,不知是否受了徐嵛观点的影响。
徐朔方在其著《徐渭年谱》中写道:
今绍兴徐氏纪念馆藏墨迹,诸诗元自注文字,缺第七首,末署“万历辛卯春,天池道人漫书于梅花馆”。辛卯,道人七十一岁,与“七旬过二是今年”不合。第七首记时事,绝不可能作于辛卵。各诗作年不一,合而为一,故有此参差。
他还对“第七首”未收作品,作了写于壬辰年的解释:
“胡烽信报收秦塞,夷警妖传自赣州。十万楼船指瓯越,结交邻国且琉球。”首句指令年三月宁夏致仕副总兵呼拜杀巡抚都御史党馨据城反,九月平。宁夏原为秦塞。次句,十七年四月,“始兴妖僧李圆朗作乱犯南雄,有司讨沫之。”以上见《明史・神索本纪》。南雄与赣州接壤。李氏虽被杀,馀众或至本年犹未散。三句指本年五月,日本陷朝鲜王城,明朝出师援之。见同书。《明史》卷三二三《琉球传》云:“(万历)十九年,遣使来贡。而(琉球王)尚永随卒。礼官以日本方侵噬邻境,琉球不可元王,乞夸世子速请袭封,用资镇压,从之。”穷老犹以国事为念。
对于“第七首”未收作品,徐朔方与徐嵛观点不同,认为是七十二岁时作,并作出解释,但对于此册中的“辛卯,道人七十一岁,与‘七旬过二是今年’不合”的问题,徐朔方则并未解释清楚,即使“各诗作年不一”,也不可能在七十一岁时写出“七旬过二是今年”的诗句来。
李德仁著《徐渭》也把《春兴诗》册系于壬辰年二月四日。而对“胡烽”的看法同徐朔方,但对《春兴诗》册中的矛盾处未作分析。
骆玉明、贺圣遂合著《徐文长评传》,也认为《春兴》八首(没有提及《春兴诗》册)作于壬辰年“二月四日”诞辰时,我虽然不同意诗歌完全作于诞辰日的观点,但非常赞同他对《春兴诗》册未收的“胡烽”一首的分析:
“胡烽”指前一年冬蒙古军入侵榆林、延绥事。《明史・神宗本纪》栽,万历十九年十二月,“河套部敌犯榆林、延绥,总兵官杜桐败之。”并见《明史・杜桐传》。“夷警”指谣传日本将交结琉球国大举入侵事。《国榷》卷七五载万历十九年事,称:“七月癸未,浙江、福建报日本谤琉球入犯,许国以闻。”又。“十一月丙寅,朝鲜国王李V报,五月有僧云:日本平秀吉并六十馀州,琉球、南蛮皆服,期明年三月相犯。”可知万历十九、二十年之间关于日本谋划入侵中国的传说很多。诗中“瓯越”指浙闽广沿海,所以“妖传”自赣州而来。但这场战事井未发生,而是在下一年(万历二十一年)眷发生了日本侵入朝鲜的战争,看来谣传并非无据。惟事实有误。从这首诗我们看到徐渭的心中仍然洋溢着报国的热情。
这种解读,与徐朔方有所不同,照此推测,《春兴》八首的最后完成时间,就不会推迟到壬辰五月以后而更合乎情理了。
另,如果徐渭第一年春天写了七首,也不见得非要在第二年再补上第八首,如其文集中就收有《燕京歌》七首(《徐文长三集》卷十一)、《香烟》七首(《徐文长三集》卷七)等,有何不可呢?从书写顺序来看,墨迹与《春兴》八首各诗的排列顺序完全一致;从各首内容来看,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春兴》八首的第七首晚于其他七首,那么,《春兴》八首为何不把这一首排在最后,而偏偏又要排在第七首呢?这些问题虽然都有偶然性,但也不妨作为参考。
单国强在《徐渭精品画集》附录,《徐渭年表》中,把《春兴诗》册列在壬辰年,没有交代原因。
2000年第8期《东南文化》刘侃撰文《明徐渭(春兴诗)册辨析》,对是册提出质疑,但其结论是《春兴诗》册书法水平不及徐渭,是因为人模仿徐渭所至,而引起文字等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人对诗文不熟悉造成的失误,这一结论同样不能令人信服(在下文辨析)。
只有刘九庵在其编著的《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中,根据把徐渭《春兴诗》册的落款系年于万历辛卯春,可能没有细读诗歌内容所导致。
2、署款地点有问题――不应该署款已离开十年的“梅花馆”
对于“天池道人漫书于梅花馆”的地点问题,更让人感到蹊跷。《徐文长三集》卷六收有《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馆三首》,其下自注云:有扁二,日柿叶堂,日葡萄深处,并梅花馆,各赋一首。由此可知乙亥为万历三年(1575)年徐滑居处是梅花馆。又考《徐文长三集》卷七收《雪中移居二首》,云:“十度移家四十年,今来移迫莫冬天。……只堪醉咏梅花下,其奈杖头无酒钱。”根据《畸谱》,可以找二十三岁至六十二岁,十度移家的轨迹:二十三岁,始一迁居俞家舍;二是,同一年又赘塔子桥妇翁家;三是,二十四岁,妇翁买东双桥姚百户屋;四是,二十八岁,离开潘家,迁寓一枝堂;五是,三十二岁,移居目连巷;六是,三十八岁冬,迁住塔子桥;七是,三十九岁,徙师子街;八是,四十三岁,移居酬字堂;九是,六十二岁,仍居目连巷金氏典舍;十是,六十二岁冬,枚决析居,舆枳徙范氏舍。
从四十六岁到六十二岁期间,经历了入狱近七年的生活,五十三岁才释归。从《乙亥元日雪、酌梅花馆三首》中的“待予新买屋,自重两三株”句看,酬字堂已经不复存在,梅花馆可能是暂居之所,所以没有列入“十度移家”之中。《畸谱》记有,万历七年,友人李子遂自福建来探视,画竹赠之。秋,改葬先人及两妻移墓于城南术栅山。而《徐文长逸稿》卷二十一《与李子遂》信中,也有“又稍治先人之茔”之语,与《畸谱》所言时间相合。其信中还说“近有友人假与一园,稍近水竹,某将就栖其间”,如果此说得到落实,那么,徐渭应该在万历七年时,就已经离开了梅花馆。
从《畸谱》可知,因为“高雪压瓦轰折椽”,从典舍徙范氏舍后,再也没有回去,也没有买得新居,甚至连程借房屋的钱也没有,而是一直寄居在他人之家。六十六岁冬,枳徙我自 范寓王;六十八岁仲春,居后衙池一段时间,盂夏,又回到王家;直到七十三岁还居王。
也有人认为典舍也有可能是梅花馆,即便如此从六十二岁离开典舍,到辛卯,也已经离开近十年了,所以《春兴诗》册决不可能书于梅花馆。
3、“乱”、“断”等文辞讹误问题――出现与原诗歌表意相反的错误
与徐渭的文集比较,就会发现,是册所犯的文辞讹误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其第三首中:
“当时小褓慈闱绣”的“慈闱”写作“慈帏”,指代父母,是可以的。但“一股虫尸忙万蚁,百须花粉乱千蜂”的“乱”,写作“断”,则意思完全相反,且文意不通。“万蚁”因“虫尸”而“忙”,“千蜂”因“百花”而“乱”,极其工稳,用“断”字则是明显的错误。
第六首中“柳色未黄寒食过,槐芽初绿冷淘香”句中,“淘”写作“陶”也有问题,“冷淘”指过水面及凉面一类食品。杜甫《槐叶冷淘》写过:“青青高槐~,采掇付中厨,新@斫市,汁滓宛相俱。”(《分集T]杜工部》),陆游《春日杂题》诗之四有:“佳哉冷淘时,槐芽杂豚肩。”(《剑南诗稿》)“冷陶”一说却不见(或许是书写不规范造成的)。同一首中还有“描写姬姜三百句”中的“句”,写成“本”,文集中本首诗下有徐渭自注云:“旧阅秋千,在临济赋诗数十首,几三百句。”“句”和“本”是不会搞错的,显然是和最后一首“急买松秧三百本”相混。徐渭怎么能把它错写而不加纠正呢?这首诗歌中的“描”字也写错,多了一横,这种笔误也是不应该的。
4、不应是“旧抄”――“奉览”之作也不容疏忽出错
徐渭在《与钟天毓》中说:
正苦焦渴,蒙惠石埭甚感慰!《春兴》都漫作,奉览。徒取哂耳。俟当中善抄者来抄寄耳。腕病不胜书也。……写答了,忽寻封套,得《眷兴》旧抄奉上。
从“腕病不胜书”与“近日来作春蛇秋蚓,腕几脱”可知,此时徐渭书写不便。在善抄者还没有来时,发现了《春兴》旧抄,可见此处所言的“旧抄”,不一定是他抄,也可能是自抄的。他在《与萧先生》书中说:
渭素喜书小楷,颇学钟王,凡赠人必亲染墨。……令试书奉别等五六字,便手战不能,……因命人代书,其后草者则渭强笔,殊不似往日甚。
其赠人之作,一般是“亲染墨”,且特地交待是“颇学钟王”风格的小楷,又因为生病,迫不得已才“命人代书”,即便如此,还要“强笔”签名,所以我认为这本《春兴诗》册作为赠人的作品,与上述习惯并不相符。还有,徐渭《与钟天毓》中所说的,故友和门生们的爱好,是《春兴》“诗”,而不是“书法”。所以,即使有“善抄者”,也未必就要模仿徐渭的书法风格。既然注重诗歌内容,如此醒目的文辞错讹,并未得到纠正,难道徐渭会置若罔闻而贸然送出,让人“奉览”吗?如果是善抄者书,还要写上“天池道人漫书”,并且自作主张署上现已不住的“梅花馆”吗?所以我认为,此件作品同《与钟天毓》中所说的“旧抄”无关。
5、书法水平有问题――与“精奇伟杰”的评价实难相副
判断书法作品真赝,最直接的判断标准,是看其书法风格。黄宗羲《思旧录》载:“史盘,字叔考。徐文长之门人,其书画刻划文长,即文长亦不能辨其非己作也。”如果今天流传的徐渭作品中,混有“文长亦不能辨其非己作也”的作品,从风格与水平的角度看,我们是无法分辨其真伪的。换句话说。其水平也一定是很好的。但《春兴诗》册却不然。一百多年前,汤贻汾(1778-1853)就说:“伧父纷纷直取闹,大书青藤名敢盗。”潘曾莹(1808―1878)也说:“予见青藤墨迹甚多,真赝各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所面对的署名徐渭的书画作品,不仅风格多样,而且水平差异也很大,到底哪一种才是徐渭的风格呢?笔者以为应当从历史记载中去寻找答案,如自言的“颇学钟王”、陶望龄说的“防诸米氏”、《嘉靖绍兴府志》也有记载:“于古书法多所探绎其要领”,袁宏道又说徐渭的书法“姿媚跃出”。通过这些形象的描述,我们可以探绎出徐渭的书法风格,笔者认为小行草《先后帖》(图2)、《一窥帖》(图3)、博物院藏《鞋底布帖》、《感惠帖》,大字作品上海博物馆藏《行草七言古诗春雨》卷(图4)等都与历史记录、述评相吻合。从现有材料看,隆庆前后,徐渭的书法风格已经确立,且有相当的水准,即便是年老“眼昏作书”的《尊笥帖》(图5)也是如此。如果以这一标准衡量晚年作品《春兴诗》册,则风格与水准都相去甚远了。其用笔拖沓不爽、结字也经常失控,杳无古法,如第六首“昨冬”的“冬”字、“寒食”的“食”字等。哪里还谈得上“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于行草书尤精奇伟杰”呢?
《春兴诗》册还有张廷枚的题跋:“天池先生自品平生笔墨,以书居第一,识者以为至论,遗迹为四方争购,近习流传唯赝本而已,此册是其暮年老笔,真迹中之佳者,曩时得于越中书贾,近不易觏,宜珍藏之。嘉靖丁已(1797)春,罗山山人识,时年六十有八。”嘉庆丁巳,离徐渭去世近一百年,才第一次露面,且得于越中书贾,可见这件作品的流传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的,他作为六十八岁的老人,面对此等质量低劣、错误迭出的赝品,还以为是徐渭“暮年老笔,真迹中之佳者”,更可见当时的“赝本”,已经影响了时人对徐渭书法风格的判断。
6、结论――《春兴诗》册讹舛有加,乃盗名徐渭的赝品
鉴于《春兴诗》册中署款时间有误、地点蹊跷,及文辞讹乱,书法风格有别、水平较差等问题,笔者认为,它既不是徐渭的作品,也不是学生的,而是模仿徐渭书法(相似成分很少)并抄录徐渭《春兴》诗的赝品。《徐文长逸稿》收有章重的《梦遇》,他说:“菀中数岁,逢吴翁某,年八十馀,游先生门久。为予言先生文行世多讹舛。……引见其子名枳者……出先生手稿相质,果与刻本多纰缪。缘草书既难识别,校订者自谓能古文辞,妄自附会,涂饰成文。又书贾多贷中郎评点,删选几半,鱼鲁益更。”文辞的错误有作伪者自错、也会有因“鱼鲁益更”的底本造成,我以为《春兴诗》册的文辞当是作伪者自错,署款时间、地点等,则是“妄自附会”造成的。
诗经七月范文6
中国传统节日中,清明是唯一与农时节律“二十四节气”相吻合的节日。这是一个追忆和祭奠先人的日子。《左传》一书中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说法。在古人看来,祭祀的重要性甚至可与国防和军事这样的大事相提并论。所以中国古诗文中写清明的篇什着实为数不少。而众多有关清明的诗篇中,笔者以为,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无疑是出自唐代诗人杜牧的那首《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清新隽永的诗不用典故,也无华丽的辞藻,而是以白描的手法和朴素的语言,写出了清明时节的气候特征和人们缅怀祭祀故人的心情。白居易《寒食望野吟》一诗同样写得悲恸不已,诗云:“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宋代诗人高菊卿也有诗曰:“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一滴何曾到九泉!”读完这篇小诗,亦让人不禁悲从中来。宋代另一诗家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则一反常态地走出“魂断最是春来日,一齐弹泪过清明”的悲切气氛,而是兴致盎然地描述了作者踏青赏春的愉悦心境,诗曰:“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北宋文学家王禹的《清明》诗亦可算是咏清明诗中的另类:“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作者在诗中没有写踏青探春、怀古祭祖的心境,而是一反常态地描写了诗人寂寞清苦的生活和不同流俗的追求。清人郑板桥描写清明的小诗言简意赅:“小楼忽洒夜窗声,卧听潇潇还淅淅,湿了清明。”一个“湿”字,将清明前后多雨阴湿的天气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诸多古诗人笔下的清明,亦悲亦喜,亦诗亦画,亦人亦物,各种各样的情感尽在其中。
与清明节有着密切关联的是寒食节。寒食节一般在冬至后105天、清明前的一二日。是日要禁烟火,吃冷食。这一节日源自春秋时期晋文公为纪念曾辅佐他的介子推而设立的,至今已延续2640余年。唐代诗人卢象的《寒食》一诗阐明了这一节气的来历:“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唐代之后寒食、清明两节便合而为一了。
端午节在中国也是一个十分隆重的节日,曾先后入选国家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该节日本是夏季一个驱除瘟疫的节气,后因楚国诗人屈原端午这一天投江殉国,从此端午又成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唐代诗人文秀有《端午》一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农历七月初七俗称“七夕节”,因为与牛郎织女的故事有关,所以这个传统节日颇具浪漫色彩,由此也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有关七夕的古诗不胜枚举,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当属五代后唐时期杨璞的诗作《七夕》:“未来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杜牧的七言绝句《秋夕》亦堪称为此类诗文中的上乘之作:“云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写得形静而神动,表现了对爱情的向往。全诗没有一句抒情的话,但宫女哀怨与期待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见于言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白居易《七夕》:“烟霄微月澹长空,云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宋代著名词人秦观的《鹊桥仙》也是描写七夕的名篇:“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首词描写的是天上景象,实际是词人七夕仰观星空的所思所想。特别是词的最后两句,不落俗套,立意很高。时至今日,依然为人们所引用。
中秋当属一年之中又一重要的传统节日。中秋是一个天上月圆、人间团圆的节日,因而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墨客的咏月诗大都与思乡怀古有关。苏轼《水调歌头》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词句是作者大醉之后的高声纵情。中秋之夜,为怀念远在他乡的弟弟,苏轼以童稚的真率和赤诚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亲人的思恋。在幻想与现实之间,推出一轮人世间同享共照的朗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充满暖意的诗句让本是清冷的月光显得浪漫而又温馨。唐代诗人王建的《十五望月》也是唐诗中众多咏中秋篇什中的佳作。诗曰:“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首诗意境很美,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语言,渲染了中秋特定的环境氛围,把读者带进一个月明人远、思深情长的意境。加上一个唱叹有神、悠然不尽的结尾,将别离思聚的情感,表现得非常委婉动人。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八月十五夜月》采用虚实结合、借景抒情的手法,表现了作者思念家乡、怀念亲人的内心感情:“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民间在这一天有登高的习俗,故又称之为登高节。杜甫的《九日》诗曰:“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从此不须开。”诗人借助重阳登高、饮酒赏菊,因花生情,表达了思亲念乡、忧国忧民的情怀。此外,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等,都是描写重阳节的经典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