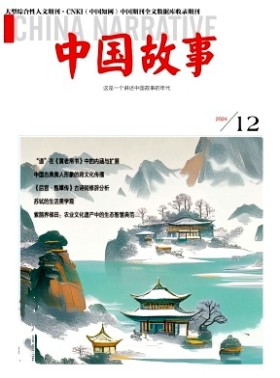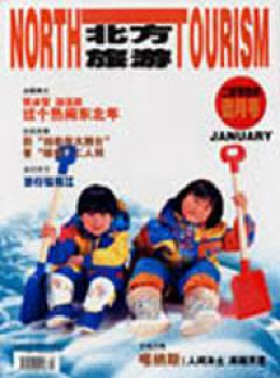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村落文化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1
现代社会,电子商务方兴未艾。作为一种全新的商务运作模式,电子商务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交易双方为主体、以银行电子支付和结算为手段、以客户数据为依托,便捷迅速,应用广泛,除国家法律限制之外的所有的现实交易都可以成为电子商务交易的对象。近几年,随着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在农村的普及,农民的消费理念和方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电子商务业务在农村文化市场的开拓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传统的农村文化消费,主要采用的是面对面的交易方式,往往交易渠道狭窄,搜集信息时间长,而且信息量小,文化产品单一,消费者的主体地位难以体现。网络普及以后,信息量骤增,网络文化产品数量丰富,文化形式多种多样,尤其是农民喜闻乐见的参与性文化节目和反映各地风土人情的地方文化产品,备受农民的青睐,农村文化市场的运作模式逐渐由以前单一的“一对一”模式向以网络为平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的开放式、多样化模式发展。
2我国农村网络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农村文化市场广阔,网络文化的发展前景无限。但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整体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文化建设优秀人才缺乏,农村文化市场体系不完善,文化建设缺乏活力,文化产品不丰富,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度不高。近几年,农村网络文化逐渐发展,但受内外在条件的制约较多,网络文化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
2.1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相对于城市来讲,整体上而言我国农村网络的普及较晚,且普及率较低。虽然我国农村网络文化建设工程已经全面启动,并向纵深发展,但农村网络文化站的设立主要集中在电力供应比较稳定、使用人口比较集中的乡镇所在地或者各村村委会所在地。这一方面便利了管理,但另一方面由于电信等基础设施的不到位,也导致偏远地区农户或者一些散户难以实现安装网线的愿望。同时,从网络运用的情况来看,农村的网络宽带能力显得不足,网速较慢就是其显著特征。网络使用和维护的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在一部分地区,使用网络还被农民认为是奢侈品。
2.2农村网络文化管理不规范
规范化的管理是农村网络文化建设质量的重要体现。从目前农村网络的使用和管理来看,这方面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政府在推动有关工作方面更看重的是显而易见的硬件建设,忽视了软件方面的管理。当地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往往受思想、能力等的影响不重视网络文化的管理。一是忽视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从走访调查来看,一些乡镇村干部及管理人员更加看重网络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网络对于文化建设的认识不足,思想上不重视就很难保障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二是将网络文化管理视同对网络文化载体的管理,认为保障网络的畅行就是对网络文化的管理,不了解网络文化管理的特殊性。三是管理机制不健全。由于受经济收入等条件的影响,农村网络入户的比例较低,大多数网民都是去网吧上网。农村网络管理机制不健全,制度执行力差,突出表现在对经营性网吧管理不善,从准入到经营到监督漏洞不少,无证无牌经营的网吧不少,收费不规范,安全措施不到位,网吧管理混乱,尤其对未成年人上网管理不到位等等都是农村网络文化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2.3农村网络文化市场建设薄弱
农村网络文化市场的建设相对于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显得十分不足。一是农村网络文化产品严重不足,且质量不高。打开各地的农民网,更多的看到的是有关经济和科技富农的信息,有关文化的信息不多,尤其是缺少贴近农民生活、反映农民心声、体现农村新变化、展示农村新面貌、凸显当地民俗民风的特色网络文化产品。与健康需求相反,由于监管不严,一些非法网站还在宣传低级媚俗的文化产品,还有以高科技包装的迷信欺骗的迷信等产品,五花八门,农村网络文化产品市场显得较为混乱。二是市场管理体系极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执行不严,监管不到位,市场基本处于无序管理的自发状况。三是农村网络文化市场的开发力不足,没有形成投融资活跃、运行健康、要素流动快的良好发展态势。
2.4农村网络文化建设人才匮乏
互联网的发展最早兴起于城市,在农村的普及较晚,而且信息化的日新月异,让从事该工作的人员都有赶不上发展的感慨,而对于刚刚熟悉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农民来说,更是跟不上信息更新换代的速度。农村网络建设人才就更显得不足。从走访调查来看,当前农村从事网络管理的人员多为返乡就业的初高中生,部分是接受过初级电脑培训的年轻农民,专门受过计算机网络及软硬件系统培训和学习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仅仅懂得基本的网络操作,因此,农村网络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任重而道远。
3我国农村网络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3.1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电信基础设施的支撑,2010年我国农村基本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目标。但网络普及入户的任务还比较艰巨。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加大对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电信、移动和联通等大运营商的良性竞争,形成整合力,节约资源,减少重复建设,推动农村基层设施建设。尤其是要积极鼓励运营商发展农村手机网络市场,当前手机上网已成为拉动农村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力量。
3.2以制度创新推动农村网络文化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首先各地政府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要充分认识到网络的发展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要清晰的认识到网络文化发展对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农民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深远影响。转变观念,创新管理模式,积极应对以适应网络时代要求,不能视而不见任其自由发展,也不能因其有弊就将其视为异物予以排斥。其次要加强制度建设,建议政府制定有关农村网络文化建设的专门管理制度,明确农村网络文化管理的目标、原则、方式、监管的措施等等,明确管理机构和人员以及职责权限。再次,加强已有制度的执行和监管。通过有影响力的媒体宣传已有制度,公开信息,引导个人、组织参与网络管理,形成全民监管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严惩农村网络文化违法犯罪行为,通过整治不良市场,提升管理效力。最后,建立完善的政府评价反馈体系。通过建立切实可行的评价体系,量化考核农村网络文化建设的基本状况,以评促建,引导农村网络文化建设的良性发展。
3.3多方联动繁荣农村网络文化市场
繁荣农村网络文化市场,积极培育丰富多彩的产品市场,一方面当地政府要采取各种扶持措施,积极鼓励和挖掘民间艺人的创作热情,鼓励他们努力创作反映当地风土人情、民俗民风的作品,并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广泛宣传优秀作品,激发民间草根文化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基础性力量。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手段对不良农村网络文化进行有效监管,通过建设网络安全系统,建立防火墙,启用过滤软件等对网络内容进行甄选,屏蔽过滤有害信息,还原农村文化市场的清新面目。同时,培育农村网络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优惠政策引导企业投资特色区域文化产品,在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促进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3.4加强培训促进农村网络文化管理队伍建设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2
芋头村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西南,距县城9km。始建于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全寨182户,该建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群因山就势,结构造型具有典型的侗族风格。建筑沿山谷层层布局,很自然地与环境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山脊型”与“山谷型”民居模式。芋头村独特的村落空间布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侗族传统聚落的研究有高度的价值。
一、芋头村寨历史背景
芋头村最早是杨姓的祖先由江西太和县迁出,经过“衡州”至“靖州飞山”后,顺渠水及其支流双江河“沿江而上”,其中经过了江口、黄柏、琵琶,最后辗转至芋头界,并在此定居。村寨中主要姓氏是杨姓,还有后来从附近的塘豹、古伦等地迁入的龙姓、粟姓,另外还有几户袁姓和熊姓居民。
二、芋头村寨选址及发展过程
为什么该村寨取名为“芋头村”?其名源于它最初建寨选址是在形若山芋头的“芋头界”。村落的生长过程是从芋头界沿山坡向谷地慢慢发展,形成由高而低层层依山盘旋而下的村落形态。现今的村寨是由三个组团构成的,牙上寨、中寨以及下寨。由于芋头村位于山地峡谷中,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耕地,故建寨首先选择芋头界顶,同时,由于山脊所对的方向是东面,利于接受阳光。随着人口的增长,村民逐渐往半山和山坳聚居,而后,发展到山脚芋头溪边,芋头溪成为村落在谷地发展的轴线。沿着芋头溪,又先后形成了溪北和溪南两个定居点,即中寨,距离寨门最近的下寨则最后才形成。
三、芋头村寨风水观
侗族村寨选址强调“风水”的理念,因此造就了侗族村寨良好的景观空间格局,形成独特的景观空间结构特征。侗寨就整体布局而言,它的村落环境与自然生态是吻合的,村内村外的环境空间也是优美的。在侗族人看来,延绵起伏的山脉可称为“龙脉”,山脉遇溪流、平坝而止之处可称为“龙头”,“龙头”面朝环绕的溪河和开阔的平坝,背靠起伏跌宕、来势凶猛的“龙脉”,村寨建在这样的“龙头”上,侗家人将此称为“座龙嘴”。再在后山蓄古树青竹形成风水林,以镇凶邪;在溪河上建造风雨桥,以锁财源。在这样风水观念的指导下所形成的地理空间模式被侗族人认为是村寨的“风水宝地”。芋头村寨是典型的多鼓楼内聚向心式布局,村寨布局形态呈带状依山体展开,牙上寨、中寨依山而建,下寨沿山脚让出中部的空间以纳气流,保证村寨空间的气韵流动。三面风水林环抱,形成沿“龙脉”分布的组团状的聚居空间和复合型村落空间形态。
四、芋头村落空间构成
芋头村寨通过形式不同,富有情趣的多层次空间,在内聚向心的结构秩序目标下,依据一定的方向性,构成了既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富有变化又和谐统一的空间环境,它们由聚落边界和村寨内部空间要素组成。
(一)边界景观空间要素
侗族村寨的边界明确了村寨的空间范围,寨门、风雨桥等要素起到边界的界定作用,是村寨内外空间的沟通与过渡。
1.寨门。寨门是侗族边界构成要素中的重要节点,它设置在村寨主要出入的道口上,最初具有防御及通风报信功能,现已进一步扩展到在意念上加强聚落群体的地域识别性和民族凝聚力。芋头村的寨门位于山体转弯处,每经蜿蜒的山路,到达寨门后,便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2.风雨桥。侗族风雨桥建造在村寨中村头寨尾的出水口处,也有少数的风雨桥建在穿越村寨内部的水面上。风雨桥既有方便交通、利于休憩交往的使用功能,又是村寨地域常见的界定要素。芋头的风雨桥造型朴素,与绿树、青山、碧水共同映衬村寨,构成良好的景观节点。
(二)村寨内部空间要素研究
以边界作为起点,侗族村寨主要由大量的民居组团空间、自由布局的水空间、位于秩序焦点的鼓楼中心空间以及穿插联系的道路空间等共同构成层次丰富的内部空间。
1.鼓楼。侗寨的活动室以鼓楼为中心展开,鼓楼是侗文化圈最具特色的公共建筑之一,是集多种功能与一体的公共场所。芋头村共有4个鼓楼,每一个鼓楼的结构、造型均不同,随着村落的变迁分布于各寨之中,鼓楼的位置,对于侗族聚落的空间构成,有一定的代表性。
1.1龙氏鼓楼:位于芋头界顶,是进入芋头界顶组团的必经建筑,有“寨门”的含义,同时,它以平实简朴的形态,成为兼凉亭、集会的场所,与旁边的古井、土地庙共同构成亲和、聚气的村寨公共空间之一。
1.2牙上鼓楼:在芋头界的半山坳口,以高脚的干栏式建筑为特点,鼓楼外侧悬空而建,成为绝佳观景点的景观中心,使村寨空间因此有很好的灵动感。
1.3芦笙鼓楼:用类似塔的形象矗立于中寨核心,9重檐,在结构和造型上都有很大的变化,是中寨村民的集聚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中心。
1.4田中鼓楼:正方形5重檐,位于芋头侗寨入口处的田中心,有着醒目而显著的空间界定作用。
2.水系串联的村落空间。侗族特别注重水空间的营造和利用。芋头溪贯穿侗寨,既是自然的泄洪通道,又是灌溉系统。在路旁梯级布置的十几处鱼塘巧妙地起到了减慢洪水流速和蓄水的作用。同时科学地利用了自然式洁污分流系统,将水统形成灵动的村落水空间。芋头水溪以其优美的形式创造出丰富的立体空间层次。水塘是侗寨水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芋头村大小水塘,穿插于密集的居住组团空间内,调节建筑空间的节奏。塘内养鱼,既调节了小气候,又方便了生活。散落于寨中的水塘使房屋保持了一定的间距,有助于采光通风,既可成为防火隔离带,又是消防水源。
3.道路形成的村落骨架。芋头侗寨道路程枝状分布,本身就具有丰富的空间节奏与层次,同时,它还是各空间内部与各空间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作为一个介入其他 空间的因素,调节了组合的疏密、强化了层次的分明。
侗族强调占用有力地形,营造适宜人生存和发展的有利空间环境,试图努力营造和谐的人居环境空间,无一不体现其“天人合一”的宇宙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夏斐.侗族传统村寨聚落中临水景观研究[D].昆明:昆明理工大学,2009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论述温州园林中乡土文化元素的应用,如城市传承历史的园林框架,内涵丰富的园林场所要素,以及底蕴深厚的建筑符号方面等,试图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以求在温州园林得到更好的应用和体现。
浙江温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永昌堡”为代表的人文遗存敦实沉稳,历经数百年风雨而弥坚,建造精美,体现了温州悠久的传统建筑文明。温州山川秀美,溪水习习,历来就是钟灵毓秀之地。以“楠溪江”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吸收了江南山水的清新秀美的地域特色,同时也蕴涵着浓厚的江浙文明,讲究小桥流水、山回路转的文化意境。
一、得天独厚、传承历史的园林山水背景
温州具有良好的自然山水环境条件,以瓯江为主要的水空间轴,南、西、北为绵绵群山,环抱城市平原。东边为东海出海口又是百岛之乡的洞头列岛,瓯海江之中又有灵昆、七都、江心屿。城市中及郊区则是河网密布,又有一些小山头镶嵌其中。景观框架:
两圈:由山体围合形成内外两圈。
外圈:以城市周边远山包括瓯北罗浮群山、景山、吹台山、大罗山等,元宝型平原形态,形成城市的园林山水背景。
内圈:围绕老城区的郭公山、松台山、积谷山、中山公园、华盖山、海坛山等形成内圈,围合温州古城,是城市的历史文化极核,也是整个城区的园林公园框架。
两轴:由水体构成纵横双轴。
横轴为瓯江。它是温州的母亲河,是构成温州城市大山水的主轴线和景观通廊。轴中包含了(江心屿、七都岛、灵昆岛)三颗明珠。江心屿风光秀靓,古迹众多。这里是温州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的凝聚点,是温州的象征。纵轴是温瑞塘河。它是城市南北走向的生态轴。连贯温瑞平原,其支流密布延伸至城市内部各处,是构成城市内部山水园林的最主要场所。
一片:三水网,是温州水乡风貌的突出反映,是城市山水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点:杨府山是城区中部最高最大的山,是主城区中部的地标和景观控制点。
二、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园林场所要素
所谓的城市文脉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元素。它取决于一个地方所特有的环境特征、文化基因及价值取向。文化是一个城市园林发展和形成特色的基础。城市园林的建设不仅要利用自然的山水环境条件,还要把山水诗和山水画这些诗情画意的文化内涵融于城市空间环境中。
(一)温州典型的山水园林空间的场所要素。古榕、小桥、河流、凉亭、远山,是温州典型的山水园林空间的场所要素,是“温州山水画面中的景物。”在园林建设过程中既要保护传统的历史文脉和山水城市空间特征,又要力求把蕴涵其中的乡土文化元素应用其中,使温州园林更具地方特色,更具生命力。
(二)人与自然山水和谐的生活空间。温州平原是水网地带,传统的村落基本上沿河布局,而且分布较散,许多村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并创造了一些人与自然山水和谐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园林建设应吸收其精华,使城市的园林山水空间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形式。
(三)手法独特、别具一格的传统人文水景。“水”的意象来自于温州当地发达的山水文化。作为江南水乡,“小桥流水”、“近水人家”、“九曲十八弯”……,传统的水系构成不仅仅体现在自然山水当中,还体现在人文景观当中。村落、城市当中的水道不仅是生活用水的来源、交通运输重要的通道,还是文人墨客反复咏唱的题材,这种亲水的居住生活方式经积淀到当地居民的文化基因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昌堡”的护城河系统就是人文水景的典型代表。永嘉芙蓉村的水系处理手法尤为独特,其按“七星八斗”的思想进行规划设计。“星”指道路交汇处方形平台,“斗”指水渠交汇处方形水池。道路、水系都是结合散布的“星’、“斗”而形成的,其规划布局隐喻村寨可纳天上之星宿望子孙后代人才辈出如繁星。另一方面突出“利为战”的目的,其星可作战时指挥台,其斗贮水以利战时防火攻以水克火。主街中部南侧凿一内湖水色清冽。村内引溪水沿寨墙、道路沟通各“斗”形成流动水系清流涓涓,迁回于宅边、道旁既可供村民洗涤、防火,又可调整小气候。
三、古意浓郁、底蕴深厚的建筑文化符号
(一)楠溪江的耕读文化和民居建筑。楠溪江中游古村落及其乡土建筑是中国乡土建筑文化中最为突出、最为综合的代表。乡土建筑的存在方式是村落。每个楠溪江村落大体可说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圈,村民的杜会生活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楠溪江村落建村古老,有建于晚唐的,如茗番村、下圈村,建于五代的有枫林、苍坡等,大量的是两宋时期所建。楠溪江建筑类型相当丰富,几乎包括了商品经济发展前农村里可能有的全部建筑类型。尤其是以文化建筑,如书院、读书楼、文昌阁、文庙和一些起教化作用的牌坊和亭阁为典型。自隋到宋,特别是至南宋末年,宋室偏安江左,大量衣冠南渡,使楠溪江文化达到高崎。楠溪江以村落建筑为代表的文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楠溪江的村落建筑虽然经历了近千年的沧桑风雨,却旧颜未改,仍然保留有宋代建筑的寨墙、路道、住宅、亭榭、祠庙、水池以及古柏等,处处显示出浓郁的古意及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泰顺廊桥的古蕴遗风和精巧结构。泰顺被誉为“千桥之乡”、“浙南桥梁博物馆”,桥梁数量达958座,石碇步248条,结构类型也多种多样,有堤梁式桥(即碇步)、木拱桥、木平桥、石拱桥、石平桥等。据《泰顺交通志》记载,到1987年底,全县现存桥累共计958座,总长16829延长米,其中解放前修建476座,7923延长米。包括木拱廊桥、木平廊桥和石拱廊桥在内的明清廊桥30多座。其中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木拱廊桥6座。即泗溪姐妹桥、三魁薛宅桥、仙居桥、筱村文兴桥、三条桥。木拱桥以较短的木材,通过纵横相贯,犹如彩虹飞架宽阔水面,其巧妙的结构,令人惊叹!
四、结束语
21世纪的园林设计思潮不应该只是符合使用机能的需求,要力避大量制造普同性东西,更应在针对设计对象使用者的特殊性及个别性上多加著墨。今天的园林更加注重对作品本质和历史文化内涵的探求,以特定的形式体现出对历史文脉和环境的关注。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一笔财富,但对历史的狭隘的理解却常常成为创作的羁绊。对历史的尊重不是沉湎于对昔日形式的怀念,而是创建一种符合当今时代的形式。园林人必须清楚,从设计对象所处的文脉中进行设计解析和创作,透过文化历史符号系统来进行创造性的设计,同时还要尽量摆脱已往的符号形式与结构,用新的技术、材料以全新的形式结构进行再诠释,发展那些有承接价值的传统文化。这样温州园林将更有乡土气息,有文化之根的作品更具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郑晓东.温州山水城市空间初探.现代城市研究,2001.1.
[2]彭慧锋.古典与现代的交融,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华中建筑,2000.
[3]何光华.贝聿铭的建筑思想及创作手法[J].中外建筑,1998,(6):44.
[4]杨裕富.设计的文化基础[M].台北:亚太书局,1998.
[5]戈悟觉. 《瓯越文化丛书》.作家出版社,1998.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乡村旅游;弱势群体;原因;对策
[作者简介]文军,广西大学生态与旅游科学研究所所长,环境景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博士;李星群,广西大学商学院讲师,硕士;陆明,广西大学商学院2005级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5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5―0066―03
一、调研背景
近20年来,我国的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迅速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亮点。目前国内对乡村旅游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近5年以“乡村旅游”为专题研究的学术论文就已超过400篇。这些研究已广泛涉及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产品开发、景点区规划、市场营销、发展模式、经济文化冲击、资源基础与保护等主题。相比之下,对于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却鲜有关注,相关研究显得严重不足,相关论述零星分散,缺乏对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研究。虽然近几年来广西的乡村旅游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在广西农民脱贫致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对广西乡村旅游的研究还比较少,且不系统,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只有10余篇论文对广西乡村旅游进行了探讨。研究层面主要基于宏观和个案研究,研究内容基本是如何开发乡村旅游,缺乏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的关注。
二、研究目的与方法
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存在,对旅游乡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十分不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极大地影响广大村民开发乡村旅游的积极性,不利于广西乡村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对广西乡村旅游开发尚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尤其还缺乏对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方面的研究,“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课题组于2006年5月~2006年12月分批对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的村屯进行了调研,旨在系统研究广西乡村旅游开发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开发对广西农民脱贫致富的作用,以期揭示乡村小型民营旅游经济发展机制等问题。调查范围涉及整个广西区域,主要调研的县市包括龙胜、阳朔、恭城、临桂、灵川、资源、灵川、桂林市近郊、乐业、田东、田阳、南宁市近郊、武鸣、靖西、东兴、北海市近郊等县市,调查村屯或乡村旅游景点共32个,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经济实体及对照样本(未进行乡村旅游经营的村民)。为保证本次调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次调查通过实地调查、问卷法与深度访谈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问卷采用面对面的调查方法,调查完即回收问卷,未能完成调查的样本不列入统计分析中,共完成调查样本250份,其中有效样本213份,对照样本264份,其中有效样本232份。深度访谈在征得被采访人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后整理,每次时间为2~3小时,共完成12份样本调查。本论文的内容取自调研中与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弱势群体的收入现状调查模块和一些实地调查内容的总结。虽然乡村旅游经济实体样本与其对照样本数不一致,考虑到样本比较多,分析的准确率会高一些,加上本论文的分析是用百分比来表示,因此,对照样本多出部分在分析中没有剔除。
三、经济弱势群体的特征分析
弱势群体是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城乡中那些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缺乏必要而稳定的经济来源,处于贫困状态或接近贫困状态的人群。农村经济弱势群体是经济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是指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及低收入者的集群,它包含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两部分。农村经济弱势群体也指现阶段我国城乡中那些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乃至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的不能平等享受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至于缺乏必要的、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已经处于贫困状态、接近贫困状态和趋向贫困状态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群。唐玉凤等(2006)认为农村弱势群体也指目前在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中参与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能力较弱、经济收入较少的社会阶层。
在项目研究中,我们将广西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界定为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及其对照样本中经济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村民群体。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相比,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具有明显的特征,除具有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社会地位低、承受能力差等一般特征之外,其特殊性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收入是指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即强调其经济状况是与本村其他居民进行比较,可能纯粹就经济状况而言,在全国范围内,这些弱势群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其二,这些弱势群体一般拥有改善自身条件的机会,但由于经济基础差、文化水平低、年龄过大等诸多因素导致贫困或相对贫困;其三,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经济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旅游乡村其经济弱势群体的状况是有区别的。
四、经济弱势群体的现状与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广西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调查样本中,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37例,占总数的17.4%。在未创办民营旅游经济实体村落中村民收入处于“下等”和“中下”的有110例,占调查样本总数的48%。以全部样本来分析,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比例为33%。在广西开发乡村旅游的村落中,已创办乡村旅游经济实体的37例样本中,我们发现其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仅有4例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其他均为文盲或小学学历,占总数的89.2%。对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对照样本,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仅有3例,其余均为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总数的97.3%。综合课题的前期研究,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与其最高学历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即文化的贫乏是导致其家庭收入少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未创办乡村民营旅游经济实体的调查数据我们得出,232个有效样本中,缺乏经济基础的占有185个样本,占总人数的比例为80%。数据证明了经济因素是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不能生产自救或脱贫致富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他因素导致乡村居民创业难的主要有年纪大、身体差或有残疾、有病、要带小孩、担心风险、性格不适合、没兴趣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占
样本总数的20%。经济弱势群体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的普遍现象,综合调查结论,广西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下几个方面:经济因素,主要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者,如缺乏创业基金等的村民;文化因素,主要指拥有信息、知识资源量少的人,如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创业的能力等无法创业的弱势群体;生理因素,主要有残疾人、老年人、妇女儿童与病人等。
五、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对策
(一)建立健全经济弱势群体的帮扶机制
建立合理和高效的运行机制是实施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帮扶战略的重要保证。应根据“帮扶战略”的要求构建一套制度化、常规化、人性化的运行机制,为解决旅游开发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问题提供各种保障,并注意措施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帮助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提高素质、转变观念、开阔思路,增强主动参与和自我发展的意识,以教育培训为主,增强已开发乡村旅游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自我造血功能。
(二)改进扶持方法。完善二次分配机制
改变当前对旅游乡村弱势经济群体的救助方式,变生活救助为旅游扶贫开发救助,在旅游扶贫开发中,方式由现金和实物援助为主转变为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援助为主,扩大在技术、项目、培训和销售等方面的有效援助。将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援助纳入发展乡村旅游开发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旅游开发项目和人工需求应该重点照顾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积极稳妥地推进旅游开发乡村的分配制度改革,既要使资源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又要兼顾社会公平,特别关注村落中的经济弱势群体。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利用税收杠杆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解力度,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村民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有效地保护和救助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
(三)重视乡村教育培训,健全科教扶贫长效机制
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科教扶贫是对经济弱势群体最根本、最彻底的扶贫,是扶贫的长效机制。实施对经济弱势群体救助单靠一时的送钱送物势必陷入“扶则解贫,不扶返贫”的怪圈,难以从根本上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应该着眼于建立救助弱势群体长效机制。研究表明,旅游乡村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文化素质低是造成其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村民的收入与他们所具备的文化素质的高低密切相关。要做到乡村旅游开发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同步进行,对于经济弱势群体要改变传统的生活救助为科技救助。加大教育援助将有效促进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增强其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获利能力。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培训,建立“校一村”科技帮扶体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为弱势群体提供多种职业、多种技能的培训服务,以改变其文化低、劳动技能单一的状况,使其尽快就业。此外,解决好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子女受教育问题,不使家长的贫困和弱势延续到下一代也非常重要。
(四)建立乡村旅游股份公司。探索多种形式的发展模式
当前广西各地乡村旅游经济多是各自为政,乡村旅游开发村落的旅游开发多以市场化形式进行调节。为加强对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经济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在乡村旅游开发村落中成立旅游公司,建立村级董事会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以分散的农户为基础,组合成团体,在协作中提高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上求生存、图发展,以统一的面孔对外。董事会要以旅游乡村的公共旅游资源为基础,村民均是公司的股东,每户村民都有基本股份,村民通过多种投资获得更多的股份。公司可以由村民自己经营,也可委托经营或聘请管理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也可将经营权作股份转让经营权,村民从分红中获得利益,从参与管理或被聘为工作人员之中获得就业机会。
(五)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旅游乡村经济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仅靠一家一户是无法解决的,要从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人手,强化村级组织功能,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积极帮助、扶持有脱贫致富愿望和条件的经济弱势群体尽快脱贫致富。在搞好村级班子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基础上,引导农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开展多种经营,村民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益农则农,益旅则旅”,积极为广大村民特别是那些经济弱势群体搞好服务,依靠集体的力量改变旅游乡村的整体面貌,走向共同富裕。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麻扎;巴合西;萨满教
“麻扎”是阿拉伯文“Mazar”的音译,原意为“访问”、“探望”意思,维吾尔语中转意为“圣灵之地”、“伟人之墓”,主要是指伊斯兰教显贵们的陵墓。麻扎朝拜在维吾尔族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在南疆农村,麻扎朝拜已成为维吾尔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麻扎被人们看成为攘灾避祸、倾诉痛苦求医治病、拯救灵魂、寻求欢乐的场所。新疆的麻扎随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而形成了各方面的组成部分。许多学术著作中关于麻扎的概念与伊斯兰教圣贤们的陵墓紧密联系在一起。
1 麻扎建筑的形式
建筑是社会意义的一种载体,是从物质上表现特定历史时期核心观念、目标和情感的方式。[1]麻扎作为维吾尔族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筑也具有各种的形式。不同的宗教文化,不同的年代的麻扎建筑有所不同。麻扎的外观和附属建筑都有所不同,一般由圆顶型的墓室,礼拜寺、罕尼卡等组成。[2]塞尔江・哈力克在“交融的趣味--浅析哈密三座麻扎建筑的风格演变”论文中说“新疆麻扎数以千计,家族麻扎尤具历史地位,其中著名的有霍城秃黑鲁・帖木儿土陵、喀什阿巴霍加麻扎、哈密土陵等。整体考察新疆伊斯兰建筑,回族聚居地的中国传统木结构风格、维吾尔族聚居地的中亚生上砖混结构风格是两个最为突出的代表。”[3]
2 麻扎村
作为传统的人民居住空间,古村落大都包含着悠久的历史,是历史的微缩,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美学、建筑、科考等价值。作为最重要的传统文化旅游地之一,古村落正正在面临瞩目与追逐,成为了新世纪旅游热点,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乡上建筑是民居的主要形式。在新疆麻扎村广泛的位于。 1997年保罗・奥利弗在们日_界乡上建筑大百科全书》中指出:“任何形式的乡上建筑都可以按照特定的需求而建,并与促生它们的文化背景下的价值、经济及其生活方式相适应”[4]。19世纪以来,麻扎村一直吸引着德、英、日、俄等国旅行家和探险家的目光,被称为“中国西部最神秘的地方”。[5]李欣华在《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这一论文中指出“特的宗教历史、民俗和独有的神秘性,使麻扎村开展古村落旅游的潜力异常巨大、优势相当明显”。[6]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的学生沙代提古丽・买明在毕业论文“麻扎与维吾尔族麻扎朝拜”中以吐峪沟麻扎村为例在吐峪沟麻扎村的地理位置,朝拜仪式,麻扎村朝拜的变化及麻扎村朝拜的功能进行了分析。比如:布施仪式、油炸食物放烟仪式、扎彩条(旗)、除秽术、洞里念经祈望等等。[7]
3 麻扎与萨满教
萨满教是一种自然的、原始的多神教,其内容是以“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观念为基础,主要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部。[8]萨满教在古代新疆各少数民族中流传的时间比较久,长期支配着先民们的精神,形成了有着民族特色的观念和习俗在与外来的宗教文化而融合的过程当中,以另一种变体的形式而出现在我们面煎而剥离这种文化现象对于识别原有文化、风俗和习惯都有着不可缺少的意义。周得华《浅谈麻扎朝拜中的萨满教遗存因素》(2011)指出萨满教在新疆古代民族中的影响。高琳的《麻扎朝拜中萨满文化的生存及原因探析》一文中指出维吾尔族独特的麻扎朝拜活动,可以视为萨满教自然崇拜、先祖崇拜和伊斯兰苏菲派偶像崇拜的一种混合体。在维吾尔族麻扎朝拜活动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萨满教遗迹[9]。
4 麻扎与妇女的生育观
麻扎朝拜是维吾尔族妇女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热依拉・达吾提在《维吾尔族麻扎的功能职司及其演变研究》说到“传统社会里,妇女们的言行平日里受各种各样的伊斯兰教教规的限制。她们不能轻易走出家门,不能参加公众活动,长期处于某种程度的心理压抑之下。麻扎活动则给了她们一个“合理合法”的机会参加娱乐活动”。[10]子求子习俗在维吾尔族中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突厥、回鹃时代对萨满教乌弥(Umay)女神的崇拜。乌弥为突厥语的音译,是突厥萨满教中的保护神和生育之神,地位仅次于男性化的保护神一腾格里(T angri)而凌居其他众神之上,享有很高的权威。从维吾尔族的其他生活习俗里也可以窥见对乌弥崇拜的痕迹[11]。维吾尔族原来是游牧民族以后把生产方式改变定居了,在游牧时期,氏族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纽带,从此后这种氏族关系逐渐被家族关系代替,而生儿育女成为维持这一关系的重要纽带。在父权制度下,男性被视为维持家庭存亡的根本,而妇女们被视为生儿育女的工具,无子成为妇女被体以及在家中受辱的理由。而即使在生育知识较为普及的今天,在一些农村地区,生育还是被看成是妇女单方面的事,这是在今天专司生育的麻扎在民间仍具有威望的重要原因。在《麻扎与维吾尔族妇女_从麻扎朝拜谈维吾尔族妇女的生育观》论文中热依拉・达吾提博士阐述了维吾尔求子习俗的历史演变及在麻扎朝拜活动中的种种表现后,她认为这种求子习俗在维吾尔族中经历了较长演变过程。[12]
5 结论
麻扎朝拜,作为维吾尔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宗教活动的一部分,在维吾尔族人们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现代人们需求的多元化,人们来麻扎朝拜的动机也各种各样,举行的朝拜仪式也多了,麻扎朝拜文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麻扎不仅是对新疆伊斯兰教的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是多层次文化现象的统一体。
参考文献
[1]艾力江・艾沙,《阿帕克和卓麻扎―一个多重意义的文本》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7月第32卷第4期
[2]宋超、李丽、路霞,《新疆伊斯兰教麻扎墓室建筑的类型研究》 ,西部考古,第6辑
[3]塞尔江・哈力克,《交融的趣味--浅析哈密三座麻扎建筑的风格演变》 民俗民艺,2009年7月
[4]荆其敏,《中国传统民居百题》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5]李欣华,《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以吐鲁番吐峪沟麻扎村为例》 干旱区地理,2006年4月,第29卷第2期
[6]李欣华,《历史文化名村的旅游保护与开发模式研究―以吐鲁番吐峪沟麻扎村为例》 干旱区地理,2006年4月,第29卷第2期
[7]沙代提古丽・买明 《麻扎与维吾尔族麻扎朝拜,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年第2期
[8]高琳,《麻扎朝拜中萨满文化的生存及原因探析》,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9]高琳,《麻扎朝拜中萨满文化的生存及原因探析》,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0]热依拉・达吾提,《维吾尔族麻扎的功能职司及其演变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村落文化论文范文6
迄今为止,对清水江文书抢救和整理工作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晓光、龙泽江《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01);龙泽江《锦屏文书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与开发利用途径――锦屏文书暨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综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04);龙泽江、曾羽《锦屏文书保护现状和出路》(《兰台世界》2011/08);龙泽江、罗康智《关于建立锦屏文书数据库的思考》(《凯里学院学报》2010/02);吴平、龙泽江《从学术资源保障看清水江流域锦屏文书的数字化道路》(《贵州社会科学》2010/12);王宗勋《锦屏民间林业契约及征集研究基本情况》(《贵州档案》2009/01);杨有赓《建设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森林生态博物馆和清水江绿色旅游刍议》(《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魏忠《独特的贵州苗族契约文献》(《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01),等等。目前,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相关课题主要有凯里学院曾羽主持的“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与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2011)。综合以上论文的分析,现分别将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与整理方面已取得的成绩及主要观点简要评述如下。
(一)清水江文书的抢救
1.清水江文书的现状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工作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开展。(1)领导机构。2006年,贵州省和黔东南自治州分别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由副省长、副州长担任组长,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县、乡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2)抢救保护实施机构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主要由各县档案馆承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天柱、三穗、黎平、剑河、岑巩、台江7县档案馆收藏进馆保护的清水江文书达8万件。其中,锦屏县档案馆收藏有35万件,已经抢救修复2万余件。2011年2月22日,锦屏文书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名录》。(3)抢救手段。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仅限于部分县档案馆的征集、进馆、修整、裱糊、编目、装盒等基础性工作。(4)保护设施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资助项目、总投资1800多万元、建筑面5400平方米的“锦屏文书特藏馆”正在建设之中。
2.抢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清水江文书的家底不清;(2)民间家户散藏的文书,折叠破损、虫蛀、霉变程度严重,存在火灾隐患,亟需探索民间抢救保护的新机制和新手段;(3)县档案馆征集文书模式的抢救力度赶不上“自然流失”的速度;(4)县档案馆的抢救资金投入得不到保障,影响抢救保护成效;(5)县档案馆的保护技术落后,存在再破坏。
(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
1.现有整理成果。目前,清水江文书的主要整理出版物,先后有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03年出版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共3卷,整理文书853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年先后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共3辑33本,整理公布文书约14万件;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整理文书800余件。其他整理的文书有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入契约130余件。
(1)编辑体例。三家出版物的编辑体例各不相同。《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并列,用铜版纸印制,每件之首撰有简约著录文字。按照:A.山林卖契;B.含租佃关系的山林卖契;C.山林租佃契约或合同;D.田契;E.分山、分林、分银合同;F.杂契(包括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G.民国卖契的顺序编辑文书,构成前两卷“史料卷”。第三卷是“研究卷”,是契约文书的研究专题论文的汇编。《清水江文书》采用文书原件影印出版,一般不对每件文书全文判读,但是每件文书都有标题(含事主、事由、文书种类及时间四大要素)。对于图黑的文书,则整理出文字,附在文书图片旁。它的编辑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寨给一个顺序号,村寨之下根据不同的家族或家庭分卷,来自同一家族或家庭所收藏的文书为一卷。同一卷之下按照收藏者的原有分类,再分别列为若干帙。每一帙内的文件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辨读全文放在一起,按契约和其他文书依次分为两大类,契约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其他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分银单、记账单等,也是按时间先后排列。
(2)分类标准。《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按性质,分为前文所述的7大类。其分类标准不是统一的,属于不完全的、概略的分类。《清水江文书》将文书按性质分为10个大类: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但是,每一大类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清晰的分类标准。其所拟定每件文书标题中的要素之一是“文书种类”,其含义是指约、字、合同、清单等不同的类别,是完全基于文书内容所包含的表述的分类。比如“约”的种类,来自文书内的表达就包含“立断山场杉木约”。《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不完全分类为:卖木契、卖山契、卖木并山契、卖田契、卖菜园、卖屋基契、卖地契、佃契、分银合同、分山合同、借契、借当契等。
2.现有整理成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整理的成果,反映了整理者对清水江文书的整体把握和认识深刻程度。《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的整理者,显然认为林业契约是清水江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单纯依靠林业契约,不足以全面、深刻地认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清水江文书》的整理者,则试图全面整理所有的文书,不局限某一类或某一领域的文书,似乎认为文书都有同等的价值,要留待研究者去挖掘和评价。但是,它需要足够的经费和队伍的持续支撑,研究者需要自己判读,难以利用。《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的整理者,认为契约是清水江文书的精华部分,选取一家保存最好的作为典型,但是难免“管中窥豹”。所以存在的问题是:(1)不同机构的整理者标准不同,没有共同的学术规范;(2)不同机构整理的成果有重叠,三家出版物整理文斗寨的文书,两家整理平鳌寨的文书,浪费学术资源和经费;(3)不同机构的整理者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到文书保存地收集,存在恶性竞争,“割肉式”整理,破坏文书的信息内在联系和完整性;(4)没有对清水江文书中苗族、侗族等文化符号(单位、名物)进行训诂和考释,影响文书的正确判读和深化研究;(5)没有建立起清水江文书全文数据库。
二、清水江文书的研究
自杨有赓1988年发表研究论文以来,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国内著作有6部,论文200多篇;研究人员主要有杨有赓、张应强、王宗勋、单洪银、徐晓光、罗洪洋、梁聪等专家学者。目前,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有凯里学院龙泽江的“贵州锦屏文书研究―以清代黔东南苗侗土地契约文书为中心”(2009),贵州大学吴述松的“清水江文书制度与苗侗经济研究”(2011年)。
国外研究清水江文书的学者主要有唐立、武内房司、相原佳之、寺田浩明、岸本美绪等。代表论文有唐立《清代清水江流域苗族植树造林的开始――林业经营兴起的各种因素》、武内房司《从鸣神到鸣官――清代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见苗族的习俗和纷争处理》、相原佳之《清代・中国清水江林业经营的一侧面――平鳌寨文书事例》、岸本美绪《贵州的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的山林契约文书》等。以上论文均被收集在《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第3卷中。另,相原佳之《从锦屏县平鳌寨文书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经营》发表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上。
三、代表性成果述评
(一) 杨有赓执笔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及系列论文。杨有赓的相关论著均是清水江文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奠基性、资料性的开山之作。一是首次对林业契约中的佃契、卖契作了解读,是以后深入研究的基础;二是依据官府文告、诉讼状稿等,对 “清江四案”(皇木案、当江案、白银案、夫役案)进行分析;三是对山客、水客、木行、排夫等木材交易主体及其行规进行了介绍;四是对木材交易和运输环节中的“技术性规则”(木材独特计量方法、单位等)作了介绍;五是民国时期的木材税收资料丰富。当然,该书阶级矛盾分析方法贯穿始终,有其局限性。杨有赓其他5篇论文也是在以上问题中展开的。
(二)张应强的研究。2002年,中山大学张应强发表了论文《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03),以碑刻和民间文书为据,考察了清水江下游木材市场的交易制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论文《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村落与族群――以锦屏文斗寨的考察为中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05)、《清代契约文书中的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以及专著《锦屏》(三联书店,2004年)和《木材与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族村落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木材市场流通历史概况。
(三)单洪根和王宗勋的研究。二人均是黔东南本土学者,前者长期担任锦屏县和黔东南州的行政领导,注意对本地契约文书的收集和研究,20062007先后出版《木材时代-黔东南林业史话》(林业出版社,2008年)、《清水江木商文化》(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及《锦屏林业契约文书――清代林业生产关系的活化石》(《凯里学院学报》,2007/05)、《林业契约与林权改革》(《林业经济》2010/08)等论文,比较系统的对锦屏林业契约进行了分类,初步揭示了清水江木商文化的特点,并对林业契约在当前林权改革重大作用进行了研究。后者一直在锦屏县档案馆和史志办工作,长期接触一手资料,在收集和整理文书的基础上先后发表整理和研究的论文有20余篇和专著《乡土锦屏》(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该书对锦屏各乡村的自然、文化、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四) 罗洪洋的系列论文。20032007年在《民族研究》发表4篇论文,以《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民族研究》,2003/03)为代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卖契、佃契、分合同和处理山地林木纠纷契约四种主要的林业契约。同时它指出“以林业契约为主的习惯法”起到了调整和保护林业产权、形成经济预期的作用。林业商品生产实践产生了法律意识,催生了林业契约样式。他还援引罗马法,来论证市场经济实践出法律意识的普适命题。至于其引申得出的“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淡薄”,则缺乏严密论证,且与林业契约的“契约设计的精妙”的结论似有冲突之处。罗洪洋还认为清水江林业经济只能是家庭私有制经济。
(五) 徐晓光的著作和系列论文。《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撷取和述评当地历史上发生过的若干重大的林业经济纠纷或问题,比如内、外三江之间“争江”、夫役之诉、民国开放江禁之争、“漂流木植清赎问题”、民国木税之争、黔湘两公司木材砍伐纠纷、控诉山客巨富“姚百万”、姚家内部山林纠纷等,试图勾勒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清水江流域林业法制全貌。法制无非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以上选取的案件涉及木材生产、运输、交易等环节中的各类主体之间主要利益关系。当然,它所呈现的法制全貌是寓于叙述和解读中的启发性,依然不是脉络连贯、条例清晰的理论形态。该著作是一部研究方法有创新、体例视角有特色、比较系统的林业专门法制史专著,对以后研究的启示有:一是立足民族法,挑战“华夏正统”观念;二是突破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三是法律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兼用。《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2007/06)是其系列论文中的代表作,针对罗洪洋的研究认为林业经营模式是“家族公有制下房族股份制”;二是罗认为清代中期林业纠纷一般由寨老解决,徐晓光认为官府已经介入到林业纠纷,并“最后裁定”;三是认为清代司法已经到达苗疆,“村规民约”所规定“送官纠治”就是依据。地方官府往往将“送官纠治”案件“回批”乡村按照习惯法处理。这体现了国家司法对习惯法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