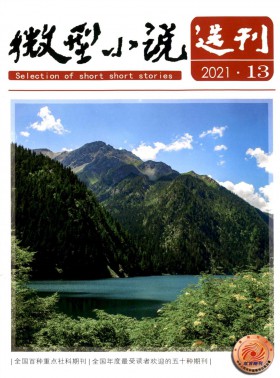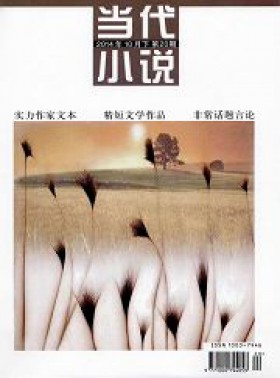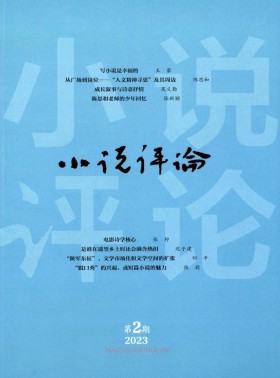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小说改编电影作品讨论,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的“姻缘” 1895年电影诞生,五年后的1900年,梅里爱早将《灰姑娘》搬上银幕,缔结了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难以割舍的“姻缘”。从梅里爱“粘贴”式的改编文学作品起,到如今,据统计,世界各国每年生产的影片50%———60%以上来自改编。作为同是叙事作品的文学与影视,都要展现环境和情节、叙述事件,并且都以塑造形象来作为自己艺术形式的本质。在我国,电影最早的观念是“影戏”,所以在电影的拍摄中,则会根据戏剧原则和舞台形式来进行拍摄。 而在改编的过程中,最强调的原则就是“忠实”。现在,则由最初强调的“忠实”进步到了发挥作品价值的“自由”阶段。80年代,以谢晋为代表,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有选择的谨慎而自由的添加入创作者的艺术审美趋向,保持了原作故事的基本形态,如《芙蓉镇》等作品取得一定成就。 二、先锋文学与当代影视结合的广泛性 时下,在这个崇尚于独树一帜、热情于标新立异的年代所探讨的文学作品里,“先锋”一词,常常被放置在一些夺目的位置上,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先锋文学的锐气、不确定性、和流动着成长的过程足够吸引人们的眼球和思想。洪治纲在《审美的哗变》中指出:“作为一个概念,‘先锋”以一种时间上的一维性永远观照着走在最前列的艺术潮流。”这就需要研究当代文学的我们,时刻保持着对先锋文学的高度敏感性,将“泛先锋”和伪先锋排斥在先锋文学的范畴之外。用审视的态度警醒于先锋文学以及由先锋文学所引发的一系列创作。[1] 近年来,将文学改变成影视作品的现象更可谓是蔚然成风,从王朔的《渴望》、《永失我爱》、《编辑部的故事》,到柯蓝的长篇纪实散文《深谷回声》(改编成电影《黄土地》),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改编成电影《菊豆》),再到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红高粱》、刘震云的《手机》等等。由于先锋文学的叛逆性、敢于对传统的挑战个性,所以在被改编成的影视的文学作品中,又不乏优秀的先锋文学作品,而在这其中,苏童的作品,可以算是改编成影视作品最多的先锋文学作品。[2] 三、影视作品对苏童小说的再创造 我个人认为,苏童是众多先锋作家中,最具有“先锋味”的作家之一———他把自己对社会、生活、生命的体验毫不吝啬的容于作品之中,用犀利、认真、又略带调侃的笔触,展现出作家对小说中人物的迷失于宿命、孤独于命运、渴求逃离既定宿命的自我理解,为人类精神家园寻求一个必不可少的伊甸园做出了作家自身的不懈努力。如,在充满了苏童对生命意识的强烈召唤的《1934年的逃亡》里叙述了“我”的祖父辈逃离枫杨树故乡的经历,祖父陈宝年于婚后七日离家出走,在九百里外的城市落足,并成功地开设了竹器店,当他们把全部的生命热情溶入城市,才意识到城市并不是他们生命的最终目的地;写实小说《肉联厂的春天》里有了现实的影子。主人公金桥爱干净整洁,一心向往着外交家般的生活,但他偏偏陷身于腥臭、油污的肉联厂;《少年血》中流动着少年人粘稠的血,表现出少年人的反抗的孤独意识;《刺青时代》里的少年小拐,因为仇恨使他忍受了成人都难以忍受的苦痛,在自己身上尝试多种方法刺青,阴郁古怪的他从习武称霸到孤僻幽居,流淌在他血管里的血液是倔强且粘稠的。 1.《妻妾成群》与《大红灯笼高高挂》 苏童的作品最先被改变成影视作品的是由其成名作《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篇小说《妻妾成群》1989年问世,小说的核心意念是由“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主人公颂莲是个受过教育的女性,父亲去世后,迫于生活的无奈,选择嫁入有钱人家,做了四姨太太,从她进入大院的开始,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她处于一个恐怖阴森、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为争一席之地,颂莲的个性在这种生存环境下有了惊人的体现。颂莲在自己遭受色劫后,也去害了他人,在自己的心灵被洗劫一空后,终究疯癫起来。苏童的文字非常细腻精致,他深入了人性的深处,用他丰富的笔触,悠扬而沉痛地体现了女性身心微妙的地方,在人物的行为活动和心理活动的刻画上具有强烈的洞察能力和先锋意识。 在改编的过程里,张艺谋将苏童作品里的细腻阴柔转为一种波澜壮阔的刚烈。苏童作品中的故事留了下来,而气氛和思想却完全改变。由于导演张艺谋重视题材的市场化原则和观众心理,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而忽视了体现社会和女性身心的作品思想意识,残忍的杀害了苏童的先锋意识!却忽视了先锋文学作品本应该具有的社会功用。苏童笔下的婉约内敛的江南风情,变成了激烈斗争的北方豪爽;江南阴柔腐朽的陈家花园,移到了中国大西北气派的乔家大院;娇小任性的颂莲,变成了高大刚烈的“我奶奶”巩俐。张艺谋把原本悲凉凄惨又略带优柔白描的小说,改成了波澜壮阔、妄图从其中窥视整个中国旧社会的恶毒的电影。最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张艺谋在电影中杜撰了挂灯笼、点菜、捶脚等小说中没有的情节,他让大红灯笼的“挂”和“落”作为各妻妾的地位,和对其他各房关系变化的象征和标志。 各妻妾的荣辱宠幸,失宠遭贬,皆集中表现在这点灯、灭灯、与封灯上。就算是捶脚、捏肩、点菜这样一系列程式化的动作也是与点灯息息相关的,在哪房太太的院子里点等,哪房太太就有权利享受生理和心理的满足感和快感,小小的陈家后院,俨然在他的篡改中,阔大成了皇家后宫。变得世俗又难以理解。我们必须承认,张艺谋能始终清醒地坚持从小说中吸收创作的灵感,挖掘叙事的素材,且选择的都是当时影响不大,而故事性很强的“俗”文本,但这只简单着眼于电影的娱乐性和观赏性,使芸芸大众普遍能接受视觉的愉悦,却不能深入解读小说对女性思想的体现,甚至将其完全改变。#p#分页标题#e# 夏衍当数我国电影改变理论方面的权威人士,他认为:“假如要改编的原著是经典的著作,如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这些巨匠大师们的著作,那么我想,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力求忠实于原著,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作,也不该越出以致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可见,这里所强调的“忠实于原著的精神思想”,已经进步于“忠实于原著文字”。但是,张艺谋背负着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枚炸弹,从空而降,不仅没有“忠实文字”,更不要说“忠实于思想”,他用这枚炸弹袭击了先锋作家,袭击了苏童,袭击了先锋文学!许多人,先认识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后知道苏童的《妻妾成群》,文学要依靠影视来做广告是多么的可悲!张艺谋用绘声绘色的影视作品将先锋文学在“精神上的超前”和“对社会、人生的本质体验和理解”残忍的鞭笞了,并且使得《妻妾成群》将死于影视的淫威之下。张艺谋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站在时代及其文学前沿的先锋文学“剥皮抽筋”,落的只剩下个空空骨架。让看过《妻妾成群》后再看《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人们,倍感对影视的失望和对先锋文学的同情。我们欣赏《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色调的使用和演员对人物形象理解的独特塑造,但是,并不赞扬它对先锋文学的任意撕裂和剥夺其思想意义的篡改,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杀害了先锋作家的先锋意识! 2.《米》与《大鸿米店》 苏童的代表作品之一的长篇小说《米》被改编成《大鸿米店》,是先锋文学遭袭于影视的另一体现。黄建中导演的《大鸿米店》由于影片所表现的晦涩、暴力、残忍的情节在雪藏七年后,于2003年上映。主人公五龙是农民,逃灾到这个小城,受到所谓城里人的欺压和凌辱,但他有顽强的生命力,他懂得什么时候低头,甚至叫人家“爸爸”,懂得委曲求全,同时心中又有强烈的仇恨,就像阿宝所说:“看到你这一双眼睛我就知道,你将来比我更狠。”五龙富于心计,心狠手辣,他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一切的人,这种方式便是最原始的赤裸裸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懂得枪秆子比大米重要的道理,换到革命的年代,他或许能成为万人景仰的英雄。同时,他的身上又有着不可改变的奴性和小农意识———绮云为他断辫,他认为这辫子授之于父母,是父母的精血;他贪恋绮云的美色,最终又嫌弃她为烂鞋,而又强奸她的姐姐织云作为补偿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他从前穷的只有烂命一条,得势之后却强迫牙医拔掉真牙,镶上黄灿灿的金牙,他要用满口的金牙来跟别人说话!电影里五龙形象的塑造在表面上看是成功的,但是在展现五龙这一人物的变化的过程节奏显的太快,让人分不清,这一切究竟是五龙的天性使然还是在残酷的生存状态下人性的扭曲?读过《米》的人都知道,《米》讲述了五龙为米而来,他的灵魂却葬于黑色的米中,五龙带着小人物的恶毒和饥饿造就的仇恨来到米店,用他的执著和阴鹫、顽劣和狠毒雕琢了他充满屈辱、劣迹、欲望,贪婪和报复的一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较之于电影,更加丰富和饱满,《米》不仅塑造了五龙、绮云、织云等人物,还塑造了抱玉、乃芳、柴生、米生等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在打造五龙对于米和女性痴迷的同时,也是在讲述一个农民的屈辱的“奋斗史”。这些都是影视未能做到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观点认为苏童的《米》“完全是一种世俗化的写作”,认为他创作的《米》是“为影视导演寻找廉价原料的殖民矿产输出”。其实,苏童正是在这种“世俗化的写作”中,淋漓尽致的展现小人物在时代大背景下努力抗争,企图逃脱既定宿命悲哀。而在影视中,这种抗争却被暴力、残忍、欲望冲淡了,甚至消散了。或许有人认为,在《米》中,全部是社会的黑暗、暴力、情欲、毁灭,通篇没有一丁点明亮,认为苏童遮住了善,只一味地写心中的恶。可是,先锋文学的实验性、探索性被忽视,这就决定了它不容易被大众所接受,而社会对先锋文学的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主人公五龙真正是个生于屈辱死于仇恨的人。当他为食欲、性欲所煎熬时,生命的张力被践踏和羞辱。 一个农民的尊严被畸形的激发了。而《大鸿米店》抛弃了主人公五龙的后半生,放弃了对抱玉、乃芳、柴生、米生等许多鲜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无视了小农民在其奋斗生命中的精神内蕴。与践踏、羞辱有关的影视作品很多,《大鸿米店》继承了小说的无主观评价色彩,对五龙不美化也不刻意丑化。而在任性斩断的“后半生”里,五龙屈辱的“奋斗精神”被遗弃了。我们发现,《大鸿米店》里,文学作品的先锋意识在不断的苦苦挣扎!遭袭于影视的先锋文学,在影视的强大攻击下,失去了作为“先锋”对传统的反叛性和对现实的不相兼容性;使得那些才华横溢、头角展露、在驾御语言文字的能力方面绝对胜过“张艺谋们”的文坛“先锋们”,无奈的扼杀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商业化所带来的挤压使作家难以静下心来写作,他们会在写作之前就要考虑作品被接受的可能性。真正的要改变这些现象,我们的先锋文学就要先于影视而生,先锋文学作家要用一种献身精神,用自我的信仰、精神品格和人性力量,努力在影视追求的票房收益、商业运作的操控下,迅速并且决然的站立起来,奔跑在时代及其文学的道路上,力争使自己永远处于时代先锋的位置上。 3.《娴的故事》与《茉莉花开》 在经历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任意剥离撕裂后,在面对了《大鸿米店》的随性斩断遗弃后,苏童的先锋小说《娴的故事》再度被搬上荧幕———章子怡主演的《茉莉花开》在经历三年的是是非非的官司之后,终于粉饰登场。导演侯咏再次用《茉莉花开》袭击了当下的先锋文学。他认为,此片不仅讴歌了中国女性的坚强和隐忍,更主要的是他让中国人看见支撑起东方都市的真正力量所在。而苏童的《娴的故事》讲述的是反映一家三代女性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分别发生在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独特视角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变迁和女人的命运。除了主人公名字有些变化外,《茉莉花开》基本忠实于苏童的原著《娴的故事》,遵循了其想要表达的妇女在时代畸形压迫下追求自我的奋斗精神。电影更强调了小说《娴的故事》中的史诗感,突出了人文情怀,而在角色上由一个人兼任的做法,是不同于常规的大胆创新,一个人在三个历史环境中演绎三代人打动人心的故事,这种“连环结构”更值得关注和期待。关于花在滂沱大雨中生子的镜头添加,多少使得导演自称自己这部电影是“简约主义”而在突然间变的突兀和无根据起来。#p#分页标题#e# 但是,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侯咏设计的结尾却是令人震撼的,他让我们看见了在这座阴柔城市里得以延续的力量所在,雨后,生生不息!虽然有些突兀,却不碍于整部电影对先锋文学所要表现的对传统的反叛性和对现实的不相兼容性的体现。对于西方电影而言,电影的功用是产业第一,艺术次之。但相对于中国电影,时代的大环境决定了其功用的教化为首,艺术次之,商业第三的排列。《茉莉花开》是近年来改编先锋文学比较精准的电影,侯咏在《导演阐述》里说:“情节剧的准则,创造非情节剧的风格。从而增强影片的非现实感和寓言性。有意识的在叙事与抒情、表象与意象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的确,他做到了。[3] 侯咏牵着《茉莉花开》的手,奔向先锋文学,二者重重地撞了个令人惊喜的满怀!先锋文学在《茉莉花开》的袭击下,痛苦的复苏、存活!我们在侯咏的思想里看到他借《茉莉花开》之际,将苏童及其先锋文学重新的擦拭了一番,让我们更加清晰的感知到了先锋文学在文学创作中不可代替的重要性和站在时代前沿的先知性。我们也从中体会到,在先锋文学遭袭于影视之后,才有了更加闪亮于时代前沿的可能性。 四、总结 虽然小说改编成影视,许多作家对此往往采取回避或箴默不语的态度,作者有时只能眼看着作品被人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东西,但小说毕竟是自己的作品,面对一部从精神内涵上被抽空的作品,原作者至少有权利站出来说句不满的话。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为导演、编剧们提供的素材,它同电影一样具有教化、艺术和商业的功用,“影视话语霸权”是眼下影视作品的硬伤,并且沉重损伤了文学的个性和作家创作的积极性,只有合理的讨论空间,有真正具有改编才能的人出来,将文学和电影这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在某个相交的平台上融合构造起来,才能促进文学作品影视改编水平的提高,才能使得先锋文在遭袭于影视之后,开出更加绚丽的文学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