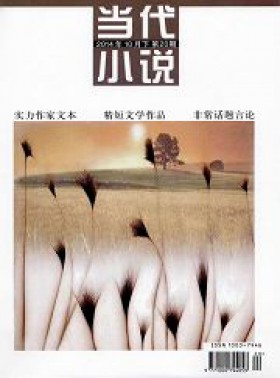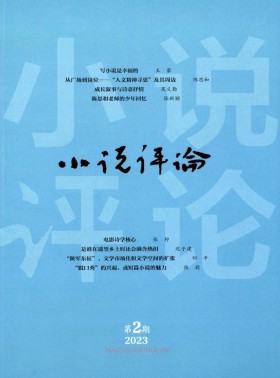随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推进,小说的创作发生了变革性的突破发展,作为独特艺术手法的“陌生化”和“虚构性”在现当代小说创作中更是不容忽视,它们是小说本体论的再现,是小说的灵魂,对其二者的区别探究很有必要。下面就其简要作一阐释分析。 一、“陌生化”与“虚构性”的概述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维克多•鲍维奇•什克洛夫斯基在191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词语的复活》中提出了“反常化”,(或译“陌生化”,“奇特化”,“尖锐化”等的理论)。后来,经由布莱希特、马尔库塞等人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充实,将其发展成为认识艺术创作规律的一种视角和切入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陌生化理论。简单地讲就是把人们日常熟视无睹的事物使用扭曲变形的方式,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重新唤起人们对它的审美感受,进而对麻木钝化的生活有更清晰深刻的认识。“虚构”顾名思义就是“虚假”、“装假”、“假装”,这近乎是其广义的意义,而本文探讨的“虚构”则是作为小说的本质特征的虚构,它历来被文学所强调。可以简单理解为作家把自己的经验生活化入小说的虚构形态,也可以是把可能的生活化为虚构,为读者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二、二者的异同关系 陌生化是西方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乎引领了整个小说创作,无论是题材、情节还是人物塑造等,无处不有陌生化的影子。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陌生化像一条没了尾巴的狗,跑遍了全世界,几乎有形象的地方,就有陌生化。而虚构性作为小说的本质特征,也有其独特关键性的作用。在西方,有许多的艺术家对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强调。普鲁斯特十分明确地指出:“没有一件事不是虚构的。”[1]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何塞•塞拉在其《虚构与自由》一文中说:“我们有思想,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在这个与经验世界相对的狭隘的意义上,自由的思想可以理解成虚构。一向连胡言乱语都算不上的东西自从有了虚构,竟能登大雅之堂,而虚构的能力也因之摇身一变,简直可与思想及自由并列为人的属性的第三成员。”[2]可见,虚构在小说创作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跟陌生化一样,总是出现在我们周围,使我们有意无意地参与或是接受着各种各样的虚构。下面就其二者的异同关系做一详尽的论述。 (一)内涵性质的差异 陌生化是小说创作的根本方法和艺术技巧,作者创作时,从小说题材、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塑造上采用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创作,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和变形,打破常规的表达和描述,使读者摆脱阅读的机械自动化,对文本获得新的审美体验和思考认识。带给读者初始的审美愉悦,不断超越读者的期待视野,从一个惊喜到另一个惊喜。这种陌生化背后产生的审美体验总是会伴随和生成新的意义,为小说创作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正是为了恢复我们第一次讲外语或是写毛笔字的感觉,一个充满震颤和新奇的瞬间,而以后只是无意识自动化地失去了感觉的重复。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特征,它不容忽视。小说的虚构往往是作家把观察到的,认识到的,想象到的,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或是未来的,甚至是另类的事物根据作家自身的经验想象加以夸张的笔墨去营造出一个使读者经验难以企及的世界。很多时候,虚构是建立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可能世界中,即将会出现在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它使读者更多地感到那是生活的部分写照。 (二)语言的作用不同 语言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小说语言中融进了作品的内容,浸透了作者的思想。在陌生化中,变异的文学语言是陌生化应用的方式手段,因为陌生化正是运用了文学语言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和歧义性特征,打破僵化的语法进行创作。例如莫言的“高密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纯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些看起来搭配有些不合理的五组肯定与否定并列在一起的词语,却通过作者对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处理,获得了新的表现功能。这种不同寻常的语言,拓展了语言的艺术表达力,还增添了新意和活力,使读者耳目一新,百读不厌,真正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所在。而在虚构中,是那些变异特殊的文学语言决定了虚构。因为文学语言的那些特殊特征,使作家不能运用这些符号去准确真实地描述表达事物,无法实现原初的真实,不得不进行虚构。再者,文学语言还是情感性的,“文学语言远非仅仅用来指称或说明什么,它还有表现情意的一面,可以传达说话者和作者的语调和态度。它不仅陈述和表达所要说的意思,而且要影响读者的态度,要劝说读者并最终改变他的想法。”[3]小说中看起来栩栩如生的事物,都是虚构性的。 (三)作者创作动机的差异 陌生化不仅仅是给读者带去审美愉悦,使其摆脱自动化的束缚,还促使作者在认知和创作的过程中,摆脱自动化的生活模式的制约,这种制约不仅涉及作家对于创作风格和形式技巧上的更新突破,还要求作者在经验上的反省和重组,而不仅仅是把自己的经验遭遇单纯地复述,机械化地组织材料,而是一种加工创造。作者之所以陌生化创作,是创作的内在要求,读者在传统的小说中待得太久,难免会厌倦而失去阅读乐趣,这就迫使作者别出心裁,匠心独运开始新异的技巧创作,会暂时抚慰读者阅读烦躁,使他们重新感受惊奇震颤的审美阅读瞬间。而作者虚构小说时,通常是为了弥补他之前生活中的缺憾和伤痛体验,因为当时种种原因和条件限制,作者没有实现得到某些东西,所以在小说创作中会充分展开想象,尽量虚构出能补偿缺憾和伤痛的情景。或者是,作者不能满足现状或是未来所会拥有的,在现实中受限,而在小说中尽量发挥主体自由去满足那种精神需求。 #p#分页标题#e#
(四)共存“真实”因素 无论是小说陌生化还是虚构性,都存在一定的真实因素。在小说创作前,小说运用陌生化手法是打破日常生活的机械自动化,给读者呈现新异的形象,带给人一种独特的审美愉悦。作者运用夸张变形等陌生化的艺术手法写小说是为了表达一种深层本质的真实。例如宗璞在《小说和我》中写道:“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经,却求神似。”[4]小说的虚构亦如此,虚构也是作者对日常生活进行重组使其面目全非,这面目全非背后就是作者所要反映的客观的真实。余华也曾说:“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5]在小说创作后,同样存在艺术真实,陌生化或是虚构性使读者进入到作家审美的预设后,这些预设情景的表现会使读者深感真实,把陌生虚构的主体还原为真实的表体,把读者带入一种艺术升腾和超越的审美体验中,那在现实生活中虽是边缘地带,可却是文学魅力的核心。这两种多面镜地呈现生活真态,都会使读者多角度地思索变化着的生活,也别有一番情趣和韵味。 三、结语 总之,无论是“陌生化”或是“虚构性”,都是作家创作小说的必备的艺术技巧和方式,我们既要区别二者的差异,也要把握它们的联系,综合运用。二者在小说创作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是作家创作的热情和力量,无限地延长了作家的创作生命和作品的审美体验,它们为小说创作注射着新鲜的血液,使我们看到了小说的光芒,感受到了其新奇独特的魅力。但我们在创作运用时,也要注意克服其阈限,不能忽视客观存在。只有客观全面地把握了这两种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创作技巧,作者才会更好地驾驭小说,创作出更多形态各异、艺术纷呈、独具魅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