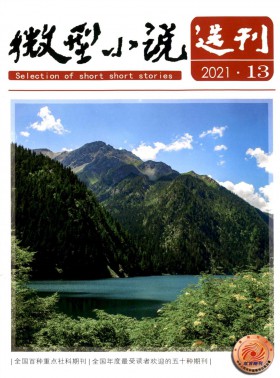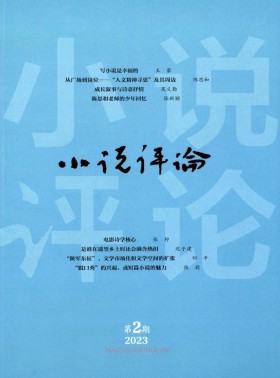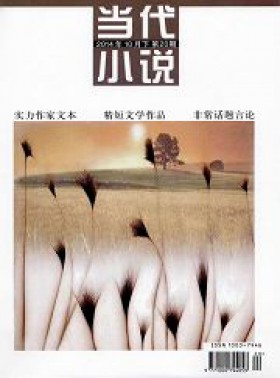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小说电影化发展探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电影自从诞生并日益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以来,选择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寻求滋养一直是创作的重要手段。尽管电影并不回避这一现实,但人们对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影视作品的水准、艺术性、思想性依然存疑,尤其是在和原著比较时。茂莱(EdwardMurray)就在其《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一书中,在列举大量事例的基础上指出,由大作家的经典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几无成功之作。诚然,因为商业利益驱动、影视创作人员的能力、素质、思想水平等原因都有可能造成改编作品的思想肤浅化、故事庸俗化、艺术商业化。但是茂莱的评价却隐然体现了一种“文学本位”,从文学出发,以文学的标准和特点来衡量影视作品,从而忽略了媒介的特殊属性导致的不同艺术形式的特性以及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必然差异。每一种艺术的诞生与发展,都必须依存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形式。而这种物质形式的媒介规定性决定了一种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属性。媒介规定性既明确了艺术的表现方式,使得一种艺术获得它的本质属性,同时又限制了艺术的表现方式,使得一种艺术只能是这一种艺术,只能在这种艺术本质属性许可的范围内探索和进步。一莱辛曾在《拉奥孔》中探讨过因媒介属性不同而导致的“诗”“画”差异。他用“画”来指代一般造型艺术,用“诗”来指代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并将两者的差异作了比较。他接受亚里士多德各种艺术形式的共同本质是模仿的看法,指出,无论是从模仿媒介、模仿方式,还是从艺术理想来看,两者都是不同的。他反对以“诗”的标准要求“画”,也反对以“画”的标准来要求“诗”。“在这两种艺术中,凡是对于某一种是正确的东西就被假定为对另一种也是正确的;凡是在这一种里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在另一种里也就必然是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的。
满脑子都是这种思想,他们于是以最坚定的口吻下一些最浅陋的判断,在评判本来无瑕可指的诗人作品和画家作品的时候,只要看到诗和画不一致,就把它说成是一种毛病,至于究竟把这种毛病归到诗还是归到画上面去,那就要看他们所偏爱的是画还是诗了。”①
正如莱辛所说,因为媒介属性本身而导致的差异不应苛责。小说和电影也是如此,无论是先入为主地以文学作为标准,还是以影视作为标准,以此来评价另一种艺术,无疑都是不公允的。因此本文既不坚持影视本位,也不强调文学本位,而是试图讨论文学与影视作品之间因媒介属性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同艺术特性。
为避免抽象与空洞,本文选取张爱玲小说《色,戒》作为文学文本,由李安于2007年执导的同名影片作为电影文本,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文本在模仿媒介、模仿方式以及艺术理想上的差异。而之所以选择这一分析样本,原因有二。
首先,张爱玲本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大,往往有意识地在小说创作中运用电影手法,有许多细节的场面描绘与展示,场景感极强。她的作品较其他的小说而言,具有更强的视觉性。
其次,由张爱玲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作品很多,也不乏大导演与知名编剧,结果却依然不尽如人意。例如许鞍华在《倾城之恋》中,对白流苏、范柳原二人爱情的渲染,将原著中两人的种种算计一概消弭;又如邹静之编剧的电视剧《倾城之恋》,更是将白流苏塑造成了抗日斗士、战火纷飞中的巾帼英雄。在张爱玲的诸多影视改编中,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算是张爱玲作品改编中少有的严谨之作。电影在人物形象、剧情安排上都颇为尊重原著,甚至于大到场景、小到道具,都极力考究和复原当时的面貌。②
一方面是小说有意识地借鉴电影创作手法,另一方面是电影严格尊重小说原著、力求展示原著真貌,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电影的《色·戒》与作为小说的《色,戒》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李安自己曾在采访中说过这样的话:“最后当看到实景、人以后,我知道我不像张爱玲了。”③这种“不像”,正是媒介规定性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艺术差异。
二首先,从媒介的使用符号和模仿方式来看,小说和电影都有着极大的差异,正是这一差异,构成了其艺术效果的不同。文学是一种时间的艺术,莱辛指出,“诗”所用的符号是在时间中存在的,认为的。文字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约定俗成的符号,它们通过实践中先后承续的线性的排列,并借助人的思维和想象来达到效果。文字作为人为符号,本身无法直接表现事物,而是通过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结,指涉事物,从而获得意义。而电影则不一样。虽然和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相比,电影已经有了时间性和连续性,但这都是通过胶卷一帧帧的快速运动形成的。也就是说,电影的时间性必然分割为一格格的画面。画面是电影的基础,在这一点上,电影仍然具有空间艺术的特性。“绘画所用的符号是在空间中存在的,自然的。”④“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既然符号无可争辩地应该和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互相协调,那么,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就只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而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也就适宜于表现那些全体或部分本来也是在实践中先后承续的事物。”“全体或部分在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叫做‘物体’。因此,物体连同它们的可以眼见的属性是绘画所特有的题材。”⑤电影也是如此。我们曾有没有对白的默片,我们也可以想象对白台词、音响效果极少的电影。但没有画面和影像的电影却难以想象。这也说明,造型艺术的“图画性”仍然是电影的根本属性。
而媒介符号的不同必然导致模仿方式的不同。莱辛在《拉奥孔》第八章中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有诗人描绘过盛怒中的爱神维纳斯。在诗中她的形状非常凶恶可怕,披头散发、怒气冲天、身穿黑袍,犹如复仇女神一般报复着曾对她不敬的人。而这样形象的爱神却从来没有在造型艺术中出现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就在于诗所使用的模仿媒介是文字符号,而文字符号并不直接展现事物,而是通过所指与能指的联结获得意义。因此,文字符号具有极大的抽象性,它可以叙述、可以定义、可以判断,这都是文字区别于画面的独特的模仿方式。而视觉符号(如画面中的线条、颜色、光影)却没有这样的便利。它是具体的、展示的。在电影这样的造型艺术里,虽然也有画外音、字幕这样的文字语言式的抽象的辅助手段,但其使用毕竟是极次要的。电影里的一切,人物、情节、心理活动等,莫不需要用画面来展示。“在绘画里一切都是可以眼见的,而且都是以同一方式成为可以眼见的。”⑥电影也是如此,它无法直接展示思想、概念、心理活动等抽象的东西,电影中的一切都是通过画面来呈现#p#分页标题#e#
小说《色,戒》仅仅是一个短篇的篇幅,并不长,但结构却十分精巧。从小说开头汪伪政府太太们的麻将桌,到王佳芝独自在咖啡厅等待,这一部分是一条明线。而从王佳芝的自嘲“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⑦开始,进入王佳芝的回忆,这一部分是一条暗线,不过三页的篇幅,几乎没有台词,全是从王佳芝回忆出发的概要叙述。从王佳芝与老易会合,再到结尾,才又是情节上接续第一部分的明线。明———暗———明,张爱玲花了力气描写和展示的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而对于第二部分即王佳芝等人的革命动机,则在小说中被淡化,仅仅是一个背景的交代和剧情需要下不得不作的铺垫。而这革命动机,也未见得多么崇高和悲壮,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王佳芝凭一时爱国心的冲动……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就干起特工来了,等于是羊毛玩票”⑧。
小说中这个“羊毛玩票”的过程写得非常清楚:王佳芝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什么坚定的革命信仰,她的革命激情,是舞台上情绪在现实中的延伸。“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也还公演过一次,上座居然还不坏。”⑨而王佳芝与其同学形成的这个小团体,也未见得有多么深刻的革命信仰。他们既无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以及由此引发的奋起反抗,也没有对时局的深刻思考以及通过革命行动改变的决心和抱负。张爱玲写得很清楚,这个小团体的形成充满了偶然和随机。
借港大的教室上课,上课下课挤得黑压压的挨挨蹭蹭,半天才通过,十分不便,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香港一般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人愤慨。虽然同学多数家在省城,非常近便,也有流亡学生的心情。有这么几个最谈得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团。一行人到了香港,汪夫妇俩与陈公博等都是广东人,有个副官与邝裕民是小同乡。邝裕民去找他,一拉交情,打听到不少消息。回来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有一个女生去接近易太太……这角色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⑩
而电影则不然。正如李安所说,“电影是一门落实的艺术,很多云淡风轻的东西必须翻江倒海地去做”???,在电影中他没有办法如小说一般淡淡地叙述王佳芝及其同学们的“一时爱国心的冲动”。小说可以抽象、可以概括,而电影却只能将一切“落实”成画面。如果说小说中还能通过文字看出张爱玲落笔的轻重、显隐的张力,那么电影则是不得不对所有情节一视同仁、平均用力。上演爱国剧、因岭大搬迁寄人篱下而产生的并不强烈的对国事的忧心以及的副官与邝裕民是小同乡的碰巧,这些原著中寥寥几笔概括叙述的次要情节,在电影中都必须用画面来直接展示和交代。而只要这些情节在电影中正面描绘和直接展示,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了强化和凸显。这种强化和凸显(如王佳芝主演的爱国剧上演时,观众的激动场面;又如邝裕民因哥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而导致的强烈的爱国抗战的愿望)就必然使“一时爱国心的冲动”在电影中被渲染成了更为强烈的爱国情怀,时局、战争、革命等张爱玲本不关心的东西,在原著中顶多只是个极淡极淡白描似背景的元素,就这样在电影中跃至了前台。
三媒介符号的不同决定了模仿方式的不同,而这两者又作为艺术的物质手段和形式,对媒介的艺术内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从小说与电影的艺术理想来看,莱辛指出,“在古希腊人看来,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凡是为造型艺术所能追求的其他东西,如果和美不相容,就必须让路给美;如果和美相容,也至少须服从美。”???文学的艺术理想是求真,而造型艺术的最高追求则是美。
影作为造型艺术的一种,对“美”的追求则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比起其他导演来,李安无疑已经可算是克制的。在演员形象上,他较好地遵从了原著。但电影“美”的艺术理想,不仅体现在角色形象、道具布景上等具体的物体美上,也体现在人物情感等抽象美上。而在后者的塑造中,李安却无法免俗,对张爱玲的原著做了改动,对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的情欲关系作了较大的美化。
张爱玲在小说中写得很明确,无论是王佳芝对易先生,还是易先生对王佳芝,两人之间并没有爱情。而王佳芝之所以放走易先生,并非是对其有多深厚的爱情,而不过是被爱错觉下的一时心动而已。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是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张爱玲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中明确指出,王佳芝之所以临时变计放走老易,原因是同学对她的恶劣态度,直接的触动正是这种“温柔怜惜的神气”给王佳芝带来的被爱错觉。“王佳芝的动摇,还有个远因。第一次企图行刺不成,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是为了乔装成已婚妇女,失身于同伙的一个同学。对于她失去童贞的事,这些同学的态度相当恶劣———至少予她的印象是这样———连她比较最有好感的邝裕民都未能免俗,让她受了很大的刺激。她甚至于疑心她是上了当,有苦说不出,有点心理变态。不然也不至于在首饰店里一时动心,铸成大错。”???而王佳芝即使“一时动心”放走了老易,但到底对老易没有抱太大幻想,并没有认为可凭老易的爱免去杀身之祸,她在计谋失败后,立即打算去一个无人知晓的亲戚家住几天,看看风色再说。
同样,小说中的易先生对王佳芝也未必就是真情。易先生本人因为权势,颇多艳遇,“惟其因为荒淫纵欲贪污,漂亮的女人有的是,应接不暇,疲于奔命,因此更不容易对付”?。起初的王佳芝对他而言不过是“跑单帮”兼“敲竹杠”、欢场女子式的人物。而刺杀事件过后,老易一边感慨“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一边清醒盘算得失、布局反扑,“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统统枪毙了”???。易先生出于对自己身家性命和前途的考虑,恩将仇报杀了王佳芝,还自诩为男子汉大丈夫的行径,并且自己说服了自己:#p#分页标题#e#
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而正是通过这一段,易先生阴暗的心态和变态的情感跃然纸上,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毛骨悚然’正是这一段所企图达到的效果”???。
而电影《色·戒》则不同。电影几乎完全改写了两人之间的关系,经过一系列的设计和铺垫,彻底将其二人之间的情欲和算计美化成了爱情。李安谈到他对《色,戒》的理解时曾说:“它还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还是由色生情,情里生爱,这是人很自然的心理取向。”???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李安在电影中增添了许多小说中没有的情节,花大力气敷演出一段战争大背景下的乱世爱情传奇来。第一个阶段,是王佳芝与老易在裁缝店、西餐厅的暧昧和试探、挑逗和追逐。第二个阶段,李安设计了三场情欲戏,两人之间从施暴与对抗,再到投入和厮缠,是为“由色生情”。第三个阶段,李安化用了《马路天使》中周璇三唱《天涯歌女》的场景,王、易二人在这一情节中“由情生爱”。买戒指也从原著中的“敲竹杠”,变成了由老易主动提出,并预备把戒指作为信物,为两人感情作个见证。接下来,影片中王佳芝放走老易就不再是“一时动心”、事出偶然,而是出于对老易的情感有意识的选择。而在刺杀失败后,王佳芝对老易也仍是抱有幻想的,小说中王佳芝去的是无人知晓的亲戚家以求避祸;而电影中王佳芝要去的则是福开森路老易与她幽会的公寓。电影中更有一个细节,当封锁开始,王佳芝被困在封锁线内时,她拿出了之前准备的毒药看了看,随即放弃了服毒的打算。可见这时的王佳芝对老易仍有幻想,希冀凭老易的爱而得以幸免。而电影中对易先生的塑造则更是与小说不同。结尾处,老易似乎动了真感情,在下令处决王佳芝时,他双手颤抖、脸色苍白;回到家里时,他又在王佳芝生前住过的房间里默然垂泪。这和小说中,王佳芝默然死去,易先生在一片喧笑中清醒算计又沾沾自喜的情形完全不同。至此,小说中完全看不出爱情端倪的两人,被彻底塑造成了相爱至深的男女;电影对王、易二人情感关系的美化完全偏离了小说中的轨迹。
张爱玲是一个对自己的创作有着高度自觉和深刻自省的作家,她在《烬余录》中曾有这样一段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
这恰是她对现实的认识,也是对小说创作的态度。她的小说是致力于表现这种“混沌”的现实,这种日常的混杂的。在《自己的文章》中,她曾表示,与其他“弄文学的人”所重视的人生“飞扬”“斗争”的一面相比,她自己要更重视人生“日常”的一面,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与“传奇”相比,“平淡而近自然”更能符合她关于写作的艺术理想。张爱玲的写作目标,总是在于将传奇还原为日常、将宏大祛魅为凡俗,她既无意于创作戏剧化的传奇式的情节,也无意于将人性的复杂与庸俗进行美化或拔高,尤其不愿将男女之间的包含了算计纠缠的种种情愫凝结和升华至爱情这一主题。
小说也许可以这样做,但电影等视觉艺术却比较难。
观众可以接受小说中形象的丑陋、情感的丑恶、道德的匮乏,因为文学求真的理想使得它致力于追求的是趋近并展示现实中可能的真貌;并且文学和视觉并不直接相关,所以对大多数小说的读者而言,文字描写中的“不美”和“丑”并不能直接激起他们审美心理上的不适感。但是,造型艺术则直接诉诸视觉,如果这种“不美”和“丑”忠实地表现在造型艺术中的话,会在视觉中得到强化和凸显,从而引起心理上的恶感。所以,即使如李安这样严谨的导演,也不得不在电影中美化二人的情感。小说读者也许可以接受王、易之间夹杂了算计的情欲关系,但这如果原样照搬到电影中,只会让观众觉得晦暗的残忍和冷酷。因此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不仅是服装道具、场景布置和演员形象(包括演员的外貌和造型)倾向于“美”,甚至于剧中角色的性格情感命运,都必须统和在对美的追求下。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这样一段话:“艺术自有其奥秘,其叙事的形式完全不同于戏剧的形式,我甚至相信,对艺术的各种形式来说,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种种艺术思维,因此,一种思维绝不可能在另一种与它不相适应的形式中得到体现。”
?也就是说,每一种艺术,都必须符合它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种艺术其本质属性正是来源于它所依存的物质形式。语言文字之于文学、线条颜色之于绘画、胶卷画面之于电影———这些作为物质形式的媒介手段,既明确了艺术的表现方式,使得一种艺术获得它的本质属性;同时又限制了艺术的表现方式,使得一种艺术只能是这一种艺术,只能在这种艺术本质属性许可的范围内探索和进步。小说和电影,也正是如此。因为模仿媒介的不同,导致了模仿方式各异;因为媒介与方式的各异,导致了艺术理想上的区别。这种差异与区别深深地植根于小说或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规定性之中,因此难以避免。
所以,在评价和判断这两种艺术时,我们需要正面其差异,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以一种艺术为标准来要求另一种显然是不明智的。对小说来说,它虽然也可以描绘和展示,但文字的种种意象仍然需要借助读者的想象力,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小说也具有电影一样生动的视觉效果。
相应的,对电影而言,虽然有思想有深度的佳作在整个电影史上并不缺乏,但电影毕竟是通过画面来展现,它必须舍弃很多通过文字语言来揭示的思想。布鲁斯东曾指出,“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电影可以安排外部符号让我们来看,或者让我们听到对话,以引导我们去领会思想。但是电影不能直接把思想展示给我们。……电影不是让人思索的,它是让人看的。”#p#分页标题#e#
?其次,在进行小说或是电影创作时,则需要各自坚守其艺术准则,而不是轻易迎合他种艺术甚至于改弦更张。事实上,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当今影视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冲击和侵袭,指出小说已经出现了严重危机。视觉文化的渗透与影视的收编,使得小说的创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益放弃其本身的艺术特性而向影视靠拢,出现写作逆向化、技法剧本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的趋势。
?这对小说本身当然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在每一种艺术形式发展的过程中,对其他艺术技法的探索和借鉴都是正常的;但当探索和借鉴已经到了逐步放弃这种艺术最基本的规定性时,无疑已经没有了积极的意义而成为自我消解、自掘坟墓的举动。
在这方面,莫言的反思值得借鉴。莫言在20世纪90年代曾为张艺谋的拍片计划写过小说《白棉花》,也正是这次经历让他有了如下反思:“写小说的人如果千方百计地想去迎合电视剧或者电影导演的趣味的话,未必能吸引观众的目光,而恰好会与小说的原则相悖。”“我认为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决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越是迎合电影、电视写的小说,越不会是好的小说,也未必能迎来导演的目光。”
小说与电影之间当然可以学习与借鉴,但这学习与借鉴必须是在对自身艺术本位、艺术规定性的坚持下进行的;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