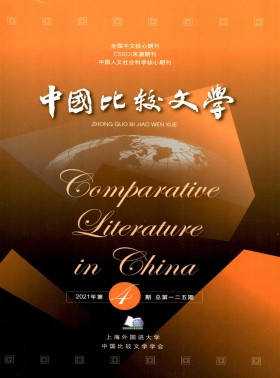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比较文学误读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罗明洲 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系
比较文学在理论上注定是要引起争议的。首先是定义之争。截至目前,比较文学没有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学科定义,虽然它不仅在国外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早已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一门“显学”。1825年,法国两个不太出名的教师诺埃尔和他的同事拉普拉斯编了一本书《比较文学教程》,首次使用“比较文学”这个名词。1827年法国学者维尔曼在巴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其后又出版一本书,叫《比较文学研究》。但他们都是只罗列史料,没有给予比较文学以明确的定义。19世纪中期,当法国出现了一批比较文学著作之后,“比较文学”在使用的层面上,意义出现泛化。在急需给“比较文学”以精确定义的背景之下,法国学者卡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1]4卡雷的学生、另一法国学者基亚也认为比较文学应是“国际文学关系史”[1]4。卡雷和基亚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贡献功莫大焉。他们从理论上为比较文学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强调了比较文学“事实联系”这一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所谓的“法国学派”的基础。二战之后,“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发难。雷马克提出:“比较文学是一国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它表现领域的比较。”[1]5雷马克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做了极为宽泛的规定:除了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之外,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研究,甚至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的范畴。
韦勒克更旗帜鲜明地要求比较文学要摆脱“从19世纪因袭来的机械的、唯事实主义的观念,注重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实行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1]5。雷马克和韦勒克的定义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突破了法国学派“事实联系”的藩篱,奠定了所谓的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基础。自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诞生以来,两国学派的争执不断。人们对两派认知的争论更是风起水生,其范围和影响远远大于两国学派的争执。这使比较文学界空前活跃,表现出了比较文学的张力和活力。与此同时,又使比较文学这潭浑水越发清浊难辨。法国学派注重历史性和科学性,主张比较文学应该摆脱美学的涵义,取得科学的内涵,使比较文学学理缜密、方法严谨,因此这种研究多适用于国际文学交流史或国际文学关系史。事实上,他们的研究确实为文学史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学派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文化精神生产,而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内所产生的文学,必然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比较文学研究不必一定拘于文学现象的事实联系,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从而更深刻地多方面了解文学的本质和价值。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现象具有“可比性”,即可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不考虑它们之间到底有无事实联系。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克服了法国学派研究中近乎于考证、过于苛求史料性的缺点,弥补了法国学派忽视美学价值的不足。由上可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优点。虽然它们为维护各自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而多有论争,其实在他们的定义表述和理论阐发中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比较文学的追随者和爱好者们不愿意实际上也不可能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得瓜清水白,着意遵循某一个学术标准,他们的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是兼备二者之长,为我所用。
其次是名称上的名不副实。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术界内部还是在学术界外部,都可能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就翻译过来的意义上解释,“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组合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偏正词组。就语法上来说,“文学”作为中心词,“比较”是修饰成分。进一步做一般性理解,比较文学在字面上的意义往往被理解为“比较的文学”。还可以理解为:动词“比较”作谓语,名词“文学”作宾语,把比较文学理解为一个动宾词组。由此,比较文学就可以误读为“对文学进行比较”。不管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甚至时至今日,不管中外比较文学学者多么煞费苦心地在理论上对比较文学作解释,并不能够阻止人们把“比较文学”当作是“比较的文学”或者是“对文学进行比较”。多少年来比较文学界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1997年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院院长巴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有学者提问比较文学究竟“比较”什么?巴柔诙谐地说:“我们什么也不比较,幸亏我们什么也不比较。”[2]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认为,比较文学不在于“比较”,而在于“汇通”。[3]照他们所说,判断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不在于它们是否使用了“比较”两字,而在于它们是否对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了体系化的、内在性的汇通。而恰恰相反,那些不仅在标题上还在内容上反复利用“比较”进行相同性或相异性研究的分析者,根本不是或者不是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看来,比较文学代表了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它要求以国际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全球观念和开放意识去进行文学研究。它试图突破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从更大的范围来洞察文学的特质。
比较是一种学术视域,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一种内在的汇通性透视。这就决定了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问题在于,“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多少还是带有人为意味的,它超越了人们业已习惯的思维定势。“比较文学”再怎么看,也要和比较相关。硬要把它赋予既新颖又深奥的内涵,确非让人一下子就能完全接受。按照一般的习惯思维:名实相符才称之为名。人们不禁要问,若“比较文学”不可以“比较”,为什么要用“比较文学”冠名呢?在这里有一个悖论:比较文学的名称不太恰当,但已约定俗成,目前在国际上仍在使用,并且没有废除的迹象。也许能寻找一个比它精当的词取而代之,但可能会引起新的更大的混乱。再次,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表面到实质的过程。诺埃尔、拉普拉斯以及维尔曼时代,比较文学仅仅是泛泛之谈,连学科意义都没有。法国学派的研究从理论上为比较文学确立赢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他们排斥对作品的价值评价。美国学派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但一些研究者对“可比性”的认识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简单比附。随后的苏联学派特别是中国学派的崛起,把比较文学中的阐发研究、跨文明跨文化的理论研究引向了纵深。可以说,比较文学在不停的争论中诞生,在不断的探索中成长,在不止步的拓展中成熟。鉴于上述,对比较文学“雾中看花”、“远看成岭近成峰”,也是自然中事,以至于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曾经把“比较”错误地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方法论。#p#分页标题#e#
像这样一位拥有国际名望的学者对比较文学尚且产生错误的理解,更遑论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在中国,比较文学曾长期被误解。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1978年以前,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高潮迭起之时,比较文学却被排斥在中国学术领域之外。二是在1978年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比较文学一下子受到学术界的热捧,并长驱直入地进入大学本科课堂,继而又逐步建立起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教学体系,出现了许多适应各种需要的教材和专著,数不胜数的比较文学论文见诸各学术刊物。诸如中世纪西方文学与中古东方文学比较、中西爱情诗比较、中西山水诗歌比较、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之比较、高加林与于连、杜丽娘与朱丽叶之比较、渥伦斯基与周萍形象分析、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蔡大嫂和包法利夫人之比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美学比较、《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拉》之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等比比皆是、屡屡翻新。它们有些出自大家之手,像学术界精英、外国文学领域宿将、比较文学界元老,甚至还有文坛大腕也多有染指。此类文章在《文艺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中国著名学术杂志上屡见不鲜。此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研究的着眼点滞留在表象上,着意去寻找两个文学现象的类似性与差异性:双方不同之处是什么,相同之处是什么,分析其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随后便是将上述两种归结为“社会背景”和“民族特性”的同异,也即所谓的“X+Y或者X与Y”式的比较研究,一种简单化的个体与个体之比或是简单类比。使比较文学陷入到“诗学比较”的窘境。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起了学术界大规模的攻击,遭到学术精英们的清算,斥之为没有意义。于是,“X+Y或者X与Y”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中国的比较文学实践注定要走过一段坎坷泥泞的。首先,中国比较文学要实现突围。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夜,在翻译西学极为繁盛的情况下,在中学西学孰优孰劣的讨论热潮中出现了像王国维、梁启超等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学者,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在平行研究方面的发展。从五四到建国,政治动荡、战争频仍,中国比较文学虽有长足的进展,但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建国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虽有一些文章谈及中外文学关系,也仅限于中俄(苏)文学,且少有深刻之论。“十年”中国大陆拒绝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文章几乎绝迹。时至20世纪70年代,台湾大学相继开设比较文学硕士班、博士班。香港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系,1978年香港又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恰值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形势喜人且逼人,比较文学全面复兴和突围迫在眉睫。应当说,比较文学在精英的头脑还没有揣摩透的情况下,中国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已经摆在了普通学者的面前。中国比较文学在摸索着前行。因此,相对来说便于操作并且在中国大陆有一定历史积淀的平行研究也就悄然前行,且呈一时之盛。其次,中国比较文学要凸显实绩。沉寂多时的中国比较文学枯木逢春,顺风顺水,不仅值大展宏图之时,而且有大展宏图之势。相对迟缓的大陆比较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突然释放了诸多能量:198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1995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比较文学博士后;1998-2000年,首都师大和四川大学先后创办比较文学系。冠以“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的论文、著作更是铺天盖地,难以备述。比较文学的学者精英也受这种潮流的裹挟而自觉不自觉地侧身其间,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中为比较文学研究增砖添瓦,或者以海纳百川的肚量以极其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平行研究的成果。以上表述,并非是说“X+Y或者X与Y”研究模式是机会主义的产物。“X+Y或者X与Y”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初期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模式,大多被用在平行研究中。平行比较是认识论的低级阶段,它常常是不可避免的。“X+Y或者X与Y”存在着简单对比和泛比即文学比较的倾向,但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可以要求人们不能停留在简单对比的层面上,但不可以彻底地、全面地、不加分析地否掉定“X+Y或者X与Y”。正如我们成年后不能去否定掉我们的童年,更不能以我们的成人处境去否定他人的童年阶段。已故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周翰先生曾说:“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4]这就是说,中国比较文学从来就不是仅和极少数学术精英有关的学问,而是始终贯穿着关心现实关心生活的人文主义精神。平心而论,“X+Y或者X与Y”模式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初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比较文学工作者甚至还包括现在的一些比较文学大师级的学者都是从“X+Y或者X与Y”模式开始走上比较文学道路的。
《比较文学读本》的作者王福和说过:“任何一个比较文学工作者,对‘X+Y或者X与Y’赞成也罢,贬斥也罢,他所从事的哪一项比较文学研究能与‘X+Y或者X与Y’脱得了干系呢?……对此,我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讨伐声中既感到恐惧,又感到困惑”。[5]269中国比较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北京师大教授陈?严肃指出:“只要人们承认平行研究还不失去其科学价值,那么‘X+Y’式的比较研究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对‘X与Y’式的研究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5]270不仅如此,陈?教授以《莎士比亚〈皆大欢喜〉与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林冲形象与威廉•退尔形象的比较研究》等为题,为“X+Y或者X与Y”模式呐喊助威,为那些现在正在从事或准备将来从事“X+Y或者X与Y”比较研究的第一线教师增加信心并予以支持。文学比较不等于比较文学,但是比较文学却自始至终离不开文学比较。如果文学比较再开放拓展一些视野,也就是说逐步进行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跨越学科门类和跨越文化文明的文学比较研究,就可以成为现行学界认定的比较文学水准。那么,比较之于比较文学,无疑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特征和手段以及研究思维的逻辑起点。
时下,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仍是一门“显学”,但绝非精英之学,着意铸造比较文学的神坛,人为地抬高比较文学的准入门槛只能使比较文学的道路越走越狭窄。换言之,既然文学比较是比较文学学科的逻辑起点、是比较文学学者的学步阶段、是一般比较文学追随者容易掌握的研究模式,何不给“文学比较”一定的空间以进一步发展学科优势,何不给年轻的初学者一定的信心以支持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当然,也期望对“X+Y或者X与Y”模式加以引导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使“X+Y或者X与Y”模式更符合比较文学的学理。#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