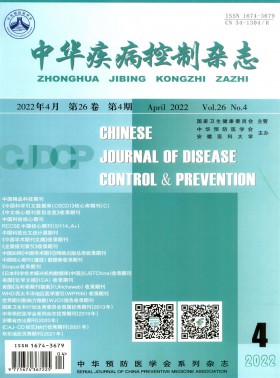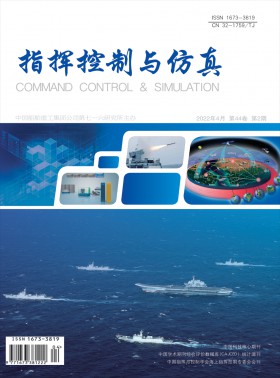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控制下交付之正当性基础,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某项侦查手段或者侦查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主要应从其是否合理与合法两方面来分析。而控制下交付作为一项特殊侦查手段,无论从合理性还是合法性来看,其正当性都是毋庸置疑的。控制下交付手段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能够适应犯罪发展趋势和特点的特殊侦查手段。从其合法性来看,它是得到国际公约肯定的侦查手段,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控制下交付这种侦查手段,但我国运用控制下交付手段是有其法律基础和依据的。
关键词:控制下交付;侦查手段;正当性;犯罪;国际公约。
控制下交付(Controlled Deliv)作为一项特殊侦查手段,最初是为应对跨国犯罪而在国际禁毒领域创设和发展起来的。在1988年联合国维也纳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首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规定了控制下交付这种做法。根据该公约的规定,控制下交付“系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麻醉药品、精神药物、本公约表一和表二所列物质或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按本公约第三条第1款确定的犯罪的人”。继该公约之后,在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都明确规定了控制下交付手段,使这一手段的运用范围扩展到跨国有组织犯罪与腐败犯罪。近几十年来,控制下交付手段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尤其是在犯罪侦查中,已成为一种十分常用的侦查手段。然而,对于这种新型特殊侦查手段,我们至今尚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有关控制下交付的许多问题尚处于“浑沌”状态,需要厘清。加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拟对控制下交付之正当性基础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问题的提出
从国家职能的角度看,国家在发现犯罪行为时,有义务立即制止,这是由国家的职责和使命所决定的。然而,控制下交付是在违禁品已被查获的情况下实施的,控制下交付手段启用的前提条件是某些犯罪行为已经开始实施、相关法律已经被违反、犯罪正在进行之中[1]。既然违禁品已被查获,该批违禁品可能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即已被切断,但为何侦查机关不当场扣押、收缴违禁品,将犯罪制止于此阶段,而冒着该批违禁品可能散失的危险放纵其继续运送?换言之,国家是否能为了打击犯罪而在相应的一段时间里放任犯罪行为的延续可能产生的风险,在犯罪实施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是否更有价值?是否才是国家的职责和使命所要求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正当性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专家学者们对此问题较少予以关注,然而这一问题是研究控制下交付手段时有必要加以探讨和明确的问题。
何谓正当性?从宏观上考量,所谓“正当性”,一般认为就是合理合法性[2]。如我国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正当”的解释就是“合理合法”[3]。所谓“合理”即“合乎道理或事理”;所谓“合法”即“符合法律规定”[4]。笔者认为,就某项侦查手段或者侦查行为而言,其是否具有正当性,也应当从其是否合理合法两方面来分析(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还涉及社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而控制下交付手段无论从合理性还是合法性来看,其正当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二、控制下交付手段的合理性
从合理性的角度看,我们认为,控制下交付手段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控制下交付是一种能够适应犯罪发展趋势和特点的特殊侦查手段。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交通、通信手段的不断进步,为人员、货物及资金的跨国往来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同时,这种大环境也促使犯罪、有组织犯罪等犯罪活动呈现日益明显的国际化态势。以犯罪而论,这类犯罪近几十年来已侵蚀到全球几乎所有地区,成为全球性公害。这类犯罪的环节具有全球配置性,世界三大产毒区(金三角、金新月和银三角)生产着全球大部分,而消费市场与产地相对分离,遍及许多国家,欧美等国是主要消费市场,由于的贩运有着巨大的非法利润,这就刺激着不法分子使他们不惜铤而走险进行贩运,盘踞在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更是趋之若鹜,大肆进行犯罪活动。面对犯罪的国际化态势,单靠一国的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即使传统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形式也难以奏效。因此,禁毒实践要求创设出一种在超越国家层次上的新的打击犯罪的侦查手段,而控制下交付正是适应这种需求而创设的主动型侦查手段。它打破了各国当局画地为牢的传统合作格局,开创了国际联合侦查、携手缉毒、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的先河。
控制下交付手段的采用,虽然表面上看在一定时间内放纵了对等违禁品的扣押,但这种“放纵”违禁品继续运送的做法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国家实施控制手段的目的在于促使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充分暴露从而将其一网打尽,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犯罪控制的法律目标。如果不采用这种手段,而是发现违禁品后一律简单地予以收缴、扣押,那么,许多等违禁品犯罪活动就只能以截获有关等违禁品为最终结果,或者至多抓获部分运送的“马仔”,而这些“马仔”对贩运集团又知之甚少,这样势必导致对犯罪打击不力,难以有效应对违禁品交易的犯罪活动,因此,这样做并不符合社会防卫的要求。而采取控制下交付这种“放长线钓大鱼”式的侦查手段,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延迟了追诉行为的及时采取,但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对违禁品流转运送过程的监控促使更多的涉案成员乃至隐藏在幕后的犯罪组织的首犯、主犯等充分暴露出来,从而达成侦破这类案件的最佳效果,大大提高对这类犯罪打击的力度。
正因为控制下交付在揭露与证实某些严重犯罪方面的独特功效,控制下交付措施不仅得到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肯定,而且联合国在有关国际会议和文件中积极鼓励和大力推广使用这一手段,诸如:在1987年联合国召开的关于滥用及贩运的维也纳国际会议通过的《管制麻醉品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指出:在国家一级“除非有关国家的宪法规定不可对法律进行修改,以允许利用控制下交付的技术,否则应考虑在事前达成双边协定或安排之后修改有关法律,以允许这一方法的使用。立法机构、有关部门或当局可遵照国内法采取必要措施授权适当使用控制下交付的技术,以便查明因中间人或携带者在被发现后立即被捕而可能没有被识破的涉及一批非法运送的受控制药物的装运、运输、交付、隐藏或接收的个人、公司或其他组织,并捉拿法办。” #p#分页标题#e#
在1998年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加强国际合作以处理世界性问题的措施》中建议各国:“根据国家之间相互同意的协定、安排和谅解,在各自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允许的情况下,确保立法、程序和实践允许在本国和国际上采用控制下交付技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还专门就控制下交付问题做出了两个决议,即2001年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形成的第45/4号决议“控制下交付”、2003年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形成的第47/6号决议《有效的控制下交付》。在这两个决议中,都积极呼吁和鼓励各国采取相应的立法等方面的措施以使这种手段得到采用。如在第45/4号决议“控制下交付”中,“呼吁尚未审查其法规、程序和做法的各国政府进行这种审查,以便得以采用控制下交付的做法”“请各国政府为有效地使用控制下交付做法订立协议和安排”“建议各国政府授权其各自主管机构促进采取迅捷而有效的行动处理控制下交付行动方面的国际援助请求,并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在第四十七届会议形成的第47/6号决议《有效的控制下交付》的决议中“鼓励会员国在必要时考虑通过关于控制下交付协定的国家法律和程序,或视情加以审查,以确保设有适当的法规、资源、专长、程序和协调机制,从而能够开展这些控制下交付行动”“促请会员国加强相应机关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以便利开展有效率和有成效的控制下交付行动”。
在联合国及其各级组织的大力倡导之下,近些年来,控制下交付手段在许多国家已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不仅已成为犯罪案件侦查的一种常用侦查手段,而且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领域也显示出其重要的运用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讲,允许控制下交付手段的实施,可以认为是法律规定的一种例外。因为根据世界各国通行的法律原则,是不允许之类的违禁品进出海关的,而且根据各国海关管理法规的规定,所有进口物品均应如实报关,海关人员同时应当彻底查验[5]。之所以法律要允许在发现违禁品后让其继续流转运送这种例外存在,不仅是因为通过对违禁品的“放行”和对此后的流转运送乃至交付过程的监控可以促使更多的涉案犯罪嫌疑人特别是隐藏于幕后的犯罪组织的首犯、主犯暴露出来从而有助于将其一网打尽,还因为控制下交付手段一般是针对贩卖、非法走私武器等违禁品交易犯罪采用,而这些犯罪属于典型的“隐形犯罪”,行为人实施的运送及交付违禁品的行为,无论是替代品或是原物的运送与交付,都因为在公安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因而基本丧失了达到法定的客观危险状态的可能。因此,在公安机关的严密监控下,交付行为即使完成,通常也不能产生法定的抽象危险状态,或者说是属于可控的犯罪[6]。
三、控制下交付手段的合法性
控制下交付手段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具有合法性。因为《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三个公约都已肯定了这种手段,而我国已加入这三个公约,根据国际法原理,这些公约都为此项秘密侦查手段在国际范围内和我国国内的运用的合法性奠定了相应的法律基础。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控制下交付这种侦查手段,但我国执法机关使用这种侦查手段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条约必须遵守”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被权威的国际文件反复确认和重申。《联合国宪章》第2条载明:“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宪章所负之义务。”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重申了这一原则,并进一步指出:“每一国均有责任一秉诚意履行其依公认国际法原则与规则系属有效之国际协定之义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条约对其当事国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条约必须遵守”还要求缔约国不能以国内法为由不履行条约义务,这在国际文件和国际司法裁决中有明确的体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规定:“一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在我国,国际条约是国家法律的渊源之一,“国家条约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不属于中国国内法的范畴。但就其通过法定程序具有与国内法同样约束力这一意义而论,也属于中国国内法渊源之一”[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1990年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所表明的态度:“在中国法律制度下,中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会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程序或国务院的通过程序。条约一旦对中国有效,在中国便有法律效力,中国便有义务去施行该条约。”[8]尽管这一表态是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所表明的态度,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上,这一原则应当贯彻到所有中国已经签署或者加入的国际公约”“国际法与国内法都同样体现了国家意志,国家既然已经庄严缔结了国际条约,就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在其领土内实施对其有效的条约。”[9]
除参加《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三个国际公约外,近年来我国与不少国家在禁毒合作、海关合作等领域签订了双边、多边和区域的协议与协定。在这些协议与协定中,也包含了有关采用控制下交付手段的内容。例如,我国先后与俄罗斯、墨西哥、塔吉克斯坦、尼日利亚等国签订了禁毒双边协议,与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四国签订了《禁毒合作谅解备忘录》,与东盟国家共同签署了《东亚和中国禁毒行动计划》,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签署了海关合作互助协定,等等。这些双边和区域的协议、协定中,大都有关于控制下交付的内容。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海关合作与互助协定中都明确规定:“如双方同意采取控制下交付以查缉涉嫌参与上述麻醉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的人,则双方海关当局应依照各自的国内法律并在其权限和能力范围内尽可能就此方面行动的实施进行合作。”在《中国海关总署和澳大利亚海关署关于海关合作与行政互助的谅解备忘录》第七条“控制下交付”中也规定有:“经请求,双方海关当局可根据双边安排允许违法或涉嫌违法的货物在主管部门知晓和监控下运出、通过或运入其关境,以便于调查和打击违反海关法的行为。如果给予此许可超出海关当局的权限,则该海关当局应尽力与有此授权的国内部门进行合作。”等有关控制下交付的内容。这些双边或多边协议与协定的规定,同样为我国实施控制下交付提供了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从广义角度看,这些双边或多边协议、协定等国际文件,也属于国际条约的范畴[10]。总之,从国际法的层面上看,我国运用控制下交付手段是有其法律基础和依据的。 #p#分页标题#e#
当然,将国际条约在国内实施,有一个如何适用的问题。综观世界各国如何将国际法实施于国内的情况,大致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转化适用(transformation),即为了在国内实施条约的内容,原则上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这便产生了国际条约向国内法的转化,英国及英联邦诸国以及意大利均属此一模式。另一种是直接适用(adoption)即不需要国内进行相应的立法而直接将条约适用于国内,当条约与国内法相抵触时,采取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11]。从我国的情况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实践中,中国没有采用第一种方式(转化制度),而倾向于采用第二种方式,即条约直接在国内适用”[12]。不过,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未对控制下交付做出规定,因而实践中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规范,虽然公安部在《犯罪案件侦查协作规定》等内部规定中对控制下交付的实施程序有所规定,然而这些规定毕竟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规范性,这就难免使得实务部门在采用这一手段时面临一些困惑,或者出现一定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一手段在实践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制,如果运用不当可能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有必要通过国家法律对其使用条件、程序及所获得材料的运用等予以明确具体的规定,以保证这一手段运用的程序正当性。
注释:
[1]P.D. Cutting, The Technique of Controlled Delivery as a Weapon in Dealing with Illicit Traffic in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Substances, Bulletin on Narcotics(Oct.-Dec, 1983)
[2] 参见唐磊、汪启和:《质疑与回应:秘密侦查的正当性分析》,载《侦查论坛》(第五卷)第151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4]《现代汉语词典》第1606、507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5]参见程雷:控制下交付手段初步研究,载崔敏主编:《刑事诉讼与证据运用》第237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参见高巍:《贩卖犯罪研究》第184、185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31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8][12]王铁崖:《条约在中国法律制度中之地位》,载《中国及比较法学刊》1995年第1卷第1期。
[9]参见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第666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0]参见赵永琛:《涉外刑事司法解析》第44-4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1] 参见陈光中:《陈光中法学文集》第664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