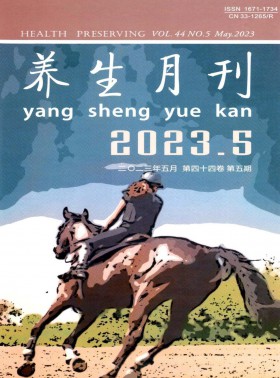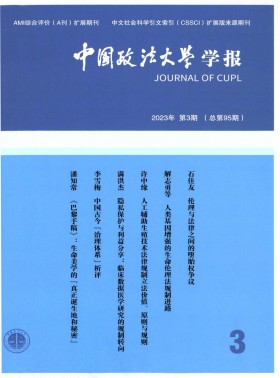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反对自由主义全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反对自由主义全文范文1
关键词:付费采访 新闻伦理 传媒市场化 有偿新闻
“付费采访”是指新闻媒体或记者为了得到某些“独家新闻”而付给被采访单位或个人一定的“报酬”。“付费采访”是当今新闻竞争日趋激烈的产物,是新闻竞争手段的一种异化,它迎合的是“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理论。
各方对付费采访的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则从新闻伦理的角度予以分析,探究付费采访的是与非。
一、付费采访引发的伦理冲突
付费采访是媒介产业化的产物,体现了媒介产品鲜明的商品性,对新闻伦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伦理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应然性认识,是个体道德与制度道德的体现形式。因而要研究伦理势必要先研究新闻道德。
1.付费采访失范的表现
付费采访本来不是就要给“一棍子打死”的事情,但由其却引发了一系列失范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乱付费采访”和“付费乱采访”这两个方面。
(1)乱付费采访
乱付费采访是指在付费采访中竞相哄抬价码,这样极易造成采访秩序的混乱,强势媒体以其财力物力支援而越来越强,弱势媒体则因无力竞争而渐弱下去,长此以往,话语权将会愈加集中,这对公众的知情权是一个极大的伤害。
(2)付费乱采访
付费乱采访是指我付费了,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要你怎么做,你就得怎么做,甚至备好了一问一答的详细台本。也就是常言的“找托”,这样一来,采访不再是采访,而纯粹沦为演戏。
2.付费采访中价值观念的冲突
(1)主导价值观与“边缘”价值观
调适社会价值冲突,首先要努力吸引各种价值观的合理因素,确立一种主导价值观,并使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义与利、理与欲等二元对立的价值观之间保持适度平衡。其次,还要承认边缘价值观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对它们采取宽容的态度,尊重人们价值取向的自由。当然,必须对边缘价值观主动地适度地进行调控,使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以确保社会既稳定又充满活力。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主导价值无疑是集体主义价值观,所以面对“付费采访”现象,我们在鼓励社会大众免费受访的同时,应该承认“付费采访”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并尊重一些人要求付费的自由,但必须认真地对之加以调控和正确引导。
(2)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
人的价值具有双重性,即人既是价值的主体,又是价值的客体。作为价值的主体,他有人的需要和享受的满足,作为价值客体,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前者是指个人通过实践去创造价值,以满足社会和他人的需要,后者指通过实践去创造价值,以满足自我的需要。个人利益的正当满足是社会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而社会利益又为个体利益的实现创造条件,二者既对立又统一。因而,只有兼顾社会和个人,才能较好地解决价值冲突,才能在冲突中寻找新的价值世界。所以,在面对“付费采访”这一价值冲突时,应该既要树立集体主义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要兼顾个人利益,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反对极端个人主义。
(3)目的性价值与手段性价值
价值总存在于现实的主客体关系之中,并通过手段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而实现。没有手段性价值的现实化,目的性价值就会变成海市蜃楼,可望不可即。同样,没有目的性价值的理想,手段性价值则会陷入盲动,导致实用主义和功用主义泛滥。处理价值冲突,必须体现现实关切与理想追求、手段价值与目标价值的统一。因此,在媒体舆论导向中必须把集体主义这一价值目标分解为一系列具体可行的价值目标,即在实践中提倡讲道德、讲奉献、讲理想。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切实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反对那种仅以一己之私利出发和损人利己的不良行为。
3.付费采访中德与法的冲突
在付费采访中,主要体现为对知识产权和劳动权的争论,赞成方认为付费采访是对采访对象个体劳动和知识产权的尊重,反对者则从道义的角度批判,认为应无偿地为社会作贡献,并且受访有利于采访对象扩大知名度,不应再收取费用。笔者在上文中已论述受访收费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只受劳动法保护,至多只能算是劳动报酬,不收费则另当别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合理处理好德与法的矛盾冲突,防止处理不当而致使付费采访走入极端。
二、付费采访下的新闻伦理理性回归
付费采访是媒介产业化的产物,较多地体现了新闻媒介的经济属性,但由于其对社会公益的忽视,引起了学界与业界长时期的争论。笔者认为,付费采访并非不可行,但是必须树立基本的可行性底线。
1.坚持社会责任论,维护公共利益
社会责任论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思想,是在1946年出版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报业》中正式提出的,它认为,报刊自由传统观念的哲学基础已被现代知识界深刻的思想革命所摧毁;古典的放任主义的经济学已被几乎所有现代工业化国家的实践所摈弃;思想自由竞争的公开市场在现代社会中不复存在。因此,它从指导思想上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包括主张政府对传播媒介进行干预、强调自由伴随着义务与责任、强调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等等。社会责任论的提出,在调节政府、媒介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付费采访也不例外,只有在“社会责任论”这一理论基础上,付费采访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2.坚持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
坚持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首要的便是坚持无产阶级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原则。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原则,才会忠于职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会充当党群联系的桥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后记
总之,新媒介生态下的新闻生产过程,使得新闻采访活动具有了经济性特征,付费采访也就应运而生了,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媒体采访是公众知情权的落实渠道,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付费采访不能无休止的蔓延和泛滥,否则必将损害新闻业的道德基石,损害媒介的市场秩序,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美】菲利普.帕特森,李.威尔金斯著,李青藜译,《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李良荣等著,《当代西方新闻媒体》,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反对自由主义全文范文2
关键词:赛珍珠 《母亲》 女性与母性 折射分析
赛珍珠《母亲》作为一部塑造中国女性形象的欧美文学著作,一经问世就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引起巨大反响,其母亲的独特身份设定,加上细腻的描写、生动曲折的故事建构,完成了生态主义视角下的女性生存权与话语权的解读。
一、赛珍珠《母亲》小说的整体概述与文学价值解读
作为赛珍珠的代表作之一,《母亲》无论文学创作角度还是社会思想解放层面,无疑是成功的。其创作时大胆采用自然主义艺术手法,文本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在细腻的文笔描摹下一位性格鲜明但又命途多舛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呼之欲出。独特的女性选材及特定的母亲身份将中国传统女性身上女性与母性的双重色彩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展示与表达,对于研究旧中国传统女性在当时社会制度与社会背景下的努力与挣扎具有指导与借鉴意义。
小说以两位母亲在炉火旁的对话点题并开启全文,年迈的老母亲扮演着旧中国婆婆的形象,而真正的主角是不断向炉火里补充干草的年轻女性,这温馨温情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农村几千年来底层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一生在辛劳中度过,心甘情愿。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国这种底层妇女的生活仿佛传承了千年,是注定的宿命,没有抗争只有习以为常与日渐麻木,几乎很少有女性去质问自己为什么要屈服于这样的生活安排,也很少有女性去思索我是否应该通过什么努力去改变什么,无一例外地都选择承受,自己的命运始终由男性操控。而赛珍珠似乎要打破这种既定的女性宿命,因此她在小说《母亲》中塑造了一个性格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在书中她没有具体的名字,她的名字就是母亲,她是千万个母亲形象的缩影与融合。同时她又是女性意识觉醒的新时期女性代表,她是生动化的个性化的文学人物,在她身上始终显示出精力充沛与勇敢有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旧中国的传统女性她逐渐摆脱了奴隶气质,当丈夫离家之后,她为了孩子选择了自己撑起这个家,因此她的身上又折射出自强自立,她始终用强大的心理暗示支撑着自己不倒下。即使是小儿子因为参与革命而被斩首,她依然没有选择向命运臣服。后来孙子的出生将她对儿子的爱延续下去,承受着命运挫折的考验。在这位母亲融汇着多种气质,敢爱敢恨,意识,对命运的挑战,对男性的反抗……但是故事的结尾仍没有摆脱悲剧的限定,带有浓郁的忧伤色彩,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母亲又是生活中的胜利者,是命运的主宰者。悲情并不意味着母亲作为女性反抗的失败,相反这种悲情意蕴的背后彰显出的是母亲作为女性与母性的双重人性光辉。
二、赛珍珠《母亲》中的主人公母性光辉的阐释与母性意蕴的解读
立足中国传统话语权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母亲话语权往往基于男性得以体现,其话语权的获取与使用带有极强的被动色彩。母亲往往是生儿育女的工具,是相夫教子的代言,是繁重家务任劳任怨的操持者,因此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对母亲对母性几乎每个人都心怀敬畏之情,因此受这种既定女性形象思维定势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形成了“贤妻良母”的女性审判标准,母亲作为母性的光辉被无限拉大。中国母亲与牺牲、奉献、忍辱负重等同起来,成为义的化身。我们完全忽略了母亲的主体意识,固执地认为当主体意识丧失才更能彰显母性的光辉与伟大。赛珍珠作品《母亲》之所以取得文学上的成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主要原因是打破了中国传统思维意识里对母亲形象的界定。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的推动下,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母亲独立的人的形象,开始关注其本能的原始的生命力与情望,因此母亲不再是完全道德化的模范典型,母亲形象才开始真正脱下神圣的外衣,让自己的人性与欲望得到充分的暴露,将自身生存状态中的阴暗面进行了话语的表达与倾诉。赛珍珠的《母亲》无疑为僵化的旧中国女性刻画打开了一个缺口。赛珍珠在着力塑造母亲这一人物形象时也不惜笔墨对母亲的母性温柔光辉进行了描摹与抒写。这位反传统的独立的母亲也依然带有温柔温馨的母性光辉。首先她有着深刻的护犊情怀,即使社会与命运对她百般折磨,但是消磨不掉她对孩子对后代深沉真挚的爱。当她初为人母之时,她都不能忍受娇嫩的孩子发出一丝丝的啼哭,为孩子的啼哭而担心担忧,一旦孩子开始啼哭,她便会丢开一切工作,去给孩子喂奶,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呵护。其次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条件的,没有丝毫的重男轻女。这也是母性温情光辉的折射。在旧中国,重男轻女思想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但是赛珍珠笔下的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公平而无私的。她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当不满三岁的小女儿患了眼病,焦急的母亲希望自己的丈夫进城卖完稻杆时能够给小女儿带些眼药来,当女儿眼病被耽误最后双目失明时,她不停地责备自己而很少意识到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当看到大儿媳妇故意欺负瞎眼姑娘时,她心理像被针扎一样痛苦。最后小女儿被迫出嫁,母亲极力反对,担心女儿日后的生活,担心女儿离开自己的庇佑后会遭遇不幸,当最后女儿惨死的噩耗传来,当她目睹女儿的遗容时,她最终无所顾忌地放声大哭将她对孩子的爱推向。最后她的母性光辉还表现在她对鸡鸭猪等牲畜家禽的关照中。母亲的爱已经超越了人与人的界限,在人与畜之间得以深刻体现。当牲畜在夜里打闹,她会平静地对他们说,“请安静些吧,天亮还早呢”,温柔的语气是母亲对这些动物打闹的容忍,也是对他们的哄劝。像对孩子一样,充满了母亲的柔情。母亲没有姓名,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迹,却在身上集中体现出温情的母性光辉。她的整个生命都在诠释着母亲的职责与母爱的深沉。对比同时期涉及母亲形象的文学作品,无论是鲁迅笔下哀怨的祥林嫂还是张爱玲笔下被金钱所束缚的七巧,我们都很难感受到《母亲》作品中所传递出的母性温情光辉。如果说祥林嫂的爱是因为过度惊吓,那么七巧的爱则显得过于畸形。只有赛珍珠的《母亲》对人世间真实的母亲形象进行了深刻的展示,对母亲对孩子无条件的呵护进行了灵魂深处的解读阐释。
三、赛珍珠《母亲》中女性的个体意识的关注与女性话语权的争夺
旧中国是父权的社会,女性往往作为男性的附庸,在历史舞台的阴暗面扮演着被忽视的角色,上演着自己被欺凌的命运故事。作为男性的附庸,女性,尤其是母亲与繁重的家务劳动、隶、生育工具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中虽然给予母亲极高的价值定位,但是那只是神圣不可触及的虚妄神话。并不是该时期女性真实地位与真实生存状态的写照,女性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被父权掩盖,成为自我牺牲的祭品。赛珍珠在塑造母亲形象时,从自身经历出发,以自己的母亲形象为原型进行了文学性的创造加工。赛珍珠的母亲凯丽婚姻上情感枯竭,生活中颠沛流离,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赛珍珠敏感的神经,成为文学创作的原始素材。赛珍珠早年就读于美国弗吉尼亚梅康女子学院,受美国女权运动影响深刻,自觉地将女权意识融汇到文学创作中,加上中年与丈夫布克的婚姻破裂都促使赛珍珠创造母亲这一女性形象时带有自身的影子,作为女权意识觉醒的女人,她不甘心在生活的打击与命运的安排中丧失女性的自尊。于是母亲形象作为女性又是觉醒的,带有个人主体意识,实现了旧中国女性话语权的争夺。
文章不止一次地暗示母亲在家庭中的女性话语权。《母亲》这部小说是对男性家庭支配地位的破解与消除,是对父权社会中二元对立结构的打破,开始重新获取女性的发言权,女性的家庭地位,寻求女性解放的突破口。作为女性,母亲不再沉默,不再居于边缘地位,母亲作为独立的女性开始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文中写到当母亲在田间劳动给孩子喂奶时遭到男人的指责:“你就干这个?把所有的事留给我吗?这不过是你的第一个孩子!”如果按照中国旧社会传统话语权的设定,那么此时的母亲则是默不作声,顺从丈夫的指责,而这位母亲则很凶地将丈夫的话顶了回去,她向男人叫道:“难道我不该稍微补偿一下我的痛苦吗?你在干活的时候,难道有像我一样挺着几个月的大肚子?”母亲不甘示弱,母亲将自己的磨难进行了一股脑的倾诉,这何尝不是女性地位的觉醒,母亲开始意识到这个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对女性的苛刻,因此她要据理力争,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平等话语权。母亲女性意识的觉醒还表现为她对的渴望与欢爱的表达。在男人还没有离去时,她内心里那克制不住的,激动起来会像暴风雨一般,会把所有无名的怨气和爱意尽情地向男人发泄。在旧中国当女性有表达意识时往往被认为是奸的代表,就像《水浒传》中潘金莲追求时被世人所诟病,即使是后来的观众也不能消除对潘金莲形象的谴责,但是却忽视了潘金莲这位年轻女性对爱情的幻想的合理性,并不认可她是解放的代表。男欢女爱其实只是正常的表达,当男性主宰则被认为雄性与力量的象征,而在女性却成了龌龊的代名词,这其实就是两性话语权不公的体现。当丈夫离开后,母亲对地主管事流露出的渴望其实是合情合理的,管事欢笑的面孔与灰色长衫自然倾泻出的美妙力量,仿佛像火焰的舌头舔舐着她焦渴的内心,她的表达体现得是那么真切。她感觉到全身散发出对的渴望,她连做梦都想不到像现在这样需要。当肉体的渴望在与灵魂理性的抗争中占据上风,她在一个乌云翻滚的午后实现了心中对欢爱的渴望表达。赛珍珠通过潜意识下母亲女性心理结构的剖析,借助细节与场景的渲染让母亲的表达展现得恰如其分,从而完成了小说对女性角色潜意识心理的真实折射。同时期的作家张爱玲仿佛也意识到女性话语权的争夺问题,因此在《金锁记》中她将女性的渴望意识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描绘,但是对比赛珍珠的女性话语权表达,前者显得过于强烈,甚至成为畸形。张爱玲说,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是不能引以为傲的。这无疑是对赛珍珠女性话语权争夺最合理的解释。
结束语:作为母性与女性的双重折射文学作品,其在世界文学殿堂中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本文选取母性与女性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生动的母亲形象,也在文本阐述中对赛珍珠卓越的文学贡献致敬。
参考文献:
[1]王维. 女性主义视角下赛珍珠《母亲》中的“母亲”形象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