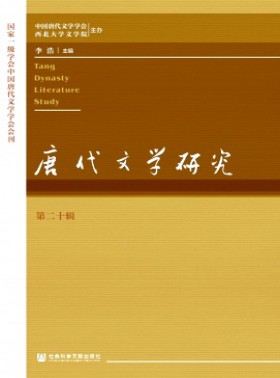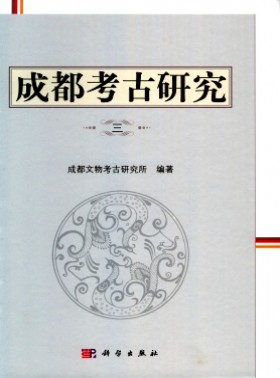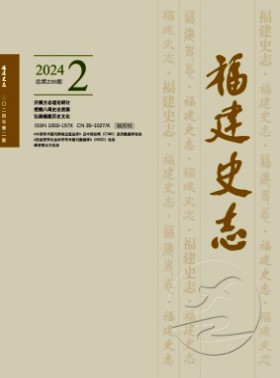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唐代古诗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唐代古诗范文1
关键词:古代诗歌教学策略;创设情景;诵读理解;拓展迁移
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非常重视古代诗歌,要求中学生能“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作为初中语文教师,要根据新课程标准设计古代诗歌的课堂教学,要把学生引入古代诗歌的殿堂,才能使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的智慧,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底蕴。
为了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古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效率,教师可以设计如下的教学策略进行教学。
一、创设情景,让学生从背景了解主题
这里所说的背景包括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活背景及其创作背景。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有助于缩减学生和诗人之间的情感距离,填补由于语言表达形式的限制而形成的许多空白,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诗歌内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课前自行搜集有关资料,在课堂上交流,这样既能调动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教师也可以采用猜谜语、讲故事、提问题、设悬念等方法,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如教学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时,可先让学生交流课前搜集有关作者和东晋政局的资料,教师再讲讲作者的生平经历,为了使学生更好地了解诗歌的主题,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为学生讲一讲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二、诵读理解,让学生从字面读出感受
1.朗读品析法
教学伊始,教师通过创设情景,带领学生走进文本,这时再加以适当的朗读指导,激发学生的生活积累,引发学生的情感体验,拉近学生与文本的距离,让学生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朗读品析,可以从语言的气势、韵味、节奏、停顿中,引领学生辨别语言的感彩,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领悟作品的思想内涵,使体验更加细腻,使感知更加深刻,最终促进知、情、义的和谐发展。
例如在教学杜甫的《石壕吏》时,教师可以设计这样的朗读品析训练: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一句,你们认为应该抓住哪些词语,加以重点朗读,比如情感上的重读、语气上的处理、节奏上的变化。刚开始学生可能抓不住朗读的重点,教师可以适时点拨:关注一些看似平常的虚词,也许更能体会人物的情感,经过教师的点拨,学生很快就抓住了朗读的重点:“且、矣”,并读出了诗歌的内涵,读出了老人的悲情和哀伤。
2.拆字释读法
初中语文对古诗词阅读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涵咏积累,二是初步鉴赏。古诗词阅读的初步鉴赏,其核心是“读懂”,要引导学生读懂古诗词,欣赏其语言美、意境美,就应该让学生过语言这一关。怎样才能使学生读通、读懂古诗词呢?
一拆:古诗词都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词所构成,因此可将每句诗拆成单独的词。如《山中杂诗》: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二释:根据拆出的每一个独立的词,采用换词、扩词或选词的方法来进行解释。如上面例句,可进行如下解释。
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
(鸟儿)(向)(房檐上)(飞),(云朵)(从)(人家的窗里)(飞出来)。
三理:在古诗词中,有些诗句因押韵、平仄等需要,采用了倒装句式,因此理解时要适当地调换一下词的顺序或句的顺序。如: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词序调换后为“天外七八个星,山前两三点雨”);有约不来过夜半(词序调换后为“有约过夜半不来”);白头吊古风霜里(词序调换后为“白头风霜里吊古”);遥看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此句序应调换为“为有暗香来,遥看不是雪”)。
四补连:古诗词的语言具有凝练和跳跃性大的特点,理解时在诗句的词与词或句与句之间适当增加一些成分,使诗句的意思表达更清楚。如:“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在通过“拆、释、理”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补连”,其意思就可理解为清晨我走进这古老的寺院,朝阳初升,照着高高的山林。通过以上的方法相信学生基本能读懂诗的大意了。
3.语境解读法
为了能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教师可以在一定的语境(包括文化背景)下展开古诗文语言层面的教学,通过“语境创设”让学生走进文本,从而带动对字词的理解,这比单纯讲解字词要生动、有效得多。还原语境,还能使学生在阅读古诗文时做到如临其境,从而与文本发生深入对话,领会作品的精彩之处。
三、激发想象,让学生进入诗境
叶圣陶曾说过:“诗歌的讲授,重在陶冶性情,扩展想象。”激发想象,让学生进入诗境的方法有很多,如:放录像,赏图片,配音乐,想画面,画画等。
如教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当学生了解全诗大意后,笔者设计道:如果你是一位摄影师,根据《钱塘湖春行》的内容拍摄西湖风景你决定拍哪些镜头?(如果指导细一点,可以再加一句:“比如哪些水,哪些景,什么样的人,等等。”)待学生各抒己见后,可播放一段配有音乐的西湖风景录像供学生借鉴。
中国古代诗歌就像中国文化浩瀚海洋里的一颗明珠,熠熠闪光。璀璨的光辉映照你我,以它那或阔大,或深曲的意境,或澎湃,或温婉的情韵,或典丽,或朴质的语言怡养着我们的性情,影响着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发挥自己的智慧引领学生走进古代诗歌的殿堂,遨游其中,乐而忘返吧!
参考文献:
1.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2.语文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
唐代古诗范文2
关键词:古代诗词 引入 数学课堂
一、诗文中看数学知识
数学,相对于其他学科,确实抽象,这也是数学的一大特色。但是,将数学知识与诗词结合,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化呆板为生动。这样既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数学知识,还能创造优美的教学情景。对称,数学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指图形等在运动变化中保持的一种不变形。它与文学中的“对仗”有相似之处。在讲解对称时,借助“对仗”来说明,可达到更好的效果。“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王维的诗句,明月一清泉,松间一石上,照一流,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非常类似于数学上的对称。清初女诗人吴绛雪作有一首辘轳回文诗:“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夏凉风动水,凉风动水碧莲香。”全诗共十个不同的字,描绘了一幅风吹水动,花香暗浮的夏日图。妙的是诗的上两句倒着读过来就是诗的下两句,可谓数学上标准的对称。极限,数学中重要的概念。古人以“一尺木椎,日截其半,万世不竭”来说明。徐利治先生引用“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来描绘,可谓妙绝。
应用题是数学教学中的难点,学生往往感到枯燥乏味。其实,在我国的数学宝库中,有许多以诗词形式出现的数学题目。讲相关内容时,如能将他们引入教学,可为课堂注入生机,令数学多一份亲切,教学多一份趣味。略举两例:远望巍巍塔七层,红光点点二倍增,共灯三百八十一,请问顶层几盏灯?这是明代数学家吴敬偏著的《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中的一道题。附:解各层倍数和:1+2+4+8+16+32+64-127。顶层的盏数:381÷127-3(盏);李白街上走,提壶去打酒;遇店加一倍,见花喝一斗;三遇店和花,喝光壶中酒。试问酒壶中,原有多少酒?这是一道民间算题(李白打酒)。题意是:李白在街上走,提着酒壶边喝边打酒,每次遇到酒店将壶中酒加一倍,每次遇到花就喝去一斗(斗是古代容量单位,1斗=10升),这样遇店见花各3次,把酒喝完。问壶中原来有酒多少?附:解设壶中原来有酒x斗。得【(2x-1)×2-1】x2-1=0,解得x-7/8。
二、教学语言多一些文化色彩
在教学中,教师除了利用专业术语向学生介绍数学概念、抽象化的定理、法则外,如能恰当地运用诗词点缀数学课堂,既可启迪思维,又能增加情趣,有时还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可得到不同的结果,教师可引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句诗来形象地说明。数学解题教学,特别是难题教学,若与王国维“三境界”结合,则另有一番风味。学生看到题目,由于思路模糊,找不到任何突破口,心情烦躁,但又必须耐心地分析题意,尽最大努力从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中提取有关信息,好像进入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绞尽脑汁,冥思苦想,久而不得其解,亦如迈入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找到方法,则达到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样,师生不仅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解决了题目,还共同经历了成大事者“立志”、“执著”、“成功”的过程。具体地说,学生刚接触题目,未弄清题意,不知如何求解,正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分析时,抓住问题本质,解决主要矛盾,好像“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想了许久,终于有了头绪,但又不能使问题彻底解决,还要继续思考,犹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陷入困境,感到困惑,努力后得出新的思路,教师可配以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三、激励评价文学化
学生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烦恼和挫折,这时就需要教师对学生进行及时地思想教育加以疏导。若用平淡无味的语言对学生进行说教,就显得平铺直叙,缺乏激情和感染力,也就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上进心,说服效果当然不好。反之,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若能适时地引用浅显易懂、琅琅上口的带有格言警句性质的诗词进行教育,学生不仅乐于接受,而且还能增强说服力。当学生学习不刻苦时,教师可用诗句“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或“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来勉励;学生在取得成绩沾沾自喜、骄傲自大时,可用名言“谦受益,满招损”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来警戒;学生取得成绩,教师进行评价并希望他再接再厉,取得更大进步时,可说“小菏已露尖尖角”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来鼓励。数学与文学联姻,对数学教学是大有裨益的。但在许多人看来,数学与文学好像磁铁的两极,相互排斥,在初中数学课堂上,卖弄文学诗词,既影响学生学习数学,也战胜学生宝贵时间。其实不然,在数学教学中,多一些文学气息,让学生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学习,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对学生日后在教学上有所成就,也是十分必要的。
唐代古诗范文3
1、排骨不要焯水,焯过水的排骨肉比较柴,可以直接放冷水里浸泡1小时,中间多换几次水,把血水都泡出来就好了,软化把排骨煮开,如果还有浮沫捞走就可以了。
2、海带在排骨煮好之后再泡,海带本身有咸味,所以汤里面就不用放盐了。
3、煮海带排骨汤时,海带不是和排骨一起放,也不是中途放,而是等排骨煮好了,再把海带放进含有醋的水里泡2分钟,再洗干净,放进排骨汤里面略煮2分钟。
(来源:文章屋网 )
唐代古诗范文4
本课是根据浙美版八年级第十五册热爱祖国优秀传统艺术内容展开的一节欣赏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传统艺术日益受到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挑战。通过本课的学习,让学生学会正确对待我国传统艺术,从小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优秀传统艺术的美好情感。
唐代的人物绢画已趋向成熟,人物的动作姿态刻画非常细腻,尤其是人物的心理和神态的描绘。本课主要是通过对唐代人物的动作、神态的观察,让学生多角度地分析中国古代人物画作品,了解唐代宫女的生活、劳动场景,古代人物画的特征,学会一般欣赏人物画的方法,从而培养学生欣赏评述能力。
【学情分析】
传统人物绘画对于八年级学生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但他们的理解比较单一,往往停留在表现了什么内容,而要更具体、全面地分析起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对《中国古代人物绢画――捣练图》的欣赏,不能仅仅看成是唐代妇女劳动生活的再现,而应引导学生从画中人物的动作姿态,尤其是传神的细节描写去探讨,从而认识到唐代仕女画所达到的高度成就。
【教学目标】
1、以强烈的视觉形式来展示我国传统的人物绘画,使学生率先获得一种视觉上的体验,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欣赏水平。
2、初步了解唐代人物画的相关知识,初步掌握中国人物画作品欣赏的方法。
3、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传统艺术的熏陶,培养学生从小热爱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美好情感。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欣赏中国古代人物画中人物的动作姿态,尤其是细节的描写;掌握一般中国人物画欣赏的方法。
难点:画中刻画的人物如何做到传神,如何体现唐代仕女画所达到的高度成就及艺术和历史文献价值。
【课前准备】
学生:相关唐代人物画的知识,唐代人物画家周、张萱和宋徽宗赵佶。
将所有的课桌分成四组集合在一起,学生按U字型坐下。
教师:多媒体课件、视频片段、四张《簪花仕女图》四张《捣练图》高清印刷品。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
课堂礼仪:师生问好,开始上课。
师:同学们看一下我们的课桌上多了什么?
生:(齐答)中国画印刷品。
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中国古代绢画,中国画的一种。
二、视频欣赏 导入新课
师:我们先来欣赏一段视频,在欣赏过程中请同学们思考两个问题:剧中体现的是什么朝代的故事?妇女的体型、服饰和穿戴又有何特点?
(学生欣赏视频片段)
生A:唐代。
生B:妇女体型很胖。
生C: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只有唐代是以胖为美的。
生D:这个就是刘晓庆主演的《武则天》。
生E: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她做了女皇后,减轻赋税,重用优秀人才,对大唐的兴盛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师:同学们讲得很好。电视剧《宫》相信很多同学都看过,今天我们也来穿越到唐代,看看唐代的画家是如何描绘她们当时的生活场景的。请同学们打开课本40页及欣赏古代人物绢画印刷品。
【设计意图】运用视频电影片段欣赏,通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课堂学习的欲望,再现唐代宫女的生活场景,学生观察她们的体型和服饰非常直观。
三、作品欣赏 共同探讨
1、欣赏《簪花仕女图》
师:周是唐代仕女画最有名的画家之一,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欣赏他的名作《簪花仕女图》,谈谈你对这幅画的感受。
(欣赏唐代周的《簪花仕女图》)
生:(齐答)非常精细,画得很逼真。
师:这是中国古画中所使用的一种材料绢,特别适宜于表现一些精细的人和物。绢画在唐宋时期是应用非常普遍的一种绘画材料。
生A:描绘了一群贵妇人在庭园中闲步赏花的情景,里面还有小狗、白鹤、花卉作为点缀。
生B:她们的生活很惬意、悠闲,不过从她们的表情、神态上,我感受到她们虽然衣食无忧,但内心是比较空虚和寂寞的。
师:同学们观察得非常仔细,回答得很好。我们再仔细观察她们的服饰、装饰上有什么特点。
生C:她们穿着非常华丽,而且贵妇人发髻上都有花卉做装饰。
生D:她们都披着纱,皮肤都隐约透出来了,穿得很开放。
师:这是一张以头簪鲜花而得名的画作,大唐与很多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借鉴了国外服饰的特点。唐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下面请同学们齐读杜甫的《忆昔》,看看我们的大诗人杜甫是如何来描绘唐代的盛况的。
(学生齐读杜甫的《忆昔》――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师:杜甫曾经目睹了唐由兴盛转向衰弱的整个过程,谁能简要描述这则诗篇大概讲了什么意思?
生:描绘的是开元盛世时,百姓安居乐业,生活非常富裕。
师:回忆开元全盛时,小小的县城里就有上万户人家。农业连年获得丰收,粮食装满了公家和私人的仓库,人民生活十分富裕。
师:为什么唐代的妇女要以胖为美?
生:(齐答)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师:这一点确实是比较直观的原因,老师这里还有第二种说法,唐高祖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游牧民族人,游牧民族的妇女很多也都会骑马、射箭,相对她们的体型上也比较健硕,后来的帝王也受此影响喜欢这种体形的女性。
师:我们再仔细观察这张画中用线、用色上有什么特点?
生A:线条简练、自然。
生B:衣纹自然,衣服颜色鲜艳。
师:好。线条是中国画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线条有轻重、长短、粗细、虚实等变化。作为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中国画有其自身用笔和用墨上的特色,特别是线条的表现。
师:人物绢画有什么特点?
生:工整、细腻,而且人物的表情、动作和神态的描绘都很自然、真实。
师:真聪明。形神兼备是人物画最高境界,画家不仅仅满足于形似,更重要的是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的揭示。
师:如何欣赏一件中国人物画作品?
生A:画了什么内容,想揭示什么主题。
生B:线条、明暗、色彩带给我们画作的整体效果。
师:对。构图、线条、色彩、对比、虚实关系的处理,当然我们有时还需了解画家及他所处的年代、生活环境及创作的背景等,一般我们欣赏作品就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去分析。
生:(惊讶)有那么多啊!
【设计意图】每一组课桌上都有与原作尺寸一致的高清印刷品《簪花仕女图》,学生能近距离观察到作品中人物线条、动作和神态的细节刻画,便于欣赏评述。将美术与诗歌相结合,引用杜甫的诗,来进一步说明唐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全盛时期。通过《簪花仕女图》的学习,概括中国人物画欣赏的一般方法,为重点学习《捣练图》作更好的铺垫。
2、重点欣赏《捣练图》,写出你的感受
师:根据刚才总结的欣赏古画的三要素,我们来重点欣赏唐代张萱的《捣练图》,先请同学将你对这一张画的感受写出来。
(学生欣赏唐代张萱的《捣练图》,书写自己的感受)
生A:这也是一张古代绢画,画得非常仔细,描绘的是一群宫女在工作的场景,有缝纫等。
生B:因为描绘宫女,所以这些人的衣着都穿得比较朴素,颜色没有《簪花仕女图》那么鲜艳。
师:大家理解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捣练。练是一种布料,它的面料比较硬而且有点黄,需要冲捣漂洗,布料才能变得又白又软。
生C:(迫不及待)老师我知道了,第三个片段就是捣练。
师:整个画面共描绘了几个工作场景?
生:(齐答)三个。
师:那么还有一个片段是在做什么?
生D:在拉布。
生E:把练熨平。
师:非常好。那么我们看到描绘了三个工作场景,熨烫、缝纫和捣练。
生F:老师,不对,顺序应该是捣练、缝纫和熨烫。
师:这位同学说得非常正确。中国画的一大特色就是运用散点透视,它把多角度事物的特征或多侧面刻画人物形象表现在同一个画面中,使画面所表现的内容更全面、生动。中国古代一些字和画一般都是自右向左欣赏的。
师:我们再来看作者。
生:唐代张萱也是一个人物画非常出色的画家。
师:恩。据传这幅画是宋徽宗赵佶的摹本,那宋徽宗又是怎样一个人物?
生A:他是北宋末年的皇帝。
生B:书法和绘画很好。
师:看来我们同学的知识面还是很广,他是北宋末期的皇帝,没有治理国家方面的特殊才能,但绘画上的造诣很高。我们来欣赏他的作品《写生珍禽图》,这是一张由12张写生的禽鸟图构成的画作,2002年它从海外回流北京,在北京的拍卖会上,最终以2530万元的价格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绘画拍卖成交的世界纪录。他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师: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欣赏《捣练图》,画家是如何来刻画人物的细节的,把细节找出来。
(学生进一步欣赏《捣练图》)
生A:看画面中第二个片段缝纫中,两位坐着的妇女刻画非常仔细,她们手中拿着针线,小时候我看我奶奶就是这样缝的。
生B:我还看到其中一个妇女还在咬线。
师:这种生活场景我们很多同学都没看到过,理解起来就有难度,所以我们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多观察、发现生活中的美。我们再来看看其它两个片段。
生C:第一部分捣练中,有四个女工,有两个动作一样,正要放入水中冲捣,有一个似乎刚准备好要工作,还有一个觉得袖子太宽松,所以把袖子往上卷。
师:这位同学观察得非常仔细。多人从事一样工作时,每个人的动作、表情肯定是有差异的,而画家往往把这种不同点描绘非常清楚。
生D:熨烫部分也描绘得很仔细。特别是最左边的那个妇女,身体都微向后仰,目的是把布拉得更平直一点。
生E:熨烫的人眼神特别专注,似乎很小心。练下面还有个淘气的小女孩估计是比较贪玩,觉得新鲜,在那里玩。
师:小女孩的描绘给整个画面增添了一定的生活趣味,是画面的点睛之笔。
生F:旁边还有个生炉火的小姑娘,因为怕热,把脸都侧过来了。
生G:对了,那个碳火是用于熨烫的。
师:太好了,看来老师的第三个问题同学们也已经解决了。那么什么是仕女图。
生:描绘宫廷中的女性。
师:对,宫廷中的女性生活、起居场景的画作。以后我们欣赏一张画就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去具体分析,这样就比较完整了。
【设计意图】《捣练图》的印刷品让学生欣赏过程中,对其中的三个场景观察得更加仔细,分析更为清晰。有了《簪花仕女图》的学习铺垫,学生已经能比较全面地去欣赏《捣练图》,再进行局部工作场景分析就显得比较容易了。
四、分析比较层层深入
师:欣赏西方古典人物油画,说说你的感受。
(学生欣赏西方古典人物油画)
生A:很逼真,很漂亮,跟照片差不多。
生B:它的明暗和色彩处理特别到位。
师:下面请同学们来完成表格。
生A: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是笔墨纸砚,一般是画在绢、宣纸上的。
生B:油画是用油画颜料在画布和画板上的。
生C:油画非常真实,跟照片一样。
师:中国画主要以线作为造型的主要表现手段,而油画主要采用明暗和色彩,注重真实性。
生D:中国人物画以形写神,特别强调神态的描绘。
【设计意图】将西方古典人物油画与中国传统人物画比较,并制成表格,学生回答起来方向比较明确。
五、 提供课题 研究拓展
师:今天我们重点欣赏了《簪花仕女图》和《捣练图》,了解了从三个方面去欣赏中国人物画作品,同学们也观察很仔细,以后我们在欣赏很多艺术作品时,都可以借用以上的方法去分析评述。老师再推荐两件作品,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和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同学们可以通过查阅书籍及网络,进一步理解中国古代人物画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设计意图】推荐上述两作品,更好地巩固中国人物绢画中对人物动作、神态的刻画,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人物画的艺术特色和魅力。
【板书设计】
【课后反思】
《中国古代人物绢画――捣练图》是我国传统绘画中的经典作品,而欣赏课在农村初中的美术学习中,为了避免单调、枯燥、难理解,我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作了调整与补充。在教学过程中,我非常注重学科综合,将美术与影视、文学、诗歌、历史相结合,使学生在美术欣赏课学习的过程中获取更多的其它方面的信息,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对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物画起到了很好的“突围”作用,同时也充分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养成良好的欣赏美术作品习惯。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注重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积极性,给学生足够的自由思维时间和空间,建立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为了更好地体现合作探究,我把班级里所有学生分成四大桌即四个大组。欣赏课中作品的印刷质量很重要,每个大桌我都准备了一张《簪花仕女图》和一张《捣练图》的印刷品,并按原作尺寸制作的,使学生能更近距离地欣赏到作品,能观察得更仔细、更真实,设计好欣赏作业,引领学生更好地分析、讨论和评述。
(萧山区瓜沥镇一中浙江杭州)
管庆伟点评:
唐代古诗范文5
【关键词】唐代 诗歌 女子体育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兴盛、最繁荣的朝代,这一时期疆域辽阔,国势富强,社会相对稳定,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唐朝精神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产物——诗歌,进入了其发展的辉煌时期,产生了众多的诗人和数以万计的诗歌作品。其中,许多诗歌以体育活动为创作内容,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我们反映了唐代体育活动的发展面貌,尤其是以女子体育运动项目为题材的诗歌,更是在各种诗歌流派中大显光彩。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唐代女子的体育活动,可谓最为兴盛,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种类上、形式上、规模上都在我国女子体育运动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本文试图从唐代体育诗歌的角度来对古代女子体育运动进行分析,以对唐代女子体育发展特点及其兴盛的原因做更多方面和深入的探究,从而为弘扬传统体育文化和发展我国现代女子体育运动提供借鉴意义。
一 唐诗中女子体育概观
唐代女子体育出现繁荣景象,项目之丰富、参与人数之多,都是先前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在体育史上也有:“惟有‘大唐三百年’,是
(3)杂技。唐朝时,宫廷中训练女伎,每逢统治阶级、达官贵人的庆典宴会,她们往往应召表演。杂技的项目主要有马技、绳技、戴竿。刘言史《观绳技》中“重肩接立三四层,著履背行仍应节。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学垂柳”、刘晏《咏王大娘戴竿》中“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分别描述了绳技、戴竿这些惊险的杂技活动。
4.骑射游猎活动
唐代帝王后妃为了满足奢侈的生活欲望,经常组织一些体育活动,当时唐尚武之风大兴,故而骑射活动普遍地开展起来,帝王出猎时,嫔妃宫女经常结伴而行,女子骑射游猎的很多。杜甫《哀江南》中有:“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中双飞翼。”这首诗突出描绘了宫女骑射的英姿。韩偓的《从猎》:“小镫狭鞭鞘,鞍轻伎细腰。”妃嫔宫女能够行弓射猎,纵马飞驰,她们的技艺已相当高超。另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宫中,端午日造粉团,角黍贮盘中,小弓射之,中则得食,都中盛行此事。”可见,唐代女子骑射游猎活动已成为一项充满竞赛性的娱乐体育活动了。
二 唐代女子体育发展特点
1.娱乐性
从以上唐诗中举出的体育活动项目和内容来看,唐代女子体育活动以各类游戏为主,虽然活动范围和活动强度较历代王朝有所增加,但这些活动竞技性少,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娱乐别人和娱乐自己,表演成分多,带有明显的娱乐性。
2.崇尚健壮的审美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更迭频繁,形成了民族冲突与融合共处的局面。唐王朝地域辽阔,境内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唐实行开放、平等的民族政策,使得社会风气日益开放,加之“唐代大有胡气”冲淡了传统的儒家伦理,礼法束缚减轻,唐王朝开始崇尚“健美”,宫廷妇女积极投身于显现力健之美的体育活动中,从而使得唐代女子体育活动多突出其健美的身躯,如健舞、骑射、马球、蹴鞠等。
唐代古诗范文6
“两面三刀”是个贬义词,比喻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玩两面手法。其实,它原是古代的一个建筑术语,是瓦工技术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
两面三刀的原意是指瓦工砌墙的基本功和基本动作。古代砌墙没有水泥,墙体粘接材料大多用黏性较好的黄泥,考究一点的工程用灰泥,这种灰泥浆制作要求高,黏稠度好。
两面三刀包含了两面和三刀两个内容。
“两面”是指砖的两个粘结面,一般是指下面和一个顶面或侧面。当瓦工左手拿起一块砖时,砖块同时会在手掌上迅速打转、翻身,目的是在观察砖的外形,确定两个合适的粘结面。
“三刀”就是指砌一块砖时,瓦刀从灰泥桶中挖上一点泥浆后,分三次批上砖的粘结面,即正面粘结的两条灰埂子和顶面或侧面粘结的一条灰埂子。技术水平高的瓦工师傅,砌出的砖墙平整美观。而技术较差的师傅,不是两个粘结面选得不好,就是瓦刀上挖的灰泥量有多有少,批灰泥埂子时,不是三刀定案,而是要四刀甚至五刀才能定案。
古代对学徒瓦工的培养,也是从两面三刀开始的。上墙操作时,师傅故意将徒弟夹在技术较好的师傅中间,在同一道墙上砌筑,目的是要逼迫他注意质量,加快速度,徒弟在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背痛的同时,技术也上了一个新境界。
日本和服原形是三国吴服
文/方徐盛
每到一个地方旅游,我对于当地的山水美景并不是那么动情,但如果能听到一两个自己不知道的典故,我就会对那个地方记忆深刻。
去日本,富士山脚下的静冈县三岛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那里,有一天我们看到好多年轻人都穿着和服。上前询问,原来,他们在进行成人礼的仪式。后来,我问导游,为何这天要穿和服?导游告诉我,日本人在重要的日子才穿和服,大多数日本人一生中至少要穿4次和服:753节,成人礼、新婚和丧葬。
753节很有意思,在每年的11月15号。这天,凡是3岁、7岁的女孩和5岁的男孩,都会穿上和服,在父母带领下去神社跪拜祈福。
导游还说,日本的和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因为在日本,和服又叫“吴服”,即是三国魏蜀吴,吴国的服装。其实,在三国时代,吴人便早已穿这种服装,汉末传入日本,和服的原形是吴服。
在日本,一件和服的制作时间较长,最少需要7天左右,好一点的和服则非常昂贵,需要几十万日元。
冰糖葫芦的前世今生
文/李祥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