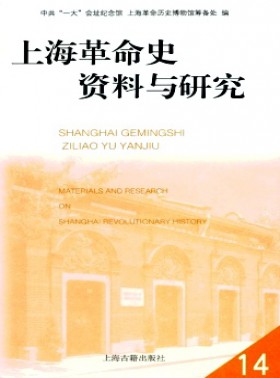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革命电影的文化探索,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周冰 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近几年,以革命为题材或背景的革命电影呈现出少有的繁荣迹象,一大批制作精良的影片得到上映,如《集结号》、《南京!南京!》、《建国大业》、《天安门》、《斗牛》、《沂蒙六姐妹》、《铁人》、《风声》等等。影视中现代性元素的考虑与运用,不仅使它们获得了“喜闻乐见”的受众效果,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合谋。然而,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在这些热映的革命电影中,革命记忆却以某种“异质性”的方式呈现着,它们不再完全崇高,相反,革命叙述似乎在有意暴露着自身的污渍与不合理。如果说在50—70年代有关革命的影像还是一种“卫生化”,80年代是“告别革命”的悲情叙述,90年代是革命的怀旧,那么现在,革命记忆的传达则是正反合和的互渗,革命的正面与负面矛盾性地统一在影像文本内,召唤着红色的集体革命记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这种记忆差异性呈现?在它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玄机?
一、记忆断裂与回忆弥合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及“告别革命”的呼声中,“中国人文思想界的主导潮流是对50—70年代(即时代)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思想的批判”,“‘现代化’意识形态”成为此后的普遍“共识”。(1)批判的兴起与共识的获得使得现代化重新崛起,可与此同时,广义的革命文化却遭到了否定与掩埋。然而,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维度,早期的革命与建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与意义。这种人为割裂历史的做法造成了历史与记忆的断裂,也形成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无根性”,似乎它们凭空而来。康纳顿曾经指出,“作为记忆本身,我们可能会注意到,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社会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2)记忆的断裂使得人们无法回溯自我产生的部分历史,导致“前现代”共同记忆的缺失,进而影响到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90年代应运而生的主旋律影视,试图重建革命史的合法性,弥合被割裂的历史与记忆,但是由于它刻板的说教而遭到受众拒绝,只能在市场边缘游走而无法真正实现其功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年代惯常运用的策略与手段——革命回忆受到了主旋律与市场的青睐。众所周知,早期革命中的“忆苦思甜”或“回忆革命史”等往往通过让革命者展示革命记忆,对接触革命者的记忆进行回溯与修正,进而将之重构,以便确证革命的合法与合理性。“”时期的样板戏如《红灯记》中“痛陈革命家史”就是以人物诉说的方式将革命记忆展现出来,在敌人与革命者的对比中,对聆听者的记忆施加影响,将之导向革命的道路。站在历史与记忆的断裂处,这一手法显示出了它的巨大价值与意义,它不仅能够重建已经被异化的革命文化形象,而且也能够对接革命记忆与现代化建设的裂痕,增强现有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一批早期热播的电视剧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狼毒花》等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段。而在当前热映的革命电影中,通过对革命记忆进行美学再造来实现记忆的价值指向,弥合历史记忆的断裂,也正是其基本的叙述策略。
可以看到,从《色•戒》中因抗战而诱发的谋杀与情欲,到《沂蒙六姐妹》中解放战争带来的“美丽守候”,再到《天安门》中“小人物”为“建国大业”的操劳,直至《铁人》中建设祖国的“铁人”精神等,这些电影在取材上都直接返回历史,利用革命年代的政治话语、事件、经验等,释放革命记忆,带有浓厚的回忆色彩。它们往往以“向后看”的回溯姿态,唤醒沉睡的历史,唤起人们的共同历史感知。在这些电影中,革命以极其现代性的面目呈现,如《色•戒》中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的阴谋、爱情、性等,或者如《风声》中对谍战、心理的运用等,有的甚至还表现出“娱乐革命”的倾向,如《斗牛》中人与牛之间的悲喜剧,它们改写了革命僵硬的面孔,在保证革命本色不变的情况下,从“分裂”的层面使革命走向了多元化展示。但是,这些现代性的精神、情感、娱乐等元素在电影中并不独立存在,它们受革命记忆的调度与支配,实际上成了革命历史的一种现代性表达,电影也变为不同于历史实录的另一种革命“回忆录”。从某种程度上说,热映的这些革命电影通过将革命与现代性元素的夹杂,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共谋。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弥合了断裂的记忆;另一方面,市场也成功地将主流意识形态装扮在现代性的背后,在确保主旋律的情况下实现了影片的商业价值。于是,在影音世界中,历史以图像语言的方式获得了再生,记忆时间作为“绵延的流”得到了接续,完整的革命历史感也得到了呈现。
二、暴露伤口与创伤净化
从记忆出发,这些革命电影讲述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故事,弥合了断裂,构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前史,有力地确证了现有社会秩序的合理与合法性。然而,在利用革命回忆弥合断裂时,它们似乎并不回避革命的血污与不合理,这与之前主旋律影视有关革命讲述中的“卫生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对这一差异性呈现进行考察,我们感到这是一种深层次的讲述革命记忆的方式,而其策略也更为深远。在早期的革命战争题材电影中,往往通过强调战争的“崇高”来超越其“创伤”,从而将个体痛苦导向一种“崇高”遮蔽。然而,冯小刚的《集结号》对革命战争的记忆呈现却采取了另类的讲述方式,他在叙述战争惨烈性的同时,加入了战争的创伤记忆。该部影片由前后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描写战争,突出战争的惨烈以及个人英雄主义;后半部分讲述战争幸存的“小人物”谷子地为战友洗刷“沉冤”,恢复烈士身份的故事。前后两部分形成张力性结构,战争越是残酷,越能突出个人英雄主义,而后半部分“烈士”身份的追寻与确认也就越有力度。
但是与其说它讲述了一位战斗英雄的故事,不如说它讲述了一位战斗英雄如何面对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为被遗忘的英雄恢复身份名誉的故事。《集结号》通过谷子地锲而不舍为战友恢复名誉的过程,将战争的创伤性记忆直呈在观众面前,让人们感受到大历史对“小人物”吞噬的残酷性,影片因此而有了批判性的力度。但是,对革命创伤的揭示只是“反”的层面,主流意识形态以“你们受委屈了”的愧疚与追认,很快就将这种“反”导入了“正”,使得这些被遗忘的英雄获得了不朽的“丰碑”,而战场上从没有吹起的集结号也在墓碑前奏响。从这个角度来说,《集结号》虽然突出了革命战争异质性的精神创伤,但同时它通过对创伤净化实现了对革命战争的重新认同和体谅。于是,在暴露与净化中,革命记忆改写了僵硬的崇高面孔,以更为完满的形态展现出来。#p#分页标题#e#
这种暴露伤口,进而净化之的现象,同样存在于《沂蒙六姐妹》中。该部影片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记忆,讲述了沂蒙山区六位女性为革命战争所做的奉献,以及她们的不同遭遇。影片一开始就将叙述引入张力中,一方面是紧锣密鼓的战争动员,一方面则是大嫂抱着“公鸡”与新娘子的成亲。革命战争动员造成了新媳妇丈夫的缺失,也导致了她的压抑与无奈守候。她虽然“识大体”,但随着战争过度动员,这种创伤似乎也越积越多。终于,在“输血”一场中,革命压抑变成了高声的怒斥。当医务人员喊,“我要男人,男同志”进行输血时,新娘子开口了:“你瞎了吗?俺们沂蒙山的男人都在前线呢!”或许这句话仅是她对医务人员蔑视女性的反驳,但从侧面却也将革命战争过度动员的弊端暴露了出来,革命并不意味着完满,它同时也意味着血污、不合理以及对人的戕害。然而,影片对革命战争给人造成的压抑与创伤只是“点到即止”,随着影片叙事的展开,这种创伤迅速被战争的胜利以及革命对烈士的确认走向了净化。与《集结号》颇为相似,在电影结尾,“满门忠烈”的牌匾、革命“祭祀仪式”等将革命带来的冲突与负面因素消解于无形,通过精神的抚慰而实现了对个体价值、生命的指认。实际上,在这种对立与消解中,重建的正是有关革命的正反记忆,弥合的是这种“异质性”的历史,而这更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记忆法则。相似的情况在《斗牛》、《风声》、《铁人》等影片中也同时出现,如《斗牛》中八路军的“欺骗”与牛二的“二牛/牛二之墓”身份的确认等。但是,与其说这种暴露是自我的揭短,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意识形态实践。以与早期革命叙述看似矛盾、悖论的方式,弥合了革命创伤,也缝合了革命记忆,从而有助于统一历史感的获得,最大程度上确证现有社会秩序与体制的合法性。
三、“小人物”与人民主体
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在暴露伤口与创伤净化的过程中,革命记忆中的人民主体地位也得到了新的凸显。如果说主流意识形态试图以张力性质的叙述净化创伤而使电影表现出不同于早期的“异质性”,那么以回忆的方式再次确认人民主体的地位则有着一脉相承性。但是与50—70年代革命叙事中的“高大全”式英雄不同,这些革命电影中的“英雄”大多为“小人物”。可是,通过对“小人物”的刻画,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将革命记忆中“高大全”之外的记忆修补完整,而且再次将自我的合法性建立在牢固的人民基础上,从而为“后革命”时代的建设铺垫了前现代的完美记忆。《天安门》讲述了一群“小人物”——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在天安门城楼布置“开国大典”的故事。影片一反有关“天安门”题材的宏大叙事,而只是用线性叙述的方式将一个又一个小的细节串连起来,刻画了这群“小人物”从接受任务到完成任务的曲折与波澜。在流畅的影音叙述中,导演让“小人物”来“说话”,凸显“人民”主体性这样一个“大”的命题。影片中不时出现有关“人民”以及与之相关的对话、情节、场景,如“我,算不算人民”,“您,我,”都是人民,而天下则是“老百姓的天下,是您的天下,也是您的天下”等;建设工地的高音喇叭广播的则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而蔺师傅对清政府的回忆以及自我主体观念的确立也形象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人民”的主体地位。耐人寻味的是,在他们即将退出“开国大典”的“舞台”时,影片又以诗意的手法,让这些“小人物”把一朵野花安插在天安门城楼的花盆里,形成了他们不在场的在场,来见证“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从这些微小的细节可以看到,《天安门》表层讲述的虽然是“小人物”布置“开国大典”的故事,但是在深层却隐含着一个“历史性”的主题,即人民的主体性。因此,与其说《天安门》讲述的是一则小人物布置天安门的故事,不如说它讲述的是人民的一种“创世神话”。
在《沂蒙六姐妹》中,以“六姐妹”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同样传达出了人民作为革命主体这一历史内涵。为了支援革命前线,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彻夜摊煎饼,直至参加战争,用孱弱的肩膀架起了一座行军的“浮桥”。相比革命影像中的“高大全”英雄,她们只不过是“小人物”,但是正是由于她们的支持,革命战争最终走向了胜利。影片行将结束之时,以孟良崮战役的最高领袖的话对人民主体进行了确认:“我就是躺在馆材里也忘不了沂蒙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集结号》中的谷子地也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然而通过他前后自我“身份”的丧失与获得,电影以“含泪的笑”传达出了作为主体的人民这一历史意旨,正像冯小刚所说的,“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斗牛》中的牛二同样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但他却能够“巧奔妙逃”,以顽强的意志力完成了八路军与村里信守的诺言,最终获得了一块不朽的“丰碑”。更为有趣的是,以流水账方式叙述历史的《建国大业》,在刻画众多领导人形象之际,似乎刻意加入了一个镜头特写,即那位给做饭的“小人物”厨师,他因抢救饭菜而被敌机轰炸至死,但却受到了的鞠躬立碑。这一镜头显然不是无中生有,它实际为“小人物”在革命中安插了一个历史位置,让人们省悟到,在领袖、英雄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普通群众集体,而正是他们托起了共和国的脊梁。由以上简短论述可以看到,借助于对革命中“小人物”的讲述,这些革命电影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意涵凸显了出来。在消费盛行、娱乐化、价值缺失的“后革命”时代,通过对人民主体的寻唤,它不仅能够消解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对普通群众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为现代的建设主体提供一种影像记忆路径,而这也正是主旋律的意图所在。#p#分页标题#e#
结语
可以发现,在一个“告别革命”的年代里,主旋律与市场相结合对已逝的革命记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与重塑。通过这种特殊的记忆影像叙述,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弥合了因“反思”、“寻根”、“选择性记忆”所造成的记忆裂痕,而且稀释了革命夹裹而来的负面因素,重新确证了人民的主体位置,从而为现有社会秩序提供了合理与合法证明。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既是对中国民族革命精神的继承,同时也是“和平崛起”背景下对历史的追忆与凭吊。它们服务于新的文化意识形态生产,反映了大国崛起过程中直面自我历史的信心与勇气,体现出建构现代人民建设主体之目的,一如康纳顿所说,“所有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