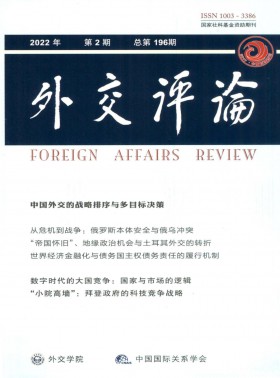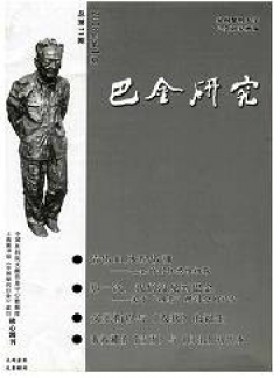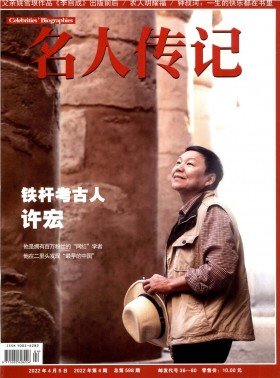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回忆的独奏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回忆的独奏范文1
曾效力英国吉百利、美国摩托罗拉、通用电气。
现任美国戈尔北京分公司总经理,领导中国区市场部策略及组织工作,提升品牌形象和促进销售。居美国戈尔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的张静葳不仅是一个幸福的妻子,快乐的母亲,还开启了每个都市人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户外梦想”。 登山、徒步、旅行、读书、骑马、听音乐、逛街?她样样喜欢!
视员工为合作者
走进位于北京高级写字楼里的戈尔北京分公司,朱红色的装饰墙上整齐地挂着极具现代感和装饰性的相框――原来这是戈尔公司获得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佳雇主”获奖证书。美国戈尔公司以其高性能防水、防风、透气的戈尔特斯@面料著称,在全球户外运动行业中几乎无人不知。在通讯行业、消费品行业拥有18年的策略、市场开拓、销售经验的张静葳便在这里工作。
在公司,张静葳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对团队的要求非常严格。“对于一个高端品牌公司来讲,如果员工做事没有章法、不到位,或者只因为人情而放弃了规则,那将会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可怕后果。最终受害将会是每个员工,大家都不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她如此看待公司管理。
虽然在工作要求极为严格,但张静葳却并不独断专行。恰恰相反,她对员工非常尊重。在她眼中,公司的所有员工都是一起做事的合作伙伴,而不是雇员:大家只是职务有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只有每个人都尽力发挥各自的专长,才能把事情做好。这种人性化的现代管理理念让员工获得了尊重和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成为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
张静葳是一个非常热爱学习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梦想,只要你觉得这个梦想是对的,就要尽你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学习、进步。”她告诉周围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潜藏在心底的梦想都在渴望被点燃。坚持梦想的人,终将有一天会看到梦想成为现实。
她的人生经历便实实在在地印证了这份感悟。以优异的成绩从对外经贸大学毕业后,她顺利进入吉百利食品公司工作。10年之后,张静葳时任摩托罗拉中国区市场经理,一切顺风顺水,此时她却选择了放弃优厚薪金,赴加拿大学习深造,攻读MBA学位。学习已经成为她的日常生活习惯,直到现在,在飞机上的分分秒秒也成为她专享读书乐趣的阅读时间。
“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对于张静葳来说,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能够做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才是职业女性最高的智慧。户外运动是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她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也乐于和朋友分享的户外心情。“当你站在山巅,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受,只有勇于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才能体味得到。”这是户外运动带给她最大的感触。
在户外活动中,张静葳体验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惊心动魄。当张静葳第一次站在10 层楼高的大坝上体验速降运动时,耳畔是呼啸的风声,眼前是迅速掠过的峭壁,而手中紧握的只有一根直径11毫米的绳子??虽然拥有专业装备和教练、朋友在旁边做安全后盾,但仅仅是闭上双眼,想象一下速降的情景,就已经让她双的双腿不由自主地剧烈抖动起来。如果想要速降成功,她必须克服自己对高度、速度的恐惧,相信别人。相信他人,突破自己。她想过退缩和放弃,不过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当她开始大胆地放松手中的绳子,任由它呼啸着从手中穿过,下降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她开始享受起这样的过程。张静葳事后回忆说,隔着厚厚的手套,她甚至能感觉到“8”字环已经变得烫手了。十几秒之后,当她安全到达地面时,她特别开心:“那一刻我感觉战胜了自己的恐惧感,锻炼了自己勇往直前、坚持到底的决心。”
回忆的独奏范文2
《白映》是高梨康治的作品,是一首以追忆为主题的歌,吉他独奏,这首歌在火影忍者的剧集中经常出现在鸣人对自来也回忆、长门对弥彦回忆、动画原创羽高、幽鬼丸等回忆过去片段的背景音乐,曲风风格惆怅,略带哀伤,会让人陷入对往事的无限遐想之中。
高梨康治:1963年出生于东京都,日本作曲家、编曲家、键盘演奏者,和风硬摇滚乐队“六三四Musashi”的成员之一,早年曾在J.D.K.BAND等诸多摇滚乐队中活跃,因格斗大会PRIDE的主题曲为人熟知后,逐渐开始涉及剧伴音乐,现今主要致力于动画音乐的制作等工
(来源:文章屋网 )
回忆的独奏范文3
今年的北京新年音乐会上,三位川军大将范竞马、李云迪和宁峰同时加盟成为一大亮点。宁峰因在2006年“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勇夺金奖而名声大噪,音乐会前,记者在排练场见到这位25岁的小伙子,宁峰回忆起参加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的点点滴滴都还历历在目:“我参加这次比赛压力很大,因为其中有位选手刚刚在意大利里皮泽尔国际小提琴比赛、也就是当年我的老师胡坤获得金奖的赛事上拿了第一名,另一位选手在德国莫扎特小提琴比赛上拿了第二名。高手云集,竞争从一开始就白热化,但我这个中国人笑到了最后,这是我的荣幸。”
宁峰介绍,第51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5名青年小提琴家参加,其中有4名中国大陆选手和3名中国台湾选手,也不乏一些已经在世界音乐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新秀。比赛分三轮,第一轮的曲目并不很多,但却是小提琴技艺的“测金石”――巴赫,帕格尼尼的无伴奏作品和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比赛进入复赛之后,只有两成的选手晋级,宁峰成为了硕果仅存的中国选手。回忆起复赛,宁峰微微皱起了眉:“复赛是最紧张也是最辛苦的。每名选手需要演奏一整套的独奏音乐会曲目,必须包括一首完整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一首专为这一届比赛而作的意大利现代派独奏小提琴作品,和一首帕格尼尼的炫技型乐曲。连续演奏下来每个选手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对所有人都是考验。”最后11名进入复赛的选手6名晋级决赛。
决赛要求选手分别演奏两个协奏曲,一首是帕格尼尼协奏曲,另一首则在规定的大型协奏曲里任选一首。宁峰的决赛曲目选择了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用这种不容易讨好评委,音乐深奥、不易煽情的作品去参加决赛,需要演奏者对自己的音乐表现力有很大的信心。因为帕格尼尼比赛以往的金奖获得者,往往是以技术准确精湛取胜,而宁峰这次获胜,则是在技术和音乐表现上赢得评委一致认可。
“说起来还有点‘喜剧’,评委会主席是用纯正的意大利语颁奖,我一共去领了三次奖,但根本不晓得是什么奖。最后一个奖,观众报以了最热烈的掌声,我心里就在琢磨:可能有点搞头了,但我听不懂,不敢肯定那是金奖。最后,评委会主席找了一个翻译告诉我:金奖是你的,中国小伙子!我那一刻真的太激动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事后才知道,宁峰还获得了《随想曲》演奏特别奖、马里奥・鲁米内罗奖两个特别奖项。
回忆的独奏范文4
酒的迷醉,烟的颓废。
花落花起,又是一季。
能否想起,谁是唯一。
精致的音乐盒飘出美妙的音章夜幕谱写寂寞的优美独奏章落下一生的遗憾
日出日落月亮可曾代表我的心
独奏的篇章时常在脑海里回首
愚弄的剧情让我在醒魇中去适应
腐朽的音符唱不出原有的音调
这是一首无名小诗,由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写成,它被刻在一块墓碑上。
IfTearsCouldBuildAStairway
AndMemoriesALane
I’dWalkRightUpToHeaven
AndBringYouHomeAgain
很难用中文译出诗中那深切的思念,那无可挽回的哀伤。
从字面上直译为:
如果眼泪能够搭成通向天堂的梯子
如果思念能够铺成通向天堂的道路
那么,我就会径直走入天国
再一次把你带回家
非常简单的用词,却从内心最深处呼唤出崩碎的悲痛。是那样的静穆,却听得见一声声不掩真情的哭声,仿佛在天空中久久回旋,令人至感至恸。
没有逝者的姓名,亦没有立碑者的署名。那么,这墓碑下躺着的是谁?这立碑的,又是谁?我们无从知晓。
也许,躺着的是父母,立碑的是子女。父母的承诺仍在心头,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你遇到什么事,这里永远是你可靠的家,常回家看看。可是没料到,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永远却是那么短暂,如今早已欲归不能。
也许,躺着的是子女,立碑的是父母。曾经的幸福与快乐,曾经的希望与心血,原以为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却被命运的风暴彻底摧残。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原点,但又回不去。宁愿一切从未发生,徒然地奢望一切能够从头再来。只恨上苍冷酷无情。
也许,躺着的是夫妻中的一个,立碑的是夫妻中的另一个。缘份,说不清道不白的缘份。原以为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风雨相伴走完一生,如今才知道,实在都是缘份的无奈。
也许,躺着的是情侣中的一位,立碑的是情侣中的另一位。无数个花前月下,憧憬着鲜花与婚纱,一生的承诺,天长地久。却不曾想,世事无常,造化弄人,山盟虽在,却永失我爱。
也许,躺着的是朋友,立碑的也是朋友。或许曾经同窗共读;或许早已失去联系,却一直心心相映;或许彼此间无话不谈,相交甚深。总是以为,一辈子的友谊,山高水长。但是,却从没有想过会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彼此之间的友情。
或许,思念比分开更难受,哭泣的月亮能否带回从前的原汁原味;格桑花的幸福能否实现在这个世界中;哽咽的畏惧真的可以在时间的消逝中去适应?
生活并不总是能继续,人生并没有多少深邃的意义。直到有人悄悄躺下去了,很多事便成回忆,才知无可挽回。
将来的某个日子,我也会精疲力竭地躺下去,到那时,不需要在墓碑上刻下什么,只要有人在心里也对我诵读这一首小诗。不管是谁,我能听见。也许能抵消生前的许许多多遗憾和失落。让我能够合上双眼,了无牵挂地离去。
泥土的气息将绕身回旋
重温梁祝才知那份痛
回忆的独奏范文5
弯月的银色荡漾着怅怅的梦
星华里飘忽起朦胧的倩影 纱衣如莲长丝盈盈。
或许那不是你 只是从你方向吹来的风
风里夹杂着幸福的味道 像浓浓的香茗
如你安好 我哭着也有满足笑容
我想你了 想那年被一切幸福的词句簇拥
现在 空了视线 空了枕边 空了心灵
现在 空了双手 空了胸膛 空了这城
现在每一个夜里梦死醉生
现在每一个夜里都有你那年在我胸膛抽泣的泪声
那年你的泪声在回忆里如此动听
窗外缤纷的霓虹不断变换姿态在我眼中倒映
我一丝丝的扫过不放过任何一处
我想看到哪怕是我用模糊的视线勾勒出的叮咛
我羡慕着那些人儿手挽手 在北京的冬天相拥, 并行
羡慕着 盼望着 惶恐着再波澜不惊
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望着远处 望着那些人的故事想着自己的心情
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看某一类书某一类电影
我以为这样哭了有理由遮掩积淀的思念 交错纵横
夜色浓浓
我为回忆开着一盏摇曳的灯
记忆里的你像沙画一样淡了妆容
再难触及 读不懂 看不清
唯有那年你在我胸口的泪声在回忆里如此动听
像一场戏曲 闭上眼还有音符悦动
像一场旧梦 醒来后眼角还有晶莹
像一场大雨 淋漓后还有长虹贯空
像一场哑剧 除了泪声再也没有语言交汇 温情
我们相遇时的江湖 如诗如画 ,我们走过的江湖 刀光剑影 ,我们分别后的江湖 只有我伴着斜影 冷清 伶仃
想你时 说起你时还是会嘴角上翘 不管谁与你月下华亭
我有我的殊荣 是那年你在我怀中抽泣的泪声
那年你的泪声在回忆里如此动听
那年你的泪声在回忆里如此动听 ,盖过了整座城的喧嚣轰鸣
那年你的泪声在回忆里如此动听, 像茅檐下的翠玉风铃随风而动
那年你的泪声在回忆里如此动听 ,却只能在心里独奏那是你我独有的曲风
回忆的独奏范文6
作者:[美]罗布·谢菲尔德
定价:24元
类型:回忆录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美国音乐记者罗布·谢菲尔德的一本回忆录。作者用15盘自制卡带为叙述框架,构建了这个他与妻子勒妮的故事。勒妮曾是一名DJ,也是自制卡带的发烧友。她于1997年死于肺梗塞。谢菲尔德从他们的相遇一直写到勒妮在他怀里去世,在这7年的时光中,饱含幸福的爱情和难以忍受的痛苦。用这15盘他最热爱的自制卡带,罗布展现了音乐的力量,它能沟通人们的心灵,越过生死的界限。
咖啡凉了又续
“我几乎认不出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姑娘,她正跟着电台里的钢琴独奏高唱。我想,此刻宇宙中再没有别的地方让我更愿意置身其中。假如她今后会让我心碎,无论她令我遭受怎样的痛苦,我都可以说值得,只因为我有过此刻。”这是罗布与妻子勒妮无数美好时光中的一个片段。音乐围绕的记忆更加清晰生动,那些逝去的时光,都封存在自制卡带里。罗布总是在寂静的深夜里,用自己对音乐特有的敏锐,把记忆交给卡带飘出的音乐,直到他感觉自身变成了卡带,一盘被倒转太多次的卡带,能听见粘在身上的指纹。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滴落,每一分钟都似乎彻底弯曲着他的形象,在空荡的房子里,他感到自己在变形。手边的咖啡凉了又热,音乐带来幻觉,仿佛他的勒妮从未离去。
音乐在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