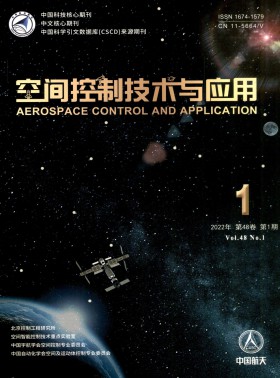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空间思维之于历史研究思考,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不同形态的空间通常是不同的建构逻辑运作的结果。不同形态的空间通常也是不同权利资源实践的结果。比如说,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北京,把北大的红楼变成驻军的场所。战时北大清华举校南迁,到了南方,把庙宇变成教室,把民居变成宿舍。从物质观点来看,校园或庙宇,公主府第或军队营房,各种不同空间在形成或建构的时候常有若干内在的规划或则律,并且依循这些原则安排门户或者墙壁。各类空间秩序一旦形成,这个秩序对于其间所将要开展的活动,也常常具有或多或少的指向性或规范性。人们一旦进入或使用这个空间,就不得不跟这个规划逻辑进行某种有意或无意的对话。这种对话往往是具有文化以及社会意义的,我们如果开发这个意义,应当可以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谈史学研究中的空间思维,目的并不在于狭义的提倡城市研究。我认为,空间思维可以为一般史学研究加分,正是因为一般凡夫俗子不能够神行,而大家又都想象或希望神行。能与不能、以及想与不想,其间有个张力。这个张力十分有趣,能为史学研究增色。至于如何增色,进而发挥宏旨,则关键在于我们在研究的设计之中,是否能把空间结构看作权利以及资源关系的产物,把空间形态解读成具有社会文化经济意义的历史积淀,把历史人物的空间经历开发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实践与物质权利秩序建构逻辑之间的对抗或对话。我们回顾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这类把“空间建构”与“社会实践”看待成对抗或对话过程的作品似乎还不算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这回的论坛,既然以中华民国史的回顾与前瞻作为题目,我想我们如果在史学领域中开发空间思维,今后或者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史学维度。
以上已经指出,我所论述的民国史学中的空间思维,虽然离不开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但是这并不等于主张把民国史研究变成民国时期城市史研究。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以下我想以伯克利加州大学20世纪中期历史学系的列文孙教授的作品作为例子,透过对他的思想史论述的重读,思索他的作品中的空间思维,着墨以上所描述的空间思维。
列文孙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转型》三卷本,不但提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同时也着眼西方与中国之间文化上的张力。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所以断裂,在他看来,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便是东西交汇、中国的世界空间秩序被动地被重组。这个传统空间秩序所指的不只是众所周知的朝贡体系以及明清帝国所图绘想象的天下,同时对内而言,也是以科举为制度、以儒学士人为干部团队的政治社会秩序。这个以四书五经为课本的秩序建构在一个区分夷狄华夏、核心边陲的文明想象之上。晚清时期这个秩序被动的被重组,打破了中国世界内部原有的文化社会资源利益的分配,也打破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一贯论述。戊戌以后,中国面临空前的文明挑战,传统知识人也面临权利话语的挑战。根据列文孙的看法,这样的双重挑战促成了中国历史千年以来首次的根本断裂。
列文孙的文化论述粗枝大叶,他的结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遭受到许多学者提出来的许多辩驳。我们只能说,他的作品产生在20世纪中期,无可避免的遭受到当时的不少时代局限。但是他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作为东方与欧美作为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碰撞的问题,则仍然是至今没有完善解决的史学问题,这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以各种面貌继续衍生存在。列文孙可以重读,正因为他所提出的历史问题不但至今还没有解决,而且他的论述方式,正可以帮助我们检视这些问题今天之所以继续是问题,其中在西方学界所曾经走过的话语建构的道路。
列文孙所运用的历史分析方法,一方面具有时间纵深,在时间跨度上从晚明一直关注到人民共和国,一方面具有空间跨度,把中国放进世界地图,透过这个地图在近现代的重新绘制,来谈文明以及国家问题。他说16世纪的东西交通,是耶稣会传教士积极寻求被中国士人接纳的过程。中国是天下,欧西是外洋。而19世纪晚期以后的东西交通,则成为中国知识人一力寻求加入西方世界的过程。以欧西为核心以及主导的世界成为世界,以中国为疆界的传统天下沦为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次要的特定地区或省份。这种空间关系的变化具有极大的现实文明以及政治上的意义。列文孙的空间思维,体现在他对空间结构及其变化的关注,以及其间所引发的权利关系位置转移的现象。我们姑且把他所使用的阐释方法称之为“位移”。
列文孙说过,一个人如果在沙漠之中迷途,他如果想知道他在哪,他所该用的方式并不是描述自己的所在,因为他不会不知道他的存身地点。他所该知道的是其他的人在哪,知道了以后才能定出自己该行进的方向。他又说,我们如果要完整认识一个提法的内涵,就不能只看这个提法的字面意义,而需要看这个提法所针对解答的问题,以及当这个提法被肯定的时候,有哪些其他相关的提法遭受否定。换言之,一个话语的意涵,包含它所肯定与否定的多元层面,也包含它的功利指向。
我们衍伸他的意思:一个历史现象,可以具有两个层次的意义,一个层次来自表象,一个层次来自这个现象在空间结构中所占据的特定位置。这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方面每个棋子各自具有车马炮之类的特质与分疏,一方面每个棋子透过在棋盘上所占据、跟其他棋子之间相对位置的不断变化,结构成一盘流变不息的棋局。每个棋子在棋局中所代表的,都是对通盘来说、不断流变的意义。
我们如果把这个“位移”的概念用到列文孙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解读:他认为中国在跟西方接触之前,原本有一套浑然天成的世界观。科举制度之下的士人是这套秩序的受益者。这一套东西在中国范围里有普世性的说服力。但是一旦传统中国与近代西方的价值相互碰撞,这种浑然天成的局面就被打破,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也就受到挑战,中国文化的内部结构被改变,中国世界旧有的空间秩序也被颠覆。
列文孙把中国文化看成传统文化,把西方文化看成现代文化,把传统与现代对立,把中国与西方对立。他认为在全球化的空间格局里,中国文化没有普世价值的说服力,只有地域性特殊价值的历史性。中国人如果要成为现代人,就得背离传统中国,走进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世界。
列文孙评价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定位为帝王体制之下官僚们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套思想所凭借生存的,是科举制度。1905年科举废弃,1911年辛亥革命,这两个事件对儒家思想的传承来说,都是深刻打击,这是因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国以后,旧式熟读四书五经的儒家知识阶层失去了文化资源与政治权利之间相互转换的千年通道。列文孙认为,儒家中国的传统到此就可以算是全盘结束。民国以来,固然有些传统元素继续存在,但是他认为,凡是在现代社会里能够存活的固有的中国成分,都必须是能够经得起西方或现代尺度验证的成分。#p#分页标题#e#
列文孙的思想史文章还有许多论述,我们在这里用不着一一继续说明。我们谈传统中国跟世界的关系,他只是一家之言。如今进入21世纪,列文孙在半个世纪以前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未必是今天大家认为无可置疑的世界秩序。他当年透过“位移”的思考方式来展现各种权利以及资源结构变化了以后所产生的问题,他的历史想象,针对的是19世纪下半期以后所形成的世界。今天我们进入21世纪,世界秩序如果有了根本改换,能够支撑我们重新想象一种不同的世界秩序,列文孙的论述就值得让我们以疏离了19世纪以后的眼光,重新进行审视。
我在这个论坛上引用列文孙,只想说明一个意思,就是空间思维在史学作品中可以发挥基本的作用。空间思维可以为我们打开比较以及辩证的视角。空间思维并不等于作城市史。近代各种历史事件具有跨国、跨地域的成分,适当地思考各种历史元素在空间格局中位置上的转移,以及这种转移所代表的社会文化意义,应当可以为史学研究开拓新意。
列文孙透过空间思维来分析近代中国思想史,他谈东西方碰撞、全球性权利版图空间格局的升沉变化。他所使用的空间思维方式,是把全球看成一体,把世界看成既有核心又有边缘,把空间的历史看成空间结构重新布局的变化史。然而,列文孙所描述的近代全球布局,虽然可以涵盖欧洲大发现、大航行以来海洋帝国西力东渐的历史,但是却不见得能够涵盖近代城市化、工业化、科技化的经济社会史。他所认定的空间格局,所依据的是鸦片战争以后,由民族国家与条约关系所建构成的国际社会与秩序,但并不等同于由现代资本、资讯、科技、人口、货物流动所建构成的跨国城市网络与区域经济社会秩序。
此外,列文森谈传统儒家体系跟中国,他其实只谈了孔孟“治国平天下”的制度性的一面,他并没有注意到儒家实践之中修身齐家的理念,也就是说,他忽略了儒家伦理作为俗世人本主义的宗教性。他把大一统帝国的官僚体系,看成民间教化的制度性基础,而彻底地忽视了地方书院在社会伦理秩序实践之中的功能。换句话说,如果儒家实践在传统中国制度性的基础,在书院而不在科举,在地方而不在朝廷,在民间社会而不在官僚体系,那么,有关儒家传统的传承与断裂的问题,我们所应当关注的,也许就不止是由帝制到共和的转变,而应当进一步的分析,由书院到学校所代表的社会文化资源的再分配。
如果我们循着社会文化资源再分配的线索来思考问题,那么粗略说来,民国时期所呈现的文化资源再分配大概至少可以包含以下的几个层面:
第一,近代学校跟沿海城市的关系非常密切。列文森谈了许多东西方对话碰撞、全球性权力版图、空间格局的生成与变化,但是他关注的是由国家主导的文明格局。我们如果着眼城市空间以及知识网络,就会看出不同的形态与动力。
第二,如果我们把学校或者是城市作为一个场域来对待,学校跟城市在这个场域里所展现的都是知识和文化的重组以及重新的建构,也就是说,我们一旦把学校跟城市当作空间思维的一个环节而引进来,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新的角度来解析其中所蕴含的中西关系。
第三,知识人跟国家关系的重构,如果在城市空间或者是透过城市里的学校来进行重组的话,这个重组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并且跟列文森所预言的或者是所认定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不同?
第四,城市是生产民族国家概念的重要场所。民族国家概念的生产,跟城市里具有跨国文化经济元素的生产机制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有个张力。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学校如何生产近代民族国家概念,也是一个值得从空间思维加以开发的课题。
总之,列文孙的史学虽然空间思路活络,但是我们作历史研究,可以把重点放在另一种形态的空间想象之上,这个另类空间是以网络横向联系为主的空间建构,而不是以核心边缘等差分配为主的纵向空间建构。我们关注的民国史课题,除了儒家中国的崩解,还可以包括城市、学校、科技、知识、公众、与国家的建构。这些问题未必是列文孙曾经充分注意到的,也未必是中华民国史研究过去的重点,但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却可以进一步开发。
本文作者:叶文心 单位:伯克利加州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