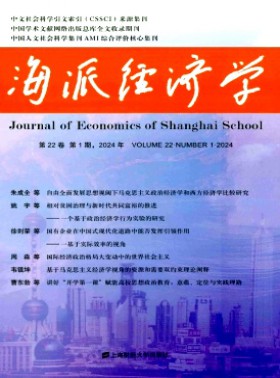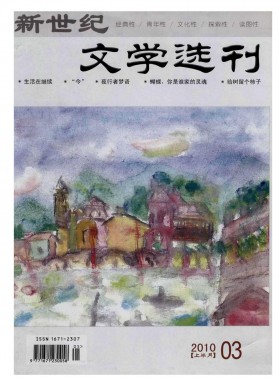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不以为然的意思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不以为然的意思范文1
不以为然的反义词 :
五体投地、理所当然、所言极是、顶礼膜拜、仰承鼻息
不以为然造句
1、对待欧洲的金融危机决不能不以为然,因为它对我国的经济贸易有影响。
2、我劝告他不要赌博,可他不以为然,不改恶习。
3、在美国,有钱永远可以使鬼推磨,但我对此不以为然。
4、他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还是坚持己见。
5、一些人的确关注这个问题,但另外一些人却不以为然。
6、大家都劝告张洪,他却不以为然,转身就走了。
7、尽管世界其他地方对礼貌问题不以为然,礼节仍相当重要。
8、他嘴上虽然没有说不对,心里却不以为然。
9、她倏地站了起来,脸色虽然红扑扑的,但并没有不以为然的意思。
10、你也许会对一条鱼或者一只螃蟹不以为然,但是它们也是一条生命。
11、老师批评了他,但他却不以为然,满不在乎。
12、小明说吃苹果时一定不要削皮,我不以为然的说:胡说!
13、西方人也许对传统捕猎的减少不以为然,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也依靠格陵兰冰盖而活。
14、听他说洋人不是,口虽不言,心下却老大不以为然。
15、一个人感到有压力的事情,另一个人可能不以为然。面对压力,我们每个人的反应也完全不同。
16、他的发言,大家不以为然,反而把他驳得体无完肤。
17、他带着一种吃惊的、不以为然的神态看着我。
18、刘英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的意思范文2
积少成多,一般人们都是用来形容好的词的吧,比如快乐积少成多,钱积少成多……等等,都是指好的事物吧!可有的时候,积少成多也可以指不好的事物。比如说,问题积少成多,失败积少成多……嘿,这是什么意思呢?
现在越多的人都不敢去举起自己的手了吧,因为害怕同学和老师质疑的眸光。可她们知道自己不懂还不敢举起手,害怕是有一部分的, 还有一部分肯定就是不以为然了。为什么呢?她们肯定有一种潜意识的心理,比如说,我只是一道题不会而已,其他题我都会做,一道题有什么好问的啊,又没什么,我其他题目会做不就行了吗?哈哈哈,这个想法真是可笑大错特错!问题都会积少成多,别看现在只是一道题,那么像它这种类型的题目,你肯定都不会做,那么去掉的只是四五分吗不!这种分数积少成多,带给你的就只有深深地悔恨了。
要是考试的时候碰到,那么你就真的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了。哪怕,考试之后,你试图去搞懂这些题目,可是考试已经过去了,分数已经扣了,那么就再也回不来了!真的,别惊奇,问题也的确可以积少成多。就这样吧,本来你不会的只有一点点的,可是经过你一次又一次的沉默,一切又一次的胆怯,你的问题越积累越多了,直到后来可能你一整张卷子都不会做了呢?到时候怎么办呢?你还准备不以为然吗?
这就很可笑了吧,唉!请别把你的问题积少成多了,勇敢一点,生活也会更美好!
不以为然的意思范文3
出自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所著作品《孟子》。
原句为: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解释:管仲令他的君主推行霸道而知名,晏子使他的君主显扬而知名,孟子对于管仲推行霸道,对于晏子未能力行王道,都是不以为然的。
不以为然的意思范文4
晚间一家子正在看电视,爸爸突然收到了朋友请求帮忙充话费的信息,爸爸一看到信息立马就要用支付宝帮忙充话费。
在一旁的老妈看到了,赶忙制止了他:“你也不打个电话确认下,就盲目的充啊!”爸爸有些不以为然的说:“确认啥啊?微信都是他的,还能有错。”老妈便开始念叨,说现在有很多诈骗的,确认下也无妨。但老爸还是坚持自己的,他说自己了解那个朋友,正因为爱面子,才不会打电话过来,再打过去岂不搞得更没面子。
老爸和老妈坚持己见,声音越说越大,逐渐演变成了争吵了。我站在那里听着,真的是左右为难。老爸最终还是帮他朋友充值了,老妈还是不服输,让他打个电话去问收到了没有,这总不失面子了。老爸无奈的打过去了,可是,一询问,顿时傻眼了,那朋友根本就没有发过信息。原来,这微信被盗了,话费也不知道充到哪去了。
老爸想起刚刚和老妈的争吵,不好意思的回房睡觉去了。
不以为然的意思范文5
然后最近和一个新朋友的相处,让我真正地明白了有没有“默契”的差别。
也许平时和身边人已经悄然间有了默契,只是自己没有去察觉而已,所以当和这样新朋友之间经常出现了一种“鸡同鸭讲“的疲惫感时,我才明白了这个词的意思。
同样的一件事,讲过一遍,她经常不会去记,所以我就自认为很详细地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发送给她,生怕到时候她又不懂得,一问三不知。结果,我发现也许人家根本就没有去看吧,因为几乎是一转头她又开始问相同的问题。
说实在话,起先这让我很受打击,开始细细地研究自己与她的每一句对话,发现个别句真的还挺有歧义的,尽管有时候字斟句酌地去讲,但总归以为和平常身旁人相处,大家有时一个眼神就懂得,更何况是如此的一大堆话,所以还自以为她已经是懂得了。
不以为然的意思范文6
魄力:(1).指临事的胆识和果断作风。 (2).气魄,气势。
魅力的意思是极能吸引人的力量。常用于指某样事物、景色、动作形为对他人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比如:
①在颁奖晚会上,明星们魅力四射。
②泰山的魅力无穷,有史以来一直吸引着人们前去观赏。
③刘德华的舞蹈太有魅力了,我们班的男生全都模仿着跳了起来。
魅力的近义词不太好找。意思大概相近的有:魄力、引力、吸引力
魅力是指指处置事情所具有的胆识和果断的作风
引力是物质之间存在的互相吸引的力量
吸引力和引力意思基本相同,指的是某种事物对其他事物的使其靠近的力量。
魅力造句
1 这些富有魅力的神话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孩子们的心。
2 这幅画呈现出的艺术魅力令人赞叹不已。
3 色彩斑斓的秋天为九寨沟增添了无穷魅力。
3 造 句 网是一部在线造句词典,其宗旨是让大家更快地造出更优质的句子.
4 没想到这里区区弹丸之地竟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来无数文人墨客。
5 你的魅力在于你对人生天真烂漫的态度。
6 难怪她获得胜利,因为她有令人一见如故的魅力。
7 人格的魅力是任何话语难以比拟的。
8 凡尔赛宫的内部陈设和装潢富于艺术魅力。
9 这栋建筑的设计很是别具一格,具有独特的魅力。
10 绘画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
11 他具有令观众爱戴和尊敬的自然魅力。
12 她的裙子和上衣搭配起来有别具一格的魅力。
13 他知道,有些人觉得他很有魅力,有些却不以为然。
14 绘画有着别具一格的魅力。无论是漫画、水粉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尤其是漫画人物,是我一直以来酷爱的。
15 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无时无刻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16 他的球打的炉火纯青,深刻体现了网球运动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