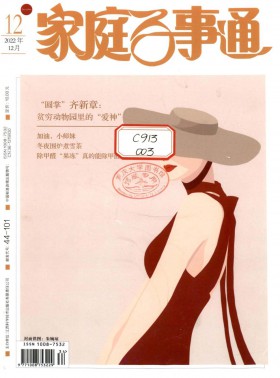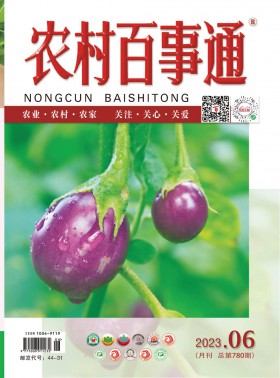百事哀范文1
家庭是一个共同体,不光是感情上的,同样也是经济上的共同体。受全球金融气候影响,从家庭成员口中听到裁员、降薪这类词已经不再新鲜。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最重要的不是如何省钱,也不是如何赚钱,关键是要想办法保证家庭和睦,使小家紧缩的日子照旧温暖如春。
经济危机袭卷,幸福指数暴跌
口述:肖华
早晨“叮铃铃……”电话响起,话务员用柔和的声音提醒上个月的电话账单还没有付清,我要赶着到电信局交清账款;还有电费账单上,赫然写着:您上个月的电费还没收到,请尽早补缴;这时,水表抄表员又上门通知,你们家的水费已经拖欠3个月了……忙乱中我想让陈宇帮我一下,没想到经济的“亚健康”影响到他的情绪也“亚健康”了。
“我已经快累死了,你能不能不为这种小事和我唠叨!”陈宇撂下这句话,重重地摔门而去。我只能幽怨地叹气,难道曾经的幸福生活只能停留在锦衣玉食、香车豪宅?看来经济状况不好,大家过日子的心情也越来越糟。
前几天陈宇公司受金融危机影响开始裁员,他们管理层的薪水降了2000多,工作量也因为人员调整的关系而加剧。另外他在股市和基金上的长线投资都已严重缩水。所以他心情不好我能够理解,但这种阴霾持续时间越长,对家庭的和谐越不利,还会影响到身边人的心情。
陈宇在事业上一直很顺利,那时候他最喜欢说的话就是“你尽情享受就是,我会给你最好的!”其实,他降薪后我担心的倒不是钱,我担心的是他一直太顺利会自信过头,适应不了突然的变故。
我还记得公司正式通知降薪、裁员的那天,我第一次听到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很害怕,问我能不能请假回家陪陪他。我忐忑不安地赶回家,看到陈宇坐立不安,神情阴郁得可怕。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可看到目光呆滞,说话有气无力的他还是大为吃惊。我安慰他,损失惨重的又不只你一个。他忽然拉住我的手感激地说:“别人一败涂地就会被妻子扫地出门,你却这样安慰我,放心,我总有一天我要东山再起的!”
出乎意料的是他的情绪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渐严重起来。他变得非常易怒,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也变得非常敏感多疑,经常对我说,你还年轻漂亮,哪会心甘情愿守着一个输得一财涂地的男人呢?
最离谱的是前几天,我在家里的电脑上竟然发现了一份他起草的离婚协议,我删除了协议,歇斯底里地朝他吼:“谁告诉你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不是贪慕虚荣的人,从来也没有逼迫你去飞黄腾达,粗茶淡饭的日子有什么不好?”他一言不发地拉自己的头发。
经济危机也是感情危机
婚姻分析师:丁一平
经济压力对家庭功能与家庭关系有重要影响。
由全球危机带来的家庭经济压力使家庭成员在家庭资源无法满足或短缺时,在感情上、认知上和行为上容易发生反常反应。家庭财产的缩减,以及就业的不稳定,另外有关医疗,教育,养老和住房等方面的负担会加重,容易影响家庭成员日常生活,增加家庭成员的抑郁情绪,敌对情绪和悲伤情绪。
就家庭层面来看,一方面,家庭资源匮乏会使成员因为资源分配而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应付匮乏的焦虑、紧张,沮丧和敌对情绪可能会使家庭成员间的相处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家庭在遭遇严重经济压力时,婚姻冲突甚至解体,家庭秩序混乱,家庭暴力,以及儿童忽视等风险会增大,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与和谐程度会降低。
预解决问题必先打开沟通的渠道,丁一平约陈宇到工作室沟通。
爱你就想给你最好的
口述:陈宇
从认识肖华的第一天,我就发誓一定要让她成为天底下最富足最幸福的妻子。
其实她不知道,前一段我做的投资很顺手,我以为很快就能赚够让我们幸福一辈子的钱了,就把大部分积蓄都投了进去,没想到老天这样捉弄我。本来想证明给她看当初她没有选错人,没想到却让她看到了我最颓废的一面。除了男人的面子,我也觉得自己很无能,甚至无地自容。
我觉得肖华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过于轻松和妇人之仁。我们手头的那点存款是用于我们自身和父母养老,还有孩子上学的钱,怎么能随便动用呢?同时,这也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我的压力自然很大,心情不好,脾气有时也就不能受自己的控制。
我承认已经习惯一帆风顺的我在面对危机时确实有些措手不及,可是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那种目标唾手可得,却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真的让人很受打击,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但还要硬撑着,因为我是一家之主,心累到了极点。
后来朋友介绍我去另一家公司做兼职,在那家公司我在朋友手下工作,我们是大学同门,从上大学到现在他什么都不如我,没想到今天我却落到这种境地,心里当然觉得不平衡,不舒服。再加上我在本职公司怎么说也属于管理层,可是兼职的那家公司却要看着人家脸色过打杂的日子,这也让我觉得委屈和不服气。
我就是不能适应已经改变的生活,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呀!
经济危机:男人的压力,女人的动力
婚姻分析师:丁一平
夫妻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有认知差异。“女性――关系趋向”夫妻和谐,丈夫尽责,家人平安;“男性――经济取向”集中在对家庭经济问题的深度焦虑和自我进行压力定义。
与男性相比女性通常对关系维护和取向的事件觉得有压力,而男性则对威胁他扮演家庭经济支持者角色的事件更有压力感。
那么家里谁的压力最大?在这一问题上夫妻双方都不假思索地认为男性压力更大。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经济压力定义模式减轻了女性心理愧疚感,但并不阻碍她们为缓解家庭经济压力而做的努力。正是因为这种“次要位置”的定义模式,使得女性对家庭压力的认知更为正面积极。一方面,与很多压力下的男性采取归因社会的认知态度不同,女性对经济压力更加隐忍和宽容,她们会采取一种更为自省的视角。这种从自我出发看问题的方式,让女性在压力面前更为坚韧。女性不会拒绝从事非正规、低薪工作,而这些男性会认为是丢脸或不值得。
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男性对经济压力更为敏感,但这种敏感也有可能导致男性彻底崩溃或逃避责任,不履行家庭关系职责。相反,它却降低了女性对经济压力的心理焦虑,更为平和务实地应对压力,提升了脆弱家庭面对种种风险和威胁时的弹性和凝聚力。
最为重要的是家庭经济变迁的适应与应对策略。
家庭经济压力事件越多,压力事件持续时间越长,家庭产生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从家庭发展看,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发展阶段,本身面临子女教育,老人照料。加之中年人自己的身心体力开始下降,参与社会竞争带来的工作压力与日俱增,更容易形成压力累积和失败,产生中年危机。这时家庭处于弹性较差的紧绷状态,一旦遇到非预期的经济压力,则导致家庭关系不和。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分两步走:一方面,焦虑可以通过自省方式调节;自省要从理财角度入手,考虑几个方面:
你的工作是否稳定?固定的收入在经济危机中最为宝贵;你有其他固定收入吗?比如房屋租赁、存本取息,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你还有债务吗?做好平衡债务关系;计算过家庭的月平均支出、月最低支出吗?知己知彼,节能省钱;有足够的现金储备(含定期存款)吗?你的现金储备够你支付家庭月最低支出6-12个月,或月平均支出3-6个月吗?在最坏的情况发生时――夫妻双双失业,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抵御风险、维持生活。在经济危机中,这种抵御能力需要更进一步巩固;另外最好有足额的保险,意外险、健康险,经济萧条期,会得到足够的财务补偿;最后是你有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吗?最后一个问题最重要。越是困难时期,心态越重要。调整好自己――知足常乐。
另一方面,外因配合。配偶的支持和关注是非常重要的。
节省的日子,不节省的温馨
口述:肖华
夫妻同心,其力断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困难的时候,就是考验人的时候。力往一处使,才能将生活经营得更好。
我和陈宇谈过,从前在经济好的时候,我的工作收入平稳,虽然没有出色之处,但是一旦经济萧条了,我的工作就显示出了它的优势,综合来说算是一个稳健的“家庭投资组合”。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平衡也是一样的道理,从大局出发,有稳定的,有激进的,这样的组合才更趋向于稳健合理。你以为你的收入出现了滑坡,我们就只能过质量很低的日子吗?这样吧,马上要过春节了,以前的春节都是你安排饭店和车,这一次让我安排。
第二天正好是休息日,一大早,我就拉着陈宇直奔附近的市场,准备年货。我面带笑容熟练地和摊主们讨价还价。逛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提着大包小包,吃的用的,还有买给老人的礼物回到家,他一边往冰箱里装,我一边报账,我告诉他采购食物才花了400多元,买礼物也不到500元,以往他在饭店订一桌饭也不止这个价钱呀!他目瞪口呆地说,原来日子还可以这么过。
那是我们夫妻俩第一次准备年夜饭,也是陈宇第一次下厨。我熟练地择菜、剥鱼,他在一边给我打下手,厨房空间有限,我们不时会碰到对方,两个人心里涌动着一种热乎乎的感觉,这才是家的感觉!
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年夜饭就张罗好了,一家老小围坐在桌边有说有笑,反而比往年坐在富丽堂皇的餐厅里更亲切,更热闹,更有年味。收拾碗筷的时候,陈宇忽然对我说,原来真正欢声笑语并不昂贵。
初三的时候我和陈宇开始去亲戚朋友家拜年,开始他还很抵触,怕别人提到他最近的失意,可是大家根本就没人在意,其实谁不明白,没人能一帆风顺。
百事哀范文2
2、安危相易:平安与危难可以互相转化。易:变换。
3、爱屋及乌:因为爱那个人,而连带爱护停留在他屋上的乌鸦。比喻因爱一个人而连带喜爱跟他有关的人或物。
4、爱莫能助:虽然同情但无力帮助。(正:同情;误:喜爱)
5、安土重迁,并非看重迁移的意思,而是形容恋乡土,不愿轻易迁移到外地。“重”在这里解释为“难”.在家乡住惯了,不愿轻易迁移。形容留恋故土。
6、百身何赎:意思是白死一百次,也换不过来。后来表示对死者极其沉痛的悼念。赎:抵偿。
7、白驹过隙:白驹:原指骏马,后比喻日影。比喻时间过得很快,就像骏马在细小的缝隙前。
8、按部就班:按照一定的条理,遵循一定的程序。
9、哀而不伤:悲哀而不过分。多形容诗歌、音乐等具中和之美。并非悲哀而不伤心。
10、哀兵必胜:遭受压迫而悲愤地奋起反抗的军队必定胜利。“哀兵”不能误解为哀丧的军队。
11、百年树人:培养人才是长远之计,需要付出艰辛。(正:培育;误:树木)
12、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满足于现有成就.继续努力,以取得更好成绩。百尺竿头:百尺高的竿子,佛教比喻道行修养的极高境界。
13、稗官野史:稗官:古代的小官;野史:古代私家编撰的史书。指记载轶闻琐事的作品。
14、坂上走丸:坂,山坡。走:快跑,像在斜坡上滚弹丸一样,快地往下。形容事情发展很快。
15、鲍鱼之肆:卖咸鱼的铺子。比喻恶劣的环境。鲍鱼:咸鱼;肆:店铺。
16、暴殄天物:原指残害灭绝天生自然资源。暴:损害。殄:绝。
17、暴虎冯(ping)河:赤手空拳打老虎,没有渡船要过河。比喻有勇无谋,冒险行事。暴:徒手搏斗。冯河:涉水过河。
18、毕其功于一役:毕:尽,完成。一次战役就完全成功或一下子把几项任务都做完。
19、筚路蓝缕:驾着柴车,穿着破衣服,去开辟山林。形容事业的艰辛。筚路:柴车。蓝缕:破旧的衣服。
20、表里山河:内有高山,外有大河。形容地势险要。
21、不可胜数:数都数不尽,形容极多。(正:尽;误:胜利)
22、别无长物:表面上看起来是别无特长,其实是指再没有别的东西,形容除此之外空无所有。
百事哀范文3
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日: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日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
这段摘自范晔《后汉书》中的哀牢夷感生神话,只164个字,却传递了哀牢夷物质生产、人生礼仪、社会组织、图腾崇拜等诸多方面的民俗文化信息,是我们探索被尘封的哀牢夷历史文化的一把金钥匙。
“沙壹九隆”神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真实记录了哀牢氏族部落的社会经济状况。而“沙壹触木成孕”和“九隆背龙而坐,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则显得飘渺玄虚、光怪陆离,带有原始神话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以现实主义笔法为基调,又掺入了浪漫主义色彩的远古神话,最早见于东汉杨终《哀牢传》,后失传。范晔《后汉书》和常璩《华阳国志》都收录了这一神话故事,并保留至今。也许是传写的错误,常璩《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的记载稍有出入,“沙壹”变成“沙壶”、“九隆”变成“元隆”。
这一古老的边地神话,因其哀牢始祖不平凡的贞洁孕生和多为中原王朝正史所记载,而广为流传。南诏蒙氏、大理段氏和明代居于喜洲的故国遗老,他们曾是这一边陲社会的统治集团。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皆攀附“九隆”,将其祖源与九隆神话嫁接,牵强拼凑整合。于是乎,元、明、清的云南地方史志中便出现了很多被有意篡改过的九隆神话。以元代张道宗《记古滇说》,阮元声《南诏野史》和已失传的《白古通记》最具代表性。
《记古滇说》之九隆神话
张道宗《记古滇说》云:
“哀牢国永昌郡人蒙迦独娶摩梨羌,名沙壹,居哀牢山。蒙迦独捕鱼,死哀牢山下水中,沙壹往哭,忽见一木浮来,坐其上,平稳不动,遂常浣絮其上,若有感,因生九子,是为九隆。后又产一子,即习农乐。”
建国一百多年后的南诏,被深陷于战祸连年、危机四伏的泥潭里。南诏国主蒙氏突然向唐叙述其家世。追溯其祖源于哀牢,认为自己是哀牢之后。“蒙舍诏姓蒙氏,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樊绰《蛮书》卷三)。南诏建国以来,曾若干次遣使朝唐,都未曾向唐讲述其族属源流。这种有失常态的作法,令人费解。我们不禁要问“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的根据何在?“献书”“自言”的动机又何来?
唐朝初年,洱海地区的蒙舍川山林茂密、土地肥腴,稻稗轮作、牛羊被野。习农乐“耕于巍山之麓,数有神异,孳牧繁衍,部众日盛”,正是蒙诏农牧业发达的写照。军事上,冶铁业的进步与普及,蒙诏走进“铁剑时代”。外以唐朝扶持为后盾。就这样积攒了武力征服所有“乌蛮”部落和“白蛮”村社的实力。诏主皮罗阁挟带唐朝的军事力量,“二河既宅,五诏已平”(《南诏德化碑》),史无前例地完成了洱海地区的统一大业。“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遗中使黎敬义持节册袭云南王”。
然而,唐朝的大民族主义和剥削压迫的阶级本性。遭遇了新兴“乌蛮”奴隶主富于扩张统治的欲望,遂与唐在东爨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引爆了“南唐矛盾”。
激起洱海地区各族人民奋然拿起武器,粉碎了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和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连续三次对南诏的大规模侵略。第三次由将军李宓率领的二十万唐军与南诏军民会战于西洱河,“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包括李宓在内的二十万唐军,或是被杀,或是被俘。
经过天宝战争,南唐决裂。此后几十年间,南唐处于强烈对抗状态。南诏不得已暂附吐蕃。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献书于唐剑南节度使韦皋。向唐苦诉南诏隐忍吐蕃的诸多侵附、百般要挟,即“四忍”、“四难忍”。所谓“四忍”,忍受向吐蕃交付各种贡纳,忍受军队供吐蕃调动驱使,忍受神川都督府监视南诏军事、政治行动。而“四难忍”中最难忍的。便是向吐蕃称臣。以及难忍吐蕃支持原浪穹诏贵族孑遗利罗式重回故地的威胁(《新唐书・南蛮传》)。
南诏为摆脱长期挣扎于唐、蕃军事对峙的水深火热之中,也出于对大唐文化的仰慕,异牟寻每叹“隔越中华,杜绝声教”,决心弃蕃归唐,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誓为汉臣。遂“效法东汉初年(公元47年)哀牢王‘遣使诣越太守’,‘愿率种人归义奉贡’之例,在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献书’于唐剑南节度使韦皋,说明它的民族源流,郑重表明愿归唐和好之意”(石钟健《论哀牢九隆族和洱海民族的渊源关系》)。
“沙壹九隆”神话见于中国正史。为华夏人群所熟知。东汉初年,带有“九隆”世系血缘的哀牢王附汉。东汉王朝遂在永昌地区设置郡县,还开辟了沟通南亚、东南亚的蜀身毒道,历史上首次将滇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也是首次建立了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华夏统治集团一直为此留有美好的回忆。蒙氏欲借“沙壹九隆”的记忆来传递愿归顺大唐的美意。加之九隆数有神异,“遂共推以为王”,蒙氏正好借此宣扬君权神授,以稳固他们在边陲社会的统治地位。此意图实际上是肤浅的,决非南诏王最深沉、最欲表达之意图。贞元中,南诏之主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暗藏玄机,闪耀着约1200多年前的边疆地方民族羁縻国家及其首脑的智慧光芒!
我们比较古哀牢国和南诏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两个边疆民族政权虽所处朝代不同、管辖范围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主体民族不同,但与中原王朝亲疏离叛的过程却很相似,先臣附后反叛。哀牢附汉29年,遂反叛。建初元年(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便“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率众攻唐城,永昌郡太守王寻被迫退至叶榆。另有哀牢人三千多进攻博南县(《后汉书》)。蒙氏自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梁建方率军深入洱海地区招降蒙诏附唐起,至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出兵攻陷姚州,杀了都督张虔陀止。蒙氏附唐102年,遂反叛。
中国文献曾记载大理又名为“鹤拓”,“南诏或日鹤拓”(《新唐书・南诏传》)。“法(隆舜)立,国号鹤拓”(《资治通鉴》乾符四年)。据方国瑜的考证,鹤拓便是“乾陀”的异写。“乾陀罗”以香而闻名,也称“妙香国”,为北天竺的一个重要城邦。至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为孔雀帝国所统一。佛教早在阿育王时代就已开始到这里布教。及至责霜国王迦腻色伽时代,这里已成为印度佛教的中心。创造了辉煌灿烂、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乾陀罗佛教艺术,兴起以希腊艺术为形式来表现印度佛教内容的风格独特的雕塑艺术,主要是佛像。
“鹤拓”指涉大理城邑或是国名的时间。可往前追溯到南诏中期(约公元9世纪),时值天竺高僧赞陀崛多不远万里来到有“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之誉的大理地区布教。“赞陀崛多神僧,蒙氏保和十六年(公元839年),自西域摩伽陀国来,为蒙氏崇信,于鹤庆东峰顶山,结茅入定,慧通而神”(《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南诏自劝丰时开始筑寺修塔、凿龛造像、臣民皆把信仰当成生活的首务。隆舜透过王室的力量,将国名梵化为“乾陀罗”。缅甸《琉璃宫史》中曾提到阿奴律陀到乾陀罗求取佛牙的故事,指的就是南诏国都阳苴咩城。
“阿育王入滇”、“阿育王为白国之祖”的传说,已成街谈巷语。“阿育王寺”、“轮王塔”、“鸡足山”、“巴连弗”等等难以计数的阿育王在滇遗迹见诸于明清云南方志。“《白古通》云:‘苍、洱之间,妙香城也。’”(李元阳《大理府志》卷二)“考《白古记》一书,鸡足山上古之世原名青巅山,洞名华阴洞。”(范承勋《鸡足山志》卷二)、“《白古通》载迦叶尊者繇大理点苍山入鸡足。”、“《白古通》载阿难亲刻尊者香像于华首门。”(高映《鸡足山志》卷一)、“世传苍洱之间在天竺为妙香国,观音大士数居其地。”(《滇略》卷四)、“大理府为天竺之妙香国。”(清释同揆《洱海丛谈》)、“妙香国老僧,未识名,妙香即今大理也。”(清释圆鼎《滇释记》卷一)、“妙香国,即今大理。古初国属天竺。”(清曹树翘《滇南杂志》卷十七)
这些文字参录法显《佛国记》、汉译佛典《阿育王传》等佛教文献,以乾陀罗国即今大理,苍洱之间为北天竺妙香国(城),遍布了古印度佛教遗迹。明代中期以后,因为对《白古通记》没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不少人看到云南地方史志中有关阿育王遗迹的材料时,都信以为真。事实上,大理既非印度,阿育王也没有来过云南。
《南诏野史》之九隆神话
阮元声《南诏野史》云:
“哀牢有一妇名奴波息,生十女,九隆兄弟各娶之,立为十姓,日董、洪、段、施、何、王、张、杨、李、赵。九隆死,子孙繁衍,各居一方,而南诏出焉,故诸葛为其国谱也”。(王崧本“南诏历代源流”条)
明中叶以降。大量刻有“九隆”或“九龙”字样的墓碑出现在了大理喜洲地区。这些墓主人皆为世居喜洲的九个白族大姓,分别是尹姓、杨姓、董姓、赵姓、何姓、杜姓、张姓、李姓、段姓。这些大姓称自己的祖先是九龙氏或自称为“九隆族裔”。这和以往的墓志铭都要详细描述每一世系的名字以及政治上的功业所不同的是九龙氏族只用“九隆族裔”一语带过。
“九龙族”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表征,华夏的英雄祖先诸葛亮所绘图谱之“神龙”乃南中人、畜的起源,强调了九龙族在边陲社会的正统地位。传说中的阿育王裔之九隆,已具有佛教意涵。同时也不离本土哀牢沙壹传说。它本身所蕴含的这三层意义。足以保护喜洲的名家。同时也满足了这些故国遗老,在面对外来政治力量,过去佛教王权以及本土社会这三股力量的冲突时。仍可以面对一个共通的历史基础。
唐将梁建方奉命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率兵入西洱河及“白水蛮”地区,进行政治招降活动。期间,撰《西洱河风土记》记录了“西部白蛮”的社会经济状况。详实可靠,史学价值极高。“松外诸蛮,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通典》卷一百八十七)
值得一特的是,这里“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与明代喜洲墓碑上自称九隆氏的杨、李、赵、董等姓相吻合,可以确定唐初“西部白蛮”就是明、清时期九龙族裔的先民。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自汉晋以降,先先后后迁入洱海地区的汉族人口。又先先后后与当地土著的叶榆蛮通婚、结亲,发展而成了数十个以华夏文化为内核,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为“夷”、汉混合体的名家大姓,如杨、赵、李、董。“杨、赵在晋朝时期为永昌郡大姓,其居地当在博南县(今永平县),后稍向东南扩展至洱海东南地带。李、董二姓,在汉晋时期已见于郡和建宁、晋宁二郡,大概是同时期前后,有一部分李、董家族中人西迁入洱海地区焚族中,至唐初便为了‘白蛮’”。(尤中《云南民族史》)以一姓、两姓或数姓聚族而居,形成了大大小小散落在洱海附近的西部平原的白蛮村社。段家登、高家营等等村名,经常在云南遇到,在白族地区更是常见。
九龙氏之杨、赵、李、董、尹、段等姓,有很多代表人物参与南诏大理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决策和管理,身份地位显赫。
南诏高级官员中数杨、段、赵三姓人数最多,人才济济。杨氏共五十五人,段氏二十四人,赵氏二十三人。三大名家共一百零二人,占南诏清平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大军将的百分之四十。军将的百分之五十七,入唐使的百分之八十。清平官等四大官职,三大名家即占百分之七十,几乎全部由他们霸占。他们树大根深,因而其子孙继南诏之后而有赵善政、杨干贞、段思平登上了王位。
南诏中后期。世隆宣扬“阿磋耶观音得国”。阿吒力教的形态也就在那时基本形成。大理国时期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统治术。受到王室的极力信奉和推崇。九龙族多皈依佛教为阿吒力僧,娶妻生子,与俗人生活无异,但有僧人身份,在地方上操持法事,为人祈福禳灾。王室倚重他们并授之各种尊号。他们透过佛教神力――梵僧或是有法力的国师,贯注于世系来源,其身份职业可以世代相传。董氏就以世袭阿吒力僧职传统而立于名家贵族之列的。九龙族裔天生就是政治官僚以及梵僧后裔,外以继承政治地位,内则继承教法家业,颇有汉地“书香门第”的味道。
元代,以段氏总管为代表的九龙氏名家大姓所信仰的佛教密宗阿吒力教得到了元王朝的支持。九龙族裔的杨、赵、李、董、张、王、尹、何、杜等姓的密宗大师即阿吒力可以继续传承和发展。
15世纪。对九龙族裔而言。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期。1382年,明军攻下大理后,设立大理府,大理路结束。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云南的代表人物傅、蓝、沐在对待故国统治集团中坚的九龙族裔及其统治术阿吒力教的政策上采取的是残酷的压制。未代段氏总管段名及二子苴仁、苴义俱被擒。其他大小官员头目,包括大僧侣、大巫师数百人在内都解送南京。关押了四五十年后,一部分僧巫被释放,大多数头目被杀。段氏王室受到打压,僧官制对僧侣各方面的管制。威胁了以佛教圣王为核心,自南诏大理以来所建立的社会系统。九龙氏族被迫进入较低级的官僚系统。或是介于官方和地方的中介人物。但僧职传统却“内化”成为他们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皈依了“置身事外”的“印度婆罗门族”,并宣称自己为“婆罗门僧”,表示非正式的官方认可的僧业。他们开始过着退隐的生活。保持僧职。或是从事地方性公共的宗教事业,这样可以使自我的过去,获得神圣的延续,也有利于子孙繁衍。
西洱名家在有关“始祖”以及人生来源的认识上,将人置于远古神话“九隆后裔”来解释。“九龙族”的说法。无异是大理故国遗老对明朝统治的一种妥协,以此逃避现实世界所带来的诸多干扰。
百事哀范文4
关键词: 潘岳 元稹 悼亡诗 比较
“悼者,哀也”(《广雅释沽》)。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哀悼亡者的诗篇。悼亡诗究其源流,则可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三百》,其中《诗经·邶风·绿衣》当可推为“悼亡诗”的发轫之作。该诗说的是一男子手抚亡妻遗物,悲戚不已,追忆旧时情谊,感念妻子对自己的照顾和规劝,感伤如今再也没有人能如此贤德美惠,可以理解自己的心了,其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但“悼亡诗”名称的出现,当自晋代潘岳以《悼亡》为题写的三首追悼亡妻的诗作之后,“悼亡”二字似已约定俗成地成为丈夫哀悼亡妻诗作的专称,以致后人一见“悼亡”字眼,便自然联想到这是悼妻之作,而每逢丧妻,也都习惯以“悼亡”为题。《辞源》对“悼亡”的解释:“晋潘岳妻死,赋《悼亡》诗三首,后因称丧妻谓悼亡。”
在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诗以其特殊的题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类诗歌的主要内容多突出表现妻子生前的贤、惠、笃,以及作者对亡妻的深切追思。其表达方式是由景到人,睹物思情,超越时空,物我统一。诗篇的基调表现为一种凄婉沉痛、孤寂落寞、缠绵悱恻的悲情美。其中潘岳追悼亡妻的诗以其情真意切、缠绵悱恻见长,千百年来叩动人们的心弦,后影响唐代元稹等人,而元稹的悼亡诗则多一些俊朗直率、浅切通畅,正是他们二人使悼亡诗成为专指悼念亡妻的诗歌门类,并确定了悼亡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为此,笔者将潘岳的《悼亡》与元稹《遣悲怀》悼亡诗进行对比,探讨在同一题材下,他们诗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异同点及元稹对潘岳的继承与发展。
潘岳(247—300年),字安仁,祖籍荥阳中牟(今属河南),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刘勰曾这样评价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忻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龙.明诗》)。与当时的陆机并称,并被前人屡加比较,或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或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虽各有得失,亦不无高下。但潘岳“善为哀之文”,这是古今一致的公论,《悼亡》之作,传诵千古。潘岳的妻子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杨氏订婚,结婚之后,夫妻两人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杨氏于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卒。二人感情甚笃,杨氏去世后,潘岳除了《悼亡诗》三首外,还作有《杨氏七哀诗》等悼亡她,情深义重可见于此。
《悼亡诗三首》(之一)是诗人为哀悼亡妻所作《悼亡诗》三首中的第一首,也是三首中最让人动容的一首。诗歌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哀伤的永恒时空,充满生死两茫茫的悲痛之情。诗中诗人以时间为经回顾了与妻子生前“如彼翰林鸟,如彼游川鱼”,如胶似漆般浓炽的爱,伤吟现如今物是人非、阴阳相隔“双栖一朝只、比目中路析”的孤单落寂之感,以及不因“光阴荏苒”、“寒暑流易”,而改变诗人对亡妻的“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的永恒哀念,反而越来越沉重。但由于伤悲难遣,孤寂难耐,情思无依,因此他发出了“庶几有时哀”的慨叹。面对这种无奈的悲苦,诗人开始羡慕庄周犹有缶可击,因此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庄子那样从感情的重压下解脱出来。而这种企图,则又暗示出诗人的这种哀伤不仅剥夺了他的今天,而且将吞噬着他的明天、后天……读罢全诗,一个陷入永恒哀痛之中的诗人形象粲然浮现在眼前。同时,诗人又以空间为纬,使妻子生前的景物随着自己的步履移动逐次展示出来:庐舍、居室、帷幕、屏风、翰墨的余迹、檐头的滴水等,物是人非,睹物思人,这些连续的空间场景弥漫着阴沉凄凉的气氛,在沉寂中倾诉着诗人丧妻的悲痛、孤单的追思,流露着低沉、伤感的情绪。这首诗情至深而意至切,悼亡的深情婉转地流淌于字里行间。
在潘岳悼亡诗中,诗人擅长于用精密而细腻的文思编织着对妻子无尽的追思和自己的孤寂之苦,而这种情思诗人能巧妙地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意象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同时,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也达到了情景交融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这些意象看似信手拈来,即景生情,实则不然,此物此象在诗中皆成了诗人寄托哀思的载体,承载着诗人浓浓的、深深的情思。因此,潘岳的悼亡诗都写得情真意切,以致李商隐说:“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但由于受当时魏晋文风的影响,潘岳的悼亡诗辞藻过于华丽,倒掩盖了不少真情实感,正如元稹所评“潘安悼亡犹费词”。
元稹的悼亡诗深受潘岳的影响又超越了潘岳,也正是元稹诗的出现,才使得悼亡诗的风韵气势最终成型。
元稹(779—831年),唐代文学家,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元稹在文学上以写传奇和艳诗闻名,但他的悼亡诗也同样让人感动。元稹的妻子韦丛是太子太保韦夏卿的,二十岁时嫁给元稹,那时元稹没有功名利禄,虽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但“野蔬充膳甘长藿”,俩人恩爱有加,度过了七年艰苦却幸福的生活。七年后,元稹已经当上了监察御史,韦氏却离他而去,元稹十分悲痛,为她写了很多可称为千古绝唱的悼亡诗,包括《遣悲怀》三首及那首著名的《离思》。
我们来看看元稹的《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在三首悼亡诗中,元稹几乎没有对环境的直接描写,主要运用叙述和议论的表达方式直叙其事、直抒其情,但同样达到追思抚昔的“悼”的效果,同样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哀动于衷,潸然泪下,字字透露着诗人对亡妻椎心泣血的思念。亡妻韦丛聪颖美丽,在元稹出仕之前就已亡故。“自嫁黔娄百事乖”、“贫贱夫妻百事哀”,都隐含着诗人的无奈自责:妻子生前未能尽享自己给其营造的温暖和幸福,反是随着自己一道尽尝生活的艰辛与悲苦。
三首诗按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顺序展开,以一个“悲”字贯穿始终,题为《遣悲怀》,实际上则是越“遣”越悲,越遣越不能忘怀,越欲罢不已。悲痛中夹杂着愧疚、遗憾和报答无门的复杂心情。如:第一首以叙述的手法刻画出韦氏“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相濡以沫的品德,使韦氏贤惠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首写物是人非、思念不已,只好通过“托衣裳”、“存针线”、“怜婢仆”来弥补对亡妻的愧疚之心,以慰藉亡妻,寄托自己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第三首主要以议论的方式倾诉着对亡妻的日炽的追思,仍导致“自悲”,“自悲”的是生前没有使妻子过上好生活,“自悲”的是自己日后难遣的孤寂、悲苦,以至于发出了“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的慨叹,而只能无奈地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方式来抚慰自己对亡妻的追思和愧疚。在诗中诗人同时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今昔之反差来强调往日之贫、欢,妻子之惠,反衬今日自己之“悲”、“愧”、“责”。昔日妻子“野蔬充膳食”,今日诗人“俸钱过千万”;昔日妻子“泥他沽酒拔金钗”,今日诗人“因梦送钱财”;昔日是妻子“添薪仰古槐”,今日是诗人“针线未忍开”;昔日是妻子“平生未展眉”,今日是诗人“终夜长开眼”。一鬼一人,一昔一今,一虚一实,一死一生,处处对照使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尽是艰辛与沉重、悲恸与深沉。同时,元稹的悼亡诗中微观上细致刻画,极为真实具体,在这方面元稹的诗要较潘岳显得更为悲痛深沉,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往往从日常小事、真事入手,小处着笔,通过某些极具感染力的细节描写表达出来。在这些诗中,元稹用浅切的语言,通过平凡的琐碎的家常事,表达了对亡妻深深的追思,使自己波涛汹涌的情感潮水般倾泻奔腾而来,拨动着诗人的心弦,撕扯着诗人的愁肠,在诗人那早已枯竭的心灵上又榨出了最后的一滴眼泪。妻子走了,留下的是孤零销魂的诗人;妻子走了,留下的是诗人对妻子深深的追忆和思念。
唐人崔颢有诗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悼亡诗作为一种主情的诗歌体裁,完全靠真挚的情感动人。潘岳和元稹都是在相同的境遇下有感而发,故而他们的情感都是真挚感人,写出来的诗歌也是动人心魄。难怪清代的纳兰性德在笔记中,把唐代元稹的《离思》、宋代苏轼的《江城子》、宋代贺铸《鹧鸪天·半死桐》与潘岳的《悼亡诗》并列为四大悼亡诗,可见潘、元二人的悼亡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
悼亡诗始于潘岳,但是真正意义上把悼亡诗推向更高境界的却是元稹。潘岳的悼亡诗为后世悼亡诗人提供了一个范本,文风追求绮丽、喜欢铺写,文字连接比较紧密,然而具体就诗歌艺术特色分析此诗,就会发现虽然诗句通顺流畅,语句连接紧密,但是缺少精美工致、深于刻炼的句子,在语言的创造方面显得比较平庸,语言堆砌过多,意思重复明显,缺少一些亮点和闪光点。而元稹从潘岳的诗作中汲取了不少艺术营养和创作灵感,“潘岳悼亡犹费词”,元稹既深受潘岳的影响又超越了潘岳,也正是元稹的出现,才使得悼亡诗的风韵气势最终成型。《离思》三首也延续了他一贯的诗歌作风,语言平易浅近,流露的情感却真实动人,感人肺腑。其中诗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更是广为流传。清代蘅塘退士评论元稹这首诗时说:“古今悼亡诗充栋,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潘岳和元稹的悼亡诗不仅打动了世人,更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苏轼、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创作。
参考文献:
[1]辞源[M].(修订本1-4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刘勰.文心雕龙.明诗[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3]隋书.经籍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百事哀范文5
一个让世人和华夏大地的炎黄子孙铭记一生的日子,四川汶川发生了八点零级以上的超大地震,其覆盖面和强度超过了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灾难的来临,总是让人措手不及,甚至,来不及悲伤。
当天,我们便从网络上得知了这个消息,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同情那些死去和失去亲人的同胞们,为死去的人哀伤。网上公布的图片惨不忍睹,从废墟中伸出的求救之手、被无情的砖瓦压住的血肉之躯……最可怜的是那些孩子,刚刚来到这个世界,还未感知人间真情,就匆匆地奔赴黄泉;那些求学的少年,正含苞欲放,却过早地夭折……想到这些,我的喉咙哽咽了,心里几乎被巨大的哀伤混浊地糊成一团,开始闷闷地痛,开始疯狂地抽搐,然后又被击打得碎成一片一片。
同学们在一起讨论,我们捐点钱吧,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一开始,各捐助机构还未设立,我们不知捐往哪里,于是四处打听,看哪里有可捐款的地方。幸好,第三天,学校领导大家捐款了, 接着,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两百元、五百元……不论金额多少,每位同学都迫不及待地奉献了爱心。似乎,只有捐了,我们的紧揪着的心才能安定。
接下去的几天,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灾区。捐款、捐物、捐血,渗透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大小企业、各个明星,到普通的农民和下岗工人,无不慷慨解囊。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沿街乞讨的老人,他掏出了身上所有的角角分分,到银行兑换成一百元,然后投入捐款箱;还有一位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家徒四壁,她从家中的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里得知地震的消息,硬是把积蓄多年的两千四百多元全部捐给了灾区。真是灾难无情人有情啊!
这次地震,我们国人空前团结,人民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和速度,写下遗书,从五千米高空跳伞到徒步二十个小时赶往受灾现场,他们一致地想: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能轻言放弃……胡主席和温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抗震救灾最前沿,为灾区群众分忧解难,为部队官兵加油打气。
“别哭,别哭,这是一场灾难,你们幸存活下来,政府会管你们的!管你们生活,管你们的学习,要好好活下去!” 温总理对被安置在绵阳九州体育馆的孤儿说;
“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十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 总理在电话里大喊,说完摔了电话;
“我们要第一步救人,要不断努力把他们救出来,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部队指战员排除一切困难,就是步行也要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在一线的军人已经被下达死命令,必须冒雨解救,前线空降兵是写了遗书再上去的;数万官兵已经20小时未进食!却仍在用血肉之手刨救受灾的同胞!
……
无怪乎美国一位著名军事家说,“中国人一瞬间由一盘散沙凝聚成钢板一块,真是太可怕了!”
五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为全国哀悼日。十九日下午十四点二十八分,举国上下为灾难中失去生命的人默哀三分钟,我刚巧坐在公交车上,两点二十八分,所有的公车不管开到哪里,全部停下,刹那间整个城市喇叭齐鸣,哀伤肃默的气氛在城市上空流转。车里的移动电视播放着全国各地为灾民默哀的现场直播,三分钟的悲鸣,飞散开来。
网络上,各大网站的主页全部成了灰色、网友们的QQ头像亦换成了哀悼图像、行人们手臂上都扎了黄丝带……所有的中国人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灾区同胞的哀念之情!
地震的发生,让活着的人更珍爱生命,心胸仿佛开阔许多,有什么能比活着更幸运呢?对生命意义的诠释也有了新的理解,也许是在生与死之间获得了彻悟……原来,没什么可以让人放不下的。
我还明白了,灾难之中,散发开来的那种温暖的,令人感动的气息,它有个温暖的名字——“大爱”。
百事哀范文6
【关 键 词】宰予;阚止;孔子;关系考辨;思想史。
【作者简介】席云舒,原名席加兵,曾任《南方文坛》副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社科图书出版中心主任,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
宰予,字子我,孔子的学生。《论语·先进篇》中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据此列孔门十哲于篇首,置政事于言语之前,宰我排第七[2],为孔门高第弟子。然而观诸《论语》,所记宰予事只有五章,仅“先进篇”一章褒之过甚,其余四章均贬之,分别为“八佾篇”哀公问社章,“公冶长篇”宰予昼寝章,“雍也篇”宰我问“井有仁焉”章,以及“阳货篇”宰我问三年之丧章。其中,宰予昼寝章和宰我问三年之丧章贬之尤甚。在孔门四科中,宰我与子贡同列言语科,且宰我列于子贡之前,《孟子·公孙丑上》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3],《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说他“利口辩辞”[4]。然子贡善为说辞多见于《左传》《史记》,而宰予之“辩辞”却不见于《左传》,《史记》亦仅记《论语》所见之言。孔子对宰予的评价何以前后判若两人,则无更多信史可考。
阚止,字子我,为公子阳生(齐悼公)臣,齐简公宠臣。据《左传》,哀公五年(前490年)秋,齐景公卒,安孺子荼立,冬十月,公子阳生逃往鲁国[5];哀公六年(前489年)八九月间,陈僖子使人召公子阳生回齐国,阚止知公子阳生欲归,“先待诸外”,意欲同行,公子阳生担心回到齐国后未知吉凶,嘱咐阚止先待在鲁国,并将其子壬(即后来的齐简公)托付给阚止。是年冬十月丁卯,陈僖子立公子阳生,即齐悼公[6]。《左传》未载阚止何时护送姜壬回到齐国,但可推知当在齐悼公即位后不久,即鲁哀公六年年底前后。哀公十年(前485年),鲁、吴、邾、郯四国伐齐于鄎,齐人弑悼公[7],齐简公姜壬立。“哀公十四年”载:“齐简公之在鲁也,阚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陈成子惮之,骤顾诸朝。诸御鞅言于公曰:‘陈、阚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8]此言谓简公在鲁国的时候就宠信阚止,即位后使阚止为政,陈恒很害怕;御官鞅建议简公在他们两人中选择一个,简公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后阚止又因陈逆杀人事而有隙于陈氏。及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即齐简公四年,时陈氏族人陈豹为阚止家臣,阚止对陈豹说自己欲“尽逐陈氏而立女”,陈豹以告陈氏,陈恒遂杀阚止,执齐简公[9]。是年甲午(六月五日),陈恒弑简公于舒州[10]。
《韩非子·难言》中说:“宰予不免于田常。”[11]《吕氏春秋·慎势》说:“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于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非而细人所能识也。’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于庭,即简公于庙。”[12]《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则言:“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13]《史记·李斯列传》记李斯上秦二世书又说:“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14]此外,《淮南子·人间训》[15]、《说苑·正谏》[16]记述与《吕览》相类。《说苑·指武》则说:“田成子常与宰我争,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见旌节毋起。’鸱夷子皮闻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17]《盐铁论》“殊路篇”说:“宰我秉事,有宠于齐,田常作难,道不行,身死庭中,简公杀于檀台。”[18]“讼贤篇”又说:“故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弱杀。”“子路、宰我生不逢伯乐之举,而遇狂屠,故君子伤之。”[19]这些记载,均认为宰予与陈恒(即陈成子田常)相争,为陈恒所杀。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贞“索隐”按:“《左氏传》无宰我与田常作乱之文,然有阚止字子我,而因争宠,遂为陈恒所杀。恐字与宰予相涉,因误云然。”[20]按照司马贞的说法,是因为宰予和阚止二人的字均为子我,《左传》未记宰予事,但记阚止事,而《左传》又多称阚止为子我,所以韩非、李斯、司马迁等人都搞错了,把阚止当成了宰予。那么,究竟是阚止、宰予二人均为陈成子所杀,还是宰予、阚止本来就是同一个人,还是韩非、李斯、司马迁等人误把阚止当成了宰予,被杀的只是阚止,根本就与宰予无关?这个问题成了一宗悬案,历代学者争论了两千余年。若宰予和阚止均只是无关紧要的人物,那么即便考证出他们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人以及宰予是不是为陈恒所杀,其意义都不太大,至多只能证明宰予清白与否罢了。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孔子对宰予的评价,甚至进而涉及孔子的思想、观念是否在某个时期发生过变化,因此证明宰予是否曾与陈恒相争并为其所杀,对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变化就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了。
赞成司马贞“索隐”之说的,后世有苏轼《史评·宰我不叛》[21]、苏辙《古史·孔子弟子列传》[22]、孔平仲《孔氏谈苑·司马迁之误》[23]、洪迈《容斋随笔·宰我作难》[24]、孙奕《履斋示儿编·杂记》[25]、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宰我》[26]、崔述《洙泗考信馀录·宰我》[27]、赵翼《陔馀丛考·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28]、惠栋《春秋左传补注》[29]等;赞成宰予即阚止之说的,后世有全祖望《经史问答》[30]、宋翔凤《过庭录·阚止》[31]等。钱穆先生《宰我死齐考》说:“余每疑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而宰我居先,孟子称其智足以知圣人,其在孔门,明为高第弟子矣。而《论语》载子我多不美之辞,如昼寝及三年之丧两章尤甚。诸弟子中,独写宰我最无情采。《论语》本成于齐鲁诸儒,其书出于战国时,田氏已得志,而鲁亦为田齐弱。岂田氏之于宰我,固有深恨。而朝政之威,足以变黑白……《史记》谓孔子耻之,岂不宜哉?”[32]钱穆先生驳崔述《洙泗考信馀录》所言哀公六年公子阳生托其子壬于阚止之时,“宰我方从孔子于陈蔡之间”,为“疏阔之论”[33]。显然,钱先生是主张宰予、阚止为同一个人的。钱穆先生这里主要是从《论语》成书时代的社会环境推导出宰予即是阚止的,但是钱先生的考证并没有告诉我们,孔子对宰予的评价之改变以及哀公问社于宰我而孔子闻之,此二者最有可能发生于何时,或者不可能发生于何时。而赞成司马贞之说的,亦多出于情感认同,鲜有严格的论证。笔者以为,无论是以时间推之,还是以《论语》《史记》所记孔子评价宰予之言的语意推之,宰予和阚止都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其一,从《论语·先进篇》所记孔子以德行言语四科评价其十个弟子的时间来看,宰予和阚止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以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来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澹台灭明传下孔子所说的“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34]是可信的。前者为孔子给予宰我的很高评价,后者则反映了孔子十分后悔因自己的错失而失去了宰予和子羽这两位优秀的弟子,与《论语》其他几章所记的孔子斥责宰予之言相比,这两句话充分体现了孔子对宰予态度的转变,从内容上看,这两句话所表达的孔子对宰予的态度是十分一致的,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孔子说这两句话的时间相距必不太远。子羽即澹台灭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其“状貌甚恶”。但韩非之说则与此相反,《韩非子·显学》中说:“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35]戴德《大戴礼记》和王肃《孔子家语》的说法近于韩非,但其书更为晚出,清人孔广森已有辨正[36]。据《论语·雍也篇》所记:“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37]依子游之言,则韩非之说误。第一,孔子问子游有没有得到什么人才,子游回答说澹台灭明“行不由径”,则是指子羽做事不取捷径,其行为中规中矩,是合乎礼的,根本不是韩非所说的“君子之容”而“行不称其貌”。第二,孔子问子游“得人焉耳乎”,假如此时子游向孔子推荐的却是一个“行不称其貌”的人,这从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因而《史记》说澹台子羽“状貌甚恶”是可信的,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意思,就只能是悔之恶其状貌而失去贤德之人。那么孔子把“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并列而论,二者的意思就不可能恰好相反,这显然也能够与“言语:宰我、子贡”这一评价互相印证,表达的都是孔子对宰予的肯定性评价。
那么,“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孔子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据《论语·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38]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言偃为吴国人,少孔子四十五岁;《家语》说他是鲁国人,但未言及其年龄。据《左传》,孔子于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冬自卫返鲁[39],时孔子年六十八岁(岁末)[40]。依《史记》,子游时年仅二十三岁,定公十三年春孔子去鲁适卫之时子游才十岁。武城为鲁邑,在曲阜东南,子游为武城宰,而孔子又得至武城,必在孔子自卫返鲁之后。而澹台子羽又由子游推荐给孔子,从而成为孔子的学生,此时当是孔子六十九岁之后了。子羽貌恶,“孔子以为材薄”,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羽离开孔子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41],子羽不可能在朝夕之间便“名施乎诸侯”而又“孔子闻之”,因而推算下来,孔子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应已年逾七十了,最早也应不早于哀公十三年,而不可能在孔子自卫返鲁之前。
《论语·先进篇》未明言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评价孔门十个弟子是出自孔子,还是出自编撰《论语》的孔门后学。程树德《论语集释》“考异”引日本山井鼎《七经考文补遗》称:“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唯清人翟灏《四书考异》不持此说,认为:“此章无子曰者,是记者所书。”[42]其他注家则少见对此语出自孔子持有异议者。参照《论语·先进篇》其他诸章,我们可推定此言必出于孔子之口。“先进篇”第十八章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43]此章亦未明言是否为孔子所说,但称子羔愚笨、曾子迟钝、子张偏激、子路卤莽,必不出自孔门后学。“先进篇”多有孔子对其弟子的评价,如:“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44]“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45]“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46]“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47]孔子对弟子或褒或贬,有的写明了“子曰”,而有的没写,但这些话都是出自孔子之口则毫无疑问,而非出于孔门后学之口。翟灏之说并无实据,当不可信。“乡党篇”则与此不同,“乡党篇”为弟子记孔子行状,其记述则均出自孔门弟子。孔子以四科评价十弟子的时间,如前所言,与孔子悔其失之宰予、子羽的时间相距必不太远,可推知此言当出于孔子自卫返鲁之后;若进一步推测其时间下限的话,似乎应在颜回去世之前。若此言是在颜回去世之后所说,则孔子当单称颜回,而不是将其与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并称,理同“雍也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48]可见在颜回死后,孔子对他的评价是不与其他人并提的,原因或许不只是孔子对颜回厚爱有加,而且孔子一生对死者都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正如“乡党篇”所言:“见齐衰者,虽狎必变。”[49]颜回卒年历来存有争议,但据钱穆先生《孔鲤颜回卒年考》,颜回之死应在哀公十四年春[50],钱穆先生此说较为可信。另据《左传》,哀公十五年闰十二月,子路亦死[51],在颜回卒后一年。因此,孔子评价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此言应出于哀公十二年至十四年春之间,最大的可能性是孔子在哀公十三年至颜回死前所说。退一步讲,孔子此言即便不是在颜回死前所说,也应该是在孔子六十九岁之后所说,因为孔子自卫返鲁是在其六十八岁岁末,而孔子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时则已年逾七十,孔子此处对宰予的评价,应为其晚年定论。
宰予从孔子游,每每反诘孔子,《论语》虽所记不多,但从宰我问“井有人焉”章和宰我问三年之丧章也可以看出,这两章宰我对孔子的反诘,是令孔子无法正面回答的。如“雍也篇”:“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52]宰我的这个问题,如果从正面回答,就应该答“从之”或者“不从之”,理由是什么,但孔子显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回答说君子是不可以陷害和愚弄的,但问题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仁人掉到井里了,君子究竟该从之与否,孔子却没有说。再如,“阳货篇”:“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53]同样,宰我说“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是一个问题,不服满三年之丧能不能心安,是另一个问题,孔子说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和宰予所说的“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则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这也许可以说宰予善于逆向思维,善于提出与孔子观点不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孔子难以正面回答的。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宰予的观点更多是针对春秋时代之现实而言的,而孔子的观点则是基于其“复周礼”的思想。
据毛奇龄《四书索解》[54]、《四书改错》[55]、《四书賸言》[56]以及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57]、胡适《说儒》[58]等篇的考证,三年丧服乃是殷人及殷遗民的通丧,春秋以前周之贵族尚不行此礼。《孟子·滕文公上》记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问孟子居丧之礼,孟子劝其行三年之丧,“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但滕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欲”,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59]可知在孟子以前的鲁国和滕国,国君都是不行三年之丧的。傅斯年和胡适都认为,就鲁、卫、宋、齐四国而言,宋国的国君和百姓均为殷遗民,而鲁、卫两国的国君为姬姓宗亲,齐国的国君姜氏为周之功臣,但鲁、卫、齐三国的百姓却多为殷遗民。《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60]可知傅斯年、胡适之言不虚。再如,鲁国有周社、亳社,《左传·定公六年》记阳虎执政,即“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61];宋国亦有亳社,《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或叫于宋大庙,曰:‘譆譆,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灾。”[62]亳是商汤的都城,亳社之“亳”即殷都之“亳”,亳社乃殷社,是殷遗民的祭祀之所。至于卫国,《尚书·康诰》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63]《史记·卫康叔世家》亦记,周公旦平武庚禄父和管叔、蔡叔叛乱之后,“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64];而齐国则是殷末薄姑氏之地,“薄姑灭,始有齐国;商奄灭,始有鲁国”[65]。此皆可证鲁、卫、齐之统治者为周之贵族,而百姓则多为殷遗民,这些贵族和百姓所行之礼及祭祀也都是不尽相同的,最初也只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而已。虽然自周初至春秋末期已六百余年,贵族与百姓的礼俗文化应有相当的彼此渗透、交融,但至少贵族与百姓的丧服之礼的差异仍然很明显。孔子是殷遗民,孔子所说的“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应为百姓(即殷遗民)的通丧,当时鲁国的贵族是不服三年之丧的,孔子的“复周礼”也是要恢复“监于二代”“因于殷礼而有所损益”的周礼[66],而宰予所说的久丧则礼必坏、乐必崩,或许亦有为鲁国贵族不行三年之丧辩护的意图。
因宰予的这些观点往往与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相左,所以孔子斥之“予之不仁也”,进而又有宰予昼寝章所记的怒责之辞:“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67]前文已论证过,孔子对宰予的肯定,是在孔子晚年,因而孔子对宰予的这些批评,时间必远早于后来对他的肯定,而不可能相反。到了孔子晚年,具体来说应在七十岁以后,孔子逐渐原谅了宰我,承认了宰我的言语思辨之才能,后悔自己早先对宰予责之过甚,并反思自己“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据《论语·先进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68]反过来看,能够帮助孔子完善自己学说之不足的,或许恰恰是敢于逆向反诘孔子的宰予,这可能也是孔子晚年原谅宰予并给予其很高评价的原因之一。此外,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假设。据《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自楚返卫后,卫出公辄欲使孔子为政,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随后孔子又讲了一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69]。据《左传》,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卫出公之父、卫灵公之大子蒯聩,因不满灵公夫人南子与宋朝,欲谋杀南子不成,故逃亡在外[70]。灵公卒后,南子立蒯聩之子辄为国君[71],即卫出公,蒯聩因不得归。按照昭公二十五年孔子适齐时对齐景公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72]的道理,出公辄理应迎其父蒯聩回来继位,但出公也许是迫于南子的势力,拒绝其父返卫,匡亚明先生说:“(出公辄)不论在所谓‘君臣’的名分上,还是在‘父子’的名分上,都不正。”[73]既然出公欲得孔子为政,而孔子言“必欲正名”,当然是要为出公正名,否则孔子就不可能打算出仕卫出公了。可见此时孔子的思想较其三十五岁适齐之时的思想已大有不同,孔子此时更加认同的是现实的情势。由此可以推想,当初宰予言久丧则礼必坏、乐必崩,也是出于鲁国贵族并不行三年丧服的现实情势。也许正是因为对现实的逐渐认同,孔子到后来或竟也能同意宰予当初所言的道理,这也不失为孔子晚年原谅宰予的理由之一。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未能得到证明,暂且存此一说,以待有心者辨之。
我们已经推定,孔子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应不早于哀公十三年,也就是说此言必为孔子七十岁之后所说,孔子以四科评价十个弟子的时间亦应与此相距不远,如前所述,其时间上限当不早于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返鲁,下限应不晚于哀公十四年春颜回去世。而孔子对于宰予,是专门说过要“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孔子晚年给予宰予很高的评价,当然应该看作是孔子长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果。而阚止在哀公十四年五月,就因与陈恒相争,而被陈恒所杀,司马迁说“孔子耻之”。哀公十四年,孔子七十一岁,距孔子自卫返鲁亦仅两年多时间。如果阚止就是宰予,我们该如何理解孔子的“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晚年对宰予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如果仅仅过了一两年,孔子就以之为耻,那么孔子对宰予的评价岂不是过于草率?对此我们只能认为,司马迁不可能比孔子更加了解宰予,在齐国为陈恒所杀的阚止,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宰予。司马迁说“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实应系误袭讹传。
其二,从《论语》哀公问社于宰我章所记之事可能发生的时间来看,宰予和阚止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论语·八佾篇》哀公问社章说:“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74]据《史记》“卫世家”[75]和“十二诸侯年表”[76],孔子于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去鲁适卫,然后周游列国达十四年之久,孔子去鲁之后至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返鲁以前鲁国发生的事,尤其是那些具体而微之事,若无专人传达给孔子,孔子是不可能了解得十分详细的。《左传·哀公三年》记鲁司铎失火,“火踰公宫”,大火烧了桓公、僖公的庙,“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77]春秋时期信息传达并不发达,鲁宫失火烧了桓、僖之庙这样的大事,孔子即便远在陈国,也是能够听说的,但孔子应不可能很快就知道具体情况,所以没有发表评论,只是感叹“其桓、僖乎”,如果当时孔子能够了解救火的细节,他一定会对弟子南宫敬叔在救火中首先抢救御书的出色表现大加称赞[78]。至于王肃《家语》“桓、僖之亲尽矣……是以天灾加之”之说,是为衍作,杨伯峻先生已辨之[79]。“哀公十四年”记陈恒弑齐简公,孔子请伐齐,以及“哀公十五年”记孔子闻卫乱,这些都是影响十分重大的事情,孔子当然也能够听说,子路和子羔都是常年跟随孔子的弟子,孔子十分了解他们的性格,所以也能猜到“柴也其来,由也其死矣”[80]。然而像哀公问社这样具体的事情,如果发生于哀公六年年底(即齐悼公即位,阚止和姜壬回到齐国)之前,当时孔子远在数百里乃至千里之外,或正辗转于陈、蔡及自楚返卫途中,且经历在陈绝粮等厄难,他如何能够了解到这些细节并做出回答?
哀公问社之事不可能发生于哀公六年阚止在鲁以前,其原因有三。第一,倘若问社之事是发生在阚止在鲁以前,而孔子听说这件事是在哀公十一年冬以后,则事情已经过去五六年了,孔子此时回答“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就只能理解为仅仅是孔子对哀公问社之事的态度,而不再是对宰予所答之事的态度,意思就成了“(哀公问社之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去追究这件事了”,这显然与文意不合。第二,据《左传》载,哀公七年夏,公会吴于鄫,吴征鲁百牢,“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81],其时应是孔子自楚返卫后,子贡去了鲁国,又受季康子委派至鄫辞吴。《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在陈绝粮,而使子贡至楚[82]。孔子在陈绝粮,杨伯峻先生认为时间是在哀公四年[83],此说盖本自江永《乡党图考》“绝粮陈蔡之间,当在哀四年自陈迁蔡时”[84];钱穆先生《孔子在陈绝粮考》和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则认为此时应为哀公六年[85],钱穆先生说“绝粮则以陈之被兵”,据《左传》,哀公六年,吴伐陈,楚救陈,“师于城父”[86],《史记·孔子世家》亦记在陈绝粮为“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之时[87],因而钱穆、匡亚明之说更为可信。据《史记·孔子世家》,则哀公六年子贡方从孔子游于陈、蔡,而孔子当年即自负函返卫,子贡为卫人,焉有不从孔子返卫而径去鲁国之理?崔述《洙泗考信录》也说:“吴人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贡辞,是子贡于反卫后先归鲁也。”[88]若子贡是自卫去鲁,则应在哀公七年春夏间,时间与季康子使子贡辞吴相符,而阚止已于哀公六年冬齐悼公即位后护送姜壬去了齐国,若阚止即是宰予,子贡至鲁应未及见到宰予。考诸《左传》《史记》,哀公六七年间从孔子于陈、蔡而后又得至鲁国,有可能了解鲁国细节之事的,仅子贡一人,然而即便我们假设问社之事发生在哀公六年,子贡在鲁国也听说过此事,亦无任何史料记载子贡曾向孔子转述过此事,更何况这一假设本身就于史无凭,因而难以据此推定问社之事发生在哀公六年之前。至于是否会有别人从鲁国来到陈、蔡,把这件事告诉孔子,可能性似乎也不大,即便有人从鲁国到卫国或陈、蔡见到孔子,也未必会把这么具体的小事告诉孔子,原因正如前面提到的哀公三年孔子在陈闻火,却不能了解到救火的细节一样。如果孔子不是在陈、蔡或返卫之时听说此事,并评论宰我之言,问社之事则不可能发生于哀公六年阚止如齐之前。第三,《论语》所记哀公事共五章,分别是“为政篇”哀公问何为则民服章,“八佾篇”哀公问社于宰我章,“雍也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章,“颜渊篇”哀公问有若年饥章,“宪问篇”孔子告于哀公陈恒弑君章,其中哀公问有若年饥章不涉及孔子,有可能是在孔子去世之后,而其余四章均与孔子有关,其中,哀公问何为则民服章、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章、孔子告于哀公陈恒弑君章均为孔子与哀公当面的对话。由此亦可推知,哀公问社于宰我,应距孔子自卫返鲁之时不远,而非在阚止如齐之前。且从此章孔子的语气上看,孔子之言若非亲自对宰予所说,亦必在哀公问社之后不久,孔子虽不同意宰我的观点,却没有像宰我问三年之丧章那样斥责他,说明此时孔子对宰我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与孔子自卫返鲁后所说的“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较为相近。
李惇《群经识小》说:“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灾,复立其主,故问其所宜木也。”[89]亳社灾见《春秋》“哀公四年”经,《左传·哀公七年》记“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囚诸负瑕”[90],说明亳社于哀公七年之前已复建,“复立其主”只能在哀公四年六月至七年之间,而哀公三年孔子在陈,后又至蔡、负函,钱穆先生《孔子自楚返卫考》和匡亚明先生《孔子评传》均认为,孔子于哀公六年当年便离开负函返卫[91],如前述,这期间孔子显然不太可能了解宰我答哀公之言,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再者,前文已说过,亳社乃是殷社,殷社的社主自当是“殷人以柏”,如果是亳社复立社主,宰予建议“周人以栗”,即采用周人的规矩,以栗木做社主,并意在“使民战栗”,那就只能理解为欲使作为鲁国百姓的殷遗民感到害怕。据胡适《说儒》的考证,“儒”作为一种职业,本是殷人中专司治丧相礼的教士,“儒”字的本义就是柔弱的意思,且凡从“需”的字多有柔弱的意思[92]。在某种意义上,“儒”的柔逊精神正代表着周代殷遗民的精神面貌。孔子之时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孔子对“儒”进行了改造,赋予了其“刚毅”“弘毅”“直道而行”等新内涵,但整个殷遗民的社会仍然是以柔逊为特征的,胡适说:“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的一种遗风。”[93]鲁哀公之所患不在国人,而在三桓,《左传》未见昭公、定公、哀公时鲁国有国人为患的记载,有作乱者皆三桓及陪臣。既然作为鲁国百姓的殷遗民本来就柔逊顺承,宰予又为何要建议哀公在亳社立栗木社主,而使百姓感到害怕呢?如果宰予确实是为了使鲁国的“民”(即殷遗民)感到“战栗”的话,恐怕即便孔子当时就能够听说哀公问社于宰我之事,他的回答也不可能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这几句话了,孔子应当会比昼寝章之言更加严厉地斥责宰予。因而可以断定宰予答哀公问社之言与亳社复立社主无关,宰予所说的“使民战栗”之“民”,绝非指祭祀于亳社的鲁国殷遗民,李惇此说是不可信的。
那么哀公问社之事究竟可能发生于何时呢?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引俞正燮《癸巳类稿》之说,“社”为木制土神牌位,即木主,国家有对外战争,则需载这一木主而行,木主即哀公所问之社[94]。考诸《左传》,自哀公元年至十六年孔子去世,不算哀公二、三年三桓伐邾,鲁国共对外用兵六次。其中鲁国被动迎战三次,分别是:哀公八年三月吴伐鲁,鲁国被迫与吴国结城下之盟[95];五月齐伐鲁,取讙及阐[96];十一年春,齐伐鲁,战于雩门,齐败[97]。鲁国主动出征的也有三次,分别是:哀公七年秋,鲁伐邾,囚邾子益于负瑕[98];十年春,鲁会吴伐齐,适逢齐悼公被弑,未得志而返[99];十一年五月,鲁会吴伐齐,于艾陵大败齐师[100]。六次战争,鲁国三胜、两败、一次罢兵。其中哀公七年伐邾得胜,又因八年吴、齐伐鲁而归邾子,这次胜利不能算完胜,而鲁国两次完胜,均在哀公十一年。那么,会不会是在鲁国两次打败强齐之后,哀公问宰我社主所用之木?我以为极有可能。
鲁国是弱国,夹在吴国、楚国和齐国三个大国之间,晋国亦虎视于西北,鲁国历来不敢与大国用兵。据《左传·定公十年》记载,定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因孔子相,定公方免受齐人之辱[101]。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大败齐师后,据《左传》载:“季孙命修守备,曰:‘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102]可见鲁国战胜强齐,是多么不容易的事。鲁国是周公的封国,于周礼最为完备,但据《左传·昭公七年》载:“三月,公如楚……孟僖子为介,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103]定公五年九月,阳虎囚季桓子,以陪臣执国政[104];再如《论语·八佾篇》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杨伯峻先生认为所指的可能是昭公二十五年逊齐之事[105]。可见在昭公和定公时期,鲁国就已礼坏乐崩,到哀公时期则尤甚,哀公十四年,陈恒弑齐简公,孔子再三请哀公伐齐,公曰:“子告季孙。”[106]这就是《论语·季氏篇》孔子所说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107]。从哀公即位到孔子去世的十六年里,可以说唯一让哀公恢复了一点信心的就是在哀公十一年鲁国两次打败齐国之后,只有此时,哀公才会重新重视祭祀之礼和征伐所载之社主,因而哀公问社于宰我,当在哀公十一年败齐之后或岁祭之时,此时宰予回答说“使民战栗”,意思就是以栗木社主来树立鲁国、鲁师之威而足以使“民”惧,国人不敢造次,邻国亦不敢轻犯而已,“民”在此处就不是专指某一阶层或族群。而此时已是孔子自卫返鲁前后,孔子当然能够听说哀公问社之事,并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来告诫宰予,因为孔子向来是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08],“修文德”[109]而使天下归服的。此虽为推论,但并非无据于史实,而且也只有这样解释,宰予答哀公问及孔子告诫宰予之言才能于理为洽。与此相同的另一个事实是,《论语·雍也篇》所记“孟之反不伐”[110],说的就是雩门之战中的事情,此言亦是孔子返鲁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所说的。
至于宰予是否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已无信史可考。宰予从孔子游于陈、蔡之说,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慎人》(钱穆先生误为“慎大篇”):“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宰予备(惫)矣。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111]钱穆先生以为此说不足信,我同意钱先生的这一看法。《史记·孔子世家》说楚昭王欲以书社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说:“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112]但孔子至负函见叶公,并未见楚昭王,此为司马迁误承衍述,前人辨之已多。如果宰予没有跟随孔子周游列国,而哀公问社于宰我又在孔子自卫返鲁前后,则哀公十一年宰予仍在鲁。孔子返鲁,在齐已是简公元年,其时阚止已在齐国执政事,此时宰予就不可能既在鲁国,又在齐国为政,那么阚止和宰予也就不可能是同一个人。孔子闻哀公问社之事,回答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当然首先是孔子对宰我所说之事的态度,至于是否也含有孔子对宰予既往不咎的意思,结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说的“以言取人,失之宰予”来看,似不能完全排除此意。
孙奕《履斋示儿编》说:“哀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公遇孟武伯,问曰:‘余及死乎?’三问,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哀公二十七年)。则哀公怀去三桓之心久矣,而患其强,故假古人‘弗用命则戮于社’之意以问焉。宰我谓‘周人以栗,使民战栗’,劝之以诛也。圣人警之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之三语,谓三桓自宣公以来至于今,势偪公室,积威五世,莫能制之也。一旦而欲诛之,则昭公之事可鉴矣。哀公苟知自治,则三桓之祸自息,无事于诛也。”[113]孔子的话里似乎确有告诫宰我之意,若果如此说,则哀公问社于宰我之时,孔子已在鲁,孔子以三语“警之”宰予,不可能在千里之外“警之”,亦不可能事隔很久之后才“警之”,那么其时必在哀公十一年冬以后,如此宰予和阚止就更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了。但孙奕所说哀公问社的原因,是欲去三桓,“故假古人‘弗用命则戮于社’之意”,托社以问宰我,这种解释则恐为臆度之说。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反被三桓所逐而“逊于齐”[114],此即孙奕说的“昭公之事可鉴”;定公八年,阳虎欲去三桓,亦为三桓所逐[115]。定公十二年,孔子为鲁司寇,将堕三都而不成,仅堕费、郈二都[116],其时鲁国政在季氏,季氏政在陪臣,三桓积弱之时尚不可图,及至哀公十一年前后,三桓复为一体,伐邾、抗(伐)齐,鲁国均以三桓为主力,即使当时哀公已“怀去三桓之心”,他又何以能够除掉三桓?公室与三桓的力量之悬殊,并非只有孔子才能看得出来的。及至哀公二十七年,公为三桓所胁,不得已才孤注一掷,“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而终逊于越,这已是十几年之后的事情了。孙奕称孔子在世之时哀公便欲去三桓,因而托社以问宰我,此理由当不足信。
其三,从文献所记之事理来看,宰予和阚止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之事[117],应多为后人假托,前人辨之已多,且其所记与《左传》不合之处亦甚多。其事记艾陵之战前,孔子使子贡出使齐、吴、越、晋四国,艾陵之战为哀公十一年五月之事,其时孔子在卫,若孔子确曾使子贡出使四国,岂能不见于《左传》?《左传》记季康子使子贡辞吴,是在哀公七年,而非十一年,且子贡仅至鄫见大宰嚭,并未至吴。再者,艾陵之战为齐简公元年,阚止已在齐执政事,若阚止即是宰予,子贡到了齐国焉有不见宰予而单说田常之理?据《左传》,艾陵之战时子贡确实在鲁师,并代叔孙州仇接受吴王所赐之甲[118],若子贡确曾于艾陵之战前出使过齐国,则阚止必定不是宰予,否则子贡一定会先去见他。另据《左传·哀公十五年》载,“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119],子赣即子贡,若艾陵之战齐国大败,是因为田常听信了子贡的游说之言,子贡岂能再去见田常,并且几句话就帮鲁国要回了当年春天因叛乱而被齐国所得的成地?若《史记》所记子贡出使四国之事不实,那么司马迁说“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恐亦不实。
宰我、子贡同列言语之科,孟子称其“善为说辞”,宰予之善辩已见于《论语》,宰予提出的问题往往连孔子都难以正面回答。然而参之《左传》,阚止则不仅并非“利口辩辞”之人,反而是一个狂妄自大得有些愚蠢的人。据《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初,陈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己,已有丧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陈豹者,长而上偻,望视,事君子必得志,欲为子臣。吾惮其为人也,故缓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为臣。他日,与之言政,说,遂有宠,谓之曰:‘我尽逐陈氏而立女,若何?’对曰:‘我远于陈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陈氏。”[120]《左传》记阚止之言虽然只有这几句话,但其志得意满且目空一切的面貌已跃然纸上。陈氏在齐根深势大,不逊于世为国老的国、高两家,《左传·昭公三年》记齐景公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晏婴就对叔向说过“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121],李斯也说陈氏“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齐景公卒后一年,陈僖子即废安孺子荼,立齐悼公。至齐简公四年春,阚止为政方及三载,就欲“尽逐陈氏”,可见其于时事之不审、自大而不量力;公孙向阚止推荐陈豹时,已经告诉阚止陈豹不可用,阚止却不以为然,“何害,是其在我也”一语,足见其狂妄不智。阚止与公孙及陈豹的对话,哪里有能言善辩的宰予的半点影子?仅从这一点来看,阚止和宰予也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钱穆先生以“《论语》本成于齐鲁诸儒,其书出于战国时,田氏已得志,而鲁亦为田齐弱。岂田氏之于宰我,固有深恨。而朝政之威,足以变黑白”,以及宰予未尝从孔子游于陈、蔡,因而认为阚止即为宰予,恐不足为凭。宰予为田常所杀之说,最早见于《韩非子·难言》,《吕览》、李斯复述之,因而讹误相传,韩非之世距陈恒杀阚止时已二百余年,且《韩非子·显学》称澹台子羽“行不称其貌”已误,另外韩非说“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而智不充其辩”亦与《论语》不合,从《论语》宰我问“井有人焉”章和问三年之丧章来看,宰予是非常善于逆向思维的,韩非说宰予“智不充其辩”,显然不符合事实,真正“智不充其辩”的,倒更像阚止,而不是宰予。《论语》为孔门后学所记,距孔子年代最近;而据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考证,《左传》成书年代在前403年之后、前389年以前[122],距孔子去世亦只有八九十年。我们没有理由不信《论语》《左传》而信韩非之言,《史记》《说苑》则所出更晚,《史记》与《左传》所记相左者,我们应以《左传》为凭。依杨伯峻先生的考证,则《左传》成书亦在田氏得志以后,何以《左传》记陈氏不美之辞甚多,而齐鲁诸儒竟摄于田氏之威,加丑宰予于《论语》呢?
此外,《吕览》《史记》《盐铁论》等所记互相矛盾者甚多,《吕览》《淮南子》《说苑》均说宰予与田常相争,司马迁却说宰我“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似说宰予与田常为同党,崔述《洙泗考信馀录》就说司马迁“措辞不审”[123],郑玄和《家语》都说宰予是鲁人[124],若宰予果真为政于齐,举家迁于齐或可信,何以举族迁于齐?若否,“以夷其族”则又当何解?再者,如前文所说,宰予从孔子游时,其言论多不见容于孔子,因而孔子屡斥之,及至孔子七十岁以后,他原谅了宰予,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若仅隔一年,宰予就为陈恒所杀,而且“孔子耻之”,“听其言而观其行”以知人的孔子,焉能如此反复无常?再次,《盐铁论》说“宰我以柔弱杀”,然而观诸《左传》,阚止不仅不“柔弱”,反而恃强以欺陈氏。《说苑·指武》说“田成子常与宰我争……鸱夷子皮闻之,告田成子”,鸱夷子皮即灭吴后逃亡到齐国的越大夫范蠡,洪迈《容斋随笔》认为“此说尤为无稽”[125]。以上这等相互矛盾之说,如何可信?
因此,我们从时间上和孔子与宰我之言的语意上推论,已均可得出宰予和阚止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结论。阚止确为陈恒所杀,但没有任何可靠史料记载宰予之所终。从孔子晚年对宰予的评价来看,宰予最终是获得了孔子的肯定的,并且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孔子对宰予的看法是在其晚年发生改变的,而正是孔子自卫返鲁前后,孔子的思想在晚年发生过较为深刻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应该莫过于受到《易》的影响,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了。
(本文系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支持计划资助项目《宰予、阚止非一人辨》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jbyz-009;同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注释:
[1]《论语·先进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三)第7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2]《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史记》(卷七)第2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孟子·公孙丑上》,载焦 循:《孟子正义》(上)第2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4]《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史记》(卷七)第21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5]《左传·哀公五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6]《左传·哀公六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7]《左传·哀公十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55-16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8][9][10]《左传·哀公十四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82-1683、1684-1686、16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韩非子·难言》,载[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12] 《吕氏春秋·慎势》,载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下)第465-4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13]《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史记》(卷七)第21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史记·李斯列传》,载《史记》(卷八)第25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5]《淮南子·人间训》,载何 宁:《淮南子集释》(下)第12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16]《说苑·正谏》,载向宗鲁:《说苑校证》第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17]《说苑·指武》,载向宗鲁:《说苑校证》第3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18]《盐铁论·殊路篇》,载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上)第2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19]《盐铁论·讼贤篇》,载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上)第2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20]《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载《史记》(卷七)第21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21][宋]苏 轼:《史评·宰我不叛》,载《坡全集》(下册)第206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旧称《志林》。
[22] [宋]苏 辙:《古史·孔子弟子列传》(《古史》第三十二卷),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第371册第480-481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3][宋]孔平仲:《司马迁之误》,载《孔氏谈苑》第1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24][宋]洪 迈:《宰我作难》,载《容斋随笔》第401-40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25][宋]孙 奕:《杂记》,载《履斋示儿编》(二)第14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26][清]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宰我》,载[清]阮 元、王先谦编:《清经解》(第一册)第97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27][清]崔 述:《宰我》,载《洙泗考信馀录》第4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8][清]赵 翼:《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载《陔馀丛考》第9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29][清]惠 栋:《春秋左传补注》,载[清]阮 元、王先谦编:《清经解》(第二册)第741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30][清]全祖望:《经史问答》,载[清]阮 元、王先谦编:《清经解》(第二册)第524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31][清]宋翔凤:《阚止》,载《过庭录》第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2]钱 穆:《宰我死齐考》,载《先秦诸子系年》第59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33]钱 穆:《宰我死齐考》,载《先秦诸子系年》第60-61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钱穆先生误记崔述此语出于《洙泗考信录》。
[34]《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史记》(卷七)第2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35]《韩非子·显学》,载[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第459-4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36]参见黄怀信等:《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下册)第777页,[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37][48][52][110]《论语·雍也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二)第391、365、415、3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38][53]《论语·阳货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四)第1188-1189、1231-1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39]《左传·哀公十一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40] 孔子生年从《史记》、钱穆《孔子生年考》、匡亚明《孔子评传》之说,为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参见《史记》(卷六)第19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钱 穆:《先秦诸子系年》第1-2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匡亚明:《孔子评传》第1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史记》(卷七)第2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42] 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三)第7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43][44][45][46][47]《论语·先进篇》,见程树德:《论语集释》(三)第777、746、746、772、7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49]《论语·乡党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二)第7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50] 钱 穆:《孔鲤颜回卒年考》,载《先秦诸子系年》第55-56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51][80][106][119] 《左传·哀公十五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94-1696、1696、1689、16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54] [清]毛奇龄:《四书索解》(卷一),载《四书索解、三礼指要》第4-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另参见《胡适全集》(第4卷)《说儒》附录二第99-10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5] [清]毛奇龄:《四书改错》(卷九),见《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四书类)第165册第8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另参见《胡适全集》(第4卷)《说儒》附录二第101-10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6] [清]毛奇龄:《四书賸言》(卷三),载[清]阮 元、王先谦编:《清经解》(第一册)第75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另参见《胡适全集》(第4卷)《说儒》附录二第100-10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7] 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载《胡适全集》(第4卷)《说儒》附录一第90-9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8] 胡 适:《说儒》,载《胡适全集》(第4卷)第1-8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9] 《孟子·滕文公上》,载[清]焦 循:《孟子正义》(上)第322-3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60] 《左传·定公四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536-15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61] 《左传·定公六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5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62]《左传·襄公三十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三)第1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63]《尚书·康诰》,载[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64] 《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史记》(卷五)第15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65] 胡 适:《说儒》,载《胡适全集》(第4卷)第1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6] 参见《论语》“八佾篇”“为政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一)第182、1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67]《论语·公冶长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一)第310-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68]《论语·先进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三)第7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69]《论语·子路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三)第885-8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另见《史记·孔子世家》,载《史记》(卷六)第1933-19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70][120]《左传·定公十四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597、1683-16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71] 《左传·哀公二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72] 《论语·颜渊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三)第8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另参见《史记·孔子世家》,载《史记》(卷六)第19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73] 匡亚明:《孔子评传》第73-7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74]《论语·八佾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一)第200-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75]《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史记》(卷五)第15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76]《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史记》(卷二)第6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77][121]《左传·哀公三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22、1234-12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78]《左传·哀公三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南宫敬叔即孔子的弟子南容,《论语》中孔子曾多次称赞他,并以其兄之子妻之。
[7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81]《左传·哀公七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82]《史记·孔子世家》,载《史记》(卷六)第19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83][94][105]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10、30-31、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84] [清]江 永:《乡党图考》,载[清]阮 元、王先谦编:《清经解》(第二册)第28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85][91] 参见钱 穆:《先秦诸子系年》第49、53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另参见匡亚明:《孔子评传》第71、7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6] 《左传·哀公六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87]《史记·孔子世家》,载《史记》(卷六)第19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88][清]崔 述:《洙泗考信录》第6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89][清]李 惇:《群经识小》,载[清]阮 元、王先谦编:《清经解》(第四册)第871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90] 《左传·哀公七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92][93]胡 适:《说儒》,见《胡适全集》(第4卷)第6-7、1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95][96]《左传·哀公八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48-1649、16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97][100][102][118]《左传·哀公十一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59-1660、1661-1663、1665、16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98][103]《左传·哀公七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43、12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99][101]《左传·哀公十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655-1656、1577-15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04]《左传·定公五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5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07][109]《论语·季氏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四)第1141、1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08]《论语·为政篇》,载程树德:《论语集释》(一)第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1]《吕氏春秋·慎人》,载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第33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112] 《史记·孔子世家》,载《史记》(卷六)第19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13][宋]孙 奕:《履斋示儿编》(一)第4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114]《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463-14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5]《左传》“定公八年”“定公九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568-15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6]《左传·定公十二年》,载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第1586-15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17]《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史记》(卷七)第2197-2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前言” 第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23][清]崔 述:《洙泗考信馀录》第4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