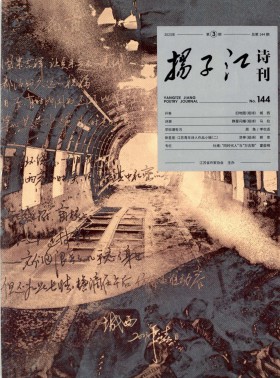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开卷有益的名言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开卷有益的名言范文1
现在的同学可能都喜欢看武侠、言情只类的小说、书刊,有时会达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程度,他们一旦看迷了书,便会走火入魔,那他们上课一心只想着书,没心思学习,成绩就会一落千丈。还有些人被书中的一些情节所吸引,模仿书中的人物,有时还会走向犯罪的道路。这不是看书害了自己吗?这只是“开卷未必有益”中包含的第一层:开卷不一定有益。还有第二层。
其二就是,我们看书,要有选择。那些不健康、对我们没有多大帮助的书,就不要看。要看书,就看一些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对我们学习、生活中都有帮助的书。这样的书就是好书,只有看好书,就不会毁了自己。有人把书比作了朋友,看好书,就是交好朋友,才会进步;则看不好的书,当然是交不好的人作朋友,那样你就会退步。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所以,只有看好书才会对你有益。因此,我的观点是:开卷未必有益。我真心的希望,每位同学都能有选择的看书。而不要因为看错了一本书,将自己引入歧途,毁了自己的一生。
“开卷有益”。这话自从宋太宗赵光义说过以后,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千年以来,它为无数人所接受,口耳相传,奉为至理名言。父母对子女、长者对晚辈常常要教导或督促他们“好好读书”,认为只要读书就会获得知识,得到好处。因此,人们常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其实,开卷是否有益是要看书的好坏而定的。那书是好书,开卷便有益;而如果那书不是好书而是坏书,开卷就非但无益而且有害。近年来我们的书刊市场上出了许多好书,但也出了不少坏书。你到大大小小的书店书摊书市去走走看看,随处都能找到几本坏书。什么《马屁精》啦,什么《损人大全》啦,什么《面子学》啦,等等,这类教人学坏的书,对青少年读者只有毒害和腐蚀作用,而无任何益处。至于那些宣扬各种消极颓废、玩世不恭的思想情趣、人生哲学的书,表现黄色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书,那就更是开卷有害的了。
讲开卷有益的人,绝大多数是出于好心。他们讲开卷有益,本意就是讲的读好书。但是,现在的世道很复杂,也确有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把坏书当作好书向世人特别是青少年推销。他们也说开卷有益,可那却实实在在是对读者有害。
开卷有益的名言范文2
齐桑镱首先向我“开炮”了,她学着教材中的人物,挺了挺下巴,笑眯眯地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有名人都是读书长大的,因此,我认为开卷有益!”
我也不甘示弱:“但书也有坏的地方啊!所有名人虽说是看书长大的,但有些罪犯也是被一些不健康的书带大的啊!而且,倘若读到一本不健康的书,甚至会影响到人的一生!”说完后,我得意地瞥了一眼齐桑镱。
似乎觉查到对手不是那么好战胜的,齐桑镱急得满面通红,突然,她急中生智地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她似乎松了一口气,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好你个齐桑镱,竟然用名人名言来压我。算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不紧不慢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如果一味按书里的话去做,等于害自己。许多人就是按照一些不健康书里说的去做,才走上了一条弯路。”
齐急了:“有这种人吗?”
我一听,急忙说:“当然有!”
齐稍微思考了一下,扬了扬下巴:“我指开卷有益的是好书,因此,我是正确的。”
这未免也太强词夺理了吧,我有点儿急了:“你知道‘未必’是什么意思吗?”
“嗯?”
“不一定。因此,‘开卷未必有益’的意思不就是看书不一定有好处吗?”我终于把这个词的意思硬是给扭转过来了。
开卷有益的名言范文3
乙方:妈妈
甲方:我觉得开卷无益,因为有些不健康的书就会错误的引导我们。
乙方:“是吗?我觉得开卷有益,因为只有增大书量,才能更好的扩大知识面,了解更多,况且,你们就一定要去看那些无益书吗?”妈妈耐心的指导我。
甲方:“那到是,像我这样非常的自觉,非常的……。
乙方:“打断,这可是在辩论。
甲方:哦。继续,继续。
乙方:如今,开卷有益这一词已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四字成语。确实,博览群书能使人拥有高深的学问,能言善辩,受人尊敬。古代诗圣杜甫有句名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你不善于去读书,那你写作文半天都憋不出一个好词好句。相反,只要你多读书,勤记录。那书的帮助就大了。”妈妈说,“你说呢?
甲方:是啊,一本好书胜过一个珍宝,一本坏书比任何坏人都坏。
乙方:一个人的美好前途就在于他所选择的书籍的种类,如果他所选择的是有益的书籍,那么他的前途将一片光明,但如果他选择的是一本无益的书,那他的前途就是黑暗的。但如果他能及时悬崖勒马,改过自新,我相信他也能有美好的前途。所以说:“开卷未必有益”这一说法也并不是完全真确的。
甲方:是啊。书能给我们提供素材;提供‘墨水’;提供知识。当然,书的好处也可想而知。但是,大家一定都知道这个故事,有一个人,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去学屠龙术,最后终于被他给学成了,但是,却找不到一条龙,学会的知识派不上用场,想必,书也要有所选择。
开卷有益的名言范文4
一、增加背诵量,积累词句
背诵,能增加词汇的积累量和句子的积累量,这是写作的根本。古人读书都是以背诵为基础的,唯有背诵足够的词句篇章,才能做到“出口成章”。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增加学生的背诵量。
为此,我建议根据学生年龄特点的不同,选择适当的背诵内容。一、二年级以背诵优秀的儿歌、儿童诗为主;三、四年级在儿童诗的基础上增加优秀散文、记叙文语段为主;五年级在散文、记叙文语段的基础上,增加经典现代诗歌的背诵;六年级则应增加优秀古诗词、古文及名人名言的背诵内容。
背诵内容的选择必须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发展特点及实际情况,还要顾及学生实际考试的需求,以课外内容为主,课内为辅。如,有些教师或有些学校,强行在一、二年级要求学生背诵《千字文》、《三字经》等古文,本人认为是十分不可取的。低年级学生在文字掌握量相当小的时候,对古诗文是难以理解的,背起来累,教起来更累,完全没有必要。倒不如背诵今人创作的儿童诗,既好背又好理解,同时也积累了一定量的词汇和语句。而到了高年级,学生对文字的感悟能力有了一定的提升,再背诵儿歌就不些不太合适了,所以可以加入古诗文的背诵。
二、增加阅读量,开阔视野
所谓“开卷有益”,广泛的阅读仍然是作文能力培养的重中之重。在大量背诵的同时,我们还要引导学生广泛地进行课外阅读。教师要努力使学生树立“开卷有益的思想,努力使学生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定期开展读书汇报,读书交流等活动,并引导学生做好读书笔记。对于课外阅读内容的选择,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广泛涉猎原则。写作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字游戏,需要更开阔的视野,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这就需要课外阅读能够涉猎更多的领域和种类。从知识领域上讲,天文、地理、科技、生物、文学等方面能读则读;从体裁上讲,散文、诗歌、小说、传记等,只要思想健康,尽量多读。
2. 兴趣先导原则。课外阅读,要先建立阅读的兴趣,体验阅读的快乐,所以初始的阅读应该是建立在学生兴趣的基础上的。要尊重学生的兴趣选择,喜欢读什么就让他读什么,不能强求一律按照学校或老师的意愿去读,那样只能是让学生更加讨厌阅读,最后事与愿违。当学生对阅读不再抵触的时候,学校或教师再加以引导,去阅读那些“指定”书目。
3. 文学名著导引原则。文学名著对学生的写作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在兴趣阅读的基础上,要逐步引导学生读一些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鲁宾孙漂流记》、《老人与海》等。低、中年级可从拼音版或简化版开始,高年级可适当读完整版。为增强学生阅读名著的兴趣,教师和学校可适当开展读书笔记展评、撰写读书体会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会读书的乐趣。
4. 恰当使用现代媒体原则。当今社会,阅读已不再只是纸面上的阅读,现代化的电子媒体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阅读空间。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媒体上有更为丰富的可读内容,且更为方便快捷。教师要善于利用这些媒体,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和《子午书简》等栏目就是非常好的拓展阅读渠道,利用好了,将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增加练习量,强化表达
在加强背诵和阅读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表达,可分为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表达能力的提升,别无他法,唯有多写多练。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地增加学生表达的训练。
在口头表达训练上,我们可以利用每节课的前五分钟,或者是课间、早自习等时间,引导学生进行口头表达训练。例如,选择最近一段时间内校园、社区、国内、网络上的一些热点事件,让学生自由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和评论。对于学生的评论,教师应鼓励个性化的看法,不必强求一致,只要不违反伦理、道德、法律等大原则即可。教师要及时予以鼓励性的评价,保护学生表达的自信心。
在书面表达训练上,可根据年级的不同,安排相应的训练内容。一年级可以在有限的文字积累基础上,做一些看图写话的训练;二年级可增加连词成段或篇的想象型训练。即给出三个或四个词语,让学生用给出的词语写一段话,并有完整的语意;三、四年级可以写周记、日记。不要怕写“流水账”,写了就比不写强,写得多了就不会再写“流水账”了;五、六年级可增加片段写作训练,如写景片段、写人片段、叙事片段。也可以写对热点事件的体会或评论。学生的书面表达训练要留好痕迹,装订成册,长期保存,以备观察分析训练效果。对于书面表达,教师不必详批详改,只需正面引导,掌握基本情况即可,无需加大工作量。
四、增加体验量,提高情商
要写出有一定水平的作文,除了知识和手法外,更需要较高的情商。情商高,才能对人、事、物有更深刻的感悟,才能使作文更加深刻,更加动人。而现在的学生整天除了上学就是与网络游戏为伴,很少接触社会,很少体会人间的悲欢离合、人情冷暖。所以就出现了智商高、情商低的现象。情商低导致学生拿到写作题目后,不知写些什么,不知要表达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也流于形式,索然无味。
那么,该如何提高学生的情商呢?我认为可以从增加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心理调控入手来进行培养。
1. 强化道德体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教会学生分辨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可以通过讲座、讨论、读道德故事等方式增加体验,也可以通过现代媒体增加体验,如电视台播出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最美教心少年”颁奖典礼等,都是强化道德体验的良好教材。
2. 强化健康的心理调控,帮助学生塑造健康的心理品质。有意识地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大力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学生控制情绪,学会处理现实与愿望的矛盾,提高承受和应对挫折的能力。教育学生要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并善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帮助学生形成健康向上的心理。
增加情感体验,提高情商,就是要让学生的情感更丰富,对事物更加敏感,更善于用心去体会生活、感知世界。把这些体悟写进作文,能让作文更有深度,更具感染力。
五、增加实践量,丰富阅历
经历就是是财富,这话一点不假。现在学生拿起笔不知作文写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历的事情太少,缺乏足够的阅历,也就缺乏足够的写作素材。现在的学生足不出户,过多地面对液晶屏幕,已成不争的事实。是现代化高楼大厦、电子媒体,以及过于封闭的生活空间造成了学生阅历的极度匮乏。我们教育者应该看到这些实际问题,也应该拿出可行的办法,有意识地给学生创造一些增加阅历的,体验生活的机会。
开卷有益的名言范文5
一、培养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是现实要求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题为《学习——内在的财富》的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教育将是终身教育,21世纪的社会将是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要求每个人都能自觉地学习,而每个人自觉地学习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是否热爱阅读。可以说,阅读是学习之本,是立教之根,是生存之道。朱永新教授说:“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在一定意义上说,读书就意味着教育。”
小而言之,课外阅读是顺利完成中学语文教育任务的重要保证。前苏联教育专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阅读可以发展学生的智力。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一次语文教改交流会上曾说过:语文教学应重视课外阅读的引导。事实也表明,要想提高语文教学的效果,提高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就不能拘泥于课本,拘泥于课堂,只有既立足于课堂教学,又注目于课外阅读,才能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纵观近10年的高考试卷,也可以看出阅读与语言的运用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方向。
实际上,我国中学语文教育对阅读也是一贯重视和提倡的。以前的“高中新大纲”突破了传统语文教学框架,建立了课内外结合的新框架,对语文课外活动做了不同于以往的强调。把课内教学和课外学习相互促进确立为高中语文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高中语文教学的一大变化。而现在《新课标》的实施将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提高高中学生阅读能力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
二、中学语文教学如何培养学生课外阅读兴趣
首先,培养学生读书兴趣,作为语文教师,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是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读书人。朱永新教授说:“学生读书的兴趣与水平直接受教师的读书兴趣与水平的影响。因此,教师的读书不仅是学生读书的前提,而且是整个教育的前提。”一个爱读书的语文教师,不会喜欢布置抄写10遍、20遍的课外作业,也不会喜欢发大量的试卷,而会鼓励学生走进图书馆,走向大自然,去阅读、欣赏、感悟、体验。而这样的教师在课堂上总是思接千载、神采飞扬。这样的教师已不再是蜡烛,而变成了引路导航的灯塔——既照亮学生,又永葆明亮。
其次,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应该尊重学生阅读自由。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能够去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也就是说在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过程中教师家长要给学生提供独立的阅读空间,给学生真正的阅读权利,在一定范围内尊重学生的阅读选择,除了必修课本上所列的那几本名著外,允许也鼓励学生再阅读其他一些有益的书。因为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阅读的兴趣是不一样的。只要是有益的东西,都要鼓励学生读。比如很多学生对大部头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感兴趣,而惊异、生动、幽默、情节曲折的作品往往能抓住青少年的心。比如 《奥秘》《小小说》《科幻世界》《灌篮》《足球周刊》等杂志,就以其内容的新奇、有趣吸引了很多的高中学生。《读者》《中学生》《格言》《意林》《青年文摘》等也以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清新隽逸的风格在高中学生中很受欢迎。现在有较多学生喜欢看漫画,教师家长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只要是健康的就放心地让学生去看去读。总之,教师家长要在“开卷有益”这一大前提下,不要太多的干预,让学生自主选择,愉快地读, 津津有味地读,尽情体味自由阅读的乐趣,收益会更大。
开卷有益的名言范文6
一、为少儿读者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
基层图书馆少儿阅览室的环境是少儿读者的第一印象,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因素。因此,每一个细节的布置都要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需求,尤其是基层图书馆少儿阅览室的环境要在满足其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在布局、装饰等方面要符合孩子的心理,做到让少儿读者进门的第一感觉就是快乐,既要有轻松、愉快的读书气氛,又要有激发儿童阅读兴趣的设施,如阅览桌采用颜色亮丽、形式活泼的几何式图形来拼装;书架的设计可以是形状各异、造型独特的“童话屋”等。墙壁上可张贴一些少年儿童自创或喜欢的图片或激励孩子们阅读的名人名言。这样不经可以提高小读者的阅读兴趣,还可以达到鼓励、培养孩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的目的。在建立良好的物质环境的同时,还要重视心理环境的营造。这就要求我门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小读者以及家长之间建立团结协作、互助互爱的关系,让家长和小读者信任图书馆,使图书馆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亲和力,营造出一种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和谐氛围。
二、合理调整少儿藏书结构
一是要重视品德方面,重视思想性格塑造需要。
二是要重视智力方面,注重开发孩子的能力,培养孩子的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是要重视体育方面,包括卫生保健、饮食营养体育锻炼、家庭活动。
四是美育方面,着重审美观点的培养,对美与丑的事物的认识与评价。可以采取多种渠道(选购、邮购)多种形式自购,师生代购(师生带去选购),到多种类型书店(综合型、专科型、特色型)来收集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献资料,使藏书结构趋向合理。
五是重视逐步引进多媒体,不断满足师生对信息的需求,应用现代化的设备整理、加工处理文献资料。
三、加强少儿读者的阅读指导
基层图书馆少儿阅览室的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同学们所具有的求知欲望开展有针对性的阅读指导。通过推荐书目、专家导读,好书共读、读者评书、读书心得点评、共同讨论等方式积极引导青少年的阅读方向,指导他们领会学习的方法,增强阅读兴趣,提高青少年阅读水平,鉴赏水平和鉴别能力,从而提高学习能力。加强阅读指导是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和引导学生们阅读倾向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它是增强少年儿童阅读兴趣的催化剂,只有树立自觉的阅读兴趣,养成开卷有益的阅读认知,读书才能真正收到实效。才能在基层图书馆少儿阅览室浩瀚书籍中,巩固学到的知识,还可以通过阅读课外读物学到课堂上所学不到的知识。
四、注重少儿读者兴趣阅读的培养
开展饶有兴趣、丰富多彩的系列读书活动。加强读书活动的宣传力度,经常推出新书介绍、推荐书目、新书陈列,组织文学欣赏、文学评论、读者荐购读书活动、陈列优秀作品和名著介绍等;另一方面,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旋律,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为主,包括中外名著佳作,中外科技文化、中外名人传记,中国悠久文化史料、革命史料、民风异俗,能工巧匠、英雄豪杰、?魍趁赖隆⒔ㄉ璩删偷裙憷?知识,推选出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系列阅读书目,提供少年儿童选读。组织观看相关电影、电视、录相;听各种讲座和报告会。讲故事会,举办朗诵演讲会比赛,开展辩论会,读书竞答活动,书评。写论文,评论文章;比如组织“文学社”,“写作兴趣小组”,“书法美术班”。开展成果展览等。在开展读书活动时,注意把读书活动与社会实践、社会服务相结合,与文学艺术、科技活动,影视评论相结合,重视青少年读书活动中的娱乐性要求,寓教于乐,使读书活动和教育融合在一起,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培养提高青少年的阅读能力、自学能力、组织能力、创新能力、交际能力、审美能力和鉴别能力,开拓青少年的知识面,陶冶他们的情操。
五、提高基层图书馆馆员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