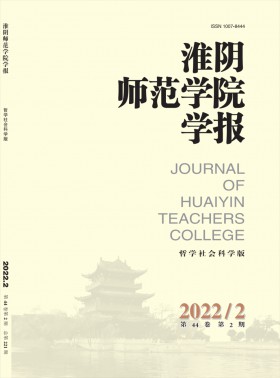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淮阴侯列传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淮阴侯列传范文1
韩信:
韩信(约公元前231年-公元前196年),淮阴人。西汉开国功臣、军事家、淮阴侯,兵家四圣之一,汉初三杰之一 ,中国军事思想“兵权谋家”的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神帅”。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是有关于他的典故。
秦末,参加反秦斗争,投奔项梁、项羽,未得到任用。转投刘邦,经夏侯婴推荐,拜治粟都尉,经萧何保为大将,为刘邦制定了汉中对策。刘邦兵败于彭城后,韩信先破楚军于京、索之间,后平定魏国。请命北伐拿下代国,刘邦收其精兵后背水一战击败赵国,派人降服燕国 。支援刘邦以及清除项羽派往赵国的楚奇兵,平定剩下的赵国城邑。刘邦成皋兵败夺其精兵后,奉命攻打齐国,并于潍水全歼龙且二十万楚军。韩信攻打楚国,项羽与刘邦签订鸿沟协议。刘邦听从张良、陈平计策撕毁鸿沟协议,追击项羽失败。汉五年,带兵会师垓下,围歼楚军。项羽死后解除兵权,徙为楚王,因人诬告贬为淮阴侯。吕后与萧何合谋,诱杀于长乐宫钟室,夷灭三族。
淮阴侯列传范文2
解释: 逐:追赶。鹿:指所要围捕的对象,常比喻帝位、政权。指群雄并起,争夺天下。
近义词: 龙争虎斗、鹿死谁手。
用法: 动宾式,作谓语、定语,含褒义。
出处: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来源:文章屋网 )
淮阴侯列传范文3
1、歇后语“韩信点兵”下一句:多多益善。
2、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来源淮安民间传说。寓意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形容一样东西或人等越多越好。益:更加,多;善:好。
3、出处及典故,西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子有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刘邦曾经闲暇时随意与韩信评论各位将领是否有才能,各自有高有低。
(来源:文章屋网 )
淮阴侯列传范文4
释义:韩信点兵的成语来源淮安民间传说。常与多多益善搭配!字面意思是:韩信带兵打仗,将士越多越好。后来的引申义为,形容越多越好,也有单取”多多益善“的。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例句:
1、学校考试的时候作文不会写,不过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只能硬着头皮写了。
2、老师决定明天带多少人去种树苗,小兰说人多力量大,当然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那干脆全班都带上。
淮阴侯列传范文5
《马政论》曰:“颡上有白毛谓之的卢。”又曰:“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谓之的吻,凶。”俗云的卢非也。刘备避樊城之难,过檀溪,谓所乘马的卢曰:“今日急,不可不努力。”马达备意,一跃三丈。又庚亮所乘马名的卢,殷浩以为不利主,劝市之。亮曰:“岂有已之不利,移之人者。”
《拾遗记》:曹洪与魏武所乘之马名曰白鹤。时人谚曰:“凭空虚跃,曹家白鹤。”
《西域赞》:蒲稍、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注:孟康曰:“四骏马名”。
《魏志》陈思王表文帝曰:“臣于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骍马一匹,教令习拜。
淮阴侯列传范文6
2、韩信点兵 [ hán xìn diǎn bīng ]:常与多多益善搭配。寓意越多越好。
3、韩信点兵的成语来源淮安民间传说。常与多多益善搭配。寓意越多越好。刘邦问他:“你觉得我可以带兵多少?”韩信:“最多十万。”刘邦不解的问:“那你呢?”韩信自豪地说:“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嘛!刘邦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那我不是打不过你?”韩信说:“不,主公是驾驭将军的人才,不是驾驭士兵的,而将士们是专门训练士兵的。”
4、多多益善 [ duō duō yì shàn ]:益:更加。越多越好。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