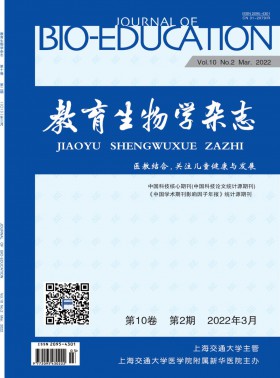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看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看法范文1
【关键词】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去哪里?” 是人类历史上对生命最深刻的追问。这种对于生命及其意义的追问。一提到生命,人们把它抽象化为一个神秘的概念,或把它看成世间生物都一样的基本存在形态。由于缺乏对生命的认识、理解、热爱和敬畏, 当个体面对自认为无法应对的压力和无法解决的困难时,就容易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彻底的解决方式,或者以伤害他人生命或其他生物的生命作为缓解压力的手段。
一、生命意义感的定义
生命意义感是一个模糊且难以界定的概念。Frankl(1969)提出人需要为某事或某人而活,人们需要他们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即有目的有意义。这种意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独特的,需要他自己去发现。
Crumbaugh(1973)认为生命意义是一种能给予个体存在有方向感与价值感的目标,通过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个体可以获得“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的认同感。
Hedlund(1977)认为生命意义指的是个体的意义,也就是“个体存在的理由”,当个体能意识到自己存在的理由时,个体就会感到有力量,并觉得自己存在是有价值的。
Fabry(1980)将生命意义分为两个层次:终极意义和此刻的意义,前者指宇宙中有一超越人类、且无法被验证的规律,有人称之为“神”,有人称之为“自然”,或其它名称如“道”;后者指在生命的每一瞬间皆有一个有待实现的使命,个人只能以负责的态度来对待。
Yalom(1980)也认为生命意义有两个层次:宇宙生命的意义和世俗生命的意义,前者指宇宙中有一不变的规律,而这规律是超越于个人之上或之外,非人类所能理解;后者指即个人有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在这过程中,个人可体验到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释慧开(2001)对人生的意义看法是:人生的意义在于不断地、深入地探索人生的意义。
综上所述,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生命意义感的定义越来越全面,尽管许多的学者对生命意义的定义不尽相同,但他们普遍都认为生命意义包括生命存在的价值和生命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两个方面。生命意义是属于高层次的心理需要,透过思索个体生存的理由或目的,找到生活的方向和目标;且每个人的生命意义会随着年龄、身分、角色、时空的不同而转变,同时生命意义感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生命意义包含着身心各方面的发展,是需要去引导与发现的。
二、生命意义的测量
在生命意义的测量中,问卷是最为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下面将介绍一些最为常用的问卷。
(一)生活目的量表
Crumbaugh和Maholick(1964)是最先根据Frankl的概念采用心理测量的方法来测量生活的意义。早期的研究几乎都是采用这种量表来测量Frankl的生命意义结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0到0.90之间。后来Crumbaugh (1977)又发展了对抽象目标的寻求量表以补充生活目的量表。
(二)生活指数量表
Battista和Almond(1973)编制了生活指数量表一种28个题目,5点计分的多维度量表,克服了生活目的量表的一些缺陷。Debat(1990)报告了Fulfillment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0,Framework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9。
(三)生活目的的问卷
生活目的问卷由Hablas和Hutzell(1982)编制,该问卷是一种单维的自我报告问卷,操作简单,用来测量社会机构中老年个体的生活意义。对年老和酒精中毒患者的研究发现LPQ与PIL的相关在0.60到0.84(Hablas&Hutzell,1982)。
三、生命意义感的实证研究
(一)对生命意义感现状的研究
周娟(2005)采用《生活目的测试》对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研究发现高职院校学生生命意义感总体状况不容乐观。42. 8%的学生处于生命意义和目的不明确状态,26.1%的学生处于生命无意义、无目的状态。
(二)生命意义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献中出现了许多有关生命意义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Zika和Chamberlain发现,在生命意义和情绪健康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生命意义能够持续地预测心理健康。Ganellen和Blaney的研究发现,淡化自我―――个同“意义”密切相关的概念,能够调节由应激引起的忧郁情。Coleman等的研究发现,药物成瘾与找不到“存在”的理由或生命意义有关。Yarnell(1971)的研究发现生命意义分数愈高的受试者,越少感到焦虑情绪,对自己的信心愈高。Reker(1994)的研究则指出,个人生命意义是健康最有力的正向指标;Weber(1996)则发现高生命意义感的人倾向于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三)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1. 性别。生命意义感是否受性别的影响,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女生的生命意义感得分普遍高于男生,贾林祥等(2008)采用《生命态度剖面图量表》研究发现男女大学生的量表总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与何英奇的研究一致。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无性别差异。
2. 年龄。Frankl (1986)指出最容易质疑生命意义的阶段是青春期。国外Meier和Edward (1974)研究结果发现 13-15岁和17-19岁两组青少年在生命意义量表之得分显著低于其它年龄组,表示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较低。
3. 不同生源。盛正群(2007)的研究发现,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生命意义的整体感差异显著。贾林祥等(2008)的研究结果,自农村的大学生意义意志因素评分高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但也有部分研究显示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生命意义并无显著差异。
4. 家庭教养方式。关于生命意义的相关研究中,对家庭教养方式的研究较少。江慧钰(2001)探讨其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气氛融洽的高中生,其生命意义相对较高,即高中生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会受到其家庭气氛融洽与否的影响。
四、研究不足
综观以往对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研究,发现国外对生命意义感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我国目前在生命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而更多地是将它看成一个哲学问题,忽略其在心理健康方面的作用。在很多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不足:
(一)关于生命意义的概念内涵尚不统一
生命意义是一个包含意义比较多的相对分散的概念,目前西方大量的实证研究也都是选择各自比较认同的理论来进行定义并验证,各研究者在同一维度上有时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因此,如何结合我国实际,确定我国生命意义的概念及结构是个待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生命意义的测量不成系统
由于概念的差异相应地也产生了不同的测量方法。不同的测量工具是否测量的同一种结构还有待验证,而往往同时不同的测量工具对同一个因素的研究结果也不同。因此,应该严格遵循科学方法,确定生命意义感的测量工具,确定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
(三)取样不全面
目前考察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龄、性别、专业等。以往的生命意义感集中于高中生、高职院校的学生,而没有对大学生这个特殊阶段的大学生进行过研究,这样就很难对整个阶段的生命意义感的进行发展性研究。
(四)关于生命意义的整体研究模型与设计不完善
虽然研究者研究了生命意义与许多相关变量的关系,但缺乏理论支持,致使相关变量的选择不成系统。因此,寻找理论依据,以理论为基础,系统地选择相关变量,探讨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生命意义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 肖长根.心理虐待与忽视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及对儿童自我意识的影响[D].中南大学,2006.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看法范文2
〔中图分类号〕 G6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4)19―0089―01
近年来,青少年非正常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其间固然有不同的个体原因,但目前青少年“生命意识教育”的严重缺失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多元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因素,使部分学生道德观念模糊、道德自律能力下降。如何让青少年学会善待“生命”,怎样更好地“生活”,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下面,笔者就结合工作实践谈几点看法。
一、当代青少年生命意识淡薄的原因
1.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当代青少年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开放式的环境,形形的思潮冲击着校园,一些不良的风气和不健康思想,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2.学校教育导向的偏差。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只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普遍忽视生命教育。学校很少甚至没有开展过生命教育,学生缺乏正确的生命价值观的指引。过分追求考试成绩的教育异化了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不懂得人到底为什么而活,怎样活,怎样面对人、面对生命。
3.家庭教育中生命教育的不足。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以及漠视生命的现象受很多因素影响,但对孩子影响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父母和家庭。很多家长把对孩子的爱极大地物质化,尽其所能地单向性给予,从而使孩子把被给予当作必然。这样容易导致孩子不懂得珍惜敬重与感恩回报,渐渐地不把父母、物质、金钱甚至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当回事。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丝毫不顾及他人的一切,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4.青少年思想教育体系尚不完善。目前,青少年思想教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不健全、不系统,尚未形成以立志建功为重点的理想教育、以学史建碑为重点的革命传统教育、以讲究职业道德、转变社会风气为标志的道德教育、以读书活动为具体形式的科学教育,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主义教育等一套较为完整而科学的青少年思想教育体系。
二、解决青少年生命意识淡薄问题的对策
1. 从社会来讲,要树立大德育的观念,发挥各种社会活动和公共环境的社会性德育作用。学校要与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建立实践基地,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等,把生命教育与实践活动融为一体;要利用媒介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比如大型健康咨询活动、讲座等来拓宽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渠道;要把生命教育纳入社区工作中,营造对青少年乃至全社会进行生命教育的社会环境。
2.学校开设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开设独立的生命教育课是实施生命教育的最基本的途径。为生命教育设置专门科目和课时,可以使学习内容更加系统和集中,降低实施的难度。学校应通过专门的生命教育课程传授生命知识,引导学生了解生命,培养他们健康的心理;通过学校德育课、伦理课与人生职业规划课程讲授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知识,引导学生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学校应通过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等形式让学生亲自体验合作的意义和关爱的价值,从而确立乐观上进的人生态度。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看法范文3
《初中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英语课程的学习,既是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和实践活动,逐步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过程;又是他们磨砺意志、陶冶情操、拓展视野、丰富生活经历、开发思维能力、培养合作精神、发展个性和提高人文素养的过程。”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英语教科书中蕴含着大量的生命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认识生命,引导他们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因此,在英语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职责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关注每个学生,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充分利用这些渗透着生命教育的载体,运用合理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汲取情感素养的精华,激发学生的生命意识,从而形成美好的心灵品格。
一、充分挖掘教科书中渗透生命教育的素材
在英语教科书中有大量有关生命教育的材料。文章内容涉及学校、家庭、家乡、社会、网络、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健康的生活方式、自然灾害、慈善活动等话题,这些都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如,学会理解尊重师长伙伴;学会建设性地与人沟通交往;学会调整和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提高承受挫折与压力的能力;积极锻炼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资源;学会拒绝烟酒和;理解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珍惜水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吃透教科书,挖掘其中的人文精神,善于创设各种生动的教学情境,完善甚至重建学生的生命意识,引导学生认识生命、珍爱生命、欣赏生命。 如,外研社编辑出版的八年级英语课本中以濒危动物为话题,介绍了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的生存现状。在教学过程中,笔者播放了两个小短片,一个是大象在非洲草原悠闲生活的影像资料,另一个是狩猎者残忍猎杀大象的影像资料,让学生看后小组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让学生进一步树立热爱动物、保护动物,共建人类和谐美好家园的意识。
二、在英语教学活动中渗透生命教育的理念
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设计中,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如研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等。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不能只靠口头传授,而应该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共同思考。
教师可以在教学中给学生布置一些与英语内容相关的任务,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完成对生命的认识和关爱。如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关爱自身健康这方面的知识,学生很熟悉。在“健康食品”一文的教学中,学生的兴趣非常浓厚,同时关爱自身健康的意识也在学生的心里得到了渗透。德国著名教育家斯普朗格曾说过:“教育的核心是人格心灵的唤醒。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讲,生命意识的培养是生命教育的起点。
教师还要充分发挥小组合作的力量。要想使小组合作学习有效地实施,首先要搭建好小组建设这一平台。我根据同组异质、异组同质的原则把全班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有组长、副组长、记录员、中心发言人等,真正做到小组内“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其次,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并以团体成绩为评比标准,激发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学生在合作学习中,通过与他人对话,可以体验合作学习的乐趣,并在相互接纳、相互诉说、相互倾听中养成尊重他人的品质,在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评价、互相激励、共同解决问题中懂得平等协作的重要性。不同的人,生命价值观是不同的,在讨论中分享各自的看法,摆正心态,学会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对于感悟和尊重生命非常重要。
三、通过积极开展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生命意识
很多学生耳熟能详的英文歌曲,不仅旋律优美动听,而且歌词积极健康,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赞美。平时,我会把歌词打印出来发给学生,并组织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歌唱比赛,让学生在边学边唱中提高英语口语及听力水平,寓教于乐,学生兴致很高;同时,通过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教育意义,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达到德育渗透细无声的效果。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看法范文4
关键词:英语教学 生命教育 学习兴趣
我们经常听到某某学校的学生跳楼自杀,某某学校的学生杀人等这样那样的新闻,终究其原因,现在的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让学生背上了很重的学业负担,老师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授,使学生能更好地参加应试,很少对他们进行生命意义的教育,因此导致这些现象的发生。
《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英语课程的学习是学生通过英语学习和实践活动,逐步掌握英语知识和技能,提高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的过程。现在大多数的孩子自我意识较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同学相互之间不能友好相处。因此,在英语课堂上,对其顺势加以引导,不但可以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同时更让学生得到良好道德情感的熏陶。所以作为一名英语老师,我们应在英语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因为可以帮助学生理解珍爱生命的含义和价值,并可以帮助学生提高鉴别、鉴赏的能力,同时通过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帮助学生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因而可以加深他们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正在形成过程中,他们思维活跃,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但他们缺乏必要的鉴别能力,容易走错路,做错事。作为一名英语老师,我们应在传授英语知识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英语教材中的丰富资源,对学生进行生命意义的教学。
所谓在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就是教师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不仅关心学生学的知识,还要关注学生情感的成长,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去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享受生命,优化生命,激扬生命,努力让学生学会感动,感悟生命的意义。如何在英语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一、充分挖掘并运用教材中的有关生命教育的素材
译林版的教材中有很多关于生命教育的素材,有关于家庭(M1 growing pains)、网络、自然、健康(M1 Losing weight)、学校生活(M1 Shool life),为人处事(M5 getting along with others),环境(M5 Environment)等题材,这些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些话题对学生传授知识教育的同时,进行生命意义的教育。例如,我们在教M1 growing pains,我们可以把话题引申到“与人为善,尊重父母,老师同学。在教M5 getting along with others把话题引申到如何建设性地与他人沟通和交往。在教M1 Losing weight把话题引申到如何调节和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去承受压力与挫折,如何积极锻炼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教M9 Aids today教会学生钦佩顽强的生命,对弱势群体要伸出援助之手。在教M5 Environment时把话题引申到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要保护环境,珍惜自然资源。在Time这一内容时,我把谚语“Time and tide waits for no man.”写在黑板上,要求学生读熟、背熟,并要求深深体会其中的含义。借此时机,教育学生千万要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发奋读书,切勿耽搁,再也追不回来的是时间、是青春,不要把悔恨留给自己,要把握今天,把握现在。
二、借助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命意义的教育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较强,他们往往不懂得关心别人,爱护别人。所以我们英语老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丰富的课外活动有目的、有计划地加以引导,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英语的热情,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得到良好的道德熏陶。例如,我每周开展一次读书活动,内容是于他们生活相关的话题,让学生讨论并提出自己该如何对待这些问题,从而培养他们关爱他人的情感意识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认知情感,使他们懂得因为人间有爱,世界才会美好。在教师节,我引导学生制作英语贺卡“Happy teacher’s Day”。在父亲节,母亲节时,引导学生制作英语贺卡“You are the best father(mother) in the world”等词。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动手交际和想象能力,而且还促进他们形成尊敬师长,尊敬父母的意识。另外,现在的独生子女缺少恒心和毅力。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要加强学生坚强的意志品质的培养。我经常开展“做……时间最长”活动,“个人爱好收藏品保存时间最长的人”“坚持写日记时间最长的人”“认真写作业坚持时间最长的人”等活动,锻炼他们的意志力,使他们在面对一个艰难的任务时永不言弃,从而在面对失败时,敢于面对,不会悲观。
三、借助多媒体引用社会素材,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
我在教“Olympics”这课时,制作了很多关于运动员的图片以及对他们的简介,同时还有意加入了很多残疾运动员的图片并让同学们讨论残疾人这个话题。当我利用多媒体播放了邰丽华等表演的“千手观音”,并介绍邰丽华的事迹时,学生们的心灵都得到了震撼,他们从这些人身上欣赏到了残疾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向命运低头那种顽强的意志力。通过这一活动,我相信他们会更加珍爱生命,努力使自己的人生更加灿烂。
四、把英语写作与做人教育结合起来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看法范文5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学;生命教育
当前,初中学生的心理状况不容乐观,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应受到广泛的关注。究其原因,“突遇一点挫折、打击,青少年就选择终结生命作为解决方式,除了青少年心理的脆弱外,还跟学校对青少年缺乏生命教育有关”。可见,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初中时期是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初中语文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塑造人的重要使命。初中课程与生命活动以及精神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语文学科当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识也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是有效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重要方式。通过将语文教学与生命教育结合起来,实现了学生与作者之间的生命交流,并最终形成了生命意识。
一、以教材为基础渗透生命教育
要在语文课堂的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通过利用语文教材中的内容,教育学生在遭遇不幸时应积极勇敢地面对,教导学生怎样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让其了解到生命的价值所在。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感情,让学生懂得珍惜生命。语文教材是实现生命教育的重要形式和载体。情景交融的诗歌、富含哲理的散文、主题鲜明的小说、哀婉动人的戏剧,各种形式的教材都包含着丰富的感情因素,也具有十分强烈的感染力。鲁迅的《孔乙己》《故乡》教导学生相互关爱、相互尊重;《谈生命》教导学生欣赏生命、关爱生命;《秋天的怀念》教导学生深沉的母爱;让学生明白,“生命中不是永远快乐,也不是永远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辅相成的”。
二、积极开展课外实践活动
要使学生感悟到生命的价值,加深对生命意义的理解,那么教师的生命教育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而应延伸到课外,教师可通过给学生布置课外的阅读,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谈生命》《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等,从而能在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的层面之下,使学生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体验以及感受,从而激发出学生强烈的珍惜生命的意识,感悟生命的含义。同时,教师布置一些教学实践活动,例如收集名言警句、以案例为基础进行讨论等,还可让学生以日记、周记的方式表达出对生命的看法和理解,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入讨论,让学生思考生命与人生,从而让其更加善待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以及热爱生命。
三、抓典型,树立正确人生观
初中语文教学中要渗透生命教学,应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抓住典型的篇目,有意识地向学生渗透生命教育。教师可在教导新课程过程中回顾学过的课程,将相关的理念整合到一起,以生命教育为主题,实现对学生的生命教育。例如,《理想的阶梯》教导学生树立理想以及实现理想;《有的人》让学生明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过零丁洋》让学生了解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命的意义》让学生体会到“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从而实现对学生的启发和激励。
参考文献:
[1]孙茂平.在语文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J].文教资料,2010(14).
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看法范文6
[关键词] 独立学院 大学生 生命认知 生命态度
近年来,大学生自杀自伤等事件经过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大学生自杀自伤事件的发生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大学生自己对生命的看法和态度等生命认知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积极健康的生命认知对大学生非常重要,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提出,高中中后期至大学阶段,青少年的主要任务是形成自我同一性,即寻求自我认同和生命意义的阶段,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生命认知。由于巨大的学业压力,我国青少年在高中时代往往无暇思考与自身生命有关的问题,高中也没有系统的生命教育,容易导致学生生命认知偏差,生命态度消极,生命意义缺乏,比如有研究发现23.12%的大学生对生命感到迷茫,4.49%的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较低[1]。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生命认知偏差,使研究者更加重视对生命认知的研究,同时对该领域的研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对大学生进行认知、情感和意志等全方位的生命教育。
在大学生群体中,独立学院大学生有一定的特殊性。独立学院是由普通本科高校与社会力量合作办学的高校,学生数量占大学生的比重逐年增高。研究者发现,独立学院的学生自我中心意识高、社会活动能力较强,但自制力差,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且家庭差距较大,贫困生问题突出[2]。以上特点使独立学院大学生在多种心理层面上与其他大学生有显著不同,因此有必要就独立学院学生的生命认知进行单独的研究讨论。
本研究将着眼目前研究较少的大学生生命认知,特别探讨独立学院生命认知的特点,为独立学院学生的教育和引导提供第一手资料。
1.研究对象和工具
1.1研究对象
共选取样本407名,其中独立学院学生254名,男生151名,女生103名,平均年龄21.30,标准差1.33;作为对比的母体高校学生153名男生107名,女生46名,平均年龄20.30,标准差0.86
1.2研究工具
选用由何英奇根据Frankl意义治疗学的核心概念编制的生命态度剖面图量表。该量表由6个因素构成,分别为“求意义的意志”,主要测量个人企图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与目的的动机;“存在充实”,测量个人是否有因缺乏生命的意义、人生目的和感受游离性空虚、焦虑所引发的“存在的挫折”的程度;“生命目的”,测量个人是否具有明确的、热烈的、有意义的人生目的,并对其生命目的感到满意的程度;“生命控制”,测量个人能自由作生命抉择与生命负责的程度;“苦难接纳”,测量个人了解苦难的意义,及接纳苦难考验的程度;“死亡接纳”,测量个人对死亡不会恐惧焦虑的程度。该量表6个因素的Cronbach系数介于0.65与0.87之间,说明有较好信度,同时它也能较好地预测心理健康程度,有较好的效度[3]。
2.结果
2.1独立学院大学生生命认知整体情况
计算独立学院和母体高校学生的量表总分和各因素的平均分,使用t检验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结果见表1:
*p
由上表可见,独立学院大学生生命态度剖面图量表上总分的平均数为137.78分,而六个维度中死亡接纳最低,为3.03分。表1同时可见独立学院学生与母体高校学生数据的比较,独立学院学生在生命目的、生命控制和死亡接纳维度上得分显著低于母体高校学生,其他维度上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2.2不同属性独立学院学生生命认知比较
以性别、年级、健康状况、在学生组织中地位等为自变量对生命态度剖面图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得分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p
由上表可见,健康状况在总分、生命目的和苦难接纳上存在主效应,经事后检验发现,健康状况一般被试的生命态度总分和生命目的维度分,显著低于健康状况好和非常好的被试。在苦难接受维度上,健康状况一般被试也比健康状况为“好”的被试得分低。
学生组织地位在存在充实维度上主效应显著,具体表现为学生干部得分高于普通学生组织成员和非成员。所有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3.讨论
独立学院大学生死亡接纳最低,显示其对死亡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恐惧和焦虑,这似乎难以理解,但据了解,样本所在学校前不久曾连续发生两起学生跳楼事件,因此可能造成学生应激地对死亡产生恐惧和焦虑。
独立学院学生的生命目的和生命控制两个维度低于母体高校学生可能是因为独立学院学生比较缺乏明确的、热烈的、有意义的人生目的。相比较普通高校本科学生,独立学院学生高考成绩不理想,自我要求又比较高,难免陷入自责与自卑当中,降低其对自我生命的评价,从而造成寻求生命目的和控制的动机减弱。他人的研究中还发现,独立学院学生自我规划较少,没有目标、 没有动力,自觉性不强,只求能够考试及格,顺利毕业[4]。
从生命态度的影响因素来看,健康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主效应在生命态度总分、生命目的和苦难接纳上均达到显著。健康状况好的被试有更加积极的生命态度,明确的,有意义的生命目的,同时也能更加心平气和地面对生命中的各项困难。因此在独立学院大学生的管理和教育中,应特别重视身体状况不好的学生,及时备案,适时关心,并开展行之有效的生命教育。
本研究发现,独立学院学生在学生组织中的地位会影响其生命态度,特别是对当前生命的充实感,因此还可以通过鼓励学生在学生组织中担任管理职务来引导和改善其生命态度。
参考文献:
[1] 林静. 湖南科技学院大学生生命认知现状研究[J]. 中国健康教育, 2007, 23(5): 382-383.
[2] 朱威. 基于独立学院学生特点与教育管理小析[J]. 决策与信息, 2011, 5: 155-156.
[3] 何英奇. 生命态度剖面图之编制[J]. 师大学报, 1990, 35: 71-94.
[4] 王成. 基于独立学院学生特点的班级管理工作研究[J]. 管理学家, 2010, 5: 1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