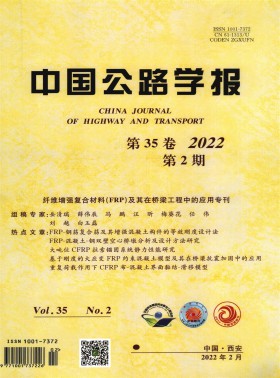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走在路上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走在路上范文1
是在搬家时发现那些未曾开封的信。白色信封,整齐叠放在一个大月饼铁盒子里,边角因岁月久了些而带些黄脆的熟禾气。稚嫩的字迹,书写着不同的地址和唯一的名字。他们一定都以为我在万水千山地寻找某个人,而事实往往最简单:那唯一的名字是我自己,那不同的地址也只是我在某张报纸,某页杂志上随意抄下的。我的信是寄给一个我无法到达的远方的。我喜欢那一枚枚印在退回的信封背面“查无此人”之下的小小邮戳。它们带着异乡的气息风尘仆仆地归来,宛若我少年时一个个远行的梦。我小心地收藏着它们,默默期盼着有一天可以跟着这些邮戳一起上路。
给自己写信的习惯在初二的春天中断。并非忘记走在路上的愿望,而是这时校园里流行起了“笔友”。仍是不同地址,收信人却再也不是自己。天涯海角,邮戳紧紧附着方方正正的细齿邮票到达我的掌心。那是陌生人之间最纯粹的心意。几处吹笳明月夜,低头处,却是春晓如画遮不住。时光穿梭而过,慢慢地,邮戳成了信任,成了挂念。青春所有青涩美丽着的心事,都被密密封在小小的邮戳下,让另一个远方的叫笔友的人收留与阅读。我与那些千里迢迢过山过水而来的邮戳们相依相靠着,成长像后院里的樱桃树一春复一春的绿,触手可及。
终于有机会走出狭窄的小镇去到远方时,我已经告别书信,告别邮戳许久。网络以速食的便利迅速侵占着生活的方寸,我早已忘记了那些收藏邮戳时的满满惊喜。那是行走于大理古城的某个春天,小小邮局里,脆生生的白搪瓷盆滚上一圈蒽蓝,淡淡晨光里端端正正立在小葱绿的邮筒边,竟是一盆清水。手指微微触及水面,细细的凉是只伏春的虫子,从皮肤上爬过去,再钻骨至心。我想象着那凉一咬上邮票就温热起来,泼墨般扑扑洒洒就化了邮票与胶水结的薄网。胶化开了,往信封上轻轻一摁,这凉,这薄网,纵是天涯,也难分了。我一下子就被击中了。那些邮戳陪伴过的日子,呼拉拉就像一阵风一样又回来了。我匆匆跑到柜台前,买了一打明信片,挑出最美的几张,寄给那几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邮戳重重摁下去的瞬间,我笃信从这儿开始,我可以与它们一起走在路上了。
走在路上范文2
我想我也是一个拥有双重性格的人,时而无比渴望平凡,时而无比憧憬轰轰烈烈。 在美好的永恒中,有一场惊天动地的梦。梦中明月当空,青砖碧瓦,霜寒露重。有白衣男子优雅从容,宠辱不惊。携一束幽兰,像千年等待的身影,等待某位佳人前来相会。
说不出的亲切感。仿佛前世某个回眸,某个擦肩而过留下的遗憾。
有的人外貌不甚如意,内里却装有一个强大的灵魂。因为灵魂真正尊贵,外貌不如人意,所以整体看起来就比较猥琐,所以不被大多数人理解,所以理所应当地孤独。如果你也是这种不合群孑然一身的人,那么请不要自卑,不要忧郁,或许你就是下一个创造奇迹的人。
有风,有阳光。
我们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去拼搏,只求日后不让自己后悔。看到一句话说的极好,爱是对的,错的是我们还没学会爱,就急着去爱。
走在路上范文3
——题记
那是一年级下学期,我刚满七岁。
那一天,我起得特别早,天还没亮,背上了书包,等待着妈妈像往常一样送我去上学。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平时对我溺爱娇宠的妈妈,却对我说:“从这个学期起,你必须自己去上学,我不送你去了。你从现在开始要学独立,不能事事都依赖我。”
“妈妈,您就送我到学校吧!就这一学期,以后我就自个儿走路去。”但无论我怎样苦苦哀求,妈妈还是那样的冷漠,甚至不愿意没多看我一眼。
开始,我还磨磨蹭蹭的,死皮赖面地缠着。后来一想到这样下去可能会迟到,于是一个人背着书包无可奈何地走出了家门。
天还没有真正亮,小路上没有人影。北风呼呼地吼着,仿佛是握着锐利的刀剑,刺穿了严严实实的皮袄,更别说那暴露在外面的脸皮,被它划了一刀又一刀,疼痛难熬。它还刮得地上的白色污染肆虐地奔跑,我忽然想起《西游记》里妖精出没时的恐怖情景,心里充满恐惧。
我心惊胆战地飞奔到学校时,天已亮了。看到校门口挤满了送孩子上学的小车,有的家长还替孩子背着书包,拉着子女的小手走进教室。我想起了自己狠心的妈妈,想起她刚才冷若冰霜的脸,泪水不住地流,心里想道:妈妈真够狠心,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上学,那么孤独,那么寂寞。
放学时,我本想回到家里。但是看到校门口又是站满等待的家长,却没有妈妈的身影。是的,当然不会有她的身影,因为她说过不再接送我。
“嗨,你妈还没来?”好友小君拍拍我的肩膀说。
“我父母……今天出差了……很晚才回来。” 我吱吱唔唔撒着谎。
“要不要先到我家吃饭,然后再回去?”好友就是好友,说话就是热心。
我毫不犹豫答应了。
晚上八时,班主任的电话打到了小君家:“你放学时有没有见到梓恩?她家里找得急呀?”
……
很快,爷爷奶奶爸爸,当然还有妈妈,一家人急匆匆地赶到小君家。妈妈把我搂在怀里,什么也不说,转而又很快地向我屁股狠狠抽了几下,用沙哑的声音说:“看你还敢不敢乱跑,也不打声招呼!”继而竟呜呜地哭起来。
事后我才得知,家人从傍晚一直找到八点,从校园的每个角落、回家路上的每个平方,到班上的每一个同学,直到小君家,在这长达三个小时里,妈妈一直受到家人的责骂——我仿佛看到了在呼呼的北风中,全家人匆匆的脚步、紧张的神色和妈妈满面的泪水与急切而沙哑的声声呼唤……
回到家,妈妈从厨房里捧出两碟我平时最喜欢的洋葱猪扒和蜜汁鸡翅,香喷喷的,叫人口水直流三千尺。我心里咕噜着:如果妈妈对我狠心,怎会不辞劳苦地做出这样的菜呢?
妈妈好像看出我的心思,语重心长地说:“妈妈以前太宠爱你了,什么事情都为你包办好。后来到莞城听了一个家教讲座,知道那是错误的教育方法……人生的路很长,妈妈总有老的一天,不可能照顾你一辈子,你必须学会独立,所以今天才硬起心肠让你自己上学,想不到你却太任性了,到同学家也不打声招呼,叫人担心呀!”
“妈妈,我知错了,对不起!”我低声说。
走在路上范文4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叫瓦娃的男孩不能去上学,好几次,他偷偷去溜索,可妈妈不准他溜索。这时,城里来的聂老师给瓦娃的姐姐娜香送来一双鞋子,瓦娃答应姐姐如果把鞋子送给自己就不再去溜索。第二天,聂老师给瓦娃买了一双白色的鞋,让娜香带回去,娜香在溜索的途中看见一只鞋悬挂在书包外,娜香伸手去拿,不慎掉入江中。娜香被水淹死后,瓦娃从此没有说过一句话......
是啊!姐弟之间的亲情是多么强烈!
我不禁想到我的姐姐,每次放假,我都会去找她玩。每次跟她分别时,心里是那么难过,那么伤心,多么希望时间可以过得慢点!每次我受伤,姐姐会为我擦药,;每次我成绩下降,姐姐会耐心开导我;每次我有不会做的习题,姐姐会一点一点教我;每次我生病,是姐姐照顾我,关心我;每次降温,姐姐会叮嘱我添加衣物;每次我......我觉得姐姐就像我的妈妈,随时都在我身边。可是有时候,我却不听姐姐的话,嫌她啰啰嗦嗦,还和她顶嘴,还跟她对着干!想到这些,我好后悔!
走在路上范文5
街道上黑色的风,无休止地灌进我单薄的衣衫,在昏暗的街道上我打了寒噤,双腿由不得的在瑟瑟发抖。我想起一年前中秋的自己,那还是在家里度过的,一家人围着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其乐融融,我吃的很饱很饱。而如今,在饭馆里还没吃下一碗简单的炒面,便觉得已经很撑。一年的时间,我怎么就离开了家呢?
一年前,有朋友在中秋的夜晚给我打来电话,说他那里的月亮很美很美,并且极力地夸大然后又贬低我所看到的月亮。我说我不信,他便照了一张相片发过来,虽然我是真的看不出有他所说的那样美好,但心里却是那样那样快乐,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纯真的友谊。那时我认为我们这样的友谊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一生都不会不变。
一年后,我一个人行走在昏暗冗长的街道上,时不时抬头望一望天空,没有圆圆的月亮,没有一丝的幸福,更没有一毫的快乐和欣慰。曾经我还信誓旦旦扳着指头数着永远不会离去的朋友,可如今现实并不是我那时所想的样子,有太多的朋友离去了,连一声道别都没有说便走开了,只留下一个无法企及的背影,以及我们之间那些曾经美好的零散的记忆。
一年的时间不长,不至于让我们变得陌生吧,可是我们的关系却令我感到害怕!我一直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时间可以改变一切,为什么世间根本没有永垂不朽,为什么海枯石烂根本用不上亿万年?我读着纳兰性德的词“点滴芭蕉心欲碎,声声催忆当初”,我似乎感觉到我的泪水在不住的滑落,心碎了一地,再也拼凑不出曾经。
曾经我满怀着信心,说什么日久天长,说什么地老天荒,如今想想全是笑谈,要变的迟早要变,要走的迟早要走,最终还是会留下我们一个人来面对这个世界,即使害怕,即使孤单。
2014的中秋,早晨我趁着晨雾蒙蒙来到教室,看着《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与《你的孤独,虽败犹荣》这两本书,前者我看到了郭敬明那清澈的忧伤的文字,以及他不放弃希望努力攀爬的身影,后者我则读到了刘同那坚定的信念,燃烧的斗志,以及他对人生大彻大悟的理解。有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思索了无数遍却终究得不到答案。曾经我最怕一个人吃饭,如今却早已习惯了;曾经我最怕一个人走夜路,如今我却能坦然面对了;曾经我最怕一个人面对是是非非,如今我却每天面对这一切的是是非非。我一个人走过了无数条街道,我一个人抬头望过了无数次星空,我一个人懂得了孤独的必要:孤独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教室里只我一个人,本想我会很安静的来思考一番我的人生,但窗外远方工地上挖掘机的轰鸣,窗外树叶在风中拼命的吼声,还有是哪位老师忘记关多媒体音响的电磁波的噪音,这一切都在打扰着我,让我哪里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让我哪里可以一个人痛痛快快?
中午到了,我看到了钟表时针、分针、秒针一同定格在12的那一刻,我的肚子又开始不争气地叫唤,非拉扯着我带他去吃饭。于是我再次走在那条熟悉的街道,树上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黄了,树上飘下的叶子一天比一天多了,然而,我却没变,我带着我饥饿的肚子在这条街上走过了无数回。我眼睁睁看着树叶抽青了,我眼睁睁看着树叶长大了,我眼睁睁看着树叶变黄了,我眼睁睁看着树叶掉落了。这样的场景,我是已经看过了多上回?多少回在记忆里早已压缩成一堆,根本无法去理清。
2014的中秋,我听了很多很多的歌儿,一首一首那样的感动,一首一首那样的真切,最后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的坚强,还是真的软弱,脑海里那些曾经美好的花面像一部电影儿,唰唰地就过去了,最后只留下了我一个人,站在一片荒芜的只有杂草丛生的地方哭泣,然后抬头时,发现天空变成了血一样鲜红的颜色。
下午天气开始变得阴沉,风停了,沉重的湿气开始腾起在半空中,似乎湿的能拧出水来,闷的让我都有些透不过气,看来是要下雨。但我等了整整一个下午雨都没有来。我觉得我是被耍弄了,气愤的向着天空狠狠地瞥了好几眼,眼睛都疼了,然而天气该怎样着依然怎样着。
我透过教室的窗户,看到了校园里那只笔直明晃晃的旗杆,上面顶着一面早已被阳光褪去鲜亮颜色的国旗,沉沉的耷拉着。我不知道这面国旗是多会儿升起来的,但好像从去年我来到这所学校时就是这样,并且从此以后根本没有卸下再升过。
2014中秋的暮色很快就降临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一下午是怎样打发过去的,杯子里的水我记得那会儿还是满满的,可如今早已尽了。我一直听着多媒体发出的电磁波的噪音,我感到很烦很烦,试图来切掉电源,但我怎样切呢?所有的插头开关都被锁进多媒体柜里,就像我的记忆被我全都锁起,又没有钥匙来打开!
起风了,风轻轻拂过我所站立的窗台,我的叹息便被遗失在这一阵阵风里,然而浓浓的雾气仍旧迟迟不散,像早已被凝固在空气里一般,无声无息地渐渐弥漫。
天黑了,路灯亮了,我开始害怕一个人度过的这个夜晚。我去了一趟网吧,想看2014中秋的晚会,但我并没有看,因为我怕我会哭出来。曾经多少次守着月饼,守着家人看中秋晚会,但如今我却什么也没有,于是我认为我现在是不适合看的:荧屏中太幸福了,而我的现实太孤单了!
昏暗的路灯光,
夹杂着一丝一丝的孤单,
在路口久久地张望,
张望着谁的背影?
潮湿的气息,
从地下浮起来,
在空气里慢慢腾升,
又将时光拉扯,
拉扯成一缕一缕的思念。
有人徘徊在路口,
有人失落在街道,
更有人迷茫,
迷茫成为潮水,
一次次没上岸边的礁石,
淡淡的,
瘦了孤影!
在回来的路上,2014的中秋没有月亮,我看着这条昏暗冗长的街道,胸口竟然一下子感觉释怀了。一个人,便是一个世界,一个只有自己才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并且自己永远是主角。
校园里是那样那样的黑,又那样那样的安静,从草坪里浮起的潮湿的气息弥漫开来,让我感觉真的不舒服。树叶有的已经掉落了,我脚下分明感觉到了柔软与腐败,草坪丛中我听不见蛐蛐的叫声,但在夏天的时候这里却夜夜弹奏,热闹非凡……
走在路上范文6
人生是时间给我们铺的路。而我,就走在路上。
人生是岁月用艰辛给我铺的路。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断行走着,路上没有捷径,更没有便车而这条路有去无返。
当我卑微地如同一颗尘埃的时候,我灰暗地低沉着头。绝望,深深地绝望,血红色的成绩划伤了我的心口,那张被我揉捏发烫的试卷沾满了我的泪水,成绩这个名词冲击着我的脑门,又如同硫酸腐蚀着我的体肤。我恨我当时的骄傲,为何要那么自豪?因为一点成果而沾沾自喜,谁会以己为傲?我后悔当初的懒惰,为何不去努力创造?因为一点作为就洋洋得意,谁会以己为豪?若是当初我开始勤奋,若是当时我开始努力,或许不会得到如此般羞辱的成绩。可是现实并没有改变什么,我开始低沉、消极、甚至沉浸在过去中回首。
可是,我们在一度的回首过去,却忘了路还要走。
人生是时空用绊脚石为我铺的路。我已经被它绊倒过一次了,为何不站起来勇敢地正视它呢?这条路注定是坎坷的,但也是人走出来的,我前面的路还很长,我要用勇敢继续走下去。
人生是梦想用“遥远”为我铺的路。在路上,我用一支笔书写了路边的风景,用文学为我汇聚了一条河流,我在路上留下了自己走过的脚印,因为我不想我的人生一片空白。
我们在憎恨从前、悔恨当初时,我们在消极低落、伤心绝望时,甚至忘了这就是人生。鲁迅是位活在黑暗社会里的作家,他用笔墨烧起了他的救国之梦;托尔斯泰一生与贵族斗争,最终逝世于一个乡间小站。难道我就不能面对困难吗?不,我能,因为我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能,因为我需要成长;我能,因为路还要走。
路还没断,为什么我要停滞不前呢?向前跑!不是做给谁看,而是向自己证明依旧活得很好,我为何还要消极?我还有时间,我为何还要低沉?我还有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