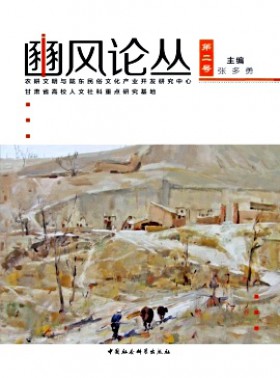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乐府诗全集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乐府诗全集范文1
2019年中考成绩预计7月12日揭晓,7月15日市区进行中招切线。
成绩查询方式:
(一)用浏览器登录到泉州招生考试信息网成绩查询系统(qzzk.cn/)成绩查询页面查询自己的成绩。
(二)拨打泉州中考查分电.话(16888999)根据语音提示进行预约查询结果。
据泉州市招考办统计,我市参加中考的考生共有80428人,比去年增加8639人,增幅12.03%;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切线以中考九个学科考试成绩的等级和中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体育与健康等六个学科考试成绩的分数作为主要依据,中招录取总分620分,其中:物理、化学学科分别按卷面考试成的90%、60%计算后计入录取总分。
考生考试成绩可在泉州市教育局门户网站上查询。
今年中考方案关注点
1、今年中考体育与健康学科满分为20分,计入中招总分,今年中招总分为620分。省一级达标高中录取的学生,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须达到12分以上(含12分)。
乐府诗全集范文2
摘 要:婚姻本质上是一种包含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长期性契约。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婚姻也表现出不完备性。低效率运行的婚姻救济制度无法避免离婚现象,离婚破裂主义的确立使问题恶化。妇女从婚姻获得收益的时间较晚,再婚也比较困难,当婚姻契约被破坏时其权益受到的损害更大,加强离婚时妇女权益的保护十分必要。
关键词:婚姻;长期契约;不完备性;救济;权益保护
一、婚姻的契约本质
关于婚姻的本质,目前存在身份关系说和契约说两种观点。身份关系说认为,婚姻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关系,反对将婚姻视为契约关系,理由如下:[1]第一,婚姻成立的条件和程序、婚姻的效力、婚姻解除的原因,甚至婚姻中的大部分权利、义务是由国家法律加以定义和体化的,而不是由婚姻双方当事人意定的;第二,在婚姻成立时,并未规定双方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没有具体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婚姻又怎么称得上是契约?第三,将婚姻视为契约,可能导致婚姻商品化,有悖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其实,稍作分析,不难发现身份关系说反对将婚姻视为契约的理由难以令人信服。首先,婚姻的契约属性并不因法律的强行性规定而有所缺损,对一般契约,法律在契约的成立条件、解除、违约救济等多方面同样有相应的规定。其次,虽然婚姻在成立时,双方没有就权利义务作具体明确的约定,但婚姻中的权利义务关系部分已经由法律作出了规定,部分可以由社会习俗加以补充,婚姻契约的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男女双方理性选择的结果。最后,契约的核心价值在于自由, 确认婚姻的契约属性,其要旨在于表明婚姻属于当事人自治的范畴, 而不是要用一般契约所适用的等价有偿原则来调整婚姻关系。
关于契约,它首先是一种协议或合意,表现出三个特征:须有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必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2]而婚姻,从法学意义来说,是指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 依法自愿缔结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两性的结合。[3]这表明现代婚姻强调“婚姻自主、自由、平等”,其基本原则与契约的本质精神是统一的。“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4]康德更直截地提出“ 婚姻是依据人性法则产生其必要性的一种契约。”[5]在实践中,婚姻契约理论也得到不少国家法律的明确承认。1791 年《法国》第7 条确认“法律仅承认婚姻是一种民事契约”。《葡萄牙民法典》第1577 条则规定“: 婚姻是两个异性人之间根据本法典规定,意在以完全共同的生活方式建立家庭而订立的合同。”自19 世纪以来,婚姻契约理论逐步为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所采纳, 并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中居于主导地位。[6]
婚姻契约论之所以盛行,根本原因在于婚姻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婚姻的产生、延续及解除其实质就是婚姻契约的缔结、履行和解除。首先,婚姻的成立以双方的自由合意为前提,充分体现了契约自由精神。婚姻史中先后出现过掠夺婚、有偿婚、娉取婚和共诺婚等几种婚姻形式。[7]除掠夺婚没有双方合意基础外,其他情形婚姻的成立都须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充分体现了契约精神。如史尚宽所言:“基于婚姻为男女双方的独立人格者自由意思之结合及其生活共同结合之特征……,然以使此关系成立之行为仍为契约者。”[8]
其次,婚姻关系内容包括夫妻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就财产关系而言,中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这正是契约自由在婚姻财产关系上的反映。就身份关系而言,其内容由法律强行规定的较多,但这些规定只有通过婚姻契约的生效才能适用。有些人身关系的成立是基于自然事实,例如父子关系;但也有基于法律行为的人身关系,例如因结婚而成立的配偶关系。在前者毫无自由可言,在后者是否成立身份关系由当事人决定,与是否缔结契约别无二致。
再次,从婚姻的无效、撤消及解除的情形看,婚姻也具有明显的契约特征。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是由于其不符合结婚的条件,从而不能产生婚姻之效力。其实质是婚姻契约缔结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是无效契约和可撤销契约。而离婚一般有两种途径,即协议离婚和法院判决离婚。对于协议离婚,夫妻双方就离婚事项达成协议而结束婚姻关系。对于判决离婚,实际是当事人通过法院协助行使契约解除权的结果。
二、缔结婚姻契约的原因
除了生育子女,夫妻可以从共同生活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包括经济扶持、互相陪伴以及定期的性生活等。显然,在婚姻存续期间男女双方可能发生的交易有很多项目能够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但是,要签订和执行一系列的短期契约需要极其高昂的交易成本,而且,毕竟有些重要服务不容易通过市场获得(比如性、孩子)。婚姻是一种长期契约,它将很多次交易都包含在其中。正如科斯所指出的企业存在的理由一样,利用包括一揽子交易的长期契约替代短期契约能够明显降低交易费用。制度演变的历史通常就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制度对高成本低效率制度进行替代的过程。人类婚姻制度先后经历群婚制、对偶婚再发展到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度,从男女双方时常发生短期交易到现在双方完全锁入相对稳定的长期契约,交易成本的节约对此现象同样展示出极强的解释力。
除了节约交易成本的原因外,婚姻采取长期契约形式还有另一重要原因――提高效率。长期契约有利于双方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激励对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能够明显提高家庭生产的效率,增进婚姻的价值。例如,当夫妻认识到可以从各自的一项或多项职责的比较优势中获得收益时,分工就发生了。由于只有女性能够生育,所以,在家庭生产中,女性具有比较优势,意识到这点,成长中的女性会对能够增加家庭生产效率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与此类似,她们的丈夫将专门从事市场生产,并选择在婚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自己市场生产能力最大化。[9]随着婚姻的延续,这种家庭内部的分工会自我强化,逐渐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这也是家庭福利最大化选择的结果。但是,家庭分工所形成的部分专用性资产(尤其是家庭主妇,当然也包括孩子)在婚姻破裂时将大幅度贬值。通过签订一个可强制执行的长期契约,可以将夫妻博弈转变成一个有合作结果的博弈,促使双方合作,增加对婚姻的专用性投资。
三、婚姻契约的不完备性
完备的契约准确描述了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可能出现的状态,以及每种状态下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通过它,能够促成权利配置给那些对权利净值评价最高的人,而将风险分配给能以最低成本避免风险的人。显然,完备的契约是有效率的,应该得到强制执行。建立完备的契约要求契约主体具有稳定的偏好体系,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获得全部有效的信息,寻找出与实现目标相关的所有决策方案,并能够准确地预测出每一个方案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所能产生的结果,选择出最优化的决策方案,而且不存在交易成本。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契约往往是不完备的。
首先,在婚姻问题上,情感、价值观等无法或至少是难以量化,理性分析受到很大的制约。其次,在婚姻决策中,契约主体在追求最大化时受到诸多约束,适婚年龄的约束尤其明显。第三,由于人们故意的隐藏知识或者隐藏行为而导致信息不对称,而且获取信息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源;第四,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无法穷尽信息的价值,这些都使得人们始终无法摆脱信息不完全的约束。第五,存在外部效应。外部效应的本质在于它导致了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成本(社会收益)之间的不一致,从而激励不足,使得经济主体从事的经济活动过多或过少。最后,零交易成本的假定很难满足。对于即将缔结婚姻的男女,都认为对方是最理想的伴侣,这事实上导致了双边垄断,引起了极高的交易成本。其次,婚姻市场是一个易货市场,进入市场的男女都是准备用自己的爱与忠诚去交换对方的爱与忠诚,婚姻的易货性增加了交易的难度。再次,缔结婚姻的信号传递非常困难。过于强烈的信号容易引起反感,微弱的信号传递却常常会在途中丢失或被歪曲、误解,而且人们不敢轻易对暗示的信号作出反应。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契约当事人的无知等因素也会导致契约不完备。
当契约不完备尤其是涉及到专用性投资的风险承担等问题没有写入契约时,一旦影响契约继续履行的状态出现, 在这种具有双边锁定特征的再谈判过程中,投资方就面临被对方“敲竹杠”或攫取“可占用性准租金”的风险,即投资者投资的边际收益中有一部分被对方分享了。预期到这种敲竹杠行为,投资者在事前就会投资不足。[10]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这种专用性资产对于婚姻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投资不足时,夫妻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会急剧下降,这也是导致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四、婚姻救济措施的无效
多数人希望能够与配偶白头偕老,但婚姻破裂和家庭解体的情况并不总是能够避免。婚姻失败的原因很多,可能婚姻的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双方无法实现对婚姻的期待;也可能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等发生了巨大的差异;最常见的也许是一方不能够坚守婚姻中的承诺,他们为了一时的喜好而采取了破坏婚姻稳定的机会主义行为;当然离婚破裂主义的确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为了保证婚姻契约的有效履行,必须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可供选择的有私人救济和公法救济两种途径。
私人救济途径,是指由婚姻当事人自己采取的对抗机会主义行为的策略,不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主要包括三种方式:第一,设定抵押。即在婚姻成立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要求将特定资产作为担保,用于抵押的资产可以是财物或者孩子等对于夫妻具有价值的资产。当违反约定时,守约方有权通过变卖等手段单独获得这些资产的价值。第二,减少投资尤其是专用性投资。当预期到契约有可能破坏,为了减少损失,夫妻双方尤其是女性往往倾向于减少投资。第三,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女性选择嫁给一个年龄较大的男性。首先,作为丈夫,年龄较大的男性具有较好的条件,这使女性能够获得较高的当前收益;其次,能够实现夫妻双方个人价值的大体平衡,降低男性离婚的冲动。
对于上述三种私人救济途径,其实际应用价值常常不太确定。首先,关于设定抵押。若是通过财产抵押的方式,往往由于结婚时男性财产较少而欠缺担保效力;而设定过高的财产抵押也会使夫妻双方有耗尽财产的冲动,引起未来生活水平下降。对于将孩子作为抵押的情形,其有效性取决于违约方在与孩子分离时感受到的痛苦程度。但是,通过再婚同样可以获得孩子,甚至形成完全替代。其次,减少投资会导致婚姻质量的下降,进而引起夫妻双方从婚姻中获得的收益下降,不利于婚姻的稳定。最后,女性选择嫁给年龄较大的男性,虽然暂时解决了婚姻中双方收益时间不对称的问题,但不同年龄段男性的死亡率都比女性要高,嫁给年龄较大的男性意味着再丧偶的可能性增加。
鉴于私人救济可能面临的困境,国家在促进婚姻的稳定上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应该是帮助夫妻实现他们的目标,即获得他们期望在婚姻中实现的收益,而不是将社会的价值观或者喜好强行地加于其他人。一般,可以选择的几种典型公法救济途径包括离婚必须经过双方同意的规定、不允许离婚、由法院判决是否离婚。
第一,要求离婚必须经过双方的同意。这样的规定使得任何一方都不能够单独解除婚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婚姻的稳定性。但是,这样的规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首先,由于固执等非理性因素,该规则有可能排除了有效率违约(即违约带来的收益超过履行约定的收益),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损失。其次,婚姻的收益大小取决于夫妻双方通力配合形成的联合产出的多少,当一方产生离婚的意图后,会降低对婚姻的投入,导致对方的收益下降。最后,在离婚意图受到阻碍后,容易导致恐吓、威胁或者家庭暴力等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要求实际履行,即不允许离婚。由于预期到离婚的不可能,这会促使人们在结婚前认真思考,避免了因为一时冲动而产生的婚姻,离婚率明显降低。同样,因其杜绝了违约,避免了违约方破坏守约方的准租金,能够激励有利于婚姻的更多投资行为,增进了双方在婚姻中的收益。但是,配偶在契约中所承诺的许多行为无法具体化且难以对婚姻中义务的履行加以有效监督,而且对于婚姻而言非常重要的情感投入实际上没有办法强制执行。实际履行的适用同样存在局限。
第三,法院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判决是否离婚。上述两种规则排除了有效率离婚的可能,但生活中确实存在有效率的离婚。例如夫妻中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或者婚姻期间与第三人进行同居,或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配偶等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婚姻的延续已经完全无法实现既定的目的,法院应该判决离婚。如果能够获取完全信息,由法院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判决是否离婚,既保证了婚姻的稳定,又允许了有效率离婚。但通常情况下,法院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去判断婚姻中的是与非。
五、离婚时对妇女的特殊保护
婚姻契约的不完备尤其是关于违约所导致的损害如何赔偿问题事前没有约定时,女性往往受到更大的伤害。这可能是由于如下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女性从婚姻中获得收益的时间比男性更晚。对于男方而言,他们更看重女方的美丽、温柔、年轻、从事家务的能力以及生育能力等,这在女方较年轻时就具有。而女方可能更看重男方的责任感、事业心、智慧、赡养家庭的能力,这些素质的获取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夫妻双方所具有的个人价值发生着相反方向的变化。第二,相对于男性来说,离婚后女性再婚成功的几率较低。首先,统计资料表明,在任何年龄段,男性的死亡率高于女性。而且,女性倾向于和年龄比自己大的男性结婚, 这使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找到适合做配偶的男性更加困难。其次,离婚后女性倾向于争取到对孩子的监护权,抚养孩子使女性进入婚姻市场的成本提高,而且男性更喜欢与没有孩子的女性结婚,这降低了离婚妇女的再婚机会。最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一般希望找到比自己更强的男性作丈夫。为了生存,离婚后的女性被迫积累了大量用于市场生产的资产以满足对丈夫的替代性需求,这使她们在婚姻市场更加不利,因为比她们更强的男性可以很容易找到年轻美丽的女性作妻子。
为了预防和制裁婚姻中的违法行为、填补损害以及对受害方进行精神慰抚,中国立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不难看出,目前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主要是离因损害,即配偶一方导致离婚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但是应注意,即使没有过错,离婚本身也会给妇女带来一定的损害。例如前面提及,家庭内部分工时常会促使夫妻共同投资于丈夫的人力资本,但是,在离婚时却出现了丈夫独占人力资本的情况,损害了妻子的合法权益,而现有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却对此束手无策。
合理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应该建立在契约婚姻理论基础之上。婚姻契约能够为双方当事人带来利益,在缔结婚姻契约时,男女双方非常清楚该行为的意义,能够预期到违约将会给对方带来的损害。若无免责事由,违约方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婚姻关系一旦成立,夫妻容易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会不断增加对婚姻的投入尤其是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以增加婚姻的收益。当一段婚姻不再延续,投入其中的众多专用性资产将完全沉没,无法实现预期收益,甚至无法弥补投资成本。预期到这样的结果,夫妻双方将减少专用性投资,呈现出不合作博弈形态。因此,理想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应不仅表现在交易成本的节约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能够将不合作博弈转化成有合作结果的博弈,增进夫妻双方甚至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契约婚姻视角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必须一并解决离因损害和离婚损害引起的赔偿问题,以保障婚姻中的投入不至于沉没。对于离因损害,利用现有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以侵权责任构筑其理论基础。而对于离婚损害,则以违约责任构筑其理论基础。即使在无过错离婚情形下,受到损害一方仍然可以基于违约事实要求离婚损害赔偿。这不仅扩大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保护范围,更重要的是,与基于侵权责任提起的损害赔偿相比,基于违约责任提起的损害赔偿将承担较低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杨大文.亲属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8.
[2]邱鹭风等.合同法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
[3]曹诗权.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36.
[4](英)梅因.古代法[M].刘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62.
[5](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M].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18.
[6]方文晖.论婚姻在法学上的概念[J].南京大学学报,2000,(5).
[7]戴炎辉.中国亲属法[M].台北:汉荣书局有限公司,1985:239.
[8]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53.
[9](英)安东尼・W・丹尼斯.结婚与离婚的法经济学分析[M].王世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89.
乐府诗全集范文3
关键词:江鲍 沈谢 元嘉体 永明体 沿革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3-0128-08
鲍照、江淹和沈约、谢眺的诗风承续关系,钟嵘《诗品》在四家诗评中曾经提及,但学界一直对此存有怀疑,或认为句意难通,或认为认错源流。笔者近来再次细读南朝五言诗,觉得钟嵘之评不为无据。对钟评的理解其实关系到如何把握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脉络,如何看待“元嘉之末,雅俗沿革之际”的事实。由于目前罕见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系统论述,本文试图联系笔者近来对南朝五言诗古近之变的认识,就江鲍和沈谢之间诗风递嬗的具体表现加以辨析,藉此进一步阐明从元嘉体发展到永明体的必然性。
进入正题之前,首先要辨明“江鲍”并称的提法。文学史上一般把江淹归入齐梁诗人,与刘宋时期的鲍照似乎不能并列。但是江淹之诗大都作于宋齐之交,是谢胱的前辈诗人,钟嵘在沈约诗评中就曾提到“于时谢胱未道,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因此江淹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在沈约、谢胱、范云这些永明体的代表作家成名之前。同时,前人也多认为江淹的诗风主要还是太康、元嘉旧体,所以有学者指出:“江淹的诗风与鲍照颇为相似,以至自隋以来屡有‘江鲍’并称的提法。”
江鲍和沈谢之间的关系,最早见于钟嵘对江淹和沈约的评论:
梁光禄江淹诗: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眺。
梁左光禄沈约诗: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鲍明远也。
关于上一段话,有学者认为“成就于谢胱”句意难通,按同书沈约诗评中所说,江淹才尽之时,谢胱尚未遒,何以江诗“成就于谢眺”?所以疑“谢眺”为“谢混”之误。因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曾拟谢混《游览》。嘲(I=310)至于下一段话,许文雨说“陈祚明以为此评明远,讹厥源流,易其说曰‘休文诗体全宗康乐……’”,认为沈约并非效法鲍照,而是全宗大谢。上一段文字中,如将“谢眺”改为“谢混”,从句意的解释上是比较通顺的,江淹确实拟过谢混和王微,而且诗集中也有类似谢混的游览和类似王微的卧疾题材,加上钟嵘又在谢眺的诗评中说谢眺“其源出于谢混”,所以“谢眺”为“谢混”之误并非没有可能。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认为“成就于谢眺”句意不通,而是从江淹和谢胱的相似之处去理解这句话。如许学夷说:“江淹(字文通)与谢眺、沈约同时,而其诗多宋齐间作。淹五言调婉而词丽,然不能如沈、谢之工。以全集观,当自见矣。”陈延杰认为:“文通诗亦能极体物之奇,而声调格律,皆逼肖谢胱,故钟氏谓成就于谢眺者,差近之。”据此,句意就应理解为江淹诗中已经出现的这些变化端倪至谢眺才获得成就。这样理解或许不一定合乎《诗品》的原文,但指出了江淹的诗句在体物以及句调格律方面与谢眺的相似,却符合事实。钟嵘又说谢眺“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认为在奇秀警道方面,谢眺超过谢混和鲍照,那么谢眺不但源于谢混,与鲍照也有可比性。所以许学夷同时提及鲍照和永明体的关系:“明远五言,既渐入律体,中复有成律句而绮靡者。……然此实不多见,故必至永明乃为四变耳。”这些论述已经从诗歌体调趋近的变化方面,将钟嵘似乎已经看到但没有讲清楚的源流联系初步发掘出来。笔者拟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从题材的开拓、体式的创新、抒情结构的处理、以及对偶句式的新变等方面再作申论。
一、题材的开拓
元嘉末被视为雅俗沿革之际,主要因为这是诗歌体调的古近之变的一个转关时期。所谓雅,指汉魏以来从太康延续到元嘉的五言古调;所谓俗,指其后在学习南朝乐府民歌的同时兴起的新体。前人看古近之变,往往着眼于声律。但五言诗的雅俗沿革,并非源于声律,而且在齐梁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并非完全与声律同步。这种变化是随着诗歌题材、体式、表现的渐变逐渐发生的,四声八病的提倡正逢其时,于是自然融入五言趋俗的潮流,最后在梁陈时期形成格调浅俗的近体,冲击了格调沉厚的古体。而元嘉末到永明年间,正是这一变化的开始。
元嘉末诗风的代表是鲍照和江淹。鲍照有大量古题乐府,从主题、内容、句调、表现都恢复了魏晋古乐府的传统。他的五言古诗也多以拟古的方式抒写自己的情志。江淹的五言诗绝大多数都采用太康、元嘉旧体以对偶为主的多层结构,而且也与鲍照一样,多拟古人之作,多用比兴之法。因此相对齐梁诗而言,他们的作品主要属于元嘉旧体。永明诗人的代表是沈约和谢眺,他们是新体诗的开创者,但是仍然有不少诗仍能延续古调。因此仅仅从律句近调来看他们与江鲍的联系,是不够的。事实上从元嘉到永明的诗风变化,渗透在各个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题材内容和体式变化的新动向。
行役诗和离别诗是自诗经以来就有的传统题材,但是将行役与山水描写相结合,是在晋宋时期,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有这类作品;而离情与山水的结合,则是主要涌现在齐梁时期。不过陶渊明仅有少量行役诗,主要抒写出仕与归田的思想矛盾,其中写景的成分不多。谢灵运的山水诗多为登临游览和证悟玄理,虽有一些与行役有关,却很少涉及离情。鲍照和江淹都有一些大谢式的专写登览观景的诗歌,有的是随从应酬之作。多罗列景物而极少言情,一片板实。但他们都有一部分诗,将行役或客游途中所见之景色与离情乡思结合起来,这类内容后来成为齐梁诗的大宗,可以说正是始于江鲍。如鲍照的《登翻车岘》、《登黄鹤矶》、《日落望江赠荀丞》、《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赠傅都曹别》、《和傅大农与僚故别》、《送盛侍郎饯候亭》、《还都道中》、《上浔阳还都道中》、《还都至三山还望石头城》、《行京口至竹里》、《发后渚》、《岐阳守风》等,江淹的《步桐台》、《秋至怀归》、《望荆山》、《渡西塞望江上诸山》、《陆东海谯山集》、《赤亭渚》、《渡泉峤出诸山之顶》、《迁阳亭》等,都作于羁旅行役途中,既有景色的精细刻画,又有孤游苦旅和流连光阴的复杂感叹,显然已经有意地将大谢式的登览诗与行役山水诗区别开来。这类诗歌在刘宋亦不多见,却成为江鲍的显著特色。而沈约诗中便有一些这类内容的作品,如《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早发定山》、《循役朱方道路》、《登玄畅楼》、《留真人东山还》等。小谢则更以这类诗歌见长,他的山水诗不但主要作于宦游羁旅之中,以抒发乡情离愁为主,而且有些题目都与鲍照近似,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休沐重还丹阳道中》、《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落日怅望》等等。再看后来齐梁山水诗主要在行役和离别诗中发展,对比大谢式的寻幽览胜之作逐渐 减少的趋势,不难见出江鲍在山水诗发展中的转关作用。
由日常生活中偶见偶遇的小事触发感想,兴起吟咏,也是晋宋之前罕见的取材方式。江鲍有少数作品正是取材于自身经历的某些小事。如鲍照的《行药至城东桥》,写晨起驾车到城东门所看见的沿路景物,由来往行人扬起的飞尘引起感触,批评市井的游宦子扰扰营营只知追名逐利,并以孤贱隐沦之人与之对照,自叹蹉跎失志。诗中的主题和对照的格局均同魏晋传统古诗,但为进城行药途中所见的景象所触发,便觉新鲜。又如《见卖玉器者》取材于路见买卖玉器的一个场景,用买者和卖者对话的口气写买者恐卖玉为假、不肯成市的一件小事,借以调侃那些不识真玉、瑜瑕莫辩的市井中人。又如《玩月城两门廨中》在公府夜宴歌舞的背景上描写观望月出升空的过程,想象月照珠栊、琐窗、离人、花树的情景。
《观园人艺植》因观看园丁种植而兴起对田园淳朴生活的赞美,《梦还乡》首尾完整地记述自己某夜梦见还乡与妻子团聚的情景和梦醒后的惆怅,也都是取材于生活中随时可遇的一些实事实景。这类诗在江淹集中很少,但《秋夕纳凉奉和刑狱舅》写秋夕日斜时虚堂渐暗、暮霞生成的景象和濯发纳凉的经过,《就谢主簿宿》记述住宿谢家当晚的景色和惆怅心情,《冬尽难离和丘长史》由冬日寒寂之时收到对方书信一事引起岁暮之离悲,也都是因日常生活中某一个具体情景的触发。尽管这些诗并非江鲍的代表作。但其取材方式越出了传统古诗的固有题材范围,后来也成为齐梁诗扩展题材的一种趋向。如沈约的《梦见美人》、《学省愁卧》、《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为邻人有怀不至》,何逊的《早朝车中听望》、《临行公车》、《夜梦故人》、《刘博士江丞朱从事同顾不值作诗云尔》、《塘边见古冢》,刘孝绰的《遥见邻舟主人投一物众姬争之,有客请余为咏》、《咏有人乞牛舌乳不付因饷槟榔》等等,从题目就可以看出都是因日常生活中某个事由或情景而引起的一时一地所感,虽然这类诗在齐梁的发展趋势是内容渐趋浅俗,但开了唐诗取材多样化和日常化的先声。
以咏物为题的诗作增多也是江鲍取材的特点之一。从楚辞中的《橘颂》到刘桢的咏松,莫不借物兴寄,其意不在刻画形貌。而鲍照的某些咏物诗虽然也有寄托,如《咏白雪》、《咏双燕》等,但有些则仅以赋法咏物,无甚深意,如《喜雨》、《苦雨》、《望水》、《望孤石》、《春咏》、《咏秋》、《秋夜》其一之咏灯等。江淹的咏物赋不少,诗则仅存《咏美人春游》、《云山赞》中的《白云》等,但其不重寄托的取向与鲍照类似。沈约与谢眺则对此种咏物路数大加开掘,数量剧增。沈约不但沿袭了江鲍的《春咏》、《秋夜》、《白云》及咏雪等题目,还将题材扩大到咏篪、笙、筝等乐器,咏青苔、新荷、柳、山榴、桃、麦李、桐、梨、甘蔗等植物果木,咏蝉、反舌等虫鸟,咏竹火笼、帐、盘、几、履、等日常用品。谢眺的咏物诗多与沈约等众人同咏,同时也有不少沈约所未写到的题材。钟嵘批评鲍照“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当然包括鲍照那些操调险急、词采华丽的乐府诗,但咏物诗的取材也是趋俗的表现之一。沈约从咏物一路大力发展,促使咏物诗成为齐梁写作新体诗的重要题材。这应是钟嵘说沈约“鲍明远”的原因之一。
二、体式的创新
江鲍对沈谢的影响还可以从诗歌体式方面见出,最显著的是乐府诗。东晋百年诗坛罕见乐府诗,至谢灵运才接续乐府古题的创作传统。刘宋不少诗人都有几首拟乐府古题之作,但存诗不多,惟鲍照在继承魏晋古题乐府诗歌传统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之后大量写作古题五言乐府的主要是沈约。沈约的乐府除了宫廷雅歌以外,自己创作的古题乐府计有二十多题。其主要内容大多是感叹征途如惊涛峻岭,光阴如奔箭闪电,揭示财尽交绝、花落爱终的世俗常理,抒发人生易老、壮心消歇的衰暮之悲,借乐府古题的传统主题来寄托自己在仕途中的衰荣浮沉之感,其创作原理与鲍照的古题乐府是相同的。这类古题乐府还有不少使用递进、顶针、叠字、重复等多种修辞,有意模仿汉魏诗歌的句调,在对偶中穿插散句,甚至探索了散偶相间、散多偶少的旬式结构。显然试图运用汉魏古诗和乐府自然流畅的构句原理来组合当代的白话散句,这与沈约提倡“三易”的主张有关。而鲍照的乐府诗也正是在恢复古乐府自然平易的句调方面,显示出与晋宋古诗全对偶的缜密结构不同的语言特色。由此可以看出鲍照的古题乐府在创作原理方面对沈约的启发。
除了恢复古题乐府传统外,鲍照在效仿当代新兴乐府方面的尝试对沈约的影响更为直接。《白聍舞歌辞》是拟东晋新兴的舞曲歌词,鲍照所拟同题乐府词是其七言诗的代表作之一。其后再作此题的就有沈约的七言乐府《四时白聍歌》五首。七言是当时被视为“俗而小”的体裁,这也应是钟嵘讥鲍“险俗,,的原因之一。不过对于永明体影响最大的还是南朝乐府民歌,鲍照正是刘宋首开学习当代民歌之风气的诗人。如《吴歌》是模拟吴声歌。《采菱歌》亦取题于南朝乐府民歌,七首诗均为五言四句,意脉顺序相连,学习清商小乐府每首情思集中于一点的表现方式。其一写水上采菱歌以点题,其二写采集香草,其三写景物引起的心意撩乱,其四写约人幽会于洲屿间,其五以烟深水急之景烘托离悲,其六写步登大堤感慨春芳将落,其七为怀古思今的感叹。七首诗虽用民歌语调和组合方式,但词采华丽凝练,尤其末二首以人比春芳,惆怅古今,已经寄托了文人的人生感慨和时空意识。所以王夫之认为王维《辋川集》中的《孟城坳》和《华子岗》诗出自末首。《幽兰》五首取琴曲歌辞的古题,但也是五言四句小诗的组合,写思妇怀春之怨,前三首化用楚骚意境和语词,第四首将诗经中蠕蛸见喜的典故和南朝民歌常用的双关语“丝”比“思”结合,反衬妾的缺乏自信,第五首用诗经陈风和郑风中《东门》之诗的典故暗示夫君在外游乐,立意既新,又含蓄有味。不仅以古题与南朝民歌风格相结合,而且努力运用古诗的意境和用典提升了民歌的表现力。此外鲍照的古题乐府《王昭君》也是四句体小诗。他还用五言四句体写了十首歌颂太平的《中兴歌》,并进一步运用这种体裁写了不少小诗,如《酒后》、《讲易》、《可爱》、《夜听声》、《春咏》等等,涉及叹老感时、潦倒失意、谈论哲理等各类内容,将内容从民歌的男欢女爱扩展到文人诗的常见主题中去,这些努力为永明体诗人创作新体小诗提供了不少创作经验。
沈约和谢眺的新体诗正是循鲍照改造乐府的路数发展。他们一方面继续效仿南朝乐府民歌,如沈约的《白铜踞歌》三首;一方面将古题乐府改造成讲究声律的新体诗,如《芳树》、《江南曲》、《洛阳道》、《怨歌行》、《东武吟行》、《悲哉行》、《有所思》、《钓竿》、《湘夫人》等,同时又继续创造新题乐府,如沈约的《夜夜曲》,谢剧E的《玉阶怨》、《江上曲》、《秋竹曲》,以及多人同作的《铜雀悲》等等。这些乐府题的新体诗虽然并不都是四句体小诗,但其原理与鲍照用四句体写《王昭君》、《幽兰》等古题乐府是相同的。他们也像鲍照写《中兴乐》一样,制有歌颂盛明的五言四句体《永明乐》,并且用五言四句体写作了大量咏物诗。谢眺的新体小诗名作《玉阶怨》、《王孙游》也是借古题乐府或楚辞之意结合南朝乐 府民歌的形式创作的新题乐府。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永明新体诗与乐府的关系,以及从鲍照到沈谢用文人诗技巧改造和提炼南朝乐府民歌的发展轨迹。此外与五言四句体密切有关的联句体在谢眺、沈约及何逊等齐梁诗人中颇为流行,其实也早见于鲍照。鲍照集中存联句三种,其中《与谢尚书庄三连句》尚有一半五言和七言夹杂:“兮”字的骚体句,可以想见,刘宋时联句尚未完全定型为五言四句的连缀。但《月下登楼连句》已经具备各人以四句五言相连的形式,与齐梁时流行的联句完全相同了。
永明新体诗的体式除了五言四句以外,较常见的是十句体和八句体。江鲍的创作高峰期早于沈约,虽然没有受到永明时期流行的声律理论的影响,但是已经有不少十句和八句的五言诗。江淹的十句体有《学魏文帝》、《寄丘三公》、《刘仆射东山集》、《悼室人》十首、《外兵舅夜集》等等,八句体有《感春冰遥和谢中书二首》、《清思诗》(其五)、《无锡舅相送衔涕别》、《就谢主簿宿》、《当春四韵同口左丞》、《云山赞》四首等。鲍照的十句体有《自砺山东望震泽》、《赠故人马子乔》六首(其三、其四、其五)、《发长松遇雪》、《绍古辞》七首(其二、其四、其五、其六)、《学陶彭泽体》、《怀远人》、《夜听妓》(其一)、《咏白雪》、《咏双燕》(其一)等等;八句体有《登云阳九里埭》、《三日游南苑》、《赠故人马子乔》六首(其一、其二)、《答休上人》、《箫史曲》、《古辞》、《学刘公干体》五首、《拟阮公夜中不能寐》、《咏秋》、《和王义兴七夕》等等。后来在齐梁时期发展起来的十句体和八句体比较接近,十句体仅仅比八句多一联,尤其在新体诗里,不少十句体删去一联并不妨碍篇意的完整。从江鲍的这类诗看,十句体和八句体的差别大致也是如此。虽然其结构不如齐梁诗规律,但是在元嘉“体语俱俳”的诗坛上,这些诗的出现以其较为疏朗简短的篇幅冲淡了凝重沉滞的诗风,突破了五古自晋宋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多层次结构。晋宋五古一般每层句子至少四句,每诗的层次也至少三层,所以一首诗大都在十二句以上。江鲍多数诗篇也是这种模式,尤其江淹,多数诗篇采用四句一层、每诗四至五层的整齐结构。而他们的十句体和八句体则减少了层次,不少只是前四句和后四句两个层次。更重要的是由于篇幅缩短,内容随之集中,抒情也相对简化,每层可以减为两句。因而这类诗里两句一对作为一层的结构比较常见。江鲍的组诗中多见十句体或八句体,正是因为组诗可以将复杂的意思分割成一诗一意的连缀,所以更便于每首诗里两句一层的小转折。如江淹的《悼室人》十首、鲍照的《绍古辞》都是写恋情,由于两句一层,情与景的组合和转折比较自由。既可以是首尾抒情,中间以两对或三对写景烘托,也可以是前半写景后半抒情,更可以全篇写景结尾抒情,或者情与景交替。后来发展起来的新体诗多用十句和八句体,情景层次的组合无非也就是这几种。因此,江鲍的十句体和八句体虽然没有讲究声律的意识,但是在体式结构上为后起的永明体奠定了基础。
三、抒情结构的处理
与题材和体式的变化相应,江鲍诗歌在抒情结构方面,也发生了不同于颜谢五古的一些变化。首先是情景关系的处理。在登览、行役等较多描写山水景物的题材中,大谢处理情景的方式较之前人已有突破,能注意结构的变化,但大体上主要是两种,一是景和情、理分咏,或前半景,后半抒情说理,或情与景分层穿插交替;一是以游踪为主线贯穿全篇,这类诗景与情的结合较为自然,但还做不到景与情的融合。这是山水诗兴起时必经的阶段。从晋宋到齐梁,山水行旅诗从情景分咏逐步发展到由景见情、情景交融,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鲍照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从寓目辄书式的全面铺写进展到对景物有所选择,使之与诗人的心情趋于一致。他也有一些登览诗,既不作大谢式的过程交代,也没有明显的主线和作者的身影,而是类似赋体的铺陈,如《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从登香炉峰》等,正如方东树所说:“细绎鲍诗,而交代章法,已远不逮谢公之明确,往往一片不分,无顿束离合、断续向背之法。”不过在一些抒写离愁乡思和有所寄托的山水行旅诗中,他就只取那些能够表现自己心境的景物,借景物的氛围来烘托愁情。如《登黄鹤矶》中“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商弦棹讴的悲哀与落叶秋风、雁唳波寒的凄凉景色正相协调。孟浩然的名句“木落雁南度,悲风江上寒”即由此脱化。《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中“风起洲渚寒,云上日无辉。连山渺炯雾,长波迥难依。旅雁方南过,浮客未西归”,取景与前诗亦相同,都是以淡墨渲染江上清寒渺远的景色,以烘托游子的旅愁。此外如《送盛侍郎饯候亭》:“北临出塞道,南望入乡津。高墉宿寒雾,平野起秋尘。”在离别的津渡和路口,只取笼罩平野的寒雾和秋尘,以渲染心情的凄寒和迷茫。小谢的山水行旅诗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善于以清淡的笔墨描写清远平旷的原野和江上景色,开出了与大谢不同的境界,溯其缘起,当始于鲍照。只是鲍照笔下的江景较为阴寒迷茫,不如小谢明净清朗。
鲍照某些诗歌还能由情思牵引出独特的观景角度。如《日落望江赠苟丞》:“旅人乏愉乐,薄暮忧思深。日落岭云归,延颈望江阴。乱流灌大壑,长雾币高林。林际无穷极,云边不可寻。惟见独飞鸟,千里一扬音。推其感物情,则知游子心。”咧‘啪’旅人在江阴落日下极目远眺,视线越过高林暗雾、大壑乱流,直到不可穷极的林际云边,最后突显出一只孤独的飞鸟,引出游子的感物慕群之心。飞鸟同有比兴之意,但诗中的视野随旅人忧愁的目光向天际扩展,这种取景角度自然令人联想到小谢的《和宋记室省中》:“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诗中之行树远阴、云霞变色的暮景,都是随着诗人目极飞鸟远去的视野展现。《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写游子还都途中登上金陵附近的三山俯瞰大江和城阙的情景:“泉源首安流,川末澄远波。晨光被水族,晓气歇林阿。两江皎平迥,三山郁骈罗。南帆望越峤,北榜指齐河。关扃绕天邑,襟带抱尊华。长城非壑险,峻阻似荆芽。攒楼贯白日,摘堞隐丹霞。”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晨光照耀大江的澄明宁静,舟船南北交汇的繁华热闹,皇都依山傍江的雄伟地势,城楼辉映丹霞的壮丽气象。而小谢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题目大致相同,只是离开都城而去,在三山回望京邑的景色中抒发对故乡的眷恋之情。由于观景角度相同,取景也是像鲍诗一样以白日辉映之下大江的澄净和京城的繁华相互映照,只不过一写晨光,一写晚霞。虽然二诗繁简有别,谢诗更为简练集中,且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一对名句传世,但其为乡情所牵引的观景角度以及构景方式与鲍诗显然有关。
观景角度的选取和景色与心情的协调,可以促使诗人集中视野,剪裁画面,自然减少面面俱到的铺写,是取境由大谢的繁富密实发展到小谢的空灵简洁的重要过渡,距离小谢的景中见情、写出活景又走近了一步。但鲍照的不少诗还是以情为主线将景自然串联成一气,这仍是古诗的传统表现,只是增加了写景的成分,如《送从弟道秀别》、《送别王宣城》、《秋日示休上人》、《和王丞》、《送盛侍郎饯候亭》、《还都道中》等等。其实小谢也有不少诗歌是以抒情为主线的,有的诗结构和构思方式与鲍照颇为相似。 如鲍照的《上浔阳还都道中》构思很见匠心和新意:“昨夜宿南陵,今旦人芦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毕景逐前俦。鳞鳞夕云起,猎猎晚风遒。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登舻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绝目望平原,时见远烟浮。倏忽坐还合,俄思甚兼秋。未尝违户庭,安能千里游。谁令乏古节?贻此越乡忧。”全篇以诗人从荆州还归扬州的旅途为主线,前写赶路的行程,中写瞻前顾后的悲伤,末以离情结束。而景色描写被“登舻”两句分为两部分,前者重点写晚风夕云下尘沙飞扬、白鸥翻浪的景象,藉平陆之昏茫和水流之急湍暗示水陆兼程的辛苦和悲哀。后者着重写远望平原烟雾飘忽、离合不定的景色,关合人生旅途去者似烟、来者似秋的感慨。因此,前眺淮甸和回望荆流的动作就成为全篇抒情的焦点,既写出了诗人向往扬州和留恋荆州的矛盾心情,又包含了诗人毕生奔波不息、珍惜逝川的倦旅之感。对比小谢的《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也是以踌躇于扬州和荆州两端的矛盾心情为全诗中心,串连起大江行舟的全程,以此展开前瞻金陵的夜景和回望荆州忆念中的晨景,使诗中前后两部分景物形成对照,巧妙地烘托出诗人既庆幸脱离网罗,又眷恋故主的复杂心绪。所以方东树评鲍照和小谢这两首诗“各极其情文之盛妙,可谓异曲同工”。小谢此诗虽为名作,但若就抒情结构紧密配合构思的创意而言,鲍照自然是先于小谢。
鲍照还尝试用不同于前人的构句方式将情语和景语紧密结合。除了上文已引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外,又如“幽篁愁暮见,思鸟伤夕闻”(《自砺山东望震泽》),暮愁中听到鸟声见到幽篁更添一层伤感;“途随前峰远,意逐后云结”(《发后渚》),既是写前后山峰相连、云雾缭绕的途中之景,又融入了因渐行渐远而郁结的意绪;“萋萋春草秀,嘤嘤喜候禽”(《和傅大农与僚故别》),则在春草萋萋、春鸟嘤嘤的景色中直接写出了内心的欣喜;“茫然荒野中,举目皆凛素”(《还都道中》其三),在独立荒野茫然四顾的主人公形象周围画出一片素白的冰雪世界;“驰霜急归节,幽云惨天容”(《还都口号》),霜天幽云惨淡的景色,也正合急驰归去复命的行人阴郁的心情。江淹也有不少这类构句,如“愁生白露日,怨起秋风年。窃悲杜蘅暮,揽涕吊空山”(《无锡县历山集》),每句以一情配一景,愁、怨、悲等各种心情都因白露秋风、空山杜蘅而生;“心忧望碧叶,涵影顾青林”(《惜晚春应刘秘书》),涵影于青林的树荫中望着碧叶忧愁,也写出了春将老去的晚景;“曾风飘别盖,北云竦征人”(《无锡舅相送衔涕别》),风飘车盖,北天云阴,既是触目之景,又使离别的征人惊心;“蕙弱芳未空,兰深鸟思时”(《悼室人》十首其一),蕙兰芳香尚存,鸟啼犹如思苦,既写春深之景,又寓悼亡之悲。江淹甚至还有一些移情于景的构句,如“吴山饶离袂,楚水多别情”(《卧疾怨别刘长史》、“山川吐幽气,云景抱长怀”、“潮澜郁东西,汀皋日惨色”(《冬尽难离和丘长史》)等等。这类构句数量虽然不多,但开启了情景交融的一种途径,为后世诗歌所常用。
在离别诗中,江鲍的抒情有时采用对比和对照的层次结构,也开了齐梁某些离别诗的端倪。虽然陆机诗里也有个别对偶句比较离别者的不同去向,如“我若西流水,子为东峙岳”(《赠弟士龙诗》),但没有形成结构性的对照。鲍照往往在离别诗中夹用层次对称的对比,如《与伍侍郎别》在首尾四句外,中间连用四层对比:“伤我慕类情,感尔食苹性。漫漫鄢郢途,渺渺淮海迳。子无金石质,吾有犬马病。忧乐安可言,离会孰能定?”分别对照了两人的相慕之情、东西相反的路途、同无金石之同的体质,并以忧乐和离会再次总结分别的无奈。《送别王宣城》首二句点对方从郢出发,次四句用楚辞典写江郊春景,接着转到眼前送别宴会,展望行者将在颍阴、淮阳留下文章政声。全诗以出发地和所赴之地作为对照,形成对称结构。《送盛侍郎饯候亭》前半首写盛侍郎冠带驱驾出征的道途景色,后半写自己负羁草野的困顿,对比二者欣悲和甘苦之不同。《与荀中书别》以自己的孤游倦旅之感领起,继写荀中书以置酒敷文慰劳自己的盛情,接写自己思念对方无从追随的感愧,也是前后对照。江淹这类诗很少,仅《贻袁常侍》共四层,每层四句。第一层以“昔我别楚水,秋月丽秋天。今君客吴坂,春色缥春泉”的隔句对发端,第二层以幽冀和沅湘景色相比照,点出离别之人所处之不同地域,第三层以涉江和采莲典故再次对照离别者和留滞者,最后以生于水中的珠贝和生于山里的兰玉比喻双方品格,依然关合人分两地而不受阻隔的友情,也是精心结撰的对照性结构。
江鲍离别诗的这些对照性结构,为永明时期的离别诗所吸取,尤以新体诗为多见。如沈约的《别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後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虽然没有用对句,但有几层意对:少年和衰暮的离别之意不同:今日之酒明日能否重持难以预期;梦中相思和不识路相对。层层递进,将老来离别之苦写到极致,情切意长,感人至深。谢眺的《新亭渚别范零陵云》除首句联交代范云去向,结尾直抒离忧外,中间三联分别以云水、车船、典故三层对比两人离别的无奈和不同前景:“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广平听方籍,茂陵将见求。”沈约和虞炎、范云、王融、萧琛、刘绘等同咏的一组新体诗《饯谢文学离夜》㈣‘一’也多以人的不同去向、车马舟船的背道、旅途和故乡等各种情景对照,以抒发离别的伤感,如虞炎的“离人怅东顾,游子去西归”,范云的“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王融的“离轩思黄鸟,分渚菱青莎。翻情结远旆,洒泪与烟波”,沈约的“湔汩背吴潮,潺谖横楚濑’’等等。这种对照性结构尤其适合对偶句和新体诗八句的层次对比,因而在齐梁新体诗中也能产生名作。如何逊的《与胡兴安夜别》:“居人行转轼,客子暂维舟。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离恨,独守故园秋。”四联连用对比,分四层对照居人和客子车船即将背向,一筵之欢笑即将分为两地的愁思,居人与客子各自对着寒塘之露和清淮之月的惆怅,最后是新恨与故园的对照,可说是充分发挥了八句体新体诗结构的长处。
四、对偶句式的变化
最后再从对偶句式的变化来看江鲍对于永明体的影响。明代已有学者看到了江鲍诗中一些近于律体的诗句,指出这是永明体变化的前兆。许学夷说:“明远五言,既渐入律体,中复有成律句而绮靡者。如‘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蜀琴抽白雪,郢曲发阳春’,‘珠帘无隔露,罗幌不胜风’,‘扬芬紫娴上,垂采绿云中’等句,则皆律句而绮靡者也。”又说:“淹五言,……中如‘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昔我别楚水,秋月丽秋天。今君客吴坂,春色缥春泉’,c愁生白露日,思起秋风年’,‘松气鉴青霭,霞光铄丹英’,‘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电至烟流绮,水绿桂含丹,,‘凉霭漂虚坐,清香盟空琴’等句,皆调婉而词丽者也。”许氏敏锐地看到了这些句子的婉丽,及其趋近沈谢和律句之处,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对偶句本来从五言诗产生时起就已经存在,只是到太康体中才大量增加,元嘉五言诗几乎都是全对偶。其实齐梁时期反而有一个破偶为散的变革过程,用因此对偶与否不是 区别古调和近调的关键。但是古体与近体之对偶确有格调的差异,许学夷以婉丽绮靡来概括以上句子,并非仅仅指其声律合乎近调,更应是就律句对偶的特征而言的。那么律句的对偶在句法上有什么具体的特征呢?当代学者吴小平曾在《中古五言诗研究》中详论齐梁陈诗“诗句语法关系的新变化”,我以为是目前所见论著中对律句语法关系的论述最切实有据的见解。因此本文不再赘论,只是就许学夷所列举的以上诗句略作分析。
乐府诗全集范文4
一、李白的仕途经历
根据日本学者笕久美子《李白年谱》(王辉斌译)记载,我们考察李白的一生,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他真正“从政”的时间很短。主要有三段:第一段,742-744年,长安“供奉翰林”。所以仅仅不到两年他就离开了长安。第二段,756年12月,李白应再三邀请赴寻阳入永王李幕僚。但是李并无讨贼之心,只想趁乱争夺帝位。后来,李兵败被诛,李白连坐。幸得郭子仪力保,方得免死,改为流徙夜郎,旋在途经巫山时遇赦。三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入宋若思幕,自四月至九月,时长不足半年。综上,如果严格一点说,如果由“朝廷”亲自任命的才是“命官”来看,那么李白真正意义上的“仕途”生涯仅仅就长安“供奉翰林”那两年时间。
二、李白的求仕方式
(一)游说干谒。李白干谒游说的方式,主要是宣传自己的文采,结交官吏,王公贵族,提高自己的声誉,以求博得辅弼明君的机会。715年(开元三年)李白15岁。因为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渴活动。从公元718年(开元六年)李白18岁,一直到公元742年(天宝元年)他42岁,他开始二十几年的出游干谒求仕生涯。他先后遍游了名山大川,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又拜谒了苏、李邕、贺知章、韩朝宗等王公大臣。在干谒生涯中,最有可能“得见龙颜”的一次是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狞猎,李白上《大猎赋》,文中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夸耀玄宗开创之功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故意宣讲道教的玄埋,来迎合玄宗崇尚道教的心情。但是,依然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以文游说干谒的方式也是李白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直到安史之乱前两三年,李白漫游于宣城、当涂、南陵、秋浦一带,仍然衣食依人,经常赋诗投赠地方官,以求帮助。
(二)以隐求仕。我们考察李白的思想经历时,会发现“隐居”的思想,其实一直都是深深地烙在李白内心深处,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时期显现程度不一样罢了。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31岁的李白到了嵩山,羡慕故友道士元丹丘的悠闲清净山居生活,隐居之意渐渐凸显。但是,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 只是思考下一步如何以求仕进。就在隐居寿山时, 他还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但是仍然没有机会。直到赐金放还之后,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夏天, 李白求仙访道之心更加执着,先到齐州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 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 成为道士。其后又赴德州安陵县, 找善写符篆的盖寮, 为他造了真寰。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 他还与杜甫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但是,李白思想深处深受法家思想影响,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完全放弃自己辅弼明君的思想。“赐金放还”之后,他一面求仙学道, 一面企图为国建功。虽然仍事漫游, 对于国家安危, 颇多关切,已与年轻时的“漫游”有所不同。李白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领大军讨伐安史叛军,他北上准备追随其从军杀敌,只是中途因病折回。所以,李白的“隐居”思想,包括他的寻仙访道、他的“纵酒”、他的与无赖儿厮混,都是他政治理想不能得以实现的短暂“放纵”或者“逃避”。
三、原因分析
(一)家庭影响。李白的父亲是突厥化的汉人,在705年李白四岁时迁居蜀地,入籍绵州。所以,李白的家庭不是一个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在四川的家庭完全是突厥化的。另外,从其诗作《上云乐》中可以看出李白深受景云教影响。李白是个忠实的道教徒,一方面是因为其内心深处,飘逸洒脱,不拘小节。
(二)教育背景。李白自幼勤苦读书,《与韩荆州书》:“观百家”。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可见,青年时期的李白骨子里就是尊法轻儒的“热血青年”。
(三)社会风气。当时唐与西域交通往来频繁,特别是关陇一带的风习“融胡汉为一体,文武不殊途”,“任侠”意识成为一时风尚,李白也深受影响。《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李白也非常崇拜鲁仲连、朱亥、侯赢等靠游说干谒博得功名的说客或侠义之士。也时常以苏张自况,也时常想贡献奇计。又喜欢佩剑,甚至终生不离。“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
(四)思想性格。李白人生观的特质是“合仙侠为一人”,而且他为人风流洒脱、无拘无束,奉行“不屈己、不干人”的信条,这些都不是一个成功政治人士也应有的性格特质。另外,李白性格和心理上具有悲观和颓废的因素,他纵酒、狎妓、空谈,他虽然也想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但是他无时不在恣情的享受人间快乐。李白的性格充满许多矛盾的,而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入世与出世、从政与还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而且,这种入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在他的思想中一直冲突斗争着。这在他的诗作里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候同一首诗前面是悲观哀怨,后面又是满怀自信。这是他性格上的原因。
(五)政治才能。李白的启蒙教育是诸子学说,遍观百家。又从赵蕤学习六十三篇《长短经》。他的思想肯定深受“王霸大略”影响尊法轻儒。李白一生中最大最主要的、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志向只有一个“想作宰相”,也就是苏秦、张仪这样的,他时常以苏张自况。但是,李白的政治才能怎么样呢?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极力推荐, 玄宗才看到李白的诗赋,便召李白进宫。值得注意的事,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 李白对答如流。这也说明李白也具有一定的洞察世事能力。于是,李白供奉翰林,得以陪侍玄宗左右,职务是草拟文告。在唐代有两个翰林院,一个是集贤殿书院,职务是侍读,也就是皇帝的“家庭老师”。另一个是翰林学院,职务是为皇帝撰写重要文件,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公厅”。李白所在的就是翰林学院。我们推测一下,在长安的两年的时间里,李白肯定也有时间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恐怕,可能是他的政治才干不足以引起玄宗的重视。756年12月,李白下山赴寻阳入永王李幕僚。李白人幕后, 力劝永王勤王灭贼。但是李并无讨贼之心,只是想趁乱争帝位。当时,江南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参加,只有李白一人应邀前来。可见,李白没有政治远见和政治敏锐性,政治才能也值得怀疑。
综上,李白文学才气过人,诗文名冠一时。政治理想远大,但是政治才干有限,性格上具有悲观和颓废的因子,又孤傲自负,不具备成功政治家的良好素质,一生或漫游、或隐居、或干谒,虽孜孜以求,但屡遭失败,仕途命运多舛,政治建树寥寥。
(作者单位:河南省三门峡市义马市千付路义马市委党校)
参考文献:
[1] 鲍方校点《李白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
[2] 李明中《李白悲剧性仕途命运解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4期,2010年7月;
乐府诗全集范文5
关键词:意象;象征;爱情;思乡;升华;灵魂
“月”从古至今,引发着人类无数的幻想,人们对它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诗人对月更是有着特殊的感情。“月”在中国文学中出现频率呈倍增长,至晚唐北宋达于巅峰。“月”自从进入人的审美视野,便不断派生、衍播出含蕴不尽的象征喻指。
由于明月意象的丰富、奇幻和精妙,中国古代诗歌长期笼罩着一层或浓或淡的“人月相得,心月互通”的趣味。诗人们创造出了许多美不胜收的吟月诗。本文从三个不同侧面归纳分析了一下古诗中“月”这一意象丰富的内涵,试图简单阐述一下明月意象在古诗中的发展变化过程。
一.月――自然界永恒的存在
月在古诗中首先便是一种永恒,一种苍凉阔大的意象
王昌龄是将这一意象融化于诗中的圣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诗的起句以眼前高悬的明月,巍峨的雄关,构成一幅苍凉壮阔,孤凄清凉淡远的画面,即所谓“发兴高远”。在“明月”和“关”两词之间又增加“秦”、“汉”两个时间限定词,让诗从千年以前,万里之外下笔,使读者将眼前明月下的边关同秦代的筑关御胡及汉代与胡人在关内外的一系列战争这些悠久的历史自然联系起来,“万里人未还”便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不只是当代人之悲剧。而是世世代代人们的共同悲剧。让诗具有一个阔大而深远的历史背景,整个历史,段续的画面化为一个整体,“征人”便是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爱国卫士”形象,平凡的悲剧,平凡的希望,由此显示出不平凡的含义。
在诗人的笔下,月不只可以化作永恒、阔大,还可以化作一种生命驰骋自由的潇洒。李白《峨眉山月歌》曰“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洲。”诗从“峨眉山月”写起,月只“半轮”,使人仿佛看到青山吐月的优美秋景,次句写月映江水,又随江水流逝,紧随依傍舟人,正是“月亮走我也走”的妙景。凡咏月之处,皆尽吐江行思友之情,诗的时间跨度驰骋自由,诗人的情怀更是挥洒自如,冲破时空,获得永恒,冲破人生的狭隘,俯瞰历史的无限,找到人生的潇洒,正是月亮赐予人类的第一灵感。
二.月――人类美好情感的载体
自古以来,“花前月下”是青年男女倾诉爱情的最佳场所,“花好月圆”更是人间美事的代称。爱情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月作为爱情的象征物,除了用来烘托渲染幽会时那种恬静温馨、柔情蜜意的氛围之外,也是借月亮的皎洁无瑕来象征青年男女爱情的纯真,给人以美好的享受。
在这类诗歌中,“月”的意象变得美丽而朦胧,色调也较明朗,不再给人以忧伤的感觉,而且往往与“花”相映,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携手看花深径,扶肩待月斜廊。”(贺铸《西江月》),这两句极其生动地写出了男女欢会时在花光月影环境中卿卿我我、情意绵绵的情态,给人以温馨旖旎的印象。而“闲云归后,月在庭花旧栏角。”(晏几道《六幺令》)又为读者点明了情人幽会的地点环境。
在古人心目中,团圆的明月,就是那爱情纯洁圆满专一的象征,而月辉的消退便是爱情蒙上了阴影,而缺月便更是令人不堪追思的离愁别绪。正是“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张九龄《赋得自君之出矣》)爱情、友彩的消退是那样令人无奈、惋惜;人们多么希望残缺的月儿快快圆。正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共勉,也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祝愿。
人间不只情人爱人的别离最令人心碎,挚友的分别也是那样地动人心魄。谢庄《月赋》曰:“美人迈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川路漫长,临风慨叹,朋友一去将无音讯,好在有朗朗明月与友相共,深切的关怀仍可寄送。正是“愿为南流景,弛光见我君。”(曹植《杂诗》)只要我们共有一个心中的月亮,即使远隔千山万水,各在天一涯,也仍会感到离而不别,别而未分,对朋友温暖的宽慰,深挚不渝的友情及别后的思念,深含于字里行间。
三.月――人生的追求和哲理的升华
月是美的,正是这美丽给诗人们以多少想象!月不仅是外在的美,它的美更给人以灵魂上的启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古往今来,悠悠万世。人生的追求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是一个折磨人的哲理之谜,诗人却从美好而永恒的自然意象――“月”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便是“月”作为中国古诗美魂的千古佳作。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五字作诗,又以月为主体。“夜”是抽象的,写好了“月”就有了特定的“夜”。故全诗见月十五处,可谓句句不离“月”。月光下的景物似万花筒,随着月的起落及月色的变化。景物也闪烁变幻。开始是潮涌月出,波光滟滟;接着是月光朗朗,花似珠霰;再则是皎月中天,碧空如洗,使人遐想无边,上穷千古,下感离情;那落月的余辉散落树梢,诗情袅袅。一个“月”字贯穿今古,朗照天地,境界顿时深邃开阔。诗人对游子思妇的同情,扩大成对人生哲理的追求,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深邃美丽的艺术世界隐藏在迷离恍惚的艺术氛围中,汇成了一种情、景、理水融的清幽,邈远的诗意美。
“月”是美好的,是永恒的。“月”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代表了生与死、离与聚、悲与欢……。它是诗人的精神参照与寄托。古代诗歌中“月”的意象经历了从代表永恒到情感载体到人生追求的转变,这也代表着人们对由生的向往到人生意义的哲理升华的转变。(作者单位:荆州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4] 清・王琦:《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
[5] 《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
乐府诗全集范文6
【关键词】中国古代诗词 经典解析
中国古代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中国古代诗词内容丰富,思想内涵博大精深,采集天地万物之精华,揭示和描绘了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其中有许多作品揭示和描绘了众多物理规律和现象,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物理学知识,实现“从生活走向物理、从物理走向生活”的新课程教学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拟对以下几首经典的中国古代诗词中的物理现象进行初步的研究,抛砖引玉,以供老师和同学们参考:
第一首:东汉曹植的《七步诗》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解析:诗句中的“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形象地揭示和描绘了“燃烧豆茎”的放热现象和“燃萁煮豆”的热传递现象。
第二首:汉代乐府诗《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解析:诗中“青青园中葵”描绘了园中葵菜看上去是碧绿色的,揭示了绿色的菜叶反射绿光而吸收其他颜色光的物理现象;“朝露待日晞”形象地描述朝露等待在阳光下晒干,揭示了自然界水的蒸发现象;“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形容在春天的阳光普照下,万物生长繁荣,揭示了自然界的能的转化现象(光合作用);“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描述了担心秋天来到,花和叶将变黄衰败的心情,揭示了秋天到来叶绿素含量的减少,黄色等其他色素的颜色就会在叶面上显现出来的色光反射现象;“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描绘了千万条大河最终流入大海的自然现象,揭示了重力作用的力学原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感叹人生短暂,光阴一去不返,揭示了时间具有一维性即不可逆性特点的规律。
第三首:唐代王湾的《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下,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解析:诗中“客路青山下”描述了路人以青山为参照的相对运动现象;“行舟绿水前”可揭示出二个物理现象:一是行舟时水的反作用力现象;二是行舟与绿水的相对运动现象。“风正一帆悬”显示了以风为动力的力的作用现象;“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揭示了日出日落刚好是地球自转一周天文物理现象。
第四首:唐代李贺的《南山田中行》
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
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
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
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解析:诗中“秋野明,秋风白,塘水漻漻虫啧啧”描绘了一幅秋夜田野图:皓月当空,秋风万里,眼前塘水深碧,耳畔虫声轻细,有声有色,充满诗情画意。揭示了月光的反射现象和声音的传播现象;“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 描绘了山间云绕雾漫,岩石上布满了苔藓,娇弱的红花在冷风中瑟缩着,花瓣上的露水一点一点地滴落下来,宛如少女悲啼时的泪珠。揭示了水蒸汽的液化现象、红色光的反射现象和自然界的重力作用现象;“荒畦九月稻叉牙,蛰萤低飞陇径斜”进一步描绘田野景色:“深秋九月,田里的稻子早就成熟了,枯黄的茎叶横七竖八地丫叉着,几只残萤缓缓地在斜伸的田埂上低飞,发出若隐若现的光点。揭示了空气动力学原理、化学能转化为光能现象和光的传播现象;“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描绘了从石缝里流出来的泉水滴落在沙地上,发出幽咽沉闷的声响,远处的燐火闪烁着绿荧荧的光,在松树的枝丫间游动,仿佛松花一般。揭示了水击沙地产生的振动发声现象、燐燃烧形成的化学能转化为光能的现象和光的反射现象。
第五首:唐代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解析: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农民辛苦劳作的农耕图。诗中可归纳出三个物理现象:“锄禾”动作是利用杠杆原理;“日当午”是地球的自转到正午太阳与地球上某地的距离最小,辐射损失最小,故最热的物理现象;“汗滴禾下土”为地球引力现象。
第六首:唐代杜甫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解析:诗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形象地说明了泰山南面受日照,北面阳光照不到形成昏晓的自然情境,揭示了光的直线传播现象。“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描写了诗人极力张大眼睛远望归鸟的姿态,揭示了透镜变焦原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得极高,群山变小。正是凸透镜成像规律的具体展现。
第七首:唐代贺知章的《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解析:诗中“碧玉妆成一树高,”形容高高的柳树像碧玉发出翠绿晶莹的光,揭示了绿色的树叶反射绿光而吸收其他颜色光的自然现象;“万条垂下绿丝绦” 描绘了万千条柳枝犹如丝带一样下垂着,揭示了万有引力现象;“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描述了春风吹起,日照时间变长,气候变暖适于植物生长,植物就发芽长叶的自然现象。
第八首:唐代孟浩然的《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解析:这是一首惜春诗。诗中“春眠不觉晓”,描写了诗人一觉醒来,不知不觉“地球又绕太阳自转了半周”的自然现象;“处处闻啼鸟”。表现了声音在空气中四散传播的现象;“夜来风雨声”,蕴含着不同物质发出不同声音的音色原理;“花落知多少”表现了风雨冲力的做功现象。
第九首:唐代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解析:诗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描写了慈祥的母亲手里把着针线,一针一线地为将要远游的孩子赶制新衣。揭示了尖针穿衣的增大压强原理;“临行密密缝” 描写了慈母忙着把衣服缝得严严实实,生怕孩子受凉的伟大母爱。揭示了严实不透风而减少蒸发降温的原理。
第十首:唐代骆宾王的《咏鹅》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解析:诗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生动地了描写了鹅在水中嬉戏时鸣叫的神态。形象地揭示了声音的传播和音色现象;“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生动地描绘了鹅游水嬉戏的姿态。深刻地揭示了“浮绿水”的浮力现象和“红掌拨清波”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现象。
第十一首:北宋晏殊的词《破阵子》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解析:词中“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燕子飞来”体现了空气动力学原理,清明节后“梨花纷纷飘落”表现了自然界中的“万有引力”现象,词中描写的春夏交替,更是揭示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季节变迁原理。“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几片碧苔点缀着满池清水”让人联想到平面镜成像原理;“黄鹂的歌声萦绕着树上枝叶”,揭示了声音在空气的传播现象;一个“轻”字,让人不禁联想到空气的浮力作用。“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其中的“逢迎”二字,正是相对运动的形象写照。
第十二首:北宋苏轼的词《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解析:此词是中秋望月怀人之作。词中“高处不胜寒” 写了月宫的高寒。揭示了气温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降低的物理现象;“起舞弄清影”表明了趁着月光与自己的清影为伴起舞的情感。揭示了月下成影的光的直线传播现象;“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描写了不起月光转过朱红的楼阁,低低地穿过雕花的门窗,照到了房中迟迟未能入睡之人。转和低都是指月亮的移动,揭示了月亮的相对运动现象;“月有阴晴圆缺”指明了月亮有被他物遮住而出现亏损残缺的时候。揭示了光的直线传播现象。
以上精选了部分经典古诗词尝试着进行了物理原理、现象的解析,相信大家一定能从解析中感悟到中华文化的涵博大精深和深刻的物理学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