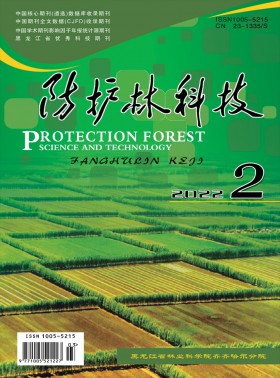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平原君列传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平原君列传范文1
平原君打算带领20名门客前去完成这项使命,已挑了十九名,尚少一个定不下来。这时,毛遂自告奋勇提出要去,平原君半信半疑,勉强带着他一起前往楚国。
平原君到了楚国后,立即与楚王谈及“援赵”之事,谈了半天也毫无结果。这时,毛遂对楚王说:“我们今天来请你派援兵,你一言不发,可你别忘了,楚国虽然兵多地大,却连连吃败仗,连国都也丢掉了,依我看,楚国比赵国更需要联合起来抗秦呀!”毛遂的一席话说得楚王口服心服,立即答应出兵援赵。
平原君回到赵国后感慨地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楚重于九鼎大吕。”(九鼎大吕:钟名,与鼎同为古代国家的宝器。)
平原君列传范文2
读音:wán bì guī zhào
解释:本指蔺相如将完美无瑕的和氏璧,完好地从秦国带回赵国首都,比喻把物品完好地归还物品主人。
出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带宝玉去秦国换取城池;见秦王有诈;便凭着大智大勇;终于使宝玉完好回归赵国。”
近义词:物归原主、物归旧主。
反义词:久假不归、巧取豪夺、横征暴敛。
例句:这些书我看过之后一定会完璧归赵,请你放心。
2、围魏救赵
读音:wéi wèi jiù zhào
解释:原指战国时齐军用围攻魏国的方法,迫使魏国撤回攻赵部队而使赵国得救。后指袭击敌人后方的据点以迫使进攻之敌撤退的战术。现借指用包抄敌人的后方来迫使他撤兵的战术。
出处:《三国演义》三十回:“曹军劫粮;曹操必然亲往;操即自出;寨必空虚;可纵兵先去曹操之寨;操闻之;必速还。此孙膑‘围魏救赵’之计也。”
近义词:声东击西
反义词:围点打援
例句:时期,日本鬼子出来抢粮,我们便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打他的县城,鬼子就急忙撤回。?
3、毛遂自荐
读音:máo suì zì jiàn
解释:比喻自告奋勇,自己推荐自己担任某项工作。
出处:《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合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
近义词:自告奋勇
反义词:自惭形秽
例句:学校需要能干的志愿者,小刚毛遂自荐。
4、负荆请罪
读音:fù jīng qǐng zuì
解释:指主动向对方赔礼认错,请求对 方责罚。
出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国大将廉颇与上卿蔺相如不和;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处处表示退让。“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近义词:幡然悔悟
反义词:死不悔改
平原君列传范文3
拼音:bù shí dà tǐ
释义:大体:关系全局的道理。不懂得从大局考虑。
出处:《史记·平原虞卿列传》:“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晋·袁宏《后汉记》卷一:“臣愚浅,不识大体。”
平原君列传范文4
[柔心弱骨] 形容性情柔和。
[风光旖旎] 形容景色柔和美好。
[婀娜多姿] 形容姿态柔和而美好。
[下气怡声] 下气:态度恭顺:怡声:声音和悦。形容声音柔和,态度恭顺。
[好声好气] 形容语调柔和,态度温和。
[怡声下气] 怡声:声音和悦;下气:态度恭顺。形容声音柔和,态度恭顺。
[轻言细语] 形容说话轻而柔和。
[轻言软语] 形容说话轻而柔和。同“轻言细语”。
[娟好静秀] 形容容貌秀美,性情柔和。
[柔而不犯] 犯:侵犯。指性情柔和,但不容侵犯。
[绵言细语] 绵:柔软。绵言:柔和的语言。细语:低细的语句。指说话时声音柔和细微,使人容易接受。
[惠风和畅] 惠:柔和;和:温和;畅:舒畅。柔和的风,使人感到温暖、舒适。
[刚柔相济] 刚强的和柔和的互相调剂。
[外柔内刚] 柔:柔弱;内:内心。外表柔和而内心刚正。
[软玉温香] 软:柔和;温:温和;玉、香:女子的代称。旧小说形容女子的身体。
[柔肠百结] 柔和的心肠打了无数的结;形容心中郁结着许多愁苦。
[刚中柔外] 刚:刚硬,坚强;中:里,内心;柔:软弱,柔和。表面柔顺,内里刚强。指人外柔而内刚的性格。也指外表和好,内藏杀机的策略。
温润如玉
【解释】温润如玉以对珍贵美玉的触感表达对人物的赞美,修辞手法上使用了通感,该词表达的不止限于外在的形象之美,更多的是指人拥有内在的气质风度与修养内涵。
【出处】《国风·秦风·小戎》里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谦谦君子
【解释】指谦虚谨慎、能严格要求自己、品格高尚的人。
【出处】《易·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丰神如玉
【解释】“丰”指的是充沛,“神”指的是神采。“如玉”指的是像美玉一般的相貌。形容一个男子长的俊美,神采飞扬的样子。
【出处】昔日你丰神如玉,英姿勃发,纵横天下,谁人敢挡。
风度翩翩
【解释】风度:风采气度,指美好的举止姿态;翩翩:文雅的样子;举止文雅优美。形容举止洒脱。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温文儒雅
平原君列传范文5
一、“穿针引线”的个人矛盾
信陵君的个人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与侯嬴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他的识人与用人上。文中说他“公子为人仁而下士”,结果“致食客三千人”。具体写了他与侯嬴的交往,可由于对侯嬴“往请,欲厚遗之”“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等的“另眼相待”,使得“宾客皆惊”。这些突出表现了信陵君“下士”的性格,也说明信陵君善于识人。就这样“侯生遂为上客”。按常理,主人一旦发生了事情,就应首先重用上客。可紧接着发生的“秦围邯郸”之事并非如此,正是这种识人与用人矛盾的体现。这样的矛盾,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埋下了强有力的伏笔,让读者感到这样矛盾一旦爆发了将不堪设想。随后,公子赴赵,辞别侯嬴,又折回问因,侯嬴向公子献计等。这样,公子与侯嬴间的矛盾就发挥了作用,从而推进了故事向前发展。同时,这也表现了信陵君信用士人、听取士人意见的性格。二是他与魏王的矛盾,作为宗室贵近,位居公子的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或养士以延誉国中,或广蓄羽翼以备缓急。可是他的这一举措对心胸狭隘、猜疑心重的魏王来说是威胁,从而形成了他与魏王的矛盾,使得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这为后文他俩之间发生权力授收反复变化的故事做了引子。
二、“政治需要”的家族矛盾
信陵君的家族矛盾在“窃符救赵”的故事中得以体现。“且公子可以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一语道破了魏公子对处在强秦虎口下的赵国解救,是在救他自己、救他的家族,这是他家族的矛盾。我们知道,在封建婚姻中,宫廷婚姻大多为政治婚姻;在封建官僚体制中,亲缘关系的远近在身份地位中的重要性。因此,他与姐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是一个隐形的“家族政治集团”。这样“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就显得自然,顺理成章了。信陵君的所作所为,从帮助平原君的角度看,体现了公子能急人所难的性格,也说明他“仁”的一面。但同时不可忽略为了家族矛盾又刻画了他自私的性格。正是在这种“自私的性格”驱使下,他必定要救赵,先向魏王请求,不成功,接着“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赴秦军”,从而推进故事向前发展。
三、“义无反顾”的国家矛盾
平原君列传范文6
一、古汉语常用字释义
1、“之”字的用法
(1)用作指示代词。如《左传》:“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中的前一个“之”指代处所,是“那里”的意思、后一个“之”指代人,是“他”的意思。又如《庄子?逍遥游》:“之二虫又何知?”中的“之”指代动物(蜩和鸴鸠),是“这”的意思。
(2)用作动词。“之”作动词,是“到、往、去”等的意思,如《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商君欲之他国。”的意思是“商鞅想要到别国去。”里面的“之”就是“到……去”的意思。又如《司马光?李愬雪夜入蔡州》中的“诸将请所之。”的意思是“各位将领请问(李愬)要去什么地方。”里面的“之”就是“去……”的意思。
(3)用作助词。“之”字比较复杂的用法就是用作助词。因为根据句式及语境的不同有不同的解释和作用。最常见的是用作结构助词,是“的”的意思。如《礼记》:“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中的“之”是“的”的意思。另外,“之”可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连接主语和谓语成一词组,取消句子独立性,可不译。如《韩非子?扁鹊见蔡桓公》:“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中的“之”在这里没有实在意义,只是连接主语“医”和谓语“治”成一词组,用来取消其句子独立性。
2、“而”字的用法
(1)用作连词。“而”用作连词:可表承接关系,如《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中的“而”是“就、然后、便”等的意思。可表转折关系,如《荀子?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中的“而”是“却”的意思。可表假设关系,如《徐珂?冯婉贞》:“诸君而有意,瞻余马首可也”中的“而”是“如果”的意思。还可表选择关系,和“则”差不多,常同“非”前后呼应,表示非此即彼的选择关系,如《史记?张义列传》:“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发征,其势不两立。”里的“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中的“而”为“不是……就是……”的意思。
(2)代词,对称代词。音义同“尔”,译为“你”。
如《战国策?赵策三》:“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里的“而母婢也”中的“而”是“你”的意思。又如《史记?项羽本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里的“必欲烹而翁”中的“而”是“你”的意思。
(2)副词,“尚且、都”的意思。如《孟子?万章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中的“而”是“都”的意思。
3、“乎”字的用法。
(1)用作语气助词。用在句末表示疑问或反问,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吗、呢”,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中的“乎”是“吗”的意思。又如《史记?平原君列传》:“赵亡则胜为虏,何为不忧乎!”中的“乎”是“呢”的意思。以及用在句末表示感叹,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啊、呀”,如《史记?吴起传》:“美哉乎,山河之固!”中的“乎”是“啊”的意思。又如《孙子兵法?虚实》:“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中的“乎”是“呀”的意思。
(2)用作介词。和介词“于”的用法相似,所不同的是:“于”字及其宾语既可以放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前,也可以放在其后,而“乎”字及其宾语只能放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乎”字常常介绍出处所、原因、或比较的对象等。可译为“在、于、比”等,如《欧阳修?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中的“乎”是“于”的意思。又如《宋史?岳飞传》:“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的“乎”是“在于”的意思。
(3)作为词尾形容词、副词词尾。如《庄子?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中的“乎”表示“……地”的意思。又如《左传?襄公29 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中的“乎”表示“……的”的意思。
二、古汉语常用字释义的技巧
古汉语常用字的释义是有技巧的,简述如下:
1、通过古汉语实词的本意来分析词义。古汉语虽然与现代汉语的差别较大,但古汉语毕竟是现代汉语的源头,故有些字意思是相同的。可根据某些实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意思来结合语境分析其在古汉语中的意思。如《贾谊?论积贮疏》:“犹可哀痛。”中“犹”是“还”的意思、“可”是“可以”的意思、“哀”是“悲哀伤心”的意思、“痛”是“痛苦”的意思。
2、借助成语来分析词义。成语:有的来自民间口语经长久演变而习用,有的来自古代典故经文人引用遂为成语,其中很多字词的用法都沿袭了本来的意思,跟古汉语中的解释是一致的。例如成语“日薄西山”中“薄”是迫近的意思。在古汉语中也常有这个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