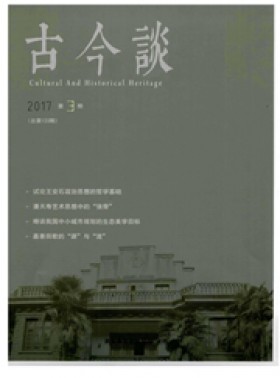史家之绝唱范文1
关键词:《史记》 文言文教学 小组合作 快速反馈 作文
文言文经过千百年淘洗而流传至今,是诗文中的极品。精华佳作,不能不读,于是《史记》作为选修教材被专门引入了高中教学。然而,文言文并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语言,学起来枯燥乏味。
作为一名一线的工作者,如何才能使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化巨著在课堂中飞扬呢?以下是我在从事《史记》教学中的几点做法及思考,与大家共商。
一、小组合作学习制度
在《史记》的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制度让我们的文言文课堂生动飞扬!《史记》的教学归根到底是要恰当处理“文”与“言”的关系,“文”、“言”并重,才能让学生爱上文言文。
1、重“言”。高考的指挥棒仍在挥舞,点句读,是读懂文言文最基本的功夫。在《史记》教学中,我非常重视“言”的教授。传统的“串讲法”能做到“字字清楚,句句落实”,但整堂课死气沉沉,因此必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全身心参与课堂教学,让学生爱上文言文。如面对《赵氏孤儿》这篇文章,我便采用了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法。五个段落分别分配给五个学习小组,每个学习小组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完成以下任务:(1)找出四个实词;(2)找出三个虚词,并重点补充一个虚词的用法;……
课堂上,每个学习小组在充分谈论之后,选出代表汇报本组的预习和讨论成果,教师只在关键处做一下补充或点评。因为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任务以及展示的机会,所以学生预习扎实、谈论积极,如此便把教师的“讲”变成了学生的“学”, 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学生喜欢学,老师轻松教。
2、重“文”。正如钱梦龙先生所说:“文言文首先是‘文’,而不是文言词句的任意堆砌。”言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最终是为文服务的。
面对文本时,重视文本人文陶冶的作用,这既是对新课标选文的理解,又是对文化的尊重,更是对学生心智的真正开启!因此,《张良》的一课,在学生预习及反复阅读之后,小组内结合文本解决导学案中的问题:(1)全文共描述到张良的哪些奇计良谋?(2)这些计策表现出张良具有怎样的特点?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十分钟的时间,教室被学生吵得沸沸扬扬,张良的计策浮出了文本,张良这一人物形象也渐渐清晰了。
总之,小组合作学习有效调动了学生讨论交流的积极性,提高了认知兴趣,形成了“组内成员合作,组间成员竞争”的新格局,从而达到了“优者更优,差者提高”的目的。
二、建立快速反馈制度
教师的检查是点燃学生学习、复习“热情”的火石。
1、导学案检查。在导学案的设计中,我们不断结合教学实践进行调整、创新。导学案主要由三部分——预案、学案、复习案构成,而预案和复习案将课堂检测及教学反馈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预案以最真实、最快速的方式将学生的预习成果展示在我们面前,暴露了学生在预习当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复习案及时反馈学生的课堂信息,最大限度地暴露了学生在自学和检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总之,在课堂中,我们以导学案为依托,建立快速反馈制度,通过小组内的合作交流、小组之间的竞赛,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的干劲足了,并且能够当堂掌握所学内容,也避免了往常“干听”的坏习惯。
2、爬黑板检查。课前我会准备好3—5张纸条,涉及内容为实词、虚词或者一到两句包含重要知识点的句子翻译,找几个同学“抽签”爬黑板。他们爬黑板前,我一般留出一定的自我再复习的时间,这样学生的积极性就大了许多,并且对重点语句的敏感度也增加了不少。
当然,快速反馈的形式多种多样,我们可以通过课上的一些活动来检测,也可以通过课后的作业来检测,还可以通过一些阶段性的测试来检测。
史家之绝唱范文2
关键词:歌唱;语言;歌曲;题材;风格;运用;规律
中图分类号:J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132-01
歌唱语言是歌唱艺术(声乐艺术)的基础,它与音乐各占整个歌唱艺术的半壁江山,语言与音乐,水融,有机统一,完美结合,共同打造出声乐艺术的无穷魅力。
古今中外的许多歌唱家与音乐理论家,都十分重视歌唱语言的运用。我国宋代沈括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说:“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有字,字中有声’。”①明代魏良辅也在其所著的《曲律》一书中说:“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②将“字清”列为“三绝”之首。我国传统的声乐理论,始终强调“字正腔圆”,“字正”即指歌唱语言运用的原则。
“不同的语言决定不同的声乐艺术风格、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声乐学派。”③而反过来讲,不同歌曲题材风格上的不同,其语言运用规律也各不相同。
具体分析,歌唱语言在不同歌曲题材风格上的运用规律,可以分解为以下四大层面进行系统化研究。
一、民族题材风格歌曲语言运用的规律
民族题材风格歌曲,在语言运用有独特的规律,这集中体现在民族化上面。
民族化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艺术的生命与灵魂,也是声乐艺术的生命与灵魂。
题材是声乐作品内容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构成音乐形象与事件的具体材料。风格则是词曲作者在歌曲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鲜明的艺术特色。显而易见,民族题材歌曲的民族化风格,决定了其歌唱语言民族化的运用规律。
事实上,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民族题材风格的歌曲,在语言运用上也都有着不同的规律。例如意大利歌曲歌唱语言的夸张外露、热情奔放的规律、俄罗斯歌曲歌唱语言的雄宏大、沉实厚重的规律、德国歌曲歌唱语言的严谨细腻、优美含蓄的规律、法国歌曲歌唱语言的浪漫清新、秀丽典雅的规律、日本歌曲歌唱语言的小巧精致、多愁善感的规律……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同样,中华民族歌曲歌唱语言的运用,也充分凸显出自身,即运用汉语与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强化其自然、亲切、真挚、含蓄等民族性,从语音、语调到语气、声韵以及字头、字腹、字尾等,直到语义,都以民族化为独有的运用规律。有许多少数民族歌曲,还充分运用少量本民族语言以突出这些民族化特点。例如藏族题材歌曲中的“雅拉索”、维族题材歌曲中的“亚克西”、赫哲族题材歌曲中的“赫呢哪”等等,都是成功的范例。
二、地域题材风格歌曲语言运用的规律
地域题材风格歌曲,在语言运用上也有独特的规律,这集中体现在地域化上面。
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是地域的,也越是民族的。因此,地域题材风格歌曲在语言运用上,就以凸显地域化为其重要规律。
在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的范例。例如郭颂演唱的东北民歌《看秧歌》、《瞧情郎》、《丢戒指》等,都以东北方言为主要运用规律。
三、历史题材风格歌曲语言运用的规律
历史题材风格歌曲,在语言运用上同样有独特的规律,这集中体现在历史化上面。
我国历史题材风格的歌曲,歌词上有的直接以古典诗词为歌词,有的虽系新创,但也吸收了古典诗词的精华,具有古朴、典雅、庄重的艺术风格,而在歌唱语言的运用中,都彰显出历史化的特点。例如杨鸿基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屠洪纲演唱的《霸王别姬》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四、现代题材风格歌曲语言运用的规律
现代题材风格歌曲,在语言运用上更有独特的规律,这集中体现在现代化上面。
其中现代化词汇,在语义、语音、语气、语调、声韵诸方面,均凸显出现代化特点。例如刘欢演唱的《千万次地问》,就融入了英语“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 sk me”,强化了现代化特色。
本文为佳木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面上项目《歌唱语言运用与创新研究》,项目编号:W2011-028
注释:
史家之绝唱范文3
【关键词】民族声乐;演唱;京剧唱腔
中图分类号:J8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101-01
在我国,戏曲艺术历史悠久,上可追溯到千年之久。京剧素来有“国粹”之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名片。民族声乐演唱同样有着特别的艺术魅力,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欢迎。京剧表演造型特别、唱腔独特,在民族声乐演唱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一些民族声乐表演艺术家已经不同程度地将京剧唱腔的精华运用到民族声乐演唱中,为民族声乐演唱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京剧与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现状
京剧之名最初出现于清光绪年间,历史上曾经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前身是以唱吹腔、高拨子、二黄为主的徽班,从乾隆五十五年徽班进京到道光末年,经过多少辈人的努力,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京剧艺术。它吸取了民间歌舞、说唱艺术和滑稽戏等各种形式,并经过长期磨合,把歌、舞、诗、画融为一体,并逐渐达到和谐统一的效果,形成了“以歌舞演故事”的表演特征。
和京剧相比,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历史较短。它的兴起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同样作为演唱方式,民族声乐艺术和京剧存在很多方面的相通之处,都是以表演与唱腔相结合,要求表演者能够很好地运用气息和调节共鸣。京剧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今天的声乐艺术表演中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使声乐艺术中唱腔的控制及声音的把握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现在,京剧式唱腔训练已经成为了民族声乐艺术培训中的必修课。经过两者多年的融合,民族声乐表演中京剧唱腔的运用表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协调性逐步提高。京剧唱腔在民族声乐中得到运用,不仅可以使两者相互借鉴共同进步,而且能够为我国的文化发展提供更好的创新思路。
二、民族声乐演唱中京剧唱腔的运用
(一)“咬字发音”在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运用。不论是京剧表演还是声乐演唱,都是内容和情绪的表达,都是以语言表达为基础的。而语言表达需要注意语音、语调和语气的变化,平常讲话尚且如此,更何况作为舞台表演艺术的京剧和民族声乐。在京剧唱腔中,对表演者的咬字和发音要求很高。咬字清楚作为京剧表演的基础,要求恰到好处,有种形象的说法就好比“猫叼耗子”,不紧不松。京剧咬字要字正腔圆、字音清晰并且不能吃音,这样才能够保证在表演中演唱发音、收韵和收声都一气呵成,旋律流畅。咬字发音在民族声乐演唱中同样重要。明朝著名戏曲音乐家魏良辅先生在《曲律》一书中曾经提到一句“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足可见咬字发音的重要性,并提示我们在民族声乐演唱中成熟运用咬字发音的必要性。
(二)“吐字行腔”在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运用。京剧中讲究声情并茂、字正腔圆,十分注重声音表达的圆润性,做到发音吐字清晰、腔随字转。在民族声乐表演中,同样要将吐字行腔灵活应用,不但要学会京剧唱腔中的发音和咬字,而且要注重声音的音色特征,根据所要表达的情感,加强声音表现的辨识度,以及声音的情感厚度。京剧中不仅讲究吐字,而且在行腔中更是唱法丰富,京剧中有连腔、滑腔、哭腔、断腔及笑腔等等各种唱法。这些唱法都有助于使京剧表演中声音的情感表达更加有层次。在民族声乐表演中运用这些唱法,可以使歌曲表现更加有意境,突出展示了歌曲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情感诉求。另外,民族声乐表演中有时也运用了京剧唱法中的“曲情”,达到了与京剧相近的艺术表现效果。吐字行腔在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运用,典型的例子就是著名的蒙古民歌《牧歌》,这首歌运用了京剧中连腔的唱法,闭目细听,可以想象到广袤的大草原一望无际,朵朵雪白的云彩点缀在蔚蓝的天空,远处成群的牛羊为草原带来生机与安详。在民族声乐演唱中灵活运用京剧唱法中的各种技巧,能够使音乐更加具有感染力。
三、结语
民族声乐演唱是一门技巧与情感兼备的综合性艺术,不仅要注意歌唱技巧的掌握还要注意歌曲情感的表达。京剧是我国的传统声乐艺术的精粹,在民族声乐演唱中灵活运用京剧唱腔,对于民族声乐演唱者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不仅要演唱基本功扎实,而且要熟练掌握京剧唱腔的唱法,另外还要准确表现曲目的情感。京剧唱腔在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运用,为我国的民族声乐演唱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为我国民族声乐的创作提供了更加开阔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王艳艳.京剧唱腔在民族声乐演唱中的借鉴与应用[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2]黄勇强.声乐演唱中京剧唱腔的运用[J].戏剧之家(上半月),2014,(04):21.
史家之绝唱范文4
去年年初,上海文化出版社资深编辑林爱莲来电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一项“与你的文学创作无关”、且“付出与得到绝对不成正比的工作”。我好奇地问,这到底是什么选题呢?她说,社里曾出版过京、沪、越等诸多剧种的小戏考,有的剧种还出过好几个版本,惟独没有出版过淮剧戏考,也从没见过淮剧戏考面市。她说,你是上海淮剧团的专业编剧,比较合适。如果我没有兴趣,那么这个选题可能就得割爱了。
我一时没有回答。于是,林爱莲请我认真考虑之后再作答复。
我上网搜索“小戏考”。果然没有淮剧的,没有,一片空白。林爱莲的话得到了证实。淮剧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进入上海也已一百多年,居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属于淮剧人自己的戏考!那么,作为一名“上淮”人,我有什么权力退缩呢――虽困难重重,却是一个历史的机遇!
我拿起了话筒,拨响了林爱莲老师的电话。就从这一秒钟起,我开始面对一个字――难。
尽管知道难,却还是没料到会这样难。我从“上淮”资料室里将上了年岁的资料、剧本、海报、剪报、宣传单片、节目说明书等等,一次次、一袋袋地拎回家中,仔仔细细地编年史,小心翼翼地选曲目,认认真真地将选定曲目的内容简介、编导演主创人员、唱词唱腔、演员小传等等一一输入电脑。那些油印剧本、宣传单片、说明书的纸张已发黄发脆,字迹模糊不清,甚至缺字少句,我细细考证、勘误,打电话询问、上网查找、翻阅资料……
这还不算复杂。复杂的是某演员当年演唱的究竟是哪个版本,一定要弄清楚,因为每个版本的唱词各异,不能出半点差池。然而,即使请教了这位演员,甚至找上了该剧编剧,但由于相隔多年,事过境迁,他们也大都记不清了。而那些已仙逝的老前辈,则更无从问起了。
但是,“戏考”“戏考”,关键在一个“考”字――考证、考据、考释、考量,来不得半点想象和马虎。在 “上淮”领导的帮助和关心以及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剧团资料室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一步步地走过来了。他们帮我从无数文字和图片资料中找寻所需要的剧本、照片,甚至是钢笔记录整理的唱词。而不少德高望重的淮剧老艺术家主动为我提供翔实资料,使我深深感动。
希望这本《淮剧小戏考》能折射出上海淮剧百年来的发展历史、演变轨迹、风雨历程,能让读者充分领略淮剧骨子老戏、经典唱段、新编剧目,更能展现海派淮剧的无限魅力和无穷韵味。
以下作为“小贴士”,共3段
淮剧又称江淮戏,发源于古楚国域内,即今江苏省境内长江以北的盐阜和清淮宝两大地区,距今约有二百年历史。淮剧主要流行于苏北、皖北、上海及沪宁沿线一些城市,现已成为江苏、上海主要剧种之一。1949年,上海江淮戏公会改名为上海淮剧改进协会。盐淮小戏、江北戏、江淮戏等被统一定名为淮剧。
淮剧在申城
1906年淮河洪水泛滥,淮戏艺人纷纷弃家逃难,涌入上海。为了生计,淮戏艺人们自由组合,在街头用筷子击打盘底敲曲演唱,内容多是具有浓郁乡土人文气息的小唱段。1912年,淮剧艺人韩太和创建“韩家班”,活跃于上海南市、南码头等地区。淮剧终于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挣得了一席之地。
淮剧的绝活绝技
爬竿《杨香武盗杯》一剧中,舞台前右侧竖立一根约十余米高的粗木桩,谓之“围杆”。演员头戴黑高冲帽,赤膊穿黑马甲,下穿黑彩裤和黑快靴,腰系紧扎,登台舞蹈亮相后,轻捷地徒手爬上高杆,在杆顶上口擒玉杯,抱杆横卧并施展“犀牛望月”姿态,紧接着悬空蹬脚,使出“金鸡独立”姿势,最后将肚子抵在杆顶,手足腾空,使出“乌鸦展翅”等一系列的惊险动作。
滚灯《滚灯》一剧中的赌棍丑角浑名“怕老婆”。舞台上用十张长板凳交叉垒塔,丑角头顶一撂瓷碗,最上面一只碗盛油点燃灯火,在十张板凳的空隙间钻进钻出、爬上爬下,转身打滚,并使出“卧鱼”、“探海”等高难度动作,其惊险程度堪比杂技。
挑花担《阴阳河》一剧中,男旦有“翻扑摔掼”的动作。演员头包大顶白球,身穿素白裙袄,肩挑水担,步伐轻盈,姿势优美。有时不扶扁担,双手临空或叉腰做出各种舞蹈和戏曲身段动作,台步稳健,圆场奔跑迅速快捷,同时还夹插左右连续钻圈的高难度动作。
史家之绝唱范文5
一
在中国民族歌剧中,这种“生”与“死”的二元对立,寓于情节发展和矛盾展开之中。剧中,主要英雄人物不幸被捕,敌人出于政治或者军事目的,先对她们进行政治说教、物质利诱,后施以酷刑,并以结束其生命相威胁,将一个“生”与“死”的二元对立呈现在她们面前。这种“生”与“死”的二元对立,正是歌剧悲剧性生成的基础。纵观古今之悲剧,“生”与“死”作为一个二元对立,是戏剧矛盾或戏剧性的集中体现。对于悲剧中的许多人物而言,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正如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那段经典的道白:“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不难看出,这种“抉择”在许多剧目中都成为一种“两难”。因此,这种“生”与“死”的二元对立本身就意味着悲剧性,或干脆说本身就具有一种基于宿命的悲剧性。然而,在中国民族歌剧中则有所不同。这首先因为,对于这些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英雄人物而言,为自己而“生”,还是为革命而“死”,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不用去做艰难的抉择。这就是说,“生”与“死”作为一个二元对立,不过是剧中“敌我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一种体现,故“生存”还是“死亡”对于这些人物来说并不是什么“两难”。但尽管如此,这种“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仍是其悲剧性的基础。这就在于,没有这种“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也就无所谓对“死”的选择,进而也就没有歌剧中那种基于“死亡”的悲剧性。
这种“生”与“死”作为一个二元对立的设置,在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的。在《红霞》以来的中国民族歌剧中更是显而易见,可以说中国民族歌剧一种重要的“造剧模式”。在歌剧《洪湖赤卫队》中,这种设置“生”“死”二元对立的创作思维尤为突出,尽管韩英这位主要英雄人物最终并没有“死”。在歌剧的第四幕,敌人让韩英的母亲到狱中劝降,说服韩英写信欺骗赤卫队,以便达到消灭赤卫队的目的。于是,母女之间就有了这样一段对唱:“(韩母唱)眼看女儿遍体鳞伤,好似钢刀割娘的心,指望母女能相聚,谁知相会在牢房。(韩英唱)我的娘,莫悲伤,让儿好好看看娘。(韩母唱)今天我能见我娘面,身在牢房无惆怅。如今我儿遭祸殃,为娘怎能不心伤。彭霸天,丧天良,要逼你写信去招降。你要是写了,怎能对得起受苦人和共产党。你要是不写,明天天亮你就要离开娘!”在这个唱段中,韩母道出了这种“写”与“不写”的“两难”。这里,作者基于亲情设置了这样一个“生”(“写”)与“死”(“不写”)的二元对立,给人以戏剧悬念。但这种“两难”很快就消除了,母女之间相互鼓励,同仇敌忾,选择了“不写”,也就是选择了“死”。这正是《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中那段气壮山河的表达:“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至此,一种基于“死亡”的悲剧性油然而生,并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尽管韩英在即将赴死的关键时刻在地下党员张副官的掩护下成功“越狱”而没有“死”成,且《洪湖赤卫队》一剧最终也以洪湖赤卫队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落幕,并非是悲剧,但在第四场这样“此时”“此地”的境遇中,其悲剧性毋庸置疑。这也是《洪湖赤卫队》这部并非悲剧的歌剧的悲剧性之所在。
总之,中国民族歌剧中这种“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作为剧中“敌我矛盾”这一主要戏剧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剧中最重要的戏剧情节,也是剧中主要英雄人物革命气节的实现方式,是剧中最重要的戏剧基因,也是歌剧悲剧性生成的重要基础。
二
中国民族歌剧中的这些革命历史题材剧目,像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许多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一样,也在设置“生”与“死”的二元对立后,继而谋求这个二元对立的统一,即戏剧矛盾的解决。这就需要变“生”“死”的“二元对立”为“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的获得就在于这位主要英雄人物对“死”的选择。在这些歌剧中,她们都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死”,履行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这些英雄人物(除韩英外)最终都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确,在剧中那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她们的“死”是不二的选择。这种对“死”的选择正是中国民族歌剧的悲剧性之所在。
这种对“死”的选择,作为一种艺术表达,主要体现在主要英雄人物的唱段,尤其是在她们慷慨赴死前的“绝唱唱段”①之中。这些“绝唱唱段”如歌剧《红霞》中红霞的唱段《我把青春迎光明-凤凰岭上祝红军》、《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江姐》中江姐的唱段《五洲人民齐欢笑》、《党的女儿》中田玉梅的唱段《万里春色满家园》、《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的唱段《胜利时再闻花儿香》、杨母的唱段《娘在那片云彩里》等。在这些“绝唱唱段”中,这些主要英雄人物义正言辞地痛斥敌人,表达出为共产主义或民族解放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决心,在“生”与“死”的二元对立中选择了“死”。但值得注意的是,整个唱段在选择“死”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对“生”的难舍割舍,对生命的无限依恋。这包括对故乡、亲人的“告别”(如《万里春色满家园》)、“托孤”(如《五洲人民齐欢笑》)等②。这种对“生”的留恋,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党的女儿》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金环的《永远的花样年华》、《胜利时再闻花儿香》这两个唱段,就充分表现出了金环这个年轻女子对生命的难以割舍。创作者也正是在对于“生”的人道主义赞颂中强调了生命价值,表现出了对生命的赞颂。应该看到,上述这些“绝唱唱段”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生命的赞美。正因为如此,这些主要英雄人物的“绝唱唱段”在表达对“死”的“无惧”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对“死”的“恐惧”。这正是一种悲剧的艺术表达方式。在这之中,“恐惧”是本能的,伴随着“同情”和“怜悯”逐渐演化为一种“悲剧”的审美心理,正是民族歌剧悲剧性的内在机缘。这里的“无惧”,则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豪情壮志,是一种非本能的“意志力”。然而,这种来自信念的“意志力”,代表着一种正义的力量,也是民族歌剧的悲剧性所在。这种“无惧”的悲剧性则来自另一种审美感受――“崇高”。于是,一种面对“死亡”的“无惧”,作为一种对生死的“超越”,就演化出了“崇高”,或者说“崇高感”。然而,这种“崇高感”作为一种美感,正是一种“悲剧”的美感。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民族歌剧中“绝唱唱段”悲剧性,既来自人们对英雄人物“死亡”的“恐惧”,又正来自英雄人物对“死”的“无惧”而产生的那种“超越感”――“崇高”。也正是在这种基于“崇高”的美感中,中国民族歌剧的这种悲剧性得以加强,得以升华。
还不难发现,在民族歌剧主要英雄人物的“绝唱唱段”中,“崇高”还不仅是对“死”的“超越”,而且还在于英雄人物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革命事业的“展望”③。如《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五洲人民齐欢笑》、《万里春色满家园》等唱段,都表达了“只有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远大理想和崇高境界。这种“展望”无疑也是一种“崇高”,并且,这种基于“展望”的“崇高”,与基于对“死”的“超越”的“崇高”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中国民族歌剧的悲剧性,既源于主要英雄人物的“死”,又来自这种基于这种“死”的“崇高”。
三
中国民族歌剧中这种基于“生”“死”二元对立的悲剧性,可以理解为古今中外一种基于“悲剧”的审美心理在20世纪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这种悲剧性也正是民族歌剧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古往今来,大凡“悲剧”都与“死亡”相关,都关乎于“生”与“死”的话题,而“生”与“死”又都设置为一个二元对立,甚至是一个“两难”。在中国古代悲剧(如《赵氏孤儿》、《窦娥冤》)中,其悲剧性无一不来自“死亡”。古代戏剧家(如关汉卿)也正是通过剧中受到恶势力压迫的人的“死亡”唤起观众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同情”、“怜悯”。这种基于“死亡”的“恐惧”、“同情”、“怜悯”正是所谓“悲剧”的审美心理,也正是“悲剧”的“美”之所在。也大概因为如此,古今中外的戏剧,最耐看的就是“悲剧”。何谓“悲剧”(tragedy)?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④这就意味着,悲剧旨在“引起怜悯与恐惧”,进而使人的情感得以“净化”。其实,这里所说的就是“悲剧”给人的或美感,“悲剧”的艺术魅力都来自“悲剧”本身给人的那种“怜悯与恐惧”。这样一种基于“死亡”的“悲剧”审美文化心理在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文艺创作广泛存在。中国民族歌剧的悲剧性,正是这一审美文化心理的一种体现。尽管中国民族歌剧中没有一部是“悲剧”,但其悲剧性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人们在观看这些剧目时同样也会因为女性英雄人物的“死亡”而感到“恐惧”和“怜悯”,于是便有了一种基于“死亡”的悲剧审美心理,这些歌剧也就呈现出了一种“悲剧”的美;进而,这些歌剧也就获得了一种基于“死亡”之悲剧性的艺术魅力。但更重要的是,人们还获得了一种基于“死亡”的“崇高感”,一种对“生命”和“死亡”的“无惧”,对“生”“死”的“超越”,一种基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超越感”,从而那种基于“死亡”之“恐惧”的悲剧性得以加强和升华。这也是民族歌剧之艺术魅力之所在。总之,正是这种基于“生”“死”二元对立的悲剧性,作为一种基于“悲剧”的审美特征,作为一种与“崇高”密切相关的审美特征,使中国民族歌剧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设置“生”“死”二元对立,进而选择“死”,变“二元对立”为“对立统一”,最终获得一种基于“悲剧”的美感,可以说是一种“造剧模式”。但这种模式也值得反思和修正。这就需要在创作中歌颂“生”的可贵和伟大,强调“死”的难以避免,从而建立“生”的人道主义价值观,进而使文艺作品的悲剧性及其艺术魅力,不但从“崇高”中获得,而且还从“死亡”的审美意义中获得。
①关于中国民族歌剧“绝唱唱段”及其相关概念,参见白致瑶《中国民族歌剧“绝唱唱段”研究》(硕士论文),南京艺术学院2011年。
②参见白致瑶《中国民族歌剧“绝唱唱段”研究》第二章第二节。
史家之绝唱范文6
一是美学特征相同。从美学的角度上说,龙江剧丑角与二人转丑角都是美的,“丑”不是丑陋,更不是丑恶,而是“美玉出乎丑璞”(葛洪),“狂欢发于丑趣”(田子馥),是一种形式美与内涵美的另一种表现。或滑稽突梯,或谲谏讽刺,或戏谑诙谐,或逸趣幽默,旨在揭示社会与人生本质,以夸张之法再现社会现实,不过这种再现采取的是曲折迂回的方式而已。
二是历史渊源相同。从历史渊源上讲,龙江剧丑角与二人转丑角都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中国戏曲与中国曲艺的延续与发展。据史料所载,丑角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20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就有关于丑角艺术的记述;至唐代的参军戏中,已有“参军”与“苍鹘”两个角色,其中的“参军”,便是丑角。再后来金院本中的“副净”,元杂剧中的“丑”,正式确立了丑行之名及其作用与地位。
三是表演功法相同。龙江剧的丑角,不论是文丑(“三花脸”或“小花脸”)。还是武丑(武三花脸),都与二人转的丑角的表演功法相同,都是说、唱、扮(相)、舞、绝五功。
四是艺术效果相同。龙江剧的丑角与二人转的丑角,都共同起到造气氛、提精神、抖包袱、引观众、活剧场的艺术效果。
五是艺术风格相同。龙江剧的丑角与二人转的丑角都以“黑土风格”为其共同特征,具有土野火爆、粗犷豪放、大棱大角等地域特色。
其次是不同之处,这也有如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