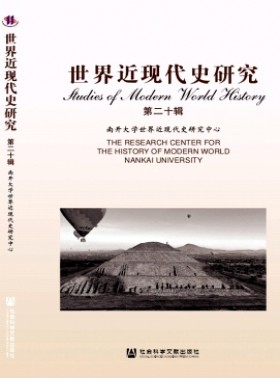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近现代与现代的史识融合,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长期有感于因通俗文学一支的阙如而导致的残缺不全的文学史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范伯群教授就把研究的视域转向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在完成了资料汇编、作家传记、重要论文等先期成果后,终于在2000年4月出版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提升了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的高度,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但范伯群并没有满足于此,为弥补《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粗放性、笔调格调的不一致等不足,他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对自己钟爱的通俗文学园地进一步精耕细作,于2007年1月出版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达到新的研究高度,贾植芳教授评价为:“这是设计精巧、施工精心的优质二期工程。”[1][p.3]对比这所谓的“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我们发现后者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作为一种“史”的整合,文学史同样需要文学史家的史识观照和勾勒,需要文学史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充分的理性把握,需要“突出文学演进的趋势,而不是大作家的生平逸事;注重结构的分析,而不是事件的叙述”[2][p.3]。否则,如果把重写文学史看作是单纯时间的延伸和叙述量的激增,那文学史就变成了散漫的“资料长编”,而真正失却了“史”的含金量。对比范伯群主编、著写的两部通俗文学史,我们发现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文学“史”的意识明显加强了。 首先,在书写体例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改变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板块式的结构形式,不再把全书主要分为社会言情编、武侠会党编、侦探推理编、历史演义编、滑稽幽默编、通俗戏剧编、通俗期刊编、大事记编等八个部分,不再遵循“大按题材小按时间”等形式的编写体例(如社会言情编分述倡门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地域小说,倡门小说,个案分析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从1848年的《风月梦》论到1938年的《亭子间嫂嫂》),而是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分时代地把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潮与报刊杂志的兴办结合起来论述,把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兴盛放置于现代传媒的文化语境中,突出了其世俗现代性的文学特质,进一步彰显了与精英文学互动相生的发展脉络:“19世纪90年代到‘五四’前,现代通俗文学曾得到大发展与大兴旺,它不仅有《海上花列传》那样的艺术成就极高的小说,而且有谴责小说这样的得到老百姓拥戴的通俗小说;而在‘五四’后,情况有了变化,它得在知识精英文学的相克中求得相生。这是一个通俗文学在被贬中不断改进自己,以求得自强,以及在自强中不断开拓新垦地,不断探索新的生长点的时期,无论是民国武侠小说的奠基,狭邪小说的人情、人道化,侦探小说的移植与本土化,都市乡土小说的崛起,电影、画报热的潮起,都说明通俗作家在相克中的求得相生,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途径;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刘云若与还珠搂主等人的作品更是形成了新的冲击波,通俗文学的成就已开始与知识精英文学‘双翼齐飞’的格局;到20世纪40年代,有的作家则已经进入‘超越雅俗’、‘融会中西’的境界,其实这是很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股势头不得不移到台、港去作通俗文学的血脉承传。”[1][p.588-589]可以说,变更体例后的通俗文学史较好地体现了上述的史识脉络,更容易从宏观角度把握现代通俗文学史的性质和发展历程,更加严谨凝练,通透性和体系性更加鲜明。 其次,在某些文学史观点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阐释,力求更加严谨可信。《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毅然把讲“史”的范围从原来的近现代压缩到现代,隐去了近代工商业日趋发展背景下的上海文学趋于现代的萌发历程,删去了关于《风月梦》、《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作品的现代通俗文学“前史”或者说近代史的论述,而把论述的起点放到了《海上花列传》上,把它界定为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并论述其六个“率先”的开创意义,赋予其成熟的现代性特征,把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这种界定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它改变了“注重作家作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突出外在价值和文学历史价值的文学史观念”[3],体现了“注重文学作品的艺术创造力、审美价值等内部本质特征,以此阐释评论作家作品本身的价值,突出作家作品对艺术本身的贡献”[3]的文学史观,不失为一种富有新意的独到见解。另外,《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又在第十九章论述新市民小说时重点论述了张爱玲、徐讠于和无名氏,称其为文学领域中的“一国两制”[2][p.573]者,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通俗文学“融会中西”、“超越雅俗”的发展势头。以三位在新文学史上叫响的作家为其通俗文学史收尾,这也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新创,既能“承上”———是现代通俗文学发展的结果,又能“启下”———为将来《中国当代通俗文学史》甚至《中国二十世纪通俗文学史》的研究提供某种契机,因此它的命名与确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还有,《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对“都市乡土小说”的命名、对“黑幕”与“黑幕小说”的概念辨析、大众化和通俗文学的生命潜力等诸多文学史命题的分析,或是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思考,或是范伯群新近的思考所得,都显示了其通俗文学史研究的继续深入。 最后,在文学现象的成因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加注重“史”的勾连,努力把通俗文学现象放到与外国文学、古代文学或者知识精英文学的关联中去做动态的分析,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孤立的存在”。既然“凝聚与变异相交而成的坐标,是文学研究整体所依据的主要框架”[4][p.34],那么古今融会、中西交流融会背景下的通俗文学同样也呈现着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复杂印痕,表现出传播与接受之间的同步态与错位态,而这些方面的分析对文学史的勾连与叙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作为“一期工程”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也非常注重这方面的论述,比如在分析通俗文学中的社会小说时,指出明之人情小说的“世情书”和清之“讽刺小说”都是近现代通俗社会小说的“渊源”[5][p.3];在论述社会问题小说时,专门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问题小说进行了比较[5][p.155-164];在分析民国武侠小说兴起原因时,首先指出了它与晚清公案小说并非同一谱系,属于“新派”而不属于“旧派”,而是与“尚武”“、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外国有关思想特别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密不可分[5][p.451]。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史”的勾连,如《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在论述“黑幕小说”时,仅仅对“黑幕”与“黑幕小说”进行了概念辨析,为“黑幕小说”正名[5][p.105-112];而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进一步把它与同时期的美国“揭黑运动”进行比较分析,找到了一个同时代的参照系,使得这时期中国“黑幕小说”的面目更为清晰。又如在论述包天笑创办的《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仅仅对这两个期刊进行了较长的资料常识介绍[6][p.576-602],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则承接上一阶段报刊文言的兴盛,进一步对其白话的运用原因进行了论析———民间倡导和官方的合围,从而对报纸传媒形式变革的论述更为周全深入。如此不一的深入剖析使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显通观理性。#p#分页标题#e# 当然,为了进一步强化文学史识的整合作用,突出文学史的整体色彩和理性意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基础上还做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比如删去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一些主观情感色彩过强的小节标题———“啊!46年尘梦,秋海棠!”“、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上海小说’”等;一些过于招摇的小节题目———“从鲜血洗过的焦土中传来的鬼哭人声”、“那张抹不掉的血纸片”“、一只半夜伸出来的手”等;一些过于深奥难辨的标题———“既无‘屈子湘江’,不如‘信陵醇酒’”、“以罗两峰画鬼之笔涂抹小说”、“秋笳复作汉槎再生”等;一些冗长的标题———“孙玉声的《黑幕之黑幕》是一部佳作”、“恋爱全建筑在‘卖方自由’的金钱关系上”等,把主标题和副标题相结合的形式变成了较为简洁明了的单一标题,进一步深化了文学史“史论”的表现力度,这些都是新著的可取之处。 二治史(包括文学史)离不开史识和史料,并且二者关系非常密切“,重史识者不能没有史料,要不然只能空口说白话;重史料者也不会没有一点史识,要不怎样知道那个是应该搜集的史料”[2][p.250-251]。虽然由于阅读对象的不同,文学史可以分为研究型文学史、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型文学史,在史识深度和材料展现上各有侧重,但是治文学史者不应以所谓的“质的规定性”从史料中抽出中意的部分来分析其线索、趋势、规律,用“性质”论来遮蔽或抹刷史料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遮盖了文学史的基本面貌和丰富内容,这样的文学史只能是某种观念的产物。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此类文学史已经产生了不少,我们的文学史家秉承着各式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断地让一部分作家作品“笔下超生”,对另一部分作家作品“草菅人命”,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接触到的往往是残缺不全的隐去真实面目的文学史,因此对它的去蔽、还原是非常迫切重要的,而要摆脱某种“性质”论的束缚和制约,文学史家必须从史料出发,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发言。为复现真实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版图,《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把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部分人“诊断”为“死亡”的通俗作家作为主体来展现,在史料的挖掘、打捞和整合上具有弥补文学史“空白”的开创意义,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做得更好一些。 首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从最原始的文学史料出发,更加注重作品的体验与分析,把作品细读与文学体验紧密结合,注重文学经验的传达。在大的编写体系上,《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更加严密了,但它并没有以大而皇之的史论代替史料细节的展示与分析,非常注重感性文学史画面的呈示,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独立的理性判断。以点带面依然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梳理通俗文学的重要方法,它把对通俗文学演进发展的论述化入典型作家与作品的论述之中,诸多文学个案的分析显示了它顽强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的努力。其实《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也比较注重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但是在专章介绍作家的时候采用史料比较庞杂,无形当中遮蔽或淹没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和作家独特的文学经验,如第二编第十章分析悲剧侠情小说家王度庐时,分四节分别介绍他的人生经历、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的心灵悲剧色彩和“平民化”追求倾向,过多地方的平均使墨使得论述有泛泛之论的嫌疑;而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把有关王度庐的部分压缩为一节,简单交代他的生平资料后,重点分析了他的“鹤—铁系列”里两部作品《宝剑金钗》和《卧虎藏龙》,在对其情节、人物、主题等方面的细读比较后,得出侠情悲剧的共同点,又看到它们的重大差异:《宝剑金钗》以情节为中心,而《卧虎藏龙》以性格为中心,由主要作品的特色突显了作家的创作特征。这种抓典型作家的典型作品的描述方法与鲁迅用“药、酒、女、神”勾勒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用“庙堂与山林”勾勒唐朝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样,在分析“超越雅俗与融会中西”的张爱玲小说时,重点分析了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从小说的文化环境、情节发展、人物心理等方面入手分析了它雅俗共赏的特征,说出了它是“将古老的‘梁祝’故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形式表现出来”[1][p.554],实质上描绘了“香港的大坟山‘活埋’了一个‘拎得清’的上海少女”[2][p.552]。这种从作品细读中得出结论的方式成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表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还原、丰富了文学史的细节,使得文学史结论更加真实可信。陈晓明论述当代文学史时认为:“对文学经验本身的关注依然是基本评判标准,在这个学科已有的历史传统序列中来思考不断变更的文学经验,显然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7][p.2]其实从文学经验出发,对任何阶段的文学史都非常重要,显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好。 其次,《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还更加注重征引前人的观点资料,或对之进行批驳,或用它们证明自己的文学史观点,从而丰富、深化了对文学史的认识。“文学史研究是一种‘对话’,与凝聚为文本的作家心灵的对话,也与落实为论者的各式诠释者对话。”[2][p.42]前者的“对话”需要研究者从文学体验、作品细读出发,而后者的“对话”需要治史者充分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突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比如在论述《海上花列传》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多处征引鲁迅、胡适、刘半农、张爱玲、孙玉声等人的观点来阐释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则在这些人论述的基础上把它定位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开山之作,深化它六个“率先”的前卫性。另外,两部书在为通俗文学“正名”时,都批判了茅盾等人在特定历史时期对通俗文学的责难和不实之论,引用了朱自清的通俗文学为文学史之“正宗”的观点,在为“黑幕小说”、前期《小说月报》、《礼拜六》等“正名”时均采用了这种批驳—立论的方式,显得论据充足、真实可信。对于独创的说法,《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也比较谨慎,力求追溯它能成立的渊源,比如为了命名“都市乡土小说”,范伯群拿来了鲁迅、周作人、茅盾等人的观点,一步步引向自己的概念,从而彰显自己概念提出的“合法性”。总之,两部书不仅大量引用了与作家作品同时代人的原始资料,还大量引用了后来者的诸多资料;不仅援用了国内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对海外学者的重要论证也不放过;不仅引用自己前辈学者的科研成果,而且重视后来学人的研究资料。这种“拿来主义”式的开放眼光既展示了文学史的厚重性,又增加了它的可信度,比如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多处援引海外学者夏济安对通俗文学的赞赏言论,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论述张爱玲的小说时,用王德威与夏志清的相关论述来论证张爱玲作品与“鸳鸯蝴蝶派”和“旧小说”的亲缘关系;在论述徐讠于时,引用自己学生吴义勤的论述,这种原援引材料的实证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p#分页标题#e# 最后,相对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而言,《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增加了近三百幅的图片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来复原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原貌”。这些来之不易的图片资料更容易把读者带向早已逝去的历史场域,在相对感性的历史语境中体味通俗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历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①重要作家或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小像;②作家的原稿或手迹;③代表作品封面或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插图;④编发的报刊杂志的创刊号;⑤与通俗文学有关的社会背景资料[1][p.587-588]。这些图片的篇幅相对于整部书而言,比例还是比较小的,只是起到了一个辅助认识的作用,并不像真正的“读图时代”那样图像淹没了文字,造就和培养了“识字一代的文盲”,使人们的思考在“视觉文化”的观赏中无所适从,委顿消弭。图片在书中起到一个介绍说明的作用,辅助于文字论述,让读者深入体会通俗文学发生的所谓的场域和契机,从而对这一被长期打入“冷宫”的文学“逆流”的生存历程表示同情和理解。相对于当前高科技的数码照相技术,这些大部分产生于旧时代的图片资料是比较粗糙原始的,有些作家小像甚至已经模糊不清了,更谈不上制作的精美与华贵。但正是由于它的原始,才显得难得,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相当一部分资料早已经“灰飞烟灭”了,这种原始资料的打捞是相当艰难的,它们不像知识精英文学的资料那样长期被人们重视而保存的相当完好(关于鲁迅、丁玲、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资料在博物馆、纪念馆里相当完备),因此需要搜集者通过向图书馆、向作家的家属和后代、向收藏爱好者等多种途径坚持不懈地摸索,范伯群在该书的《觅照记(代后记)》里详细记载了自己打捞这些图片偶遇阶段—主动“搜集”阶段—攻坚阶段“三部曲”的艰难而漫长的历程。所以,文学史叙述中插入大量的图片资料不仅仅更新了文学史的表述方式,而且也是文学史家科学实证精神的重要显现形式,它既是一种新鲜的叙史尝试,又是现代通俗文学治史者艰辛付出的最好见证。 三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还仅仅是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一期工程”基础上的“二期工程”,属于范伯群及其同事所进行的“文学史拓荒性工程”的重要成果,这一工程有“一期”、“二期”,也可能有“三期”“、四期”等等,《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贾植芳评价为:“资料更充实了,论点更深化了,历史脉络梳理得更加清晰,发展周期得升降起伏得勾勒也显得全局在胸,了如指掌;还为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不可或缺得组成部分留下一份丰富的图像资料。”[1][p.2]但是,我们在惊叹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巨大进步的同时,还应看到一些地方也值得商榷。比如,它在体例结构上更加严谨理性了,但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漏掉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某些内容板块呢?它对“通俗戏剧”和“幽默滑稽”文学的论述明显减少;它在论述“黑幕小说”时与美国的“揭黑运动”进行比较固然加深了论述的深度,但这一节是不是与全书结构显得游离呢?它在论述武侠小说家宫白羽作品的“现代”色彩时,用相当长的篇幅资料来证实鲁迅兄弟对他的大力提携,这种论证是不是到位呢?另外,该书在处理作家资料与作品细读、史的脉络与作品的赏鉴、文人群落与小说类型的关系等方面都值得我们商榷。 但不管怎样,作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留给我们的开放性启示依然是非常珍贵的,比如期刊等印刷媒介的入史,电影等图像媒介的入史,文人—刊物经营者—编辑—读者等“文化生物链条”的入史,文学史发生点的确立,文学史的分期等等。另外,这两部文学史还仅仅处于将通俗文学从“逆流”的地位挽救出来为自己“平反”的研究阶段,对之进行策略性的“彰显”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它们的内容是非常庞大的(一部130多万字,另一部近80万字),为普及实用,它们还需要继续精简浓缩,还需要在与新文学的互补交流叙述中“比翼齐飞”,因为“是现代人文主义文化孕育了新文学,是世俗的市民文化滋生了通俗文学,只有两者的并存并行发展方能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审美期待和工商社会保持平衡的需要”[8][p.13-14],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后记里有着清醒的认识:“‘现代通俗文学史’只是一部断代的专业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