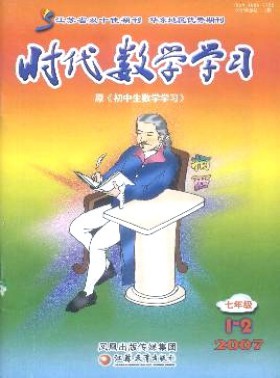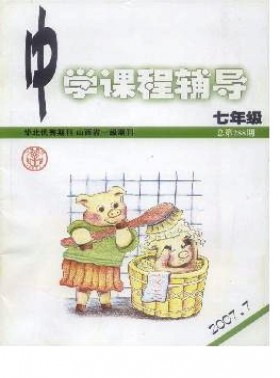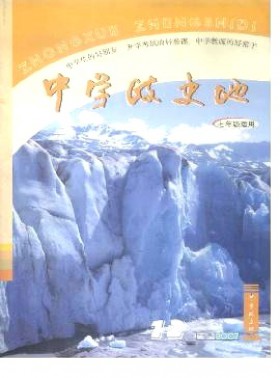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十七年文学价值评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陈建新 张玲燕 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角度看,“十七年”传统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或简称为历史文学创作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后的新时期文学,作品数量少,影响也不能和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文学创作相比。但是,在“十七年”时期还是出现了一批足可以载入史册的优秀历史文学作品,它们继承了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历史文学新范式,虽然受到激进政治的压抑,但作家的主体意识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在作品中顽强表现出来,从而使这一时期的传统历史文学叙事在与激进政治的矛盾冲突中充满了艺术的张力,并为“”后的中国历史文学创作的高潮奠定了基础。如何准确、充分地评价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学创作,这是当代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1“十七年”历史文学创作数量并不多,主要是戏剧和小说,它们在主题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符合激进政治的要求,在“古为今用”的口号下为现实政治服务,或通过对历史上有为的政治家的歌颂来礼赞新政权和革命领袖,或采取直接讲述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故事来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颂扬。前者当推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武则天》为代表,后者以姚雪垠的《李自成》影响最大。另一类则是在激进政治允许的情况下,表达知识分子的内心诉求。这一类作品也可再分成两类,第一类作品展示了作者积极入世的态度,他们笔下的历史人物,或为民请命,或与恶劣势力作顽强的斗争,戏剧《关汉卿》、《谢瑶环》和《海瑞罢官》,小说《西门豹的遭遇》、《海瑞之死》等可做代表;第二类作品则曲折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恶劣的文化环境中萌生的洁身自好的情愫,《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杜子美还家》和《白发生黑丝》当为其中的佼佼者。当然这样的分类只有相对的意义。
因为我们在后一类文学作品中,还是能够看到作家对社会的曲折批评。历史文学从本质上说,是当代人对历史的现代阐释。建国后,主流意识形态非常重视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重新阐释历史,并把这种新的阐释用文学的形式传输给人民大众,从而影响大众对历史的认知。第一,大力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并把肯定农民起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占领中国史学领域的基本要求。任何别的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理解和阐释,都坚决排除之。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统一知识分子思想。第二,大张旗鼓地开展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建国后文艺界第一次思想斗争,是1951年开展的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场运动的要害,就是要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统一思想,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取代形形色色的旧的史学观。第三,在文学创作上主张厚今薄古,提倡“大写十三年”,提倡塑造工农兵文学形象,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早在延安时期,就写信赞扬延安平剧团的《逼上梁山》让农民造反英雄和底层百姓成了文艺舞台的主人公。60年代京剧革命的主题,仍然是大力塑造工农兵底层百姓形象。60年代初,由于党的文艺政策的短暂宽松,曾引发了传统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短暂的井喷期,但随着1963年和1964年两个对文学艺术的批示,随着“阶级斗争”的锣鼓声越敲越响,随着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传统历史小说创作成了昙花一现的现象,很快陷入低谷。
应该说,“十七年”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卓有成效的,这不仅体现在这一领域中传统历史小说衰微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繁荣,而且,作家们在进行传统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时,都自觉地以新的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创作指导思想。姚雪垠在“”刚结束时说:“伟大祖国的解放诞生了新的历史时代,给我这个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改造的条件,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机会。随着我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我对接触过的历史资料获得了新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李自成》的主题思想。”“我在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中泡了半辈子,所走的道路是资产阶级的文艺道路。倘若用我原来的思想感情和遵循原来的写作道路去写农民革命战争小说,必然是南辕北辙。要用艺术笔墨拥护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揭露什么,必须先在我的思想感情中大破大立。”(1)意识形态的约束内化为作家的自觉行为,这在“十七年”文学中是一个普遍现象。
2余英时在讨论公共知识分子定义时说:“美国已故的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dter)认为现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固然与他们的专业知识或技术知识是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仅仅具有专业或技术知识却并不足以享有(上述特殊意义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1)的称号。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律师,或报刊编辑在执行他的专业任务时,他只能算是一个‘脑力工作者’。换句话说,他是以他的专业知识来换取生活的资料,而他所做的也都是他的职业本分以内的工作。如果他同时还要扮演‘知识分子’的角色,那么他便必须在职业本分以外有更上一层楼的表现。其实,相对于大多数技术知识分子来说,作家更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因为作家的写作需要他们关注整个社会,严肃的写作活动也要求作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国当代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他们更应该而且能够代表“社会的良心”。要强调的是,就“十七年”时期来说,与一般作家相比,历史文学作家的这一特性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历史文学创作对作者有特殊的要求,即作者必须具有相当高的史识。史识包括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对所描写的历史对象的理解和把握。文学创作本来是一种感性的创造,犹如严羽所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2)
但对于历史文学创作来说,书本知识的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创作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需要的是对生活的感受、体验和认知,即便是“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也如此(“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实际上并非传统意义的历史小说,因为作品所描写的这段历史,作者都是亲历的,无需传统历史小说创作所必需的广泛阅读相关历史书籍这一环节)。所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作者一般都来自革命斗争的基层,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开始创作小说时,文化水平并不高,甚至有高玉宝这样从部队扫盲班出来的作者。相反,要创作传统历史文学作品,在历史材料的搜集上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据姚雪垠自述,他为写《李自成》,从40年代就开始搜集有关材料,卡片做了好几箱。陈翔鹤也早在30年代就开始构思他的以12位古代文化名人为主人公的历史小说,搜集和阅读了相当多的相关历史材料。“十七年”历史文学作家如郭沫若、田汉、曹禺、陈翔鹤、冯至、徐懋庸、吴晗、孟超、师陀、黄秋耘、姚雪垠,都是建国前成名的作家和学者。如果说,作家因为天生的敏感和不安分,常常会对现实提出批评甚至否定的意见,那么,从事于历史文学创作的作家,因为其具有的这种更知识分子化的气质,他们的批评与否定会更激烈。因此,我们能够在对这一时期历史文学作品的考察中,感受到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和立场。#p#分页标题#e#
3从知识分子叙事的角度看,“十七年”时期历史文学的创作,继承了两种文化传统。第一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批评现实政治的传统。余英时在讨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时,曾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与西方知识分子相似的批评政治社会的传统。虽然在长期的政治权威压迫下,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精神,但他们在“道”、“势”分离时,能以“道”自任,指点江山,褒贬时势,成为与统治阶级的“势”形成抗衡的“道”的代表。(3)这种知识分子传统在五四时受到激进的反传统社会思潮的冲击而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西方式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批评。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刚刚建立不久的现代知识分子批评机制很快被消解。
但是,作为个体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在“十七年”时期完全放弃对社会的批评权利。虽然传统的道统不复存在,但中国古代文人为“道”而献身的精神却不绝如缕,前面提到的马寅初、黄万里就是例子。当然,他们依据的已经不再是古圣贤的“道”,而是科学真理。在现代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不可或缺,但也不能把他们神话化。任何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现实社会中,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美国当代作家苏珊•桑塔格说:“如果期望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以反抗非正义的行为、保护受害者、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权威的信仰为己任的话,未免太乐观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就像多数其他从事教育职业的人一样因循守旧赋予知识分子制造麻烦者、良知的代言人这样美名的人一直是少数。有些知识分子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4)如果把“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这样“少数”与“多数”两类,可能失之于简单化,起码本文所讨论的“十七年”历史文学作家就难以划入这样两类中,他们虽然还不能完全做到“旗帜鲜明,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也绝不是“在公开言论中昧着良心欺骗别人,或者对所谈论的东西一无所知却厚颜无耻地说得头头是道”那一类知识分子。
由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特殊历程,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还无法认清极左的激进政治的真实面貌及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破坏性,在这样的背景中,“十七年”历史文学作家对现实社会的批评更多的是建立在他们固有的社会良知和文化素养之上。《海瑞罢官》如此,其他历史文学作品也同样具有这样的倾向。与《海瑞罢官》的“仗义执言”、“借古讽今”相似,田汉的话剧《关汉卿》突出的是“为民请命”的主题。《关汉卿》创作于1958年,是在反右扩大化的背景下创作的,借着对关汉卿、朱帘秀等正面艺术形象的歌颂,剧作描述的主人公对暴政的反抗,与邪恶势力的殊死斗争,那让人回肠荡气的情节,充溢着作家的激愤之情。与此相似的还有《杜子美还家》。黄秋耘在“”结束后曾这样回顾自己在创作这篇小说时的心态:“解放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作家内心的东西,也不会容许你都写出来的。但我还是写了、发表了一些东西,例如《杜子美还家》”;“这些作品都代表了我的思想,表达了我的心声”;“文学创作有时是很曲折的,它并不是具体要写什么事件,而是作者心里头有了什么疙瘩总想把它说出来罢了”。“那时候我要直接写三堡村还不好写,我就只好写《杜子美还家》。实际上《杜子美还家》反映了我重访三堡村之后的思想感受。所以,你要是说《杜子美还家》有影射还可以,也不冤枉。刚才我说,文学创作这东西有时候是很曲折的。”
(5)在表达对现实社会的批评时,这一时期的多数历史文学作品都采用了塑造正面古代知识分子形象的方式。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往往正直、正义,忧国忧民,身处陋室,心怀天下。如陈翔鹤、冯至、黄秋耘笔下的陶渊明、嵇康、杜甫等。作为特定时代的历史解读,这些形象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产生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同为知识分子,同样处在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他们与笔下的人物发生了强烈的共鸣。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使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批评表现得较为委婉,以免与激进政治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4“十七年”历史文学继承的另一种传统,就是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历史文学新范式。这种新范式,一反中国古代历史文学阐释正史的“历史演义”本质,以知识分子立场观照和审视历史,从而开创了全新的历史文学传统。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由于没有世界其他许多民族那样的享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因此,历史成了我们的准宗教。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文人学士,都渴望“青史留名”,不愿做“历史罪人”,所以,在许多时候,“历史”感召力比道德律令的影响更强。这样的文化背景使中国成了历史文学创作的大国。但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主要只是作为正史的补充而存在。多数历史演义的创作者,都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正史的补充。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充分认识鲁迅首创的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范式的意义。鲁迅对待中国的历史记载,向来保持着警惕的怀疑姿态。他曾说:“‘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葫芦。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6)
又说:“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7)这种读史的态度,与美国当代史学家海登•怀特的立场非常相似,在怀特看来,“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作为叙事,历史与文学和神话一样都具有‘虚构性’,因此必须接受‘真实性’标准的检验,即赋予‘真实事件’以意义的能力。作为叙事,历史并不排除关于过去、人生和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虚假意识和信仰,这是文学通过‘想象’向意识展示的内容,因此,历史和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想象的’解决。”(8)怀特把历史记载和文学、神话在本质上看成是同样的东西,因为都是“叙事”,都具有“虚构性”,这就把历史记载从“信史”的高位上拉了下来。历史既然有这么多的可疑处,文学家创作历史文学如果食古不化,死扣住史书写作,实际上就是放弃自己的独立创造权利。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第一人,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飞跃。他的《故事新编》,不仅开创了“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9)的新的历史小说创作法,而且,这一历史文学领域里的创新,贯穿了反思历史,批判、怀疑与叛逆传统的主线,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其他文体一样,它表征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文化反省和文化批判。继鲁迅之后,郁达夫、郭沫若、郑振铎、茅盾、施蛰存、冯至、李人、李拓之、杨刚、谷斯范等都投入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从20年代的文化启蒙、30年代的阶级斗争一直到40年代的爱国主义主题,历史文学的时代母题不断变化,创作方法上也是百花齐放。历史剧的创作更是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总体上看,从历史观、题材到人物塑造,现代历史文学都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完全不同的面貌。而由于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虽然“十七年”历史文学的作品数量(主要指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文学作品,而非那一类带有通俗意味的传统历史戏曲)骤减,但鲁迅开创的现代历史文学传统,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绝迹,而是以特殊的形态保留了下来。#p#分页标题#e#
“十七年”历史文学创作大多不拘泥于历史考证,而是更注重于创作主体与所写历史人物的沟通。例如田汉在创作《关汉卿》时,因为相关史料的缺乏,他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式,把自己的心理和情感投射到主人公身上,创造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作品紧紧围绕关汉卿创作《窦娥冤》的过程,突出他对受压迫人民的同情心和反抗暴政的决心。不仅缺乏史料的创作如此,即使那些有较多史料的写作对象,作家们也决不亦步亦趋,受史料束缚。黄秋耘当年在评论《陶渊明写〈挽歌〉》时这样说:“写历史小说,其窍门倒不在于征考文献,搜集资料,言必有据;他拘泥于史实,有时反而会将古人写得更死。更重要的是,作者要能够以今人的眼光,洞察古人的心灵,要能够跟所描写的对象‘神交’,用句雅一点的话来说,也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古人的情怀,揣摩到古人的心事,从而展示出古人的风貌,让古人有血有肉地再现在读者的面前。《陶渊明写〈挽歌〉》是做到了这一点的。”(10)这不仅是黄秋耘对陈翔鹤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理解,也是作为一名历史小说家的黄秋耘的夫子自道。正是这样的创作态度,使“十七年”历史文学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文学传统联系了起来,并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文学创作与“”后历史文学创作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