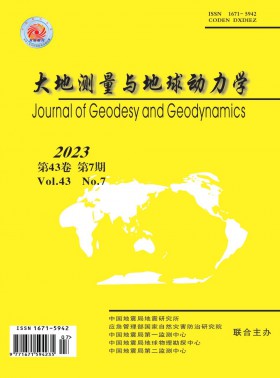【摘要】罗辛顿•米斯垂(RohintonMistry),加拿大籍印度裔作家。其作品《大地之上》出版之后,颇得广大读者的认可。本文从离散的角度来书写小说中四个主要人物身份认同的过程,旨在探讨《大地之上》中的印度裔加拿大移民作家的作品人物作为离散者的身份追寻。
【关键词】底层文学;身份追寻;离散;《大地之上》
一、前言
罗辛顿•米斯垂生于印度孟买,后迁居加拿大,1983年开始步入文坛,他的代表作《大地之上》并未局限于早期的创作风格,力求描绘波斯族群的生活,而是将重点放在了中下层的平民生活,通过主人公在绝望中生存的遭遇,表现出罗辛顿•米斯垂在对故土和民族的悲痛与厌恶中依旧不减的赤诚、善良和希望。
(一)作者与作品简介
罗辛顿•米斯垂的作品描绘了印度社会经济生活各个不同的层面,以及印度帕西人的生活、习俗和宗教,充满了对印度的怀念之情。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费罗查•拜格的故事》(TalesfromFirozshaBaag)、长篇小说《漫漫长路》(SuchALongJourney)、《大地之上》(AFineBalance)和《家事》(FamilyMatters)等。罗辛顿•米斯垂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因其深刻的内涵和细腻的笔触使人印象深刻。早期,由于特殊的童年经历和移民身份,他的创作主题关注移民和种族,描绘印度波斯裔人民的喜怒哀乐和作为边缘人的迷失。后来,他将笔触转到印度中下层人民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命运的跌宕起伏。
(二)《大地之上》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罗辛顿•米斯垂作品的分析主要涉及在作家的离散身份、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历史与文本的关系上。国内学者因研究起步略晚,大多集中在对作品的翻译研究、作者的创作风格以及叙事角度,然而对于作品人物身份的分析有待继续深入。因此,本文从离散文学的角度对小说主要人物的身份追寻进行研究和探讨。作为较早研究此作家的学者,任一鸣在《书写后殖民地时代的印度人——印度题材英语小说家罗辛顿•米斯垂》对罗辛顿•米斯垂的创作风格和个人经历做了一定的总结。此后,齐园发表的《边缘人生与失衡的印度——解读罗辛顿•米斯垂〈完美的平衡〉》从历史入手,阐释了印度的失衡社会现状。此外,张呈敏以底层叙事为切入点,对《大地之上》进行解读,深刻展现了小说中四位主要人物面对人生沉浮的乐观与斗争精神。
(三)离散文学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者对于离散理论的研究有限。1986年,加布里埃尔•谢费尔(GabrielSheffer)发表的《国际政治中的现代流散》(ModernDiasporasinInternationalPolitics),是离散研究的奠基之作。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离散现象剧增,离散研究迅猛发展,以《流散》(Diaspora)和《变迁》(Transitions)两本权威期刊的兴盛作为标志。2008年,罗宾•科恩在专著《全球流散:介绍(第2版)》(GlobalDiasporas:AnIntroduction)中概括了离散文学的如下特点:“从母国离开,奔赴离散到多个地区;出于工作规划或者殖民野心;对母国情感深植;将想象的家园理想化;渴望回归家园或与其保持一种联系;长期保持一种强烈的族裔群体意识;难以融入移民国;渴望在移民国或地区找寻自己真正的人格,从而实现生命的意义。”
二、《大地之上》的文学离散性
流散写作中人物的位移大多表现为创伤性的、不易走的旅程。主要的主题是迁徙者的苦难和痛苦。对于印度裔离散作家来说,虽然他们移居别国,但是浓浓的母国依恋仍旧根植于他们心中。从这点来看,罗辛顿•米斯垂符合流散作家的身份。从他的创作经历来看,他虽然身居加拿大,但多数作品取材于他的母国印度。《大地之上》中人物在社会制度下颠沛流离,漂泊无定,他们渴望回到故土,但回首过往,家园面目全非,尽管在物理意义上他们没有远离母国,但心灵上没有归属和寄托。这在某种程度中体现了离散文学的主题特征。
三、绝望中的失衡——身份的迷惘
小说中描写了四个主要人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身份的迷惘和探寻。
(一)男性与女性的失衡
对女性身份的描写越来越成为文学作品中的焦点。古今中外,女性形象不仅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更是女性身份变化的重要体现。不同于其他国家,印度女性深受国家、社会和家庭的重压,她们尤其渴望平等和自由的人格。但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下,女性被压迫的现状使她们的斗争举步维艰。在《大地之上》中,作家塑造的女性人物迪娜经历的种种遭遇体现了印度社会的男女失衡现状。出生于中产阶级,迪娜•达拉尔虽然不像传统印度女性地位低下,但是或多或少受到男女不平等的印度社会的影响。幼年时,她就受到大祭祀弗兰吉的性骚扰。迪娜的父亲去世后,家中失去了往日的安定和秩序,母亲精神失常,无力照顾迪娜和儿子努斯万。努斯万成了一家之主。作为哥哥,他命令迪娜做家务活,不让迪娜蓄长发,甚至连她去朋友家都要求向自己报备。迪娜长大后,哥哥不顾她的意愿找来他的朋友同她相亲。在他心里,女性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结婚对象。在迪娜找到自己的心上人时,他还多加阻拦,甚至扬言切断迪娜的经济来源。丈夫鲁斯图姆去世后,迪娜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以做裁缝为生,但这期间哥哥从未给予她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诚然,一位尚未经世事的女性,要想在不稳定的社会中谋生,实属不易。在生活和命运的苛待下,女性无路可走。
(二)个人和社会的失衡
通过裁缝伯侄的经历可以看出印度这片土地上极致的光怪陆离和极致的悲惨,生命不被尊重,人格被践踏。无边的苦难和黑暗让人们看不到救赎的曙光。个人在种种社会制度的冲击下如同蝼蚁,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伯侄二人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什是印度低种姓的代表,他们的姓氏是“莫基”,本意是“皮匠”,属于贱民族群之一。大伯伊什瓦和他的弟弟纳拉扬兄弟二人在八岁时,因为偷偷跑去村子周围的学校教室被老师痛骂和殴打,父亲向村子里德高望重的潘迪特老爷求助却遭到了嘲讽和侮辱。经历灭门惨案,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什身单力薄,唯有接住命运的一切施舍。伊什瓦的人生愿望不过是回乡为小翁讨一个媳妇儿,这是他唯一的执念,唯一试图向命运讨要的“馈赠”。然而这最朴素不过的心愿却成为伯侄唯一在世的亲人——阿什拉夫叔公的催命符,于是故乡变成恐怖异乡,在那里,裁缝伯侄被政府强掳做了绝育手术,大伯因术后感染失去双腿,侄子被家族宿敌达拉姆西塔库尔利用身份和职务之便恶意打击报复——被实施了阉割术。伯侄二人从故土死里逃生,再次来到无处安身的城市,无奈沦为乞丐。
(三)城镇与乡村的失衡
书中之印度肮脏而混乱,自由而狂野,溽热而拥挤,贫穷而人多。紧急法就像一块恶臭的疮口,紧紧黏在印度社会的大地上,也黏在每个人民身上,无所挣脱。而这也加剧了城镇与乡村的冲突。马内克幼时住在大山里,父母以经营一家小卖部为生,其中,店里热销的汽水由于新型汽水的出现而受到冲击,销量一再下滑。乡村生活看不到未来,父母决定把马内克送到城里完成学业,但马内克留恋儿时的美好回忆,舍不得将他抚养成人的父母,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安排,但无济于事,这加大了他与父母之间的矛盾。此外,房屋的拆迁破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昔日的鸟鸣流水声被机器的轰鸣声取代。而乡镇中的传统裁缝铺由于高级服装店的入侵,也渐渐失去了生路,客户大批量流失,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裁缝伯侄只好决定前往城里,以谋生计,脱离衣不蔽体的日子。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日常生活还是生态环境,城镇的发展都对乡村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和冲击。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因为现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而改变,从而牺牲环境和人民的生活习惯。
四、希望中的平衡——身份的追寻
那么,面对失衡的世界,小说人物开始追寻自己的身份,试图在迷惘中找到希望,保持平衡。
(一)迪娜对于女性独立人格身份的追寻
迪娜•达拉尔从小失去了双亲,面对哥哥的欺凌和压迫,迪娜顽强抗议,并坚持她的个性。她深爱着鲁斯塔姆•达尔并与之结婚。丈夫去世后,迪娜拒绝屈服于压力,决心重建自己的生活,在经济上不再依赖男人。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她希望在丈夫早逝后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生活,管理一家小裁缝生意,并维护自己的公寓。她雇佣了伊什瓦和翁普拉卡什,每日起早贪黑,完成公司交代的任务。由此刻画出一个远远领先于时代的女性角色,完全独立,思想自由,尽管纯粹的不幸剥夺了她年幼时的梦想,但她从未放弃谋生的希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迪娜是“新女性”的象征,并非默许和顺从,而是作为立体典型的女性角色。即使在丈夫去世的那个残酷的夜晚,她也表现得很有尊严,“不要哭泣,不要殴打,不要捶胸顿足,不要撕扯头发,就像你对一个遭受如此打击和如此损失的女人的期望一样。”在丈夫早逝后,迪娜试图在生活中重新站稳脚跟,但事实上,通往独立和自力更生的道路崎岖不平,充满障碍。然而即使面对再大的困难,她也不愿意寻求哥哥的帮助。拒绝被兄长再次掌控人生的迪娜,发誓自食其力。她用尽所有力量,与生活、与“男尊女卑”、与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相抗争,她出租房屋、聘用裁缝伯侄为成衣厂制衣,她秉持着独立生活的坚定信念,以单薄一身,奋力抵御外界一切会导致生活失衡的因素——可恶的房东、残酷的打手和豺狼般的兄长。迪娜面对这些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想要颠覆她小世界的可怕因素们,只是淡淡地说:“我的生活也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得尽力把生活过好啊。”这体现她追求独立身份的人格魅力。
(二)裁缝伯侄对于平等人格身份的追寻
虽然命运不公,全是坎坷,虽然流离失所,数次几近殒命,虽然在命运的漩涡里踟蹰前行,但翁普拉卡什仍能说出这样的话——“假如时间是一匹布,我就把所有不好的部分都裁掉。裁掉吓人的黑夜,然后把幸福的部分缝起来,这样日子就更好挨一些。然后我就把它像大衣一样穿在身上,永远开开心心的。”伊什瓦和小翁这对伯侄,勤劳又善良,尤其是大伯伊什瓦,生活的苦难他照单全收,已然习惯逆来顺受,友善地对待所有人,即便是最肮脏最卑微的乞丐,也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就像伊什瓦说的:“现在我更愿意相信上帝在做一床巨大的拼花被,有无穷无尽的布料和样式。被子做得太大、太复杂,样式已经无法辨认,正方形、菱形、三角形无法再拼接在一起,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于是他就放弃了这床被子。”小说结尾,二人沦为身体残缺的乞丐。即便这样,他们仍选择笑着继续活下去。正如大伯伊什瓦所说:“如果你的脸上满是笑容,就腾不出地方流泪了。”作为低种姓人民,他们却没有心高气傲,对村民的态度始终如一,伊什瓦认为,如果功成名就就看不起自己的街坊邻居,那和高种姓有何区别。在裁缝伯侄回到村庄准备给小翁准备婚礼时,小翁见到灭门的仇人并不惧怕。面对紧急状态下种种荒谬而又残酷的危机,裁缝伯侄有时会灰心丧气,但始终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表明他们追求平等、坚韧乐观的身份认知。他们始终相信,没有人是贱民,因为大家都是同一个神的儿女。他们时刻记住甘地的话,贱民的概念毒害着印度人民,就像一滴砒霜毒污了牛奶。
(三)马内克对于自由人格身份的追寻
马内克代表了一个正在探索自我的年轻英雄,出生在幽静美丽的山里,从小帮父亲经营商店,马内克不愿意离开家乡,但是父母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送他去了城里求学。在学校面对朋友卷进政治危机、自己饱受校园施暴者欺凌,马内克去迪娜家中借住,成了她的房客,在与裁缝伯侄的相处中,他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与快乐,他想要继续求学,做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在给父母的信中,他提到要上高中、考大学,完成学业。这表明了马内克对自由人格的追寻。但是当他从孟买归来,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他无力改变这个失衡的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强烈冲突使得他既想保持善良清澈的内心,又想与丑陋黑暗的社会作斗争。“既然如此,回忆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到头来皆是绝望。看看妈妈爸爸和杂货铺,看看迪娜阿姨的生活,看看宿舍和阿维纳什,现在又轮到了可怜的伊什瓦和小翁。不管如何追忆开心的过往,如何渴望、怀念,都无法改变眼前的苦难与折磨——爱、关切、照料、分享,皆是虚无,虚无。”这段独白显示出马内克悲观底色的内心,也许正是这深深的悲悯心才孕育了他内心里所有的柔软和美好。这段独白也暗示了马内克的结局:自绝于人世,彻底摆脱一切痛苦。切身遭遇着所有不幸磨难的裁缝伯侄和迪娜还在坚强地活着,仅仅是目睹和听闻这些人世间惨烈苦痛的马内克,他心中的光却熄灭了,平衡被绝望打破。而他的死亡让失衡的心重新得到了平衡。
五、结语
作为印度母国人,罗辛顿•米斯垂在完成《大地之上》时,是苍凉悲怆的。面对紧急状态下的母国,他失去了对母国的意识,在寻根的途中迷失了自我,这也是马内克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国就像一座巨大的牢笼,作为离根者,他心怀母国却无力改变现状,由此断裂了与母国之间的联系,成为一名寻根者,离散在外,漂泊无定。小说中人物在社会制度下颠沛流离,漂泊无定,他们渴望回到故土,但回首过往,家园面目全非,尽管在物理意义上他们没有远离母国,但心灵上没有归属和寄托。作为离根者,他们苦苦挣扎,试图在追寻身份中从失衡的状态脱离出来,从而达到某种平衡,但他们也依然时常会为曾经拥有却业已失去的对美好家园的怀恋所困扰。迪娜虽然实现了经济独立,但几次被房东驱逐后,她怀念幼时父母健在、成年婚后和丈夫的美好生活;裁缝伯侄虽然找到了精神上的某种平衡,然而由于不稳定的社会制度,他们颠沛流离,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因而时常怀念家乡的生活;马内克在小说最后选择轻生,是因为他认识到无力改变失衡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说,他的死亡让失衡的心重新得到了平衡。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离散文学的主题特征。正如罗辛顿•米斯垂在小说里提道,“总是有希望的——足以平衡我们的《微妙的平衡》(《大地之上》)绝望的希望。否则我们就彻底迷失了。”
作者:常玉丹 单位: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