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新南非英语文学的前景,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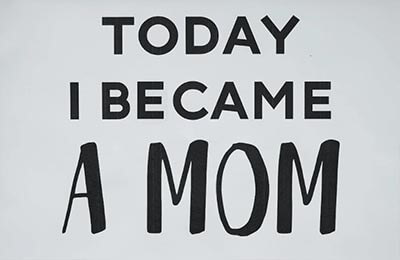
作者:张毅 单位: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
1994年,南非历史上举行了第一次多种族的民主选举,非国大获得空前胜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被选为第一位黑人总统。随着新政府的上台,臭名昭彰的种族隔离制度即被宣布废止。从此,南非各民族人民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自南非历史上举行第一次多种族的民主选举以来,经过近20年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南非,其真实地社会生活并不像南非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时,呈现在世人面前那样的炫目辉煌。种族隔离制度的余孽仍在作祟,人格的扭曲、人心的不安还弥散在躁动的城市乡村。而掀开华丽的外表,探查深层的社会矛盾,揭示人性美丑的正是南非富有反抗传统的英语文学。
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一直处于种族矛盾十分尖锐的争斗中。许多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白人在施加给别人痛苦的时候,自身也成为受害者。南非只有实行社会和解,民族平等,人民才会真正地安居乐业。面对当时的反动政权,英语作家“只能是革命的姿态”[1]。他们对非洲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不遗余力,或几番入狱仍矢志不渝,或被迫流放也初衷不改,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均以斗士的姿态活跃于文坛、政坛。在南非走向民主之后,“作家就处于创作上的两难境地:如果你不提及种族隔离,人们会说你忘记了历史;然而如果你涉及种族隔离太深,人们又会说你沉湎过去,看不到未来,过分消极”[2]。然而,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使他们不走“迎合”之路。他们以健笔为投枪,直指南非政权体制的种种弊端;以遒文为照镜,揭开了现实社会一幕幕龌龊的场景,也成就了新南非英语文学斐声世界文坛的一朵朵“恶之花”。
一、以种族隔离为主题
后种族隔离时期的英语文学,并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止而立即焕发出勃勃生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长达近半个世纪,它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种族裂痕、心理创伤在新南非仍如顽疾,令人挥之不去。历史的沉闷之音仍敲击着这块土地上不同肤色的人们。再次把人们带回历史的是马克•贝尔(MarkBehr,1963—)的《苹果的滋味》(TheSmellofAp-ples,1995)。小说以一个白人小孩马纳斯(Manus)的视角,透视出白人家庭幸福美满表象下的腐朽。马纳斯的父亲在家是个慈父,在外却是督察各地镇压暴乱的将军。让马纳斯更想不到的是父亲经常玩弄自己的伙伴,而母亲竟与智利将军有染。马纳斯的婶婶和姐姐都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准备远走他乡。黑人女佣的儿子被白人烧成重伤,几近残废。表面的幸福家庭里其实矛盾重重,十岁的马纳斯只得默默忍受,但他幼小的心灵已遭侵染。小说以苹果为书名形象地比喻了马纳斯的家庭和南非社会:苹果所散发的芳香,是已腐臭的征兆。
种族隔离制度对人心理的重创不但涉及黑人,而且也包含了白人。这种心理的伤痕一直延伸到后种族隔离时期。诺贝尔奖得主库切(J.M.Coetzee)不仅“描绘出了一个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绝望的国度”,而且还在《耻》(Disgrace,1999)中把那种创伤、无奈和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白人势力余威犹存,黑人崛起已不可阻挡。大学副教授卢里(Lurie)看不清现实,进退失据,结果弄得伤痕累累。他的女儿露茜(Lucy)惨遭三个黑人的强暴,虽极力想与现实妥协,但“像狗一样活着”的态度也道出了白人的无助与创痛。而那三个施暴者,其迸发的仇恨和快意正是历史积淀最深的种族鸿沟。这种由历史带来的“耻”刺痛着每一个人,这又需要多久的时日才能抚平!正因为有那么多的隔阂与伤痛,南非新政府推动了对隔离时期真相的调查,以期通过对受害者的赔偿来达到种族间的大和解。“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的一场场听证,两万一千名证人的陈述,再次把人们的焦点拉回到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围绕着真相与和解,南非英语作家的创作激情再次被点燃。
安特睫•克罗格(AntjieKrog,1952—)以记者的身份参与了听证会。她将典型案例和证词穿插起来,写出了她的第一部纪实小说《颅骨国家》(CountryofMySkull,1998)。许多鲜为人知的过去得以昭示,但施暴者与受害者迥异的证词正说明了南非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也预示着民族和解不可能一蹴而就。图图大主教曾对该书有高度的评价,称“南非以特有的方式来处理种族隔离制废除后的问题。对于那些深表关心的人,《颅骨国家》是一本必读书籍”。阿马特•丹戈尔AchmatDangor(1948—)则以一个黑人家庭的遭遇再现了种族主义的余孽。他的《苦果》(BitterFruit,2001)揭开了一桩在南非司空见惯的案子。二十年前,黑人民运领袖西拉斯(Silas)遭盘问毒打时,妻子被白人警察强奸。种族隔离制废除后,西拉斯与那警察不期而遇。是否出庭指证使西拉斯的家庭陷入空前的危机。最终,西拉斯的妻子离家出走,“儿子”在得知自己的真正父亲是个白人后,枪杀了警察,逃亡印度。作者由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深刻揭露了种族矛盾水火难容,新政府所要寻求的和解是多么难以达成。
对历史真相的调查以及对和解的追寻在南非的戏剧中也得以表现。民运斗士杜马•库马罗(DumaKumalo,1958—2006)的《我要讲的故事》(TheSto-ryIAmabouttoTell,1997)就以听证会上的三个幸存者为主角,让他们在舞台上现身说法,将自己家庭的不幸公诸于世人。表演结束后,三位幸存者还接受观众的提问。现场互动所激发出的深究与辩论让真相越辩越明。该剧先后在南非、欧美上演,历时五年,观众无数,深得评论界好评。而另一剧作简•泰勒(JaneTaylor,1956—)的《乌布与真相委员会》(UbuandtheTruthCommission,1997)则充满了试验性和象征性。首先,该剧的主角是个十足的坏蛋———在种族隔离时期专门镇压黑人运动的秘密警察乌布。政权转移后,乌布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不该向“真相委员会”坦白,生怕自己的罪恶得不到赦免。乌布在犹疑中展开了与妻子的对话。舞台的另一端适时地出现了三只木偶,象征不同的政治势力。碎纸机和复印机也被搬上舞台,代表对罪证的销毁和保存。结合着对话的情节,舞台的背景上也投影出相应的图片、文字、动画和录像。整个表演给人以穿越时空,充满意象之感。观众看到的恶人乌布不过是历史的产物,政治的祭品。施害者最终也是受害者。#p#分页标题#e#
二、以现实矛盾为题材
虽然新南非保证了国民的政治权利与民主程序,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失业率攀升,犯罪率增高,种族间的对立,政党间的恶斗,艾滋病的泛滥,贪污腐化的蔓延,城乡差别的扩大等正侵害着这个新兴国家的健康。这些繁杂的社会矛盾给南非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纳丁•戈迪默(NadineGordimer,1923—)在《无人陪伴我》(NonetoAccompanyMe,1994)中就展现了昔日革命者在取得胜利后内心的挣扎和孤寂。他们既走不出过去的阴影,又不被年轻的一代所理解,只能各自桎梏在自己的窠臼中,孑然老去。她的另一部小说《护家之枪》(TheHouseGun,1998)揭示了新政权的建立并没有根本消除社会矛盾,人的命运仍受到各种外部力量的操控。主人公顿坎(Duncan)本是个个性平和,甚至有点怯懦的白人青年,但社会的各种压力将他扭曲成同性恋。在遭受一连串的背叛之后,他举枪杀死了情敌。戈迪默再次警示人们,南非民主化的到来并非意味着一劳永逸。这些丑陋的社会现象不被消除,南非人民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阔别30年后回到南非的扎克斯•穆达(ZakesMda,1948—),在他的小说《死法》(WaysofDying,1995)中,把南非过渡时期的暴力泛滥写得更是入木三分。在这一转型期,暴力和死亡在城中随处可见。主人公托罗克(Toloki)的职业是专门代表死者亲属去为死者送葬。为了显示专业性和提高自己行业的价值,他居然根据不同的服务要求来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结果生意兴隆。对于暴力和死亡,辛迪微•马冈娜(SindiweMagona,1943—)更写得如泣如诉。她的《一位母亲向另一位母亲的诉说》(MothertoMother,1998)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美国白人姑娘阿眯•比鄂尔(AmyBiehl)到开普敦后积极参加反种族隔离运动,可在开车送朋友回家的途中,遭遇黑人少年的围攻,结果被乱石砸死。一黑人少年的母亲在知道自己儿子误害好人后,主动写信给受害者的母亲。小说从施暴者母亲的角度,诉说了自己的孩子之所以走向暴力的原因,进而归纳出:在邪恶的制度下,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小说语气恳切,指证有力,娓娓诉说中夹杂着对强权的愤恨,对孩子的爱怜,对和解的期盼。一些青年作家也凭借着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在英语文坛上崭露头角。达蒙•格嘎特DamonGal-gut(1963—)在《良医》(TheGoodDoctor,2003)中描述了种族隔离制废除后,南非乡村的面貌。青年医生劳伦斯(Laurence)满腔热血,要到最偏远的地方去治病救人。在破旧的医院里,他的理想与现实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农村,政局虽有改变,但暴力、腐败、人们的麻木还在延续。劳伦斯的一己之力并不能带来多少变化,因为整个南非社会还在患病。
尼格•穆隆戈(NiqMhlongo,1973—)以1994年南非的过渡时期为背景,在《狗咬狗》(DogEatDog,2004)中,通过一个贫穷大学生的撒谎和堕落来揭露南非社会的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人心涣散、百业凋敝。他的另一部小说《泪流之后》(AfterTears,2007)以一个辍学大学生到社会谋生以及回学校争取文凭的经历,再次将矛头指向南非社会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以及社会急速发展所带来的人心不稳。“泪流之后”本应是苦尽甘来,但事实是,南非的乱象还在继续,升斗小民仍看不到光明。法斯文•穆培(PhaswaneMpe,1970—2004)和克•笃依科(KSelloDuiker,1974—2005)都把笔触放到南非的现实社会,描写了道德的缺失,生活的混乱和艾滋病的泛滥。穆培的《欢迎来到希尔布劳山》(WelcometoOurHillbrow,1997)讲述一个大学讲师因爱情的多次背叛而自杀的故事。其中穿插了贫民生活、种族矛盾,巫术、艾滋病等,而死亡的阴影贯穿全书。笃依科的《十三分》(ThirteenCents,2000)以十三岁黑人男孩为主角,描写他为了生存,不得不当同性恋的男妓,后来又遭黑社会胁迫,在开普敦城里贩运。另一部小说《梦中的无声暴力》(TheQuietViolenceofDreams,2001)更以性取向为主题,探讨精神创伤、性暴力等对黑人青年的影响。穆培和笃依科的作品均揭示了南非现实社会不为人知或知而避谈的阴暗面。
三、以娱乐大众为目的
在后种族隔离时期,也有一些英语作家不再单纯地把自己的创作纠缠到政治、社会矛盾的旋涡中,而是把注意力放在文学的娱乐性上。于是,言情、魔幻、侦探、生态等文学形式逐渐流行,在南非和世界赢得更大的市场。林德瑟•阿木斯特郎(LindsayArmstrong)可谓南非最多产的作家。她从1981年开始创作,至今已出版作品八十余部,其中言情小说就多达六十五部。她的小说主要以爱情为主题,跨越时空与种族。另一位多产作家妮可拉•斯蓉(NicolaThorne)的题材涉及言情、惊悚、历史人物等,作品多达六十余部。这两位女性虽早已移居海外,工作和生活很少受南非政局的影响,但由于她们出生于南非,其作品的通俗性和娱乐性更适合南非大众的文化层次和口味,因而,她们在南非拥有较高的知名度,也是主要的畅销书作家。
迪瓮•麦尔(DeonMeyer,1958—)是当今侦探小说中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虽然他坚持用布尔语(Africaans)创作,但他的作品由于及时被翻译成英语而风靡全球。自1994年第一部小说出版到现在,他的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电视剧而广受欢迎。新近出版的《13小时》(ThirteenHours,2010)已被翻译成20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发行量超过百万,不久将被搬上银幕。一些新秀,如,理查得•昆梓曼(RichardKunzmann)、玛萁•欧福德(MargieOr-ford)和杰西•麦肯姿(JassyMackenzie)也因其作品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而早早成为欧、美等国畅销书作家。他们因走流行路线有时也受到评论界的批评,但他们的作品在悬念、惊悚中同样折射出对南非社会现实的严肃思考。在青年作家中,能够推出悬念,激发想象,创造出似真似幻景象者当数德夫•福利尔(DaveFreer)与格勒格•赫莫顿(GregHermerton)。福利尔自1999年推出首部科幻小说《孤立无援》(TheFor-lorn)后,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他的小说通过异形怪物与人的对抗揭示了人性的善与恶。赫莫顿的“生命之歌系列”(LifesongSeries),想象神奇,情节曲折,深受年轻读者的欢迎。而现今最知名的则是借助映像传播的内尔•布隆坎(NeilBlomkamp)。他身兼《第九区》(Distrct9)的编剧和导演。该片于2009年在北美首映后即成为票房冠军,被认为是突破了人们传统上对外星人的想象,也间接批判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海伦•布琳(HelenBrain)和保罗•杰拉提(PaulGeraghty)以南非的大自然为背景,以南非的人与动物为题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他们的作品清新脱俗,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人文的关怀,无论是在南非,还是其他英语国家,深受儿童和青年读者的欢迎。#p#分页标题#e#
四、结论
“一个世纪以来,种族和族群问题始终主导着南非的政治话语,这让多数南非人认为,政治是独立于社会结构之外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实施使多数人认为,决定政治的是种族意识和其他意识形态。”[3]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抵抗文学”成为促使南非“政治”改变的重要推力。而种族隔离制的废除给南非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和新的题材,作家们不需要再流落他乡,隔海命笔。面对新南非,他们敏锐洞察出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现实矛盾的层出不穷,升斗小民的脆弱无助,胜利表象下的迷茫失落。当人们以为太平盛世到来时,他们仍秉承传统,以社会的良知自省,书写出一部部警世之作。
新南非政局的开放既使文学创作空间得以拓展,也让一些文学新秀脱颖而出。随着种族对立的日益缓和,一些鲜为人知或原被忽视的社会矛盾逐渐显现,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一些新秀,更具开阔的跨文化视野,他们植根本土,放眼国际,以更灵活的手法把自己的作品推向世界。尽管针对种族隔离时期的作品仍占有相当的数量,但反映当代社会,反思传统与现代,跨越过去和现在的创作已越来越多,文学的娱乐功能也得到更多的体现。可预计,未来的南非英语文坛必将是个“彩虹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