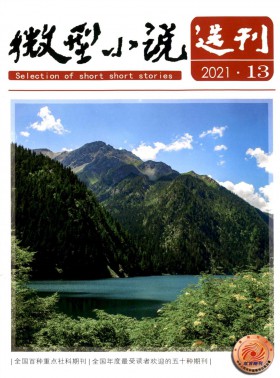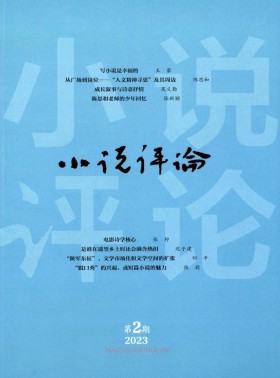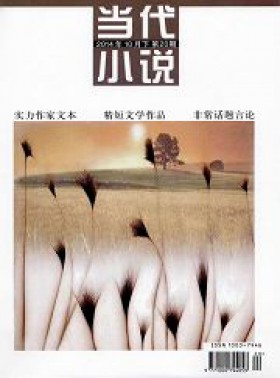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巴思的元小说创作,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约翰•巴思在对文学新手法的探索中,创造出幻想与现实界限模糊的作品。巴思认为“,正如观点是个人的,还可能是随心所欲的,所以艺术就不能希望而且也不应该试图反映客观现实的存在。艺术表现为技巧,而且肯定技巧”[1]。巴思的小说经常“把自我意识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人造品的自身的位置上对小说作业本身加以评判,不仅审视记叙体小说的基本结构,甚至探索存在于小说外部的虚构世界的条件”[2]是“一个有关讲故事的寓言”即“元小说”[3]。 巴思在小说《路的尽头》中就在叙事过程中即谈论小说文本自身,又对别的小说文本进行评论,这种形式本身就超越了叙事边界。巴思通过自己小说中医生的角度指出各种文本的虚构性,并就主次角色问题谈到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 世上角色其实没有什么主要和次要之分。因此,所有的小说、传记以及多数史料都是骗人的。应该说,公每个人自己都是他人生历程中的主人。如果从波隆涅斯来看,《哈姆雷物》也可以被称做《丹麦宫廷大臣波隆涅斯的悲剧》。 医生认为,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看做主角,就像在某个人的婚礼上,每个人都可以视自己为主角,认为这是自己生活中一个小插曲,自己只是降贵纡尊来看热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又不是谎言,而是人们对人生的曲解的描写。巴思在这里把现实世界也当作一个大文本,他认为现实世界和文学世界的真实在于它们都是虚假构筑的。医生接着指出“:是啊,我们不仅是自己生活里的人,而且还是编造故事的人,我们还让别人演次要角色。”巴思实际又借医生之口指出,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文学世界,都是人工制品。同时,巴思通过对元语言运用,对元语言系统与小说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不断将文学语言和传统的惯用手法使用到作品中,使作品清楚地、明确地显示人工制品的特征,提示了当代社会中的危机感、异化感以及压迫感与不再适应表现现代经验的传统文学形式(如现实主义)之间的脱节。从而,元小说把陈旧的惯用手段的消极价值转化为潜在的建设性社会批评的基础。 元小说对小说形式本身的审视重视。元小说还要建立在一个持续根本的对立原则上:在对小说进行幻想构筑的同时又要揭露这种幻象,使读者明白元小说只是作家的编撰,而远不是现实生活的摹本。所以,用作通俗的语言定义园小说就是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又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元小说打破了“创作”与“批评”的明显界限,紧密的将这两种过程在形式上结合,合并为“阐释”和“分解”的概念。 巴思小说中的叙述者有时就中断叙事,和读者讨论一下他目前写作中的某个论点,或某件事,从而对小说创作本身进行评述。 此时此刻(1955年10月4日,星期二,晚间7点55),我正在楼上寓所写这本书,在我看来,你若把以上结论看成是个隐喻,那么我的生平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准确地说,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并列句后面那个独立分句中的那个双谓语独立语句。你看,我可真算个语法教师了。 其中时间、地点的精确性是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嘲讽。在用直接引语表现了摩根理性主义哲学的长篇高谈阔论之后,叙事者因文本显得过于思辨性而又跳出叙事,对读者解释说: 其实大可不必一口气发表这么一大篇前后连贯的演说,但整个晚上,这的确是他讲的主要内容。为了方便起见,我以后一种连珠炮的形式将它记录于此,即说明了乔整日里在想些什么,又为我心目中的这个男子形象添上几笑色调。尽管有时他的某些观点我也能说上一通,但我始终一言不发,不过当时,驳斥他的念头不断在我内心深处撞击。常有这种情况,每当别人亮出一个极为高明而又不是无懈可击的观点时,我即不愿对他大加赞赏,又提不出独到的见解。每逢这时,我多半选定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启发式”的方法,即仅仅说“哦”或者“呵”,然后让他信马由缰地讲下去。 这是一种分解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帮助小说家与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叙述的结构,而且也为理解当代世界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极其明确的模式,因为在元小说作家看来,当代世界是一种构成品,一种技巧组合,一张相互依存的符号系统网。巴思的元小说创作邀请读者积极地参与作品意义的构筑。他并未抛弃“现实世界”,只是为了寻找一种对于当代读者来说是紧密相连的和可以理解的小说形式,并通过自身的反省来重新检视传统小说的惯用手法。元小说向我们展示文学作品是如何构筑想象的世界的,以此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每天生活其中的现实是同样“构筑”同样“写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