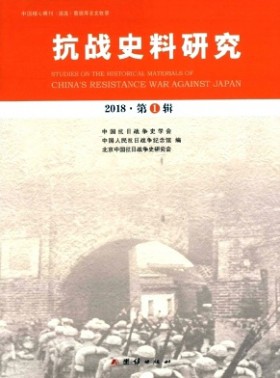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论抗战时代昆明的城市形象与文化内涵,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近代云南文化名人楚图南对云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深刻、精辟的阐述。1938年,楚图南撰文评述:云南文化“大约在汉唐以前,还是土著文化时代”,日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汉唐以后,随着滇缅交通的开辟,佛教等各种宗教传入云南,与云南土著文化相交织;“云南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是真正的华化”;到了清朝,云南文化未发生明显的变迁;“革命以后,海禁大开,云南也有滇越铁路,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侵入到云南来了。但文化的实质,仍是和以前的一样,半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国的传统的一切,仍然有着绝对的支配的力量”,“云南的社会和文化虽然从明时以来,已经华族化,但却没有现代化”;抗日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楚图南清晰地勾勒了云南文化的演进脉络,描述了云南边地文化的特殊内质,又强调抗战的发生提升了云南的文化地位。
对于云南颇为隔膜的人往往将西南边地视为蛮夷之邦,例如,从昆明走出的现代作家陆晶清在北京读书期间,“许多外省的同学,博学的教授”常常以猎奇的心态对她发问,使她“深恨不幸生长在云南”。楚图南对云南的地缘意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评估,他看到了云南的边缘优势:“云南因为地位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很可能利用了地理的特殊性,在人所不注意的环境里面,从容准备,一旦国势颠危,中原多难,振臂一呼,异军突起,也就重新奠定了危局,使当前的国运,又转危为安。”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问:“在文化上一向被视为比较落后的云南有谁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占领(据)的重要地位呢?有谁知道它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最伟大最光荣的贡献呢?”。据楚图南的理解,地理位置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云南的封闭性,却在另一方面孕育了云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优势。与此契合的是,1938年茅盾在昆明讲演时,高调宣称“云南有深山大泽,有生龙活虎”,茅盾的这个判断或许并非礼节意义上的溢美之词。
作为云南省会,昆明获得了明显的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民国文人当中,以为边疆城市昆明萧条、落后者为数甚多,然而,也有一些见闻稍广的文人确信“在所有的都市中,恐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昆明这样市内多山的都市,这真是山国的产物……在都市内住着,有山有水”,因而赞誉昆明是“山国中的天国”、“城市山林”。也有文人欣赏边城昆明的绮丽多姿:“昆明,这天然的一个华美的都市,就像是象征着南国的温馨。”还有文人澄清事实,化解外人对边城昆明的误会和偏见:“昆明在以前是被人看作边远蛮荒,瘴气苦人的所在,又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国人很少有机会去观光……要知道昆明的好处,不仅是四季长春,气候温和,而且到处都是山光水色。”于此可见,昆明的边城文化特质在民国文人那里已经得以确认。
抗战之后的昆明更显光彩夺目,那时的文人自豪地宣称“昆明,这是一个战后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它就像“一个民国以后的乡下姑娘,带着一切旧传统的性格走进了一个最现代的城市”,“于是乎就被雅称为‘文化城’,成为莘莘学子们所向往的城市”。抗战对于昆明文化地位的影响力被某些文人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断言“抗战没有发动前,昆明是被称为文化的荒漠”,正是抗战使得“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由此“把这块文化荒漠改变过来”。抗战结束之后,又有文人惋叹昆明再度冷落的历史命运:“昆明的素养原本不深,借抗战而一起的昂扬毕竟随着抗战的结束而归于一仆”,“胜利后,本市重要性顿失,中央机关多东迁,逃难学校亦相继而去,是以市容已大不如前”。在昆明发展史上,民国文人提出的“抗战”决定论或许有待斟酌,而抗战机缘改变了昆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空间地位和文化分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空间上的边缘价值与时间上的抗战分野,共同确定了民国昆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坐标。1944年闻一多大声疾呼“保卫昆明即所以保卫云南,保卫云南即所以保卫大西南,保卫大西南即所以保卫中国”,该现象无论在昆明城市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文化象征意义。
二、城市比较与空间接受:民国文人对昆明的阅读与归化
抗战机缘使昆明迎来了大批外省文人,“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来自不同区域的文人对昆明的审视与品读,伴随着异质文化的相遇和碰撞。文人将边城昆明与燕京古城、江南都会、荆楚名镇、岭南美邑作比较,折射了地域文化元素的交流和融合,反映了战时文人的故园情结和家国之思。
文人跋山涉水进入西南边疆,将滇境最繁华的昆明与他们昔日蛰居或游赏的城市进行对比,完全合乎情理。了解昆明发展史的民国文人看到:这座边城在抗战之前“是座朴素古老的山城,虽有滇越铁路交通、贸易市场,依然无甚进展,现代的建筑除却法国人的几间大旅舍外,简直是凤毛麟角,文化也无甚发达”,抗战给昆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城市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习惯了大都市物质享受的文人难以适应边城生活,战时物价的暴涨又导致了更大的经济压力,造成了部分文人撤离昆明的现象,某些文人竟然“直截了当地回港沪平津去了”。文人对于城市的选择是生活行为上的城市比较。抗战结束之后,昆明文化气氛有了显著变化,文人慨叹昆明文坛的凋零和“新闻窒息”,“住在昆明的人都说,要看新闻还是得读重庆尤其是上海的日报”,这样的城市文化比较,体现了文人对昆明政治环境突变的不满情绪。
除了少数文人认为昆明的风景“比不上江南”,觉得“昆明的翠湖自然及不得杭州西湖的体态明媚”之外,盛赞昆明胜过其他城市的文人比比皆是。有人宣称“昆明山水的清秀,天然风景的优美,国内其他都会很少能比得上”,“昆明可比一美丽的乡下姑娘,她的美全为天然;杭州可比一都市摩登小姐,她的美大半是在修饰上”;有人断定“昆明正是具有杭州同样明媚的山水,却没有杭州的洋化和僧道气的一个城市”;有人认为昆明“山明水秀”、“天然美丽”,“远非半由人工修筑的杭州西湖所能媲美”;有人觉得昆明的滇池胜过无锡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太湖少妆饰,如朴素的村姑,西湖太妖冶,似摩登的贵妇!滇池却像内地的女学生一般的健美!”有人肯定昆明的市容之美,声称“贵阳是远赶不上它的”。老舍高度评价了昆明的自然环境和城市景观,他说:“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
在翻译学界,“异化”和“归化”是两种不同的策略,分别表现为文化上的“求异”和“趋同”思维。“归化”是“将原文独具特征的东西采取‘入乡随俗’的方法融化到目的语中的转换方法”,其依据在于“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对于战乱中被迫辗转于边疆的民国文人而言,在空间感知方面更倾向于“归化”情结。
迁居昆明的文人当中,“在北平住惯了的人,到了昆明,说它像北平。在杭州住久了的人,又说它像杭州。如果再到昆明的新住宅区走走,又觉得它像天津,像南京”。有人评价昆明的正义路极像“上海的南京路,及汉口的江汉路与中山路”;马市口华山路一带是“昆明的文化街”,“可以媲美上海之四马路”。昆明“热闹拥挤的马路,翠湖里的月夜,大观楼的满园春色”,在某些文人看来“与撤退前的武汉有点相似”,而昆明“乱弹茶铺”的娱乐情形又“略同南京夫子庙清唱”。很多来自故都的文人认为昆明酷似北平:在老舍眼中,“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黄裳觉得昆明“颇有北平的风沙之意”;朱自清由昆明的白鹭想起“北平太庙里的‘灰鹤’”;吴宓认为昆明“圆通公园、翠湖”等景致“甚似北平”,“惟有昆明可谓故都北京”;陈寅恪借吟咏翠湖抒发“想京华”的幽情;冰心也肯定“昆明市像北平”,昆明的太阳令她“感觉到故都的温暖”,“昆明生活”在她心目中是“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黄卓秋指出昆明的建筑与景象“颇有北平风味”,因而“有第二故都之雅号”;绿蒂发现昆明与北平在“民风淳厚”与“古朴的市容”这两方面最为相似……在边城昆明与故都北平之间发掘诸多的空间联系和文化共性,表明由中心到边缘的民国文人恢复国家疆土、重构文化谱系的深层意识。并非所有的文人都在边城与国都之间寻找精神脉络,杭州人陈蝶仙发觉昆明与其故乡的风物之绝似。李长之关于昆明风景的点评最为精到:“它正是兼南北之长的。因此,任何游人,都在这里发现和家乡相似的部分。”“想”北平者与“思”故乡者具有文化心理的共通感———身居边疆城市而“归化”于远方的精神家园。
外省人的故园“归化”心态却有可能引起云南本土文人的不适与反感。楚图南讽刺了逃难至云南“喘息”的堕落文人,他们嘲笑边疆文化与生活之落后,却又将享乐之风与腐败习气带到云南:“据说现在的云南有些像北平了,又说有些像南京了,又说有些像苏州,只是缺少了‘吴侬软语’。”民国文人在审视和描述昆明的精神“归化”意识中包含着多重心理因素,而这种“归化”也许会在云南本土内外的文人当中引发理解及评价上的分歧。
三、风景意义与社会伦理:民国文人对昆明风土人情的评价
昆明绝美的风景给文人留下至深记忆,何兆武当年“一来到昆明就感觉天气美好极了”,刘绪贻回顾说“昆明市四季如春”、“风物宜人”。相同的地理景观展现在所有在场的观众面前,惟有心智灵敏者方能神会大自然的暗示,正如1943年的吴宓仰观昆明天空所产生的强烈震撼:“雨后天晴,观天山云之变动,形色万态,美丽难名。……宓既观其静,又观其动,心会神驰,极欣悦!”吴宓能够“于此画中,偶窥宇宙之美”。拥有吴宓那样的心灵感悟力的审美者并不多见,昆明风景对一般观赏者而言,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义来。
将昆明风景的美学价值与城市社会的道德缺陷作出尖锐对比者,莫过于沈从文。他犀利地指出:外省人来到云南不久,便不能单纯地欣赏云南的云彩之美,而天空中的美丽云朵其实能够给予世人“一种无言之教”,各类庸俗市民忙于谋求实际利益,“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沈从文经常在信件中“详细介绍昆明和呈贡特有的景物”,却屡屡抨击后方城市的不良风气,他宣称:“到云南后便接近一个新的现实社会。这社会特点之一,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地方本来的厚重朴质,虽还保留在多数有教养的家庭中,随物质活动来的时髦,却装点到社会表面。”沈从文的批评并非针对云南本地人民,而是斥责了那些战时逃难至昆明、追求城市享乐的外省人。在《怀昆明》中,沈从文表达了他对云南人的崇敬:“云南人性情坦白直爽”,“重友情,好学问”,“谦虚从善以图适应时代”。他真切希望昆明这座秀美的城市能够迎来真正的精英豪杰,当田汉来到昆明时,沈从文认为“昆明的阳光和空气那么好”,可以“让田汉先生在明朗阳光和清新空气中,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养”。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民国文人对于边城空间的和谐之美充满着强烈的文化期待。
在抗战激流中,外省人蜂拥而至,给边城社会增添了驳杂性。在文人眼里,昆明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钱的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都市”,除了本地人之外,还聚集了“广东人,福建人,四川人,北方人”,夹杂着“海外的华侨”、“越南人和法国人”、“奸商和官僚”、“谣言的散发者”以及“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人群。对于纷纷攘攘的昆明社会,文人的道德评价是紊乱的:一方面盛赞“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称昆明人既“笃厚”又“有一种潜藏的深厚的进取的心在准备着”,褒扬昆明人“非常进取,充满了朝气”;另一方面又将昆明视为“后方冒险家的乐园”,认为昆明由中国的“堪察加”变成了“暴发户”的乐园,城里充斥着“漆黑的夜游者”、“初解风情的闺秀”、“粗暴的商人和汽车夫”、“乡下来的姑娘”、“大学生”和“妓女”。文人对于战时昆明社会的伦理批评暴露了边疆城市在外力急遽推动下的文化突变及步伐缭乱。多元化的城市主体在特殊语境中的偶然相聚,生成戏剧化的城市文化场景,有的文人嘲笑“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半开化的倮族土人”在街头并行的现象构成了战时的昆明文化“奇观”,撇开了边城的发展实际和历史遭遇的道德判断,其实包含着非公正的文化心理。
若从精神维度观照昆明的风土人情,文人对于边城另有评价。艾芜看到群峰围绕的昆明“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暂住昆明的老舍“老觉得静秀可喜”,林徽因欣赏“昆明永远那样美”的同时又感到“寂静”和“冷清”,凤子寄居昆明期间“日子过得平静然而寂寞”,黄裳在春城“觉得异常的空虚与平静”,李长之对昆明过于恬静、悠闲的生活环境似乎有些忧虑:“天气诚然不错,但是偏于太温和的了,总觉得昏昏的,懒洋洋的,清爽的时候不过早上和夜里……是不是在这里住下去,将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施蛰存描述昆明附近的山城居民“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他告诫外省人说,“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象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一个喧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他又“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冯至从昆明市区迁居杨家山的林场茅屋伊始,觉得“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话,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后来却被抗战的呐喊声从田园环境中唤醒,他逐渐和林场茅屋“疏远”,城市对他“有了更多的吸引力”。从静穆安宁的山林到喧嚣紧张的都市,冯至审美趣味的变化在抗战时代的文人当中是典型现象。不少云南本土文人也希冀克服沉寂闭塞的山国心理,倡导刚健狂野的边疆人文个性。楚图南宣扬“伸出拳头,向黑暗的统治猛烈的进攻”的“云南精神”,彭桂萼认为“高山深谷的边疆,有他磅礴粗壮的气魄;荒莽原始的人群,有他生动雄奇的力量”,期待吹响“奋亢的军笳与悲壮的号角”。激荡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全国文人,以及他们对于边疆风土人情的精神体验与美学评价。
四、结语
边城的地缘属性十分不利于昆明形象的历史传播,这种情形直到民国时期、抗战以前仍未得以根本改观。1938年,李长之试图纠正人们对于昆明形象的种种“误读”:“一般人没到过昆明的,总以为还是‘五月渡泸’时的光景,以为还是蛮荒之地。实则大大不然。但照外国人的游记上说却又以为此地是象牙古玩等等珍奇东西的出产地,说来便颇神秘了,这依然是言过其实。简单明了地说,这地方有一点近代化,大体上乃是和内地的几个省会并没有太大的分别而已。”抗战兴起之后,昆明地位的骤然提升带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外来文化元素的强行注入既推动了昆明社会的现代转型、促进了边城文化的繁荣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边城文化发展的内质失衡与多元混杂。
漂流至边疆的民国文人大多以“归化”故园的目光打量边城昆明,在中华文化的版图上进一步沟通了边城与内地的联系,却也或多或少地暴露了中国文人据“中心”测“边缘”的传统文化心理。在战争情感作用下,文人更倾向于激越震撼型的审美体验,这在抗敌救国的时代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始终以此种审美心态检阅边城的风土人情,似乎不够开阔与深刻。
当代昆明正迎来“桥头堡”建设的战略机遇,边城的开放品格、文化特质、人文魅力都已被确认,这座西南边陲的大都市必将在中国发展史上不断产生新的影响、获得新的定位!
本文作者:高兴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