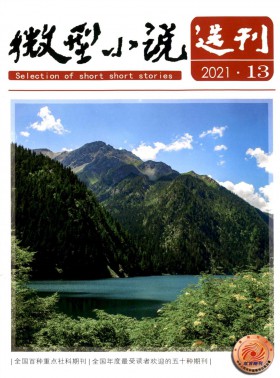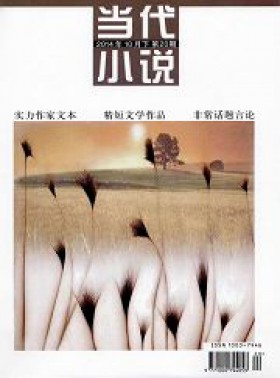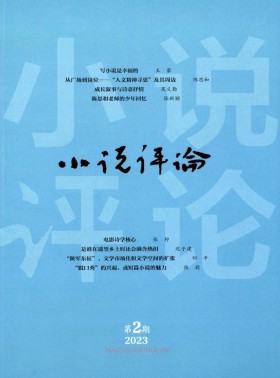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元小说的兴起及其进展,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1.关于“元小说” “元小说”一词最先是在1970年由美国著名的元小说作家兼批评家威廉•加斯(William Gass)在《小说与生活中的人物》一文中提出来的,用来描述那些关于小说的小说。麦卡弗里(Larry McCafferry)将元小说定义扩展为“关于虚构的虚构(fictions-about-fictions)”,并指出这种“关于虚构的虚构”不应只局限于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介入,也不应仅被理解为“关于如何写一本书的书(book-about-the-writing-of-a-book)”,元小说的内涵还必须涵盖“那些关注各类虚构体系之创造的作品”(McCafferry1982:6)。因此,麦卡弗里将元小说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的元小说是“那种在创作过程中直接研究自身建构,或者评论与反思前人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的作品”(同上:16)。广义的元小说则指“那些力图研究所有虚构体系的运作方式、方法论、其感染力的来源以及被教条化之后所带来的危险的作品”(同上:17)。帕特丽夏•沃将元小说定义为“赋予文学创作的一个术语。这种文学创作自省地、系统地将注意力引向自身作为人工制品的地位,以便质询虚构(fiction)和现实(reality)之间的关系。在对文学虚构自身的构建方法提出批评的同时,这种写作还研究了文学虚构(fiction)的基本结构,探讨了文学虚构性文本之外的世界的虚构性”(Waugh1984:2-3)。 元小说在表现手法和叙述策略上呈现多样化,仅沃就列举了作者介入(也称短路)、矛盾开放、戏仿(也称反讽,或者滑稽模仿)、拼贴、任意时空、文类合并、文本中的文本、过度、排列等近20种。在同一个元小说文本中,可能使用其中的一种,也可能混合使用多种手法和策略。 单纯从写作实践的角度看,元小说早已有之。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早在17世纪初即已面世,该书戏仿骑士小说,对中世纪骑士制度给予深刻的讽刺。18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 1713~1768)的《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也具有典型的元小说特征。作者不断介入自己的作品,对自己的写作发表议论,并与读者直接交流。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元小说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一股潮流,成了后现代主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小说形态。 2.元小说在中国兴盛一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在西方,元小说的产生是政治、经济、科学和哲学发展的结果,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中的一种写作方式,因而几乎当代所有实验性创作都运用了明显的元小说策略。在中国,元小说的兴起也是有其经济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逐步和国际接轨,现代化大都市迅速崛起,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普遍,为元小说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土壤。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教化功能逐渐减弱,作家获得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写作变成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众多标新立异、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作品纷纷面世。同时,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学和纯文学日益边缘化,这些都促使了雅俗共赏、以解构宏大叙事为目的后现代文学在中国超前出现。 其次,转型时期的中国对世界充满好奇,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西方文学或者文化理论思潮以及博尔赫斯、巴斯、巴塞尔姆、库弗等人的重要作品被本土研究者迅速译介到中国。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批评家哈桑、詹明信、佛克马、德里达等也纷纷应邀来华讲学,宣扬自己的理念。在这种日益活跃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密切关注着这些崭新的文化现象和理念,并迅速付诸行动,对西方文本进行借鉴和模仿,从而促进了以元小说为主流的中国后现代主义文本的迅速出现。 事实上,元小说实践在中国文学中也并非全新的事物。元小说策略的运用早在几百年前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就初露端倪。中国古典小说作家借说书人的口吻经常使用“却说”、“且说”、“闲言少述”、“不必烦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表述,这恰是在提醒读者“我正在讲一个故事”,体现了元小说策略的运用。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中国式元小说常常被冠以实验小说、新潮小说、类后现代小说之名,初期的元小说作家通常被赋予“先锋派”(avant-garde)的称谓。中国当代文坛的“先锋派”与西方文化中的先锋派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前者是指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出现在中国文坛的一批具有鲜明创新意识和革新精神的作家,包括马原、洪峰、格非、余华、孙甘露、苏童等。中国先锋派文学既具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种种特征,又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与之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注重内容和主题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流派不同,先锋派作家以求新求异为创作目标,他们不再重视写什么,而是注重怎么写。在先锋文学中,读者看到的更多的是表现形式的创新,而非创作主题的深化。正如马原(2003:19)所说,“我不知道中国先锋小说是不是一个流派。我想做的就是在小说上提供一点与众不同、新鲜的东西”。“先锋派”这一称谓直指作家的先锋意识。 3.先锋派小说中的元小说因素 马原是中国当代文坛公认的元小说作家,他的《虚构》、《冈底斯的诱惑》等可算典型的元小说,在上世纪追求创新与探索的八十年代,曾经引起轰动,为中国文坛带来不小的冲击。马原可谓元小说创作的急先锋,其作品明显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小说创作呈现出神秘的地域性。他所运用的独特的元小说叙事策略,让其作品产生出一种“陌生化”效应,人称“马原式叙事圈套”。《冈底斯的诱惑》就运用拼贴、碎片以及非线性叙述等元小说策略。该小说主要讲述了三个故事:猎熊人穷布探寻“野人”的故事;陆高和姚亮等人去看天葬的故事;顿珠、顿月和尼姆的婚姻爱情故事。这三个故事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中,除了都在西藏之外,再无关联,作者却将三个故事交错进行叙述,而且每个故事都没有明确的结尾。这些故事不再是传统的线性叙述,而是展示了相异时空中各个不同的点。故事没有完整的前因后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犹如被中途截取的一个个孤独的横切面。正如马原所说,“生活并不是个逻辑过程。那么艺术为什么非得呈现出规矩的连续性呢?”(许振强、马原1985:90)马原没有用自己作家的想象把这三个故事补充完整,而是让其以这种拼贴和破碎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使熟悉了传统叙事方式的读者对文本产生一种疏离感和陌生感,从而将读者引入“马原式叙事圈套”。马原(同上:90)说过,“生活现象不是数,不是简单的数的累积加减。生活现象不管它多么纷繁各异,都有着比表象远为丰富的含义层次,都可以提供重复思考的可能性”。#p#分页标题#e# 在《虚构》一文中,马原以虚实并置的手法,描述了“我”在麻风村七天的经历。讲述了“我”如何偶遇一位混迹麻风村三十多年装聋作哑的神秘老人的故事,以及“我”和那里唯一会讲汉话的女麻风病人的萍水情缘。小说一开头就强调“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马原等2009:1),作者马原就是小说中的“我”,而且“我为了杜撰这个故事,把脑袋掖在腰里钻了七天玛曲村”(同上:2),即麻风村。作者言之凿凿,让读者以为,在接下来的大段篇幅中“我”与神秘老人的偶遇以及与女麻风病人的情缘,都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然而临近故事结尾,作者专门用一个章节来颠覆他之前和之后对故事的叙述。他告诉读者,“我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杜撰的。……我不希望那些认真的人看了故事,就说我与麻风病患者有染,把我当成妖魔鬼怪。我更怕的是所有公共场所对我关闭,甚至因此把我送到一个类似玛曲村的地方隔离起来”(同上:36)。马原曾在《现实的虚构》中坦言,他的《虚构》既是现实又是幻觉,并且人为地把故事在时间上抹掉了,让它“在时间上不存在”(马原2001:73)。“虚构”这一题目本身就传达了该故事的创作主旨,反映了马原对于传统文学创作手法的质疑和颠覆。如果创作陈规是渔网,马原的作品确实象一条条破网之鱼。 现实主义作家愿意做隐身的上帝,而元小说作家却更愿直接现身,介入自己的作品。为了充分暴露小说的虚构性,马原不时在文本中扮演作者和批评家的双重角色,仿佛和读者面对面一般,谈论着自己作品的叙述框架和情节构思。在《虚构》一文中,马原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时插入一些关于自己如何杜撰这个故事的语句。如“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其实与别的作家没有本质不同,我也需要像别的作家一样去观察点什么,然后借助这些观察结果去杜撰。天马行空,前提总得有马有天空”(马原等2009:2)。在这个故事里,作者一边叙述故事,一边讲述自己杜撰故事的过程,探讨小说叙述理论和叙述技巧,提醒读者看到故事的虚构性。在《冈底斯的诱惑》临近结尾处,马原这样写道: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讲得差不多了,但是显然会有读者提出一些技术技巧方面的问题,我们下面设法解决一下。a.关于结构。这是三个单独成立的故事,其中很少内在联系。这是个纯粹技术性问题,我们下面设法解决一下。b.关于线索。顿月截止于第一部分,后来就莫名其妙断线,没戏了,他到底为什么没给尼姆写信,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后面的情节当中?又一个技术问题,一并解决吧。c.遗留问题。设想一下:顿月回来了,兄弟之间,顿月与嫂子尼姆之间可能发生什么?三个人物的动机如何解释?(马原1985:65) 接着作者从问题c入手,安排顿月入伍后不久就牺牲了,由此轻松地解决了问题c和b。尽管问题a的具体解决方案作者没有提及,但是他已经给予读者暗示———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解决这样一个纯技术性问题,让他的故事在喜爱传统文本的阅读者看来合情合理。 戏仿(parody)是对前文本和文学成规的颠覆性模仿,它的目的不是完全否定前文本,而是在模仿中对前文本进行嘲讽和改造,故意打破那些已经陈旧的形式和规范。戏仿既包括对传统小说主题的颠覆,也包括对传统文类的颠覆。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分别对中国某些传统或通俗文类进行了戏仿。《河边的错误》是对侦探小说的戏仿,它具有侦探小说的基本元素,有凶杀案的发生,有公安部门的侦破、走访、调查、取证、推理,然而案件最终水落石出时,却发现是一个毫无作案动机的疯子所为,而且公安部门对这个疯子无可奈何,没有实施逮捕,致使疯子后来又杀死两人。最后,警员马哲忍无可忍,不得不以牺牲个人前途为代价击毙疯子,随后自己被关进精神病院。整个故事就是一环又一环的错误、一个又一个荒谬事件的连接,与传统侦探小说伸张正义,惩处罪犯,还善良者以清白的主题截然不同。《古典爱情》是对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以及聊斋故事的双重戏仿。故事中一次次赴京赶考的读书人,年华虚度,垂垂老矣,却始终没有金榜题名。闺阁伤春的富家小姐尽管与读书人私定终身,却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饥荒年间,小姐被卖为“菜人”,惨遭屠杀之后,她的魂魄与书生梦中幽会,然而却因书生急于一探究竟,过早地挖开了小姐的坟墓,令小姐最终未能重返人间。故事中背离传统的情节、无望的爱情以及缠结于爱情中的残酷的、血淋淋的描写,与温情脉脉、皆大欢喜的传统故事形成鲜明对比,让读者在阅读的失落中,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和聊斋故事不过是一系列程式化的虚构而已。《鲜血梅花》是对深深影响了中国大众的一种通俗文类———武侠小说的戏仿。有人将武侠小说的精神概括为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但是《鲜血梅花》将这种精神完全颠覆了。小说主人公、武林大侠的儿子阮海阔,并未继承父亲的秉性和武功,可是在十五岁那年却必须踏上寻找杀父仇人的旅程。一路上,他手持梅花宝剑,却一次也没用过;尽管他浪迹天涯,却任由岁月磨灭了记忆,几乎忘记该寻找何人;当他最终知道杀父仇人是谁时,却发现仇人已死,这时的阮海阔既没有复仇的快感,也没有遗憾。其实,他的整个旅程就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浪游,时间和生命在这无意义的行为中渐渐消逝。通过阅读,读者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漫无边际的虚无,生活、生命,甚至人类的存在都是一种虚无,生命的意义仅仅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人为虚构,人类不过是生活在一个被虚构出来的、被人为赋予意义的世界中。 西方后现代文学中有一类元小说被称为“历史书写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这类小说具有历史小说和元小说的某些特征,但又与之不同。它具有元小说强烈的自我意识,却没有完全沉溺于语言游戏;它以某些史实和历史人物为题材,同时又对自身的文本虚构性毫不隐瞒。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历史书写元小说“在保持着形式上鲜明的自我表现的同时,又涉及明确的历史语境,并以此来质疑了解历史的可能性”(Hutcheon1988:106)。它不仅是彻底的自我关照的艺术,而且还根植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之中。历史学家总是从某一个角度或者怀着某种目的,来选取历史文献,而历史书写元小说正是“运用了脚注等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些准文本惯例指出这一事实,从而瓦解了历史记载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同上:123)。在近代学科细分之前,西方的历史学和文学都属于文学与创作的范畴,同样,中国历来也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许多史学大家同时被公认为杰出的创作者。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历史记录无法重现历史真实、历史只是胜利者书写的一种权利话语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是很容易接受的。在中国先锋派文学中,格非和余华等人的部分作品就具有“历史书写元小说”的特征。#p#分页标题#e# 余华的《一九八六年》中,主人公是一位痴迷于古代刑罚的历史教师。在世人眼中他是个疯子,他将墨、劓、袋、宫等古代刑罚一一施用于自己。作者血淋淋的直白描写,让人不忍卒读。在余华眼中,历史教师就是历史的化身。历史不再是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而是充斥着被权利话语巧妙抹杀的暴力和血腥。格非的《迷舟》描写了北伐军与孙传芳军阀决战之前七天,发生在孙传芳部萧旅长身上的故事。萧的父亲意外摔死,萧回到离驻地不远的老家奔丧,偶遇表舅之女杏,旧情萌动并终于私通。杏精明的兽医丈夫发现杏和萧的私情,将杏阉掉送回娘家榆关,而驻守榆关的恰是萧的哥哥所率领的北伐军部队。萧悄悄前往榆关探望杏,回来后却被自己充当上级密探的警卫员杀死。警卫员不谙世事,没有看出萧和杏的私情,认为萧是去榆关给北伐军送信。故事中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纠结在一起,而且都充满了偶然性。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历史进程都如同漂浮在大海上的“迷舟”一般,没有明晰的规律可循。所以,在格非看来,历史就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根据自己的需要将一部分偶然事件条理化后所做的失真的记录,历史记录不可能重现历史现实。格非的另一部作品《风琴》对权利话语所颂扬的悲壮英勇的抗日战争进行了重述。抗日英雄和汉奸都被描绘成芸芸众生,壮怀激烈的抗日战争成了一场闹剧。读者看到的是权利话语掩盖下的历史的另一面。 4.元小说创作中的问题 以及先锋派的创作转向元小说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以及鲜明的创新风格,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不小的冲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小说叙事观念的变化,也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主流文学的接轨。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元小说的弊端逐渐显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已经不再。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国的元小说作家过多地偏重于模仿西方表现手法,过于关注艺术形式,而忽视了对主题的探索。许多作品中充斥着暴力、欲望和虚无,而缺少人文关怀和对生活的沉淀与升华。这就造成元小说创作更多的是一种个性化的写作,甚至被许多人看成是纯粹的语言游戏,难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有学者认为,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患上了一系列病症,例如,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只有血腥暴力而没有爱和怜悯,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等等。这些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对中国元小说的批评。加上中国商业化大潮和现代影像文化的影响,元小说创作不可避免地被逐渐边缘化,先锋派文学渐趋衰落。 先锋派的衰落促使余华等一些先锋作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反思和转向。文学的思想性重新受到重视,文学创作向古典情趣回归。正如格非所说:“中国作家经过这么多年‘怎么写’的训练之后,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写什么’的问题了”(转引自李敬泽2005:10)。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体现了对“写什么”的深刻思考。这些作品已经不像《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等充斥着对历史和现实之残酷性、荒谬性的揭露,而是深入地审视了生命对苦难的承受以及平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余华(2010:3)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作为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余华等人创作风格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先锋文学的转向。 5.结语 从总体上看,元小说在中国的发展与西方文学潮流的发展是大致吻合的。与西方元小说的发展轨迹类似,中国的先锋派渐渐淡出了中心舞台,元小说这种写作策略在被作家们操练过一番之后,逐渐回归到合理的运用范畴。但是,先锋作家的创新精神和他们的元小说实验将永远都是当代中国文学宝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