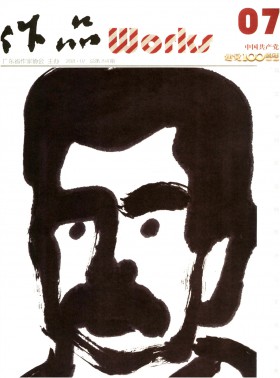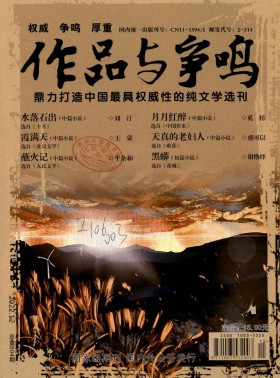严歌苓,新移民作家,编剧,被认为是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是海外华文文学中一个“了不得的异数”。[1]严歌苓目前在小说创作上十分活跃,是多产而高质的少数作家之一。其作品在国内外重要的文学评奖中屡获大奖,引起轰动,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和首肯。著名评论家如饶?子、陈思和、陈瑞林等都给予严歌苓很高的评价:如饶?子指出,“严歌苓是近十年来北美华文创作成就最为显著的作家,也是北美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她的小说闪烁着‘新移民文学’独有的精神特质”。[2]陈思和认为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作家贡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独创的艺术形象”[3]。美华评论家陈瑞琳则感叹“:扫描北美华文文坛,不能不关注严歌苓,她是一种奇异的现象。”[4]“无论她的笔端如何变幻,作品总是以窥探人性之深、文字历练之成熟而受到读者青睐,屡在台湾、香港及北美文坛获奖,从而成为海外新移民作家一面耀眼的旗帜。”[5]等等。 总体看来,在目前关于严歌苓的研究文献中,对单篇作品进行解读性评析的占了大多数,而相关硕士论文也大部分侧重于研究其出国后的作品,相当一部分分别针对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文化身份、人性等进行研究,更多的则是针对严歌苓独特的叙述方式展开论述。本文无意于再仅就某一方面继续已有论述,而只想从某种特定角度尝试整体上把握严歌苓作品风格之所以“异数”的核心性原因。 文艺学理论告诉我们:风格主要是由创作个性决定的,而创作个性往往又与那些作家一开始便遭际,并毕生反复探究的人生问题密切相关。这类问题原本是作家自行发觉的,然而运用许多观念道理却很难解释,故而它们一直缠绕着作家的灵魂。作家只能一次次用不同的人物或故事、场景“回应”这种问题缠绕。因此无数批评家前辈都一再指导后学们,足以将整部作品从形式到内容贯穿起来形成整体的,唯有人物形象(意象)。根据这一逻辑,笔者通过大量阅读,发现了贯通于严歌苓各个时期众多作品的女性“意象群”系列。 何谓意象群?要从意象说起,意象是现代文学批评中最常见、也最复杂的术语之一,最早出现在诗歌中。通常是指“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和回忆通过审美思维创造出来的融汇了主体意趣的形象”。[6]而对于叙事性文学而言,这种既能渗透作品主旨(思想、情感)又能连结并贯通作品一系列事件动作和情境场面(情节、场景)的“意象”,唯有人物形象而已。至于“意象群”这一术语是随着当代批评的新发展(如比较文学的类型学、主题学研究,神话原型批评的“原型”观念,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角色”概念等等)而在小说、戏剧、影视等文本分析中出现的。通常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中(或同一类型、同一流派、同一风格、同一时期不同作家笔下)的类似人物形象所构成的“角色”系列。例如鲁迅多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狂人”系列,“看客”系列,“伪善的吃人者”系列等等。其二是指由上述不同“角色”系列共同组合的某种关系结构,这种关系结构往往在同一作家不同作品或同一文化历史背景下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呈现。例如鲁迅作品中由“吃人者”、“被吃者”和“帮闲看客”构成的关系结构等等。显然,这种“意象群”研究可以打通不同作品,透过类型、模式发现整体的表征或结构性寓言。随着文学的外部批评和内部研究再度汇合交融的趋势不断高涨,这种研究方式也日渐流行。 本文所说的“意象群”主要是指在严歌苓小说中呈现类型性的女性形象的系列或系列结构。关注女性形象可以说是女性作家们的共同之处,然而严歌苓更加关注“边缘的女性”———这些女性游走于经济、种族和文化的边缘,在社会、人群乃至文化的夹缝中生活。笔者在研读严歌苓的小说的过程中,发现其几十年的创作始终围绕着三种类型的女性形象展开:追求社会理想、竭力成为社会认可的楷模却被异化从而丢失个体生命价值的“圣女”类型形象;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和自由,主动逃离“专制”的“叛女”类型形象;受苦受难却不为社会政治等外力所动、在原始混沌状态下本真率直、包容一切、滋养万物的“地母”类型形象。这三种类型又呈现出彼此对峙、互补或相互转化的三角形“意象群”关系(见下图),这种关系不是偶然形成的,在严歌苓小说中它们反复演变,呈现出规律性和内在机理。因此本篇论文很自然地把重心放在追寻小说中这种关系与严歌苓的生活轨迹或文化身份演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上来。 这三类形象在严歌苓每个时期小说中表现、评价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一)女性意象群演变 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了“”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国文坛兴起了“人道主义热”,此时期的严歌苓从成都军区文工团转业到北京任创作员,军队里的理想主义教育,加上“人的回归”的启蒙观念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共同影响,部队中女性的解放和自由成为她这一时期的关注对象。 最初作家是为追求“圣女”的理想而塑造一批英雄或社会楷模形象的,如《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笔力遒劲地展现了女兵陶小童为追求英雄理想而使正常自然的人性被扭曲的全过程。在《雌性的草地》中三类女性形象第一次呈现着“群”的关系(如沈红霞对理想的坚贞和坚持,小点儿最初的邪与叛逆,柯丹原始自然的母性情怀)。当然此时严歌苓的创作还主要是通过小点儿与柯丹凸显沈红霞的追逐“圣化”过程。虽然《雌性的草地》延续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的主题方向,全力刻画极端的“神圣”“理想或信仰”同个体自然本能欲望(甚至是“邪恶”人欲)之间的张力状况,但这部小说毕竟在严歌苓的创作中开了先河———日后创作中逐渐占据重心地位的“地母”形象第一次出现了,小说中人物间的冲突/张力格局也是第一次呈现为三重(或三角)关系模态。#p#分页标题#e# 这些追求“圣化”的女性无一例外地在被异化了的理想中失去了个体生命价值,走向了人生的悲剧。在发觉“圣女”异化中否定“圣女”的追求,渴望个体自我、自由的严歌苓也不例外地想要抗拒、挣脱,于是不自觉地选择了叛离,一系列叛离专制追求自由的女性形象诞生了。来到“自由”之地(美国)的女性在开始呼吸自由空气的时候,就遇上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语言不通,文化隔膜,随之而来的是寂寞和撕裂疼痛。作家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文化上的“不适”,其实隐含的不仅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乃至冲突,而是更为深刻的人化与异化的根本矛盾。于是一系列移民题材小说在严歌苓的笔下流淌出来。如安德烈对“我”的好,不过是把“我”看成竹篮里顺水漂流到幸运之岸的孩子需要呵护而已(《无出路咖啡馆》);东方和西方一样存在着“恩”“义”的悖论(《人寰》);东方妓女的被拯救,不过是西方男子为实现骑士精神的救赎举动(《扶桑》)。严歌苓在对“叛女”的思考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女性受难与宽容的内涵。渴望去国离家移居海外的女性虽然未在异化中失去个体生命价值,却也没有得到自由,反而在伤痕累累中发现了西方的自由“悖论”。严歌苓不得不向第三个维度思索。 在远离尘嚣的非洲,在贫苦却乐观向上的非洲人身上,严歌苓受到了新的启发。她开始探索既能实现着生命价值,又能免受社会异化的自然、自由的女性形象,于是那种没有“觉悟”、缺乏恐惧、不怕生人、死心眼却又善良宽容的自然“地母”———葡萄出现了(《第九个寡妇》)。在自然“地母”形象基础之上,严歌苓进而书写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地母”形象,这种“地母”形象身上既有未异化的“圣女”因素,也有渴望自由的“叛女”因素,如痴女田苏菲(《一个女人的史诗》)、“凑合”的小环和“不凑合”的多鹤(《小姨多鹤》)、及以毁掉爱情来实现爱情的May(《寄居者》),至此,三“女”结合的形象,表征着严歌苓对于多元寄居时代女性人生意义的追求与归属。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以最令人震撼的“叛女”方式去承受苦难做出牺牲,来拯救他人的“地母”女性正是最伟大、最可敬可爱的“圣女”。 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也就是本文强调的三角形“意象群”———呈现着对比和承接的结构关系,她们之间呈现出内在有机统合的逻辑。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种逻辑(关系)的演变与严歌苓各个时期不同身份下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虽然“文化身份”问题是在严歌苓出国之后逐渐显现出来的,可实际上,这个“身份”问题始终存在于作家全部人生中,也蕴含于其作品女性人物的“意象群”系列的逻辑展开中。“身份”一词不仅指“文化”“种族”的一个维度,而且也指各种召唤人们“认同”的维度,如“政治身份”、“时代身份”、“社会群体身份”、“民族(种族)身份”“、地域身份”等等。严歌苓早期作品中女性人物苦苦追求或拼命挣脱的“人生境界”其实也是一种对于“身份”的“认同”或“疏离”。(如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反复刻画部队生活里的“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就是对于一种曾经崇拜追求的“身份”的反思)。严歌苓身份的每一次转变都来自于她生活领域的转变,而生活体验与身份的不同又使得严歌苓对女性在追求个体生命自由的见解不断变化、深化。 (二)与众不同的“身份书写” 移民们从出生国移居至另一个国家,到另一种文化体系当中生活,面临的不仅仅是放弃国内既有的生活和地位到国外去重新开始的艰辛,更面临着回答“我是谁,我与谁认同”的文化身份问题,很容易发生身份认同危机。海外华人作家们的创作普遍呈现着从各个侧面向读者们展示这种文化身份焦虑: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留美留学生(於梨华、白先勇等人)主观上无法认同西方文化,却又因政治原因无法归属于中华文化,客观上又遭到美国文化社会对他们的排斥,他们的创作中呈现出“无根”的彷徨。而80、90年代出国的移民作家们在经历了“”后主动接纳西方文化,去国离乡之后更有着一种在异国打拼天下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对移民的接受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观,移民们比较容易找到文化身份认同。对待中华文化,移民作家们虽然不至于全盘否定,却可以以一种冷静的眼光去审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移民作家们的身份焦虑始终无法摆脱,虽然这种焦虑比之6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们已经缓和了很多。许多移民作家的创作,如张翎在《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等小说中展现的温州女子在温州和异域多伦多生活的艰辛与苦闷;无论是自尊自强的望月,还是羸弱却孤傲的蕙宁,抑或是自尊好强的涓涓,她们都在寻找———寻找家园,寻找归属,寻找慰藉。而她们的寻找模式也总是相同:以希望开始,以失望终结,最后总是在回归母体文化中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又如虹影的小说《饥饿的女儿》中六六对“我是谁”的身份追寻,即使最后自己碰撞得满身是伤,却始终不放弃追问。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身份认同的焦虑,然而不管是张翎笔下的温州小女子,还是虹影笔下的女儿,她们都在某一类型的“小我”之中展示身份问题。严歌苓的独特在于她跳出了某一类型女性的身份追寻,而融入到“大我”之中思索东西方文化夹缝中女性的人生意义:女性如何实现身份的主体性,实现女性的自由解放。 在多种文化交织的背景下,严歌苓早已不能简单地归属自己的身份,中国、美国、欧洲、非洲等地的旅居生活也使得严歌苓的身份认同呈现多元化,如她强调的“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寄居者的心态依然”。[7]在小说《寄居者》中她更强调了移民的多重身份问题。身份随着地域不断变化着,在美国受白人歧视的有色人种,在上海却因持有美国护照而备受尊敬。而在上海是难民的犹太人在美国的地位却比中国人高。“我”的祖辈父辈甚至“我”在美国唐人街备受歧视,然而回到上海,因有美国护照“,我”有着别人没有的优越感。“我”甚至指着父亲的小夫人凯瑟琳骂她是典型的上海小女人,却不能意识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上海小女人。严歌苓不仅仅是发现了身份归属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她还发现了身份的悖论———纵观严歌苓迄今为止的全部创作,我们不能不深切感受到作家一双敏锐犀利的眼睛和一颗苦苦寻觅又跳动不安的心。她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发问:我是谁?该成为怎样的人?为什么当我(或环境要求我)成为某种人的时候,却常常发现“她”已滑到了反面?那么我应当如何重新找到“她”,恢复“她”或保持“她”?甚至在严歌苓创作这个由“圣女”“叛女”和“地母”构成的“意象群”系列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人们为什么总要确立或重构亦即“书写”自己的“身份”?#p#分页标题#e# 严歌苓一直在追寻着身份的主体性,对主体始终处在不断地反思当中。她的创作总是企图在女性的身份选择中树立一个不被异化的尺度,为女性实现其主体性寻找一条出路。12岁就参军的她首先认同部队里的政治文化身份,追求理想主义的英雄女性———“圣女”。在这种身份追求中,严歌苓敏锐地发现追寻这种政治身份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被异化、被扭曲。认同这种身份的陶小童、沈红霞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失去了个体主体性,成为了被异化的“圣女”。本来,追求理想、为理想献身这是非常伟大而高尚的行为,然而当我们只顾强调献身,而忽视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价值的时候,这种理想已经被异化了。面对被异化的身份,严歌苓不是直接地否定,而是以启蒙者的身份去反思、批判。这样的严歌苓自然而然地想要挣脱或叛离被“异化”的理想及公认的道德价值,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 “叛女”在异国的生活中同样再度面临着身份认同问题,严歌苓很快敏锐地意识到:认同一种文化并不意味着获得这种文化身份。获得某种所谓的“官方认可”或“公众认可”的文化身份,也不见得获取这种文化中积淀的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观念总是打出某种“人性”真善美的招牌,实际却偷运着压抑、奴役、扭曲人的主体性(人的批判精神,爱与同情,创造与发现等)的“伪真”、“伪善”、“伪美”。在《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很难改变房东夫妇和安德烈对“我”救赎的观念。“我”也很难接受他们对我“太多怜悯的爱”,甚至无法让他们相信“我”不需要怜悯。“我”在这种怜悯中失去了身份认同感。严歌苓关于文化身份悖论的思考也体现在扶桑的挣扎中。扶桑在中国贞洁礼教的婚姻中被压抑了自我,失去了身份的主体性,于是她叛离了东方妇女传统道德。然而当她试图归属于克里斯的文化身份时,却失去了东方文化土壤支撑,她失去了神秘,失去了吸引克里斯的魅力。并且,克里斯所属的文化群体不认可扶桑的文化身份———她只是一个可怜、污秽且需要被拯救的妓女。因此,扶桑在追寻身份认同的道路上可谓是困难重重。 追寻身份是为了获得主体性,实现主体解放。为了摆脱身份随时可能被“异化”,严歌苓在“圣女”与“叛女”的基础上,向更广、更深邃的文化空间和历史维度中追寻,她找到了卑微、纯朴、历尽苦难却以无疆大爱回报他人与世界的“地母”———拥有主体性的葡萄是最自由的“地母”。严歌苓的独特还在于她并不因此而停下脚步,她不断警惕葡萄随时可能存在的异化,并对“地母”形象不断丰富和发展。她塑造了更多在社会生活的磨砺下形成的“地母”———田苏菲、多鹤、小环,她们不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在被“异化”了的人群中坚持自我,坚守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在不断地反思中,严歌苓以更广的视野创造了“圣女”、“叛女”、“地母”三女合一的May(《寄居者》)———这个既要逐“圣”又能承受苦难做出牺牲来拯救他人的“地母”,以一种“叛女”姿态实现自我的主体性,不被社会环境所异化。 这些女性形象,这种文化身份反思是严歌苓小说创作的一大贡献。从这种角度和层面上讲,应当承认严歌苓的“身份书写”在整个“新移民作家”文学中,在当代海外华文文学中都具有某种代表性与超前性,而严歌苓对文化身份的不断反思也使她成为华文文学中一面独特的旗帜。